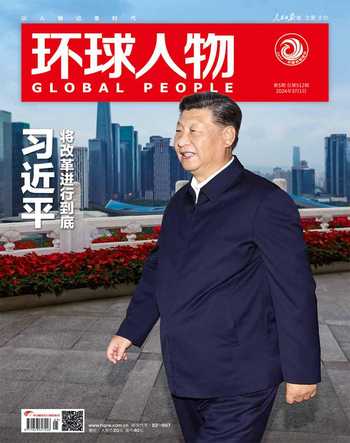创作之根在民间
余驰疆

许江
站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办公楼高层向下俯望,几乎能将整座校园收入眼底。一面是郁郁葱葱、红绿相间的象山,宋河绕山流淌,流经校园流向钱塘;另一面是大名鼎鼎的校园建筑群,灰瓦层叠,飞檐如浪,设计者便是中国首位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现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然而20年前,这片刚刚落成的校区备受争议,一度被称为“杭州最错误的建筑”。作为决策者和总统筹,时任中国美院院长许江办全国研讨会,一次次亲自为来宾做导览,许多人都以为他是导游。后来,王澍拿下建筑界最高奖,象山校区频频登上“最美校园”榜首,人们才对许江当年力排众议的决定刮目相看。
对许江而言,这片校区意义深远。当《环球人物》记者问他:“身为中国美院历史上任职最久的院长,你最自豪的三件事是什么?”他把象山校区放在了第一个——另外两个则是“构建以东方学为核心的学科链”和“进一步锻造中国美院深厚的人文学风”。
象山校区也是许江心中“大学望境”的象征,是“空间建造与精神塑造共构”的典范。他指着玻璃外的景色,与记者回忆起20年前在此眺望的心境:“那时校园周围都还没有如今的高楼,回想起来真的很感慨。”
这是许江身为艺术家的感性面,而作为参政议政的全国政协委员,他又有极为理性的一面。从2003年起,许江便开始参加全国两会,做了15年全国人大代表,如今全国政协委员的工作也来到第七个年头。每一年,他都花十足的精力和时间用于社会调研和建议、提案研究。采访尚未开始,许江打开已经背得有些磨皮的自制挎包,皮面上压印的是他自己绘制的葵花。他从挎包中拿出一摞笔记,每一页上都手写下满满的信息,重要之处还用荧光笔标注出来。
紧接着,他淡定坐下,铺开资料,讲起自己新一年的提案和调研故事。
“中国画教学很吃力”
参加全国两会的21年里,许江的建议和提案涉及方方面面:2014年,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提出“活化传统、弘扬美德、社会动员、全民推广”的建议,为传统文化传播和发展提出6个方案;2018年,初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他提出了“发展乡土文化”的提案;前年,他将目光转向生态文明建设,呼吁尽快设立“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去年,他又提出“艺建美丽乡村”,把“艺术乡建”的概念推向台前。

中國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到了今年,许江的提案又回到了他最熟悉的领域:高等教育。涉及的话题便是近两年被广泛热议的“艺考改革”。 “现在确定要提的是‘关于高等美术人才选拔和教育的建议。”2021年,教育部启动了艺考招生改革,2024年则是改革全面落地的第一年。“全国艺考改革是为了更加统一、更加公平,出发点是好的,但中间难免也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我想对这些问题做一些反映,希望引起重视。”
他的提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如何坚守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构建中国绘画人才自主的培养体系”。在许江看来,全国能够开展系统性、特色化的中国画学教育的院校不多,招生规模很小,而如今所提倡的统考,基本上是用“西画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使得在招生阶段,造成中国传统笔墨的式微,“所以我们中国画教学很吃力,专业越来越窄化,创作和研究脱节”。
“中国画是民族之画,中国画学是国粹之学,在全世界的美术史上,中国画学都占有极高的艺术地位。”许江以去年引发热议的“大道无极——赵无极百年回顾特展”为例。“赵无极为什么在世界享有如此高声誉,是因为他尽管用西画的形式,但又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汲取了山水、书法的精神,并把这些精神转化成当代油画的表现语言,因此得到西方的高度重视。这一次他的作品在中国展出,成千上万的人都到杭州来看——这就是中国画学的意义,它是中国民族价值观和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载体,是中国美学的根脉。”

位于浙江青龙坞的胶囊书店,给进行乡村调研的许江留下深刻印象。
“上个世纪西学东渐,中国画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时至今日,西方的艺术、绘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中国画学的话语权始终面临挑战。”在许江看来,除了招生选拔,中国画学的人才培养机制同样需要改革。今天的中国画教学制度,仍以类似西画的班级制为主,但事实上传统国画遵循“师徒相授”的模式:进入师门,老先生们靠着自己亲身示范指导学生,从而形成一套注重画法规范的教学方法。“师徒制尽管受到师傅学养限制,但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都学,因材施教。”
对此,许江提出两个建议:第一,坚持诗书画印和文史哲相结合,师徒制度和班级课程相结合;第二,培养中学预科到本硕再到博士的贯通式机制,对人才进行深厚的、长久的培养。
提案的第二部分则更为现实,“就是坚持德艺双馨,义理兼通,构建精英美术人才体系”。许江观察到,现在艺考对专业内涵要求高,对文化课要求更高,使得艺术考生疲于应付,考试人数也呈下降态势。
在许江看来,艺术是一种人类传统的、且生生不息地发展着的智性方式,而艺术教育更应该是对人的创造性施教。“对于那些专业型的美术人才,招生和教育应该给予政策支持,不该简单地用一把尺子要求所有学校。”他说,“有的人他讲不出来,但画得出来;有的人讲得夸夸其谈,但是画不出来。艺术教育不能因噎废食。”
“艺考改革一直以来都深受关注,相关提案也会受到更多人审视,也许会出现很多不同声音。”记者提到。“说了总比不说好,很多人说总比一个人说好。”许江回应。“我们都希望,通过振兴中国画学的教育,重启中华民族的大绘画气象,展现新时代的风骨精神。”
“很多文艺工作者,都已经落后于生活了”
除了艺术教育,近两年许江的另一大课题就是社区建设,尤其是社区中的文化建设。每一年的调研,与其说是在找问题、想方案,不如说是在学习、吸收。
“我们以前所谓调研,出去讲文化、文艺的时候,都有一点高高在上,好像是下来体验生活的。但事实上,现在好多文艺工作者谈乡村建设、乡村保护都只是停留在表面,殊不知今天许多地方已经建立起非常综合、完整的建设模式。”许江说,“真正到实际生活当中去看看,才知道我们已经落后于生活了。”
在浙江青龙坞的山坳里,他见到了全村迁移后改成的“书城+客栈”热门打卡点,大大推动了当地的文旅经济。在海边的小渔村,他看到村集体盖起比都市公寓更精致的居民楼,楼下建起礼堂、服务站,老人可以几块钱在服务站吃顿饭,社区还会解决双职工父母的孩子接送问题,甚至还有家风馆,凝聚起整个社区的归属感……“见识到这些,你才会意识到,我们的乡村建设已经走得那么远了,并且文化建设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同时,调研也从某种程度上反哺了他艺术家的身份。采访中,他不断提及两个字:“根”和“魂”。“对文艺创作者来说,其创作之根在文脉、在传统、在经典,也在民间;创作之魂在人,所以要心系人民、情系人民。今天我们的文化就在生活本身,就在乡土里头。”
在今年中国文联的过年晚会上,最后一首歌是所有人齐唱《到人民中去》。一句歌词一直在许江心里回荡:“到人民中去,让灵魂再受一次洗礼。”
对他来说,这句歌词既是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职责,也是身为文艺创作者的使命。
“天地真美好”
当话题落回艺术,许江的回忆便连绵不绝地展开了——他用珍惜二字形容自己的艺术人生。珍惜可以画画的机会,珍惜在中国美院的时光。
许江有过几次差点与美术擦肩而过,但每次最后他都紧握住了机遇。他生于福州,少年时代随父母来到沙县山区,当时便已展现出绘画天分。中学毕业后,他作为知青在农村插队落户,在茶丰峡山村学校当代课老师。每个星期三,他都要走几十里山路去教山里的孩子读书、唱歌。20岁,他又成为福州市红沙骨胶厂的学徒,工作环境恶劣,但从未放弃对美术的坚持。1976 年,许江凭美术专长进入福州美术公司。
1977年恢复高考,22岁的许江决定报考浙江美术学院(現中国美术学院)。第一年落榜,他不甘心,又拼了一年,终于在1978年踏进美院校门。他至今仍记得带着行李来到西湖边的心情:“天地真美好,天堂就在这!”
他印象最深的是刚进学校时,那一批堪称大师的教授还在“靠边站”。然而半个月后,他们分别出现在讲台上,出现在领导岗位上。“我进校的时候,扫走廊的是莫朴先生,我心想:这个学校不得了,扫走廊的都这么气宇轩昂。扫了个把月,人不见了,再过一星期,他成了院长。直来直往的金冶先生当时扫厕所,拎着一个铁桶过来了,拿了水就冲,搞得所有人‘落荒而逃。结果一个多月后,他成了学报主编,天天向我们讲解什么叫印象主义水彩。”

许江与他的葵主题画作。
那是中国美院再次“创业”的阶段,大师齐聚,条件艰苦但也别有乐趣。油画班和雕塑班26个学生住一间房,全校就一个篮球。“下午三四点不上课了,一定要出去写生。晚上就大家轮流做模特画素描。我们体育老师,晚上没事儿干也要到学生班里去,蹭写生、蹭素描。”
二十几岁的年纪,许江从未想过毕业,总觉得淳朴单纯的校园生活会一直过下去。直到4年过去,他被分配到《福建文学》编辑部才后知后觉。当时的福建,因为舒婷、孙绍振等一批诗坛名家而领军“朦胧诗”创作,《福建文学》一度成为诗坛桃花源。作为装帧设计,许江排版出众,别人要编一星期的东西他半天就能完成。工作好,收入也不错,但始终放不下内心真正想做的美术。
“做编辑对我锻炼很大,要读很多文章,应付很多事,更大的锻炼就是如何在很困难的环境下挤时间去画画,去坚持自己。”随着画作越来越多,许江在圈内小有名气,作品还参加了全国美展。到而立之年,他终于积攒了足够的能力和底气,回到中国美术学院任教。他用四个字形容:失而复得。
在中国美院,许江一面执教,一面进行现实主义创作,《华侨姐妹》《军队鼓号手》等作品引发圈内关注。1988年,他尝试用“中国象棋”为素材,设计创作出一种介于装置艺术与抽象艺术之间的作品,获得国内美术界关注。之后,他前往德国深造,创作了装置艺术《神之棋》,将东方的棋与西方的想象结合,在1989 年汉堡美术学院的联展中备受好评。
1992年,许江出任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副主任,成为当时国内美术界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整个90年代,他既是创作丰富的艺术家,又是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学者。
2001年,46岁的许江出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一做便是20年。
“回归意味着新的出发”
除了中国美院校史上任职最久的院长,许江身上还有一个“最”——他大概是全中国最会画葵的人。过去20年,他创作《葵园十二景》《葵灯》《静之葵》《葵之乐图》《被拯救的葵园》等作品,都在用葵这一形象,讲述着属于他和时代的故事。作家余华评价他的画:“向日葵是我们共同的一个记忆,是让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热泪盈眶的一个意象。很多年过去,终于有一个人让我们的向日葵复活了。”
许江与葵的故事起源于2003年。当时,他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马尔马拉海峡做考察,突然在荒原上看到一片一望无际的葵园。只是,这些葵花如同被尘世遗忘变成褐色,和亚细亚的荒原融为一体了。太阳在葵花背后西沉,花朵却坚定地朝向东方,他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了“一群老兵在等待最后一道命令,特别震撼”。在离葵园不到100里的地方,就是特洛伊古城的遗址,这让葵花拥有了《荷马史诗》般的壮阔与沧桑,也深深击中了许江。从此,葵成为他长达20年的创作缪斯:从内蒙古雪原的“沧桑如醉”,到象山葵园的“重生之炼”,到阿尔泰荒原的“群葵即人”,再到嘉兴南北湖的“此在即诗”……
许江画过一幅巨大的葵园。用笔很长,笔力很重,结果在画上刺出了一个洞,成了永远的烙印。余华看到后,说仿佛被打了一个枪眼。“我的掌心都是老茧,当我画画的时候,我的掌心有一种隐隐的触觉,葵就带出这样一种痛楚。这幅画非常悲壮,仿佛人被五花大绑了长在这里一样,带着镣铐,但是还是迎着太阳。”许江说,“所以有人说,看到这幅画,就想起了《义勇军进行曲》。”于是,这幅画被称为“义勇军进行葵”。
许江说:“我们这一代人,从一种文化的责任,一种文化上的焦虑,慢慢地,一步步地回到了真实的人生,回到真切的认识,回到了绘画本身。这种回归,和我们一样,并不意味着重复,回归意味着新的出发。”
或许是因为卸下了院长的重担,近些年的许江的确又有了新的出发——他投入到江南的山山水水,雁荡山、天台山、凤阳山……生活和思想开阔起来,连绘画也变得越发诗意。“我希望可以寄情山水,可以深入生活,山水中有深沉、有欢乐,也有知识。”许江说,“同时,我希望能在中国山水中得到一种时代性的体验,生发出一种既能与山水相婉转,又能和心灵共徘徊的创作感受。”
许江说,自己心中有三座山,第一座是福州城里的浮山,那是艺术的启蒙,已在城市建设中消失了;第二座是茶丰峡,那是他颠沛的青少年时代,是艺术的磨炼;第三座是象山,是他艺術世界最宝贵的财富。如今,他面对这所寄情山水的校园,把三座山的故事画成了生命的诗。
人物简介:许江,1955年出生于福建福州,中国当代油画家、教育家,1982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2001年至2020年担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为该校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院长,现担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