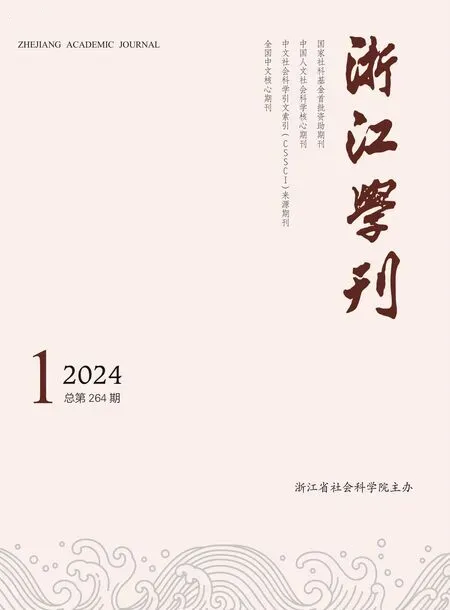在不确定中构建自主性:数字游民的日常劳动实践及其反思*
王云龙 文 军
提要:数字技术在重塑就业形态的同时也带来劳动的新异化。而数字游民凭借“信息技术”赋予的劳动资本,“工休融合”的劳动理念以及“循环流动”的劳动策略,持续型塑着自由灵活的工作体验。同时在承继了游牧主义理念下“适应管理”“生计镶嵌”“集体网络”三重技艺的基础上,得以将日常劳动情境中面临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渐确定性”,从而建构起稳固的主体性空间。此外,作为跨国劳动实践与全球化生活方式的微观缩影,数字游民的自主性本质上是源于对数字资本主义的适应而非挑战,并且随着自反性的身份建构实现再生产。
一、数字化时代来临与劳动的新异化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全面普及、全球经济结构的快速变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涌现,其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可以说,如今的数字技术已经深刻嵌入了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全领域、全要素之中。2022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就已突破3800亿大关,其中涉及生活服务、生产能力与知识技能等多重领域。(1)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3)》,2023年2月27日,http://www.100ec.cn/index/detail--6624471.html,2023年9月1日。在此阶段也相应促成了劳动方式与工作结构的系统性重构。在需求侧,由于数字化的发展使得消费者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取信息、选择服务,因此对劳动力市场提出了即时化、个性化和多样化等多重诉求;在供给侧,数字技术的进步打破了传统就业岗位惯常设定的标准化时间框架和封闭化空间,从而使得更多灵活劳动模式成为可能。于是,在供给与需求的双重推动下,诸如网络众包、在线零工、自主经营体等新型职业接连涌现,并日渐成为互联网新就业形态的核心力量。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的规模于2020年就已达到2亿人左右。(2)《努力创造更多灵活就业岗位 从业人员规模达两亿左右》,《人民日报》2020年8月8日,第2版。预计到2036年,将有4亿人参与零工经济活动。(3)云点道林:《2022中国零工经济行业研究报告》,2022年5月31日,https://zhuanlan.zhihu.com/p/522632654?utm_id=0,2023年9月1日。可以说,数字劳动作为新技术时代的关键锚点,既承载了数字生产力飞速发展的进步意蕴,也象征着劳动主体积极改造客观世界的价值取向。
当劳动者的工作模式从“工厂劳动”转向当下的“数字劳动”,诸如自由、稳定、安全等特质被提升到了首要位置。但事实上,劳动平台虽然在表面上赋予了人们极大的自由选择权,实则潜藏并沉淀着大量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数字技术非但没能按照社会的预期目标前行,反而在人工智能、算法黑箱、机器学习的中介下不断挤占着劳动者的行动空间。原本被期许实现劳动自由与解放的技术手段,如今却发现只是一种新的异化机制。从劳动供给、资源协调到服务监视、供需匹配,数字监控技术的“触手”几乎遍布于所有劳动环节中,进而使得劳动者降格为一种功能性、补充性的“机器替代物”而存在。(4)Singh,S. Jha,D. K. Srivastava and A. Somarajan,“Future of Work: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Evolution of Themes,”Foresight,Vol.24,No.1,2022,pp.99-125.此外,区别于“工厂泰勒制”阶段劳动者受固化体制约束与自身劳动行为相异化的“被动强制工作”,数字时代已深度演化为人们在自愿选择过程中的“主动强制劳动”,以至于时刻面临着被新技术操纵的危机。从“机器换人浪潮”到“大厂裁员风波”,从“困在系统中的外卖员”再到深陷“996”困境的互联网从业者,网络信息技术非但没有让劳动者获得应有的自主权,反而使不稳定的工作条件、非标准的雇佣关系和不可预测的职业前景成了数字劳动的底色。各种不确定因素的辐射力度远远超出了既有的规制范围,从而使得“不确定性”成为数字劳动领域需要直面的主题。
在此背景下,被信息技术赋能的数字游民逐渐兴起,并凭借着独立自主的劳动节奏以及乐享自由的文化习性,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数字囚笼”的突围,还成功促成了对不确定性情境的反制。因此,本研究旨在重点围绕数字游民的日常劳动实践展开讨论:一方面,主要关注其如何应对工作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失衡关系,从而重建劳动的秩序感,即“数字游牧”工作何以可能;另一方面,重点探究劳动者如何践行自身的主体性策略,进而在不稳定、不平等、不安全的条件下仍然能构造形成相应的行动空间,即“数字游民”群体以何而为。
二、“不确定性工作”:数字劳动者的隐性危机
数字劳动虽然简化了原本繁杂的工作程序与标准,但本质上对于资本的从属地位没有发生改变,劳动者的自主性仍然被视为数字资本增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根源。(5)顾楚丹、文军:《应对不确定性:互联网“大厂”实习生的数字劳动过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所以无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数字平台都旨在通过规范性控制的方式对劳动者“施压”,将“未知”的人力资源转换为“已知”的经济资本,从而实现对产业结构与劳动关系的确定性掌控。但这在无形中也将市场内部的风险因素转移到了劳动者身上,使之时刻面临较高的就业压力和职业危机。可以说,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形态,当前的数字工作正处于“不确定的不确定性(unknown-unknown)”状态,(6)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至少存在三种关系:一是“确定的确定性(known-known),”这是一种对问题和结果已知的表述;二是“确定的不确定性(known-unknown),”这是一种对问题已知而结果未知的表述;三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unknown-unknown),”这是一种对问题未知且结果也未知的表述,同时也是更宽泛意义上的“不确定性”。而所谓“不确定性工作”则是由内部组织性因素和外部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内部而言,主要涉及模糊的雇佣关系、匮乏的工作保障以及混乱的劳动规律;就外部而言,则指涉的是未知的市场环境与复杂的社会结构。内外部因素共同塑造了不稳定、不平衡且不可逆的工作样态。参见文军:《回到“不确定性”:社会风险研究的范式反变》,《浙江学刊》2023年第3期。J. Heyes,S. Moore,K. Newsome and M. Tomlinson,“Living with Uncertain Work,”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Vol.49,No.5-6,2018,pp.420-437.其与“非正式工作(casual work)”“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非典型雇佣(atypicial-employment)”等范畴紧密相关,(7)R. Grohmann,G. Pereira,A. Guerra and L. C. Abilio,“Platform Scams:Brazilian Workers’ Experiences of Dishonest and Uncertain Algorithmic Management,”New Media &Society,Vol.24,No.7,2022,pp.1611-1631.主要指代的是“不确定”的劳动过程、“无规律”的劳动时间以及“非标准”的劳动关系。(8)I. Oliynyk,T. Bezprozvanna and Maria Maletska,“Self-Identification of Precariat Representatives,”Skhid,No.5,2020,pp.24-28.深陷其中的数字劳动者既无法对现有的行动策略作出规划,也无法对未来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予以研判。再加上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从属于劳动需要,“不确定性工作”带来的影响甚至开始渗透到了数字劳动者的日常生活领域中,并由此造成工作秩序的混乱和错位,持续加剧着主体性危机。
(一)数字劳动过程的不确定性
马克思(Karl Marx)曾将劳动描述为一种改变物质世界的行为,一种满足人们自由需求的手段以及实现自身价值的创造性活动。(9)《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页。然而当前的数字劳动却依旧采用着“去技能化”的方式,希望将生产过程中的“概念”与“执行”相分离。(10)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使劳动者成为劳动生产过程中细微且可替代的部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数字平台主要是在万物互联的互联网平台与算法技术的支持下,隐秘设置了一整套系统化、组织化、层级化的“数字泰勒制度”,具体而言:一方面,在系统庞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和技术理性的基础上,平台从一开始就将权力不对等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原则嵌入了算法逻辑之中,其或是对数字劳动者进行全方位的“监控管理”,或是通过“认知规训”的方式进行控制,从而压制员工的自主知识、专业技能和个人能力。(11)贾文娟、颜文茜:《认知劳动与数据标注中的劳动控制——以N人工智能公司为例》,《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5期。长此以往,劳动者的日常工作俨然成为一种类似机器人的体验。另一方面,在“算法黑箱”的作用下,劳动主体被异化为可供计算的数据集,诸如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职业群体的日常工作惯习、行为轨迹、订单效率等数据还会在每一次任务完成后又折返回平台中,充当“黑箱”的养料,不断压缩劳动者的体力与精力。总之,当前的数字工作尽管极大地解放了劳动的限度,激活了劳动的延展性,但本质上仍然是高强度的流水线工作,劳动者的日常行动不再能够由自己掌握,而是在持续不断的“数据规制(datafication control)”过程中成为被削弱的、个体式的、分散化的要素。(12)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久而久之,数字工作者深陷于算法牢笼之中而无法脱身。
(二)数字劳动时间的无规律性
随着社会节奏的不断加速,以“即时性”为特征的工作标准开始成为市场竞争的核心指标。无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数字平台都不再仅仅满足于常规的劳动效率,还在信息技术的强大优势下不断对标准工作时间进行压缩,将日常劳动无缝接入生活领域中。(13)赵璐、刘能:《超视距管理下的“男性责任”劳动——基于O2O技术影响的外卖行业用工模式研究》,《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4期。因此从表面上看,数字资本主义似乎给予了劳动者更大的选择空间,自由决定工作强度,并由此产生“时间自主掌控”的感知。然而实际上却使得新技术工作者陷入了持续加压的状态中。一方面,将工作任务与竞争机制结合,例如互联网企业普遍采用的KPI绩效管理策略对员工进行评估,使绩效水平与劳动报酬相挂钩,在这种不进则退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过程中,即使是高技能、强创意的劳动者也只能以牺牲自由和灵活为代价,被迫沦为机械化的“零工”;另一方面,将劳动收入与工作时长挂钩,原本规律化、可预测的薪资模式被弹性收入所替代,个人的收入越来越难以获得保障,以至于必须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从而维持基本的生活条件。总之,在平台资本营造的自由表象背后,弹性化的工作体系使得几乎任何时间都有成为剩余劳动时间的可能性,而互联网平台企业正是通过对时间的隐秘操控来强化自身的资本积累。(14)N. K. Chan and C. Kwok,“The Politics of Platform Power in Surveillance Capitalism: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Ride-hailing Platform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Global Media and China,Vol.7,No.2,2022,pp.131-150.尽管数字劳动者普遍面临着越发无规律的时间制度,却又由于巨大的系统惯性而难以抽离,随之而来的便是工作和生活界限的模糊化以及劳动者越发严重的精神损耗。
(三)数字劳动关系的非标准化
在不确定性和竞争关系日益增强的市场环境下,互联网企业与数字平台开始越来越多地采取服务外包、网络众包等“非标准化”雇佣策略,试图在形式上将员工的“受雇佣者”身份转化为“独立承包商”,从而规避正式雇佣关系产生的风险成本。一方面,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平台或是以“代理”的方式通过层层“转包”获取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或是提高劳动者的流动性,使原本游离在生产体系之外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补充到数字工厂中,尽可能地消除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投入与支出;(15)P. Borghi,“The Promises of The Sharing Economy and The Dark Side of Platform Capitalism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Workers’ Representation,”Rassegna Italiana di Sociologia,Vol.64,No.2,2023,pp.397-408.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使劳动供应者直接与市场需求相连接,传统“雇主—雇员”间的标准劳动关系也被替换为“劳动者—平台—客户”的三角关系,进而将劳资冲突向社会层面转移,(16)M. Kienscherf,“Surveillance Capital and Post-fordist Accumulation:Towards a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Surveillance-for-Profit,”Surveillance &Society,Vol.20,No.1,2022,pp.18-29.不但削弱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还使得“资强劳弱”的局面得到进一步固化。总之,“非标准化”用工虽然在形式上促进了雇佣关系的多元化与用工方式的灵活化,然而就实质而言,从对劳动者施予的奖惩到单位劳动时间与劳动期限的设定,无一不彰显着固有“用工方”的权力,这在有效规避劳动资料预付和补偿的同时,还成功的将风险转嫁到了工人群体身上,使之逐渐被弱化为一个又一个的“不稳定生产者”。(17)S. Ping,“Your Order,Their Labor:An Exploration of Algorithms and Laboring on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in China,”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2,No.1,2019,pp.1-16.
三、数字游牧:一种“平衡导向”的劳动实践
20世纪末,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和大卫·梅乐斯(David Manners)就描绘出了游牧工作的基本轮廓。通过借助高速的无线网络和强大的移动设备,未来社会将摆脱传统工作的强制性和纪律性结构,使劳动者能够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的同时周游世界。(18)T. Makimoto and D. Manners,Digital Nomad,Wiley Press,1997,p.6.然而当时正处于新技术发展初期,这种高度自主、灵活、开放的工作方式仅仅停留于美好的设想。如今随着精细化的劳动分工以及日益成熟的数字媒介,一个个以“游牧式”劳动为主的数字游民群体也随之壮大。(19)M. Holleran,“Pandemics and Geoarbitrage:Digital Nomadism Before and After COVID-19,”City,Vol.26,No.5-6,pp.831-847.概言之,数字游牧是指借助数字技术的虚拟特质,使自身摆脱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束缚,在全球范围内依靠互联网从事知识生产、内容输出与经营管理,尽享工作自主性的同时赚取收入的劳动实践。数字游民虽然以知识工作为主,但并不等同于“数字灵工”,从生产、设计到翻译、编程,任何能够借助互联网提供有偿服务的工作仅仅只是具备了成为数字游民的基本条件,而真正促使数字游牧成为一种全新实践方式的重点就在从“工作即生活”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在“游牧式”的流动实践中产出富有创造性和价值意义的工作成果。(20)P. Matos and E. Ardévol,“The Potentiality to Move Mobility and Future in Digital Nomads’ Practices,”Transfers,Vol.11,No.3,2021,pp.62-79.因此区别于常规的数字劳动形态,数字游牧本身便蕴含着自由独立和自主驱动的先赋秉性。(21)根据“数字游民部落”的界定,数字游民的特点包括:(1)灵活自由的工作时间与地点;(2)以互联网为媒介的远程工作或是自由职业;(3)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等。参见数字游民部落:《数字游民扫盲》,2021年11月10日,https://jarodise.com/the-ultimate-guide-to-digital-nomad-lifestyle-2022-post-pandemic-version,2023年9月1日。尤其是随着“Z世代”逐步成长为新经济、新消费、新文化的主导力量,并随即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劳动价值偏好。对于这部分新生代群体而言,劳动已经不再单纯是为了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更重要的是工作本身具有的意义、价值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富足感。而这些诉求也在无形中与数字游牧的理念不谋而合。MBO Partners发布的美国数字游民报告显示,(22)MBO Partners,“Digital Nomads:Advancing the Next Way of Working,”Sep 6,2021,Retrieved from https://www.mbopartners.com/state-of-independence/2021-digital-nomads-research-brief/,Sep 1,2023.将自己描述为数字游民的劳动者数量已经从2019年的730万迅速增长至2021的1550万,年环比增长超过40%;就中国而言,从《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来看,76.4%的“00后”愿意成为数字游民。(23)智联招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2022年10月23日,https://www.fxbaogao.com/report?id=3417282&im=biubiu,2023年9月1日。据预测,到2035年,全球更是有60%的工作人口将成为自由职业者,届时数字游民的规模也将达到10亿。(24)A. Gussekloo and E. Jacobs,“Digital Nomads:How to Live,Work and Play Around the World,”Feb 18,2016,Retrieved from http://www.digitalnomadbook.com,Sep 1,2023.一种“不受技术手段、规则和详细程序控制,在全球地理空间内进行移动工作”的游牧式劳动实践正在逐步确立。(25)根据“2017-2023年全球移动劳动力预测指数”(Global Mobile Workforce Forecast)来看,在信息化趋势的影响下,全球移动劳动者已经从2017年的15.2亿上升为2023年的18.8亿,约占全球劳动力的43.3%。G. Luk,“Global Mobile Workforce Forecast Update 2017-2023,”May 18,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rategyanalytics.com/access-services/enterprise/mobile-workforce/market-data/report-detail/global-mobile-workforce-forecast-update-2017-2023,Sep 1,2023.区别于常规数字劳动者受到的“数字泰勒控制”,“数字游民”往往能够根据不确定性的社会情境进行调适,并通过对现有规则和资源进行重新改组和利用,从而在对立分化的劳动情境中建立起新的平衡。这也恰恰诠释了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语境下的“非常规劳动者”形象,他们“唯变化为永恒,以交融为富足”(26)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郭楠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第26页。,凭借着自身对于“迷宫法则的熟稔”,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和“钢筋水泥”束缚的工作地点,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进行着自主化的劳动实践。概括来看,“数字游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数字游牧”以劳动技术与职业身份的内在平衡为基础。虽然算法技术与平台软件的推广使劳动工具实现了从物理形态向数字形态的转换,但是从“远程监控”外卖员日常工作的平台软件到“时刻监视”互联网企业白领工作效率的电脑程序,原本被设计出辅助生产的工具反而成了与劳动者相异化的存在。相较而言,“游牧式”劳动则最大化地释放了“人”的潜力与价值。其中,数字游民或是以网络作家、旅行博主和视频制作为主的自由职业者,或是软件开发、数字设计、线上教育等远程工作人员,但总体上都属于掌握数字生产关键技术的“移动知识工作者(mobile knowledge workers)”。在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看来:“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信息主义的浮现,并成为新社会的物质基础,财富的生产、权力的运作与文化符码的创造变得越来越依赖社会与个人的技术能力,而信息技术正是此能力的核心。”(27)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0页。数字游民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以及较高的信息化素养,日常劳动实践又通常以数字软件、技术程序和移动设备等作为媒介进行高级数字产品创造以及互联网创意内容生产,难以用“去技能化”的方式实施管理,因而能够凭借对技术工具的熟练运用实现主体赋权。
第二,“数字游牧”以实现工作与休闲的均衡协调为核心。工作与休闲本质上属于生活的一体两面,是人类发展的合规律性需求,其往往能够作为功能性的补充,使劳动者获得充沛的工作活力以及精练的创造意识。但是为了加大剩余价值的获取力度,当前的工作时间被不断延伸,直至生活领域。(28)M. Toivanen,“Countercultural Lifestyle No More? Digital Nomadism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Neo-nomadic Mobilities,”Mobility Humanities,Vol.2,No.2,2023,pp.70-89.从休闲活动、兴趣爱好到情感宣泄都成为数字资本的“圈地对象”,致使工作和休闲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尤其是在以按需服务为特征的平台劳动中,网约工作者需要“时刻待命、及时响应”,通过满负荷的运转支撑机器系统的连贯运作。久而久之,人们越发难以获得身心放松的生活状态。所以与固有印象中“工作不稳定导致生活不稳定”的观点不同,凯瑟琳·米拉尔(Kathleen Millar)指出恰恰是生活状态的不稳定性才破坏了工作的稳定性,真正富有价值的工作往往是在充足的休闲基础上获得的。(29)K. M. Millar,“Toward a Critical Politics of Precarity,”Sociology Compass,Vol.11,No,6,2017,pp.1-24.因此,区别于以往需要始终保持“持续在线”或是“上班打卡”的劳动时律,数字游民主张在工作与生活之间达成平衡,从而使自身从不可预测的时间秩序中抽离出来,远离工作负荷造成的精神内耗。可以说,这也正是多数从业者选择成为数字游民的理由。当然,对于平衡性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工作和生活保持相等的关系,而是找到或者建立适合的生活方式,让两者相互协调。所以在日常情境下,数字游民在创造中赚钱、在快乐中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改变居住地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而是为了获得更加充实的生活”(30)K. Meagher,“Illusions of Inclusion:Assessment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o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Development and Change,Vol.51,No.2,2020,pp.667-682.。
第三,“数字游牧”以组织关系与空间边界的权衡统筹为目标。尽管工业革命以来劳动形态不断变化,但是雇员与雇主的依附关系却相对稳固,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工业劳动体系始终保持着“工厂中心”的组织逻辑,即通过实体空间的建设实现对身体的约束。虽然目前平台从业者的工作环境已经顺利从完全封闭的“工厂空间”转到了相对开放的“数字场景”中,(31)M. Moritz,I. M. Hamilton,P. Scholte and C. Yu-Jen,“Ideal Free Distributions of Mobile Pastoralists in Multiple Seasonal Grazing Areas,”Rangeland Ecology &Management,Vol.67,No.6,2014,pp.641-649.但仍然是在数字设备引导下,被绑定在相应区域范围内完成服务工作(如网约配送员、写字楼白领等),劳动者的从属性依旧没有与封闭的空间生产体系相脱离。因此,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对技能要求更高的个性化岗位的增加,以远程办公、虚拟合作、项目管理为特征的“后科层”劳动体系逐步兴起。数字游民也正是以此为契机,主动从高度固定的空间区位以及标准化的组织关系中剥离出来,并促成了流动化的劳动实践。(32)F. Mancinelli,“Digital nomads:Freedom,Responsibility and Neoliberal Order,”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ourism,Vol.22,No.3,2020,pp.417-437.与传统就业模式相比,这种在拉伊诺尔迪(Mattia Rainoldi)话语下的“数字茧型分离者(the digitally cocooned separator type)”,(33)M. Rainoldi,A. Ladkin and D. Buhalis,“Blending Work and Leisure:A Future Digital Worker Hybrid Lifestyle Perspective,”Annals of Leisure Research,Vol.27,No.1,2022,pp.1-21.无论是在物理层面(地理空间)还是虚拟层面(网络空间)的流动性都相对较高,在日常工作中可以不受传统办公系统(包括办公空间、生产设备、人事关系等)的禁锢,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工作/旅居地点。其并无固定的目的地,也并无固定的流动节奏,既涉及长时间大尺度流动的国际迁徙,还包括着短时间、跨省区流动的区域性移动,数月(份)、数季(节),甚至数年(度)都有可能。
四、以“不确定性”为生:数字游民的自主化劳动策略
娜塔莎·玛鲁(Natasha Maru)等学者曾指出,相较于农业、工业系统所追求的高效化、精细化特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早就习惯于在不可预测、高度多变的情境下维持生产的恒定性。(34)N. Maru,M. Nori,I. Scoones,G. Semplici and A. Triandafyllidou,“Embracing Uncertainty:Rethinking Migration Policy Through Pastoralists’ Experiences,”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Vol.10,No.5,2022,pp.1-18.所以相较于惯常所处的“确定性”生产、生活体系,以“不确定性”为生的理念长期根植于游牧民族的世界观、生活观与劳动观中,这随即也开启了对数字劳动者日常工作实践的全新认识。如何在持续的流动、迁移过程中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因素作出调节与适应,是每一位数字游民的必修课。其中的核心要件便是单位自主权的最大化,通过强化劳动者的内在弹性,将未知的风险转换为行动杠杆,最终实现对不确定性的“降解”。基于迈克尔·诺里(Michele Nori)长期在地化的经验总结,(35)M. Nori,The Evolving Interface Between Pastoralism and Uncertainty:Reflecting on Cases from Three Continents,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2021,pp.6-7.可以将游牧民族的劳动策略概括为“复杂适应(complex adaptation)”“生计镶嵌(livelihood mosaics)”和“集体创生(collectivization enactment)”。而根植于“游牧主义”理念基础上的数字游民也正是在承继了上述三重适应性策略的基础上才得以在不稳定、不平等和不安全的条件下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性空间。
(一)多元生计:数字赋能下的技术变现
稳固的生计收入既是数字游民追求自由的基本保障,也是其保持自主性的重要前提。由于脱离了依靠组织力量作出工作安排和资源配置的劳动体系,置身于个体化劳动条件下的数字游民自然成了根据市场逻辑自主决策并承担责任的独立主体。所以为了提高自身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其主要是在数字赋能的基础上,凭借自身的技术资本寻求多元化的生计途径。其中,“生计通常是建立在能力、资产和活动的基础之上”(36)B. Belton and P. Fang,“Hybrid Livelihoods:Maize and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in Southeast Asia’s Uplands,”Journal of Rural Studies,Vol.95,No.1,2022,pp.521-532.,为了降低开发成本,大量的高新技术公司开始大范围地选择“离境外包(outsourcing)”的方式,基于互联网数字平台供求信息的规模化匹配和劳动力的高效率组织,将曾经由内部员工执行的职能转包给外部技术人员,并根据任务的完成情况支付报酬。(37)S. Kumar,A. Bagherian,A. Lochab and A. Khan,“Protean and Boundaryless Career Attitudes as Antecedents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Evidence from the Indian IT Industry,”Businesses,Vol.3,No.1,2023,pp.83-97.在此背景下,“任务型”工作成了数字游民的主要劳动形态,他们通过中介平台了解任务需求,通过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设计获取收入。(38)区别于高度中心化的“微型工作平台(Microtasks)”或是“按需服务平台(On-demand Service)”,信息中介平台只是将客户和劳动供给方连接,并不参与设定服务的最低质量标准以及劳动力的选择和管理。目前数字游民市场上使用较多的任务平台诸如国外的“Working Nomads”“Virtual Vocations”“Upwork”等和国内的“开源众包”“圆领”“电鸭”等。由于难易程度、精力投入大小的不同,任务相应设定的时间限制也有所不同,因此只要对自身的工作效率与进度进行合理规划便可以实现“身兼多职”,甚至在垂直工作领域内同时进行多个项目的开发。尽管“游民”群体从事的工作内容、领域有所不同,但是区别于以往严格依靠等级划分、绩效激励、算法控制的评估标准,他们的日常工作更为关注作品质量、技术水平和行业声誉等结果导向的数据,受到正式组织结构、规则的限制也相应较小。当然,数字游民除了凭借“自雇佣者(self-employed persons)”的角色,以远程工作、自由职业为基础赚取主动收入之外,还会将劳动技能进行延伸,以“独立合同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s)”的身份,通过技术创业或是线上投资获取被动收入。尤其是数字游民的构成者多为互联网经济的“弄潮儿”和创意经济的“排头兵”,在当下更加敏锐地把握住了互联网由“Web 2.0”向“Web 3.0”过渡的阶段性红利,在借助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数据留存、智能合约等“去中心化”技术功能的基础上,(39)K. Saurabh,N. Rani and P. Upadhyay,“Towards Blockchain Led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DAO)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s,”Benchmarking:An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30,No.2,2023,pp.475-502.或是以自组织的方式发起并进行研发工作,或是选择参加其他的创投项目,设计出相应的软件、程序、插件等产品,并从中赚取资金。与传统互联网企业的运作体系不同,其中无论是“雇主—雇员”“消费者—服务者”还是“技术团队”都可以根据数字算法构建的隐含契约进行自由交互,项目完成后团队即可解散,从而将精力转向新的项目,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一种“无边界的职业生涯(boundaryless career)”(40)S. Kumar,A. Khan,A. Lochab,V. P. Gupta and A. K. Arora,“Boundaryless Career:A Bibliometric Analysis,”Prabandhan:Ind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Vol.16,No.8,2023,pp.24-44.。如果说传统职业群体凭借自身对组织的忠诚换取终身就业保障的话,那么为了应对不稳定的劳动市场,数字游民则会很少选择在相同的领域长期深耕,反而是密切跟随互联网新技术行业的前沿发展态势,在全球范围内积极“猎身”并适时变换赛道。支撑这种劳动策略的重点便是灵动的技术能力,只有掌握核心劳动技能才能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因此,数字游民在日常工作之余还尤为注重对知识技能进行“追加投资”,通过不断地学习确保自身能够在数字劳动市场中“游刃有余”。
(二)风险适应:空间迁移下的套利实践
“风险适应”强调的是劳动者在面临外部风险带来的冲击时能够主动进行调整,不断适应“恒新(perpetual)”的环境,从而获得更多的主体性空间与发展机遇。对于数字游民来说,空间迁移不仅是重要的生存适应性策略,同时也成为日常劳动实践的重要组成环节。(41)F. Mancinelli and J. Germann Molz,“Moving With and Against The State:Digital Nomads and Frictional Mobility Regimes,”Mobilities,Vol.19,No.1,2023,pp.1-19.他们“逐水草而居,顺天时而动”,时刻保持着一种易于流动、服从流动的状态,从而将自己放置在有利于发展的环境之中。近年来出现的“逃离大城市,回乡躺平”呼声之所以能够引起都市青年白领的共鸣,除了因为压力大、节奏快、工作忙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城市通常是高薪工作岗位的聚集地,但是随之而来的通勤成本、生活成本也“水涨船高”,由此便进入了收入越高、开销越大的怪圈之中。人们部分选择成为数字游民的原因也是如此,但其践行的策略并非对现实妥协,而是在“内卷和躺平”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利用数字工作的时空脱域特质,选择在高收入地区赚钱,同时迁移到生活成本较低的国家生活,从而享受“发达国家高收入标准和发展中国家低生活成本的双重好处”(42)O. Hannonen,T. Aguiar and X. Lehto,“A Supplier Side View of Digital Nomadism:the Case of Destination Gran Canaria,”Tourism Management,Vol.97,No.1,2023,pp.1-15.。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将新自由主义的主体性概括为一种激励自我行为按照理性最大化路线进行的重新配置。(43)T. Christiaens,“The Entrepreneur of the Self beyond Foucault’ s Neoliberal Homo Oeconomicu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23,No.4,2020,pp.493-511.数字游民正是通过地缘套利的劳动机制作为缓冲,得以免受不确定性工作可能带来的生活困境。当然,其劳动空间并非毫无边界,也并非游于“任何地方(anywhere)”,促使数字游民将特定国家或区域作为目的地的原因除了便于实现经济层面的套利实践之外,更重要的是随之带来的生活体验感。(44)F. Mancinelli,“Digital Nomads:Freedom,Responsibility and Neoliberal Order,”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ourism,Vol.22,No.3,2020,pp.417-437.所以除了对可供日常工作的网络设施条件以及生活成本的考量之外,“流入地”宜人的环境气候、完善的公共服务以及友好的城市氛围也构成了重要的拉力。(45)根据全球性网站“游牧清单(List)”的排名,目前最受游民青睐的前十城市是巴厘岛、里斯本、曼谷、萨格勒布、蒂米什瓦拉、清迈、柏林、马德拉、班加罗尔和汉城。参见:https://nomadlist.com/。在此过程中,其流动式的游牧节奏和规律也不尽相同,既涉及全球尺度的范围性流动,也包括长距离和短距离交错的叠加流动,最终呈现出“循环流动”的特点。如今的数字游牧甚至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和文化现象,全球已经有二十余个国家先后推出了“数字游民签证(digital nomad visa)”申请通道,并相应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旨在将自身定位为实现数字游牧劳动的理想地点。(46)J. Sánchez-Vergara,M. Orel and I. Capdevila,“‘Home Office is the Here and Now’ Digital Nomad Visa Systems and Remote Work-focused Leisure Policies,”World Leisure Journal,Vol.65,No.2,2023,pp.236-255.总之,空间迁移不但体现出了数字游民通过改变劳动轨迹获得自主性的能力,同时也展现出了其改善生活状态的积极意愿,他们就如同“候鸟”一般,在飞行中矫正目标,在迁徙中实现理想。
(三)集体创生:资源共享下的社群联结
从全球尺度来看,呈散点分布的数字游民仿佛是持续变动的原子个体,所以为了避免由此出现的断裂和离散危机,游民群体还致力于通过集体互助、互利协作的方式提高整体的抗逆力,由此在各个游牧地点周围,“游民社区”应需而生。(47)F. Situmorang and E. T. Karthana,“Redesign Rural Tourism Product Based Digital Nomadism Postpandemic COVID-19 in Bali,”Jurnal Kepariwisataan:Destinasi,Hospitalitas dan Perjalanan,Vol.5,No.2,2021,pp.1-15.其不仅通过有形的共享空间为数字游民提供日常所需的生活资源,还能够凭借无形的共享资源带来广阔的视野以及发展机遇。(48)R. Bouncken and A. Reuschl,“Coworking-Spaces:How a Phenomenon of the Sharing Economy Builds a Novel Trend for the Workplace and for Entrepreneurship,”Review of Managerial Science,Vol.21,No.1,2021,pp.317-334.实体空间往往集“远程工作、日常居住、休闲交往”于一体,更加注重贴合数字游民的日常需求。除了基本的住宿功能之外,最核心的部分便是网络设施丰富的共享工作空间以及供日常使用的会议室、娱乐区等公共区域,社区内绝大部分资源都是以共享的方式予以提供。此外,社区内还会定期组织集体聚餐、职业分享会和户外活动等,从而提高社区整体的凝聚力,增强其归属感。由于“游民”的流动性、临时性较大,因此每一个游民社区都是自主运作的典范,其日常运营更多依靠的是成员们自发形成的非正式规则。而对于数字游民的身份认同往往会强化社群成员的集体意识,使所有人自觉参与到社区的维护和管理工作中并主动维持社区利益,最终形成了一种宽容、平等、信任的空间氛围。(49)J. Berbegal-Mirabent,“What Do We Know about Co-Working Spaces? Trends and Challenges Ahead,”Ustainability,Vol.13,No.3,2021,pp.1-30.目前国外较为知名的游民社区有布莱德的“SubWork”,巴厘岛的“Polkadot Hubs”,清迈的“C.A.M.P”等,国内如安吉的“DNA数字游民公社”,文昌的“Nomad House”和“Serendipity”,大理的“Dali Hub”和“706青年空间”等。在此过程中,散落于世界各地的游民社区俨然成了关键节点,最终由点成线,串联起了全球游牧网络。数字游民不仅可以随心穿梭于任何一个基地,将之作为短期内的“大本营”,同时也能够以此为契机,在短时间内与拥有共同志趣的“他者”进行互动交流。(50)O. Hannonen,“In Search of a Digital Nomad:Defining the Phenomen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urism,Vol.22,No.3,2020,pp.335-353.从这个角度看,游民空间已然超越了单纯的物质性存在,并在潜移默化的互惠行动与情感互动中上升为一种资源配置的场域。林南曾指出:“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关系中的,能够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51)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4页。社区空间在对异质性个体进行吸纳的同时也起着提供人才聚合、互动合作的作用。他们不仅能够相互分享旅行路线、政策信息,沟通远程工作经验、生活趣事,还能通过与同频工作者的链接,逐渐将“弱关系”拓展成“强关系”,在即时真切的反馈中进行知识共享、跨界合作,依据兴趣、需求自发建立临时性团队,合作完成技术项目甚至联合创办小型互联网公司。就算日后流动到其他国家或城市,彼此之间也可以依靠通信媒介形成稳固的互联链条,构筑跨越时空的社群共同体、兴趣共同体、职业共同体。
五、总结、讨论与反思
面向21世纪,来自传统、现代与当代以及区域、本土与全球的危机症候彼此交织在一起,进而呈现出风险事件的流动化、风险议题的复杂化以及风险边界的模糊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辐射力度早已超出了确定性的预期。(52)文军:《从“结构导向”到“关系为本”:重构面向不确定性时代的全球化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随着社会整体发展进程从“线性、清晰、可控的阶段”推进到“非线性、模糊、失控”的新阶段,(53)T. Aven,“On How to Deal with Deep Uncertainties in a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Context,”Risk Analysis,Vol.33,No.12,2013,pp.2082-2091.不确定性自然也就成为数字劳动领域的基本思维框架和认知向度。马克思(Karl Marx)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曾指出:“资产者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不仅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日益迅速的和持续不断的改良,也使得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页。如今这种情况非但没有随着新技术的进步得到缓解,反而在无形中加剧了劳动者的整体危机。(55)A. Müller,“The Digital Nomad:Buzzword or Research Category?” Transnational Social Review:A Social Work Journal,Vol.6,No.3,2016,pp.344-348.源于社会层面的不确定性与经济层面的不稳定性无处不在,(56)文军:《挑战与回应:发展的不确定性与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建设》,《社会工作》2023年第6期。肆无忌惮地侵蚀着劳动者的生存空间,使之“被困在平台中,绑定在算法内、系缚在抽成里、游离在保障外”。但是不确定性的存在虽然一方面预示着消极的处境,另一方面也被视为增加主体行动意图和内生性力量的源泉。(57)O. Perminova,M. Gustafsson and K. Wikström,“Defining Uncertainty in Projects:A New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Vol.26,No.1,2008,pp. 73-79.正如弗里德曼(Sam Friedman)和劳里森(Daniel Laurison)所言,尽管置身于风险与机遇交缠而成的“莫比乌斯环形”劳动力市场中,拥有更多社会、文化和技术资本的群体反而能够从中分离出来,并更好地按照不确定的规则进行游戏。(58)S. Friedman and D. Laurison D,The Class Ceiling:Why it Pays to be Privileged,Policy Press,2019,p.133.所以相较于被动承受风险袭扰的常规数字劳动者,数字游民则会主动通过“自我去稳定化”的策略,不断践行“个人式的退场策略(individualistic exit strategies)”。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数字游牧劳动是对既有资本主义体系的挑战,反而数字游牧劳动是与新时期数字资本链条相适应的结果。从多种生计手段、地理空间套利再到社群资本联结,本质上都是在遵循全球市场机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策略变通,同时也在此基础上促成了不确定性境遇下的主体再造。概括地来看,支撑其自主性空间得以持续运作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数字游民实现了从“技术控制”到“技术选择”的转变。虽然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劳动生产关系历经解构与重构,但随之而来的还有日益分化的不稳定劳动群体。相较于“数字底层(digital underclass)”或“赛博无产阶级(cyber proletariat)”,数字游民本质上仍然属于“劳动力精英群体(labour elite)”。(59)P. Goodwin,“Mission Impossible? A Review of Kylie Jarrett’s Book Digital Labor,”Communication,Capitalism &Critique,Vol.20,No.2,2022,pp.213-220.所以区别于常规劳动者普遍受到的数字监视,数字游民不仅受到算法技术的影响相对较小,还能够凭借自身的创新知识、技术能力、生活履历获得与市场资本、国家政策甚至算法协议进行议价的可能及协商的机会,切实诠释出了非异化的主体性。
其次,数字游民实现了从“时空规训”到“时空自由”的转变。(60)D. Cook,“What is a Digital Nomad? Definition and Taxonomy in the Era of Mainstream Remote Work,”World Leisure Journal,Vol.65,No.2,2023,pp.256-275.相较于在以往“数字工厂”体制下,企业对于从业者的时间和地点作出的严格安排与设置。数字游牧劳动凭借着自由灵活的工作方式和逐利而居的生活理念,不仅“摆脱了既定组织系统和地理结构的制约”(61)C. Bonneau,J. Aroles and C. Estagnasié,“Romanticisation and Monetisation of the Digital Nomad Lifestyle:The Role Played by Online Narratives in Shap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Work,”Organization,Vol.30,No.1,2023,pp.317-334.,同时还能够根据自身的意愿与需求,独立进行工作安排。当劳动者不再被争分夺秒的“计划表”所困扰,也不再为封闭压抑的“格子间”所围困时,随之而来的就不仅仅是身体的解放,还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想象力、意义感和幸福感,这使工作真正变成了自在、自觉、自为的活动。
最后,数字游民实现了从“组织性自我”到“创业性自我”的转变。(62)D. Cook,“What is a Digital Nomad? Definition and Taxonomy in the Era of Mainstream Remote Work,”World Leisure Journal,Vol.65,No.2,2023,pp.256-275.其中的核心变化便是数字游牧劳动已从传统的“非标准雇佣”转向了理性化的“自主经营”。这既不同于压制主体性的“责任自治”,也不同于制造生产意愿的“文化认同”,而是在互联网平台企业与数字游民之间形成的一种全新交互模式。数字游民不再是“出卖”自身劳动力的受雇劳动者,而是投入知识和技术的企业“合作者”,与资方是基于等价交换形成的市场契约关系。因此能够凭借着更加宽广的职业选择空间和平等的劳动主体身份规避“非标准”雇佣方式带来的风险。
总之,数字游民作为全球化时代生活方式的微观缩影以及数字时代劳动者生存的真实写照,本质上正是在自我审视、自我反思和自我赋能的自反性身份实践过程中对各种不确定性力量的调和,他们不断的寻求甚至创造着专属于自身的确定性空间。当然,在这种浪漫的形象背后,“游牧式”的劳动策略也终究难以完全脱离技术与资本相勾连的权力之网,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国际移民制度的变动以及全球经济市场的波动等结构性因素都会对数字游民造成更加剧烈的影响,使之时刻面临劳动降层与生活降级的双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