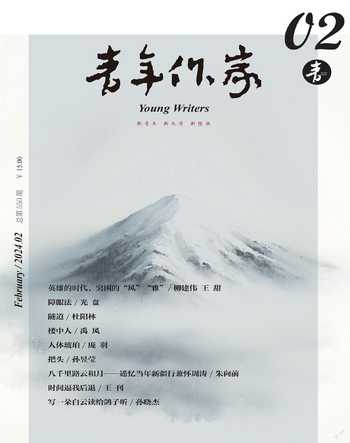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是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学员,1984年9月1日入学,学制两年。转眼就到了1986年春节。在军艺文学系学习的一年半,也是我此生中的黄金岁月——是知识上如饥似渴的一年半,也是创作上激情迸发的一年半;是时间上争分夺秒的一年半,也是身心放松空前愉悦的一年半。好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眼看就要毕业了,第四个学期是实习和创作毕业作品,基本上是在校外完成,时间自己掌握。
2月23日元宵节一过,春节也就过完了。满打满算,距6月1日返校还有三个月时间,除去五月实习,创作时间只剩两个月了,好不紧张!毕业作品没有规定写什么体裁、篇幅多少,只有一个要求,返校报到时把作品交给系办公室。这就是徐怀中的风格,举重若轻,欲擒故纵,把压力甩给大家。一年半下来,他心里明镜似的,谁不想把这一年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学以致用,来它一个总爆发,露它一手,放它一炮——至于怎么露,怎么放,大家心里还没数吗?莫言在前面走着呢……
我当时因搭上了莫言的快车道,俨然摇身一变为青年批评家,毕业作品写一篇论文是必须的。但是写小说的梦想就这样放弃了?似乎心有不甘。于是从春节到三月份,整整用了一个半月,整出了一朵“奇葩”——赣西方言小说《地牯的屋·树·河》。三十多年后,江西文学界进行回顾时,还中允公正地评价道:“朱向前受到新时期文学创新的精神鼓舞,大胆尝试、艰辛探索,用赣西方言写出了小说《地牯的屋·树·河》。作品在1987年《青年文学》4月号隆重推出,并同期配发了文学系首任主任徐怀中先生的评论《探索性的,又是深思熟虑的》,随即又被《小说选刊》7月号转载,并入围1987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最后一轮。虽然最终铩羽而归,但是,该小说不仅首开用宜春方言介入新时期文学创新的先河,并以一朵绝对奇葩的风采挺立于80年代文学寻根之潮头。”
再说论文。当时我心说,小说就算告别演出吧,咱看家的还得是评论呀,评论家的气质必须拿捏得妥妥的。4月份倒真是憋了一个大招——把一年多来深思熟虑的一个“理论发现”——军门子弟与农家子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创作之异同撰写成文:《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该文由《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隆重推出,成了我荣登此刊的第一篇正式论文(此前上过一篇笔读和一个短论,都还不足为据),也成了此后一个阶段内我的军旅文学批评和部分青年军旅作家创作的重要参照。
过了五一劳动节,到了“驴友”的约定时间,该岀发实习了,问题也来了——按上学期末系里通知,实习时间一个月左右,自选方向,自由组队,差旅费凭票报销(团以下干部不能坐飞机——同学中只有李存葆到了团级)。条件太宽松了,太优渥了。我第一个报名新疆——要跑就跑一个最远的地方,不跑白不跑。跟着就有李荃、刘宏伟等五六人報名新疆,系办公室指定以我为领队……我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还有点号召力。殊不料,过了一个年,全都“叛了变”,各有各的理由,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反正,没有一个跟我去新疆的了。我心说,不去是你们的损失,我还是我,我还非新疆不去了!正要打点行装出发时,还真来了一个小插曲。这事跟我爱人有关。
我爱人张聚宁,时任江西省宜春行署文化局长,是全省数得着的最年轻正县级干部,已经列入了好几个后备梯队。这不,好事又来了,省委组织部通知她做好准备,九月一日上中央党校青干班,学期一年。怎么办?莫非我毕业刚要回来她又去北京?要不然我也找个机会看能不能先留北京?灵机一动,我提起笔来就给徐怀中主任写了一封信,说了一下原因:爱人进京学习;提了一个请求:本人愿在任何一个驻京部队从事文字工作。第二天把信往军艺文学系一寄,我便出发了。我的目的地是新疆,是南疆喀什,一不做二不休,我要走就走到头,单枪匹马,勇闯天涯。
回到北京,屈指一算,时间紧迫。坐火车到乌鲁木齐就要三天,往返六天,来不及了。我当机立断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坐飞机!无非就是机票自理呗,虽说单程500多元在当年堪称巨款,但借机开个洋荤也值了!没想到,有了这一个第一次,就将带出来一串第一次。我赶到东直门购了票,直通机场的大巴刚开走了,如等下一班还得一小时,又是一个来不及。怎么办?坐出租!单程40多元,贵是贵了点,但不是又开了一个洋荤么?值!
待我慢嚼细咽了飞机上的免费午餐之后,就品着免费的西湖龙井,双肘支在小桌板上点燃一支烟——那时我还是一天一包的标准烟枪,那时飞机上还允许抽烟——此后再无此待遇了,俯瞰窗外蓝天如洗,一朵朵白云之下,西部群山绵延,一望无际,真是心旷神怡,感觉到了人生巅峰。
当日傍晚7时许,飞机降落乌鲁木齐机场。当同机乘客全部走完了,我还没有看到周涛。
周涛,著名西部边塞诗人,军旅诗坛大将,我虽不认识,但神交已久——我曾多次拜读他此前的诗作,散文《蠕动的屋脊》等更见奇气,堪称妙品。当时我是托新疆军区创作室评论家周政保与他联系,请他关照朱氏新疆之行包括接机。他也都答应了,但他却没有来。
我跟了一个便车,自己找到军区招待所住下了。洗漱之后,约9时许,正是乌市吃晚饭的饭点。我信步军区大门之外,寻入一巴扎,找到一烤羊肉摊前坐定,要了40串羊肉串,2瓶啤酒,开始撸串。不夸张地说,这是我此生吃过的最美大餐,妙处难与君说。
虽然当天傍晚周涛没去机场接我,但我并不在意,一是我们原本就不认识,只是托了周政保的关系,他没接我是不给周政保面子;二是周涛已是诗歌大咖,我至多是文学新人,而他还不一定认可,他讲究的是实力派,这个我懂;三是我独闯新疆,目的地还在南疆,这人生地不熟的,有问题我找谁去呀?不是还得找周涛嘛。
翌日早饭后,我寻寻觅觅,径直找上了周涛家。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年方40的周涛英气逼人,但说起头晚接机之事,略有尴尬,我哈哈一笑,就算过去了。不冷不热地寒暄了几分钟,突然之间话题就跳到了莫言身上——应该是因为说起了《红高粱》,可能周涛刚刚看过。一般情况下,我不是一个善于聊天的人,但只要一说到文学,特别是说到莫言,那就算打开了话匣子啰,主要是他问我说。周涛是智者,又善于倾听,加上他长期偏于西北一隅,比较闭塞,他有点信息饥渴感;此外,以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一年半的学习储备,聊文学、聊莫言,可以说都是上好的话题,他听着还受用。而他每日与博格达峰对视,所获得的神示一样的有关人生和艺术的感悟,也不是一般课堂上能听得到的。我们的投缘是一种相互的激发与吸引、碰撞与启迪。就这样,我上午9点进的周家,下午9点出的周家,中饭晚饭都吃在周家。不可思议吧!事后连我自己也觉得匪夷所思,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一连聊了整整三天!好像我此番来新疆就是专门来找周涛聊天的。那真是聊得天昏地暗,乐此不疲,具体聊了什么早都不复记忆了,但彼时彼地我们对文学的热忱与激情由此可见一斑。这在我的交友史上也绝无仅有。
聊了三天既无疲倦也不厌倦,只是时间确实不够了,我的目的地还在南疆的喀什呢。刚开始两天,周涛老说不急,路途太遥远了,一千五百公里,要坐三天长途汽车,太辛苦了,等我给你找个便车吧……等聊到了第三天下午,他也绷不住了,怕耽误了我完成实习计划,同意我翌日坐长途汽车去喀什。他交给我两封手札,一封给他的大学同学时任喀什公安局长的柳耀华,请他帮忙解决交通工具,争取把我送到红其拉甫口岸;一封给喀什文联某主席,主要请他给我安排一场讲座,原话大意是:这个小老弟肚子里有油水,要好好榨一榨他,不要轻易放过此人……我把此二信札视为周涛从心底里认可并接纳我的通行证。
翌日一早,我终于爬上了一辆去喀什的长途汽车,坐在最后一排最左边,还好有半个窗户透气。它的一切的脏、乱、差都在预料中,唯一没想到的是,脚下软乎乎的总踩不实在,到底怎么回事?待人们都把大小包裹从空中放下并逐一落座后,我才能弯下腰看清楚,原来瓜子壳和香烟头在下面铺了一层,足足有两寸厚。这得多久没清扫啊。但这一切都没妨碍客车在烟雾弥漫和欢声笑语中欢快地前进。当地朋友的乐观情绪也感染了我,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他们的笑声不用翻译,而且极富感染力。况且,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曾反复深入福建闽西山区采访,坐简易汽车跑简易公路是常态,早就练出了半天不喝水不撒尿不说话的过硬功夫,现在跑在这广阔平坦的大路上,只感觉到了一个爽字。
真正突破我认知的是晚上住店的情形。
为了将三天的路程两天跑完,司机师傅两头抢时间,早上7点出发,下午9点收工。車子在一个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拐进了一个围子里面,像是一个小学校操场,围墙口外有一个小餐饮店,每人吃完一碗羊肉面天就向黑了。司机大喊:住店了,住店了!人们跟着他复又进了操场,走到一排平房的门口,他大脚一踹,人们往里一瞧,只见一枚15瓦的灯泡散发出昏黄的光,照着一间足有一百平米的教室一般的房间,里面贴着两边的墙筑了两长条炕,均匀间隔一米,摆放着一坨坨黑乎乎的被子,用手摸上去,厚厚的、潮潮的,还有点滑腻……司机又喊道:住店的5毛一个哈。有人嘀咕:这能住吗?我们不住,我们要回车上去……司机又说:车上过夜3毛一个。忽啦啦一伙人复又涌上车去,过一会儿,又有一半的人退回来了。这时天已黑下来,困劲也上来了,由不得你不睡。我交了5毛钱,走到最里边,挨着被子和衣躺下。刚迷迷糊糊要犯困时,起风了。风越来越大,很快就随着风声起伏,听到头上哗哗的响动。赶紧打开电筒查看,原来在天花板的高度上,用尼龙绳拉成的网格托了一层报纸,就权当是天花板了。这时风一吹,沙子便落下来,我只好脱下上衣反过来蒙在脸上。在风声中,细微地感到沙子落在报纸上、衣服上、脸上,还是睡着了……我终生难忘这次住店的经历。
到得喀什,入住地委招待所后,速将周涛手札送到收信人手中。柳耀华局长很重视,在得知我想去红其拉甫口岸后立马就告诉我,每周只有一班车,你等不及了,这样吧,你留下电话等我通知,我来帮你协调车子……文联某主席看了周涛的信,只是对我笑了笑,说:“我尽量给你安排一次讲座吧……”
一早就得到了柳局长的信息,喀什市外经委有一部日产巡洋舰要上红其拉甫口岸接巴基斯坦外商,后排有空位可以带我上去,但回来时有外商,就不能跟车下山了。去不去?去的话半小时后车来招待所接我。我二话不说,半小时后带了一件外套就上车坐在了后排。
红其拉甫位于帕米尔高原,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县境内,海拔5100米。从喀什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县城300公里,从塔县再到红其拉甫口岸100多公里。在内地这绝对算得上是长距离,但我刚从北京飞了近5000公里到乌鲁木齐,又坐了1500公里长途汽车到喀什,深切感受到了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1000公里以内在新疆不算长途。而且又有巡洋舰这么高大上的越野车,再加上一路大道辽阔平坦,就更有观景心境了,只觉得满眼都是风光大片,痛惜没有带相机!
不料跑了200多公里后,路况出问题了,一打听,方知前方在修路,如若继续前进,只能脱离公路主干道,进入与路伴行的河道。好在河床裸露,基本没水,但由无数大小不同高低不一的鹅卵石铺就的“路基”实在是太颠簸了,车子就像一个喝得酩酊的醉汉,左右摇晃,高低跳跃着以大约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顽强前行,让人在内心深处佩服这车的抗造性。前面4人不时地发出惊叫,足可以据其音量大小来判断车子底盘下面“路基”的状况。坐在最后一排的我,屁股不能挨座,只要坐实了,就随时可能伴着车子一个大跳,脑袋咚地一声撞在车顶棚上。有一阵子搞得我手足无措,无所遁形,几乎被撞得头昏眼花。好在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窍门,即双手伸开抓住两侧车窗上的把手,将身体提至悬空,屁股始终和座位若即若离地保持15厘米的间隔,完全用双手和双脚来支撑身体并调节缓冲车子的颠簸,达到人车一体,自动减震。如此一来,双手吃劲,但身体获得了自由,颠簸能奈我何?就这样,我利用这种独一无二的“双杠式坐车法”坚持了一个多小时,熬过河床路。车到塔县时,暮色四合,天已向晚。因海拔超过了4000,双臂酸胀疲劳,加上大脑缺氧,草草洗漱,倒头便睡,一夜无话。
第二天上午我们轻松抵达红其拉甫口岸,结果又大出意外:巴基斯坦商人因故未来赴约,外经委同志准备即刻原车返回,征询我的意见,是否继续跟车,如果不跟那么就此别过了,也就是说把我放下,什么时候再有车拉我下山就只能看运气了。环顾四周,此处除了口岸,和远处的一个哨所、一个雷达站之外,别无所有。见我一脸纠结,他们又开起了玩笑:你面子好大呀,我们为你上山不光派了专车来,还派了我们做陪同,你要不跟车走,我们的任务就没完成好呢……虽说是玩笑话,但道出了实情,此行我成了最大受益者。我也不能不识抬举了。在他们的注视下,我走到口岸边伫立片刻,再默默远眺了一下著名的红其拉甫哨所,就算是到此一游吧。
回到喀什又是晚上。
翌日,终于有一段放松的时间了,看清真寺,逛大巴扎,领略一下南疆风情,买了两把著名的英吉沙小刀……身体放松了,心里却不知不觉又紧张起来。喀什文联主席上午就通知我,已经为我安排好了晚上的讲座,文联人太少,专门协调了喀什师专中文系的师生,颇费周章。下午7点半来招待所接我,其他问题见面再聊……电话中我已听出了主席的一些话外音:安排此讲,纯属落实周涛信中所嘱,你小伙子面子好大哟……讲什么呢?怎么讲呢?这毕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讲座,我有点心中无数,有点小激动、小兴奋、小紧张。我早早回到招待所午休,养精蓄锐。
下午7点半,文联主席领我出门,走出了招待所小楼,也没见到一个随员,比如办公室主任啥的,我们在一辆自行车跟前停住了。这是啥情况呀?文联主席开腔说:朱作家,不好意思,我请你就近去吃个便饭,单位也没个车啥的,这样吧,你上来,我驮着你,好在不太远……我急忙抢过自行车龙头说:主席,您是老前辈,您坐上去,您指路,我来……就这样,我骑着讲座主持者的自行车并驮着他向着讲座地骑去,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讲座之旅。
9时许,我们赶到了一个我始终没搞清楚的什么单位,找到办事员,被告知场地临时调整了。到了会场,只见两个人正在打扫卫生,尘土飞扬。到了预定时间9点半,又有人告诉主席,喀什师专的车还在路上……整个过程,都显露着人们对这个即将开始的讲座的不热情、不欢迎,甚至是不耐烦。
9点45分,当那个小一百人的会议室基本坐满之后,文联主席开始了主持。在他介绍时,会场仍被一片嘤嘤嗡嗡的杂音所笼罩。但这时,我的心中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紧张了,有的只是一股难以抑制的演讲甚至是辩论的冲动。
我忘了怎么开的头,但反正没有按设计的套路来。开言三分钟后,全场变得雅静了。在这个暮春的西部边陲小城喀什,我恣意地与大家分享着新时期中国文学大潮的壮丽景观。很快就来到了11点半,听众刹不住车了,问答阶段更加热烈。12点时,文联主席抢过话筒强行结束,他激情洋溢,与主持开场时判若两人。他最高调最夸张的结束语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同志们,同学们,我们今晚见证了一个著名评论家脱颖而出的历史时刻。以后跟人聊起朱向前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自豪地说,我听过了朱向前的第一场演讲!
这时候,文联的摄影师背着相机钻出来,“咔嚓咔嚓”一通猛拍。大家簇拥我下楼,我正寻思着,这下是我驮他呢还是他驮我?结果出门一看,一辆黑色桑塔纳横卧门前,主席带着两个随员护送我上车,送到地委招待所。待他们走后,我又独自出去就着啤酒撸了20串烤羊肉。那才叫一个爽啊!
翌日下午,柳局长请我吃了一个便饭便安排车子把我送到了喀什机场。虽然飞机延误两小时,夜里11点才到乌鲁木齐,但我相信这一次周涛肯定会在机场等我。果然。上车后,周涛说了一件事:昌吉市文联拟请他去作一场演讲,咱们俩一块去讲如何?这样的好机会和好队友,我自然很心动,但是我实在不能再待了,急着要回北京返校报到了。
当我提前5天回到系里时,却不由地大吃一惊,多数同学早已经回来了。我问他们都在干吗呢?答曰联系留京啦、留校啦。我稍一打听,就基本有数了,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创作室是第一选项,差不多有一多半同学——比如我同宿舍的李存葆、李荃、苗长水三位,来自济南军区,这次都一块进了军区创作室。另有几位京外同学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有几个留在系里了……哦,还能留系里吗?我心想怎么没早想到这一步呢,给徐主任的信也写得太晚了……咱就别吭声了,就当啥事也没发生过,翻篇吧,该干吗干吗。我正在宿舍里听同学们讲八卦时,系秘书林晓波来敲门了:朱向前,你到赵副主任办公室来一下。同学们都怪异地瞪了我一眼。
我刚刚知道徐怀中主任已经升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了,此刻系里工作由赵羽副主任负责。他笑眯眯地问我:你是不是给徐主任,不,徐部长写了一封信?
哦,我不了解情况,考虑不周,给领导添麻烦了,我……
不,我现在代表系里正式通知你,你留系当老师了!就在前天,就在这间办公室,徐部长拿着你的信,请胡可院长、魏风政委一起当面商定的。祝贺你,向前同志!
幸福来得太突然,我不知所措,有一种缺氧或者醉氧的眩晕感。赵副主任又说道:后天徐部长就要下部队去检查工作了,你是不是抓紧时间上家里去看看老主任?
徐主任、徐部长他家住在哪里啊?
在总政歌舞团,来,这是门牌号……
就这样,徐怀中把我留校了!
留校以后的多年间,我会偶尔翻出珍藏的“留言布”来摩挲——“留言布”谐了“留言簿”的音,它就是一块朴素而别致的30厘米×50厘米的小白布,但却充分体现了徐怀中的个人风格和匠心,体现了徐怀中对弟子们的深情和厚望。它是专为1985年12月25日圣诞节晚会设计的,全系师生和员工人手一块,用于晚会上相互留言——考慮到第四个学期是实习,大家实际上把这个晚会当成了毕业晚会,把这个留言当成了临别赠言。大家写起来都非常认真,觉得一时措不好辞的,还留到第二天甚至下一周再写。徐主任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他在我的留言布上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句:我一想到你,就记起你在文学系第一次讨论会上的发言。
随后,钱钢马上就跟了一句:你的成功在于选择。莫言倒是十分慎重,先写了一句鲁迅语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第二天又把布要去补了一句:足上又加聚宁嫂。
这块留言布上这些饱含师生情谊的金玉良言,伴随我度过了漫长的军艺岁月。
实际上,除了徐怀中主任,还有赵羽副主任,还有吕永泽、冉淮舟两位老师和林晓波秘书、刘毅然参谋,他们都见证了我在文学系的成长。此后的岁月里,我也努力向他们学习,传承文学系的优秀基因。比如在不拘一格招人才方面,我学习老主任,在打破常规方面,也创造了两个纪录。一是第四届的学生柳建伟,是第三届的阎连科向我推荐,推荐的作品是一篇万字评论《伟大的夭折——评<古船>》。评论家不好找,文学系自第一届至第三届,学生总人数已过百,但从事评论者仅我一人。阎连科带信来说,柳建伟是通讯工程学院毕业,已获得学士学位,这个大专上不上,他还要考虑考虑……这也许是柳建伟的欲擒故纵之计,但是我已经沉不住气了,立马写下了苦口婆心劝柳建伟上学的信,请阎连科传递。大家都知道,历届文学系,特别是前六届干部班,都是打破脑袋往里挤,只有柳建伟是一个例外,是被朱向前写信动员来考学的。这算是创造了一个纪录。
第二个纪录是第六届的余飞创造的。他的报考作品是中篇小说《老虎脸排长》的打印稿,也就是说他报考时还没有正式发表过作品——而两部公开发表的作品是报考前提,也是底线。但是我从这部打印稿中看到了余飞可以预期的潜质,于是就力排众议将他招进来了。结果余飞是个典型的大器晚成者,此后二十多年我一直默默地关注着他,总是在检验自己是否判断失误。一直到了前两年,两部由余飞总编剧的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巡回检察组》横空出世,我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在文学系前后13年,和文学系一道成长,尤其结合自己的评论专业,为以后的著名学员如阎连科、徐贵祥、麦家、柳建伟、石钟山、赵琪、陈怀国、李鸣生、余飞等人的脱颖而出锦上添花,从推荐作品、撰写评论到作序,无不竭尽绵薄之力。
【作者简介】 朱向前,著名文学评论家;1954年1月出生于江西宜春,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著有《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莫言:诺奖的荣幸》《军旅文学史论》等专著、文论集二十余种;主编《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现居宜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