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气氛转向”的美学批判潜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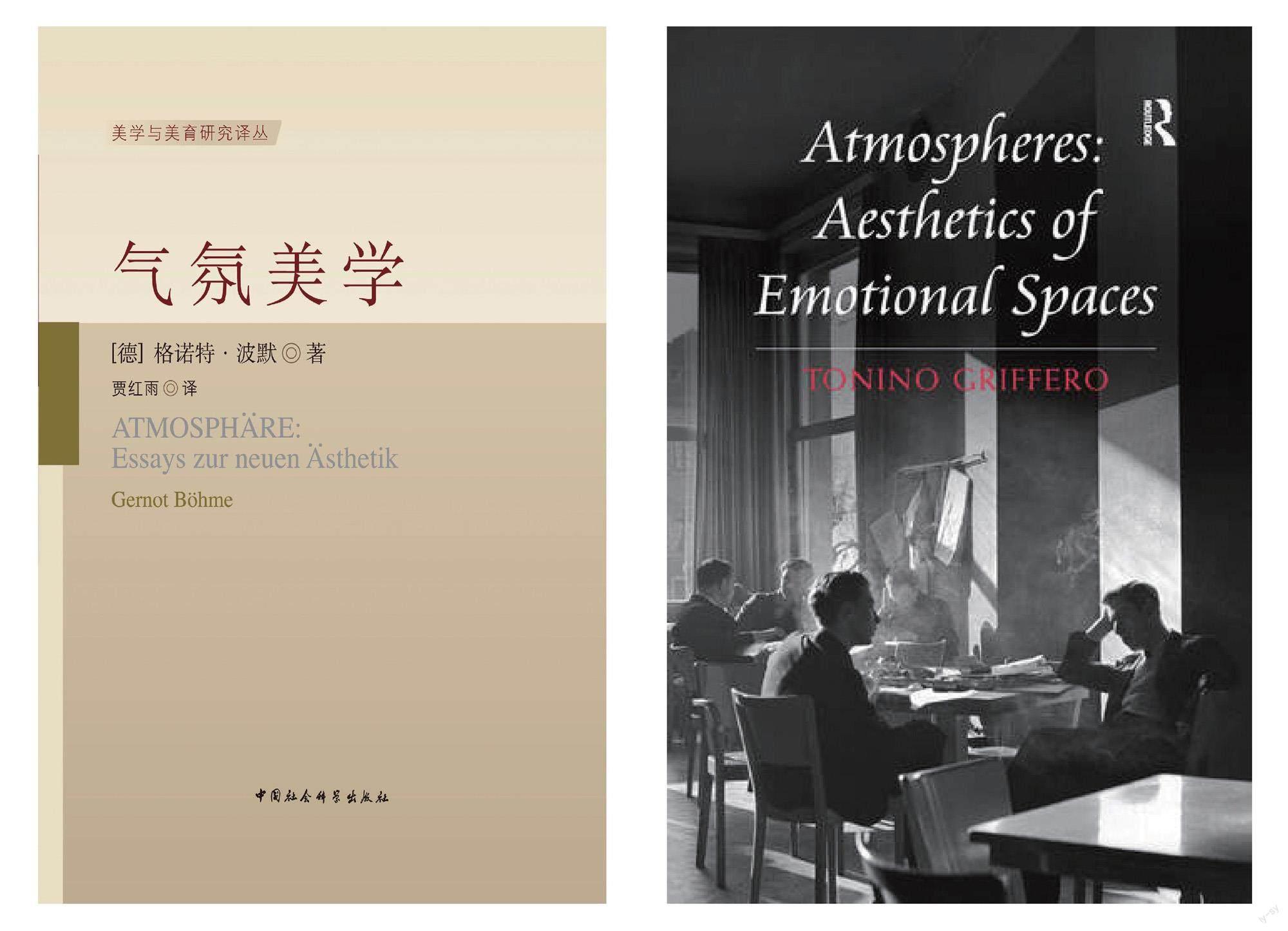
摘 要:在西方视域下,以“气氛”为转向的美学批判潜能,聚焦于美学领域。气氛美学重新审视西方的主流美学——判断美学,强调复兴美学的初心——感性学,把具有间性和准-物特质的气氛作为美学的本体论,将自然生态学纳入审美活动,将美学延伸至社会批判领域。
关键词:气氛转向;感性;美学批判;社会批判
气氛美学的美学批判潜能首先针对的是对审美低级领域的辱骂,并指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合法性。只有在美学层面的祛魅,才得以将审美眼光延伸至日常生活之中,将气氛作为工具加以利用才得以合理化。至此,在美学层面的批判潜能仅仅针对的是美学本身,甚至对审美傲慢的批判[1]30。以气氛作为根本概念的新美学回归到美学古希腊词源“aisthetikos”(表示“感官的”或者“感知”的意思)的最初意义上来,在以往对美学感性的扼杀和对理性的吹捧双重作用下,气氛美学对以理性作为审美判断标准的美学的批判是一种对传统美学作为感性学原意的回归。对以崇尚理性判断力为主要评判标准的美学来说,审美工作是对美背后深层理性符号学的挖掘,而非是对美这一事物或者气氛的体验和感知。以往的审美工作也仅仅是对高级艺术的评鉴活动,并不下放到日常生活乃至自然环境之中。气氛美学为代表的新美学对传统美学的反戈一击,正是对美学本意及传统美学的反思性继承。
一、美学本体论转向气氛本体论
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哲学阐述,美学本体论是企图寻找一种具体的事物或者概括抽象同一性概念来说明美的形成过程及其变化的原因。在18世纪之前的西方美学界,对美的本体论研究是处于主流地位的,而在18世纪之后逐渐式微。对西方美学本体论的研究方式主要采取的是哲学思辨,对美的本体论研究就是源于哲学本体论研究。在美、艺术尚处于萌芽时期的希腊、罗马时期,所谓“美”(kallo)并非只是用于人、物的外观或者自然对象、艺术作品发展,而是蕴含着道德论、精神层面以及广泛的学问、文物等人类活动、产物[2]。古希腊思想家认为世界是由某种元素构成的,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找到具体元素来阐明世界的本质。柏拉图在《大希庇亚篇》中记录的苏格拉底与希庇亚的对话并没有直接回答关于美的本质性问题。但是,苏格拉底提及美本身是超越现象和感觉的真实客观存在,苏格拉底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以及主张“智慧就是美”。柏拉图是最早注意到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审美现象、探讨美之所以为美的本体论原因的思想家。并且柏拉图认为“美”是一种隐藏在事物之中的元素,是真实存在的事物。在柏拉图之后,追求美的本质之时,实际上是从现象的视角出发逐渐过渡到超越性的、形而上学的领域,同时,对美的本体论认知也由具体的个体要素转变成抽象笼统的概念。
在西方哲学甚至美学的视阈下,直到18世纪中叶,德国的哲学家鲍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方将希腊语言中意为“感知,感性”一词作为“美学”这门学科的名称,所以自鲍姆加登之后,美学正式作为一门学科和一门学问问世。美学一科的产生缘由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内在的思想发展来看,18世纪是经验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哲学家们纷纷将视野转向人们的美感经验,并且探讨美感与主观性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是在18世纪时期,强调主体性已成为哲学史上的重要改变,从古代的比较重视客观性的哲学,发展到近代之后,主观性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变得愈加重要。主观性使得我们在讨论美学的时候,关注对象转变成关于对美感和人的体验这方面的感知。这两方面的进展使得美学逐渐成形。美学发展的外在缘由是18世纪早期博物馆的发展。欧洲多数博物馆收藏了许多脱离原本历史文化背景的艺术品。在此类情况下,鉴赏者只能更加仰赖自身的美感经验。这些艺术品脱离了它原先的文化脉络,变成一个孤立的艺术品。任何一个进入到博物馆的人都是暂时脱离了原本的文化内涵欣赏艺术品的,他们对这个艺术品所知可能不多,感官所能纯粹捕捉到的就是这个艺术品的形象,也就是这个艺术品的样子外形。所以多数鉴赏者只能够用视觉所看到的感性的形象,去感受这个艺术品。那么在这样一个外在的条件下,我们渐渐地就会从一个独立的纯粹就外形的欣赏来谈对一个作品的感受。美学学科的正式确立是对传统美学本体论的批判,是美学注重本体到过程的转变,具有超出美学本身的意义。
在美学作为一门学说被大众接受之后,针对“美是什么”的本体论讨论也在由关注美的具体存在转向对美的认识和体验之中。在气氛为代表的新美学之前,对实在事物的审美化早就开始,在强调事物美的同时,相关艺术评论对事物的评价都是基于对美的判断以及对美学相关品味高低进行审判。例如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其《品味的标准》一文中便提出了品味的“五项标准”,即敏锐的感官与想象力、练习与实践、多方比较、排除偏见以及健全的感官。休谟并不否认审美品味有高低之分,甚至还提出了自己的划分标准。
20世纪中后期生态自然美学兴起,新美学的代表格诺特·波默(Gernot B?hme)认为迄今为止的美学实际上多数是判断美学,以往的美学很少涉及人的自身感性经验,也很少是对美学古希腊感性传统的回归。美学不再是纯感性的经验分享,而逐渐变成了判断、言谈和对话。最晚从康德开始,美学涉及的是评判,即鉴于美和崇高的判断能力。康德企图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来调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美学在康德的解释下归属哲学一个系统之中,它是通过人的能力的级别来规定的,这一美学被冠以“判断力”之名。针对康德以来的审美判断及当代美学艺术的概念化、去感性化倾向,波默试图在鲍姆加通感性认知与理性认知的框架下重新建立一门普泛的感知学。这感知学在以气氛作为情感空间下的居间体所被人察觉。所谓“新美学”就是对鲍姆加登美学最初设想的感性学的再次复兴。
总體来说,迄今为止的美学因其感性内容过于缺乏,情感的参与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估,并不是鲍姆加登意义上的“感性学”或者是波默提出的“感知学”。以往的美学它们更多地是作为智性的判断标准,而不是感性经验的交流,缺乏对人的身体性和情感性的体验和研究。判断美学并不强调身体性在场的切身体验,而强调对艺术作品符号化象征意义的解读。原本抽象的甚至是无对象的图像艺术导致的对其本身蕴含意义的消解,符号化的图像概念不断被提及,失去原本艺术本真的审美品格,那些不可言说的图像艺术,新美学尝试将气氛引入到对艺术的品鉴活动中,不仅仅追求艺术的符号化象征意义,而更多地是让受众感知到艺术渲染的气氛空间中。通过感知者所处的环境,我们的身体所能感知到的是情感的弥散。
气氛,即从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生产美学以及接受美学两个方面来看待气氛存在的本体论。波默对气氛的论述以气氛的存在为切入点,认为气氛是处于主客体之间的“居间位置”,因此,这一重新划分将打破原有二元论的简单切分,美学开始考虑到“居间”这一模糊地带。一方面就其客体而言,“气氛仍是某种似物的东西”(etwas Dinghaftes)[1]22,另一方面就其主体而言,“气氛是似主体的(subjekthaft)东西”[1]22。某种程度上,波默所强调的气氛存在于主客之间的区域,虽然使得气氛摆脱了二元对立的窠臼,但对气氛本体论的证明还是保持从主体以及客体的角度出发,使得气氛的存在仍处于传统的方法论之中,居间的特性首先保证的是主客双方的在场。因此,气氛的存在状态或者说是对气氛的本体论探讨都要直面气氛的居间属性。气氛的居间属性并非只是特指气氛居于物理空间中的居间。而是“气氛的本己的存在方式”,气氛本身就是居间,气氛之所以成为气氛,是“得以存在论规定”的[3]73。因此,气氛的居间性正是气氛能成为“准-物”的保证,居间性才使得气氛拥有物的部分客观物的属性。
在新美学的视阈下,气氛就是具有某种非理性、无法言说的东西。对居间气氛的感知转变成为对身体性在场的印证,也正是因为身体性在场的参与,感知对象能够注意到情感的触动,情感空间中的气氛才能被感知。波默所提倡的气氛美学以赫尔曼·施密茨(Hermann Schmitz)的新身体现象学为基础,施密茨对气氛的引介是现象学式的。更进一步说,施密茨对气氛的解释涉及情感的历史。他认为客体的领域透过知觉的实证而成形,主体的领域因“情感的内在化”及“心灵的构造”而产生。气氛概念的提出是对自然科学以及理性主体的批判,气氛不只是主观层面的,而是一种“客观的情感”。施密茨的新现象学连接了身体和气氛,使得气氛与身体在情感空间中融合汇通,身体现象学视阈下的气氛概念认为作为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的现象,打破了原本占据主流地位的二元对立,这一居间的现象着重强调气氛的内在情感性以及气氛的外在感染性。它着重讨论气氛的空间特性,在空间中,气氛是没有边界的,涌流进来的,同时还是居无定所的,也是无法定位的,它是情调的空间性载体,例如音乐会上的情绪激昂。情感的波动侵袭着植入身体空间下的气氛,使得个人能够感知到情绪的弥散。这种对传统判断美学的摒弃的新美学显然是通过人或物身体上的在场,也即通过空间来经验的。气氛所代表的新美学就是在日常经验相联系,不是判断性的美学,而是注重对美感体验和情感感知的新美学。
为了强调气氛的存在,主客二元论也就被改写成为三元架构,也即形体、身体以及精神构成一种新的主体性范式。在此基础之上,波默的气氛美学突破了原有的主体范式和西方主流物论,而将气氛作为一种空间,这一空间是被“物”与“人”的“在场”及“外射作用”所“熏染”的空间,透过使“物”周围的空间充满张力和动态,“物”向外的散射使得感知者对“物”的“在场”有所感觉。由此可见,气氛不是独立飘浮在空中的,而是从物和人,或者是存在于物和人两者的各种组合中所生发出来的形成的“准-物”。
二、艺术哲学转向自然美学
早在美学建立之初,鲍姆加登就将美学与艺术进行捆绑,而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则是直言审美存在就是“美的艺术”,美学对象的范围狭小化也正是因为美学与艺术的过度绑定而导致的。这一趋势对美学研究对象的限定在康德发展之后成为一种主流趋势。黑格尔在《美学》三卷本中曾说美学的范围就是艺术,或者说是美的艺术。黑格尔将自然美和艺术美相区分,并且将艺术美确定为是“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抬高了艺术美的地位,自然美则成为冷遇的对象。与此同时,黑格尔认为自然并不包含和归属于美的范畴之中,而只有在艺术品之中复现的自然才是美的,外在的自然总体并不能包含在美学的认识对象之中,而更多的是将美学的目光专注于艺术品中的“拟像”自然。在此种种前提之上,美学的名称被艺术哲学所取代。自然这类不属于人类艺术创造的范围之内的对象就被割裂出审美活动之外。艺术在谢林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的至高位置一脉相承,无论是谢林的美是“被实际直观的绝对者”还是黑格尔主张的“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4]。美之所以呈现出理性,都是因为美的感性存在是以理性为前提而规定的感性,艺术哲学就是将审美这一感性活动包含在哲学理性的框架下进行呈现和认识。哲学对审美活动或者是艺术的加工使得美的感性层面成为被人舍弃的存在,而艺术哲学这些理性层面的认知则成为形而上的存在。
康德对美与艺术的结合在强调艺术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中与黑格尔泾渭分明。康德强调“美的艺术是一种就其同时显得是自然而言的艺术”时,其核心意旨便是要通过艺术与自然的关联来让审美领域中的规则以新的方式呈现[4]。虽然康德认可艺术理性的中心地位,但是康德对美的引进,借助与审美的关联尝试将艺术落实于感性基础之上,改变了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康德的这一创举将美与艺术结合起来,艺术不再仅仅作为理性的代言人而存在,美的参与使得艺术可以被人感知,在感性活动中探求理性的存在方式动摇理性的确定性根基,对艺术的审美活动的感性认知也在为艺术将自然的纳入打破了壁垒。在18世纪,鲍姆加登对美学作为学说的开启回归希腊原意之时,感性思维的独立以及审美建立在感性活动的基础之上,自然也逐渐被纳入到美学领域,成为美学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罗纳德·赫本(Ronald Hepburn)开创性文章《当代美學对自然美的忽视》中,他指出通过从本质上将所有美学还原为艺术哲学,分析美学实际上忽略了自然。通过对自然的关注,赫本证明了可以对艺术世界之外的世界的审美体验进行重要的哲学研究,因此,为环境美学的纳入审美范畴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奠定了基础。
波默的气氛美学正是在对生态危机所产生的根源批判反思中逐渐成形发展的。生态美学只是作为自然科学社会性的一个维度,它致力于人类环境的审美特质。在他看来,气氛概念已然成为生态美学的核心概念,气氛促进了客观的环境条件与人们在这个环境中的感受,在身体为核心感知的自在自然的基础之上,气氛美学对以往判断美学的批判性主要关注点聚焦于身体以及感知性这一层面。
波默的自然美学包含两大类:人与身体以及人与自然环境。“身体”(Leib)成为关键的概念,可以说我们是基于身体性在场的生态学视角来考察气氛美学对以往艺术哲学的批判性。在波默的语境中,身体并不是指向简单的肉体,而是带有现象学和存在论意味的身体感,是一种自我经验。施密茨在其著作中就曾区分过“Leib”和“K?rper”(“身体”与“躯体”)的概念,后者是通过五官接收信号的被动的器官性存在物,前者是通过整体性的情感反应觉察到自己在场的此在[5]。存在着不同身体器官之间的通感来感知气氛的在场,通感上的体验立足于身体性的张力,这一具身性正是梅洛-庞蒂所言的身体是“在世存在的载体”。气氛不仅是具身的知觉场、具身的境域世界,还是具身的现象空间,或者说是作为具身域的现象空间即是情感气氛空间[3]100。这样的身体是具有开放性和场域性的,气氛的生产也在以身体作为空间形式中被感官所捕捉,气氛是知觉的第一对象。
从艺术哲学过渡到新美学,这一转折通过对气氛的引介从而将感知者的身体性在场推向关键性的地位。感觉是具体的,理性抽象地探讨感觉经验的思路是不适用的。普通感知学为支撑的生态自然美学理论始终将人的感觉经验放置在核心地位,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美学学科创立之初的宗旨。进一步说,生态自然美学是对美学的延伸,将自然从理性的数据考究中解放出来,纳入到感性的审美体验之中。它致力于向感官经验领域全面开放,以身体的感知为基点,将人的感知放置在周遭环境和自然之中,以此来重建当代人对自然的多样化体验。在生态自然美学中,占据重心地位的不再是充满理性意味的趣味判断或保持间距的审美认知,而是人们在特定自然环境中的体验所形成的身体感官经验,以及自然环境与人的感觉经验之间的互动关系。波默试图通过人與自然的融合,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的关系。在气氛与自然的关系中,身体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环,身体能够感知气氛,身体作为自在自然的一部分,是气氛能够被感知到的情感空间。显然,能够感知气氛的身体是自然美学中所要考究的重点,是将美学从艺术哲学转置到自然美学的关键。
在气氛空间中,身体所能感知的经验是感知者自我本身所创造的经验以及对自身感觉的认知[6]。在感知活动中,身体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媒介,身体所拥有的敏锐的感知力是一切感性活动的根基。身体作为自在自然,在身体这一空间便成为体验外部世界的场所以及自我感知的所在之处。波默对身体的阐述倾向于对身体现象的自身描述以及对身体所引发现象的感知辨析。例如对身体中的面相进行的探讨,波默认为面相涉及到的并不仅仅是隐藏在内在性的外在标志,更准确地来说是身体性在场的表达。面相或者说是面孔的出现,通过这一现象来加以认识该事物,这一认知可以被看作为某种在“感触”(affektiv)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的外在特征[1]194。由特定感知对象所引发的情感震颤让我们认识到自己身体性的在场,并且更为关注身体的自然属性。在审美活动中,通过身体所感知到的对象是在以“气氛”这一居间的方式存在。气氛是一种弥散在空间中的准-物,一方面,气氛与主观的情感有关,带有主观层面性质;另一方面,气氛是由客观方面的物所营造的,符合客观因素的属性。总之,气氛是介于主客体之间的东西,本身具有“关系”的属性。在居间的关系体系下,气氛可以通过身体性在场所感知,也可以通过物的属性加以营造。
而在意大利哲学家托尼诺·格里菲洛的笔下,“身体是气氛与其他准物产生共鸣的舞台”[7]25。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共鸣是身体通过客体或者是具身化的实体之间的互相交流实现的。感受中的身体是由多个“身体群”(felt-bodily isles)组合而成的,它们之间的空间距离能够引发连续的身体感觉运动。格里菲洛认为,感知中的身体机制所产生的持久效应会将“身体感觉群”遮蔽起来[7]26。眼睛所关注的对象会随着场景的变化转变视觉重点,在参与情感运作的身体感觉群中,感知对象并不拥有恒定感官位置,而是在这过程中,更为注重对体验的感知和对情感的捕捉。包括整个身体所能产生出相对和谐统一的知觉,也是得益于精细的知觉与原始感受力之间的微妙平衡。
概括说来,以气氛为本体论加以讨论的新美学中,感性元素的加入带来了对感知体验的关注度。气氛美学所代表的新美学是对判断美学转向哲思理性层面的反驳,在将美学从崇高的艺术作品中扩大到真实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甚至是身体的具身空间之中,审美工作的扩大化以及对审美范围的泛化是新美学之所以成为“新”的缘由之一。而作为自在自然的身体空间,在气氛的情感空间的熏染下也成为气氛美学关注的重点。气氛在这天然的身体空间场域之中能够被感官所感知,各个不同感官之间所能形成的通感以及在不同具身性之中形成的情感共鸣,都是对以往判断美学强调美学的精英主义截然不同。气氛美学针对的就是对审美气氛以及情感空间的营造和感知。
三、审美判断转向社会批判
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学成为对艺术和艺术品做出理性判断的理论学说,美学对艺术的批判导致了一种强势的审美判断标准:美学仅仅只是有关艺术的审美。它涉及的是本来的、真正的和高级的艺术,研究的是货真价实的艺术品和有声望的艺术品。就算是美学家意识到美的范围是广大的,美无处不在,但还是没有改变美学滑向艺术哲学的事实,尤其是对崇高的追求和对理性的强调。对于崇高的追求的反面,美学家对生活中或者是自然中的美嗤之以鼻,使得生活美学以及自然美学日趋边缘化。所有的创作都是在艺术的视角或者是对崇高的追求下进行的,以美为其标准来衡量艺术的高低优劣成为艺术界的共识。
现代主义观念的取消,使得康德和其门徒已降的美学传统的批判范围被拓展了。先前艺术与美学判断的绝对性被从社会和哲学角度而来的观点所替代[8]。这一视角的改变要追溯到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著名的短篇理论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雅明将艺术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仪式阶段、美学阶段以及政治阶段。在美学阶段,艺术作品不再同仪式程序相关,而是属于超验的、个人的,但在艺术机械复制时代中,艺术作品获得了政治形式,政治同时也获得了艺术展演的样式。这正是法西斯主义动员大众的重要手段。艺术从艺术美学转变成为大众文化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对艺术的操纵也是对政治的操纵[9]。原本属于艺术的原真性被机械复制大量生产所摧毁,原本附着在艺术品上的光晕(Aura)消失。本雅明并没有明说机械复制时代的大规模复制生产艺术的优劣,在他看来,光晕的消失带来的是机械式大生产的生产方式,但是艺术的原真性却在伴随着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普及的过程中逐渐消失,艺术的膜拜价值也在随着机械化大生产的兴起而付诸东流。在文化产业以机械化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如波普艺术(Pop Art)等大众文化普及之前,本雅明看到了政治审美化,他将生活世界的审美化作为一种严肃的现象加以讨论。波默所提倡的新美学在理论上实现了本雅明扩大艺术美学范畴这一视角的转变。审美工作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去确定艺术的高低,而是将范围扩大到自然美学和生态学甚至是整个生活美学之中。美的无处不在使得艺术品对美的独占条件并不成立。而在整个生活美学之中,强调美意味着关注对美感的体验以及对美的营造。审美工作在此范围下的主要任务一般被认为是对气氛的营造,在这一基础之上,审美工作的范围包括了建筑、广告、室内设计、舞台效果、政治宣传以及商品品味的宣传,甚至是之前的狭义艺术的审美也包含其中。
正是因为波默所提出的气氛在生活之中无处不在,美学的审美工作的普遍化与气氛的结合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加以利用。尽管美学作为一种软性权力难以抵抗和避免暴力的压迫,但是也正是因为气氛难以掌握,难以抵抗,方使得气氛的审美工作有着与生俱来的社会批判潜能。
气氛美学的批判潜能首先针对的是政治审美化,权力将自身场景化,统治权的布置打扮使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分更为明显,统治者通过一系列对权力的布置操控,并用此去影响被统治者自身对权力的认知。例如纳粹对艺术权力的把握而举办的“堕落艺术”(Degenerate-Art)将犹太艺术视为低劣艺术品,在权力伪装成艺术的同时,通过将当时的画作放置于不利的光线条件下或者将相关艺术品故意以倾斜的方式展览,利用审美效果来强化公众对犹太艺术家创作的相关作品的偏见认知。另外,纳粹对“堕落”艺术家的处决也并不是强权杀害,而是假借由头吊销他们的艺术家身份头衔,通过说服公众将他们排除在艺术家的行列之外,剥夺他们进行艺术创作的权利,以达到对艺术的干预。同时,希特勒所强调的是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在艺术界暴力权力的渗透使得强权主义的氛围在整个社会范围之内形成,对犹太人的排斥氛围,对审美领域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控制也在不断增加砝码。法西斯主义敏锐地通过美学手段以期实现政治权力巩固,并且通过气氛召唤来权力的自我场景化和权力的实施。政治审美化在大型庆典上的面孔的呈现和伪装,对社会情绪的把握,以及对社会气氛的营造都在不断加强权力宰制生命的力度。
权力的场景化不仅在纳粹统治时期表现明显,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部分建筑中。权力通过建筑制造出处境感受(Befindlichkeit)。建筑,比如说教堂的建造,营造出的是神圣或者是谦卑的气氛。建筑在以往都是处于统治权的气氛营造的枷锁中,并不是为了中立的态度而加以建立起来的,教堂这类建筑营造出的气氛侵入步入审美空间的感知者的处境感受。类似于教堂的建筑总体是带有某种政治性的,权力通过变装换转成为感知中的处境感受让人生畏。设计是审美工作的一部分,在设计师对外表和形式的制造活动中,也决定了感知者要以何种身体性方式来经验自己。
通过审美手段来实施权力,在经济领域转变成利用审美手段来实现资本的增殖。在此脉络下,美学包含消费文化、行销、广告等美学工作,波默基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性美学,将焦点聚集在“美学经济”上,形成了审美经济学。在审美经济学中,审美工作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大部分工作,并且审美工作不再服务于商品的生产,而是服务于商品销售的场景化,商品的使用价值无时无刻不被加以场景化运用,因为人们注重在大型超市或者购物商场的场景氛围。在审美资本主义时期,广告宣传推销的不再是简单的商品,而是生活方式。通过设计和包装以及对颜色区分的敏感性,商品被赋予其畅销的品质,这一品质不再简单依靠商品的使用价值来实现。再者,商品的销售环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商品进行价值的重新衡量。在本雅明的“拱廊街”中大面积使用了超出当时生产力的玻璃,将商品尤其是奢侈品放在透明的玻璃柜中进行展示,透明的玻璃目的是减少视觉负担,营造轻盈、没有边界的空间效果。将艺术展览中的玻璃运用在商品上,玻璃的阻隔使得消费者与商品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艺术品中的光晕复刻至商品之上,加速对商品品牌的形象塑造,使得消费主义在审美资本主义的阶段对消费者的宰制愈演愈烈。商品的交换价值或者如鲍德里亚所说的商品的符号价值在审美资本主义阶段的不断放大,追求商品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在资本与审美的合谋下成为现代消费社会的主流。商品的场景化的功能作为气氛营造的元素,成为商品销售自身的手段。所以波默强调的是商品的场景性价值,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改造来营造特定的氛围,消费者置身其中,物的迷狂下的身体性在场,气氛得以感知。
在波默看来,西方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无疑是一种浪费型经济。审美价值的创造,包装设计以及商品自我场景化的大规模生产都不能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求,只是不断地激发消费者心中的欲望。在经济领域的美学批判保持在审美领域之中,而在传统领域之中的美学批判对场景化经济视若无睹。气氛美学专注气氛的可营造性以及对个人的感知性体验,使得气氛成为资本加以利用的力量。消费主义通过气氛的制造而独占消费者的时间,对消费者的行为进行诱导和捕获。与此同时,气氛美学有传播相关知识用以打破资本主义的劝诱行为的可能性,使得人们与气氛之间的互动转变成为自主的良性的交互行为,而不是势力不均的单方面牵制。以气氛作为新美学的根本概念,主要強调美学的感性体验,对自然以及对生活的审美使得美学的范围在逐步扩大,新美学主要针对的是对以往判断美学所狭窄化的审美对象进行扩张,在不断追求审美的日常化下,也在审视美学在环境以及自然之中的作用,讲求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的和谐共生。
总而言之,气氛美学打破了以往对美学的固化认知,将日常生活以及自然美学方面的认知纳入到了新美学的范式视野下,展开了对美学工具化的讨论,使得对政治甚至是经济方面的美学批判成为美学批判性的新兴发力点。波默所提倡的新美学即关于知觉的一般理论,感知主体在知觉活动中感知到的第一对象即是气氛,它不是情绪也不是形体,不是对象或其性状,亦非像格式塔心理学所说的那样,而是最先且直接地被感知到的东西[1]35。新美学不断探寻实在审美化的进程。气氛美学的批判性所要表达的是存在着多样性的审美需求和繁多的审美供给,因人而异的审美兴趣以及权力领域不同程度的审美操纵。一般美学的任务在于让这个宽广的审美现实性领域变得透明和可言说性[1]35。以气氛美学为代表的新美学在本体论上是以气氛相对应的感性体验作为美学的存在方式,将感知主体置身于情感空间的环境之中感受气氛的变化,关注对自在自然身体的关注较之以往判断美学更为具体和深入。另外,新美学将审美工作由对艺术品的审美判断扩大到环境以及自然层面,甚至是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之中。美学所带来的审美工作的推进对社会层面的批判潜能可以被研究者不断开掘,权力将自身场景化,通过相应的审美途径渗透到个人群体的感知中。无形之中,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社会层面的隐性渗透都在强调新美学与以往判断美学的不同。
参考文献:
[1]波默.气氛美学[M].贾红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梅洛—庞蒂.眼与心[M].龚卓军,译.台北:典藏艺术家庭,2007:7.
[3]程赟.现象学视阈下的气氛美学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22.
[4]卢春红.从“感性认知”到“新美学”:美学何以复兴?[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3-53.
[5]杨震.“存在即显出”——伯梅“气氛美学”述评[J].外国美学,2018(2):41-55.
[6]王卓斐.试析格尔诺特·伯姆的生态自然美学观[C]//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卷),2012:224-245.
[7]格里菲洛.气氛与身体共鸣[J].陈昊,译.外国美学,2018(2):16-40.
[8]朗西埃.何谓美学?[J].关秀惠,译.文化研究,2013(15):338-349.
[9]仰海峰.鲍德里亚的“诱惑”概念[J].哲学动态,2008(1):13-15.
作者简介:陈佳欣,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感性与幽默的生活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