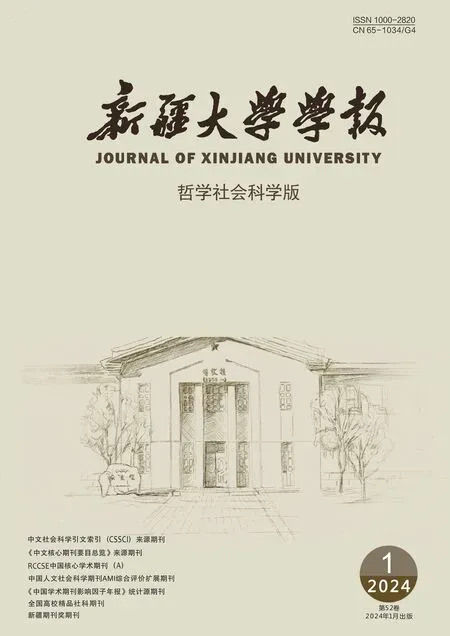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生成与具象传播*
李秋梅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①参见习近平《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第1版。范畴。自此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中得以重申。实际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话语和政治话语的重大创新与发展,是内嵌着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②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45页。的共同体理念的话语。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主要是从其理论渊源、概念内涵、现实意义、实践路径等维度展开讨论,③参见刘金林、杨楚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现状及趋势——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23年第2期,第9-17页。而较少研究作为话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而,本文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生成的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和文化基因,有利于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与建构的规律性,进而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创新。而话语创造与生成并非终点,需经由传播逻辑才能获得人们的认知和认同。因而,在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逻辑的基础上,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传播逻辑,有利于建构与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认同。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的现实逻辑
话语作为理论知识的外在表达,其生成离不开现实问题的发现与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服务于现实需要的话语,其生成的背后有着重要的现实逻辑。
(一)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的现实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1],这是我们当前需要关注和正确处理的重要现实问题。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呈现多元一体的格局①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页。,“一体”更为强调的是共同性,而“多元”更突出的是差异性。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中,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张力问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第一,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强调对国家身份、国家共同体的认知和认同。而民族认同是包含特殊的语言、情感与象征符号的集体现象②参见〔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2页。,是对所属民族的自觉确认与认同。可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首先表现为认同对象的差异。国家认同的认同对象是国家,表征的是人与国家的关系,更为强调共同性维度。而民族认同的认同对象是具有差异性的民族,反映的是人与本民族的关系,更为强调差异性维度。因而,就生成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张力问题。第二,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格局内含着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存在。就中华文化的认同强化而言,更为突出了共同性,就各民族文化认同强化而言,更为突出了差异性。此时,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张力表现为中华文化认同与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张力。而这些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张力若是处理得不恰当,就会引发一系列矛盾与冲突,动摇社会的稳定,阻碍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话语是沟通的中介与桥梁。那么,如何通过话语沟通共同性与差异性,调和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正是在这种现实境遇下建构起来的话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绝不主张通过消灭一切民族的差异性而实现民族完全同质化,也绝不主张片面突出民族的差异性而忽略民族之间的共同性,所强调的是尊重各民族差异性与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统一。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能够正确处理和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
(二)抵制西方话语对中国民族政策污名化的现实需要
当前,西方话语对中国民族政策污名化情况依然层出不穷。戈夫曼认为污名是社会对个人或特定群体的羞辱和贬低③参见〔美〕欧文·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体管理札记》,宋立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82-187页。,实施污名化最直接的路径是话语的贬低与侮辱。因而,污名化实为“竞争和排斥所驱使的话语建构”[2]。污名化扩散的过程,主要是污名话语建构与传播的过程。巴赫金认为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普遍适应性的特点④参见〔俄〕巴赫金《周边集》,李辉凡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7页。,因而,话语不仅是一种交际和交往的工具,而且与意识形态发生着关联,话语背后是权力意志与价值意指。这就意味着污名话语内嵌着施污主体的价值追求或意识形态导向。中国作为全球范围的“个体”存在,在西方强势话语之下被塑造出污名化的话语形象。西方话语凭借其话语霸权,在内容上炮制侮辱性和虚假性话语污蔑我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发展成就。譬如,西方政客与媒体污蔑中国在新疆搞“灭绝种族”、对维吾尔族妇女实施“强制绝育”、设立“拘留营”对维吾尔族儿童实施“强制转移”和“隔离”、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等,恶意抹黑和攻击中国的民族政策;在形式上,充分运用西方主流和非主流媒体、通过大量的影像符号、数字符号、商业符号等形式展开污名化中国民族政策的宣传。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的污名化手段,都是西方话语霸权实践的图式。在这种强势霸权之下,西方的是非标准成为唯一标准。这样,西方就随意设置国际话语议题和话语基调,遏制中国话语议题的正常表达,肆意定性和定价中国的行为,歪曲解读中国的民族政策,黑化中国民族发展事实,这对中国形象和外部舆论环境造成很大危险和破坏,还会扰乱对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发展事实不甚了解的人们的认知与认同,从而影响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因此,我们需要更加主动地通过有说服力的话语和真实有力的证据来揭穿西方的谎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是新时代中国民族团结话语的创新,蕴含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思想立场和主张,是我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的外在表达,是一种表征中国真实的民族政策的具有说服力的话语。因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生成是抵制西方话语对中国民族政策污名化的现实需要。
(三)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现实需要
列宁强调“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3],语言的这种“交际”功能不仅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领域,而且还体现在民族理论政策解释与宣传领域。民族理论政策语言或话语是理论政策制定主体与大众“交际”的工具与手段,民族理论政策话语的创新力、供给力和解释力对于推进理论政策的传播,进而增进理论政策的认知与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的话语体系”[4]和建构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①参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3年10月29日,第1版。,这就为向国内人民大众与国际社会解释好、宣传好我国的民族理论政策以及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提供了思想指导。而当前中国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与民族理论政策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现象,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与我国经济实力增长的匹配度有待进一步提升。这就会带来两种影响,一方面会影响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解释与宣传,另一方面会导致我国民族话语在国际社会“失声”、在重大国际议题处于“失语”的被动局面。因此,我国亟需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发展实际相结合,努力生产高质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增强话语的创新力、供给力与解释力,以改变或避免我国在民族领域“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态势和增强中国在民族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为讲好中华民族大团结、繁荣发展的故事提供话语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正是在急需话语创新与创造的现实背景下生成的。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是话语创新的一个生动典型,可以为中国民族理论政策话语创新提供重要的现实借鉴,有利于推动民族话语概念范畴的创新,进而从整体上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创新。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的理论逻辑与文化基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生成离不开现实问题的发现与关注,但话语的生成逻辑并不是直接从现实逻辑到话语范畴的演化,其生成也离不开一定的理论指导和文化基因的传承。
(一)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遵循
马克思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者辩证关系进行了阐释,他提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5],这句经典的论断传达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内在意蕴。第一,上层建筑的生成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作为一种政治话语表达方式,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而此范畴并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话语,而是依赖于中华民族发展的物质经济基础,立足于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基础之上而建构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一言以蔽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生成是由新时代中国社会物质经济所决定的,并反映新时代中国社会物质经济发展的现实。第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非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因素是“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性因素,但并不否认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决定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除了经济因素,“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6]。因而,经济因素并非唯一的话语生成的决定性因素,文化、政治制度等其他的上层建筑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生成产生一定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的文化土壤,党的领导和中国民族政策的发展完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重要的政治保证和条件等。因此,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理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的理论遵循,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形成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阐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生成是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
(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指导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作为一种创新的话语,是在以往关于民族理论与民族团结话语的历史积淀基础上以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指导下的话语创新。毛泽东作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的开创者,他以战略性的眼光和前瞻性的视野提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国家统一以及人民团结是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②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4页。可见,毛泽东把民族团结作为事业胜利的三大保证之一,突出了民族团结的重要地位;邓小平强调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7],这里的“大团结”强调不仅要加强民族内部团结、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也要加强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即团结的对象为全体中华儿女。同时,邓小平还强调搞好民族团结是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①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这就明确指明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方向,要把民族团结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来完成;江泽民从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维度强调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提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8]等重要思想;胡锦涛从社会主义视角出发,明确地把“团结”作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之一②参见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15页。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这是新时代民族团结话语的重大创新,该话语的创新是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因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的理论指导。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团结文化是话语生成的文化基因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着的丰富团结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的文化基因。第一,“大一统”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典型的团结文化因素。孔子主张大一统,强调在大一统下明“华夷之辨”,实际上这就是萌芽于先秦时期的“华夷一统观”。这种“华夷一统观”实际上蕴含着承认文化差异、和而不同的内涵,也蕴含着华夏族与夷狄族、内地和边疆的整体性;孟子提出“用夏变夷”(《孟子·滕文公上》),即以诸夏文化影响中原地区以外的僻远部族,这实际也蕴含着夏夷一统观;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四方民族,无不为黄帝子孙”[9],即是说四方民族加上华夏民族都为黄帝的后代,实际上就是强调夏夷皆是同宗思想,这就明确了中华各民族大一统的前提。这些华夷或夏夷一统观,有利于各族人民走向聚合。而“大一统”的文化传统最初旨在维护和确保中原王朝获取正统地位。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制,把抽象的“大一统”观念发展为各民族共为一体的“华夷一统”的现实图景。此时期的“大一统”主要表征为政治权力和领土的统一。到汉代董仲舒结合了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对“大一统”文化内涵进行了新诠释,其天人合一论即是强调万物为一体,并强调“大一统”付诸于制度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③参见李零《我们的中国》第一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62页。此时的“大一统”所涉及的领域不仅是政治和领土层面,而且推广到社会、学术、文化等领域。一言以蔽之,“大一统”文化经由秦汉大帝国的空前统一得以确立,而后经过两汉400 年的统一实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之争、隋唐大一统、元明清时期的大一统实践,“大一统”文化观念已经印刻在了人们的内心深处,成为中国人共同的信念。在“大一统”文化基因的影响下,生成了强调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第二,“和合”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团结文化的又一典型。“和合”文化是由“和”与“合”范畴构成。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孔颖达则在《春秋左传注疏》中提出“和,犹合也”,这就说明“和”与“合”具有相似性。古人基于“和”与“合”的相似性创造了“和合”文化。中国“和合”文化的内在构成元素丰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④参见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5月16日,第2版。都是“和合”文化的内在构件和精神追求。“和合”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过程中也发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的重要文化基因。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传播与认同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之后,如何传播开来,从而形成社会共识性话语,如何在传播中建构与增强话语认同,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作为一种创新话语以及承载着抽象意识形态的话语,其话语内容及其精神实质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建构与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认同,就要使其实现具象化传播,而修辞化、视觉化、音乐化、故事化等可成为具象化传播的重要路径。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修辞化传播
修辞化传播是指“巧妙利用修辞技巧增强传播势能的重要思路”[10]。这种传播思路的实践展开是以修辞手段和方法对语言和非语言信息进行加工,从而使得语言交流更具艺术性。实际上,话语的修辞化传播是一种能够依据传播客体的生活背景、接受习惯、心理特征等因素调整话语表达的方式。政治话语是一种严肃性的理论话语,该话语的传播需要根据政治话语传播客体的接受心理,使严肃理性的政治话语通过一些语言修辞艺术,更加准确和鲜明生动地传达政治话语的精神实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就是一种创新性的政治话语,这就意味着使用通俗化的修辞会给传播客体提供一个更为形象直观的理解和接受视角。比喻修辞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传播中使用得较为频繁。比喻是运用分属不同范畴但具有相似性的事物描述另一事物的语言修辞,孤立的事物以及单一的词语无法构成比喻。比喻修辞使抽象思维通过比喻得以表征,抽象事物通过比喻得以理解和接受。当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传播过程中,主要是以“石榴籽”意象比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石榴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分属不同范畴但具有某种相似性的两种事物。石榴籽“千籽环抱、千籽同房”和“千房同膜,千子如一”(潘岳《石榴赋》)的特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深刻意蕴具有相似性。而“石榴籽”是人们生活中熟悉的事物,以“石榴籽”意象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贴合人们的生活背景,符合人们已有的认知结构和接受习惯,使人们更易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精神实质。因此,可通过通俗的语言修辞艺术,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认知与认同。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化传播
海德格尔提出了“世界图像时代”这个范畴,旨在强调世界被把握为“图像”,①参见〔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8页。这种思维即是强调视觉元素在理解世界中的重要性。在叙事与传播场域,视觉元素对意义和信息的吸收、加工、表征、传递等起着重要的作用。英国学者罗戈夫提出“在当今世界,除了口传和文本之外,意义还借助于视觉来传播”[11]。由此可知,整合视觉元素的视觉化传播是一种新的意义和信息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是以影像为传播载体,以技术化的视觉媒介为传播手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意义和信息的认知和认同效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必然是携带着特定的意义或信息的话语,视觉化传播能够更好表征话语蕴含的意义、信息与精神实质。因而,视觉化传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具象化传播的重要理路。
何以必要通过视觉化的方式来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呢?第一,“读图时代”的新要求。当今社会已进入“读图时代”,这个时代呈现高度视觉化和普遍视觉化的特征。以视觉元素为轴心的“读图时代”的到来,使得语言符号文化让位于以形体面部表情等形象占据中心的视觉文化。②参见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因而,当前的社会发展现实迫使我们要优化传统的话语传播方式,要充分发挥视觉元素在话语传播中的优势。第二,传播客体的形象化、通俗化接受意愿的现实要求。当前,人们不再满足于灌输式和单向的政治话语传播方式,而是希望通过更为直观的方式认知、理解、认同政治话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作为一种创新的政治话语,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距离感。因而,可通过形象直观的视觉化的方式来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拉近与受众的距离。而视觉化改变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能够使人们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听众”逐渐转向话语的“观众”。因而,视觉化传播是表征和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意义与精神实质的重要手段。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通过视觉化的方式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呢?影像表达是视觉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具有形象的直观性、价值内嵌性的特征。要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传播,就要掌握影像赋意与赋词的主动权,运用影像这一叙事方式进行传播叙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实现具象化,唤起大众的情感认同和行为自觉。譬如,通过《同心共筑中国梦》专题影像,增进国内民众和世界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内容和精神实质的认知、理解与认同。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音乐化传播
所谓音乐化传播即以音乐为媒介或载体进行传播。具体而言,音乐化传播是指通过化词入乐的方式进行传播。音乐不只是听觉艺术,正是因其脱离了有形的物质实体,以无形的声音属性承载着精神力量和传递着特定的信息。换言之,音乐是一种能够承载与传递特定信息的听觉叙事方式。在早期中国,音乐这种能够传递特定信息的功能被统治阶级关注,他们把音乐纳入了政治宣传与传播体系中,从而使传播客体“审乐以知政”①参见戴德、戴圣《礼记》,杨靖、李昆仑编,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5 年,第157 页。。实际上,从早期中国开始,一直延续至今,音乐就作为政治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黑格尔关注到了音乐的情感性特征,他认为情感作为内容的包衣,正是音乐所要据为己有的领域。②参见〔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45页。如今,音乐化的表达方式能够突破其时间维度的单一表达,开辟“由视听知觉双重参与对话式、浸润式体验的音乐新境”[12],构筑情感空间,焕发情感共鸣,进而激发人们对政治信息的认知与认同。
作为一种承载着特定政治信息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要实现具象化传播,音乐化的传播方式可成为一种新的选择。第一,对于人们大众而言,音乐无处不在,音乐与人们生活紧密相连,甚至是人们生活场域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人们能够随时随处触及的对象。因而,以音乐化的方式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人们能够在有意无意的音乐播放中,接收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信息,使话语融入社会大众的生活中,渗透进人们的思想中。第二,音乐化的传播方式更为契合人们的接受兴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传播要想实现具象化传播并获得大众认同,就必须首先尊重受众的接受心理和接受兴趣。音乐化的表达与传播,能够把话语内容与特定的音律、曲调、情感、情境等要素融合在一起,把抽象的话语范畴转变为生动而富有情感的音乐欣赏与体验。而特定音乐欣赏与体验的过程,实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传递与交流的过程,可以激发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兴趣,增强话语识记与话语认同。但也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以音乐化的方式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应避免娱乐化、低俗化。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故事化传播
话语的故事化传播是指通过特定的故事向某个受众群体传播特定的话语范畴及话语精神实质,使其获得认知与认同的过程。故事是人们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方式,人们通过故事将零散的事件、信息与价值观联系起来,理顺其中顺序与逻辑,而后形成观念和产生评估。作为一种叙事传输方式,故事融合了交流与抒情的特征,使独白转变成对话,使理性的认知转变成感性的体验,使单向的灌输转变成双向的互动,这意味着与直接的、单向的话语宣讲相比,兼顾理性与情感的故事化传播更能让人接受。同时,“故事是一个很好的记忆模型”[13],有画面感和情节性的故事更容易使人记住,并能够塑造长时记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创新性的政治话语,与民间的大众话语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着一定的传播障碍。因而,要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较高的传播效度,就需要寻找一种能够跨越政治与大众之间距离的传播方式。而故事化传播是使其从抽象到具象、从理论到现实的有效传播方式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故事化传播,就是通过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从而在故事中唤起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认同。具体来说,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故事化传播可从三个维度展开。第一,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历史形成故事。话语的认知是话语认同的前提,因而,要使人们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先要使人们认识该话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作为新时代的民族团结话语,是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而形成的话语。因而,我们要讲清楚该话语经历了什么样历史流变?为何会经历这样的历史流变?其流变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通过嵌入以上问题逻辑的故事,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认知。第二,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昨天”的故事。“昨天”的故事是人们的集体记忆“储存器”,时间的推移会弱化、甚至消除人们的记忆。通过故事叙事实现集体记忆代际传递,使得集体意识与集体记忆获得时间上的连续性。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昨天”的故事,能够唤起共同的祖源记忆和共同体意识,进而使人们深刻领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共同性特征,唤醒人们的情感认同。第三,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今天”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人们更能理解与感受的故事。要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共同抗疫、共同脱贫攻坚、共同繁荣发展等身边真实动人的故事,使人们真切认识到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共同体,从而激发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认同和践行。
四、结 语
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话语和政治话语重大创新与发展的话语,并不是凭空生成的。具象传播是建构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认同的重要路径之一。当前,我们要继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基础理论研究,进一步厘清“四个与共”“五个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内容的关系,阐释好与传播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实质意蕴,以进一步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认知与认同,并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精神实质,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合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