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油画到丝网版画的转换
——以罗中立《父亲》为例
张琦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一、乡土写实主义
乡土绘画,特指20世纪70年代末期涌现出的以乡村景观为主题的艺术创作,多表现农村风光和农民生活的场景,由此表现人民真实的精神状况。乡土绘画在1978-1984年这段时间得以发展,艺术家多集中于四川地区。如高小华的《赶火车》,程丛林的《1968年x月x日雪》,王亥的《春》等以及罗中立的《父亲》,罗中立创作的《父亲》在庆祝建国30年的全国美展中获得一等奖,被认为是“乡土写实主义”的开端,这一艺术现象的兴起展现了艺术家对时代的思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画坛开始将关注点从知青转向农民,被称为“乡土”美术时期。这一时期,原有的固定表现模式——如农民形象是喜庆或慈祥的——被打破,艺术家们的关注点开始从表现理想、英雄题材转向对现实生活及普通大众的关注,作品中所展现的人物、村景、建筑都取材于现实生活,艺术家们以独特的视角,深入挖掘乡村生活的点滴,通过细腻的笔触,将这些平凡的事物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和艺术价值。
对乡土美术的研究成果诸多:何桂彦将四川乡土绘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1981年为早期阶段,1982年至1984年属于第二阶段,即鼎盛时期;第二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在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上,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创作获得了近十个奖项;1984年之后是第三个阶段,乡土绘画逐渐走向了衰落①。殷双喜按照创作类型将乡土美术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是从政治的角度看乡村现实;第二类是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角度去关切农民的生存,这同时也是四川乡土美术的基本内涵;第三类是画家把乡村的生活场景和农民的朴素形象作为画家的绘画题材进行表现,以此来传达出艺术家的思想感情和个性语言;第四类则是从文化的角度去分析乡村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心理和内在精神,然后较多地去借鉴民族美术和民间美术中的造型语言和符号②。”
罗中立是较早开始这种转向的画家之一,他创作的油画作品《父亲》一经展出就引起了全国性的大讨论,成为促使当时艺术家进行思考的作品之一。吕澎曾对乡土绘画艺术的发展倾向进行分析:艺术家对普通人状态的挖掘与表现,是一种人道精神的延续与深化,是对朴素人道情感的发挥。在刚刚过去的十年,艺术中所呈现的那种异于现实的积极向上情绪的农民形象,一方面是因为特殊政治时期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50年代以后,中国美术创作一直以苏联为模板,革命题材成为艺术家表现及关注的重点。乡村主义画家的创作多是结合自己的观察与写生,引导人们将视线放在小人物、真实的生活状态及迷茫的精神状态上,回归到生活本身,表现了对个体的关注。
二、油画《父亲》的创作过程
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创作于七十年代末期,在创作时更多基于艺术家个人对现实的感受以及对历史产生的思考,与大巴山的农民同吃同住的经历使他产生了表现农民的欲望,并创作了劳动、爱情等系列表现乡土的作品。在创作油画《父亲》时,他提到超级写实主义并希望运用照相写实的手法,使《父亲》最大程度化写实。
2022年6月8日,在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举办了罗中立回顾展,展出了罗中立创作《父亲》 一画的手稿及作品。1978年的手稿是此组系列手稿中时间较早的一幅手稿作品,表现的是罗中立在大巴山居住的家庭主人邓开选及村民,此时是否以老人形象进行创作在罗中立心中尚未敲定,1978年手稿中出现了不同身份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农民,两个手拿镰刀背箩筐的年轻人以及两位背部佝偻的坐姿的老人。在之后的创作中,对于原型的选取一直是罗中立创作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1979年的手稿《粒粒皆辛苦》表现的是农作中的农民,图4则使用军旅壶和帽子刻画了一个年轻的生产队长形象。1979年的手稿中,一个新的形象出现,即罗中立所描述的引起其极大同情怜悯的盯着粪池的老人。在一个除夕夜晚,罗中立偶然发现了这个在厕所边的老人。这位老人的形象使他对在当时的画坛上被表现为富足、祥和形象的农民产生了反思,罗中立当即决定以艺术的方式表现真实的、处于苦难和创伤中的农民。他曾这样表述其内心想要创作此幅作品的冲动:“一双牛羊羊般的眼睛却死死盯着粪池,这时,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地向我袭来,我要为他们喊叫!”。在最终定稿中(图5),《生产队长》的军旅壶和帽子由头巾和瓷碗代替,脸上的褶皱显示出农民历经的沧桑。这个老人的形象带给罗中立创作的思考,不再是“高大全”的构图,在之后的手稿中,罗中立开始考虑构图,如手稿《粒粒皆辛苦》(图2)上写有“头部放大”字样,他本人也曾说到过正是从这一稿开始,才决定使用大幅肖像。最终,罗中立第一次以“伟人像”的巨大尺幅、纪念碑的方式、“超写实”的手法表现出这一普通的农民形象。标题从《粒粒皆辛苦》、《生产队长》、《我的父亲》最终敲定为《父亲》,一个极具典型特征的农民父亲的形象展现在观众眼前并颠覆了以往的农民形象,不再是洋溢着喜悦与幸福,而是孤独、无助,眼神中透漏出的空虚与迷茫以及粗糙的充满了伤痕的端着破旧茶碗的手,一个符合中国大众心目中典型的农民形象就此产生。

图1 《父亲》系列手稿 纸本素描1978年

图2 《粒粒皆辛苦》纸本素描1979年

图3 《父亲》系列手稿 1979年

图4 《生产队长》1979年

图5 《父亲》197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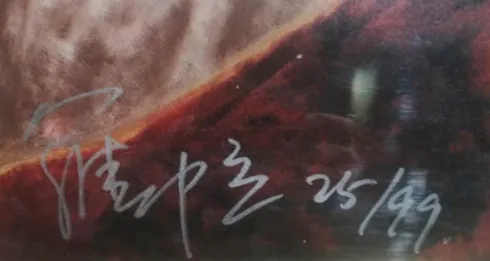
图6 罗中立丝网版画亲笔签名
1980年《父亲》一画被数次展出,并且在1981年获得了“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的一等奖,这幅纵216厘米,横152厘米的画作使每一位观众在其面前伫足。在80年代,“超级写实主义”并没有进入大众视野,这一放大了千万农民迷茫的双眼和满脸的褶皱的作品引发了讨论,观众们的反应再次证明了此画的成功。
三、《父亲》油画到丝网印刷的转变
在首届北京798国际版画博览交易会上,《父亲》一画以丝网版画的形式被展出,尺幅大小是56cm×75cm,占据了一面墙的空间。这是由百雅轩与罗中立共同制作的版画,据说,这幅作品使用了60多个版,制作了一年多的时间。被展览的作品下方标有“23/99”的标注,表示印制的版画数为99版,此画是其中的第23张。在此次展览中,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王炜提到艺术与大众的关系,“画家的天职是把画画好,把最好的作品送到千家万户去。此次版交会在艺术家和百姓之间架起了桥梁。”
油画《父亲》在80年代展出后,一度成为开创新时代艺术代表作品,引发了人们对集体主义时代的反思,同时《父亲》以极具典型的艺术形象令观者动容。正如罗中立所言,他曾多次见观者在此画前久久驻足并泪流满面,《父亲》一画所产生的社会性价值不断在评论家和观者的反应中被肯定。但是,在“居住在成都——2005中国当代油画邀请展”上,罗中立却说:“当时《父亲》的社会性更胜过艺术性。如果在20年之后的今天,让我再画《父亲》,我会更多地从绘画、艺术本身来构思,不会还是社会属性很多的那种东西。”他还表示,20年后画《父亲》,“想表达的就是我20年油画艺术、油画语言的体验,展现我鲜明的艺术风格,给人视觉欣赏的感觉”。罗中立表达的希望降低此画的社会性意味着在当代,以《父亲》一画为代表的乡土绘画已经失去了适合其产生的社会土壤。一方面因为以《父亲》为代表的乡村景观在当代已不再像80年代那样具有颠覆性和典型性,其次是艺术的经济及资本市场的到来,使得此画的生存状态从反思变为对时代的适应。
此画在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后,对于收藏市场和罗中立本人而言,对此画的调动都显得十分困难。2005年,罗中立联合百雅轩限量做了一批尺幅大小不等的丝网版画,并亲笔签名。与此同时,罗中立的其他艺术作品《父与子》、《冬水田》、《背孩子的女孩》、《巴山情》、《过河》、《举灯人》,何多苓的《有鸟的风景》、《在梦中奔跑的女孩》等作品纷纷以丝网版画的形式问世,有限的复制赋予这些艺术作品新的时代意义。这些丝网版画的特点是:1.由艺术家亲自参与,与专业技术人员合力完成;2.不对原作进行再加工,运用技术尽可能仿真原作。3.有限的复制,每幅作品在复制时限量99版,并有艺术家亲笔签名。在丝网印刷的过程中,原作的艺术性受到挑战,油画笔触消失,产生的新的艺术品呈现出的是不同于油画的平面化视觉特征。对于原作以及热衷于笔触的观者而言,笔触及油画材料特性的消融是遗憾的。但是对于脱离了原本环境的艺术作品,社会赋予其的符号意义也值得重视。以《父亲》为象征的乡土主义作品在艺术市场中之所以可以和丝网版画成功结合,原因在于乡土主义时期的作品所带来的时代价值已然成为过去,艺术形象足够典型使其成为“农民”、“父亲”等形象的视觉表征,使原本的艺术作品符号化,并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产生了大量商业复制品。除艺术家亲自参与的丝网版画和雕塑制作外,还常以电影宣传海报、书籍装帧以及文创衍生品等视觉形式展现出来。可以说,极具时代意义的作品被不同时代的受众赋予了新的社会意义,视觉艺术品开始向符号化转变。尤其是当油画《父亲》以漫画的形式加以夸张变形时,不仅引入了崭新的艺术元素、时代特质以及社会观照,而且原有的社会性也在其中逐渐渗透并融入了历史内涵。
四、结语
20世纪初,丝网印刷在波普艺术家的引领下发展起来,传入国内后以其复制艺术品的能力被艺术家们青睐。当不可复制的艺术品被收藏入美术馆和画廊后,几乎无人可具有收藏能力,即使是艺术家个人都难以调动。对于艺术爱好者而言,暂时的参观已经满足不了日常的需求,丝网印刷的引入在保证艺术复制品的还原度的同时也降低了收藏的难度和成本,为大众的审美和消费提供了方便。同时艺术家参与制版并限制其出版数量保证其艺术价值。
80年代的乡村写实主义在当代已不再具备对特定时代的反思价值,但艺术家创造的高度概括的艺术形象在历史的沉淀过程中逐渐具有符号化,成为时代的标识。作为印刷品的油画作品《父亲》,本身仅仅是对原作的再现,之所以具有市场价值在于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在当代成为千万农民的代表,这种符号化使其在不需要反思其本身意义的时代依然具有广大的受众。无论是对于收藏而言,还是从社会传播的角度出发,丝网印刷对于不可重画的艺术作品的再呈现,都具有平衡艺术与大众之间供需关系的价值。
注释
①何桂彦.传承与超越:1976-2006“四川画派”三十年[M].吉林美术出版社.2007:25-26.
②殷双喜.现场——殷双喜艺术批评文集[M].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