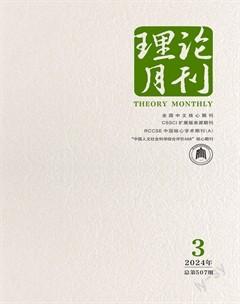税法总则优于税法典:税法编纂的限度省思
[摘 要] 税法总则所代表的税法编纂是否应在我国启动,一旦启动应选择何种法典化道路,需要阐明理论基础,提供实践方案,以为立法机关的研究工作提供建议。税法编纂具有推动税收法定导向更高水平、高效简化税收法制、实现税法体系正义等治理价值,也面临税法统一性与开放性的矛盾长期存在,我国税法编纂环境依旧受到诸多限制等实践隐忧。税法编纂在域外代表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早已广泛盛行,只要我国宏观上始终保持合适的编纂尺度,微观上厘定妥适正确的编纂内容,税法编纂就应予以开启。税法编纂是税收法治的核心建设路径之一,相比规范主义进路和工具主义进路,功能主义进路更适合作为我国税收法治的评价与建设基准。在功能主义税法进路指引下,只制定税法总则、放弃制定税法典的半法典化模式是我国税法编纂的最优方案。
[关键词] 税法编纂;税法总则;税法典;功能主义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3.012
[中图分类号] D922,22; DF4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4)03-0109-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税法保障研究”(22BFX09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数字经济时代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优化的税法保障研究”(22XJC820002)。
作者简介:邹新凯(1993—),男,经济法学博士,西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问题意向:税法编纂的启动与选择
为了更好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提高税收法律的法定性、体系化和科学化,制定税法总则并在此基础上编纂税法典从学界呼吁走向立法研究[1]。相比“一税种一法律”的单行税法模式,以税收实体与程序法中的基本与共性规则为主要内容的税法总则和涵盖绝大多数税收实体与程序规则的税法典则体现出集成税法的新型模式。实际上,编纂理念在域外并非新生事物,一方面,税法总则、税法通则、税法、税法典等早已在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施行多年,在学理与实务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值得镜鉴;另一方面,税收基本法曾被列入第八届、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税收基本法(第六稿)和税收通则法(专家意见稿)先后提出,全国人大、国务院、税法学界均开展了大量起草、研究和论证工作。如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的新时代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法总则或税法典,颇有研究必要。若要对这一重要税法理论与实践命题展开论证,宜分为两大步骤:第一,我国是否有必要运用编纂理念,开启法典化进程,制定税法总则或税法典;第二,若税法编纂很有必要,我国应在“只制定税法总则”“只制定税法典”“先制定税法总则后制定税法典”三种方案中如何抉择。
鉴于此,本文聚焦税收规则法典化的编纂评估与方案比较,以求系统论证中国特色税法编纂之路,相应结构如下。首先,闡明税法编纂的治理价值,描绘税法编纂的实践隐忧,为论证税法编纂即税收法典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奠定基础;其次,在规范主义与工具主义的税收法治建设进路之外,证成税收法治评价与建设新的具体路径——功能主义的税收法治建设进路;最后,运用功能主义的税收法治建设进路,为税法总则优于税法典即“只制定税法总则,放弃制定税法典”的编纂方案辩护,期冀加快开启中国特色税收法典化进程。
二、理论功能:税收法典化的治理价值
事实上,从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到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法典》,从法国《民法典》到德国《民法典》,编纂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理念,以对某一特定法律领域作出最完整、最系统、最长久的规定为最终目标,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鲜明的推动作用。税法编纂即税收法典化进程绝非凭空产生,而是税法理论与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和时代吁求。整体审视,税法编纂即税收法典化有税收法定、税制简化、税法体系化原则的坚定支撑。
(一)税收法定的更高水平建设
税收法定作为税法帝王级原则,在实体要素上,税收法定要求有关纳税主体、课税对象、归属关系、课税标准、缴纳程序等,应尽可能在法律中作出明确详细的规定;在程序要素上,税收法定要求税务机关严格依法征税,不允许随意减征、免征或停征,更不能超过税法的规定加征[2](p105)。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质是通过民主控制和程序规范来限制课税权的行使空间与方式,进而保护纳税人权益,维护人的尊严和主体性[3](p16)。
税法编纂可以将散落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各级税收规则)中的共性规则,例如税法原则、征税主体、纳税主体、纳税义务、税收规则制定程序、税收征管与纳税申报程序、纳税人权利保护、税收处罚与法律责任等纳入税法总则,予以统一和集中规制。在国家一侧,这有利于显著降低单行税法的立法成本,提高各税种法的统一适用效率,助力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在纳税人一侧,这有利于显著改善纳税人对各级税收共性规则起源与内容的理解困境,提高税收确定性,降低纳税合规成本,助力纳税人权益保障。税收共性规则的法定化带来税法基本规定的稳定化、规范化,如同大厦之地基、轮船之龙骨,可发挥支柱性作用,不断稳固并持续引导税收法定向具体课税规则与征管制度迈进。倘若税法编纂将各税种主要税收规则细化融合,系统部署于税法典,在国家一侧,税收法律中不确定条款与抽象概念的具体化不但会助力从根本上扭转“授权立法多于职权立法”的法律倒置现象,推动不断压缩国务院及其财税机关行使税收剩余立法权与行政解释权、出台部颁税收规则的职权空间,降低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夯实税收形式法治基础,各税种各级税收规则法定性与透明度的提高可以极大稳定并强化纳税人的税法预期,有效减少税收征管与执法风险给纳税人带来的权益侵害。
(二)税收法治的高效简化利器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当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因素越发繁荣创新,发挥重要性作用的政治形势越发错综多元,立基其上的税法制度必然日趋复杂。税制复杂性一旦走向过度,其一,烦琐的基准税制、复杂的税收优惠必然增加税收征管费用和纳税人合规成本[4](p1233-1256),降低税收效率。其二,这些过度复杂税制极易损害纳税人合理预期,诱发税收不确定性[5](p645-746),更引致纳税人因理解乏力而对税收公平度产生猜疑甚至存有敌意,打击税法遵从意愿[6](p319-360)。其三,税收法律与政策多变,例外规定和临时规则又较多,税务机关、税收中介、纳税人应接不暇,既使得税务执法、税收征管、纳税服务等难以及时跟进[7](p625-652),又为分利者抛开社会其他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展开勾结行动提供空间。尽管未来税制走向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动能十分充足,但正因如此,税制简化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用以寻求在一国发展的不同阶段均能减避税制复杂性过度对法定、公平、效率、中性、透明等税法正义价值的侵害,由此形成税法上的简化原则。简化税制要素、精选税制工具、致力透明税制、减少例外规定、降低征管费用、压缩合规成本、便利救济渠道、实现内外协调等则是常见的简化方法[8](p147)。
税收法典化进程中,无论是制定税法总则抑或税法,首先,立法者不必在各单行税法中就共通性或基本性问题再行规定,多余和矛盾的税收规则必定被识别和消除,各类税制要素均得以简化。其次,税务机关的执法与征管活动越来越直接建立在统一、具象、明确的法律规则指引下,有助于统一税法评价、税负分配与税责承担的标准,不断减少部颁税收规则中与税收法律不一致的异化规定、例外情况与临时规则。这不但高效简化了税制,尽力避免了不必要复杂税制的产生,而且提高了税务机关的行动透明度和纳税人对各级税制的理解透明度。自此,简约税制使得税务机关征管费用从根本上得以降低,纳税人合规成本从根本上得以压缩。最后,税法总则、税法典所代表的法典化文本使得司法机关可以凭借在法律解释与漏洞填补上的丰富经验与职权优势,逐渐摆脱在税务司法中过于遵让、倚重税务机关判断的尴尬处境。对税务机关行政行为和纳税人税法义务作出独立判断,既可以维护税收法律权威,促进税制要素更加精准科学,又可以消减税务机关滥权空间,增强纳税人对税收规则的安定预期。
(三)税法体系正义的实现平台
我国用以创制、解释、评价、修正税制的税法理论,与德国税法学界的主流代表之一——科隆学派所提倡的税收正义理论[9](p71-155)存在颇多相似之处,也积极借鉴了德国的先进理论成果。德国税法学界一直存在法律实证主义(法律即正义)和反法律实证主义(法律之外有更高正义)之争,税收正义理论作为反法律实证主义的税法代表,主要包括形式正义观与实质正义观两大部分[10](p15-23)。形式正义观除要求税法坚持法定主义,排除纳税义务上的特权与歧视外[11](p15-26),坚持法律本身的标准必须具有一致性。实质正义观要求平等负担纳税义务,实现量能课税原则的具体化:在世界观层面,这一具体化过程必须与其他宪法上的价值原则相结合方能最终形塑成追求分配正义的实质正义观;在方法论层面,量能课税原则通过保持法律形式的一致性、遵循事物正義即根据事物性质与运行规律加以推导来实现具体化平等,相同具体化方法的使用维护了立法与司法机关在税收评价与认定上对量能课税原则的一致认知。结果便是,虽然税法纷繁庞杂,不同具体税收领域遵循不同的事物正义标准,并不必然构成一个完全同质的体系,但各领域事务正义仍然遵循一致、同一的税法基本原则或伦理基础。由此,税法秩序的体系统一目标仍然能够达成,并带来体系正义,体系化原则得以形成:税法内部各项规定皆具有量能课税、法定、效率、中性、透明等正义价值评价上的一致性,彼此又可以相互推导,无价值或内容矛盾之处,自此税法质量与税收科学性大幅提升。
整体审视,德国税收正义理论的本质是在各级税收规则、税收权力机关、纳税人之外建立一个超越民众有限理性的客观正义标准。这是因为,税收正义理论认为民主制度受利益集团、政党政治、立法妥协等限制,并不一定能生产正义的税收规则,反而造成了德国税法规则的混乱武断与价值失序状态[12](p449-497)。客观正义标准通过形式与实质正义观自成体系,规范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权力行使,指引税收规则设计、解释、修正与续造。体系化使得该理论能够随着民众对量能课税等税法价值伦理认知水平的提升而自动更新,从而永葆时效性与科学性。德国税收正义理论的诞生背景与作用机制同我国税法的发展环境与改革蓝图存在部分相似之处,主要内容值得继续借鉴。
税法总则或税法典的制定绝非现有各级税收规则的简单总结,编纂理念内置的整合性、统一性、体系化要求[13](p94)本就是在践行税法体系化原则。其一,编纂要求明确的税法原则、统一的基本税制、集成的税收责任在法律文本内部以体系化的法律条款形式存在,并尽力排除各单行税法和税收征管法在设计与适用上的分散、零碎、矛盾、失序之处,这在法律层面能推动实现各税种在税法评价、税负分配与责任承担上的整体判断一致性,逐渐强化了税制实质内容上的体系化。其二,随着时间流逝,当单行税法或国务院财税机关的部颁税收规则模棱两可、理解困难,无法提供明确指引致使纳税人权益存在较高受损风险时,系统化、体系性的法典化文本自为一种稳定的客观标准和法治支柱,助力司法机关运用体系思维和解释方法从税法总则或税法典中得到启发,进而对下位税收法源、具体税收规则作出与法典化文本相一致的结论,是维护税收法律权威,增强纳税人税法预期,践行税法价值伦理的税收法治2.0版。
三、实践反思:税收法典化的编纂隐忧
不同于税法编纂在我国的蓬勃兴起,法典化虽然是欧洲法律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但向来颇具争议[14](p653-662)。编纂被宣称为理想的立法目标,为立法者的努力提供恒久方向,不但是法律合理化的形式之一,也是立法者因监管各类社会关系而需要法律具有确定性的反映。与之相反,部分学者主张编纂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已经不适用快速发展的多元化现代社会[15](p453-488)。对于我国税收立法,相比明晰编纂的功能、洞悉法典化的价值,编纂的潜在风险与适用挑战更有评估必要。
(一)宏观层面:税法统一性与开放性的矛盾长期存在
历史考察,税法编纂理念及其法典化行动主要受三大因素驱动。其一,税收法律渊源的无节制扩散,执法中出现的困难与差异,共同引发税法设计与适用危机,法典化有利于规范税收法源,统一税收标准,消除不公执法。其二,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或出现经济运行困境,法典化借助满足纳税人对法律统一性、确定性、效率性的需求,或导引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或拉动经济社会走出衰退泥潭,重新步入正轨[16](p374-396)。其三,税法编纂或法典化进程带来的税收规则整合化、统一化具有强化法治权威、促进法律遵守的功能,税收规则的简约化、体系化具有优化政府监管、创新法律规则的功能。这些驱动因素在任何一国皆有可能出现,为此,税收法典化进程及其编纂理念是各国提高税收治理能力的一种共同策略。
与之对应,税法编纂理念及其法典化行动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弊端和风险。结合我国发展现状考察,伴随科技发展、商业创新和社会进步,税收规则需要始终保持规制先进性与竞争力,以充分因应不断出现的新兴领域。税法内置的规范理财行为、促进社会公平、保障经济发展等功能[17](p162)要求税收法律和其他税收规则明确、公正、有效率地对新经济、新业态、新发展作出税法评价,以确保均衡实现税负公平分配和经济调控目的。是故,立法机关若要在短时间内出台税收规则,使之对新兴领域起到合理税收监管、避免课税失衡的作用,就必须努力达致税收规则的因应性、灵活性、动态性。详言之,数量上,税收规则根据新兴领域的演进态势或不断推出、或随时修改;质量上,税收规则必然会经历一个从粗疏到精细、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此期间,新兴领域的国家税收治理能力在缓慢、稳步提高。税法编纂理念及其法典化行动所代表的静态性、稳定性、成熟性策略无法应对新兴领域中税收监管需求和规则演进趋势的挑战,不仅极易阻碍税收规则的规制创新与制度功效,还迫使法典化文本在整体上变得过于抗拒变化,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和累积过时规则[18](p1025-1032)。
典型例证存在于法典化后的各国税制实践。税收法典化事实上是一个逐步编纂过程,税法适用更面临着编纂、解编与重编的阶段性循环[19](p7-53)。具体而言,在讲究开放、多元、创新的现代社会,为了实现税法统一性与开放性的平衡,不断提高税收规则质量和规制效能,税法编纂必须与时俱进、适度靈活,故而法典化后的税法在必要时部分规则应从中分离出来或在法典化税法之外新设部分税法规则,构成税收特别法,开展税收如何对经济社会新领域新情形有效监管的规制试验。当税收特别法累积了成熟的监管与规制理论,此时编纂理念便有强大的号召力,吸引立法机关将税收特别法法典化,故而形成编纂→解编→重编的无限循环。简言之,正因在税法编纂前后,税收领域统一性与开放性的矛盾长期存在,我国税收法典化的开启与否、怎样适用、如何更新,需要详细审视、综合权衡。
(二)微观层面:我国税法编纂环境依旧受到诸多限制
根据域外发展成熟、经久考验的编纂理论,法律编纂的启动至少需要仰赖五大环境要素[20](p69-93)。第一,编纂是对生活中至少一个领域的全面监管;第二,编纂工作需要系统性结构;第三,编纂的法律适用范围覆盖一国境内,并消除法律适用上的分散性;第四,编纂的法律对法官有约束力,并尽可能地排除法官的司法裁量权;第五,编纂的法律不是随机与任意编纂,而是在特定立法目的指引下根据其税收功能设计具体规范。照应至我国,第一、第三和第四环境要素均会受到较为严重的实践限制,难言良善税法编纂环境。
其一,税法编纂难以实现对某一税收领域的全面监管,司法机关对税收法治的贡献更不能放弃。税法总则是对税收共性规则或基本规定的编纂,税法典则是对税收领域绝大部分规则的编纂,但法典化的域外经验早已指出,并非所有法律领域均适合编纂或长期保持编纂状态[21](p97-99)。不同于民法和刑法,税法作为公法,向来就与税收公权力的规制关联密切。不同的规制对象,同一规制对象的不同发展阶段,都要求立法与财税机关出台的税收规则相机抉择、有效应对。关键在于,我国立法机关相比财税机关在税收立法上专业性不足、立法不及时,加之会议较少、会期较短、日程较多,立法机关的税收立法与解释权鲜少使用。税收立法主要由财税机关提供原初设计,税收法律法规由财税机关行使税收剩余立法权与行政解释权供给执行规则,加之国税总局力主将税收行政复议打造为税收争议解决的主渠道①,司法机关对税务机关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行政认定多有遵让[22](p123),国务院财税机关实质上获得了大部分税收规则的制定权、大量税法解释的垄断权以及大多数税收利益的初始分配与裁量权[23](p77)。这种特殊的税权分配与运行结构必然会筑成税收规则的数量和影响力随着税收法源层级降低而逐级递增的金字塔形结构。除非立法与司法机关在税权分配与行使上超越财税机关真正占据主导性地位,否则这一税收规则层级结构很难根本改变。
据此,大多数税法学者与实务人士均提出既要强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税收立法上的领导地位与核心作用,又应采取取消税收行政诉讼“双重前置”,增强审判人员税法专业能力,设置税务法庭与专门法院等措施,开放税务司法,发挥司法机关对财税机关的监督与促进作用。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税改举措来看,上述主张虽然起到了对改革的优良指引作用,但立法与司法机关相对财税机关的税收地位和税权行使格局尚未根本扭转。相反,近年来一部分税法学者与实务人士逐渐主张财税机关每年批发生产大量部颁税收规则,其中绝大多数符合税法法理,是我国税法的主要渊源之一,对指导税法实践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今后也会长期存在[24](p185),国税总局的税法解释权实际上能够经受税收法定主义的合法性审查与功能适当原则的正当性审查,当务之急是建立国税总局税法解释权规范运行的保障机制[25](p112),昭示出对金字塔形法源层级结构的支持。不同税改主张间相互对比,可以看出,若强行使用编纂的立法技术,径直增加税收法律规则、降低部颁税收规则的数量与影响力占比,却对“金字塔形”法源层级结构的形成背景——立法机关、财税机关、司法机关间的税收权力行使结构充耳不闻,不对各级税收规则制定机制作深层改进,无论是税法总则的部分编纂还是税法典的全部编纂,轻者充其量仅为法典化治理价值的昙花一现,因无法真正、长久抑制财税机关行使税收剩余立法权和行政解释权而逐渐快速回归至当前金字塔形的法源层级结构;重者不但可能会阻碍财税机关及时出台税收规则对新业态、新经济、新发展进行创新监管与规制完善,而且极易导致立法后的法典化文本因传统规则过时和新兴规则缺失而日益降低权威与效能,引发对税法编纂和税收法定建设成果的质疑,殊值警惕。
其二,税法编纂难以消除下位税收规则在法律适用上的偏离性。税制实践显示,在各级税收规则中,税收优惠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其适用上的分散性在未来恐难以轻易扭转。宏观层面,“十四五”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发展规划均需大量税收优惠根据各项规划的不同发展阶段予以针对性支持。除为避免法律执行的刚性与经济社会的动态发展需求产生龃龉,造成税法规制的缺位、错位、越位等失灵现象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规制不仅相比财税机关的行政规制专业性较弱,其立法、修法程序还相对漫长,容易错过税法规制的最佳时期,故而立法机关不宜将所有税收优惠上升到法律高度。尽管具有抽象税法条款的授权并未明显逾越税收法定原则,但若将税收优惠纳入税法编纂之中,财税机关却延续使用部颁税收规则对税收优惠予以管理的模式,这将不可避免地削弱法典化文本的适用效能,财税机关税收优惠的管理失当又将与法律文本产生联结,损害法典化文本正在促进的法定、平等、效率、简约、便利等税法价值。
微观层面,近年来影视行业逃避税、直播行业逃避税、霍尔果斯税收洼地事件等映射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税收优惠的政策芜杂、恶性竞争与管理失序。违反上位税收法源的核定征收、财政返还、税收奖励、征管弱化等灰色税收优惠加剧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区域壁垒等乱象,严重妨碍国内统一市场构建、公平竞争维护和营商环境优化①。2014年11月,《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全面开展地方税收优惠专项清理活动,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优惠政策一律停止执行,没有法律法规障碍确需保留的,汇总后于2015年3月底前经财政部请示国务院。但在地方招商引资和民生经济等巨大压力下,《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国发〔2015〕25号)紧急叫停雷厉风行的专项清理活动,待另行部署后再进行。截至2023年底,国务院再也没有部署实施对地方税收优惠的全面清理活动,只在税收征管与稽查的少数高风险领域不定期实行清理。问题丛生并且具有法治风险的地方税收优惠,清理规范难度可想而知。中央与地方在税收优惠规则上对法律的偏离适用,给法典化后的税法总则或税法典带来巨大挑战。税收优惠在税法总则或税法典中如何设计与适用,方能尽力降低央地税收优惠相对法律的适用偏离风险,成为税法编纂启动尤须重视的前置性问题。
四、应启动税法编纂:域外比较与深层评估
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立法史一直由重要的法典塑造,并对德国法律理论与实务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響。典型代表便是1814年萨维尼与蒂伯特围绕是否应制定《德国民法典》产生的编纂之争,不仅掀起德国学术辩论的早期高潮,更将德国民法典的编纂历史延后近百年。也由此可见,税法编纂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综合衡量的系统过程,需要理论辨析,经受适用挑战。
(一)税法编纂的域外探明
审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前20名国家和其他代表性国家可知,税法编纂的启动与法典化程度因各国国情而异,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无直接关联。相关国家的税法编纂总共有三种模式:部分编纂、全部编纂和特别编纂。部分编纂是指只编纂税收通则、税法总则等一般税法,代表性国家主要有德国、卢森堡、挪威、日本、韩国等;全部编纂则是将大部分税制编纂入法,代表性国家主要有巴西、俄罗斯、墨西哥、美国、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而根据编纂内容的不同,特别编纂有按不同税种编纂以及按实体或程序编纂两种思路,前者以以色列为代表,如以色列的《所得税税收法令》;后者以法国为代表,包括《税收法典》和《税收程序法典》。在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欧盟、金砖国家、独联体等典型国际组织中,代表性成员国均已不同程度实现税法编纂。伴随我国全球经济影响力不断壮大、国际政治地位日渐提升,尤其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和代表性国际组织的联系日益紧密,我国有必要与主要国家接轨,开启税法编纂,加快制定税法总则或税法典,凭借法典化具有的深入推进税收法定、助力税法简化、提升税法体系化等巨大治理价值进一步增强确定性、公平性、简约化、透明度、有效管理等现代税制优良品性,将纳税人权益保护提升至更高层次,进而能够高效因应国家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对税收法治建设与现代税收制度的进阶要求。
尽管税法编纂受税收固有矛盾与国内编纂环境影响并未在当下形成一个十分理想的编纂条件组合,但一方面,税法编纂前的理想状态只是法典化准备阶段努力导向的目标,在我国税制实践中难以完全实现;另一方面,风险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税法编纂在我国无法成形,而是应秉持“边走边试边改”的改革精神,将“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对税法编纂的启动与否作深层次评估。
(二)宏观方面:始终保持合适的编纂尺度开启税收法典化
法律一经制定,就与多元社会逐渐保持距离,成为一种凝固的智慧,法律供给与现实需求间不可能达到完美匹配,供需缝隙永远存在,立法者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缩小它们之间的缝隙[26](p97)。例如,作为久负盛名的法典化典范,《德国民法典》在制定过程中汇聚了几代德国学者的学术努力与先进成果,但在20世纪50年代便被一些学者指出,在核心领域,民法典解编的趋势、民法特别法的产生以及法律碎片化现象就已经十分明显[27](p477-484)。因此,税法统一性与开放性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最多只会在更加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加大税法典编纂难度,增大税法典适用挑战,无法构成对税收法典化的根本否定。关键应对之策是在税收法典化的编纂范围、结构厘定和条款设计上把握统一性与开放性的合适尺度,并定期审查与更新。倘若编纂尺度失准,任何税收法典化文本都难以在国家、社会、民众间达成一致共识,甚至引发对法典化文本正当性的质疑,导致编纂流产。
例如,一些德国学者认为税法编纂的时机已然成熟,应制定作为税法典的《联邦税法》,其中以前联邦宪法法院法官、海德堡大学教授Paul Kirchhof于2011年提出的《联邦税法草案》(又称“海德堡草案”)最具代表性[28]。Paul Kirchhof认为德国税法日益复杂、武断、多变和难以理解,应制定一部简约、系统和具有长期约束力的税法,以使征税原因简单明了,为企业的商业活动提供确定、公正和可信赖的法律基础[29](p3217)。为此,海德堡草案将现行200多部税法、33000条法律规则合并为一部仅有146条法律规则的单一税法典,30多种税相应被压缩为所得税、增值税、遗产与赠与税、特别消费税四种,并在税负水平、税法语言、税法渊源、税收优惠、重点税制上大幅简化、重组和更新,意图借此使德国税法中久经考验的原则得以保留,而法律异化、扭曲和象征例外与特权的所有税收优惠均被终止。海德堡草案的设计风格引发德国学理界与实务界的强烈争议,普遍认可其制定初衷与税法愿景,但草案存在强行统一所得税率、取消所有税收优惠与例外规定、偏袒高收入者、创造出新税制不公、无法反映真实复杂的经济生活等弊病,并未在税收复杂性与简约性、法律统一性与开放性之间保持合适尺度。激进的简化方案也因此无法获得议会政党、税法学者、税务顾问、纳税人等各方共识,最终未能成为正式法典,值得警思。
(三)微观方面:厘定妥适正确的编纂内容开启税收法典化
其一,国内税法编纂环境依旧受到诸多限制,税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税权实际运行格局难以对税收法典化进程构成根本阻碍。尽管当前税务机关占据优势乃至主导地位的税权运行格局造就了金字塔形税收法源层级结构,但对税法编纂的不利风险与适用挑战若要从理论转化为现实,需要结合可以纳入税法编纂范围的税制内容厘定。详言之,若税收法典化仅是将各级税收规则中的基本、共性制度或各税种法中长期稳定、变化不大的税收规则编纂入一部法律,这既是对成熟税收立法经验的总结,还能直接修正部颁税收规则数量与影响力较大、税收法律法规数量与影响力较小的金字塔形法源层级结构,提高税收法治化水平。若税收法典化将新兴领域或讲究因地制宜、因时而变领域中的税收规则编纂入法,法律的安定性、强制性必将与规制对象的不成熟性、动态性、灵活性发生冲突,不但阻碍编纂后的法律适用,而且税收支持相关领域的乏力将引致更多部颁税收规则出台,形成税法编纂→法典化文本规制乏力→部颁税收规则重新增多→法典化文本更加规制乏力以致需要重新编纂的恶性局面。在法典化文本重新编纂之前,这一局面及其对依法治税的负面影响不会改变。因此,税法编纂的范围与程度至关重要。目前来看,税法目的、税收管辖权、税法原则等框架性规定,法律以下税收规则的制定程序,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主要内容与实现机制,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纳税义务的发生、承继与消灭,税收征收与纳税申报,税收处罚与税法救济,皆属共同性、基础性税收制度,可纳入编纂范围。
其二,税收优惠相比基准税制的法律适用偏离性难题并非不可缓解。考虑到当前具体税收优惠规则升级为法后,依然难逃造成更多法律适用偏离、扭曲甚至异化的风险,我国税法编纂完全可以不将税收优惠纳入编纂范围。如果立法与决策者依旧决定法典化税收优惠规则,应如何布局方可缓释央地税收优惠对法典化文本的偏离风险,应予以进一步论证。按照税制目的不同,税收优惠分为保障型税收优惠和调控型税收优惠,前者意在执行社会政策、维护社会公平,主要以教育、文化、医疗、体育、宗教、社会保障等公民基本权利为规制对象;后者意在调控国民经济、推动相关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故而可细分为产业性税收优惠和区域性税收优惠两大类[30](p115)。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具有宪法上的最高依据,相关税收优惠的扶助与促进具有稳定性、长效性。与之相对,产业性和区域性税收优惠讲究因地制宜、灵活自主,随着国家对特定产业或地区的规划变动而相机增减,不宜开启税法编纂,以规避法律适用与偏离风险,降低对法典化文本法治效能的侵损。是故,若要将税收优惠纳入编纂范围,只可推动保障型税收优惠法典化,以提升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税法保障水平,增进纳税人福祉。
综上所述,一方面,编纂或明确、或规范、或统一了相关领域的税法评价、税负分配与税责承担,提高了税法的适用性与权威性,不同程度上简化了复杂税制,便利了纳税人,完成了税法体系化,对法定、公平、效率、简约、中性、透明等税法价值的实现均有极大促进作用,域外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代表性成员大多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税法编纂,彰显了这一立法技术的优越性。另一方面,编纂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与适用挑战固然存在,应予重视,但可通由厘定妥适正确的编纂内容、不法典化所有税收优惠、对央地税收优惠进行分类化编纂等途径竭力规避理论风险与适用挑战转化为现实。一言以蔽之,立法评估结果显示,税法编纂不应被否定,而是要与国际编纂形势接轨,和税法治理价值相融,加速启动。
五、只应制定税法总则:功能主义进路上的法典化编纂边界
提升税收法律制度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和科学性是我国税收法治的未来建设目标[31]。税法编纂若要从理论价值转化为制度优势、斩断实践隐忧,对我国税收法治建设发挥引领性、支柱性作用,法典化的尺度与内容是关键步骤,那么,应如何对“先制定税法总则后制定税法典”“只制定税法总则”“只制定税法典”三大编纂方案作出抉择,实质上是在进一步探讨通往未来建设目标的具体税收法治进路。有鉴于此,需要强化对税收法治进路的理论探讨,以论证税收法典化的具体编纂方案中究竟何者为最优选择。
(一)税收法治评价与建设的基本立场:规范主义与工具主义
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會主义法治国家。具体到税法领域,则要求完善税收立法体制,强化对税务机关行权履责的制约和监督,保障税务公正司法,增强全民税收法治意识等。因此,全部税种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各税种基准税制与税收优惠管理法制化,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开展税法编纂立法论证等举措相应推出,本质上意在不断提高税收法制的规范主义风格,推动税收法制贯彻规范主义进路。规范主义进路是指通过不断提高税收规则的法源地位,丰富优化税收法律的条款内容,持续加强税收法律权威,致力于充分发挥明确与规范征纳双方税收行为,限制与监督各类税收机关权力行使的作用,确保税制始终以纳税人权益保障为优先考量。可以看出,行走在规范主义道路上,先制定税法总则后制定税法典是最优选择。虽然规范主义进路十分契合编纂理想,必将促动法治内含的诸多功能在税收领域充分释放,但在我国发展模式下,鉴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较少行使税收立法权、极少行使税法解释权,税务司法尚未完全开放且对税务机关税收行为多有遵让、监督能力有限,国务院财税机关在税收权力行使格局中的特殊优势地位未来将一直延续,难以撼动,央地税收优惠由财税机关主导的管理模式也同样得以继续存在。目前来看,财税机关为主的税权行使格局和税收优惠管理模式对推进税收法治建设和深化税制改革利远大于弊,而且越发得到“放管服”等政府自我革命的严格规范。严格、纯粹、完全的规范主义进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国税权行使格局及其现实功绩,片面地对基准税制实施和税收优惠管理给予负面法治评价[32](p27-37),较少真正顾及我国特色发展模式和税收权力体制,以至于其法治主张的施行极易变得困难重重,严重者长此以往会降低税收法治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事业规划的支持功能。
与规范主义进路同时存在但区隔鲜明的是,大规模减税降费和留抵退税、科技创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健康中国、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发展规划,均需各式税收制度工具辅助施行:一方面,税制工具凭借其筹集财政收入和服务政府调控的功能定位,为各行业、各群体、各领域发展供给政府支持、减轻成长负担、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也为金融、产业、价格、管制、劳动、保险等其他政策工具提供运行资金,确保实施成效。这些税制工具通常以财税机关部颁税收规则而不是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并视规制对象变化而动态增减,凸显出法治发展的调控性、效率性、灵活性等工具主义进路。工具主义进路是指税制更多成为推行政府政策、服务国家发展的利器,税收规则的法源地位与法律治理更多具有形式化与象征性意义。尽管财税机关相较立法与司法机关更具税收管理专业性,更能有效应对相关行业的复杂经济态势,这在全球经济下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当下与未来尤其重要,但各级政府在税制工具的设计与运行上享有较大权力,人大、监察委、审计机关、司法机关等只能进行事后监督,一旦政府内部出现大量腐败、权力失衡、监督失效等情形,纳税人的税收确定性、预期稳定性、税制透明度均会走低,税收复杂性、肆意性陡增,税收中性更不存在。各国实践皆证明,税法中的工具主义进路将刺激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产生背离税收法治要义、诱导税收权力腐败、损害社会公平、削弱广大纳税人权益等极端危害[33](p67-76)。可以看出,行走在工具主义进路上,永不开启税法编纂是最优选择。
不难发现,规范主义与工具主义立场各有成长逻辑与发展需求,税收法典化中的风险和弊端亦来源于两大立场的现实纠葛和价值博弈。为避免出现税收领域的规范主义冒进和工具主义泛滥现象,有必要引入新的税收法治建设进路予以调和,竭力确保规范主义与工具主义进路在税法中的优势均能长效迸发,在税法中的劣势均能相互弥补与遏制。
(二)税收法治评价与建设的新基准:功能主义的税法进路
为调和不同的税收法治建设立场,可借鉴发端于社会学研究,在法学领域最早应用于比较法研究,近几年在民法、刑法、行政法、宪法、经济法等部门法中大放异彩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通过证成功能主义的税法进路,绘制规范主义与工具主义之外的税收法治评价与建设第三条道路,为选择最能推动中国特色税收法治建设的编纂方案奠基。
结合民法、刑法、行政法、宪法、经济法中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可知,功能主义税法进路由两大环节构成。第一环节,税制的创设、解释和续造需要首先考虑税制的目的及其在经济社会中承担的功能,从最适宜实现税制目的和功能的角度进行创设、解释与续造。税制应纳入何种法源层级出台、用何种解释方法适用、应如何修改完善,皆以落实税制目的、导向税制功能最大化为首要遵循[34](p23-49)。第二环节,为避免过分关注税制目的、过于偏爱税制功能而陷入工具主义进路,进而对法治内在价值构成冲击,使得税收法治有名无实,对前一环节得出的税收规则与解释结论,还要进一步接受法治审查,不同法律部门法治审查的方法和特色各有不同。
深入分析,功能主义税法进路相较规范主义与工具主义进路具有更大优势。规范主义进路推动税收法制提升各类法治品格,但这种推动力需要放置在社会系统中整体考察,评估规范主义进路的功能及其力度“是否为我国当前发展阶段所需要,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35]。一旦枉顾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实际,片面强调法治的形式理性,一味限制财税机关税权行使,降低国家收入汲取能力,压缩政府税收调控空间,冒进的规范主义进路不但会削弱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财政基础,更可能使税收法治因缺乏与我国发展需求的充分融合而走向盲目和僵化。相比規范主义下的传统税收法治评价与建设进路,功能主义税法进路力求创造出最能贯彻税制目的、最能释放税制功能的税收法源规则,但这绝非法治对国家政策与税收行政的妥协,而是对后者做温和渐进的法治化规制。之所以如此认定,是因为功能主义进路第二环节即对税收法源规则的法治审查旨在避免税制成为“可被任意打扮”的工具,既是在税制目的与功能之下尽力践行法定、公平、中性、透明、纳税人权益保障等税法原则,也是通过法治化审查增强税制法治效能,补充既有税制功能,加快实现税制指向的特定目的。综合来看,功能主义税法进路将税收法治与税收权力行使格局相结合,更充分照应我国特色发展模式和税收体制,两大环节不但融合了规范主义与工具主义进路的双重优势,而且确保了税收持续在法治轨道上协助落实国家战略。随着未来我国对税收法治与现代税收制度认识的不断提高,将温和渐进地实现税收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
(三)功能主义视角下“只制定税法总则”的正当性基础
在新的税收法治评价与建设基准——功能主义税法进路审视下,“先制定税法总则后定制税法典”“只制定税法总则”“只制定税法典”三种编纂方案中,“只制定税法总则”即放弃“总则+分则”“税收实体与税收程序法分别法典化”“税收实体与程序法综合汇编”等域外高度法典化模式,实行“税法总则+单行税法+税收法规和部颁税收规则”的半法典化模式更优。
1.税制目的与功能层面
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蓬勃兴起以及国家各类发展规划的相继提出,越发需要各级财税机关发挥其专业素养,有效应对税收复杂性与技术性日益叠加的新态势。值此之际,若将大部分甚至全部税收实体与程序规则编纂入税法典,内置强大稳定性、权威性特征的高度法典化模式不仅无法契合税收对经济社会的规制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这一客观规律,反而衬托出部颁税收规则的规制优势。结果便是,不但金字塔形的税收规则法源结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而且税法典中过时、缺位、无效的税收优惠会持续阻碍各级政府对不同产业、行业、地区的及时调控、灵活支持。若改为将较为稳定的税收实体与程序税制编纂入税法典,对较不稳定、更新频繁的税收实体与程序税制予以搁置、暂不编入,此一高度法典化方案仍不可行。这是因为,现代税法由财政收入规范、社会目的规范、简化规范[36](p13)以及其他规范构成,但在法律形式上,一项法律条款可能是不同特质规范相互交织的结果,难以完全剥离。若强行在各税种法中不同规范间或同一大类规范但稳定性不同的子类规范间作切割,很可能使同一法律条款支离破碎,不同法律章节中的条款却在税法典中强行排列组合,由此彻底打破了单行税法的现有体系,各领域税收规制规律的杂糅难以建立起比原有单行税法更强的融贯水准,尚未纳入税法典的余下各级税收规则也难以再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体系,税法典内外条款皆呈现规制碎片化、逻辑分散化、监管复杂化,既为税法典适用带来巨大障碍,加剧税收复杂度,税法典所具有的统一性、整合性功能也将彻底丧失。
只将当前各级税收规则中适宜编纂的共性规则、基本规定编纂入税法总则,本身即为注重把握编纂尺度、筛选妥适正确内容的体现。如前所述,除能够将税收法定、税制简化、税法体系化推进至更高层次,发挥对税收法治的引领性、支柱性治理价值外,属于税法分论层面的单行税法及其部颁税收规则依旧按照现有的、已经取得大量税收法治建设成就的税权实际运行格局运行,可达致税法统一性与开放性矛盾的平衡、规范性与灵活性规制方式的协调,有力防范对法典化文本可适用性和国家税制工具扶助功能的削弱。即便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越发复杂和不确定,我国税收法治建设仍然可以稳定渐进地推进。
2.税制的法治审查层面
功能主义进路上的法治审查,可由税制目的审查与税法教义学审查两大环节共同建构。在每一审查环节,“税法总则+单行税法+税收法规和部颁税收规则”模式更有利于加快实现各税种法、各类税制的形式与实质法治化目标,长久提升税收法治建设水平和国家税收治理能力。
目的审查层面,税制目的与税收规则之间需要符合比例原则:审查目的是否具有合法性、正当性或必要性、可行性;创设、解释或续造的税制是否是达成税制目的与功能的适当手段;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实现税制目的和功能的适当手段对其他利益主体的损害可以控制在最低程度;创设、解释或续造的税制引起的不利后果不得超过条文所承载的目的本身。表面上看,税法典中各税制的目的一致性或融贯性更强,实际上,为因应新兴领域的税法创制和传统领域的税法解释与续造,“税法总则+单行税法”模式由于相较税法典更为分散的结构,在税制与法源文本目的一致性或融贯性的判断上包容度更强,税制创设、解释与续造时规则与目的之间的比例原则审查更为宽松。是故,为税收规则决策者在法治框架内开发新兴税制工具、增强传统税制适用、优化各类税制要素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决策空间,强化了税法对经济社会传统和新兴领域的个性规制和协同规制能力,在符合形式法治原则基础上更好发挥筹集财政收入、维护税收公平、促进经济发展等税制功能,迈向税收实质法治。
法教义学审查层面,虽然各种法律创制、解释与续造方法在税制目的与功能指引下可以自由灵活使用,但应充分考虑条文的立法初衷、演变历史以及在既有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得出有说服力的正当结论。法治的最低要求,在价值上是法的安定性,在制度上是建构融贯的法律体系[37](p58-75)。在实现最低要求即形式法治后,法治还包括实质法治即法的正确性,核心在于分配与权衡上的正义,法定性与正确性也构成了法的双重本质[38](p134-135)。
具体而言,只设置税收总则,将各税种的共通性、基本性实体与程序规则编纂入法,各税种继续以单行税法的方式自我适用与完善,有利于在各单行税法间创造一种旨在推动税收法治向前深入的竞争环境,这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地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上已经展现出杰出先例。若某一单行税法在税收法律制度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和科学性上取得任何进步,例如法律中税收构成要件的精准规制、税收法律规则的细化完善、税收优惠法律治理能力的提升,都对其他税种法具有显著的示范与带动效应,激励处于相似监管情形、有着相似规制问题的部分税种法锐意进取,作出相似的法治化完善举措。相比之下,另一些税种法尽管并未处于相似情形,但其在税收法律规则规范化、法治化、科学化改造上越发显得落后,这同样会刺激相关税种法逐渐开启条款形式更新与实质內容优化。当更多税种法在税收形式和实质法治建设进程中迸发出示范与带动效应,便会形成单行税种法间的正向循环和竞争效应,从而加快建立现代税收制度。
相反,表面上看,税法典具有更强的法定性和体系性,但实际上,若在未来将大量甚至全部各级税收规则编纂入税法典中,无论是因应新兴领域的税法挑战,还是税种法治化的示范与带动效应,都将迫使税法典频频修正。首先,这不利于保持一部成文税法的安定性和法律权威,破坏了纳税人对税法的稳定预期和自信心,进而无法长久有效地安排投资、生产与生活;其次,税法典的频频修正与“税法总则+单行税法+税收法规和部颁税收规则”模式相比,前者提高了立法成本,降低了立法效率,更为财税机关凭借其专业能力和既有职权广泛介入直至控制税法典创造了合法空间,这绝非税收法治的正确之道;最后,我国极少存在法律尤其是重大法律出台后定期或经常性修改的立法惯例,民法典于2020年实施后,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出台适用解释,法典本身从未修改。因此,在并不理想、存在颇多限制的税收编纂环境中,只制定税法总则的编纂方案更能发挥财税机关对税收法治建设的功能优势,更能保有法典化文本对税收法治的优良功效,更能推进中国式的税收法治建设与税法现代化。
六、结语
经过税法编纂治理价值与实践隐忧的综合权衡,只要保持合适的编纂尺度,厘定妥适正确的编纂内容,我国宜开启法典化进程。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规范主义和工具主义立场更优的功能主义进路审视,只制定税法总则更能落实税制目的、发挥税制功能,更能经受税收法治的目的审查与法教义学审查,将税收形式和实质法治提升到新的评价与建设层次。税法典制定的前提条件和编纂环境在我国极不成熟,强行推进仅具有形式化、象征性意义,对税收法治的实质推进并无助益。学理与实务宜秉持谦抑审慎理念,正确对待税法编纂思潮。
参考文献:
[1]金辉.财税法专家呼吁制定《税法总则》[N].经济参考报,2020-01-21(08).
[2]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刘剑文.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现实路径[J].政法论坛,2015(3).
[4]Hirsch W Z. Reducing Laws Uncertainty and Complexity[J]. UCLA Law Review,1974,21(5).
[5]Donaldson S A. The Easy Case Against Tax Simplification[J]. Virginia Tax Review, 2003, 22(4).
[6]Pollack S D. Tax Complexity, Reform, and the Illusions of Tax Simplification[J]. George Mason Independent Law Review, 1994, 2(2).
[7]Erwin M E. Policy Analysis and Critique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s Simplification Study[J]. Tax Lawyer, 2003,56(3).
[8]邹新凯.结构性简约税法的理论证成与工具适用[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
[9]Tipke K, Lang J, Seer R. Steuerrecht[M]. O. Schmidt, 2015.
[10]钟芳桦.租税正义与一贯性原则:论Tipke租税正义理论及其对税捐法律的标准[J].台大法学论丛,2018(1).
[11]Kirchhof P. Der Verfassungsauftrag zur Erneuerung des Steuerrechts[J].Akademie-Journa,2002(2).
[12]Kirchhof P. Die Reform des deutschen Steuerrechts[J]. Zeitschrift für Staats-und Europawissenschaften (ZSE), 2010(4).
[13]施正文.税法总则立法的基本问题探讨——兼论《税法典》编纂[J].税务研究,2021(2).
[14]DAvout L. Das erstaunliche Projekt eines europ?ischen Wirtschaftsgesetzbuches[J]. ZEuP: Zeitschrift für europ?isches Privatrecht, 2019 (4).
[15]Kahl W, Hilbert P. Die Bedeutung der Kodifikation im Verwaltungsrecht[J]. RW Rechtswissenschaft, 2013, 3(4).
[16]Droege M. Steuergerechtigkeit–eine Demokratiefrage?[J]. RW Rechtswissenschaft, 2014, 4(4).
[17]刘剑文.财税法功能的定位及其当代变迁[J].中国法学,2015(4).
[18]Kahl W. Kodifizierung des Verwaltungsverfahrensrechts in Deutschland und in der EU[J]. Jus: Juristische Schulung, 2018 (11).
[19]Sloterdijk P. Die nehmende Hand und die gebende Seite: Beitr?ge zu einer Debatte über die demokratische Neubegründung von Steuern[M]. Suhrkamp Verlag, 2012.
[20]Droege M. Die Kodifikationsidee in der Steuerrechtsordnung[M]//Zukunftsfragen des deutschen Steuerrechts Ⅱ.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4.
[21]Kraft W. Zum Luxus eines Einheitsgesetzes: Aktuelle Uberlegungen zum finanzgerichtlichen Verfahrensrecht[J]. Zeitschrift für Rechtspolitik, 1985.
[22]董学智.论税法上不确定的法律概念[J].交大法学,2018(2).
[23]邓佑文.论公众行政参与权的权力性[J].政治与法律,2015(10).
[24]滕祥志.部颁税收规则:从形式到实质[J].公法研究,2011(2).
[25]叶金育.国税总局解释权的证成与运行保障[J].法学家,2016(4).
[26]徐伟功.我国冲突法立法局限性之克服[J].社会科学,2022(3).
[27]Meder S. Die Krise des Nationalstaates und ihre Folgen für das Kodifikationsprinzip[J]. Juristen Zeitung, 2006.
[28]Kirchhof P. Bundessteuergesetzbuch: Ein Reformentwurf zur Erneuerung des Steuerrechts[M]. CF Müller GmbH, 2011.
[29]Kirchhof P. Die Kunst der Steuergesetzgebung[J]. Neue Juristische Wo chenschrift, 1987.
[30]王霞.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研究——以法律的规范性及正当性为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31]朱宁宁.全国人大财经委:加强税法总则研究论证[EB/OL].(2021-12-08)[2022-08-20].http://ustr.gov/about- us/policy- of?fices/press- office/press- releases/2017/december/ustr- rob?ert-lighthizer-statement.
[32]席卫群,胡芳.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状况及指数化评估研究[J].当代财经,2019(12).
[33]邢会强.财政政策与财政法[J].法律科学,2011(2).
[34]劳东燕.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体系性控制[J].清华法学,2020(2).
[35]王吉全.习近平提出改革评价新标准[EB/OL].(2016-02-29)[2023-08-20].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229/c1001-28156660.html.
[36]陳清秀.税法总论[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2.
[37]雷磊.法教义学与法治:法教义学的治理意义[J].法学研究,2018(5).
[38][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的安定性与正确性[J].宋旭广,译.雷磊,校.东方法学,2017(3).
责任编辑 杨 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