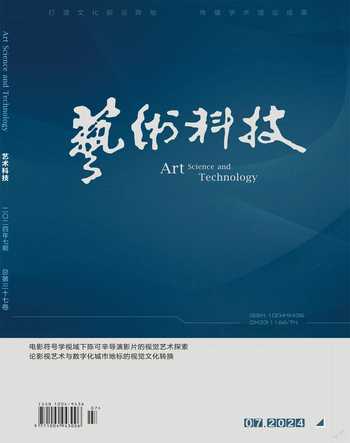毕赣电影中的作者·观者·角色三重梦境建构研究
摘要:目的:文章深入探究毕赣导演的作品,分析毕赣导演如何利用银幕构建梦境空间,拍摄出带有强烈主观情绪的、极其私人化的作者电影,同时探寻如何将其个人体验加上梦境的叙事空间,使电影展现出一层又一层梦境,使观者获得如梦如幻的观影体验。方法:依托精神分析中梦的理论和人格理论,将毕赣电影中的梦境空间分为作者梦境、观者梦境、角色梦境三种空间,分析导演的超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与银幕、现实之间的关系。结果:通过分析导演各个作品中的梦境空间发现,导演有意识地运用梦的机制和意象为文本角色塑造梦境,有意识地运用奇观和碎片化的结构为观者创造梦境,同时电影文本后涌动的潜意识为导演塑造了一场自我疗愈的白日梦。其创造的电影是理性与感性的交织,是三种层次的梦境空间的融合,给予观者如梦如幻般体验的超现实主义电影。结论:毕赣导演的电影作品中梦境空间的建构是有意识的创作,同时融入了潜意识。导演通过银幕梦境的建构,将自己深层的潜意识情感展现给观者并感染观者,引起观者强烈的情感共鸣,这体现了毕赣导演对自己内心世界与人类潜意识世界的深入探索。
关键词:梦的理论;俄狄浦斯情结;潜意识;超现实主义;毕赣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4)07-0-03
青年导演毕赣无疑是中国电影圈近年来攀升最快的导演,从偏远山区的婚礼摄像,到凭借处女作《路边野餐》一鸣惊人,迅速获得资本的青睐——得到5000万元的投资,再次创作长片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毕赣的电影大多是表现梦境,同时带有强烈主观情绪的、极其私人化的作者电影,个人的体验再加上梦境的叙事空间,使电影给观者带来如梦如幻的体验。本文基于精神分析视域,以《地球最后的夜晚》和《路边野餐》为例,从电影文本中的角色、观者、作者三个层面探析银幕与现实的关系。
1 角色梦境:长镜头下角色的欲望达成
1.1 电影创作与梦的运行机制
毕赣导演有意识地运用电影创作和梦的运行机制,为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的角色塑造了一个多小时的梦境叙事空间。尼克·布朗认为,“首先梦与电影之间有相当明显的相似性”[1]。毕赣将电影与梦境融合,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方法,用这种方法设计梦境空间的叙事逻辑、人物、符号元素,通过梦境展现角色的内心世界,也对前文的种种谜题作出解答。
首先是运用梦的运行机制来设置长镜头,实现梦境片段的深层叙事。弗洛伊德指出,“梦,完全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达成。这是一种被“超我”壓制的“本我”的欲望经过改头换面的达成[2]。主人公所有的愿望在影片后半段达成了。《地球最后的夜晚》的主人公因儿童时期母亲缺位,受到了极大的心理创伤。在梦境片段中,导演让主人公遇见了母亲并与母亲和解,弥补了主人公儿童时期的遗憾。人物的欲望、遗憾和压抑的情绪都在这层梦境空间中展现出来,毕赣通过这层梦境展现角色的内心世界,全面剖析了角色的心理。
其次是运用梦的运作机制中的凝缩作用来设置梦境中的人物。精神分析学表明,梦有凝缩或压缩的功能,外显的梦比内隐的梦具有较少的内容,即在梦中可以得到“数人合为一人”的例子。混合而成的影像,形状像甲,衣服像乙,职业像丙,这种人物也被称为集锦人物[3]。这种集锦人物在《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后半段梦境空间中也有出现,主人公在梦境中遇到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身上有死去兄弟的文身,也带着头骨,拿着乒乓球拍,象征着主人公还未出生就被打掉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集锦人物,是去世的兄弟与孩子的集合体,表达了主人公对两人死亡的遗憾。
1.2 意象符号的对照与互文
意象符号是情绪的实体化表达。在毕赣作品的梦境叙事空间中,充满了隐喻性符号。其中,具象化其实就是将梦思翻译为形象语言。毕赣在银幕上表现梦境就运用了具象化的手法,将思维、情绪转化为视觉形象在银幕中表现出来。其一方面运用符号将现实空间和梦境空间联系起来,形成对照和互文,正如《地球最后的夜晚》中水与火的意象。在影片前半段的现实和回忆部分,情人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水的意象,情人总是穿着绿色的衣服,出现在潮湿的环境中,而梦境空间中的母亲往往伴随着火的意象出现,正如燃烧的房子、火红的头发。前后叙事空间中火与水两种意象的对照和互文,展现了情人与母亲是主人公女性角色迷恋的综合体[4]。所以在毕赣的电影世界中,人物角色的属性界限是可以被打破的,一个母亲可以是和别人私奔的情人,而一个情人也曾短暂地做过母亲。两种意象的对照展现了毕赣对因果轮回的思考。另一方面,意象符号是人物情绪和思维的实体化表达,也是主人公梦思的形象语言。导演通过意象的设置,在梦境空间中表现主人公的情感和与其他角色的联系。在《路边野餐》的梦境叙事空间中,主人公所唱的《小茉莉》这首歌表达了沉默的个体对逝去亲人的无尽思念。同时,主人公帮老医生带的花衬衫和录像带,象征着老医生和情人的爱情。不同的意象符号蕴藏着人类对亲情、爱情的渴求,在梦境叙事空间中表达着人类共通的情感。
2 观者梦境:影院中非现实的观影心理
2.1 视觉奇观与语言奇观的展现
电影与梦境的关系,不仅体现在电影文本中的角色与其梦境上,还体现在电影观者和梦境的关系上,因为观影主体与做梦的主体相似,都具有梦幻、想象的特质。观者处在非现实的位置,这决定了观者对影片采取非现实观影态度,这种观影心理会让观者有种做梦的感觉,可以被称为观者梦境。
首先是影片中各种超现实奇观的展现,导演通过小镇奇观和语言奇观,让观者处在非现实的观影位置。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梦境的构造。“梦的肉欲性或官能性、梦的绝对自由、梦的绮靡特征以及一种能够唤起无限和永恒的氛围。”[5]毕赣电影中各种奇观的展现,如充满了舞厅霓虹灯的镇中心、屋内缓缓驶过的火车、隧道里的电视机,这些景观与现实中的主体功能、外形都不符合,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同时极具冲击力的视角又产生了梦幻性。通过这些超现实的奇观,整部电影呈现出迷幻感,观者无论是视觉上还是心理上,都可以感受到超现实的美感。
毕赣导演的电影中,方言的运用同样会使观者感受到语言上的隔阂和陌生,从而产生非现实的观影心理。无论是《地球最后的夜晚》还是《路边野餐》,导演都让方言贯穿整部影片,运用贵州话造成语言上的奇观化,让观者在观看时需要时刻注意字幕,从而产生一种隔阂。同时,方言的讲述也让全片更加贴合实际,使观者产生一种现实与非现实交织的错乱感,再穿插上运用方言朗读的诗句,观者从剧情中抽离出来产生碎片感。语言在整体上形成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让观者处在非现实的观影位置,产生做梦的感觉。导演使用小镇景观的奇观化和语言的奇观化共同奠定了整部影片的超现实主义风格。
2.2 现实·回忆·梦境碎片化叙事结构
梦境具有连续性、无逻辑性和非线性,毕赣的电影结构就是以此构建的。首先是连续性,观者观看完整部电影的过程就模仿了梦境的连续性,任何电影都是如此,这也是弗洛伊德认为的观影主体和做梦主体的相似性。其次是非线性,毕赣导演的电影叙事空间都是多重的、复调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和《路边的野餐》都是三重叙事空间,其中包括现实、回忆、梦境,主人公在多重时空中寻找自我。《地球最后的夜晚》讲述了主人公罗洪武在现实里丢失情人与母亲,在回忆的时空中寻找她们,最终在梦境时空中与其相遇的故事。最后是无逻辑性,毕赣的电影叙事空间是碎片化的,将现实抽离出来穿插在回忆中,现实与回忆时空的交织叙事使剧情变得扑朔迷离,没有任何逻辑。这样的碎片化叙事留下了许多谜题,影片最后加入梦境叙事时空,在这层时空中对前面的谜题和人物动机进行解释和回答,形成完整的回环叙事结构。
连续性、非线性和无逻辑性是梦境的特性,也是毕赣电影叙事空间的特性,将时间和空间打碎后重组,会使观者的时空观念在观影过程中被迫打乱,现实和非现实在心中混合后会产生一种超现实的暗示,这是一种“双重错觉”[6]。这引发了观者非现实的观影心理,导演从视觉、听觉、时空三个层面影响观者,使观影主体也成为做梦的主体。
3 作者梦境:文本后导演的自我疗愈
3.1 作者视域下的毕赣
毕赣这个造梦师将梦的理论和影视创作相结合,创造出角色的梦境和观者的梦境,而创造过程中涌动的潜意识也在为他自己造梦。分析其作品,能看到文本后导演潜意识的深海,他的潜意识潜藏在电影的各个部分。
首先从个人经历上看,毕赣出生于贵州凯里,故乡凯里一直是其故事的叙事空间。同时,毕赣的父亲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母亲是一个理发师,在毕赣小时候,父母不合最终离异,毕赣从小跟着父亲生活,母亲的角色在其童年时期一直缺席,这导致毕赣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出生于離异家庭。在主题上,无论是《地球最后的夜晚》还是《路边野餐》,主人公都在寻找自我并与自我和解。所以应用精神分析中的人格理论进行分析会发现,毕赣的潜意识深藏在其作品之中。因此,毕赣创作电影也是在为自己制造梦境,以实现对自我的救赎。
3.2 俄狄浦斯情结的暴露与治愈
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次。其认为潜藏在水面下的冰山即潜意识,更加深不可测,是动力的源头。而任何一种艺术创作,创作者的潜意识都深藏其中,这是依托方法论但又超越方法论的创作本质,所以电影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创作者的潜意识[7]。
深入剖析毕赣导演的作品可以发现,从电影的角色设置到电影的主题,无不暴露出导演自身的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情结又被称为恋母情结,取自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毕赣从小生活在离异家庭,作为出租车司机的父亲是父权的象征,母亲一直缺席。在这种情况下,毕赣的俄狄浦斯情结被父权压抑但没有得到消除,母亲角色的缺失使这种情结持续影响其成长,最终暴露在其电影中。
在角色设置上,从《路边野餐》到《地球最后的夜晚》,故事的主要叙事者都是一个来自凯里的男性,而这个男性总是缺少母爱的。陈升的母亲因病离世,而罗洪武的母亲在其小时候与一个养蜂人离开,两个主人公都在童年缺失母爱,同时在不断地寻找这份缺失的情感。在其他人物设置上,《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男主人公身边有男性角色死亡,这些角色其实是父权的象征,这些角色的死亡是导演潜意识中对父权的解构。俄狄浦斯情结的重点是弑父娶母,在电影角色设置上,毕赣完成了“弑父”,消解了父权,然后去追寻情人或者母亲,完成“娶母”的使命。所以不仅在角色设置上,整个故事的深层叙事逻辑就透露出导演的俄狄浦斯情结。其故事的叙事逻辑可以理解为在现实里缺失母爱的儿子在梦境中再次寻找到母亲。对毕赣来说,电影就是他的梦,深藏在故事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就是他潜意识的展现。毕赣让角色通过梦境实现与母亲重逢与和解,借此实现毕赣与自己的和解。
4 结语
毕赣导演构建出的三重梦境空间是由意识与潜意识交织而成的,毕赣有意识地运用梦与电影的相似性,同时释放自己的潜意识,向观者分享个人体验。导演的潜意识与观者的潜意识碰撞,能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导演的潜意识会感染观者,触及观者潜意识层面并发挥作用,造就优秀的梦境电影。毕赣银幕梦境的建构不仅给观者带来了如梦如幻的体验,还探索了新的电影拍摄范式,实现了导演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剖析,对人类潜意识世界的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 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136.
[2]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55.
[3] 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15.
[4] 李敬翔.梦是遗忘的现实:浅析《地球最后的夜晚》[J].视听,2019(6):83-84.
[5] 理查德·阿贝尔.法国电影理论与评论[M].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396.
[6] 楼俊辰.从《路边野餐》看毕赣电影的超现实主义建构[J].视听,2020(11):106-107.
[7] 王昱华.精神分析人格理论在电影中的无意识再现[J].当代电影,2020(7):12.
作者简介:吴贯豪(2000—),男,江苏南京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影视艺术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