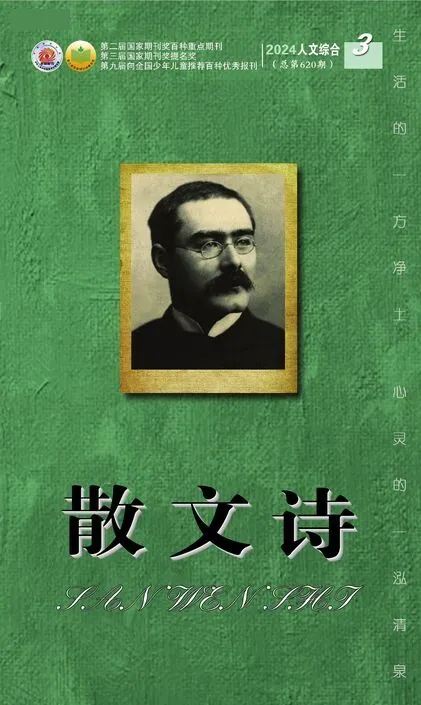乌贼悄悄隐藏自己的骨架
◎苗红年

图/王琼辉
浪 花
浪花的子弹似雪子飞溅,中弹的潮汐蟹却在雀跃,你们横行霸道,螯足张扬。如果分担多项工作是种负担的话,我们不妨学学那些家伙把每一桩事都干得悄无声息却凶猛无比:捕食。挖掘。防御。噢,可爱的朋友,你们从眼眶里伸出圆润的眼球,打探着澄明里游动的食物和我。
堤岸已经狼狈不堪,而涛声带着鸥鸟的唳声,擦碟者擦出金属般激越的旋律,只是为了黄昏慢慢登场。皮肤油滑的礁石如一头海豹,我一会儿骑,一会儿爬行着。想起身后的步步逼近的潮水,如果这时候我还没有撤走的念头,那就等着被围观而来的海蟑螂嘲笑吧。
世界的胸膛(礁石)千疮百孔。只有水在自娱,像一位魔术师在练习如何从无垠中掀起狂飙,又转换手法偷梁换柱,在退潮后把溺水者从原地隐失。在追逃中获得乐趣,而我的儿子却来不及佯装,也无法逃脱。一颗落在衣袖上,他用手掸了掸,仿佛隐匿的浪花,在润湿过程中带走记忆的滚烫。
我们跳出礁丛的围剿,刚刚还在追剿的弹片也悉数落尽,大海抛来一整张完美的沙滩。
乌贼悄悄隐藏自己的骨架
40 年前,我还生活在嵊山岛后头湾。那里的疾风与劲草计算出日历的趣味,海水夹杂浓烈的醉腔。眼前的蓝燃烧着,不断淬炼出昼夜。四季都有鱼群洄游而来,短暂的交欢,像母体里的精子用完美的泳姿荡漾着找到合适的配对。岙口里泊满刚刚从近洋捕获乌贼回来的舢舨,我在人群里接过外婆递来的一把利刃。
我挥霍着,像现在手中写诗的钢笔,空气里腥香阵阵袭来。古老的手法让人们得到了鲜活的经验:墨的射线终于遂愿,从寄居到贯穿脱离洁白柔软的小径(导管),脱离轻浮的骸骨实现了怀素般激情跳跃地抒写,同时也没有牺牲诗行的紧实抒情缠绕。
它将获得多种奖项,美食评委们开始品头论足:须足有嚼头,可以锻炼乳牙的生长发育。墨能养胃。在人们的体内荡气回肠,滑溜溜的皮肤有星光般的点睛之笔,从中可以判别出雌体与雄体,噢,细微的星象术正在揭秘。
这张丰富、多元的曲谱被坐在礁石上的婆娘哼成快乐小调,被一桩买卖成功定价,被唤醒了一门新型教义而受人尊重的挑剔,在分理后,乌贼尸身包罗万象,籽捣散后用来晒成饼。卵去咸菜汤里成为提鲜的佐料。肉体变成鲞时,泛出诱人的酡红。像酒醉的蝴蝶,对称的设计张扬出如某个画面里的受难之躯。海平线在不远处停止起伏,我不会美化苦难,也无意触及饕餮前面是锋利的剖割,后面是刺目与血腥的追赶。
悬挂在渔网制成的凉架里,一阵风过后,孩子们在母亲的教诲下,熟练地用手翻动这爿安静的泅水者肉体。
大海的熔浆是惨白的
一
风。地壳。树桩。海平面。无论硬的还是软的,万物的内心都可能藏着一只赴火的蛾子。昏沉的暮色掩饰不了它们扑腾的粉末,崖壁间,断翅随处可见波浪模仿岩浆。若是海星,它必有脱身和抬头遥望的想法。船队因送别而返航。
潮水休眠后又恢复了呼麦的精力。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漂流瓶。礁岩、沙砾、断楫、浪涛、逆水……的大合唱里暴露出阵痛与不安定因素。它们咬紧牙关,每一粒晶盐是一腔苦水压缩成的,又咸又涩。这愁眉苦脸的样子,随时会从我的身后喷出。“看样子,这老头要疯掉了。” 他(大海)不停地哮喘。口气中混杂着烟腔味,鱼与海鸥被一次次揪心。仿佛全是他咳出的痰,直到天色露出青面,神灵黥面的乌鸦衔来枝丫,准备填平眼前的坑坑洼洼。
二
干脆拧开盖子,挤了挤,清贫的波涌如同转世。小时候对捡破烂的迷信至今还没消逝,凭什么让扁平的身体保持住牙膏皮弯曲的形状,掘出船体木料里横穿的废铜烂铁,就可以换取童年甘甜的味觉。想着如跟屁虫一样,对物物兑换的模式乐此不疲。
总是要求切麦芽糖的刀片再次起落,残余的逻辑还在砥砺,我却放弃庇荫还心有不舍。想着有一天拿起锯齿,剖开翅膀中那对隐藏的骨架,对剧情中致病的描述怀有深深的歉意。我注定是那位沉沦于深水的观众。
面对波澜壮阔的布景,鼓掌后,我又说不出逃票的理由。
三
那海底下跳跃的海星是他正在调试的海拔高度,如果我潜入其中,像盛夏的果子,与女孩们攀比时尚的色香,谁又会感受到“清贫” 是美德还是羞耻。
我迷恋过漩涡。它那么自信,在辽阔的海面跳出一曲惊骇的舞姿。我一直认定它是大海零星的熔浆,摸一摸冰冷的时速。刀锋朝着同个方向盘踞,头颅在身体里陷落。看得出,内省需要多大的勇气,调整好焦点,把天空拉到海平线的高度。谁还会去质疑,笔直中,哪些是女孩们画出的星星,哪是她爷爷晚唱的渔舟?
四
暴风雨压近,世界如同一只单边擦亮的铜器
发出嗡嗡的低鸣
我们到底需要准备些什么
来捂住它的豁口,或者对即将落下的拳头
递上一团棉絮
瞧,那只寄居蟹正撕裂虾壳
津津有味的时光就是这样
别人忙于奔波。而另一位就这样毫无责任地活着
塌下来,就让那块酒鬼模样的礁石顶着
反正躺平者有自己的处世法则
平民的身躯。被多少风雨踩踏后
仍然拥护着筑起那道绵延的沙滩
暴风雨压近
每次鼓掌,拍瘪的都是冲浪者鼓起的腮帮子
落日画出斑斓的晚霞
却被一颗孤星淡定地收走
五
大海的熔浆是惨白的,浪花把沸点保持在0 度。她们麇集在一起,在黑暗里炮制出绚烂的不确定。
花鸟灯塔
被黑暗囚禁的拳头,慢慢松开遒劲的力量,慢慢松开卡在风暴喉结的喑哑,松开一团打结的光静伏已久的激情。松开闪电的隐喻,刺目的感染力……
它还在不停给紧缚的世界松绑。给悬崖下纷至沓来的马群解去缰绳,给受抑制的船队划出一条明亮的直线,给提灯的守塔人自由出入渺小的邮票。
它还在不停旋转,像意味深长的木马不断提升孩子们的斗志。
迎面而来的候鸟正在穿越低矮的灌木。它噤若寒蝉,为夜的防空洞,搭建供繁星与萤火虫交流的旋梯。
出 海
不远处,赭石如一枚棋子,等着不明的角力,天气依然没有好转的打算。西北风青睐着狗儿的黄毛:火苗与曙色交错,煽动出鹦鹉螺般交辉的星辰。岸上的人帮我们解开缆绳的结扣,海水怂恿木船离开港湾。
有人在登山,而我偏爱这低于海拔的深陷。
叔叔说:“你身旁的水总是微笑的。”
我立刻得到了鼓励与警觉,同时又想起班主任老师的脸。她曾经布置过作业,是用一个夜晚的时间来背诵白居易的 《琵琶行》,以至于我第二天在桌位上保持住“枫叶荻花秋瑟瑟” 和“犹抱书本半遮面” 的真实意象。微笑是编译者头痛的哑语。船,航行至洋地,我第一次站立在了世界的中央。没有浮标,铜制的司南赋予它最大的盲目。前方漂来一截断楫,它是孤勇者的代名词,带来暗示与沉重,却还浮着,像一具失魂的身体,把这个世界的谜托付给现场。叔叔说“看得轻淡些,否则容易走失。千万不要相信月亮是圆的,我们就是它缺失的那块。”
“但我害怕,叔叔。海水看起来并不完整。”
“鱼群在哪里,我们可以撒网了吗?”
我并不怀疑他捕鱼的技艺,就像他从来没有对我的学业有所苛刻,觉得能识几个字就可以,但我一走心就被诗歌迷住。蓄意绕道而行却没有游出来。那条鱼,省略了距离,在交尾过程中感受到爱的振荡。在螺旋上升的穿梭里,把自己献给那张扑朔迷离的网。
船身开始不停颠簸。与海水形成响板,仿佛风雨中的两位生死之交,彼此为对方低声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