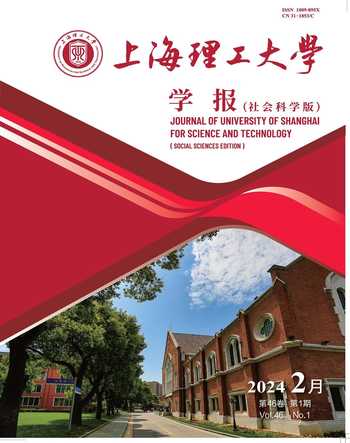蒂姆·温顿作品中的元素诗学
朱倩
摘要:澳大利亚作家蒂姆·温顿的作品中有许多描写自然力要素的佳作,他将土、水、火、气自然元素融入到文本的叙事空间中,形成了从山川到河流、从麦田到海滩,从日月星辰到烛火家园的主体们的活动空间,从而构建了物质与想象并存的诗意的自然空间。在此,自然元素连结了主体和客体,强调了元素本原和生命本真的统一,同时透露出温顿对人类诗意栖居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温顿;自然元素;自然空间;加斯东·巴什拉
中图分类号:I 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24)01-0043-06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11116419
自然元素是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澳大利亚当代作家蒂姆·温顿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蒂姆·温顿常把人物置于土、火、水和气等元素中,他在一个访谈中曾承认说:“我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以很直接的方式完全沉浸在自然和自然力对他们生活的冲击之中。我对这种自然力要素的联系很感兴趣。”[1]出于自然力的推崇,温顿视自然力要素为永恒的生命基础,这点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四大元素的物质起源学说是一脉相承的。比尔·阿什克洛夫特分析了温顿小说中的“水”[2],亚瑟·罗斯从气动唯物主义分析了温顿小说中的“气”[3]。国内也有学者从“极限运动”[4]和“文化霸权”[5]角度分析了气元素,但从整体自然四元素进行分析的文章还几乎没有。
本文以温顿的小说为考察对象,以加斯东·巴什拉所建构的火、土、水、气在内的元素诗学的物质想象为参照,来探讨生命本原、原初的自然空间。本文从元素诗学角度探讨其作品中所构建的自然空间,试图从这四元素中一窥温顿的自然观,进而提炼出与海德格尔-“诗意栖居”一致的人文精神,体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狂喜,启发人类对自然的思考。
一、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
土地是生命之根,是生命之源。人类对土地的尊敬、崇拜、敬仰与膜拜之心,使之称大地为母亲。温顿在访谈中也曾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安于变成尘埃。因为我们本都是碳基生命,源于星辰,也必将归为尘土。”[1]温顿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在1999年发表了纪实小说《回归土地:澳大利亚风景》(Down to Earth:Australian Landscape,1999)来表达土的重要性。在巴什拉看来,土地与意志相关,土元素本身具有意志,又把意志传递给人类,给人慰藉,让人依靠。泥土的形象在温顿小说中多次出现,土对小说中主体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对其他缺失具有补偿作用-主要是情感缺失,但也有相关的社会和心理缺失[6]。《土乐》中的人物总是对泥土具有一种天生的依赖感。福克斯喜欢在瓜地田边散步,弹奏的音乐起名为土乐,到达布鲁姆的时候想给乔吉写封信,纸笔在手中的时候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寄给乔吉的信封里也只是一茶匙的红色尘土。所有的思念、愧疚、计划、决定都只汇成一小撮红土[7]243。这撮红土暗示了他与土的亲近,隐喻土是他的根。他试图烧毁身份证件但是不离开这片土地,来保证自己与土地的联系,土地代表了他的“身份”[6]。土著人埃克斯则喜欢赤脚走在土地上,直接感受这片荒原土地的温柔与残酷。
除了泥土的形象,土元素最为典型的形象就是荒野和沙漠。温顿在访谈中说:“巨大的沙漠和荒芜景色使我们容易想到人类的渺小。”[8] 小说中荒芜的无边之地,代表着衰败的现实,这里是生命的初始与源泉,象征着主体凄迷中的追寻与探索,展现的是主体们艰难跋涉的不屈灵魂。《土乐》的荒野情节最为突出,正如伯德(Bird)所唱:“我爱着一个被阳光灼晒的国家,有着广袤的平原……”[7]116福克斯只想去荒野中[7]243。《牧羊人》中荒芜的内陆,是一片被开采矿产后遗弃了的荒野,杰克希在荒野中奔跑,开启了一场寻我的精神之旅;《浅滩》中维拉普山上的田园家宅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荒野。
除此之外,土地还以石块、山等其他形式出现:《浅滩》中山上的岩石;《牧羊人》盐湖中的人形石块。这些形象充满神秘,或给人安慰,或提供庇护所的崖壁,或供人做忏悔的对象。《土乐》中当福克斯到达皮尔布拉矿山的时候,这片土地“充满了力量和神秘感”[7]。巨大的岩石的严肃、压迫性体现了巴什拉笔下的土元素令人生畏的“对抗性意志”。
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泥土是人生命的最终栖息地,《牧羊人》中费坦去世后,被埋在了盐湖里[9]210。同时,温顿对土地有着“母亲”“精神家园”般的感悟和认知。拥有土地,就像拥有了独立的精神和庇護所。福克斯回想起与母亲在瓜地里的农耕生活,治愈了因家人车祸、天灾而造成的精神心理创伤,从心理情感上接受了现实,结束自我流放,在返乡中完成了救赎之旅。土地哺育人类,赋予了人们神奇的力量,是独立的存在,又保护人们成长为独立之人。土的另一个重要形象是(岩)洞,巴什拉通过对洞穴的想象来隐喻物质的根。温顿小说中的岩洞,都是指某种隐秘安全的存在,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某种回归到原初的愿望。温顿笔下的人物总是想着要逃开、躲藏,洞穴成为他们最向往的地方。《浅滩》中纳撒尼尔·库帕和丹尼尔·库帕经常藏到洞穴里,在那里点燃篝火。《土乐》中的福克斯从白点镇逃脱,逃到一个荒岛的岩洞中,这个洞与无花果和藤蔓完美融合,他在岩洞中获得了宁静,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安全感”[7]140,身体和心灵感受到了回归原初的温暖。
通过以上小说中土元素的阐释,温顿旨在说明:对土地的热爱和尊重是人类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是建立和谐的人地关系的基础,同时也是重建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前提。
二、火:在爱与死亡中重生
在《火的精神分析》一书中,巴什拉明确地指明了火的本质与精神:“这是一位守护神,又是一位令人畏惧的神,它既好又坏。”[10]13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火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产生了大量与火相关的隐喻和象征。升起的火焰唤起生命活力,燃烧的火焰则代表着死亡和净化,常使人想起地狱之火。火首先代表暴力与毁灭。《浅滩》中1956年的森林大火,吞噬了山上的小屋里的每件木制品,只留下了摇摇欲坠的石头。火会有死亡的味道,其暴力也有着保护的作用,《浅滩》中昆尼点燃一根火柴发誓要保护安吉勒斯[11]。
其次,火是温暖的,有着陪伴的功能,给人“几乎不可战胜的力量”[10]38。这种原始的火在温顿的作品中具有重要意义。燃烧的篝火作为“原始的火”成为其作品中最鲜明的元素。《云街》中,女人围着炊火烧煮食物,孩子围着火柴堆嬉戏;《土乐》中,福克斯在荒岛上点燃篝火,有时候只是为了看见点什么;《牧羊人》中,杰克希点燃篝火,并不是因为冷,只觉得火可以陪伴[9]49。这种火温暖,给心灵以慰藉,像朋友、家人一样给人以陪伴。
无火焰的火也在温顿作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代表精神上的指引、救赎与信仰。巴什拉认为“可以把指导着信仰、激情、理想和人生哲学的某类遐想同火这种物质本原联系起来”[10]。自然界中的日月星辰是大自然永恒的光芒,这是温顿笔下重要的无火焰之火。《云街》中,奎克守护麦田时,南十字星的光冲破了停滞的时间直指奎克的灵魂深处,驱逐了他心中的阴霾,让他找到了人生归处。最后,奎克和罗丝带着费希和儿子去旅行,他们晚上点燃篝火,躺在大地上,满天的星光将他们融入庞大的宇宙空间系统中。温顿甚至把《云街》这部小说最后一节命名为“月亮,太阳,星辰”,这些无火焰的火代表着庞大的宇宙的奥秘。《牧羊人》中,温柔清冷的月光是火最富有诗意的化身,它照耀着游荡的人,那巨大的白眼睛向下凝视,照亮内心,引导灵魂,让人内心平静又赋予人力量。《土乐》中,月光让福克斯顿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7]338。《浅滩》中描述的无处不在的桅灯、街灯、泛光灯、相机闪光灯、霓虹灯、信号灯、电视灯、反射灯、大吊灯、手电灯,这些无火焰的火是现代都市中喧嚣、拥挤的表现,冷冰冰的工业化的产物,反衬出人内心的孤独。
火,除了象征光明,还有着神性的光辉,象征着净化和重生。巴什拉认为“火燃烧起爱和恨,在燃烧中,人就像火中凤凰涅槃那样,烧尽污浊,获得新生”[12]4,因此火具有净化的内涵,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烛之火,其像精灵一样住进人的心里,让孤独的人的心里升起一团火,拯救自己和他人,获得精神自由。奥瑞尔总是在深夜点燃一盏烛火。她虔诚的动作表明,其一直深陷于费希事件的痛苦之中,灵魂不断受到内心的炙烤,希望通过火的洗礼得到救赎,走出痛苦,获得重生。她帐篷中的烛火也很容易让人体会到巴什拉笔下火的温情。烛火是家园,是归宿,是对主体的救赎和洗礼。
除此之外,火是“超生命的”[12]13,生命就是一种火[12]51。火与生命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火的产生和熄灭预示着生命的开始和消逝。“火是一种激烈的元素,被认为是生命力的象征,是行动(Tatigkeit)的象征。”[13]130《云街》中描写了奎克身体里发出的生命之火,他与罗丝的彼此遇见,就像两束光相遇碰撞出火花[14]278。这些火使周围的阴影徘徊、止步、颤栗。他们相遇,彼此找到了一个新的住所[14]278。奎克看护麦田时,在一次瞄准袋鼠过程中,在准星镜里看见了自己。自此,他大病了一场,浑身散发光芒。他就像一个六十瓦特的地球仪一样发光[14]192。火是巴什拉首要的研究对象,是他元素诗学的源头,温顿也在作品中把火与生命、死亡、毁灭联系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巴什拉对火的物质想象。
三、水:生命本源与永久回归
水与火一样,都有好有坏,但水比火更早存在。这是一种比火更女性、更温和的本原,这种更为稳定的本原,通过散发更隐蔽、更简洁、更简单化的人性力量而具有象征性[10]6。在大自然中,它是唯一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元素,如蒸汽、露水、冰雪等。这一特征又凸显其美学效果:透明、流动、平静、镜面效果、可挥发性、可穿透性。这些特点让水“可以被穿透”,体现了其无限的包容,因此具有很深的象征意味。
小说中水无处不在,人们在水上航行、潜入水中、生活在水的边缘。很明显,大海和河流是温顿个人经历的重要方面,水不仅仅无处不在,也是他故事的背景,有时甚至是主体本身。温顿借着水将现实与非现实联系起来,水里映照出记忆里的童年、风景、梦想。在其作品中,有各种形式的水反复出现:海水、泉眼、井水、暴雨、瀑布、潮水潭、小溪、河水、雨水、大海等。
水与净化、皈依相关。“水具有一种内在深处的强大力量,它能净化内在深处的存在,重新给予有罪的灵魂以雪的洁白。”[10]158 《云街》中的主体们都与水有着深厚的渊源,水在文章中起着重要的叙事作用。奥瑞尔在水中受洗,在水边收获爱情;水也带给人悲痛,在玛格丽特河里,费希落水成了智障。除了悲痛之外,水的可吸收和洁净功能使费希脱胎换骨,实现永久的回归。水本身代表着自由,是一种逃离和自由的媒介[2]。水流动着,自由来去,所流之处,万物生长。奎克与水有着异常的亲密情感,他经常带着费希划船,长大后出海打鱼。每次在水上待一段时间后,他感觉又找回了自己。《浅滩》中的奎尼最钟情于水和大海。在水里,她自由地游泳,感受水的灵动,在孤独中寻求心灵的宁静。人们一直在渴求水,维拉普山上一百八十多天没有雨水,人们幻想着在古老河流的深处流淌的泉眼。《牧羊人》中“寻找水”“活下去”是杰克希一路奔波的动力。
水帶来希望,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更没有希望。大海是水的另一个典型代表。作者是在海滩上长大的男孩,远望大海,凝视就慢慢变成了沉思,也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其笔下的人物几乎都与大海保持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其早期作品中,海洋占据着突出地位。主体们都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大海的热爱和向往,生活中的各种欲望、性与爱、生与死,都在深邃海洋中得以表现。《浅滩》和《土乐》里的大海是主体的活动场所,是一个避难所。奎尼喜欢在贝壳里听大海的声音,丹尼尔也“渴望山峦、大海、错综复杂的干枯水道”[15]87。《土乐》中,被禁锢在海景房里的乔吉喜欢冲浪和游泳,在她眼里,大海代表着自由,是她苦闷生活的避难所,只有在海边的时候,才能平静地面对自己的困惑、恐惧,从而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除了海洋,河流也是气韵流动之灵物,那些孕育人类的母亲河成为温顿构建文本的重要意象。巴什拉认为,水是用来滋养大地和空气的,因而水进入了哺育本原之列[10]15;“水是摇晃的本原,这又是一种水的女性特征,水像一位母亲那样摇晃”[10]145。水与生命、死亡和母性的联结成为温顿对于人的生存的一种思考,他借助水元素来赞美自然。《云街》中的玛格丽特河,《浅滩》中的哈克河和桑德河,它们有时平静深邃,有时欢快奔腾,赋予人们深沉和奔放的爱,滋养着人类的生命和灵魂。对于温顿来说,“珀斯周围的那些西澳的河流和海岸是唤起他的情感的地方”[11]84。“水的深刻的母性”[10]15的形象伴随着主体们的成长。无论是奎尼、奎克、珍妮弗、福克斯,还是乔吉,她们的逃离与回归都经历了河上或者是海上的漂浮。水面摇晃着一个个微缩版的家宅——船只,船是“漂浮的空间”[16],是一个个微型的世界,在水面上漂流,犹如在母亲的子宫里被重新孕育,使主体认识自己的身体和身份,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联结。
巴什拉指出,相比于土与尘、火与烟,水的消融更完全,水似乎有助于一种彻底的死去,一种永久的回归。“静观水,就是流逝,就是消融,就是死亡。”[10]53比尔·阿什克洛夫特在解读温顿作品中水的隐喻性时说,水是家园的象征,是一个可以联想到死亡、重生和救赎,产生空间归属感的地方[2]。他写道:水,死亡和更新紧密地联系在温顿的小说里。无论是从水边下水,从梦中浮现,还是从自由的水中浮现,或是在自由潜水中摆脱死亡的诱惑,水都是重生的媒介[2]。《蓝背鱼》中母亲朵拉去世时对亚伯说“我们来自于水,属于水”[17]76。在水中死亡带有母性色彩,正如巴什拉所说,在水中死亡意味着“死者重新交还母亲以求再生”[10]81。水与生命、自由、死亡连结在一起,构成了温顿小说中重要的主题。
四、气:自由生命与灵魂的追寻
气与呼吸有关,呼吸与生命相关。气是维系生命的重要元素,象征着生命,一刻也不能停止。巴什拉认为,气作为自然四元素之一,它的运动是所有意象中“最为根本性的”[18]17。它赋予生命以最本质的呼吸,它盘踞在天与地之间,维系着这两个世界[19]15。为了强调气的重要性,温顿用“呼吸”作为小说的标题,此作品中所有的冲浪、滑雪等极限运动,都与呼吸密切相关。女主人公伊娃(Eva),玩自我窒息的游戏,失去呼吸,从而失去生命;派克为病人做人工呼吸,都暗示了呼吸对生命的重要性。《云街》中,费希(Fish)溺水,因失去呼吸成了智障儿。就连《云街》里的大房子,也在罗丝的孩子出生后,呼出了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无痛的气息”[14]385。亚瑟·罗斯认为,温顿的文本中,呼吸是一种神学上的科学精神(theologico-scientific pneuma),可以指呼吸的物理功能或者圣灵本身,是处于物质和精神之间的,一种超越了死亡,但是还没确定为生命的“残留物”,他认为温顿通过“一个生理呼吸的过程来开启一种精神上的表达”[3]。
气是透明的,但蓝天、云彩、鸟儿和风都与气相关,在小说里象征了自由,代表漂泊的灵魂对自由的向往;它有时带着气味,有时带着声音,是传递信息的使者。温顿笔下的人物喜爱风,也是因为风带给他们自由的感觉。《云街》中,费希喜欢风,喜欢站在院子里看鸟儿在风中移动的方式,他会激动地打招呼:“Hello,风!”[14]60《淺滩》中,奎尼喜欢爬到风车上,听风的叹息[11]16。《土乐》中,乔吉在海景房的露台上吹着海风,轻柔的南风吹拂,带走内心的苦闷与烦扰。乔吉说:“在中西部的海岸,风也许不是你的朋友,但它一直会是你的邻居。”[7]141 风是自由的精灵,南风吹拂,吹走闷热,带来凉爽。有时,风又露出其暴力的一面。在岛上,福克斯面对暴风雨,只能缩在洞穴里。有时,风代表一些“宏大的东西”[7]247-死亡。福克斯遇到的老妇人贝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想追求“宏大”,例如旋风、日落、山脉、两英里宽的红河。福克斯弹奏土乐时回忆起母亲去世的情景,风成了死神,狂风就是死亡的预兆。母亲被狂风拧断的树枝插进胸口而死去。岩石下的飓风“都像母亲离世时的风一样,他对风太了解了”[7]360。气与水火一样,是好的也是坏的,它代表着自由,也可以带走生命。
风是流动的,可以带来声音和味道。如卢梭赞美自然的声音一样,温顿也在小说中赋予自然言说的能力。卢梭曾高度赞赏自然的语言,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人们所使用的最普遍、最有力、唯一的语言,就是自然的呼声。”[20]91 福克斯用一根尼龙线弹奏出的音乐,与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讲到的无弦琴(即“宇宙七弦琴”,那是由森林上空的风拨弄松树的枝叶发出的天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道德经》里也说,风声是大自然的孔窍里吹出的音乐。《浅滩》中,对于奎尼来说,躺在蕨丛里聆听自然的声音可以让她几个小时陶醉。自然界中,“有生命之物相互呼应着,模仿着本原的声音”[10]237。鲜活的自然世界成为了“叙事的场所(a site of narrativity),……具备了自然的叙事能力”[19]283。
声音是对自然的模仿,在《土乐》中,无论是用吉他、曼陀铃、小提琴还是班卓琴所弹奏出来的声音,都只是自然声音的模仿。土乐所发出的嗡嗡声不仅仅是一种感官上的解脱,还是精神上的回家,“撕开了他在存在、生存和情感之间建立的屏障”[6]。那根尼龙钓鱼线发出的“Boom-booma-boom-boo!”的唯一的音符,“代表了一个命令,一个上帝,一个愿望,一个律法……”[12]313此时的福克斯,与卢梭在《遐想》中任舟飘游在水上的无欲无为,与生态运动的先驱约翰·缪尔(John Muir,1838-1914)在田野报告中体验到的物我两化,与中国老庄天人合一的境界都如出一辙。那一刻,“万物在歌声中节律性地运转”[21]67。人物完全融入自然,传递了万物与人类本质一致,人与自然同根同源的生态主张。
五、结语
温顿作品中充满对四种自然力元素的礼赞。这些原初元素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相互交融、渗透、辉映,构成了一个诗意立体的自然空间。在其对这四大元素赞颂的过程中,没有像歌德那样高声地讴歌自然“水啊万岁!火啊万岁!……欢呼四大,地水火风!”[22]527,但是人们似乎也看到了“物我共生”的呼求。正如温顿所说:“我们需要充分认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赖性,虽然我们只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然而所有物种的命运都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1] 巴什拉通过对四元素进行整体性的诗学阐释,构建了一个诗意的、和谐的、原始的自然空间,表明人与自然是一体的。温顿的作品延续了这一灵性的自然空间,自然力元素意象把人类唤回到最原初的状态,表明人类与自然是平等的,人只不过是生命之链的一环。作者对自然力元素以及生态环境的关注,正是对以“整体论”为最基本的哲学立场的生态诗学的一种观照。因而,本文分析表明,温顿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理念- 自然元素本是具有生命力量的,以及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同质性,寄托了作家“万物是一”“天人合一”的生态诗学思想。这也与澳大利亚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生态保护意识相呼应。作家以一个环保主义者和艺术家的身份,书写澳大利亚的自然元素,赞美自然,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奏响了“诗意栖居”的绿色文学序曲。
参考文献:
[1] 刘云秋.蒂姆·溫顿访谈录[J].当代外语研究,2013(2):61-65.
[2] ASHCROFT B.Water[C]//MCCREDDEN L,OREILLY N.Tim Winton:Critical Essays.Perth:UWA Publishing,2014:16-49.
[3] ROSE A.Tim Wintons pneumatic materialism[J]. Interventions,2020,22(5):641-656.
[4]徐在中.极限快乐与危险游戏——评蒂姆·温顿的新作《呼吸》[J].外国文学动态,2010(5):25-26.
[5] 侯飞.极限运动背后的霸权——评蒂姆·温顿小说《呼吸》[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5):121-126.
[6] CRANE K.The beat of the land:place and music in Tim Winton's Dirt music[J].Zeitschrift fur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2006,54(1):21-32.
[7] WINTON T.Dirt Music[M].Sydney:Picador,2004.
[8] 刘云秋.蒂姆·温顿访谈录[J].外国文学,2013(5):149-155.
[9] WINTON T.The Shepherds Hut[M].London:Picador,2019.
[10]加斯东·巴什拉.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M].顾嘉琛,译.长沙:岳麓书社,2005.
[11] MURRAY S.Tim Wintons “New Tribalism”:Cloudstreet and community[J].Kunapipi,2003,25(1):83-92.
[12]加斯东·巴什拉.火的精神分析[M].杜小真,顾嘉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13] BOHME G.Goethes Faust als Philosophischer Text[M].Zug:Die Graue Edition,2005.
[14] WINTON T.Cloudstreet[M].London:Penguin,1998.
[15]蒂姆·温顿.浅滩[M].黄源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6] FOUCAULT M.Of other spaces[J].translated by MISKOWIEC J.Diacritics,1986,16(1):22-27.
[17] WINTON T.Blueback[M].Australia:Penguin,1985.
[18] BACHELARD G.LAir et les Songes[M].Paris:Libraire Jose Corti,1943.
[19] MENNIG M.Dictionnaire des Symbols[M].Paris:Eyrolles,2005.
[20]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1]约翰·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M].郭名倞,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22]歌德.浮士德[M].钱春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