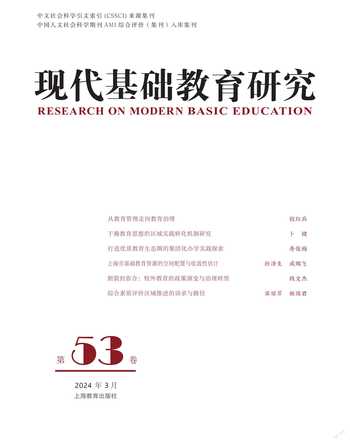割裂到弥合:校外教育的政策演变与治理转型
钱文杰
摘 要: 校外教育既要立足学生的补充性需求,又要回归教育的公益性本质。经历了公主私辅、公兴私盛与公弱私乱等阶段,校外教育发展面临着政策激励、规范引导及政策约束的转向调整,以应对利益驱动之下乱象丛生的现实困境。应当坚持从行业自律性、行政主导性和家校协同性等多角度出发,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在公私分化校外教育中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关键词: 校外教育;公私分化;政策演变;治理转型
据统计,我国青少年每年累计假期和校外时间近170天,他们大约84%的成长空间在校外。义务教育更是经历了“高校内竞争、低校外竞争、低补习参与”到“低校内竞争、高校外竞争、高补习参与”的结构性转变,中小学生普遍在校外培训机构接受培训1,供给主体也具备多元性特征。近年来,作为正常教学有益补充的校外教育发展迅猛,同时也面临校内校外同质化、公私逐利趋同性等瓶颈,尤其是商业思维惯性所带来的行业混乱,《人民日报》就曾四问校外培训:“这是做教育,还是做生意”“这是教知识,还是教套路”“要深挖病根,更要对症下药”以及“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怪圈怎么破”。2 为此,2021年7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3,开启了深化校外教育治理的新阶段。
一、政策与实践:校外教育公私分化的演化逻辑
在“扩大到学校范围以外”全球教育发展的总趋势下4,人们对学校范围以外的教育机会、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等的期待日益增强,这也带来了公立与私立校外教育此消彼长的发展与困顿。
1.公主私辅:校外教育的政策激励
在基础教育未普及、学校教育不完善的特定时期,校外教育起初是为了应对学校教育资源有限、学生校外生活贫乏等现象,表现为一种具有官方背景的青年宫、少年宫和少年之家等事业单位,提供不完全竞争的准公共产品性教育服务,是“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学校,开展文体娱乐活动的场所”。例如,1957年4月,教育部、团中央联合印发的《关于少年宫和少年之家工作的几项规定》1,明确规定了“配合学校”的基本任务,例如“配合学校教程举办各学科的辅导讲座、专题报告会”。
1978年之后,公立性校外教育组织全面恢复并再迎新机,县以上的少年宫已由1979年的92所发展到1984年的700多所,并广泛开展趣味性、实践性等教育活动。但是,这种模式也面临着经费保障不足、个性化服务有限等挑戰。一方面是要转变以财政为主要经费的运行机制,探索提供有偿服务的新模式,1986年颁布的《青年宫、青少年宫管理工作条例(试行)》2 和1995年颁布的《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工作规程》3 都提出了“通过开展有偿服务的形式以解决活动经费不足”的方案。另一方面是调整以公立性为单一主体的框架结构,“动员和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发展校外教育事业”,民办校外教育培训组织应运而生。
2.公兴私盛:校外教育的政策引导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校外教育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特别是以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和2004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印发实施为契机,呈现差异化发展的上升态势。其中,针对公立性校外教育有如下举措:一方面是逐步建立统筹协调机制,例如,2000年举办了由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以及团中央等多个部门共建的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全国各级各类青少年学生校外教育工作。另一方面是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扶持贫困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建设,覆盖全国的校外教育网络初具规模。截至2008年,“国家支持建设县级未成年人活动场所1092个,地方自建769个,全国90%的县拥有了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免费向农村留守儿童开放的活动阵地不断涌现。4 同时,民办校外教育服务功能及范围也不断拓展,例如,少数少年宫市场化的转型改制,从少年宫到少年宫有限责任公司;新东方、弘成教育、环球雅思等培训机构相继入市。
从公私分化的侧重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目标导向的分化,公办机构强调将校外实践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重视对校外活动场所的建设与规范5,以及政策文本中“社会育人环境建设”“思想道德建设”和“公益性作用”等主题脉络;6 民办机构突出将校外培训作为校内课程的巩固,在去异存同的发展思路下积极向学校教育靠拢,组织放学时间、寒暑假和节假日等课外辅导亦成规模。另一方面是组织经营的分化,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拨款性事业单位,大多是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进行梯队建设,师资培训也被纳入国家教师培训予以统筹安排,“在科技类、实践类、活动类与艺术类课程建设的合作上,师资合作是少年宫与中小学校最重要的合作形式”。1 与之相反,民办校外教育机构的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水平参差不齐、管理体制混乱以及人员流动性较强,校内教师的校外兼职问题严重,引发了民众对教学质量的质疑。
3.公弱私乱:校外教育的政策约束
作为21世纪第一个国家级教育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 既强调“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又突出“规范各种社会补习机构和教辅市场”,特别是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大力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政策导向之下,校外教育机构却又层层加码,呈现一种“公弱私乱”的发展态势。其中,既包括部分少年宫违背公益性原则获取营利性收入,以及违背学校、校外双重互补原则而成为学校教育的延伸3,学科培训占半壁江山,应试升学成金字招牌,甚至沦为培训考级的圈钱机器;也包括私立性校外教育机构市场化竞争愈演愈烈,学科类培训呈“井喷式”增长态势,行业规模和市场资本连年上升,例如,2015年平均每1.45天就会产生一起教育培训融资。
为了回应人民教育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一方面是强调少年宫公益性的素质教育回归,进一步加大和规范公立性校外教育的政策引导与财政支持。例如,2021年颁布的《关于开展“双减”自查清理工作的通知》4要求全面开展培训项目自查工作,并对学科类培训项目予以停办、清理,引导开展与中小学、社区联动的兴趣活动等。2022年颁布的《青少年宫管理工作条例》5 第22条规定,“严格执行国家关于校外教育各项规定,一般不得开展学科类培训。不得出租或者变相出租,不得用于与青少年宫宗旨和任务无关的经营活动”;第24条规定,“在坚持公益性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收取培训及活动的成本费用,作为运营成本的补充”,实现“有偿服务”向“成本服务”的公益性本质回归。
另一方面是民办校外教育机构分工负责分散治理向联合参与专项治理的演变,形成了一种由教育系统牵头的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受制于立法闕如、监管不力等问题,民办校外教育机构大多是以教育咨询(服务)公司等市场主体开展活动,双重身份带来了市场监管无抓手、教育执法无权限的“真空地带”,教育系统更多也是通过规制体制内的教师行为以实现利益无涉。例如,2015年教育部《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6 将治理有偿补课纳入督导检查的重点内容,并定期开展专项督查,本质上遵循一种校外教育“外部”治理的行为逻辑。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7 提出“规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严格办学资质审查,规范培训范围和内容”,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8 则正式吹响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的号角,形成一种“齐抓共管、高效联动、密切配合”的共治格局。
二、现象与根源:校外教育行业乱象的比较分析
校外教育由热及乱、乱而失范,“傍品牌”“搭便车”和“打擦边球”等投机行为屡见不鲜,“包教包会”“零基础入门”“万中选一好老师”等营销广告漫天飞舞,“双减”之下的校外教育行业转型也使得矛盾纠纷呈现“井喷式”增长。
1.非均衡分布:校外教育纠纷的差异分析
以涉诉案件为例,截至2021年6月,符合条件的民事判决书共60292份,结合彼时校外教育机构数量与学校数量基本持平的实际1,进一步得出28.57%的平均涉诉率。从机构分类来看,公办校外教育机构332份,民办校外教育机构59960份,后者俨然成了行业乱象的“重灾区”,并且多以校外教育机构的败诉而告终。从地域分布来看,省级行政辖区分布差异显著,教育资源均等化程度较高的北、上、广地区案件数量相对较多,也有研究发现教育均衡发展对学生参加校外培训具有显著负影响。2 从涉诉时间来看,从2012年及之前的102件到2020年的20989件,整体上保持了一种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公立性校外教育机构呈波动式增长;私立性校外教育机构呈直线式增长,尤其是2018年以后的案件数量激增,专项治理之下行业发展的不规范问题集中显现。
在“公少私多”行业乱象的非均衡分布中,一方面是公立性校外教育机构的服务性纠纷,作为原告、被告应诉的案件数量、胜败概率等大体相当,作为被告也多以生命权、健康权等侵权纠纷为主,是否“尽职尽责”以及“存在过错”构成了法院裁判的根本考量,并且在校内、校外人身侵权案件中的责任划分具有同质性。另一方面是私立性校外教育机构的市场化矛盾,不仅作为被告的占比高达86.13%,与此同时,作为被告应诉的败诉率也高达95.36%,突出反映了行业经营的混乱无序。特别是在预付款消费模式之下,不仅合同纠纷是消费者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而且合同纠纷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群体性纠纷多发。
2.深层性矛盾:校外教育内卷的恶性竞争
内卷时代引发社会性焦虑,也带动了校外教育市场的虚假繁荣,甚至形成了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一套教育体系和产业集群,其中的纯商业性经营思维也引起了管理混乱、师资造假和虚假宣传等行业乱象,不仅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还造成学生的不堪重负、家长的疲惫不堪,进一步加剧了恶性竞争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式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教育愿望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在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中,校外支出占三分之一3,很多家长既感叹内卷之艰辛,又不断加码教育投入。4
在教育场域里,为了占有更多的文化资本、掌握更大的文化权力、占据更高的场域位阶,不同竞争主体总是处于持续的争夺和较量中5,资本扩张中的校外教育也是充斥着(恶性)竞争,并对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构成严重冲击。首先是机构与机构之间,行业内存在严重的抄袭、挖人、竞相压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次是通过超纲教学、提前教学等“抢跑式”教学吸引生源,有的更是通过与学校勾连牟利、采取不正当手段高薪挖抢学校师资等方式6,破坏和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再者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竞争不断升级,扩大了城乡家庭、高低收入和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家庭之间在校外培训活动的参与率上的差距1,可能会进一步激化教育不平等矛盾。最后是学生与学生之间,近乎全员参与的校外培训加剧了学生群体性的“内耗”和“空耗”。
3.逐利化经营:校外教育利益的博弈驱动
中国家庭历来高度重视教育并保持着对教育投资的极大热情,对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投入具有工具理性和情感表达的双重特征。2 与此同时,利益驱动型服务本身又带有隐蔽性、投机性和松散性等特点,特别是在教育收益、服务成本以及行业管控等博弈性角力之下,行业乱象也就极易出现。
首先从收益角度看,主要源于家庭教育支出,而家庭教育支出又存在一种较为明显的邻里效应,特别是同社区平均家庭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依然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3 移动支付比例上升,以及教育贷款金融政策支持,也进一步拓展了校外教育支出的发展型消费。其中,教培机构往往掌握着市场定价的主动权,价格竞争、市场溢价等问题突出,虚构、诱导构成了市场典型套路,发展出了一种失衡供需结构下的非协商性经营模式。
其次从成本角度看,成本涵盖场馆建设、课程开发、师资队伍以及市场营销等费用。公立性组织靠财政,却又面临经费不足的普遍性问题;私立性机构靠市场,但又隐藏市场逐利投机的先天性局限。资金流压力之下,“开源”与“节流”也成了经营者的惯例。一方面是积极销售商品,回笼资金;另一方面是努力控制成本,压缩投入。
最后从监管角度看,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法律主要是调整体制内的教育关系,但是教育法律制度对于教育行政执法方式的规定偏弱,一些违法行为的追究存在制度上的缺失。4 特别是在早期激励、引导的政策背景之下,行政干预校外教育更是表现出了零星分散、滞后缓慢等特点。例如,部门间缺乏长期有效的联动机制,教育行政强制又多依赖于其他部门联合执法,实践中的无证经营“黑班”问题严重,甚至形成了一种“民不举、官不究”的执法潜规则。
三、自律与他律:校外教育共治格局的现代转型
“教育治理呼唤社会参与”5,社会参与是现代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同治理的普遍性逻辑也为校外教育治理提供了结构性支撑。应规范、引导教育发展的良性“差序格局”,以克服“双减”政策执行的碎片化困境。
1.市场化公益:校外教育治理的自我规制性
自我规制具有公益取向,市场化公益行为是现代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处理公益性事业与市场关系的行为模式。6 校外教育的自我规制既包括主体对自身行为控制的“自治”,也包括集体对成员行为约束的“自律”,是成本最小的善治。
针对公立性校外教育机构,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公益事业属性,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拓宽普惠优质的校外教育覆盖面;保持好配合学校任务属性,将时间、内容、课程与目标等衔接落到实处,例如,“日课”与“晚课”以及“校内”与“校外”相结合,形成少年宫模式与学校课后服务合力优势;维护好素质拓展功能属性,设计学科拓展、艺术培养、体育锻炼、社会实践等板块,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以及发挥好快乐参与体验属性,让儿童在活动参与中学知识、长见识,并且要就人身侵权纠纷等做好具体应急预案和风险排查。与此同时,推动中国青少年宫协会等在行业自律、信息交流、青少年文化教育活动等方面多加探索,扩大行业组织影响力。
针对私立性校外教育机构,通过对办学行为安全性、功能定位辅助性和市场逐利克制性等规范,助力国家“双减”政策落地实施。例如,解决机构“有照无证”与“无证无照”的经营问题,学科类校外教育机构必须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取得《办学许可证》,并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为非营利性法人;非学科类校外教育机构必须经有关主管部门许可,并依法进行法人登记后规范教学活动。解决机构“学科类”与“非学科类”的占比问题,突出强调校外教育素质拓展功能的回归,坚持从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等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实现“学科类”向“非学科类”的主体转变与功能转型。解决市场逐利问题,通过执行政府指导价、一次性收费、示范合同等专门规定,营造良性竞争氛围。
2.多元化协同:校外教育治理的行政主导性
早在2013年,包括新东方、学而思等在内的17家校外教育机构签订了《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自律公约》1,强化对机构资质、服务、质量、收费等方面的规范引导,但是自律公约自治未能推动培训行业的长效健康发展,亟须市场主导式向行政主导式的结构调整。
其实,从行政主导的教育治理演变来看,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最早于2019年5月专设校外教育与培训监管处,主管业务由早期的指导中小学校外教育调整为监督和管理校外教育,将内部指导性的“软规范”调整为管理性的“硬约束”。2021年6月,校外教育与培训监管处升格为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明确管理校外教育培训的综合执法权。
教育执法弱势现象长期、普遍存在,执法强制性有赖于外界提供稳定且充足的执法资源供给。例如,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着力校外教育市场的秩序维护和信用建设,围绕标价不明、虚构诱导、夸大宣传等典型问题,特别是对于其中虚构教师资质、执教履历和虚假优惠等问题,利用《广告法》《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组合出击。多元化协同参与的校外教育行政执法也应当充分发挥联合执法的优势,整顿办学乱象。
3.合作式共育:校外教育治理的家校协同性
实施“双减”改革对家校协同育人、重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关系提出了新要求2,要求发挥好学校和家庭的各自优势,发展“同心”“同向”“同行”的和谐关系,形成“共构”“共育”“共享”的育人格局。
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来看,难以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多元的教育需求是校外教育发展壮大的直接诱因,全面深化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构成了校外教育乱象治理的关键,但也要警惕教育改革助推校外培训的负面效应。例如,出于中小学“减负”考量的提前放学政策就带来了“家长接送孩子難”的问题,客观上也造成了市场化托管班的顺势而兴。在全面深化学校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学校要做好课后服务的连贯性,制订为学生提供合理补习的制度和体系,为合理补习提供人、财、物等方面的全面支持3,切实满足学生针对性需求;教师要恪守教书育人的伦理性,不得到培训机构兼职教学、不得有消极授课负面行为、不得以成绩好坏差别对待;以满足人民教育的多样性需求为目标,强化学生兴趣培养、特长形成和创新实践的支持工作,形成与校外教育之间的规范衔接和优势互补。
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看,家庭教育缺位、越位、错位等可能会给孩子发展造成消极影响,特别是要警惕很多家长认为的“花钱给孩子报校外培训班就是尽了家长义务”的错误思想。4 作为教育服务的直接买受方,家长在校外教育市场中的非理性选择和跟风型倾向亟待纠正,亟须克服盲目攀比、教育焦虑和分数至上等不良心态。首先是家长要理性看待校外教育服务,避免陷入一种“群体性压力”之下的“内卷式竞争”。其次是家长要科学选择校外培训项目,围绕“全人教育”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结合孩子的自身实际和兴趣爱好,通过兴趣特长类、实践创新类、体育运动类等学习锻炼,助力孩子个性化成长。最后是家长要正确辨别规范办学机构,通过查询办学资质、师资条件和收费名目等筛选优质教辅机构。
综上所述,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只有以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为己任,教育领域只有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努力方向和行动指南,才有获得社会各项支持的合法性。1 伴随着校外教育国家政策的鼓励、引导到约束,是回应公私分化校外教育行业乱象发展困境的历史抉择,以保持校外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初心归位。校外教育的共治格局,经历了单纯自律到融合他律的过渡演化,未来应当坚持从行业自律性、行政主导性和家校协同性等多角度出发,共担责任、形成合力。
From Separation to Healing:Policy Evolution and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of Off-campus Education
QIAN Wenjie
(Shen Junru Law School,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Zhejiang,310000)
Abstract: Off-campus education should not only be based on the supplementary needs of students,but also return to the nature of public welfare of education. After experiencing the stages of an emphasis on education at school with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a focus on education at school with popularity of private tutoring and a decline in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t school with a chaotic private tutoring market,the development of off-campus education is also facing the shift and adjustment from policy support,normative guidance to policy constraint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a chaotic tutoring market driven by interests. Off-campus education should adhere to industry self-regulation,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and family-school collaboration,and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peoples sense of gain and satisfaction of off-campus education when public education is separated from private tutoring.
Key words: off-campus education,separation of public education from private tutoring,policy evolution,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