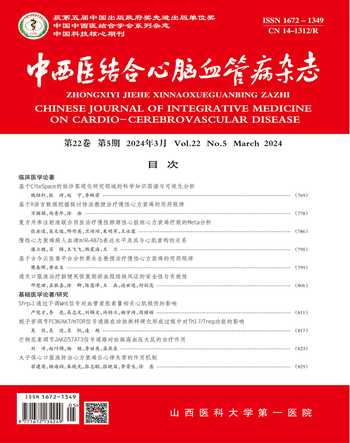基于厥阴理论探讨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的中医诊疗思路
付蔷 李忠 吴红金
摘要 随着早期检查策略、外科手术及肿瘤治疗的进步,癌症相关死亡率稳步下降,伴瘤生存稳步上升,然而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是影响病人生存质量的第二大原因,亟待中西医结合及交叉学科的全程管理。在既往对肿瘤病机、病位的总结基础上,梳理《伤寒论》中厥阴理论,并结合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的临床表现,提出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应在厥阴理论指导下管理,抓住病在厥阴的阴尽阳生受损及经络循行受累两大特点,从动态角度把握两阴交尽、阴尽阳生的特点,关注病程中形成的气滞、血瘀、痰湿致病因素。临证施治时严谨遵循六经辨证原则,选择乌梅丸、当归四逆汤、茯苓甘草汤等加减,并结合病人兼有症状进行遣方。
关键词 心脏毒性;肿瘤治疗;厥阴理论;伤寒论;中医诊疗
doi:10.12102/j.issn.1672-1349.2024.05.034
作者单位 1.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 100700);2.上海中醫药大学博鳌国际医院(海南琼海 571437)
通讯作者 吴红金,E-mail:drwhj@outlook.com
引用信息 付蔷,李忠,吴红金.基于厥阴理论探讨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的中医诊疗思路[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24,22(5):942-944.
近年来,随着早期检查策略、外科手术及肿瘤治疗的进步,癌症相关死亡率稳步下降、伴瘤生存率稳步上升。研究发现,肿瘤生存期及死亡率与肿瘤外的其他器官损害相关,尤其是因肿瘤治疗引起的心脏损伤,已成为影响癌症病人长期生活质量及死亡的第二大原因[1]。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管理癌症治疗相关的心脏并发症、提高病人生存率及生活质量,是中医药在肿瘤治疗领域中的重要任务及研究方向。六经辨证在中医施治方面发挥着指导作用,其不同于八纲辨证的一般规律,将疾病按照表证、半表半里、里证3个层次进行分类,每个层次又包括“阴、阳、虚、实、寒、热”[2],正邪交争贯穿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的全程,根据正邪盛衰、疾病侵犯部位、寒热虚实属性的情况将六经各阶段归纳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及厥阴病,各阶段虽独立存在但又密切相关,存在传变规律。因此,临床应关注疾病发生、传变、预后的规律,分析正邪交争情况,“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六经辨证提示临证施治时需因势利导明确辨证思路[3]。
肿瘤疾病症状复杂,常表现为寒热错杂、虚实夹杂,本研究团队临床观察中总结肿瘤根本病位在厥阴,本质为“阴阳气不相顺接”形成肿块,阳化气、阴成形的正常生理功能难以维持,寒从中生,形成气滞、血瘀、痰湿的病理产物,最终转变为有形的癌肿。厥阴论治肿瘤从经络角度,包括足厥阴肝经及手厥阴心包经,过去认为厥阴肝经交通涉及面广,可反映脏腑病变,肝转移是肿瘤疾病发展的常见现象[4]。随着心脏相关辅助检查技术的提升、临床对循环系统疾病认识的深入,肿瘤心脏病学在肿瘤全程管理中的地位也逐渐提升,面对这项亚专科的复杂表现及临床所需,本研究团队基于过去的临床经验总结认为厥阴理论可解释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的病机,现围绕厥阴理论探讨其内涵、临床表现及诊治思路,以期为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的中医药诊疗提供新思路。
1 厥阴本义阐述
汉代张仲景参考《黄帝内经》根据阴气、阳气的多少将阴阳各分为三,三阴由阴气最多至最少分别是太阴、少阴、厥阴,厥阴是六经辨证中疾病传变的最后一个步骤,其重要的两个含义即为阴气最少、阴尽阳生。《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厥阴的概念:“两阴交尽”,即阴气最少之义,又称其为“一阴”。《素问·阴阳类论》记载:“一阴至绝作朔晦”,晦本义为月尽而朔为月初,由晦至朔代表了阴尽必然生阳的自然规律,因此,提出厥阴为主司阴阳转变枢纽之功能,即两阴交尽、阴气最少、阴尽阳生、阴阳转换,这种转换是有规律的,犹如月满则亏、月亏则盈。从生理方面分析,厥阴为阴尽阳生;从病理角度分析,损伤厥阴即阴损及阳至阴阳两虚,若阴阳偏盛表现为寒证或热证,若不偏盛一方则为寒热并存,然伤寒界普遍认为寒热错杂为主证,符合肿瘤心脏毒性病人病情复杂的临床表现[5]。
2 厥阴在脏腑包含心包,心包代心受邪
根据古代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帛书中记载的手厥阴心包络研究发现,古代医家对心包和心的认识尚存混淆。《阴阳十一脉灸经》曾提及少阴脉的循行:“臂少阴脉起于臂两骨之间”,实则为手厥阴经的循行特点,可见当时医家对心包的认识仍有不足。《阴阳十一脉灸经》提出臂少阴脉存在向心性循行的特点,符合手厥阴经的特点[6]。《灵枢·邪客》中对心有过这样的论述:“黄帝曰:手少阴之脉独无腧,何也?岐伯曰:少阴,心脉也。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故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包络者,心主之脉也,故独无腧焉。黄帝曰:少阴独无腧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经病而脏不病,故独取其经于掌后锐骨之端”。心脏是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在,若邪入心脏则失神人亡,外邪难达心脏,故邪气应达心脏时却在心包络,心包替心受邪,体现了其代君行令的指导思想。
3 厥阴病的表现
提及厥阴病,应先建立整体观念及疾病传变思维,厥阴病处于六经病的末期,因此病情复杂危重,表现为寒热错杂。厥阴在脏腑为肝及心包,肝为阳脏,体阴而用阳,主疏泄、喜条达;心包位于膻中,主司气化,厥阴的阴尽阳生有赖于肝的疏泄、心包的敷布。肝为风木之脏,具有舒展曲直的特性,肝主藏血而又称柔脏,若邪伤厥阴,心包敷布失司、肝失疏泄,肝脏刚柔失济生风,气机郁闭内生邪火,风火上炎,耗伤津液,则心中烦热、消渴。肝病乘脾,中焦运化失司,不欲饮食;风煽火炽,火必不能下达,膈下生寒。厥阴生理条件下阴尽生阳,阳气贵在生生不息,但若一旦邪伤厥阴则阳气不能外达,因而手足逆冷;阳气若得以敷布则手足冷退;若阳气渐旺,则邪去病退;需警惕厥多于热,此为阳气渐衰、正不胜邪、病进的信号。动态观察厥阴病变,是一个正邪交争、阴阳消长失衡到平衡、邪去病退的过程,再次验证了中医理论中阴阳平衡、相互依存的生理意义[7-8]。
本研究团队总结肿瘤发病的根本病位在厥阴,本质为“阴阳气不相顺接”,具体为阳化气功能失司及阴成形有余,阴成形有余但阳气气化不足而剩余有形之邪,此邪即阴性癌毒,不同于外感六淫和内伤七情,而是阴阳气不相顺接的气血阴阳经络失调的产物,包括气滞、血瘀、痰凝[9]。
4 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病位在厥阴
肿瘤病在厥阴,其为阴阳转变枢纽,蕴含了阴尽阳生、阴中求阳的过程,阴阳的消长转化、互根互用是人体阴阳平衡的关键,若因各种原因伤及厥阴,病机表现为阴阳气不相顺接。《伤寒论·厥阴病篇》记载:“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阴主寒、阳主热,阴成形有余,阳化气不足,成形而不化气,成形为实化气为虚,因而形成异形之物,对应现代医学的肿瘤,病伤厥阴,阴损及阳、阴阳两虚,阴阳无法互根互用,致使虚实错杂、寒热夹杂的复杂表现,与肿瘤症状的多样吻合[9-10]。
心为阳脏,位于胸中,属阳中之阳,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阳的温煦推动血脉、心阴的濡养[11];肿瘤病人邪伤厥陰,阴阳互根互用失衡,无论阴阳偏盛某一方或皆不偏盛,均对心功能造成影响,血脉推动无力、心神不足甚则神明被扰,发为心脏毒性,根据心脏表现对应中医学“心悸”“胸痹”“心衰病”等。《伤寒论·厥阴病篇》对心系症状有所描述,326条提及气上撞心、心痛症状:“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下之利不止”,351条描述了心脉受损的表现:“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
前文提及了厥阴与阴阳的关系,从经络循行可知,厥阴分为手厥阴心包经及足厥阴肝经。《素问·灵枢经脉》详细描述了心包经的循行:“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行两筋之间,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从循行路线可知,心包经联系心、胸等部位;从经气相通角度分析,肝经与心包经同属一个经别,心气充沛、脉道通利有赖于肝经的协调气血功能[12]。本研究团队通过临床观察总结肿瘤本病病位在厥阴,厥阴肝经受邪影响心包经功能。因此,厥阴心包经的变化可直接或间接反映肿瘤治疗中常出现的心脏并发症。
现代医学认为,心脏是通过心室充盈及收缩功能完成对全身器官组织的血液灌溉,是人体完成体循环与肺循环的重要器官。在肿瘤治疗过程中,常用的治疗方案涉及蒽环类、靶向治疗、放疗等,通过加剧氧化应激、抑制拓扑异构酶、影响DNA复制转录、细胞凋亡、钙调节失调、炎症反应激活、细胞衰老等机制影响心脏的收缩、舒张功能及正常电活动[13]。从中医角度可知,肿瘤治疗可产邪毒蕴结阴分,耗伤气阴,气化功能受损助有形之邪损伤心络,阴阳失衡[14],加剧阴阳气不相顺接、厥阴病难愈,针对不同心系并发症进行治疗。
肿瘤治疗过程中可能破坏作用于心脏保护的多种机制,从中医角度分析,无论从整体观念的阴阳角度放眼全身、影响心系功能,还是从经络循行角度的聚焦心脏,厥阴理论均可阐释肿瘤心脏病学的病机,气滞、血瘀、痰凝是肿瘤与心脏疾病的共病因素,对应中医整体观念及对立统一的辨证思想。
5 基于厥阴理论的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的治疗思路
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是病在厥阴的核心病机指导下,形成了气滞、血瘀、痰湿等病理因素,逐渐产生心脏毒性的一种临床表现,故从厥阴论治取得良好的疗效。厥阴理论指导下的方药治疗应谨遵寒热错杂病机变化及病证相应原则,严格按照诊断标准施治,避免误判、误诊,抓住病人病证要点拟方,提高治疗的有效性[15]。
5.1 温清并补,敛肝息风
肿瘤,尤其是治疗中出现心脏毒性的病人病证错杂,通常表现为寒热并存,《伤寒论》第338条记载:“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蛔厥也……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临床应用中不局限于蛔厥与久利,久利恰好开拓了乌梅丸的主治,“久”代表延绵不绝、迁延不愈,对应现代医学的慢性病、疾病中晚期等,与肿瘤治疗心脏毒性的疾病性质相同。因此,应充分理解厥阴病寒热错杂、缠绵难治的基本病机及疾病特点。厥阴病在血分、阴分故君药为乌梅,用量较大(三百枚)起到收敛之用,防止辛散太过;臣用干姜、附子、细辛、蜀椒大温大热之品温中散寒;当归、人参补益气血,同时健胃辅助补益津血;苦寒之品黄连、黄柏以泻为补、亦防火去伤阴,最后以蜜调和全方起到安中补虚之效[16]。现代临床研究显示,乌梅丸治疗肿瘤及心系疾病,对肿瘤病人应用该方发挥减毒增效、改善肿瘤治疗伴发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的作用,对心悸、胸痹、眩晕、心力衰竭的治疗均有效[17-19]。
5.2 温通经脉,散寒止痛
《伤寒论》第351条记载:“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以寒凝体内为表现,寒凝除是肿瘤的病机,也促进了心系疾病的发作,如外感寒邪经脉受阻引起的胸痹、寒邪内侵阳虚水泛加重的心衰病等。当归四逆汤系由桂枝汤演变,桂枝汤本为治疗外寒的经方,去生姜换细辛,加用当归、通草而成当归四逆汤,当归是血中之圣药,善补血养血,入手少阴、足太阴及厥阴血分,在该方和乌梅丸中均有使用,是治疗厥阴病重要的中药单体。该方温通为主,温阳散寒共举,补而不滞,寒热共治[20],全方共奏补津血、调营卫之效,其中当归滋补养血,通草通利血脉,细辛、附子大温性药以祛寒通利关节。多项临床研究显示,当归四逆汤临床治疗心系疾病的有效性[20-22]。
5.3 温通心阳,健脾利水
《伤寒论》356条云:“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当服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茯苓甘草汤以桂枝、甘草为基础,用于治理气上冲心;导致心下悸的水渍入胃当用茯苓,同时配生姜健胃。此厥非寒厥热厥而是水饮所致,因此先治水,水利所以治厥。
6 小 结
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治疗难度较高且意义重大,亟待中西医结合及交叉学科的全程管理,此类病人可能出现寒热错杂、虚实夹杂等复杂临床表现,应在多样症状中寻求主要思想诊治。本研究团队在既往对肿瘤病机、病位的总结基础上,提出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应在厥阴理论指导下管理,抓住病在厥阴阴尽阳生受损及经络循行受累的两大特点,从动态角度把握两阴交尽、阴尽阳生的特点,关注病程中形成的气滞、血瘀、痰湿致病因素。临证施治时严格遵循六经辨证原则,选择乌梅丸、当归四逆汤、茯苓甘草汤等加减,并结合病人兼有症状进行遣方。从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的交叉学科需求出发,结合既往经验及六经辨证,为该病的中医诊治提供新思路。
参考文献:
[1] CURIGLIANO G,CARDINALE D,DENT S,et al.Cardiotoxicity of anticancer treatments:epidemiology,detection,and management[J].CA,2016,66(4):309-325.
[2] 庄振杰,周岱翰.《伤寒论》六经辨证及方证对应在肿瘤临床中的应用与启示[J].中医肿瘤学杂志,2022,4(6):36-39.
[3] 马千,程荣菲.基于正气存内理论谈六经病辨治[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23,21(1):56-58.
[4] 李忠,白桦.从厥阴辨治恶性肿瘤的临证思考[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3(6):353-354.
[5] 娄政驰.《伤寒论》厥阴病辨证论治思维研究[D].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09.
[6] 李岩,王燕.试谈手厥阴心包经的沿革与完善[J].天津中医学院学报,1999,18(1):38-39.
[7] 赵睿学,王停,李海燕,等.从厥阴病探讨“络风内动”学说[J].现代中医臨床,2022,29(2):29-33.
[8] 周唯.论六经辨证的阴阳一体观[J].中医研究,2007,20(2):11-14.
[9] 祁烁,陈信义,董青,等.中医肿瘤病机再思考[J].中医学报,2018,33(3):345-349.
[10] 邹万成,张六通,邱幸凡.古籍中恶性肿瘤之各种称谓文义考析[J].湖北中医学院学报,2008,10(2):16.
[11] 彭禹菲,张明雪.基于心为阳脏而主通明谈对冠心病调治的启发[J].国医论坛,2022,37(1):63-64.
[12] 黄昌锐,喻正科.从厥阴论治心病[J].湖南中医杂志,2021,37(10):124-125.
[13] 亓晓涵,王福,孙慧,等.肿瘤与心血管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J].临床心血管病杂志,2022,38(7):585-592.
[14] 李应东.肿瘤心脏病:中医药防治的潜力与切入点[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22,20(19):3480-3482.
[15] 崔书克.《伤寒论》六经辨病思维探赜[J].河南中医,2020,40(4):487-489.
[16] 陈荣武,叶文彬,王雪萍.乌梅丸方证探析[J].光明中医,2022,37(24):4553-4556.
[17] 刘签兴,李晓洁.李士懋应用乌梅丸治疗心系疾病经验初探[J].环球中医药,2018,11(6):914-915.
[18] 朱燕,张慧敏.乌梅丸临床应用进展研究[J].实用中医药杂志,2022,38(12):2249-2253.
[19] 王秀芳,牛鑫,姚娓.乌梅丸现代临床运用和药理研究进展[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25(3):136-141.
[20] 郭芮,司廷林.当归四逆汤方证的临床应用[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9,17(3):59-61.
[21] 杜红,雷锐,张鸿雁,等.加味当归四逆汤治疗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阴寒凝滞证)的临床观察[J].中国中医急症,2022,31(5):875-877.
[22] 王多德,席孝萍,刘吉宗,等.当归四逆汤治疗阴寒凝滞型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痛疗效观察[J].西部中医药,2021,34(5):120-121.
(收稿日期:2023-04-06)
(本文编辑薛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