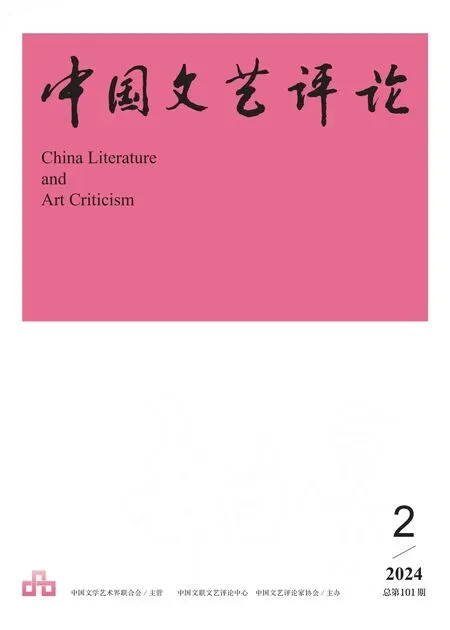黄药眠文艺思想的内在逻辑
■ 周小仪
重读黄药眠是一种独特的学术体验,也是让人不断惊叹的理论旅行。虽然他的语言有些陈旧,不乏那个时代的痕迹。他的论辩也十分直白,甚至尖刻,充满了火药味。但他的逻辑起点、思想高度、真知灼见、生动例证都让人无法忽视。他“聪明的唯物主义”(列宁语)、他的实践哲学和能动主体性、他复杂而令人信服的阶级论,对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建设,毫无疑问是一笔丰富的思想财富。童庆炳曾经感言,黄药眠是北师大乃至全国文艺学学科的开创者,并一口气列举了他的五个“首创之功”。[1]参见童庆炳:《黄药眠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的文论与美论——为纪念黄药眠教授诞辰百年而作》,《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6期,第87页。这让人想起伊格尔顿1980年代说过的话,他说当今英语系所有的人,都是F.R.利维斯的学生。同样,今天很多文论工作者,或多或少都继承了黄药眠和童庆炳的学术火种,即王一川所说的“黄童学派”的思想基因。[2]参见王一川:《革命的浪漫诗人文论家——黄药眠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艺术评论》2013年第12期,第26页。
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中外国际关系迅猛发展。在此背景下,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看待这个理论家,又如何对他进行重新评价?全球化不仅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国际化生活体验,也促使我们把国内的文化现象放在世界范围内加以考察。和过去相比,我们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也可以把当代生活经验融入新的思想框架中。从新的生活、视野和角度看黄药眠,他的文艺思想就不断有新的意义开显。李圣传将黄药眠美学概括为社会性、实践性、阶级性和价值论[1]参见李圣传:《黄药眠:生活实践土壤中的价值美学倡导者——从朱光潜与黄药眠的“梅花之辩”说开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20页。,对他丰富的批评实践予以分门别类。我们在此基础上微调,从存在论、主体论和阶级论三个方面对黄药眠理论进行归纳,以期理解黄药眠文艺思想的内在逻辑。所谓美学价值,对黄药眠来说就是阶级评价,是阶级分析主导的价值判断,也是他阶级论的组成部分。
一、黄药眠的存在论:对形而上学的美学批判
20世纪四五十年代,黄药眠对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关于直觉、距离和艺术独立性等观念进行了批判。朱光潜对待古松的三种态度,即伦理、经济和审美相互独立的三单元,实际上是按照克罗齐心智分类法对康德的另类阐释。审美判断力在康德那里是连接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桥梁。虽然康德也强调艺术的无目的性,但这是作为中介意义上的功能,而非实体意义上的独立性。这种“对康德的创造性误读”[2]Nicholas Shrimpton, “The Old Aestheticism and the New,” Literature Compass, No.2(2005), p.1.,有欧洲浪漫派和唯美主义传统,是当时文艺批评的主流。德国浪漫派的席勒、史雷格尔兄弟把艺术解释为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进而看成是独立于伦理和理性之外的精神实体,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在德国学习的法国浪漫派——史达尔夫人、贡斯当和库赞。他们发明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并带回法国,继而传给英国留学生惠斯勒、史文朋等人,普及了艺术独立性思想。朱光潜三分法的通俗阐述,加上20世纪初流行的移情说、距离说、内模仿等文艺心理学,形成艺术与生活截然二分之后再结合,即主客体统一这样一个审美流程。而黄药眠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文艺思想,他的结论正相反:艺术绝非远离生活,割裂于生活,相反,艺术“把生活向前拉近一点”;“把人带到更深的生活里去”;“把客观世界拉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给予审美的评价”。[3]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17、60页。他的观点明确、论证有力、表述清晰。艺术与生活、主体与客体统一于实践的思想,不仅在当时非常先进,即使是在今天后现代氛围中,在人文主体性、形式主义和文本中心论以多元文化的名义尚在流行之际,黄药眠的一元论实践美学的价值仍然非常显著。
黄药眠美学可以称之为“存在论”。黄药眠对现实生活的描述有两套术语:一套术语以“存在”概念为核心,如“社会存在”“阶级存在”“抽象的存在”“客观存在”等;另一套术语是以“实践”概念为中心词,如“社会实践”“生活实践”“人的实践”和“劳动实践”等。如果我们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作为阐释框架,就可以把存在看作是更为基础的概念,而实践就是现实存在的特殊表现。实践论可以作为把握黄药眠存在论的第一种阐释方案。这种阐释是黄药眠自己认可和充分论证的,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在《提纲》中,马克思用实践论对机械唯物论和唯心论进行了双重批判。黄药眠强调实践论对主体论和客体论美学的超越,重述了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不能直观地去理解,而是“当作人的感性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的观点。[1]黄药眠:《由“百花齐放”所想到的》,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童庆炳也把文学理解为“生活活动”或“人的一种存在方式”[2]童庆炳:《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8、51页。,进一步从审美心理方面聚焦其过程性,主导了中国文化诗学的发展。
黄药眠存在论的另一个思想先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著名的生活美学观提出了“美是生活”[3][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周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6页。,黄药眠概括为“生活高于艺术”[4]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页。。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周杨推崇的俄国批评家“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之一;周扬也以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而出名。黄药眠是周扬志同道合的朋友,据赵勇考证,周扬曾将第二次文代会报告交由黄药眠审阅,可见对其信赖。[5]参见赵勇:《周扬请黄药眠审阅文代会报告考——纪念黄药眠先生诞辰120周年而作》,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编:《“黄药眠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出版),2003年10月,第38页。黄药眠讨论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命题“我们所希望的生活就是美”,赞成他将生活和审美合二而一。但黄药眠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论是前马克思主义的,“生活就是美”的信条“太笼统了”,他改为“为革命而奋斗的生活是美的”。[6]黄药眠:《我又来谈美学》,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2页。实际上,后期唯美主义者如王尔德也超越了德国和法国浪漫派的艺术独立性观念。他和尼采、福柯等回归古希腊传统,认为生活本身就是艺术。虽然朱光潜也追随尼采,在静观的日神精神之外并列生命的酒神精神。但他没有解决酒神和日神的分离,即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独立性的内在矛盾,不能从实践论的高度对艺术客体的独立性进行否定。当然黄药眠的立场不可能和唯美主义一致,他们所属的阶级不同。王尔德是“披着鹅绒大衣”,拿着向日葵“招摇过市的唯美主义者”。[7]黄药眠:《文艺家应该为谁而战?》,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王尔德关于生活就是艺术的观点,以及对主客体二元论的扬弃,可以看作是黄药眠实践论的通俗版本,也是第二种理解黄药眠存在论的途径。
超越主客体二分法的哲学当属现象学“主体间性”和存在主义“此在”概念。黄药眠的能动主体性和实践论与现象学、存在主义之间存在关联和互文。推进两者之间联系的理论家是卢卡奇。卢卡奇早年交往了很多现象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也经常出现在他的著作中。但他把现象学的“主体间性”和存在主义的“此在”进行了置换,把劳动过程和阶级关系作为社会存在的主要方面。他认为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决定了人对审美对象的看法,从而形成意识形态,这一点正是黄药眠不断强调的。由于当时我国受前苏联影响,将卢卡奇视为修正主义者加以批判,黄药眠很少直接使用卢卡奇的理论。但如果我们用卢卡奇的思想来对比黄药眠的实践论,就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卢卡奇认为社会存在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具有一种“历史的、过程的特性”,在某些时段就是“阶级斗争的过程”。[1][匈]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沈耕、毛怡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4、59页。我们在黄药眠的著作中对此耳熟能详。简单说,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可以看作是理解黄药眠的第三种阐释方案。
最后,我们用现象学家伽达默尔的审美无区分理论对黄药眠的存在论进行总结。审美过程中的主客体区分是如此武断,完全囿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形而上学首先把主客体分开,然后再拼命寻找两者的同一性,这对伽达默尔来说是画蛇添足。伽达默尔在《真理和方法》中称之为“异化”。在人类历史大多数时段,没有文学概念这种奇谈怪论。文学独立性是晚近的观念,从18世纪开始,风行200年结束。既然之前的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之后的文学是一种社会文本,或一种施事性语言;那么文学与生活就没有分别。伽达默尔在谈到艺术时,反对将审美经验看作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静观活动。他认为审美活动和其他社会存在没有分别。艺术和生活合二为一是回归其本源状态,是回到海德格尔的“作为此在本身的存在模式”。因此伽达默尔抛弃席勒美学的“审美区分”(aesthetic differentiation),回归“审美无区分”(aesthetic non-differentiation),让艺术回到生活。[2]参见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second,revised edition), trans.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Marsha, London: Continuum, 2004, p.xxvii.评论家指出,现代美学“在主体和客体之间设立了距离,然后使克服这个距离成了一个问题”。我们过去的文学理论,无论是反映论、表现论还是形式论,都在为解决这种分离费尽心机。对伽达默尔而言,审美意识从属于它所感知的对象,“它是世界的一部分,过程的一部分”。[3][美]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著,张世英、赵敦华主编:《伽达默尔》,何卫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1、29页。这是超越主客体分离的美学理论。伽达默尔的理论符合黄药眠审美体验基于生活实践的观点。
黄药眠的文艺观让我们认识到,文学是生活实践的聚集升腾,艺术是生活方式的密度强化。两者区别只是量的差别,而非质的不同。我们过去的文论将注意力集中在艺术和生活的区别上,而且总是偏重艺术这一面,把这种特殊的生活修辞看得至高无上,并定为一切价值的核心,忽略了它们的性质在更为基本的存在层面上实质相同。文学观念的历史如此短暂,在19世纪旨在弥补宗教衰落留下的精神空白,不过这是中世纪宗教情怀的回光返照,改头换面为资本世界的审美拜物教。黄药眠把朱光潜聚焦感觉而非生活实践的理论称之为“感觉的拜物教”[1]黄药眠:《论食利者的美学》,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9页。,这个评价可谓振聋发聩。对于伽达默尔、福柯、王尔德、尼采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而言,美学就应该回归生活。海德格尔早就指出,古希腊语技艺(techne)包含技术和艺术两个意思:精湛技术也是“各种美好艺术的名称”[2][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31页。。就像中国的庖丁解牛,技术也是艺术;生活和艺术浑然一体:“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3]郭庆藩:《庄子集释》(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8页。只是黄药眠和卢卡奇一样,认为社会存在主要是由劳动实践和阶级冲突构成的现实。黄药眠美学就是陈雪虎所说的三种“生活美学”中的那种“革命生活美学”,有别于闲适文人的“传统生活美学”和“基于市场和消费”的现代生活美学。[4]陈雪虎:《生活美学:当代意义与本土张力》,《文艺争鸣》2010年第13期,第35页。
二、黄药眠的主体论:能动性和介入行动
把生活和艺术统一到社会实践中去,走向能动主体性就是一个逻辑必然。生活实践是主体的行动过程。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不是像以往的哲学家那样去认识世界,而是用行动去改造世界;这就是主体的实践哲学。黄药眠的“主体能动性”受到童庆炳的高度称赞。童庆炳认为1980年代中国学界对“文学主体性”的呼唤,“黄先生早于三十年前就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而且黄药眠的主体性理论种类齐全,“从文学创作的主体、文学对象的主体、文学鉴赏的主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童庆炳认为,黄药眠的鉴赏主体或“预成图式”理论“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的基础”。[5]童庆炳:《黄药眠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的文论与美论——为纪念黄药眠教授诞辰百年而作》,《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6期,第89—91页。童庆炳关于创作主体和审美心理的研究就是沿着黄药眠的主体理论向前推进的。
既然黄药眠的主体性是实践,那么它与浪漫主义、人文主义和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说的能动主体性就会有根本不同,甚至和李泽厚的历史实践带来的文化积淀和情感本体也有所不同。我们可以用当代文论术语来表述这种区别:结构主义之前的能动主体性和结构主义之后的能动主体性截然不同。结构主义之前的主体性是主体的表现、移情或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结构主义之后的主体性是一种发展过程,用德勒兹的话说就是一种生成。无论是克里斯蒂娃还是德勒兹,主体或生命强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生生不息、向前发展、不断流动的。所以德勒斯推崇柏格森生命的动态绵延、斯宾诺莎的幸福过程和尼采的永恒轮回。这些都是动态主体,也就是说,主体就是主体化的过程。如果我们把德勒兹的生成置换为实践,我们就得到了黄药眠的主体理论。黄药眠的主体是融入火热革命斗争的主体,是“从生活的实践去看出美来”的主体,是“在阶级生活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主体,是“人在劳动中……发现了美的形式”的主体。黄药眠说:“作家只有和人民长期地斗争在一起,他对于现实才会有更亲切的关系,才会有更丰富的情感色彩,对人民和人民的事业才会有更深更高的审美的评价。而且也只有在生活的斗争中才能显示出他的崇高的美的品质。”[1]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23、31、57页。
这个生活实践中显示出的“崇高的美的品质”就是黄药眠的能动主体性。对于黄药眠所说的“主动地去感觉”,或丰富的生活会“增加自己的感受性”这样模棱两可的表述[2]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4、348页。,我们只有从实践论这方面去理解才符合黄药眠的本意,才与他作为革命家的主体保持一致。主体的能动性在于主体实践中的情感生成而不是主体已有的情感的对象化和表现。
这说明了为什么黄药眠认为能动主体性的核心是行动,因为主体化过程是人在社会实践中身体力行。在这方面,黄药眠对列宁哲学情有独钟。黄药眠在著作中频繁引用列宁,虽然这与当时的学术氛围一致,但毕竟黄药眠将他的主体思想和列宁的行动哲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行动哲学是解决主客观矛盾的有效途径。他推崇“人的主观力量”,反对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黄药眠说:“这个新兴阶级的革命主观意志和行动,就不仅是推动客观的因素之一,而且成为了变革这个世界的决定的因素。考茨基的机会主义的最主要的错误,就是在于他只静待客观形式的‘自动’发展,或只是把主观力量看成为客观的因素之一。忽视了主观力量在那一个时期之决定性。”[3]同上,第29、252页。
我们在这里很容易辨别出列宁的痕迹。主体的能动性在客观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正是列宁的行动哲学。他的主动介入行动由齐泽克重新解读,已经成为行动主体的典范。齐泽克说,列宁在俄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并没有循规蹈矩,恪守陈规地等待资本主义的成熟和社会主义自然而然地到来。他没有被机会主义蒙蔽双眼,像考茨基那样软弱无力,惧怕革命的残酷、激烈和可能的失败。列宁认为,时机永远不会在等待中到来,坐等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按部就班地发展,就永远不会得到革命成功的机遇。[1]参见[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03页。于是列宁果断行动、先发制人、主动介入、组织罢工、拼死一搏,引爆十月革命,改变了俄国,也改变了世界。齐泽克的行动主体,不仅超越了传统的人文主体性,也超越了结构主义的空白主体性和德勒兹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生命主体性,成为对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能动主体性思想的出色表述。而黄药眠对“人的主观力量”及在某“一个时期之决定性”的强调,对党的组织架构及其推动力的重视,对列宁“共产党人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注入到工人阶级里去”的介入思想,只有从行动主体理论的角度才能充分理解。正因为如此,黄药眠要求作家“要真的参加到实际行动中来,成为被压迫者队中的斗士”。[2]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30,326、172页。
三、黄药眠的阶级论:“尖锐期”与“和缓期”的切换
受当时理论氛围和时代因素的影响,黄药眠倡导阶级论是顺理成章的事。黄药眠的行动主体是“推动历史的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是“阶级的人的主观”。[3]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0、235页。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阶级论受到理论界的摈弃,也使学界对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评价不足。实际上,黄药眠的阶级论是非常复杂的,绝非简单生硬的理论。他专门批判了那种简单化的阶级观点。他用五个“化”来描述这种简单的、机械的阶级论,即阶级斗争的“庸俗化”“永恒化”“扩大化”“凝固化”和“绝对化”。对刻板阶级论的超越,使黄药眠站在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理论高度。
那黄药眠的阶级论是什么呢?他的阶级论首先是历史主义的。黄药眠认为:
我们必须全面地、具体地、历史地分析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第一,阶级的特性、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是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绝不是固定僵化永远如此的;第二,每一个社会形式都有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矛盾。但这个矛盾也有时和缓些,有时尖锐些,有时要彻底决裂,而不是从始到终永远都是尖锐的,或是只凭猜想认为越来越激烈的。[4]黄药眠:《试评普列汉诺夫的审美感的人性论》,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
虽然阶级关系就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最重要的表现,但阶级冲突有激烈和轻缓等各种不同表现形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氛围,有时激烈,有时平缓,不可等同。“尖锐期”与“和缓期”是黄药眠对阶级关系历史化所作出的重要区分,也是他不断重复的核心观点。他对不同时期的阶级状况区别对待,是复杂、具体和令人信服的理论。黄药眠解决了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也解决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问题。由于我们过去对黄药眠的阶级论关注太少,我们不妨再引用一段他关于阶级的论述,看看他的思考是多么细腻和中肯:
这种审美能力,特别是审美观,不能不受社会存在的影响。当阶级斗争激烈时,其审美观有浓厚的阶级色彩;有时斗争处于缓和状态,各阶级生活在同一时代中,各阶级的趣味就会相互影响,虽然影响的程度不同。教养不同,阶级不同,美的评价也会不同,但无论哪个阶级,审美评价是通过个人而表达出来的,因而一定都带有个人的情绪色彩。[1]黄药眠:《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36页。
黄药眠的阶级论和我们过去所说的个性表现和人的普遍性并不冲突。在特定时代,特别是在阶级冲突的“和缓期”,各阶级和平相处并“相互影响”,交融现象和共同美感就会十分突出,以普遍性的美学表现出来。因此,构建一个全面、具体、历史的阶级论,就要把社会存在、阶级状况与文艺思想联系起来通盘考查,关注不同阶段的不同组合。在对文艺作品进行阶级分析时,对这种复杂性要了然于心,不然就会走向教条和僵化的庸俗政治批评。黄药眠的这种历史分析方法还有许多精彩的段落和观点,因篇幅关系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除了两个阶级的矛盾斗争之外,黄药眠还讨论过“中间阶层”,即中产阶级,也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在《论食利者的美学》中,黄药眠从阶级论的角度批判了朱光潜的中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美学。黄药眠特别指出,中产阶级不从事物质生产,不接触下层人的生活,在象牙之塔中思考形而上学问题。黄药眠的看法虽然激烈,但和现代社会学家对中产阶级的评价不谋而合。社会学家马丁·尼克劳斯(Martin Nicolaus)指出,中产阶级的产生有其经济根源。他认为剩余价值可分割为再生产资本和政府税费,而后者比例不断扩大。中产阶级占有社会生产的部分剩余价值,从事“非生产性服务”,包括文艺活动,是“剩余阶级”(surplus class)。[2]参见John Scott, ed., Class:Critical Concepts (vol.4),London: Routledge, 1996, p.204.中产阶级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将社会剩余价值带来的局部生存状态看作是普遍性的、全人类的生存状态,这是一种政治无意识。中产阶级把自己的品位和嗜好扩大为全人类的代表,当然遭致黄药眠的反感和严厉批判。黄药眠指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们怎样主张的呢?他们不是主张人们去参加实践,去认识现实和现实中矛盾发展的规律,不,他主张人们加强主观。他主张‘生命力’的高扬。”[1]黄药眠:《〈矛盾论〉与文艺学》,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8—279页。
“‘生命力’的高扬”这个术语我们是不是很熟悉?从尼采、柏格森、德勒兹、李泽厚到后人类主义者布拉伊多蒂,对这个抽象概念的阐释不绝如缕。分析哲学家对此嗤之以鼻,现代神经心理学也不支持这种观念的神学。不过批评家却总是对此情有独钟,让这个老旧的生命恋物癖得以代代相传。黄药眠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把所谓永恒“生命”称之为“抽象概念的拜物教”[2]黄药眠:《黄药眠文艺论文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9页。。虽然他的声音现在很小,但他的穷苦出身和下层人立场,让他保持着卢卡奇式的对社会整体性认知。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不能认识真理,因为整体性不符合他的阶级利益。只有下层阶级才能看到社会的二元对立和不合理性,因而他们的利益可以和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利益保持一致。这也是黄药眠所理解的阶级性的根本内涵。除了对朱光潜中产阶级美学的阶级局限性进行批评之外,黄药眠也阐述了他的阶级观点:
文学作品里表现进步阶级的阶级性并不妨碍它表现人类共性。有各种不同的历史时代,有各种不同的进步阶级,因此,它们所表现的人类的共性也就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所谓表现进步阶级的阶级性并不妨碍它表现人类的共性,就是说进步的阶级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文学作品表现了阶级性也就表现了人类的共性。[3]黄药眠:《问答篇》,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7页。
这里蕴藏着黑格尔的辩证法,即具体的普遍性,而非抽象的生命力普遍性。具体普遍性备受齐泽克推崇,被看作是劳工阶级的特征。齐泽克说:“借用马克思的经典例证,‘无产阶级’之所以代表人类普遍性,并非由于它在最底层,受剥削最深;而是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根本失序和断裂的体现。”[4]Slavoj Zizek ,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 Verso,1999, p. 225.这就是为什么黄药眠说进步阶级表现了人类共性,因为劳工阶级的解放就是消除人类社会的不合理性;劳工阶级的利益代表人类的普遍利益。同理,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世界工厂的劳工国家也代表了人类的普遍性。
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的阶级状态就像黄药眠所说,进入了一个和缓时期。但是我们如果放眼全球就会发现,国内阶级冲突的平缓期伴随着一个阶级空间化过程。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国家关系、民族关系、南北关系和东西方关系仍然表现出对立和冲突。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10亿人口和其他地区近70亿民众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冲突更为明显。因此,如果我们从历史阶段和全球化背景的角度把握黄药眠的阶级论,从整体性角度看待不同国家民族所代表的不同阶级立场,就可以对我们当今的文化现象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四、结语:黄药眠的当代意义
黄药眠的存在论、主体论和阶级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链条。我们今天如何发掘黄药眠美学思想中活的东西、考察其当代意义,需要我们对理论和现实进行深入思考。他关于艺术与现实的一体化,参与生活的实践主体和情感表现的阶级构成等观点,都值得我们继续探讨。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旧瓶装新酒,用当今的理论来重新表述黄药眠的文艺思想呢?
首先,黄药眠让审美和艺术回归生活,从实践和生存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有助于克服我国学界流行的形式美学,即把艺术独立出来观照、把文学当作纯粹客体进行细读和分析的理论。伊格尔顿说这是切断文学与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使其“达到单纯恋物癖的地位”[1]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8, p. 19.。彼得·威多森认为,英国19世纪用这种审美拜物教取代宗教;阿诺德、T. S.艾略特和瑞恰慈等文化理论家,让文本神话风靡一时。艺术作品从此成为审美分析的客体,促成“文学文本的拜物教化和物化”[2]Peter Widdowson,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2004, p. 52.。中国学界延续这种形式主义,是从马克思《提纲》这一理论高点的倒退。而黄药眠早于伊格尔顿和威多森几十年就开始质疑美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的拜物教模式,实为难能可贵。他使我们重返实践论立场,让我们在生活中理解文学。
其次,黄药眠也取消了主体的独立性,主体成为社会中的一员,投身于火热的生活实践。这符合当前流行的斯宾诺莎过程哲学以及巴迪欧、齐泽克关于行动主体的理论。黄药眠强调的是主体化过程: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对现实有更为亲密的关系,在实践中显示出其崇高本质。这一主体超越了人文主义情感主体、不在场的结构主义空白主体以及德勒兹后结构主义抽象的生命主体。黄药眠的主体性强调具体的生活、劳动、实践,是我们理解主体的方向。
最后,我们还可以对黄药眠阶级论进行扩版。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间交易上中下三层社会结构的矛盾,阐明了世界上“经济不平等纯属社会不平等的翻版”[3][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9页。。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分布,就是空间化的阶级对立。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掠夺性积累,揭示出现代社会中“圈地运动”持续存在。[4]参见[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奈格里和哈特重读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用“一般智力”描述当代信息劳动与情感劳动的剥削机制。[1]参见[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32页。刘禾的文明等级论表明西方国家如何通过文明与野蛮的划分,建立起全球秩序的金字塔结构。[2]参见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5页。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阶级论的升级换代,而黄药眠的阶级情感理论则可以对此进行补充。
实际上,黄药眠本人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全球化问题,他说:“剥削阶级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它的思想也就随着立即消亡了,还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残存下去,何况还有外来的影响呢?这一点我在这里不能不着重提出来。”[3]黄药眠:《试评普列汉诺夫的审美感的人性论》,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在封闭多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初期,黄药眠能够“着重提出来”这样一个“外来的影响”问题,试图把阶级关系放在国家关系中去考察,在国内阶级问题的“和缓期”思考国际阶级状况,指出“国内的资本主义已扩大而为世界的帝国主义”[4]黄药眠:《文艺家应该为谁而战?》,陈雪虎、黄大地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1页。这种空间走向,为我们今天的思考指明了方向。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坚持二元对立框架,并注入新的全球化生活内容。黄药眠关于社会存在如何向审美文化转换的内在逻辑,以及他对行动主体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描述,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只是我们应该把存在、主体和阶级这个国内闭环“扩大化”。这个扩大化不是像过去那样,将国内的阶级问题扩大到一切人群,把人民内部矛盾解读为阶级矛盾。如上所述,这早就受到黄药眠的批判。我们的扩大化是追踪晚期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轨迹,把审美问题看作是存在问题,把主体问题看作是行动问题,把国家关系看作是阶级问题,这样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冲突就会反向外溢到全球范围。当我们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世界,就可以看到卢卡奇所说的整体性,对国内的文化现象也会有一种全新的理解,从而避免对世界范围内的文明等级和阶级冲突视而不见。因此,我们对存在、主体和阶级问题的空间化处理、全球化处理和历史化处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绘黄药眠式的整体性构图,就是对他的理论最好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