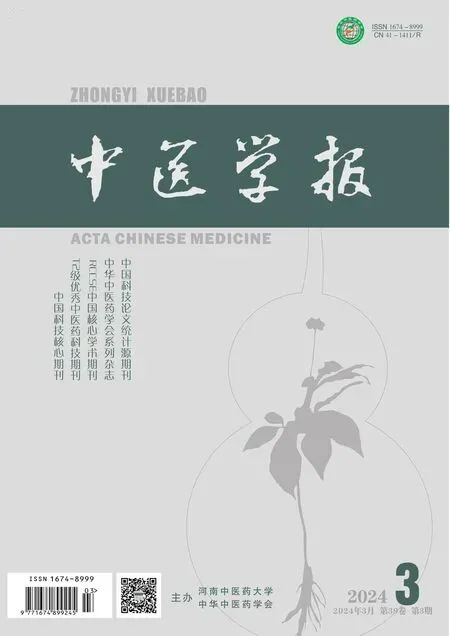从胆论治室性早搏伴焦虑抑郁*
陈琛,王玉玲,2,沈子焕,2,焦林珂,2,丁帆,2,崔向宁,2
1.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100053; 2.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室性期前收缩(premature ventricular contractions,PVC),简称室早,在普通人群中的发病率约为3%~20%[1-2]。PVC常见于器质性心脏病患者,多由电解质紊乱,精神因素,过量饮用酒精、浓茶、咖啡等刺激性饮料诱发。PVC患者轻者可无症状,或偶有心慌不适,严重者可表现为头晕,甚至晕厥死亡[3]。现代医学治疗PVC虽有一定优势,但其手术并发症及药物不良反应较多,且患者常伴发焦虑、抑郁,严重影响抗心律失常药物的治疗效果[4]。研究表明,75%的焦虑、抑郁患者出现过心悸症状,从而加大患者的精神压力,继而增加PVC的易感性[5]。
PVC伴焦虑、抑郁是一类双心疾病,根据其发作时惊悸难安、不能自主的临床表现,可将其归属于中医学“心悸”“惊悸”“怔忡”“脏躁”等范畴[4]。《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曰:“心与胆通,心病怔仲宜温胆”,而胆以和为“温”,强调胆清净之府的特性,以恢复胆疏泄升发之性、固护决断之权。又言:“心气通于胆”,心胆气通,胆气失和则会影响到心的功能。宁博等[6]指出,双心疾病主以情志为病,不论是否兼具器质性心血管疾病,皆可以“情”为因、以“神”为源来论治。心为神之主,胆为神之枢,二者相互协调,共同完成“神”的活动[7]。胆气冲和,则心气安逸,神无所偏;若胆气失和,则心气难安,神明动乱,终致惊悸难安、不能自主。本文基于“心与胆相通”理论探讨PVC伴焦虑、抑郁的中医病机,并探讨从胆论治PVC伴焦虑、抑郁,以期为“双心疾病”的临床诊疗提供新思路。
1 “心与胆相通”理论内涵阐释
《五脏穿凿论》首载:“心与胆相通”。后明代医家李梴在《医学入门·脏腑条分》引曰:“心与胆通,心病怔忡,宜温胆为主;胆病战栗、癫狂,宜补心为主”,为后世医家从胆论治心系病证提供了理论基础[8-9],从“心与胆相通”理论治疗心系疾病的疗效也已得到证实[10-14],并已广泛应用于临床[15-16]。此外,中西医的心、胆概念虽不完全等同,但是现代医学“胆心反射”“胆心综合征”等生理病理情况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胆、心之间的密切联系[17-18]。
1.1 心、胆沟通于经络《灵枢·经别》云:“足少阳之正……循胸里,属胆,散之上肝贯心。”表明胆、心之间存在经络联系。而《医贯·十二官论》又云:“脾、胃、肝、胆、两肾、膀胱各有一系,系于包络之旁,以通于心。”提示心、胆之间可以通过肝、脾胃等经络渠道相互联结。同样,在病理状态下,心、胆常以经络为基础,相互为病,如《素问·阴阳别论》中“一阳(指少阳胆)发病,少气善咳善泄,其传为心掣”指出若胆有病,可通过经脉上冲于心,导致心掣(心悸)[8]。
1.2 心、胆协调于气机《素问·六微旨大论》载:“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气机升降有序是人体生长化收藏的前提。心居上,主降,降中有升;胆居下,主升,但又为六腑之一,以通降为顺,故升中有降[10]。气血运行是心、胆协调气机升降的具体表现。心主血脉,血液循行于机体各个部位,依赖心气的推动,心血上荣头面,下行全身脏腑,所养之腑包括胆腑。李杲《脾胃论》曰:“胆者,少阳春升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五脏六腑的功能,还要依赖于胆的正常升发之气,又因胆腑纳藏精汁,胆液下行,可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及气血生成。心气健运,心脉畅达,有助于胆气复苏,血得以养;胆气升发,胆道疏利,有助于心气调畅,血脉得充[19]。心、胆气畅,相须为用,对维持气机运行通畅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心、胆之气升降太过、不及或郁滞时,常可互相影响而致病,正如《外经微言》言:“胆气郁导致心气不顺,脾胃失养,胃气不畅导致痰淤血滞。”他邪作祟,变生诸病[17-18]。
1.3 心、胆统一于神志心为神之主,胆为神之枢。《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具有统帅人体生命活动和精神、意识、思维的作用,胆腑也要在心神的主导下才能发挥其正常功能[12,16]。“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胆也可影响某些精神活动,如张景岳在《类经·藏象类》中指出:“五脏六腑共为十一,禀赋不同。情志亦异,必资胆气,庶得各成其用,故皆取决于胆。”心、胆二者在调节神志方面相互协调配合,如《重订济生方》云:“心气安逸,胆气不怯,决断思虑,得其所也。”心任物为神志之主,胆行决断之职,胆气通于心,心气安宁,胆气不怯,则心之神明决断果敢而不惊。因此,心胆相辅相成,共同影响精神、情志活动。
2 基于“心与胆相通”探讨PVC伴焦虑、抑郁的中医病机
2.1 心胆失和为发病基础
2.1.1 气机失调《素问·举痛论》记载:“百病皆生于气。”心、胆共同调控气机之转输。《辨证录·怔忡门》言:“夫胆属少阳,心之母也,母虚则子亦虚,胆气一虚而脏腑之气皆无所遵从,而心尤无主,故怦怦而不安者。”提示心悸与心、胆气机失调有关。若人体心、胆功能出现异常将引发气机失调。《灵枢·口问》曰:“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情志过极,首伤心神,轻者心神不宁,重则扰乱脏腑气机,或胆气升发失权,肝气疏泄不及,导致全身气机失调,气结胸中不散,心必受其扰而发为心悸[16];长期忧思过度,超过胆主决断的自身调节能力时,若不能及时调畅情志,则见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18]。
2.1.2 君相失和胆为甲木,心为丁火,胆中所藏的精汁在肝气疏泄和升发的作用下,又可由精汁化为清气,从而循经上行,进入心中以助其“奉心化赤”之功来化生血液。《张聿青医案》言:“肝藏之气上升,则与少阳胆木交合,而心血以生。”心胆经络相通,若胆腑得不到充养,无以生心血,必将影响心的正常功能。加之心悸的频繁发作、长期的情志异常,导致PVC患者心体受损,而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其功用渐失,则会引起心之病变,加重心的搏动异常。胆合于肝,属木,内藏相火,心属于火,内藏君火,心为胆之子,胆火盛则母病及子,心火亦亢[19]。《医宗必读》说:“心悸症状不齐,总不外于心伤而火动,火郁而生涎也。”火邪与心相应,一方面耗气伤阴,加重心体损伤,另一方面可上扰神明,出现烦躁、焦虑失眠等表现。
2.2 神明动乱为病机关键心主藏神,胆主决断,心胆神合,以气为疏,以血为要,神安则志定。人体精神情志的正常,需要心主神明与胆主决断两者密切配合,缺一不可。《太平圣惠方》云:“夫胆是肝之府,若肝气有余,胆实,实则生热,热则精神惊悸不安,起卧不定,胸中冒闷,身体习习,眉头倾萎,口吐苦汁,心烦咽干,此是胆实热之候。”心胆枢机不利,气血津液不得输布,形成痰火、水饮、血瘀等不同病理产物,导致心神失于宁静,心脉失于滋润,从而表现为PVC;心神不能内守,情志失于调达,则生消极情绪如焦虑、抑郁等,可直接影响心脏自主神经功能,加重PVC的严重程度[20]。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加之PVC易受多种因素诱发,服药及复发等事件更让PVC患者压力倍增,情志不畅,五志过极,引动相火;气机郁滞,津液输布不畅,易凝滞成痰,久郁化热生火,动扰神明,发为惊悸不安。加之神明动乱则气血失和,久致五脏虚损,引起各种躯体疾病,加速疾病进程。
3 从胆论治PVC伴焦虑、抑郁
PVC伴焦虑、抑郁病位在心,与胆关系密切。李中梓曾在《医学入门》中提出了“心病怔忡宜温胆”的观点,徐春甫亦在《古今医统大全》中指出:“治惊悸有从肝胆二经,肝出之谋虑,游魂散守,恶动而惊,重治于肝经……又或嗜欲繁冗,思想无穷,则心神耗散,而心君不宁,此其所以有从肝胆出治也。”心与胆相通,故心系疾病如怔忡、心悸等,可从胆治之。
3.1 胆通则枢机转利情志过极是导致PVC伴焦虑、抑郁(惊悸不安状态)产生的始动病因和显性病因[21]。《证治汇补·郁证》云:“郁证虽多,皆因气不周流,法当顺气为先。”可见郁证的根本病机在于气机郁滞。而胆与全身气机的升降协调息息相关。《证治汇补·郁证》言:“有本气自郁而生病者……胆郁口晡热,怔忡不宁。”说明本病与胆气郁结密切相关。胆腑以通降为顺,正如《外经微言》所言:“胆之汁主藏,胆之气主泄,故喜通不喜塞也。而胆气又最易塞……一遇内郁,胆气不通矣。”胆腑清净,气机疏调,则心亦得清明,神志安定,主明下安。若忧思无度,致肝气不舍,胆气不通,气机不能斡旋升降则生郁,兼生湿、痰、郁、瘀等病理产物[22],旁扰及胆;胆失清净,决断之令不行,则最终影响心神,导致人体出现焦虑、抑郁、汗出、心悸等一系列异常心理改变与躯体化表现。
这类患者的早搏多由焦虑、抑郁、恐惧、烦躁等不良情绪诱发,又因疾病所引起的症状和对疾病缺乏正确的认识而加重。双心疾病患者初病时可仅有气化和神志问题,且发病多与情绪有关[23],常表现为心烦,胁肋胀痛,纳差,触事易惊,眩悸呕恶,失眠,舌淡,苔白,脉弦或沉弦,故治疗着重以疏胆理气、解郁安神为主,方选用柴胡疏肝散加减。若症见胁肋胀甚,善太息,嗳气不止者,可加木香、郁金等疏通肝胆之气,使肝气条达、胆腑通利则升降自和,心气通畅;若见痛甚者加檀香、青皮、川楝子、延胡索等行气止痛;若见食欲不振者,可加神曲,鸡内金等;若见多愁善感,睡眠质量较差者,加淮小麦、大枣养心安神。但要注意行气之品多伤阴津,故在治疗的同时勿忘酌加滋阴之品,常以白芍敛阴止痛。
3.2 胆清则火郁得散胆木性似肝木,喜条达而恶抑郁。《杂病广要》言:“夫胆是肝之腑,若肝气有余则胆实,实则生热,热则神惊而不安”,若数谋虑而不决,胆之枢机不利,则胆木易郁而化火,正如丹溪所云“气有余便是火”。胆与心沟通于经络,火性上炎,导致神失清明,出现精神活动异常,如烦躁、心悸等表现,正如《血证论·脏腑病机论》所说:“火扰其血则懊,神不清明则虚烦不眠,动悸惊惕。”此外,由于PVC病情易反复,焦虑、抑郁情绪伴随疾病始终,郁证经久不解,《临证指南医案》言:“因郁则气滞,气滞久则必化热,热郁则津液耗损而不流,升降之机失度。”气机失调,津气升降失常而生痰,痰湿化热化火,胆火夹痰上攻及心,痰得火而沸腾,火得痰而煽炽,火郁于内不散,进一步形成痰火胶结的病机,危害心神,导致心神浮荡,神惊于外,而致惊悸不安。正如《血证论》所说:“又凡胆经有痰,则胆火上越,此胆气不得内守,所以惊也。”
现代人因工作、社会及环境等原因,常于午夜胆经循行之子时久视熬夜,易致胆气运行失常,气机郁滞不畅,加之饮食习惯更多偏向于辛辣炙煿、肥甘厚味等易生痰湿之品。故临床上PVC伴焦虑、抑郁患者以痰湿体质偏多,此类患者大多数体型偏胖,临床多以心烦不寐、焦虑不安、面红油腻为主症,伴有胸闷脘痞、口黏口臭、咽干、多梦、身重困倦、便秘、舌红、脉滑数等症。此类患者当清胆化痰,散火安神,可用黄连温胆汤化裁。黄连温胆汤出自清代陆廷珍《六因条辨》,方以黄连泻火除烦,半夏、陈皮、茯苓燥湿化痰,枳实、竹茹理气和胃、清热除烦,胆南星清热化痰,对于合并失眠者,还可合生龙骨、生龙齿镇惊安神。现代研究亦发现,加味温胆汤可以有效减少室早次数,并对失眠、焦虑、抑郁等精神类疾病效果明显[24-25]。
3.3 胆壮则神有所主《医参》曰:“气以胆壮,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指出:“气以胆壮,邪不可干。”胆气充足,则脏气充盛,内、外邪气皆无从侵犯。一部分室早多由患者本身存在的器质性心血管疾病引起。身体虚弱,加之忧思恼怒多无以倾诉,各种过度的忧思、燥烦情绪会严重耗伤正气,故“久病多虚”。胆属少阳,为心之母,母虚子亦虚,正如《辨证录·怔忡门》载:“胆气一虚,而脏腑之气皆无所遵从,而心尤无主,故怦怦而不安。”心虚则神不内守,心神不定,从而导致惊悸不安状态的发生。另胆主少阳,胆虚则少阳之气失于升发,如《成方便读》所云:“胆为甲木,其象应春,今胆虚则不能遂其生长发陈之令,于是土不能得木而达也,土不达则痰涎易生。”胆虚不壮,枢运功能失调,痰浊内生,扰动神宅,又加重神气的损伤,使心气、心血、心神、心脉的损伤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正如周扬俊《金匮玉函经二注》所言:“胆气不足则疏泄不及,上为宗气不利,心气失和,心神无主则易生惊惕、恐惧。”
临床上伴有器质性心血管疾病的PVC患者,往往长期处于焦躁、孤僻、愤怒、失望、悲伤等情绪中,影响脏腑气血运行,使病情加重;而疾病反过来也会影响患者心理状态,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宋代《太平圣惠方》载:“夫心虚则多惊,胆虚则多恐,此皆气血不实,腑脏虚伤,风邪所干,入于经络,心既不足,胆气衰微,故令神思恐怯而多惊悸也。”此类患者的治疗首先当扶助正气,兼化痰祛湿、宁心安神,常选用安神定志丸化裁。若症见神疲气短明显者,加用人参、茯苓、茯神、党参补益心气,合用远志、石菖蒲安神定志;惊悸难以自止者,加用生龙齿、生龙骨、琥珀粉镇惊安神;惊悸不眠者,配伍炒枣仁、夜交藤、远志、珍珠母等宁心安神。
4 结语
心理压力与PVC的发病密切相关,各种外界因素导致的情志障碍使PVC患者常合并焦虑、抑郁状态[26-27]。目前,西医多采用抗心律失常及导管消融术等治疗方法,没有认识到焦虑、抑郁等情志障碍对于患者的影响,以及使用抗焦虑、抑郁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临床疗效不甚满意。随着“双心医学”的提出,给了中医中药治疗更广阔的空间。心胆相通,胆与本病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双心疾病的诊治上,现代医家多从肝论治,而鲜从胆论治[28]。心胆失和、神明动乱是本病的重要病机,胆为心之木,在临床治疗上,应重在恢复胆疏泄升发之性、固护决断之权,即通过调治胆腑,使胆通则枢机转利、胆清则火郁得散、胆壮则神有所主,如此胆气畅达无碍,心脉通畅而搏动有序,神明无所偏倚,有助于双心疾病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