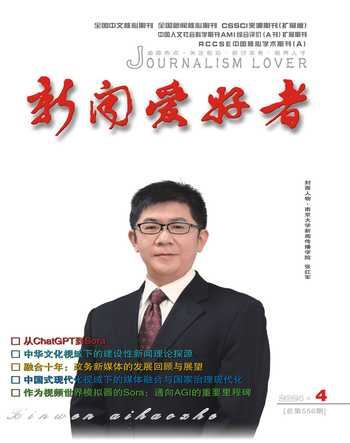深度媒介化:逻辑起点与形成要素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的深度媒介化已成为必然趋势。数字时代,深度媒介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自身的逻辑起点与形成要素:第一,深度媒介化需要重新聚焦媒介的物质性,深刻认识到深度媒介化时代媒介已经渐趋日常语境化,从而展开一种“去中介化”的研究,这亦是提出“深度媒介化”的逻辑起点;第二,数字媒体变革、先锋社群、传播型构三种要素分别为深度媒介化提供了技术支撑、驱动力量与分析框架,它们使得“深度媒介化”一词有了具体内涵而不至于沦为一种概念潮流。在厘清深度媒介化的逻辑起点与形成要素的基础上,我们应深入思考数字时代媒介化研究的可能性与发展方向。
【关键词】深度媒介化;先锋社群;传播型构;媒介物质性
随着数字媒体变革的深入发展,算法、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使得过去与媒体无关的实践转变为媒体实践,媒介也不再是“由某一类具体的数字媒体形塑而成,而是与这些彼此高度连接的数字媒体间的差异性息息相关”[1]。赫普与库尔德利等学者将其称为“深度媒介化”,试图以此来形容媒介化在数字时代的特征,并借此阐述“数字媒介在建构社会组织过程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2]。与原先的媒介化研究相比,深度媒介化既与之相连又有所区别,其形成和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起点与形成要素。
一、逻辑起点:媒介的物质性回归与日常语境化
早在2014年,便有学者指出媒介化这一概念过于抽象,且制度化研究路径与社会建构研究路径之间存在“结构”和“能动性”的二元矛盾。对此,赫普等学者在深度媒介化到来之际开始积极寻找两大研究路径对话的可能性,并试图发展出一个与媒介化有关的中层概念,以此来缩小媒介化这一抽象理论与实证研究之间的鸿沟。
(一)媒介化研究的物质性回归
夏瓦在2013年就曾从中程理论的视角审视媒介化研究,他坦言媒介化研究从未放弃过实证研究,并且强调将经验资料置于具体的时间、地点脉络下分析的必要性。这意味着要想厘清新的社会现实是如何基于媒介化过程而被建构的,需要建立一个中观层面的研究视角,将“结构”和“能动性”有效结合起来,以建立一条解决两种研究传统之间二元对立的“中间道路”。[3]
这需要重新聚焦媒介本身的物质性,赫普在其著作《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一書中特别强调,要想从过程的角度去探究媒体及其形塑力,除了媒介逻辑以外还必须考虑媒介的制度化与物质性,尤其是在考虑到算法、自动化和交流机器人之时,而这也是进行媒介化实证研究和批判性分析的必要条件。这种物质性转向并非是媒介化研究学者的“一家之言”,而是新闻传播学界对长期以来“重精神、轻物质”研究的学术性反思。正如章戈浩与张磊两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主流的传播学与媒介研究从未将技术与工具逐出视野,但“它与文化和符号形成了一组鲜明的二元对立,由此形成了‘媒介-物与‘人的二元对立。从李普曼引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开始,传播研究似乎就将实体和它的影子割裂开来,长期把话语以及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作为分析对象,并把传播效果放在核心。这一长期走势使得物质性成为传播研究的盲点”[4]。
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将媒介的物质性问题推到学者们的视野之中。默多克认为,媒介系统中使用的原材料、资源、各种支持日常活动的设备及维护其运作所需的劳动链都是媒介物质性的体现。媒介化时代这种物质性的内涵得到了丰富与延伸,既指传播活动中的媒介“不能被转化为人类意图性的对象特质”[5],又可以指“在具体社会建构活动中人类意图所遭遇的一种隶属于物本身的‘固着性”[6]。基于这种理解,媒介的物质性被纳入原有媒介化研究的社会建构视角中,制度化视角所强调的媒介的“结构性”也得以与“能动性”相关联。这便于学者尝试展开中观层面的研究来考察社会互动实践及其模式变迁,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社会和传播形式。
(二)媒介的“去中介化”与日常语境化
尽管深度媒介化仍然属于媒介化的一个阶段,但加上“深度”一词是有必要的。首先,媒介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媒介新特征的彰显,比如媒介多样性的增加、媒体融合的加快以及媒体更新间隔的缩短。其次,这些新的特征都指向了媒体的数字属性,也让学者意识到,要解决算法、数据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等问题,必须思考媒介化的现有研究路径,并对已有的概念进行整合分析。最后,“深度”一词也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社会媒介化程度的加深,即社会实践与媒体实践的界限日益模糊;二是各媒体间的连接也在加深,各种媒体的内部关系也被纳入重点关注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深度媒介化时代,媒介的社会角色由原来的“中介化”逐渐过渡至“去中介化”,逐渐入侵人们的日常生活,于无形中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内在逻辑。
早期的媒介化研究并非是“去中介化”的,它依然是中介化研究的延续或深化。这一点在深度媒介化到来之际有所改变,究其原因在于媒介逐渐趋于日常语境化,人们很难将那些媒介物所具有的独立性、空间层面上的之间性(in between)与桥接作用区分出来并加以阐释。换言之,深度媒介化时代的媒介是一种数字基础设施,它融合在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各个领域中,并重塑着人类的日常生活。各种平台媒体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平台化的媒介形态带来的是传播实践的平台化以及个人媒介权力的延展。媒介权力分散至个人导致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规范的“去中心、去权威”构成了平台化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亦是对日常生活的时空重塑:“现实的时间流转越来越多地被抽象为社交媒介中的‘时间线……现实空间也变成了媒介表演与分享的道具。”[7]
由此可见,在深度媒介化阶段,媒介化时空的泛化使得媒介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媒介也不再是人们传播活动或传播实践的“中介式”存在,而是一种侵蚀现实空间并影响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语境化存在。这要求我们必须从更宽广的社会语境中去理解媒介机构与传播过程,破除媒介中心化的迷信。
二、形成要素:深度媒介化的技术支撑、驱动力量与分析框架
观深度媒介化形成过程,其绝非是单一力量或要素发展和演进的结果,而是多种要素的联合推动。具体观之,深度媒介化的形成有其自身的技术支撑、驱动力量与分析框架。
(一)数字媒体变革:深度媒介化的技术支撑
互联网的商业化与私有化是深度媒介化形成的基础。回顾互联网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互联网的发展和西方解除管制并非偶然,而是一个“持续的政治选择”[8]。冷战期间,美国为了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政府机构、军事承包商和教育机构三方联合,共同促成了计算机网络的诞生。互联网自诞生之初便一直由美国军方把控,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互联网才逐渐走向大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盛行使得互联网领域要求解除管制的呼声日益高涨,美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开始推动互联网的私有化进程,大力扶植大型企业与集团,并鼓励其将互联网视为自身私有财产进行开发和利用。这种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意味着大型商业集团与公司拥有了媒体话语权,对公众话语和政治的影响力也日益提升,甚至渐成垄断之势。
为了谋求更多利益,这些大型商业集团与公司致力于加深和拓展互联网的数字化进程,使自己“得以在传播领域扩张商品的形式”[9]。数字技术通过广告、公关、智库等手段不断维护和巩固互联网的话语霸权,并推动互联网向电子媒体转变。从国际层面来看,对线路、路由器等基础设施拥有控制权的国家从理论上来说也有权决定别国是否能够进入国际互联网领域,而拥有更高端数字技术的企业则在该领域成为行业发展的标杆与领头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些技术公司决定着各网站的链接形式以及媒体的呈现内容和呈现方式,如阿里巴巴、苹果以及Facebook等大型媒体与通信服务公司,它们通过推动基于数据的价值模型向客户提供服务,成为塑造社会数字化进程的主要力量。
每一次技术层面的突破和发展必然带来数字媒体的根本性变革。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逐步完善,互联网的信息从“只读”走向开放和共享,最终实现“万物互联”。从互联网到移动终端、从传统媒体到平台媒体,媒介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突破和创新,原有的媒介生态格局也焕然一新,数字媒体成为连接社会各要素、构建传播环境的必要桥梁。这种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数字媒体变革“正逐步引领人类社会由工业经济时代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也必将造就新的传播形态与商业模式”[10]。
毫无疑问,数字媒体变革为深度媒介化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第一,新媒体尤其是平臺媒体的发展使得媒体内容的生产者呈指数级增长,随着媒体使用门槛的降低,普通民众也可以在媒体上发声。第二,数字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大型集团或公司的垄断局面,普通用户也能凭借自身能力获得特定的受众甚至是粉丝群,从而在一定范围内获得特定的话语权威。第三,数字媒体带来了新的生产和分销形式,许多媒体获取新闻信息的来源不再是政府或本站记者,而是普通的网络用户。这些改变都推动了新闻业的变革。一言以蔽之,在深度媒介化时代,各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数字媒体及其基础设施。
(二)先锋社群:深度媒介化的驱动力量
作为一个受社会约束的元过程,深度媒介化的基础仍然是人类实践。因此,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看待深度媒介化是有必要的,其中涉及诸多类型的“超个体行动者”,主要包括公司和政府等“企业行动者”以及社会运动和先锋社群等“集体行动者”[11]。随着媒介化研究的深入,赫普等学者发现,媒介化的首要推动者并不是大型科技公司与政府等“企业行动者”,而是类似创客、早期黑客等先锋社群。
在社群形成之前,零散的先锋者们基于一种使命感进行自我身份的建构:他们将自身视为先行者,并在实践中发挥中介作用以推动与媒体相关的变革,这种自我意识促使他们尝试在实践中超越自身所处的领域,并将不同的领域联系起来。媒体则为早期先锋者们提供了交流和传播的技术手段:它们通过塑造先行者的形象使其成为主流媒体和博客争相报道的对象。简言之,媒介变革为更广泛的社会话语演变提供了方向,并在媒介相关的变革中扮演了桥梁的角色。在赫普看来,与深度媒介化相关的先锋社群主要有三个:量化自我运动、创客运动和早期的黑客运动。[12]这三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但在具体的实践方向、对集体和社会转型的看法以及各自的影响范围等方面有所不同。
量化自我运动先锋社群的成员对自我实践相关的媒体技术有着共同的兴趣,他们致力于以数据为中心的自我生产,即收集与个人相关的大量量化数据以改善自身生活。这种强调不断进行自我衡量以改善自身和集体甚至社会的方式在今天已经被广泛采纳,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便是运动健身类APP的使用,它通过精确计算热量的摄入或消耗以帮助使用者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身材。创客运动将DIY、手工艺品和自主技术创新相结合,是一个聚集了世界各地拥有共同爱好者的社区。该社群成员有着共同的愿景,即物联网和相关生产技术将会带来一场新工业革命。多尔蒂在旧金山成立的创客媒体公司是创客运动的重要助推力,2019年,他还成立了创客社区以策展先锋社群。早期的黑客运动与后来被称为计算机程序破坏者的黑客不同,最初的黑客群体既没有破坏信息,也没有窃取各类数据,他们对计算机技术以及数据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就更广泛的意义而言,我们可以将早期的黑客运动理解为更为深远的“先锋新闻”领域的一个中心社区。对早期的黑客群体来说,新技术为他们带来了乌托邦式的可能性,极大地开发了人类的潜力。比如随着新闻业的彻底变革,早期的黑客群体与记者和技术爱好者们合作,为新闻工作描绘了新的、以技术为导向的愿景。其中最著名的是开放数据运动,它与计算机的开源运动联系紧密,并朝着开放数据新闻的目标不断前行,试图以此来重新思考新闻与新闻业的未来。因此,早期的黑客运动在推动当时的变革和丰富公共话语方面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个先锋社群对深度媒介化的贡献显而易见。作为各自领域的先锋,他们不断寻求最新的技术创新以推动与媒体相关的最新发展。通常而言,这些先锋社群对未来的设想往往超前于其所处时代,这往往会导致他们的设想难以实现,但重要的是,他们为技术变革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空间。正是通过对这种可能性空间的不断尝试和回顾,先锋社群在各自领域的成就和影响才能不断扩大。比如创客运动的实践者也尝试开发了许多没有市场的产品,且从未停下他们探索的脚步。因此,不妨将先锋社群视为深度媒介化的驱动力量:尽管他们的探索会失败,但他们对各种可能性的尝试开启了对深度媒介化未来的多元化想象。
(三)传播型构:深度媒介化的分析框架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社会被认为是由不同的实体组成的,比如学校、家庭等,每个社会领域自然也被概念化为围绕人类个体的静态存在。埃里亚斯却持相反观点,他认为个体与社会并非是独立的实体,而是从根本上相互纠缠的。为了进一步了解社会文化的交织样态,埃里亚斯提出了“型构”这一概念工具,意为经由不断地往复互动所形成的人的网络。换言之,社会机构和制度都以人类实践为基础,而每个个体都存在于其所属的社会关系,所以这些机构和制度可以看作是与个体相关的“型构”,个体则存在于他/她所发展或参与的不同型构的交叉点上。因此,型构可以被视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变量,作为理解社会领域的简单概念工具。
赫普等学者借鉴了埃里亚斯提出的“型构”这一概念,提出了“传播型构”的分析框架,将个体置于其所在的集体或组织,以此为起点考察与媒介相关的变化。赫普和哈泽布林克对“传播型构”进行了较为清晰的阐释:它存在于多媒体语境,用以指代一段各种传播行为之间交错联结的过程,其所蕴含的传播行动拥有共同的主题框架。赫普进一步指出,传播型构立足于三个假设:其一,社会生活是相互联系的;其二,社会生活具有过程性;其三,意义产生于相互作用的过程,并且是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这种型构与传播实践的结合为理解媒介与人的双向关系提供了一条新颖且有效的路径。具体而言,传播型构有三大特征:一是作为传播型构结构基础的“行动者丛”——一个由相互关联与沟通的个体网络;二是具有支配性的“主题框架”,它定义了每个传播型构的“主题”,对个体行为有着导向作用;三是具体的“传播实践”,这些传播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相互纠缠,并形成自身的“媒体集合”,这里的媒体集合包含了每个传播型构中涉及的所有媒介。
通过对传播型构的成立假设与特征的强调,可以更清晰地描绘出媒介的制度化与物质性是如何对媒介化世界的传播建构产生影响的:行动者丛、主题框架和传播实践中的媒体集合,都在不断因为现有媒体的更迭或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改变。这表明媒介化研究并非是研究变化中的媒介本身,而更关注媒介—传播和社会文化变化之间的勾连关系。
三、总结与展望:深度媒介化的未来研究路径
2018年,夏瓦将“可供性”引入对媒介化的阐释之中,认为可供性使得媒介促进或形塑传播行动成为可能,这为后续诸多研究提供了可供切入的视角。如喻国明等对虚拟偶像的“破圈”机制的研究、韩传喜等对网络文学的媒介化转向研究等。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双重应用彰显了可供性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它“将技术物视为嵌入人类日常行为与实践中的重要元素,聚焦人与技术互动关系中的行动机会,为探索建基于技术物基础上的日常行为特性提供了持续性的、分析力极强的研究纲领”[13]。
在最新研究中,赫普等学者在进一步论述“传播型构”时,指出拉图尔行动者网络视角、方法的“同步性媒介化研究”对媒介化研究极具指导性意义,可帮助聚焦具体的传播型构的过程。国内学者方念萱也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中层理论视野用“网络”“联结”这类地方性概念替代了传统媒介研究中的“结构”“整体”等宏观概念,以帮助媒介化研究聚焦传播实践中的行动框架。戴宇辰则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指出ANT视阈下未来媒介化研究的三个重点,即新媒介技术的“驯服”、媒介使用者的“能动性”以及媒介使用者对新技术的抵制及其开创另类的可能性。
尽管目前直接指出哪些理论或研究进路对媒介化研究可以有所借鉴的文献尚不多,但这些零星的思考和发现为媒介化研究的学者们带来了新的研究启发与关注点:对“网络”的重视更加强调了媒介与其他建制间的联结,媒介如何形塑社会,媒介实践又如何催生新的社会关系。这些新的关注點不仅可以促使学者对已有的媒介化研究进行回溯,更可以激励他们跳出现有研究的桎梏,以一种新的视野重新审视媒介化研究的未来。
参考文献:
[1]Hepp A.Deep Mediatization[M].Taylor&Francis Group,2020:5.
[2]常江,何仁亿.安德烈亚斯·赫普:我们生活在“万物媒介化”的时代——媒介化理论的内涵、方法与前景[J].新闻界,2020(6):4-11.
[3]戴宇辰.媒介化研究的“中间道路”:物质性路径与传播型构[J].南京社会科学,2021(7):104-112+121.
[4]章戈浩,张磊.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J].全球传媒学刊,2019,6(2):103-115.
[5]Aakhus M.,Ballard D.,Flanagin A.J.,Kuhn T.,Leonardi P.,Mease J.,&Miller K.Communication and Materiality:A Conversation from the CM Café[J].Communication Monographs.2011,78(4):557-568.
[6]戴宇辰.媒介化研究的“中间道路”:物质性路径与传播型构[J].南京社会科学,2021(7):104-112+121.
[7]彭兰.媒介化时空重塑的日常生活[J].新闻与写作,2022(6):1.
[8]Schiller D.Digital Capitalism: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M].MIT Press,1999:74.
[9]陈世华.数字资本主义:互联网政治经济学批判[J].南京社会科学,2017(9):110-117.
[10]许志强,王家福,刘思明.物联网+大数据:数字媒体变革的思考与未来媒体进化[J].电视研究,2017(11):37-40.
[11]Schimank U.Handeln und Strukturen:Einführung in die akteurstheoretische Soziologie,4[M].Auflage.Juventa,Weinheim,Basel,2010.
[12]Hepp A.Deep Mediatization[M].Taylor&Francis Group,2020:46.
[13]张昱辰,王智丽.超越社会建构论:STS与媒介研究的“交光互影”及其对传播研究的启示[J].新闻大学,2022(7):81-94+119-120.
作者简介:顾烨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后(杭州 310014)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