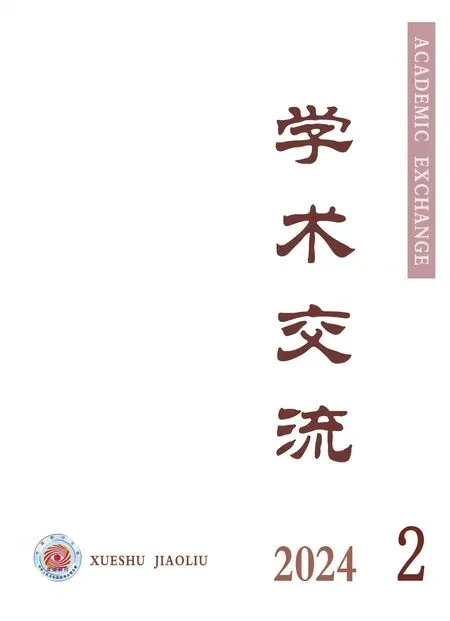从“定向”到“创新”:“期待视域”文化图式的演绎逻辑与内在理路
周文娟
(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在文学接受中,文本所“揭示的意义之所以被读者错过,不是因为意义过于隐蔽,而主要是因为读者的阐释框架不允许他们发现其实就在眼前的意义”[1]。究此窘况的成因,不外乎文本文化特质与读者“期待视域”文化特质错位所致。“期待视域”对于文学接受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期待视域”的理解,不能仅限于“读者在阅读前就已经形成可以赋予任何一个文本的‘先在结构’”[2]82-83,亦不可将其视为“一经逻辑的延伸,困境便接踵而至”的“未解之谜”[2]83。“关于‘期待视野’的更为合理的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揭示。”[2]82(1)大多探讨接受理论的文献将“expectation horizon”译为“期待视野”。然笔者认为,鉴于姚斯强调读者期待存在相对确定的“界域”,且姚斯“期待”术语本身源自伽达默尔“视域融合”(伽达默尔:《诠释学: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16页)思想的影响,因此,本文对这一术语均以“期待视域”表述。为“发现其实就在眼前的意义”有必要就文化图式视角,认真梳理“期待视域”图式改变的演绎逻辑和内在理路,深入揭示“期待视域”引导主客文化互动,改变且重构主体文化结构图式、实现文学意义准确诠释的“合理内涵”。
一、“期待视域”文化图式与文学接受
现代认知心理科学将“图式”定义为“人们过去的经历在大脑的动态组织,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模式”[3]201和“人们所有一般知识的总和”[4]35-58,并因此认为,“图式”为主体知觉、组织、获得和利用信息奠定了认知心理基础。也就是说,“图式”是归纳且抽象了大量事物特征信息的知识结构组织,它不仅为主体经验储备输入知识,也能动地输出知识文化、理论观点等智性信息,并能够在新旧知识信息交流、主客文化“顺应”与“同化”的往复中不断迭代更新知识域,能动地实现对客体文化图式的辨识、认同抑或融合。因此,对文化的“图式”理解是讨论文学接受的必然前提。
文学接受研究所关注的文化图式,通常指具备上述一般图式基本特性且系统体现文学社会属性的知识系统结构。文化图式的结构性认知,是“通过先前的经验储存的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块,可以调用来感知和理解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5],具有揭示人类文化认知一般性规律的强大解释力,是文化互动与文学接受得以产生和实现的社会性认知基础。文化图式作为个体文化特质不断凝练积聚的结果,通过主体知觉记忆比对辨识外部事物,体现了主体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影响形成的价值认知结构特质。同一文化图式间交流,可省略话语背景却不会发生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的理解歧义。而不同文化图式间,尤其是跨时空的文化图式交流,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差异性。这一差异状态形成的“意义真空(vacuum of sense),往往难以建立起理解交流所必需的语义连贯(semantic coherence)和情境连贯(situational coherence)”[6],最终使作者“揭示的意义……被读者错过”。无疑,文化图式相异或部分缺省,易导致文化意象缺失、错位甚至文化冲突,以致无法完成预期的认知推断而使接受受挫。文化缺省是文学接受中的常见现象,但缺省与受挫并不意味着文化互动和文学接受的终止。相反,缺省可能刺激主体强化对客体图式信息的加工接收,使缺省成为融合主客体文化、产生新文化图式结构的基础动力。正因如此,不同图式非但不会成为文化交流不可逾越的障碍,两种图式的相遇与互动恰恰会带来文化意识的沟通与互识,使其成为形成不同文化间性共存和实现图式更新与文学接受的基础保障。依据上述文化图式的本质特征,比对姚斯认为“期待视域”“具有一定制约性的方式获得‘视野交融’的性能”[7]38,“由传统的流派、风格或形式形成,却又只是为了一步步地摧毁它”[7]30,终“将自身区别于以前历史上的生活实践中的期待视野……从而打开未来经验之路”[7]50-51的质性描述,可以确认“期待视域”即一种产生文学的文化图式。
实际在文学事件中,作家通过故事情节以文学符号形成的文化图式与读者“期待视域”图式结构产生互动,届时对文本文化符号的解读,取决于读者由生活实践和文化积淀形成的心理期待定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由于自己所受的文化教育和文化熏染,在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中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化定式和文化价值作为唯一的或基本的标准、尺度和参照来度量、理解和评价其他文化,并将自己的文化观念、文化情感和文化追求作为一种文化定式而投射到对象之中”[8],文学接受正是建立在“期待视域”这一图式前提基础之上的文化心理交互活动。因此,任何文本单向度的文化输出都无从实现文学接受,只有读者与文本二者文化图式相向作用,才能最终促使读者“期待视域”图式变更形成新文化图式。也只有这样的文化图式改变,方可能使文本文化内涵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姚斯的读者“期待视域”、伊瑟尔文本“不确定性”的“空白”“召唤结构”[9]278理论概念,都是据此帮助读者解读文本文化符号、更新主体文化图式结构,进而理解文本文化内涵的文学接受引导策略。
二、“期待视域”图式融合与“先在结构”改变的演绎逻辑
如前所述,文学接受发生在读者与文本二者文化特质互动融合、结构图式重构改变的过程中。换言之,文学阅读并不仅限于对文本具体叙事符号的理解,“接受活动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对作品意义的重新发现和建构”[10]。文学接受是读者主体以自身文化图式“先在结构”,与文本客体文化特质产生异质交流碰撞,主体文化图式“先在结构”发生更新改变,进而“重新发现和建构”作品“现在意义”的文化融合过程。
读者文化图式“先在结构”凝聚了主体生存经历、文化素养、价值观念、性格气质以及审美经验等读者可能具备的全部主观因素。同理,文本作为客体也同样聚合了作者“可能具备的全部主观因素”。鉴于读者与作者往往所处不同时空,文本所体现的文化特质必然难以完全对应读者既有的文化图式结构。因此,读者与文本间产生文化错位在所难免。阅读中,由于当前解读的文本意义并不足以呈现作品的完整内涵,所以常常需要读者通过填充文本中的未及之事与未尽之意,主动对接并延伸已经获取的有限理解,方能进一步从中引申出文本整体文化的深层蕴含。在这一过程中,文本中未定性的“空白结构”无疑是主客体文化互补交融的重要媒介。读者填补“空白”不仅使文本叙事获得了持续不断的连贯化建构,也因填补“空白”生成的主客文化交互“潜在联结”秩序,促进了读者对文本意义综合理解的稳定性,形成了作者对作品寓意诠释的有效控制机制。基于这样“潜在联结”的控制机制,在“空白结构”对读者介入作品二度创造的诱导下,文本符号意义的“创造性理解在继续创造”[11]456,主体对文本文化符号依次往复的理解更新,亦持续贯穿于整个阅读过程。这一状态下的主客体文化图式“先在结构”的互动,“不断超越本文的历史视界,使之与我们自己的视界交融”[12]7-8,持续推动读者文化图式“先在结构”的演绎改变与迭代更新。姚斯将这一文化视域图式融合重构的逻辑现象,直白地解释为“打开自己的视域以吸收别人的视域,通过新的经验来纠正自己的期待,以便最后在承认别人的同时重新认识自己”[13]2。
透过上述视域图式的融合演绎逻辑分析,可清晰地看到,阅读中的文学“理解是能动的,带有创造的性质”[11]456。文学接受“永远不停地发生着从简单接受到批评性的理解,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从认识的审美标准到超越以往的新的生产的转换”[7]24过程中,伴随着阅读持续定然不断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新理解。接受活动这一主客文化图式改变融合的演绎逻辑,不仅确证了文学接受理解的创造建构性,也同时揭示了这一创造建构的丰富性。当读者以主体自身文化特质填补文本客体的文化“空白结构”之后,随之产生新文化特质并因此引发当前结构图式改变。起初,由于文化互动交流使异质文化特质被主体归纳为分类信息储备,因此主体结构图式存储增量。虽然这些附属增量储备的异质文化信息未必直接影响主体判断,但增量储备信息在与主体文化信息接触并存的同时,仍不免能动地渗透且悄然引发主体文化图式产生质变。由此,潜性的影响主体产生不同于原本文化的新意识倾向。与此同时,客体增量引发的质变,还必然引起主体原本信息次序的动态调整。这一指向重新平衡的动态调整,可能导致并不关联信息发生连接或使关联信息脱离,主体自身文化特质的如是动态变化,亦会导致主体“先在结构”图式改变。此外,除上述异质信息储存增量的影响,由主客互动而质性融合形成的新文化特质,更容易产生颠覆主体原有文化意识的价值判断,从而形成完全突破主体“先在结构”的另一种全新文化图式。文化互动与接受作为一种认同与接纳不同事物、更新认知关系序列的能动意识和能力倾向,其不仅可能使文化交流实现多种途径的有效互动,也可因此产生多种使主客关系转换、形态渗透交融的多样结构图式样态。正是这种文化转换和交融的多样可能性,使文学接受者可能凭借对文本客体文化的互动交流,在文化融合基础上不断更新自身的文化结构图式,与文本结构共同造就“带有创造性质”的文学作品。一如姚斯所言,尽管接受行为先验地存在着“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显现方式的定向性期待,这种期待有一个相对确定的界域,此界域圈定了理解之可能的限度”[14]289,但理解仍然可能产生多样的结果,或“被完整地保持下去,或被改变、重新定向,或讽刺性地获得实现”[7]29。
质言之,文学文化图式“先在结构”之所以能够在主客体交流中不断走向图式的融合与重构,使其演绎为创新作品“现在意义”的创新结构,引起这一“超越以往的新的生产的转换”的动力,归根到底源于作者在文本中预设“期待视域”“预先提示”的潜在引导作用。而文本多样“不确定性”“空白结构”的本质,亦不失为读者“期待视域”的实现路径,二者异曲同工且缺一不可。“期待视域”“空白”“召唤结构”共同吸引并引导读者能动地介入文本的意义建构。文本“期待视域”预设以文化特质的近似性吸引读者介入阅读思考;而文本“空白结构”则“召唤”读者去填补“空白”,使之能动地连接起整体文本的文化符号体系,在向文本填充、类比、提问、推理的组合推衍中解读文本文化特质,完整地达成了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与接受。其中读者对文本意义的能动填充,体现了主客体文化特质的相通融合;类比则使主体将当前体会到的文本文化与自身文化特质进行分类比较,由此获取对文本内涵的进一步解读;基于“空白”而来的提问,既包含了依据客体外在属性直接比对的感性推理,也包含了对客观对象各种普遍规律总体把握的一般性寻绎;与此同时,归纳多样文化特质与文本文化特质的组合推衍,又综合了文学文化的社会集群性和历史性,使读者克服了自身“先在结构”对文本历史文化的理解限阈,促进了读者对文本历史集群文化内涵的深入理解。
通过对读者文化结构图式改变的讨论可以确认,文学接受主要“研究的不是作品,而是文学话语的潜在可能性”[15]125。正是主客文化图式互动融合和读者“先在结构”改变的演绎逻辑,形成了读者主体文化图式结构量、序、质动态改变的结构状态。这一结构性改变“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16]380,文学接受是基于与文本互动而至的读者主体文化图式创新的结果。随着文本阅读主客体文化特质的深入互动,基于读者“期待视域”“先在结构”的“定向期待”,必然演绎出多样“创新期待”“现在结构”的发展理路。
三、“期待视域”由“定向”走向“创新”的内在理路
文学作品跨时空的传播特点终使作者缺位,使得其中的文化传递仅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展开。为此,文学作者往往需要事先将接受者区分成为某类同质群体,且抽象集群文化图式特质而为之设置“期待视域”。读者“期待视域”是主客体文化互动融合的基础前提,预设“期待视域”的主要作用在于吸引读者对作品产生意欲了解的阅读兴趣。因此姚斯将“期待视域”定义为:读者“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显现方式的定向性期待”,认为文学接受语境中的“期待视界正是定向期待与创新期待的对立统一”[17]146。并认为文学作品“即便它以崭新面目出现,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绝对新的姿态展示自身。但却可以通过预告、公开的或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隐蔽的暗示,预先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接受”[7]29。无疑,姚斯在这里表述了两层意思。首先,读者期待具有“相对确定的界域”而并非无矩可循,作者可以据此“界域”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接受”;其次,无论怎样“崭新面目”的文学新作都不可能产生“在信息真空中”,它必然存在着过往历史的文化痕迹。而这些文化因素,便是预设读者“期待视域”的依据所在。正因具备了这两点可供依仗的根据,作者才有望以某种“熟悉的特点或隐蔽的暗示”预设一定“特殊的接受”,以吸引读者在与文本交流中改变既有的“定向期待”而形成“创新期待”,进而实现对文本的理解与接受。
显然,姚斯“期待视域”理论概念的核心,在于其坚定不移地肯定了读者视域的动态性。尽管读者“期待视域”不容置疑地“先在”而客观地存在着,但这一“先在结构”的“定向期待”,却从不曾一成不变恒定地存在着。因此读者与文本客体之间,才不足以形成不可逾越的认知鸿沟。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与生俱来就具有探索未知事物的开放心态;吐故纳新是人客观认识外在事物、改变主观内在的意识前提,文化更新更是人类生存意识的超越性体现。所以,文本和读者文化图式之间存在的审美距离与视域张力,必然使“期待视域”结构图式成为并存“定向期待”与“创新期待”两种相对场力的间性结构系统。其中“定向期待”是主体对客体信息相对稳定且非刻意的基本反应力,是一种基于“类型的先在理解”期望,属于心理感受内化积淀的“现在结构”。但另一方面,鉴于人本性求变的意识属性,这依照自身心理预期选择接受的“定向”性,并不足以阻止主体对未知“视域”的探绎以及不断自行修正与改变。实际文学事件中,读者阅读既可由新文本唤起与既往经验对应的审美意向,也可以因好奇填补文本“空白结构”而产生新的审美理解。这样的审美经历,不仅可能促使主体修整既往“定向”的“期待视域”,甚至还可能颠覆和重构当前视域的图式结构,使主客体文化图式在“同化”与“顺应”中不断“创新”重建。显然,“期待视域”在“定向”之余还同时具有开放性的结构特征,具备适时认同客体先进文化特质而能动调整现有视界的自适应机制。“期待视域”由“定向”走向“创新”,不仅是人类文化意识自我超越的本然反应,也是主客体文化交流融合实现文学接受的必由之路。实际阅读进程中,读者“期待视域”在文本文化特质的“召唤”下,持续调整和迭代更新自身既有图式结构。这一动态反应的本质,是读者主体对象化与文本客体主体化的互动交替过程。而正是“期待视域”结构图式“定向期待”与“创新期待”并存的系统张力,决定了读者期待“界域”的动态调整性。随着主体与文本二者文化图式的互动融合,主体不仅能动地接受具有自身共性特征的文化特质,还会出于当前文化心理的需要,接受客体的异质文化特质,并因此对文本文化理解产生积极能动的创造性建构。因此,文学接受不容忽视读者与文本间文化互动可能产生的一切结果,不宜单纯从“定向期待”的“先在结构”视角来理解“期待视域”。“期待视野更加完整的含义应该是在‘先在结构’与‘体验建构’中互动生成”[2]84,进而创新“文学话语的潜在可能性”[15]125的动态结构图式。
从系统科学视角来认识文学接受,可将文学的话语结构区分为“含义”(meaning)与“意义”(significance)两个层面。阅读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实际上并不是本文的含义,而是本文对作者来说的意义”[18]16。“文学阐释实际上乃是一个意义生成、意义建构的过程”[19],所谓“含义”是作者赋予文本话语的固有存义,而“意义”则产生于读者与文本话语所发生的互动关系之中。当前“意义”随读者视域的改变而变化,是读者与文本话语相互作用而走向创新的结果。故此,读者介入文本互动的目的,并不仅在于揭示作者赋予作品固有映射的“含义”,而更在于攫取与文本互动中所生发的新的“意义”。这样的创新“意义”生成,并不来自主客体之间的图式重合,而是来自读者期待与文本视域之间的视域差距,视域差距是读者视域图式改变的基本动因。当读者在文本预设的“期待视域”引导下展开阅读,主体视域与文本视域相遇互动,一方面读者从自身的“期待视域”出发不断向文本索问;另一方面,文本也以所设定的“空白结构”“召唤”读者参与补充,以此“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随之开始唤起‘中间与终结’的期待”[7]29。正是在此基础上,读者在对文本空白的填充、接续互动中实现了相互文化的“顺应”与“同化”,使读者“期待视域”由“定向”走向“创新”,形成了对文本寓意的当下理解与接受。
姚斯还认为,“假如人们把既定期待视野与新作品出现之间的不一致描绘成审美距离,那么新作品的接受就可以通过对熟悉经验的否定或通过把新经验提高到意识层次,造成‘视野的变化’”[7]31,使读者“从阅读中获得的经验进入他生活实践的期待视界”[12]62,形成新的“界域”。就此不难看出,显然姚斯对“期待视域”的理论诠释,并未局限于读者“经验”对文本“意识”理解的引导作用上,同时他还强调了读者既有视域图式“对熟悉经验的否定”作用,而这正是“期待视域”之所以能够由“定向”走向“创新”改变的关键理路所在。值得强调的是,“期待视域”结构图式与文本的信息交流,不仅只是一种从记忆中检索提取相关信息以对应客体信息的单向度运作,而是一个通过“同化”“顺应”“平衡”图式结构的互动和间性同构的系统过程。“同化”是主体对信息输入刺激的过滤或适应,“顺应”使原有认知结构顺从客体文化引发图式改变重组,而“平衡”则体现了主体通过“同化”和“顺应”客体文化图式之后,文化同构重建图式所达成的新认知平衡与理解的接受状态。“期待视域”结构图式具有的可激活特性,能够使主体能动地从既有图式中提取可能适合的相关信息,以对应并判断理解外部的刺激信息,也会选择接受非记忆储存信息而修正既存图式。主体对文本叙事能动拓展的创新评价,皆起因于这样的图式修正效应。
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来看,任何文学都并非来自真空,它们都被镶嵌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文学的“写作和阅读是同一历史行为的两个方面”[20]377,作者和读者各自处在一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具有不尽相同的文化视域,“理解活动乃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21]372,“只有在文本结构与阅读行为的互动关系之中才能真正理解文学意义”[22]。而预设“期待视域”之所以能够使“阅读中阐释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弥合了当下与过去之间的历史间距”[23],使当前的读者重新与作品历史建立起意识联系且发掘出新的理解,是因为“期待视域”既是读者从自身条件出发对文学作品所能达到的理解程度,也是主体审美与文本叙事两极间互动融合的媒介纽带。文学接受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一种守恒,还有其发展”[24]406,“期待视域”在阅读中连接起主客体彼此的文化图式,由既有“定向”平衡状态向“创新”平衡状态不断演化。随着对文本认识的不断发展,那些由历史与时空因素造成的主客体文化视域差异不仅可以逾越,还恰好成为刺激主客视域融合和图式创新的起始动因。文学接受中“期待视域”的图式更新,往往能够“让个人进入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的传统之中”[21]372,使读者个体视域与文本历史视域“顺应”“同化”为创新作品价值的全新视域。一言以括之,“期待视域”结构图式是一种以先在“定向视域”起始,在交流互动中走向“创新期待”,且始终保持视域动态发展的认知进程,其文化意义“不可能与不断更新意义的历史过程相脱节”[25]206。预设“期待视域”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连接起作品“现在与过去的历史距离”,并使作品产生当前阅读的文化意义。显然,文学接受作为主体的内在文化心理建构,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由“定向期待”走向“创新期待”的发展过程。
格式塔心理美学异质同构论认为,需要从主客有机统一的角度整体地认识表现性,在强调客体具备刺激感知觉作用的表现性的同时,也须认识主体知觉对客体表现性的积极应和性。异质同构论认为主体之所以能够感受到客体表现性,正是因为力式样结构对精神世界和物理世界同样存在普遍的价值意义。审美主客体意识异质同构“实际上乃是一切存在物的基本存在形式,不论在我们心灵中,还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不论在人类社会中,还是在自然现象中,都存在着”[26]625。即便“那些不具有意识的事物……都和人体具有同样的表现性”[26]633。异质同构论从主客有机统一的整体认识观出发,认为表现性既属于生命体也属于非生命体,是世间一切事物的固有特性,并将表现性深刻归结为力式样的异质同构。这一主客整体性论断,超越了移情说、主观联想说、客观性质说、心理距离说、精神分析说等多种审美理论对表现性的有限诠释,为文学接受理论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
从这层意义上来理解,“期待视域”结构图式作为一种文学接受的心理认知模型,存在于语言认知、客体物质和主体意识层面,且具有可激活的开放包容性与强大的生产创新性,是作者引导读者理解和有效把控作品信息准确传递的不二利器。阅读之前先在的文化心理场是当下阅读接受活动的心理基础,每一次阅读接受过程既影响当前对文本的理解接受,也影响主体内在文化心理的动态发展建构。文学接受的文化心理异质同构,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动态平衡态,任何对接受主体心理场的刺激“都将导致重新建立起一种平衡的状态”[25]406,并使之再度走向新的“创新期待”。由于文学接受本身处于社会文化历史不断演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因此“创新期待”亦将循环往复持续发生在文学接受活动的全过程之中。归纳其荦荦大者,由“定向”走向“创新”,是文学“期待视域”结构图式改变的基本理路与恒定法则。
四、结语
接受理论将“视域”概念的所指从物理界域延伸至文化意识层面,喻指直觉、感知、判断、想象等文学信息理解行为的全部能及范畴。文学接受作为主体文化意识和文本文学意义感知、判断二者互动生成的审美心理机制,“现实地产生于阅读过程中,是文本和阅读交互运动的产物”[2]85。读者“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熟识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7]31,体现了读者对作品文化的理解融入程度,决定了作品的生命价值。因此可以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12]64。即便是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如果缺失后来者与之不断延续的对话,也不可能引发阅读主体的当前心理体验;假如果真如此,那么无论怎样的经典作品仍会无可避免地归入落寞,无从继续维持其曾经的历史盛誉。区别于鉴赏历史典籍,文学阅读主要关注的并非文本描述的过去事件,而是作品中那些值得读者重新解读、挖掘和发现的,具有深层内涵并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可以再度付诸实践的东西。因此,读者“期待视域”无疑是主体基于自身文化图式“先在结构”,在文本阅读中不断演绎发展、动态生成的当下“体验建构”。“期待视域”在“先在结构”与“体验建构”中动态生成的认识观,体现了接受理论视文学接受为读者与文本“对话交流”的根本理念。
“期待视域”文化结构图式互动与重构命题,既是具体的文学生产方法论探究,也是对文学接受理论学理法则的抽象阐释。当代文学接受理论,正处于“过去与未来的交接点上的那种鲜活的、搏动的、漂浮的,变动不居和闪烁不定的未就绪状态”[27],尤其对于姚斯“期待视域”概念的学理性,多有见仁见智的差异性理解。因此,文学接受亟待形成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和严谨缜密的研究范式;接受理论的“期待视域”结构图式研究,亦如同接受理论本体一样,需要不断从“定向期待”走向“创新期待”,以获得更为开阔的时代视域和更为科学的当代探索心得。“期待视域”文化图式演绎逻辑与内在理路研究的价值意义,亦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