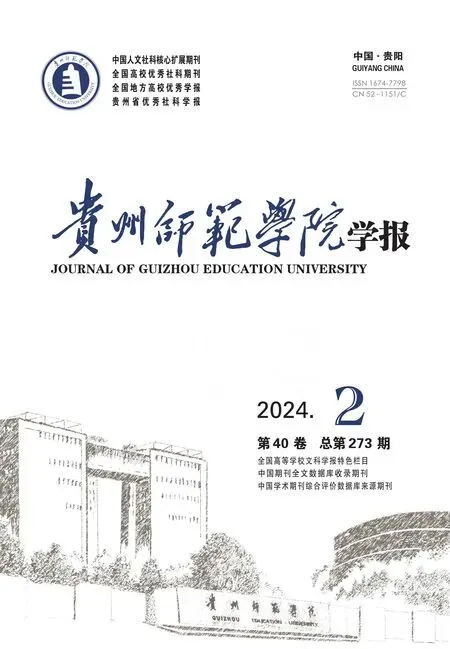原型传承与嬗变:《南柯太守传》与《南柯记》之比较
肖俏妮,米进忠
(东华理工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江西 南昌 344000)
唐传奇的诞生,标志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发展达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其曲折离奇的情节,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灵感来源。元杂剧中《倩女离魂》《西厢记》等作品,其基本人物形象与情节架构,便分别源自《离魂记》《莺莺传》等作品。明清时戏剧对唐传奇进行改编的现象更加普遍,汤显祖的《南柯记》便取材于《南柯太守传》。
目前学界关于两作的比较研究还不多见,已有成果多侧重于对两者佛道思想、情感内蕴等进行分析。(1)如李芳《情入梦中梦是情——试论<南柯太守传>与<南柯记>的内蕴差别》(《商》2014年第13期),杭蕾、丁海华《出处:道教还是佛教——浅析<南柯太守传>与<南柯记>结局之异同》(《文教资料》2017年第26期),邓斯博《神性视野下<南柯太守传>与<南柯梦记>人物形象比较研究——以淳于棼形象为中心》(《戏剧之家(上半月)》2014年第3期)等。而详考可知,《南柯记》中许多文学形象在《南柯太守传》所创原型基础上,既有传承又有嬗变。按弗莱的解释,原型“是指将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系起来的象征,可用于把我们的文学经验统一并整合起来。”[1]因此笔者拟从形象比较入手,分析《南柯记》对《南柯太守传》中原型的继承与嬗变,并结合创作心理、历史语境与传播方式等因素探讨其中原由。
一、原型传承:相似创作心理驱使下的选择
《南柯记》(2)本文所引《南柯记》内容选自:汤显祖,《汤显祖全集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是汤显祖对《南柯太守传》的改写。(3)本文所引《南柯太守传》内容选自:《唐宋传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前者中许多人与物,在后者里都有相应原型。据科瓦列夫观点,在作者以创作反映现实的过程中,其思想观点、趣味爱好、目的需求、个性气质等都会完整地、间接地表现出来。生活在同一环境中但怀有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作家,可能以不同方式反映生活;生活在不同环境中但立场与观点等一致的作家,可能以相似方式反映生活。[2]两作间原型传承现象,可从创作心理角度探讨。
(一)“廿载南柯寄一枝”:驸马身份背后的官场生态
《南柯记》的淳于棼与其原型多处相异,却继承了原型的驸马身份。现实中淳于棼因在官场孤立无援而被撤职,这是许多寒门官吏的真实写照。成为驸马意味着淳于棼能依托皇室入仕,该安排折射出李汤二人对官场的相似认知。小说家李公佐现存记载不多,但《酉阳杂俎》提到他创作《南柯太守传》前曾于庐州任职。[3]唐朝选官以科举和门荫为主,无世家倚仗而想为官实非易事。有学者认为小说家李公佐与“千牛备身”李公佐为一人[4],隋唐千牛多为以父祖封爵和资荫为官的亲贵子弟[5]。若真如此,李公佐自身便是淳于棼式角色,然而该推测缺乏确凿史料。与之相比,唐朝官场生态更值得参考。文献有载,唐中晚期“以崔、卢、李、郑、王为代表的山东旧士族出身的人在高级官员中数量较唐前期增多,他们在中央政权或地方藩镇中都占有重要地位。”[6]世家根系复杂,官僚互相荫庇,党同伐异是常见现象。在此背景下,李公佐让主角成为驸马,不单为创造一场美梦,更映射着他对官场关系的思考。
《南柯记》中驸马更是尊贵,不仅使右相忌惮“疏不间亲”,更让蚁王对淳于棼的军事错误“妨亲碍贵宜包奖”,与淳于棼现世遭遇反差极大。在与权势的抗争中,汤显祖也历经坎坷。他天资聪颖,二十一岁中举。可惜此后时运不济,两次应试不第。万历五年再次赴试,又不幸与张居正产生矛盾。他因多次拒绝张居正示好,直到对方去世次年才以低名次考中进士,后又因不愿受两位内阁大臣拉拢,被委以闲职。[7]6-9汤显祖出生书香门第,看待官场的视角与世家子弟不同。科举之路表明他不愿依附权势,也不赞同他人趋炎附势的行为。讽刺的是,《南柯记》的淳于棼本无做官之心,是瑶芳主动问“驸马你如今可想做甚么样官儿。”三言两语体现出权贵阶级对官位的志在必得,反映出的不仅是世家相互荫庇的现实,还有汤显祖对官吏彼此攀附等现象的控诉。
淳于棼提拔友人、结交权贵等行动不仅暴露出其受名利腐化后的劣性,也揭示出一条依权上位、提携他人、不断扩大关系网络的官场生态链。汤显祖为淳于棼安排的身份与遭际,投射出他对此类人物在官场生存状态的审视与思考。
(二)“端然气象君臣”:蚁王形象承载的君权意识
《南柯记》的蚁王继承了其原型任人唯亲、忌惮臣权的专制作风,既能凭女儿要求便将南柯转交“异族”,也能因“玄象谪见”将驸马逐出槐安,许多行为与封建君主别无二致。该原型的传承,离不开君权意识对两位作者潜移默化的影响。《礼记》有言:“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8]隋唐时期科举造成的思想控制,更加强了这一观念。《南柯太守传》问世前,李唐王朝方经安史之乱,内部藩镇割据严重,外部民族矛盾加剧。中央集权制度动摇,统治者易产生了更强的专制意识。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到唐德宗在东宫时,继承权并不稳定,形成了多疑性格。史料便载,“郜国公主以蛊事得罪,太子妃其女也。德宗疑之,几废者屡矣”,“顺宗在春宫,妃萧氏母郜国公主交通外人,上(德宗)疑其有他,连坐贬黜者数人,皇储亦危。”[9]蚁王同这一统治者十分相似。作为虚构角色,他若以明君或昏君等形象出现,有利于情节理想化或曲折化,可李公佐却淡化了其政治方面的优缺点,从心理层面将其塑造成一个多疑善变的形象。惟其如此,该角色才更有现实意义,他是君权意识的化身,是君主专制留在作者潜意识里的认知。
《南柯记》之蚁王亦同理。淳于棼因“玄象”而被幽禁的情节,涉及的便是君权与臣权的较量。其境遇由盛转衰,隐喻了臣权强盛至威胁君权,从而受到君权打压的过程。君权与臣权这对矛盾的互动,始终伴随封建社会历史进程。汤显祖所处时期,程朱理学因论证了君主专制的绝对性而被统治集团奉为正统,成为思想控制的有力工具,君权依旧是国家权力核心。[10]明代君臣冲突也较严重,著名的有洪武时期的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汤显祖生活年间有万历六年的买办银之争、矿税之争、国本之争以及织造、烧造、珠宝加派之争[11]等等。究其本质,皆因君臣矛盾导致君主怀疑权力遭受挑战而起。
文化思潮的延续和政治背景的相似,使汤显祖心理与李公佐不谋而合。蚁王原型与君权意识的传承,君权与臣权矛盾的延续,不仅承载了君主专制等传统观念,也成为时代政治局势和作者自身生活经验的缩影。
(三)“非惠政不能治之”:南柯中政治理想的寄托
李公佐笔下的南柯,是个丰饶但“政事不理”的大郡,为淳于棼提供了机会。《南柯记》里同样有这样一个等待贤政的地域。淳于棼本性粗犷且并不善治,后又在权势中迷失自我。如此人物,却创造出了古今士人的理想政局。两位作者如此安排似乎矛盾,却又耐人寻味。
角色完成能力范围外的行动,并不合逻辑。只因南柯不仅是淳于棼治理方案的试验场地,更是两位作者政治构想的显现。从该层面而言,作者是将思想与期望寄托于人物身上,驱使其按自己意志活动。《南柯太守传》中淳于棼治理南柯施以“省风俗,疗病苦”等方针,《南柯记》中淳于棼也推行“征徭薄,米谷多”“行乡约,制雅歌”“多风化,无暴苛”等政策。两个南柯都贯彻仁政德政、注重民生等儒家理念,最终达到政通人和的状态。这类情节,正出于两位作者相似的治理思维和政治理想。
高祖以来,唐代统治者尊崇儒道,士人大力迎合。[12]《南柯太守传》的治理观念,正切合儒家追求的政治秩序——以“德治”和“礼治”管理人民,从而实现和谐与融洽。[13]德宗朝内忧外患,加之“天灾流行, 四方代有, 率计被其害者, 每岁常不下一二十州。”[14]在此历史环境里,李公佐理想的社会秩序难以实现,他只能将对安定社会的向往寄托在南柯之上。这便解释了为何淳于棼能拥有不切实际的成就。而汤显祖师承泰州学派罗汝芳,自幼受阳明心学熏陶。他接受的也是“行仁政”“施仁德”“兴教化”等政治理念,渴望构建出理想社会。[15]然而明后期外有倭寇内有党争,土地兼并严重,朝廷随意征税,导致国内“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16]。彼时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社会矛盾加剧。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仕途的艰险以及抱负无法施展的苦闷,使汤显祖也将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于南柯中。
鲁枢元曾说,人作为一个复杂整体,其丰富的心理结构会潜在地影响作品的主题、倾向、基调、氛围,以及作品的情节、结构、语言、节奏等要素。[17]两位作者接受的思想文化和面临的社会环境有一定相似性,内心共同渴望改变政治局势、救民生于水火。他们试图构建出一个实施着自己理想主张的,成功创造出美好社会的政治幻想。相同的心理投射到作品中,《南柯记》便得以传承。
二、原型嬗变:不同历史语境留存下的烙印
汤显祖在传承《南柯太守传》中原型的同时,也对部分原型进行了完善或重塑。《南柯太守传》文末自述作于贞元十八年,而《南柯记》成稿据徐朔方所考是万历二十八年 。[18]2285两者相隔近八百年,政治局势、社会经济及思想文化等都已变化,历史语境已然不同。童庆炳认为,历史语境不仅是对某个时期历史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把握,更是对作品所产生的具体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的揭示。“只有揭示作家和作品所产生的具体的历史契机、文化变化、情境转换、遭遇突变、心理状态等,才能具体地深入了解这个作家为何成为具有这种特色的作家,这部作品为何成为具有如此思想和艺术风貌的作品。”[19]
(一)“风流一种生来带”:淳于棼性格嬗变中“情”的凸显
对淳于棼风流之描写,《南柯太守传》并不多,《南柯记》则全篇反复渲染。汤显祖此举,有其深意。《南柯记》里琼英评价淳于棼为“有情人也”,并以此选其为驸马。他是因“有情”,才获得了汤显祖的肯定,从此出发便能理解淳于棼的风流色彩。淳于棼之风流,不仅代表其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更是其自然情欲的流露。汤显祖塑造此角色时,重点在“情”而非“淫”,他突出的是淳于棼有情、重情、多情的形象。
汤显祖在《复甘义麓》中谈起《南柯记》写作思想,说“性无善无恶,情有之。因情成梦,因梦成戏。”[18]1464以“情”为核心,以有情与否衡量一切,在这方面他与琼英相似。先秦以来儒家便提倡以礼义约束人欲,宋明理学盛行时期理学家更直接将“天理”与“人欲”对立,抑制自然的人欲人情。然而明后期随着社会矛盾加剧及商品经济发展,思想控制逐渐松弛。统治阶级试图以理学枷锁否定基本人欲的同时,反封建反禁欲思潮也逐渐产生。汤显祖深受陆王心学及明中叶以来思想解放运动影响,在封建统治阶级与个性解放先驱的斗争里,矛盾集中于“情”与“理”的冲突,他正是主“情”派先锋之一。[20]210如周育德所言:“在当时那种思想解放的学术空气中,汤显祖要求表现‘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自由精神,要求顺乎天性自然,直言饮食男女,要求表现人的自然感情和欲望,正是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21]90汤显祖所言之“情”不限于男女之情,还包含一切合乎人类生存需要的情感和物欲。
叶朗曾总结汤显祖创作中“情”与“梦”的关系,汤显祖之“情”,与封建社会里的“理”与“法”相对,是人生而有之但后期被束缚住的东西。“情”既是与封建伦理对立的范畴,其中必存在超越封建社会的因素。汤显祖无法在现实里找到所追求的“有情”,便只好向“梦”中寻寄托,在“梦”中(即其文学创作中)他才能实现理想的“有情之天下”。[22]淳于棼之风流多情,恰是人类最本真、最自然欲望的体现。汤显祖塑造的,是未受礼教思想等压抑的人,是情欲与人性自由流露的人。在当时人性受抑的历史语境里,这一人物替汤显祖发出了反抗的呐喊。
(二)“金穴名姝”:公主形象嬗变与女性意识的提升
《南柯记》另一变化较大的人物是瑶芳公主。其原型金枝公主形象单薄,是作为淳于棼权力象征的工具性人物。相较而言,瑶芳形象便立体许多。汤显祖费大量笔墨为她设计了三大情节。其一,淳于棼思父之时,金枝只被动地执行“致馈贺之礼一以遣之”的指令,瑶芳却主动建言献策。同为贤妻,但瑶芳更具独立意识。其二,瑶台遭围时,瑶芳竟独自守城与檀萝太子对峙,临危不乱且智勇双全。其三,瑶芳深知淳于棼权盛易树敌,特在死前予他告诫。她能看破淳于棼看不破的世道人心,其心思之通透、眼光之深远非常人可比。
公主原型的嬗变,既体现出汤显祖对女性能力的肯定,也反映出社会上女性地位的提高。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各种新思想涌现,理学于女性的禁锢已日渐松弛,女性地位与话语权有所提高。当时女性的变化可概括如下:自我意识觉醒;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提高;知识型女性大量出现。[23]其整体形象已不同于李公佐时期。她们不再被彻底约束于传统观念中,拥有了更鲜明的性格与更自由的人格。
伴随历史环境变化,许多文人拥有了新女性观。李贽曾言:“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24]。他肯定女性才华与能力,对女性给予了相当的尊重。同为泰州学派一份子,汤显祖与李贽对待女性的态度多有相似。受社会思潮和师友思想等影响,汤显祖在创作上秉持“贵生”观念。他贵天下之生,重一切生命,也未轻视同样具有人权的女性。他本身创作过不少优秀女性角色,如杜丽娘、霍小玉、崔氏等。在封建社会中能做到同情女性的悲惨命运,赞赏女性的杰出才华,这是十分可贵的品质,公主的形象变化便是佳例。
(三)“弄威权要把江山霸”:右相形象嬗变中朋党相争的隐喻
相对于其出场极少的原型,《南柯记》的右相不仅戏份重大,更被塑造成了长袖善舞、嫉妒心强的反面形象。正是他推波助澜,使淳于棼被逐出槐安。这一弄权角色是对官场现实的又一反映。若蚁王是君主专制的象征,右相之所为则是朝廷上臣权此消彼长、派别互相倾轧的暗示。权臣只手遮天、官吏互相拉拢或敌对,是封建官场常态。受阶级背景、思想观念、政治立场等因素影响,任何时代的官僚间都存在明争暗斗,晚明也不例外。
据周育德整理,汤显祖与政界有过不少矛盾。他入仕前期是张居正独揽朝纲时期,他因拒绝张居正招揽而两度名落孙山,而张居正却营私舞弊将落第的儿子们送上榜。不仅如此,张居正因反对讲学之风严厉打击泰州学派,还罢免了汤显祖恩师罗汝芳的官职。[21]109-112一面是亲受的不公,一面是师友遭遇的打压,汤显祖对高位者的权力压迫有了深切体验。此外,当时官僚集团彼此倾轧,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因不愿同流合污,汤显祖曾上书直陈,神宗在位二十年内“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此奏疏无异于说主昏则臣佞,皇帝当即震怒,将汤显祖远谪广东。[7]13-14虽无史料证明,汤显祖创作的槐安朝廷是映射神宗时期,但很多时候神宗对权臣的偏信及权臣们在官场搅弄风云的行为,的确与蚁王和右相颇为相似。
结合晚明历史语境分析右相的嬗变,不难发现其中蕴含汤显祖对官场现实的理解与感触。他在宦途里未尝不曾扮演过淳于棼原本的角色,因受右相一类高官排挤与倾轧而落个凄惨下场。若汤显祖所处的历史阶段若是圣主贤臣,朝廷上下一心,右相形象应当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这既是历史语境对创作的影响,也是创作对历史趋势的真实反映。从《南柯太守传》到《南柯记》,故事角色与走向如此相似,然而每个形象的变化都各有意义。在汤显祖的南柯梦里,既传承了与李公佐理念相同的部分,又在时代变换与思想更迭中,为原型赋予了新的意蕴。
三、文学传播对原型嬗变之影响
《南柯太守传》与《南柯记》间原型嬗变,从文本与作者角度分析,是因两作诞生时历史语境不同。然而传播载体、传播方式、受众群体等外部因素的变化,也会导致原型嬗变。本部分就此展开,从传播与接受角度,对两版“南柯梦”间原型的变化进行了探讨。
(一)原型因适应传播载体而发生嬗变
信息从发送者到接收者,必须经过一定的渠道。通过该渠道时,信息必须采用一种能被接收者感知的物质形式,这种物质形式就是中介。[25]对于文学活动而言,这个中介就是传播的载体。
《南柯太守传》属唐传奇。鲁迅曾概括道:“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以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然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日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26]按其观点,唐传奇特点在于情节曲折离奇,具有讽喻劝诫功能,多用以寄托思想。至于人物形象,多依靠故事中偶尔穿插的人物活动来呈现。《南柯太守传》的公主便是如此,正面描写她的文字寥寥无几,其存在只为推动情节发展。李公佐的创作动机,从当时社会环境和唐传奇性质来看,确实有讽劝意味。当故事核心聚焦在淳于棼南柯一梦的隐喻中,公主形象自然被忽视了。
《南柯记》是明代戏曲的一种,戏曲重要的是靠人物表演再现故事,同时吸引观众。为达该标准,人物更需要生动、立体、有个性。此外,戏曲虽也有一定教化意义,但更注重音乐性、娱乐性、审美性等特征。这是两作在传播载体特性方面的区别。载体不同,作者希望借此取得的效果也不同。从戏曲受众视角而言,《南柯记》中淳于棼的爱情故事是一大看点。瑶芳作为跟淳于棼有多场对手戏的旦角,外貌、神态、语言等描写都大量增加。汤显祖为使作品适应观众审美需求,更好地迎合市场,会相应地将人物形象改造得更饱满生动,因而瑶芳也需拥有更鲜明的个性、更多高光时刻和更深刻的爱情故事。小说作者注重借故事表达思想观念,戏曲作者则还需考虑故事是否能给受众审美愉悦感。一部戏曲若尽是说教内容,则容易落入俗套,无法吸引观众。汤显祖改造后的淳于棼、瑶芳、右相等形象,既更贴合文体,又更能顺应受众期待。
(二)原型因适应传播方式而发生嬗变
小说和戏曲传播方式也不同。小说一般靠单纯的文字创作,凭纸稿或口头传播。因叙事篇幅短,文本容量有限,要求故事精简和思想突出。而戏曲需考虑角色行当、对白唱腔、配乐伴奏、妆容服饰、舞台场景等众多元素,作者要塑造人物或叙述事件有更多表现工具。据整理得知,唐代小说较普遍的传播方式有三种:传抄、书肆、口头。[27]78无论哪种方式,都是将文字直接传达给接收者。当读者或听众接收到小说内容时,仍需根据生活经验加工理解。然而每个受众记忆力与思维能力不同,在接受过程中可能出现信息遗忘、理解偏差等情况,因此作者必须慎重考量文本重心与详略。再结合唐传奇重文采、重情节、重思想等特征,作者自然会优先选择利于表达思想感情的写作策略,相对而言形象塑造便被排在了后位。
戏曲虽然也有文本,但更常以演出形式传播。徐子方认为,戏曲是“以舞台扮演为中心,融唱做念打于一炉;以剧本文学为基础,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绘画、建筑等在内的,并依赖观众直接参与的一门综合性艺术。”[28]戏曲演出对观众的影响也是综合性的、多方面的。戏曲受众无需对文本加工转换,呈现在其面前的是兼具文学性与审美性的舞台实景。在《南柯太守传》中要判断人物性格,需从文字描述中推测。而《南柯记》以生、旦、净、末、丑等行当分配演出的方式,使观众能依经验或演员神态大致判断出人物类型。比如净扮周弁,末扮田子华,行当不同两人表演便大不一样。演员们“笑”“泣”等神态表演,也能让人物心理得到更多展现。以戏曲形式传播的故事,除了靠情节打动人心,还能从念白、戏腔、肢体语言角度,带给受众听觉与视觉的多重感染。汤显祖为了达到更好的戏曲效果,也会运用丰富的表现方式对原型做出相应改动。
传播载体的变动,对原型嬗变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汤显祖在创作过程中,为适应戏曲的审美要求,需要不断调整并完善人物形象。在其创作完成之后,作品也会因搬上舞台表演而产生新的内涵与意义。
(三)原型因适应受众群体而发生嬗变
唐传奇在唐代主要传播方式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幕府文士间的闲谈。当时科举艰难,许多文人选择入幕为官,文士聚集在一起,交流间不仅能获得材料,也能互相传看或转述作品。此过程中文士群体兼备了作者、传播者、读者三重身份[27]21-31。另一类文人行卷之风。唐代科举考试不糊名,举子考前常将作品呈给政坛或文坛名人,以求获得推荐。贞元、元和年间行卷正盛,传奇也名篇倍出。[29]由此可知,唐传奇受众多是有一定学识或地位的文人与显贵。作者会有目的地创作传奇,展示思想与才华以寻求伯乐,因此唐传奇才更注重情节性与思想性。《南柯太守传》主角一朝富贵又终成幻梦的故事,篇幅不长但情节曲折完整,可有仁政爱民、反藩镇割据、超脱名利等多种解读,正适应唐传奇受众的接受心理与阅读取向。
相对唐传奇而言,戏曲受众群体已逐渐扩大。施旭升将戏曲传统受众做了以下分类:庙会演出时的村镇观众、勾栏瓦舍的市民观众、豢养戏班的商人观众、文人士大夫观众、宫廷观众等,此外还有剧本读者。[30]其中市民阶层占很大一部分。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其娱乐需求的增长。戏曲是面向市场的产品,若只有思想性和文学性是不济的。为迎合观众审美需要与接受喜好,作者需灵活改变。比如增强剧本情感色彩与通俗色彩,提高其趣味性与娱乐性。比之《南柯太守传》,《南柯记》人物更生动立体、冲突更加尖锐,也与此相关。淳于棼与公主的缠绵爱情及他迷恋群女的情节,更是观众闲暇时喜闻乐见的内容。于市民阶层而言,若作品内核晦涩沉重,反觉枯燥难懂。因此创作需通俗浅易,以贴近民众心理。正因重视受众心理,汤显祖的戏曲取得了深广影响。许多青年妇女阅其作品后深受触动,甚至出现了“愤惋而终”的俞二娘,和“自祭肖像,端坐梳妆而死”的冯小青等人。[20]225-230
四、结语
文艺作品是人在意识指导下的创造,既受后天经验影响,又是对现实的反映。南柯梦这一经典题材,千百年来不断被后人吸收运用,成就了不少佳篇。它以人生如梦之喻为核心,构建起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又在人美梦正酣时使之骤然倾塌。主角梦醒后立在幻想的断壁颓垣里,正如作者徘徊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回味无穷之处,恰是故事魅力所在。惟其如梦,方可寄托平生无法实现的理想。正因可堪寄托,才承载了作者们难以诉诸于口的情感与思想。《南柯太守传》与《南柯记》两部作品,因原型而建构起沟通的桥梁,体现出作者们创作心理的暗合,也反映出历史语境与其他因素的变化,为后世留下了通过文本探索作者与回溯历史的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