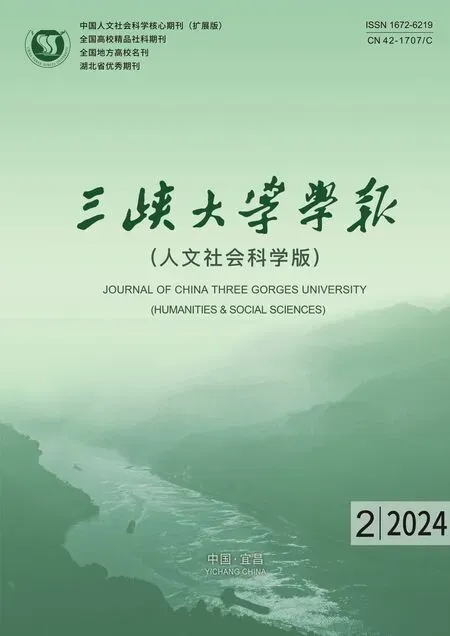文坛交互与自我重塑:对沈从文20 世纪30—80 年代自订选集的综合考察
宫震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0 世纪30—80 年代,沈从文出版了多种小说自选集,先后有良友版《从文小说习作选》、开明版“沈从文著作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沈从文小说选集》和《沈从文小说选》以及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沈从文选集》等。 与他选本不同,自选集更强调作家本人的主体性。 实际上,“亲选亲校”这一行为本身就有类似于文学批评的尺度性:在与选文活动相伴生的删、增、补、改、编等过程中,不符合作家审美理想、艺术准则的文本被舍弃,而留存的大多是作家心目中的善本。当同一文本在不同版本的选集中被反复辑入,该文本在作家心目中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这一过程也常常被研究者称为作家的“自我经典化”①。 不过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这种“自我”的主体性也是有其限度的,作家的自我批评视野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特定历史语境的规范。 故而在考察作家自订选集时,应该特别注意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与作家思想意识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 沈从文小说自订选集的编纂、出版,就是外部文坛生态与作家本人的文学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对话的结果。
一、沈从文自订选集略述
沈从文的选文活动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三四十年代,选集主要有《从文小说习作选》和“沈从文著作集”。 其中,《从文小说习作选》为1936 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内收“代序”一篇、短篇小说十五篇、短篇小说集(《月下小景》)一部、中篇小说(《神巫之爱》)一篇、自传(《从文自传》)一部。 而“沈从文著作集”由开明书店承印,出版和再版时间主要集中在1943—1949 年,各书均再版三到五次。 该选集原计划出版30 种,实际上仅出版了不到三分之一便中途夭折。 1953 年,沈从文接到开明书店通知:“所有作品已过时,已印、待印及纸型”,皆已全部焚毁[1]267。 现在该著作集比较可靠的书目包括《黑凤集》《春灯集》《边城》《长河》《湘西》《湘行散记》《月下小景》《从文自传》八书[2]。 二是1950 年代,选集主要有《沈从文小说选集》。 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7 年出版,共收入序言一篇、短篇小说二十二篇、中篇小说(《边城》)一篇,是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出版的第一部选集,也是50—70 年代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唯一一种沈从文选集。 三是80 年代以后。 此时沈从文的身体每况愈下,工作状态不佳,很多选集是在夫人张兆和和青年学者凌宇、邵华强等人帮助下选校而成。 但在修改和选篇上沈氏也都参与其中,所以80 年代选集也基本能反映作者本人的意见和设想②。 这一时期的选集主要有《从文散文选》《沈从文散文选》《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小说选》(上、下)和《沈从文选集》等。其中《从文散文选》为1980 年香港时代图书公司出版,内收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和小说集《劫后残稿》(《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 该书或许是沈从文亲校亲选的最后一部自选集,除了出版此“散文集”外,按原计划该系列书目还包括“短篇小说集二,长篇中篇集一(包括《边城》、《长河》),故事合印集一(包括《月下小景》及新补三文)。”[3]然而《从文散文选》出版后,其余选集未见下文。 《沈从文散文选》和《沈从文小说选》是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邀在1981 年出版的选集,题材以湘西优先。 虽然“印的不如香港那本散文选好,错字也多”,但依然算得上是沈从文近三十年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重印的两本旧作[1]340。 《沈从文小说选》(上、下)为198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青年学者凌宇的帮助下完成选印。 有上、下两卷,内收“选集题记”一篇,小说三十五篇。 《沈从文选集》由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3 年出版,在凌宇的帮助下选印,该书共五卷,主要包括:“散文一卷,小说三卷,(短篇二、中、长为一),文学评论及其他杂论一卷。”[4]1这与1980 年准备在香港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选集的体例安排比较相似,可以看作是1980 年代初沈氏选集理想的一种实践。
在20 世纪30—50 年代的作品中,沈从文比较看重1936 年的《从文小说习作选》和1957 年的《沈从文小说选集》。 他说:“作品文字比较成熟,大致只是良友图书公司《习作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从文小说选》,及开明书店印行的十个短篇及杂著。”[5]414。 沈从文认为也只有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选集“选得比较精”[6]396。 各版自选集不但集中展示了作者各个阶段的创作实绩,更反映了他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状态和文艺观。 本文拟以上述三个选集为切入点,通过考察时代语境的变化对作家选文活动的影响,进而深入研探作家与文坛互动机制。
二、在自我重塑中申述文学理想:1936 年《从文小说习作选》
1936 年沈从文应赵家璧之邀,于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第一部自订选集《从文小说习作选》(下称《习作选》),来作为自己“这个乡下人来到都市中十年一点纪念”[7]7。 然而通过考察《习作选》的结构体例、选篇内容与生成过程可知,该选集的出版并非如沈氏所言是一次“纪念”写作私史的个人活动,而是作家创造的一个重塑自我的言说契机。 具体来看,这种重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以“精选”代“多产”,通过选文活动来重塑自己的写作史。 沈从文自20 世纪30 年代初便有“多产作家”之称,1934 年苏雪林不无惊讶地写道:沈氏“是一个以作品产量丰富迅速而惊人的作家”,他自从事创作以来,至今不过八九年光景,而已经出版单行本二十余种,其他零星发表于报章杂志者也另有十来种[8]。 由此可见,在《习作选》印行以前,可供作者参考的选文底本是极其庞大的。 然而,1934 年最初萌生“印个选集”想法的沈从文,却只预备“取精摘优”选入十五篇[9]182。 显然,《习作选》实际收录的篇数与沈氏庞大的写作成果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这种事实上的“多产”与自我展览时的“精选”形成一对饶有意味的对照。 在30 年代,“多产”并不一定是对作家的褒奖之辞,其语义反而常常与公式化、粗制滥造、追求利润联系在一起。 1931 年韩侍桁曾撰文批评沈从文作品中的情色描写,指斥他故意迎合“一般人的本能的低级趣味”[10]。 换句话说,批评者暗示沈从文的“多产”实际上是利用现代商业文化机制,为了销量一味生产迎合市场需求的作品。 这种批判并非空穴来风,沈氏晚年在谈到“多产作家”这一名号时坦言“实为应付生活”而形成的。 自己“直到抗战,已出了约六十个小册子,稿费一个季度还不会到三五十元。 维持家中生活,还要靠一只手不断写下去,才能得到解决。 作品当然不免泥沙俱下。”[6]431然而,在《习作选集代序》中,作者却有意识地将过去十年的个人写作史概述为“终生工作(写作)一种初步的实验”:“我总以为这个工作比一切事业还艰辛,需要日子从各方面去实验,作品失败了,不足丧气,不妨重来一次;成功了,也许近于凑巧,不妨再换个方式看看。”[7]1-2不难看出,通过出版《习作选》,作者希图将追求“实利”的卖稿行为转化为一种纯粹的、艺术性的写作活动。 他在文章中态度鲜明地批判文学“趣味化”与“商业化”的倾向:商人建立书店,用“不过大的本钱”购入作家版权,相互竞卖。 目前,这种“商业”的竞争,已逐渐“支配了许多人的兴味”[11]。 对新文学流于“趣味”化和“商业”化的反思批判显然启发了他随后对“海派”的挞伐,而自己为生活而卖文、追求“实利”的写作史与此时的文艺主张不但格格不入,反而与自己所口诛笔伐的“海派”存在某种相似性。 因此,以“实验”代“实利”的自我形象重塑对30 年代的沈从文来说十分必要。
其次,去“思想”而留“热情”与“悲痛”,通过选文活动申述自己对审美理想的持守。 与左翼批评观所肯定的具有“思想性”的作品不同,沈从文的作品不但极少直面斗争和冲突,其清新质朴的语言也很容易被视作一种远离生活的“轻飘的文体”。 有批评家就认为,沈氏作品的内容“对于社会的进展与对于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的认识”是毫无启发的[10]。 在他们看来,沈从文就像是“裹着小脚躲在深闺的小姐”,只会在“自己的园地”里浅吟低唱。 与之相比,那些在街头往来的“摩登女郎”至少是“社会的,和社会接触的”[12]。 总之,沈氏“在艺术上固然有独特的造就,而在思想上是不能获得人民的好评的。”[13]面对这种批评,沈从文意图借助出版选集的机会,对自己的写作追求作一重新申述。 一方面,沈从文认为自己并未离开人生,只是他关怀人生的方式与左翼话语有所不同。 他在《习作选》的序言里说:批评者所谓的“思想”,无非是强调作品要“有‘血’,有‘泪’”,且要在故事情节里表现社会现实和斗争。 但是真到执笔的时候,为了使作品“浸透作者的人格和感情”,就必须要学会离开表象的现实,必须要“彻底地独断”[7]2。也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读者在其文本中往往只是发掘了一层表象的东西:“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7]5。另一方面,沈从文意图通过现代都市题材和湘西边民题材对照的方式,来表现他的道德批判和人文关怀。实际上,“乡下人”对沈从文而言并非一种既得的理想人格,而是在现代都市文明的颓丧与堕落中不断生成的参照系。 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中有意识地收录了两种题材或许能反映这种对照性:
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7]4。
通观入集的短篇小说,涉及湘西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题材约占总篇目的一半,这也可以体现沈从文从湘西寻求优美和道德理想的愿望。 而其余诸篇皆以城市生活为题材。 与湘西小说不同,沈从文在城市题材的小说中总是无法节制讽意。 例如《腐烂》中那种肮脏腐臭的贫民窟环境,《八骏图》中“上流社会”知识分子的虚伪与可笑,都表现出作者对城市的厌倦。 而湘西题材则以“乡村平凡人物为主格,写他们最人性的一面”[9]182,他们简单纯粹,追求着人类最基本的感官享受,追求快乐,在秀美原始的山水环境中张扬自我。
简单来看,沈从文编选《习作选》的直接目的主要是为了回应文坛质疑,进而重塑自己的写作史,表现对自己“实验”方向和文学理想的持守。 他说:“不特读者如何不能引起我的注意,便是任何一种批评意见,目前似乎也都不需要。”[7]4这其实是言过其实了:一方面,沈从文一直有修改旧作的习惯,而且在校改原稿时也会参考批评家的意见;另一方面,文本必然要在与时代的对话中不断生成,因此作家无法彻底屏蔽批评家和读者的意见。 小说《菜园》涉及革命者的家庭题材,故事的悲剧结局为作品笼罩上一层痛苦的色彩。 韩侍桁曾批评沈从文以一种虚浮轻飘的笔调叙事,从而将这种痛苦破坏掉了[10]。 后来,沈从文将该作收入《新与旧》时做了一定改动,增加了小说的悲剧氛围。 例如,初刊本述及母亲自杀时轻描淡写:“到了儿子生日那天,忽然用一根丝绦套在颈子上,便缢死了。”[14]但在选入《新与旧》时,沈从文将其改为:“到儿子生日那一天,天落大雪,像这样活下去日子已经够了,春天同秋天不用再来了,忽然用一根丝绦套在颈子上,便缢死了。”[15]如此修改,更加凸显了母亲的绝望,也使小说基调更加沉痛。 就《习作选》来看,沈从文的校改同样受到当时文坛上各种声音的影响。例如,苏雪林评论说虽然作者用笔“力求短峭简练,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 有时累累数百言还不能达出‘中心思想’。 有似老妪谈家常,叨叨絮絮,说了半天,听者尚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又好像用软绵绵的拳头去打胖子,打不到他的痛处。”[8]沈从文对这一弱点心知肚明,因此在语言的修改上下了很大功夫。 《柏子》的初刊本写作时间仅一个下午,写成后即寄送《小说月报》③。 虽说顺利,但其粗糙程度也可想而知。 例如,初刊本在述及柏子和妇人“胡闹”时写道:“柏子只有如妇人所说,索性像牛,牛到后是喘息了,松弛了,像一堆带泥的吊船棕绳,散漫的在床上。”[16]该句接连转换主语,不知道“牛”是何指,句意十分模糊缠结。而《习作选》收录的版本显然经过作者认真的雕琢:“柏子只有如妇人所说,粗卤得同一只小公牛一样。到后于是喘息了,松弛了,像一堆带泥的吊船棕绳,散漫的搁在床上。”[17]通过修改,作者以“小公牛”来比喻柏子粗鲁笨拙的用意便十分明显了。
总之,《习作选》的选编与出版,不但是沈从文对自身写作史的一次有意味的重构,更是对1930 年代中期自身道德理想和文艺观念的申述。 这种转变也体现出作家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对其文艺理念的影响:此前沈氏受制于文化市场的稿酬秩序,为了获取足额的生活费而不得不高效“产出”大量作品。 30 年代中期,沈氏获得北平的教职,跻身于“京派”学者名流之间,其文学理想更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三、政治认同与形象“比附”:1957 年《沈从文小说选集》
1950 年代中期,国内的文艺政策有所调整,文化环境也相对宽松。 在胡乔木和严文井的支持下,沈从文于1957 年出版了《沈从文小说选集》(下称《小说选集》)。 这是作者在转业到历史博物馆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选集,也是50—70 年代沈氏在内地出版的唯一一部作品选集。 相对于《习作选》来说,20 世纪50 年代沈从文重新校编选集时对篇目调整较大、对选篇内容删改较多。 新的政治体制和文艺要求使沈从文在50 年代的审美理想和认同机制发生转向,编选集使得“转业”之后的沈从文重获了一次检视30 年来的写作史和自我心路历程的契机。 但作者却在这一过程中生出了许多恍惚之感:“现在来看看自己过去的写作,倒像是看别人的作品,或另一世纪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古典’的作品了。 不仅不像是自己写的,也不像是自己能够写成的。 自己这几年也不能欣赏这些作品,哪能再希望在这个新社会还有多少读者来看他?”[18]139“另一世纪的作品”或“古典的作品”等用语与“新社会”并举,一旧一新,既显示了沈从文在新中国文艺评价机制中无法自适的痛苦,也体现了沈氏在时代语境影响下审美追求的变化。 相对于30 年代,此时的沈从文正有意无意地贴近50 年代主流话语,他曾反思道:自己曾经的工作“离于群的发展和要求以外,误人兼误己”[19],我现在应“想办法重新归队。”[20]而新的“自我”仍然是在与文坛的不断对话中生成的:40 年代左翼批评界对沈从文作品的批判愈演愈烈,到了50 年代,这些意见被看成沈从文作品的定论收入种种文学史著中。 作家认为,那些“写近代文学史”的人,并未深入研究自己的作品,就用“三五百字贬得我一文不值”[6]220-221,这让他颇感不平。 因此,《小说选集》的出版就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展览意图,以期给那些并未读过原作,而“习于相信一种混合谎言和诽谤的批评”[18]179的读者一种新的印象。 具体来看,沈从文重塑自我形象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首先,为了尽可能消弭20 世纪40 年代以来弥漫在文坛上的那些负面评价,沈从文在《小说选集》的选汰和删改上颇下了一番功夫。 例如,丁易曾批判沈从文始终站在“资产阶级或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来认识现实,他所创作的人物,与社会游离,没有阶级属性,不过是“作者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观念中的人物”[21]。 对于这一点,沈从文本人也有所反思:诸如《月下小景》《七色魇》等旧作,都“充满了一种观念的注释性,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逃避”[22]。 因此,《神巫之爱》《龙朱》《月下小景》等充满浪漫传奇色彩的作品皆不能选入《小说选集》;再如,在40 年代末郭沫若曾与沈从文发生过龃龉,特别是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称沈从文是“桃红色”作家,称其“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23]。 后来,王瑶在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时引述了这一评价[24]。 沈从文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选集题记》里说:“习作中文字风格比较突出,涉及青年男女恋爱抒情事件,过去一时给读者留下个印象的,怕对现在读者无益有害,大都没有选入。”[25]此外,他还大量删改了旧作中那些露骨的情爱内容,对小说作了一定的“洁化”处理。 例如《贵生》初刊本中有这样一句话:“贵生知道这个故事,男的说起这个故事时,照例还得说是木簰流进妇人的‘孔’里去的。 所以贵生失口说,‘都是女人。’”[26]在1957 年的选集本中沈从文将该句删减为“贵生知道这是个老故事,所以说:‘都是女人。’”[27]391虽然文本“洁化”符合50 年代文化环境的要求,但是后天对文本进行生硬的干预,仍然有导致意义流失的风险。 在《贵生》的初刊本,曾有“四老爷”和“五老爷”拿“八月瓜”开下流玩笑的情节[26],作者将其删除后,后文写贵生因为预备送八月瓜给金凤,“耳听到四爷口中说了那么一句粗话,心里不自在”[27]393就略显突兀。
其次,沈从文在校编选集时大量选入革命题材小说,修改文本时也大力凸显革命者形象,以彰显自身的“进步性”。 沈从文的小说中有大量纪念友人的题材,这类小说一般会在文末注明为纪念某某而作。 例如《习作选》和“沈从文著作集”中收录的《若墨医生》《春》就是为纪念张采真和樊海珊而作。 但是在《小说选集》中,这两篇因有“极端怀疑共产党革命”等语[28]和涉及男女恋情而删去,取而代之的“友人篇”是《生存》等小说,他们大都以参加过革命战争和民族战争的朋友为主角原型。 《生存》原本写的是知识分子的艰难困苦,但是作者在末尾特别补注“1936 年5 月15日于北京为长荣表弟所作;1940 年在洞庭湖抗日战争中牺牲”[29]。 “长荣”即沈从文的表弟聂清,作者曾在《白魇》中提到聂清“为写文章讨经验,随同部队转战各处已六年”,最后在“洞庭湖谷仓争夺战”中牺牲④。《生存》初刊本其实本无此注,沈氏之所以要在《小说选集》中刻意强调,或许是为了宣告自己的经验中不单单只是观念的人和乡村,也有在数十年革命和民族战争中留下的血痕。 此外,从选篇题材来看,直接涉及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小说就有《菜园》《过岭者》《大小阮》《新与旧》四篇,这对本来就不擅长写此类题材的沈从文来说已经十分不易。 在将它们辑入选集的同时,沈氏也对小说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以期更好地符合50 年代文化环境的要求。 例如,沈氏在《过岭者》的附注中说:“当时忌讳删去的用×代替,恐失原意,不再补充”[30]317,但这其实是一种“叙事圈套”,沈从文不但补上了许多此前隐去的内容,还有意识地强化了小说的革命性色彩:初刊本中“至于那个岭头的关隘,一礼拜前却已为××××占领去了”[31],通过文意可以猜出作者所隐去的应是“国民党军”之类的称谓。 而在1957 年的选集本中,作者将其补写为“白军部队”[30]312,意在表现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认同。 甚至于在字词选用上,沈从文也有意识地向主流靠拢。 例如作家曾在旧作中大量使用“特务员”一词,这在1949 年以前本是个中性词,但在新中国语境下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 对此,作者表现得极为谨小慎微:“许多名辞在我情绪中永远引起一种恐怖,如像反动、特务,因为使用界限没有一定。”[32]因此,1957年校改《过岭者》时,作者将其中所有的“特务员”改为“通讯员”。
最后,沈从文通过遴选和删改小说,隐藏了三四十年代的审美追求和道德理想,进而通过人物和题材的“比附”来展现自己对50 年代文学话语的认同。 他将审美和道德意义上的“乡下人”形象转化为革命话语范畴内的农民形象,既强调农民的美好品质,也强化农村题材的阶级冲突。 例如,在《贵生》的初刊本中一群长工在议论“四爷”欺男霸女时自嘲道:“你我的命和黄花姑娘无缘,和银子无缘,就只和酒有点缘分。”[26]1957年选集本改为:“你我是穷人,和什么都无缘。”[27]388这一改动删去了长工们对财色的“歆羡”,纯化了农村底层穷人的形象。 与这种刻意的“美化”不同,作者在《小说选集》中对地主乡绅等压迫者的角色进行了“丑化”,在描写“四爷”“五爷”时增加了“私欲过度的瘦面”“猥亵而又放肆”“像叭儿狗”等讽语;再如,《牛》本是一部不太受作者重视的作品,该文写作时间较早,语言和技巧都略显生涩,此前只在《沈从文甲集》中辑录过,后来又因其题材直接描写农民的哀乐而被收入《小说选集》。 在1957 年选集本中,作者力求消弭牛伯和小牛之“奴役”关系,将“老爷”“主人”之类的字眼全部用更显亲昵的“大爹”来代替,表现出劳动者质朴善良的一面。 与此同时,又强化了混乱的社会环境下军阀对农村的盘剥,在《牛》初刊本中,甲长本要去和牛伯一起去看牛,只不过因为军队过境而被临时召去开会。 在1957 年选集本中,作者加入了需要“办招待筹款”的细节,而后文也补充了甲长的抱怨:“办你妈的个鬼招待,总是招待!”[33]农村所受的苦难与压榨可见一斑。 这种改动和50 年代沈从文的思想变动有关,他试图以阶级叙事的立场来重审农村的社会关系:“眼看到象征封建的极端落后区域用屠杀支持传统,农村的朴素安静变为一片废墟,善良的人民也大半转而成为呆呆木木。”[34]51除了用新的立场来理解农村关系外,他还以同样的视角反观城市,原本批判讽刺城市士绅男女道德堕落的题材也被转述成对“上层社会”和“商业资本”的批判[34]52。 因此,像《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描写都市“绅士”生活腐化堕落的文本也就获得了收入《小说选集》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作者还进一步矮化了这些城市“高等人”的形象,嬉笑怒骂更甚于原作。 例如《绅士的太太》中,将“××公馆”皆改为“废物公馆”[35]。 此时的作者显然是抛弃了30 年代初反对“诙谐”“趣味”,提倡“端重”“严肃”的小说语言观[36],对人物的情感好恶更加鲜明。
总之,20 世纪50 年代的选文活动不但为沈从文驳斥文坛上充盈的负面批评提供了窗口,同时还获得了重新展览自己的契机。 实际上,沈氏的这种努力在批评界也收获了一定的效果,后来唐弢等在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时,便从《小说选集》里获得了左翼批评话语所期待的“思想意义”:“在他的小说中,也有一些描绘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的,偶或出现革命者的形象,如《大小阮》、《过岭者》;或者比较真实地反映贫困者的挣扎,如《生存》;或者揭露反动势力的腐败,如《顾问官》、《失业》,都是他作品中较有思想意义的部分。”[37]
四、重评的契机与文事龃龉:1983 年《沈从文选集》
进入新时期以后,文坛上对沈从文全面否定的倾向有所减弱,但过去的一些判语仍然顽强地遗留在一些批评文章和文学史著中。 1980 年代初,沈从文曾多次向友人提到“九大院校廿多位老师”在合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时,“竟没有一个人认真读过我的作品”,而该书的一些判语也“多照解放以来的‘权威批评家’定的基调去做”[6]73。 实际上,九院校合编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沈从文作品“消极方面”的批评还是主要集中在没有“正确世界观的指导”,未投入“现实斗争的洪流”等方面[38],即50—70 年代主流批评话语所谓的缺少“思想性”。 此外,随着“作家”沈从文的形象重新引起时人关注,一些旧作、旧文事在80 年代特定历史语境中衍生出来一系列新问题。 例如,当时文坛上蔓延着对沈从文旧作的质疑之声,称“30 年代文学重新出发是‘炒冷饭’”,称“沈从文的一部分作品‘是黄色小说’”[39]。 特别是自1983 年下半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兴起后,沈氏30 年代有关表现“人性”的审美追求又被推上风口浪尖。 朱光潜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在作为序言收入《凤凰》(沈从文著,凌宇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时,为了避免争议,不得不将其中赞许沈从文追求“人性”文学理想的部分删除[40]。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沈从文在80年代一直渴望出版一套体例相对完整的选集来对写作史进行重新展览。 然而,该计划先是在香港时代图书公司那里中途夭折,后来的《沈从文文集》则又选得“差些,杂些”[7]396。 直到1983 年的五卷本《沈从文选集》出版后,才算了却沈氏的心愿。 实际上,《沈从文选集》的编选同样不仅是为了展现作者已有的创作成绩,更与80 年代文坛生态息息相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沈从文不满于文艺界延续20 世纪40—50年代的批评话语,希望通过选文活动获得重评的契机。 1979 年,第四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后,标志着“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空前团结”[41],新时期的文艺政策也发生重要调整。 与此同时,港台和海外地区兴起了一股“沈从文热”,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都给了沈从文极高的评价,其中司马长风认为:“沈从文在中国有如十九世纪法国的莫泊桑、或俄国的契诃夫,是短篇小说之王;中长篇小说作品较少,但是仅有的几篇如《边城》、《长河》等全是杰作。”[42]如此盛赞让长期遭受“酷评”的沈从文颇感兴奋,他称赞三册《中国新文学史》“材料不少,且分析比较,笔下极中肯,比夏著各有长处。”[6]47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将在不久之后得到重估。 然而,事与愿违,研究界和批评家们面对沈氏的作品时,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转变。 沈从文曾在书信中与友人提及这一情况:
一切多照解放以来的“权威批评家”定的基调作去,可说实已全面成功。 虽上面近来曾提出过“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文学史,应当把作品成就放在主要位置上,不宜当成‘现代政治’去着笔”,但能烧的已经烧尽了,为省事计,教材照旧作去,还是一种必然合理趋势。[6]73
所谓“能烧的已经烧尽了”指的是1953 年承印“沈从文著作集”的开明书店突然致信沈从文,告诉他“所有作品已过时,已印、待印及纸型”,皆已全部焚毁[1]267。 加上数年来国内政治运动的冲击,沈从文作品散佚极为严重。 到了70 年代末,作家本人为了编选集四处搜罗旧作,竟发现“国内大图书馆亦少有廿本以上”[6]22。 实际上,三十年来大陆只在1957 年重印过一次沈从文的作品,而民国时期刊印的旧本流失也十分严重,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没有充足的参考材料,只能盲人摸象似的为其草草下一个结论。 对这一现状的不满,是新时期沈从文期望重新展览自己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时期出版的各类沈从文选集都在篇幅上对沈氏作品做了极大地扩充。 仅短篇小说来看,《沈从文选集》不但囊括了《习作选》和《小说选集》的所有篇目,还在此基础上新收了31 篇,这无疑能更好地展览沈从文的创作面貌。 从内容来看,《沈从文选集》更加侧重选取湘西边民生活和军人生活题材的小说,这与1957 年的《小说选集》重视反映民众苦难的题材和贴近革命话语的倾向截然不同。 湘西题材的偏向既出自代选者凌宇对沈从文的理解,同时也得到了作者本人的认可。 基于此,在80 年代的一些文学史家、批评家那里,沈从文的乡土形象变得更加清晰:1987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对沈氏的创作便主要聚焦于“湘西题材”,“湘西人”“乡下人”“特殊民情的乡土小说”等都成为沈从文研究中的重要标签[43]。
其次,沈从文在80 年代的选文活动还受到当时文坛上一些新旧文事的影响,其中最著名无疑是“丁沈失和”事件。 1979 年丁玲回到北京后,从拜访者那里收到两册沈从文的《记丁玲》,据称这也是她第一次知道此书的存在。 丁玲在读完该书后非常生气,认为有些叙述是作者虚构编造的。 1980 年,恰逢《诗刊》向丁玲约稿,丁玲便将这种不满发泄在回忆文章《也频与革命》中。 沈从文得见此文后,感到十分愤怒和委屈,认为丁玲此举完全不顾自己“四十年前为之奔走”的情意,“只图自己站稳立场,不妨尽老朋友暂时成一‘垫脚石’,亦可谓聪敏绝顶到家矣。”[6]68虽然他从未公开表达过自己的这种情绪,也从未撰文公开反驳丁玲,却将这种不满渗入了80 年代选文活动中。 1980年,他在复邵华强的信中说:“我正在编选集,得知有此事,便把有关他夫妇二书全取消了。”翻检香港时代图书公司的《从文散文选》、湖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沈从文散文选》和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沈从文选集》都没有收入《记丁玲》《记胡也频》等文章,只有在规模庞大且“选得可能差些,杂些”[6]396的《沈从文文集》中收录了《记胡也频》,但仍然坚持不收《记丁玲》。 此外,在《沈从文选集》已收的一些作品中,沈从文对涉及丁玲等处也作了一定删改。 例如,凌宇曾提到:丁玲的《也频与革命》“很伤沈从文的心,在这以后出版的文集和选集上,一律改用‘××’取代小说中的‘梦珂’与‘璇若’。”[44]凌宇提到的这篇小说是《三个女性》,在1933 年《新社会》半月刊的初刊本中,通过黑凤、仪青和蒲静三人的对话透露了梦珂被捕和璇若南下营救的事。 其中女主人公“黑凤”显然是以张兆和为原型,而其新婚丈夫“璇若”则是沈从文的笔名之一,应暗指沈从文。 另外,《梦珂》是丁玲的成名作,作者在小说中以其代指丁玲,而梦珂被捕的遭遇显然是在影射丁玲被国民党秘密囚禁一事。 后来这篇小说在1943 年收入开明版“沈从文著作集”之一的《黑凤集》时,所涉人物并未做改动。 但在1983 年《三个女性》收入《沈从文选集》第三卷时,“璇若”和“梦珂”等姓名都被沈从文隐去,并以“××”代替[45]。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沈从文否定了50—70 年代主流批评话语对自己的指摘,却并未像50 年代一样通过选文和修改活动来否定“旧我”、重造“新我”。 他在30 年代和50 年代通过选文活动重塑写作史,都有实践新的文艺观的目的。 但80 年代沈从文不但没有迸发第二次创作活力,也没有成为新时期的“归来者”,反而彻底放弃了文学志业,且一再强调自己“不再‘冒充作家’,只随事随时就本业所学为各方面打打杂服服务”[6]378。 因此,作者是以一种整理“陈迹”的心态来对待80 年代选文活动的:“对于这些过时旧作,我并不寄托任何不现实希望,认为即点缀作用也不大,且不多久即将完全失去意义,成为陈迹。”[46]这种心态一方面得之于对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忧惧,沈氏以为“虚名过实,不祥之至,所以总觉得不冒充作家为得计也。”[6]270另一方面,文学志业的丧失还来自沈氏对动荡中旧作毁尽的失望和无奈。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无奈地感叹道:自己的作品在30 年前因为“过时”业已被开明书店“付之一炬”,已出版的各书遗失严重,“世上那有无作品的作家?”[6]268正因为80 年代的沈从文放弃了文学志业,所以同时期的选文活动中并未继续凸显对新的文艺观念的追求,而只是在与文坛上各种声音不断交互的过程中渴求获得重评的契机。
总的来看,1936 年的《从文小说习作选》、1957 年的《沈从文小说选集》和1983 年的《沈从文选集》是沈氏文学活动中比较重要的三部自订选集。 其中,《从文小说习作选》意在回应文坛对自己追求“实利”和缺乏“思想性”的批判,进而重塑写作史,表达对自身审美追求和道德理想的持守;而《沈从文小说选集》在回应文坛上关于自己“站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立场”的批判外,重塑了沈氏关怀底层民众苦难、表现革命历史的“进步”形象,体现了作家对新中国历史话语的认同;《沈从文选集》既适应了作家在80 年代重新出版选集的愿望,也促使作家获得了重评的契机,其生成过程与最终形态更是受到了新时期文坛人事龃龉的影响。 由此可知,沈从文不同时期的选文活动与文坛生态一直处在一种不断交互的状态,后者直接影响了选集的具体形态。 实际上,随着选集的出版由私人活动转变为一项国家文化工作,其性质也逐渐转变成一种兼及文化与政治的身份认同活动。 从这一层面上来看,作家选集所彰显的不仅仅只是个人写作史和文学理想,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学观念的更新。 总之,通过关注现代文学作家选集等方面的问题,不但有利于理清作家文学活动与文坛交互的影响,还有利于研探作家文学史形象的生成过程。
注释:
① 这类研究成果有罗义华和蒋士美的《论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刘奎的《〈从文小说习作选〉:自我经典化与文坛形象重塑》等。
② 例如,张兆和在校对沈从文旧作时,“一遇到有疑问处”,即向沈从文“一一提出”。 参见《从文全集》第26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 页;据凌宇回忆,自己在编选集时,也会将选目寄送给沈从文一一过目。 参见凌宇《风雨十载忘年游——沈从文与我的沈从文研究》,《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纪念版)》,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年版,第369 页。
③ 沈从文曾说《柏子》和《雨后》“似乎皆为一下午写成”。 参见沈从文《题〈雨后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14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年版,第435 页。
④ 结合《白魇》中的内容判断,聂清可能牺牲于1943 年的常德保卫战或1944 年的常衡会战,1957 年版《沈从文小说选集》所注“1940 年牺牲于洞庭湖”应有误。 参见沈从文《白魇》,《时与潮文艺》1944年第3 期,第70-7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