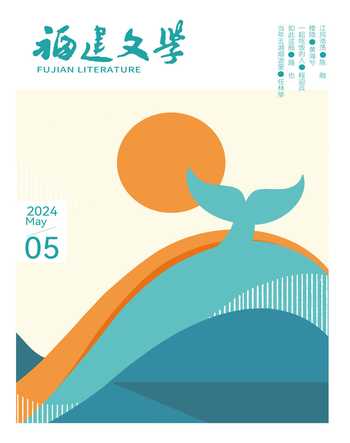当代人的惶惑与释然
徐阿兵
假如有一位知识女性,人到中年,阅历日增,情感累积丰厚而深沉,当下生活状态又较为平稳安逸,她是否愿意向合适的听众讲述自己的见闻和感想?我想,她有可能是愿意的。假如她的身份恰好又是作家,那么,她还很有可能讲得细腻、婉转、动人。中篇小说《江风浩荡》的叙事框架,恰是中年女作家唐念真向理想读者讲述有关自己家族的故事。考虑到小说中的讲述者唐念真与小说家陈融本人曾一路辗转于同样的时空背景,并拥有同样的作家身份,读者若觉得这样的故事具有相當程度的自传性,也无可厚非。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故事的讲述方式和深层意味。
巧合的是,作家陈融的名字与已故著名作家谌容同音,而后者曾在40多年前以小说《人到中年》轰动文坛。将《江风浩荡》与之对读,我们或能更深刻地领会中篇小说这一体裁的独特魅力。好的中篇小说,不仅能以适度的叙事规模使自己区别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还往往表现出独有的叙事语态和审美气质。作家汪曾祺在《短篇小说的本质》中打过一个绝妙的比方:中篇小说的作者是坐在读者的“对面”讲故事。他们不仅对故事该如何“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分即全,一切一切”了然于胸,还能够出之以“流利,委婉,不疾不徐,轻重得当”的语气。唯其如此,对面的听众方有可能入神、颔首、感同身受,以至于“毫不反抗地给出他向我们要的感动”。在《江风浩荡》中,作家唐念真一边回顾过去一边关注当下,巧妙地将追溯父母一辈的心路历程与勾勒儿子陶翰墨的思想动态编织成文。一边是父亲唐家葆作为上海知青插队边疆,与母亲卢玉敏组成小家庭、开始新生活,却也与此同时与上海的父亲和那个家摩擦了几十年,直到唐卢二人自己也告别人世,将那些无法说清道明的情感纠葛和人事是非留给后人。另一边则是更年轻的新一代陶翰墨的成长轨迹,他自主选择求学道路,并与室友安东尼志同道合地萌发探究历史问题的兴趣。如此这般,作为中间代的“我”,唐念真忠实履行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叙事职责:既借助母亲的日记和自己的回忆,挽留上一代人即将消逝的历史和情感;又通过微信聊天,带出下一代人步入生活舞台的精神面貌。小说叙事双线并行,又自然而然地以“我”的见闻感受作为两条线索的结合点、转换器,较为从容地显示了中篇小说应有的生活容量和叙事弹性。再加以诸多上海地标的在场,新疆、山东、安徽等地方元素的介入,从“上山下乡”到新冠疫情等确切年份标记的凸显,叙事时常以高度逼真感使人觉得这不是小说,而竟是生活本身。这种高度逼真感,或许也可以说是中篇小说审美气质的标记之一:它既不像短篇小说那样选取生活的横断面或纵剖面,也不像长篇小说那样企图全景式地摄入生活画面,而是以长短自如的方式贴近生活现场。
一篇小说读下来,读者是否会如作家所愿,“毫不反抗地给出他向我们要的感动”,取决于小说家叙事技艺之精或粗。同时,“感动”之说颇能让人感动,但它在阅读活动中却是一个很难量化的评价指标。或许我们可代之以更直观一些的“感慨”。《江风浩荡》让我感慨的首先是这一点:虽说其中同样出现了“人到中年”的知识女性,但陈融不再像谌容那样尖锐地表现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人到中年》当年之所以引人瞩目,主要原因在于它写出了知识分子的贡献与待遇之间的极大反差,以及陆文婷身为女性对家庭的深重愧疚和无力感。眼下的唐念真不必再陷入陆文婷的困境,她可以凭借自己不错的文字功底,通过公开招考而进入“令人羡慕的”电视台做编辑工作,业余还可以做一个剧作家,才会有一定的闲暇和宽松的心境,用于打捞父辈历史、关注儿子成长。这固然是唐念真的努力和幸运所致,但从中也可窥见时代的变迁和进步。其次,唐念真没有陷入陆文婷式的困境,并不意味着她没有陷入困境。事实上,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中年人,敏感的知识分子,心思细腻的女性,这三者中的任一要素都可能使当事人遭遇某种程度的精神难题。唐念真身上既然三者兼具,就几乎注定了她不可能与困境体验绝缘。小说中的她之所以从头到尾都在讲述,正因为有很多东西令她无法保持沉默:她一方面恼怒于丈夫提及“你家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一方面又以“谁家没有一堆不能揭的老底”而自我安慰;她一方面自省“出于一些不太明朗的心理”而在过去的文字中提到过家族往事,一方面又归咎于父母“他们还在世时就让我入戏太深”;一方面承认“很难说母亲没有把她的爱憎如遗产一样留给我,很难说这些遗产般的爱憎没有遗落在我的文字里”,一方面又试图在接下来的讲述中“保持宝贵的冷静和客观”。从这些矛盾之处可以看出,唐念真事实上长期身处于某种微妙的困境之中。最后,我们的问题是,这种困境有何性质和意味呢?
相比于父母一辈,唐念真的困境是隐性的。父亲唐家葆的困境是生长于上海而无法回到上海那个家,母亲卢玉敏的困境是虽与上海人唐家葆结合却必须与他背后的上海那个家斗争到底。作为新一代人,唐念真自以为能够轻易告别家族历史中的是非恩怨而开始新生活,其实不然。每一个表面全新的当下总是汇聚着过往所累积的诸多能量,一旦被某种适宜的情境激发,当下与过往之间看似可有可无的关联就会被证实和强化。父母相继离世,使她不由自主对他们的历史加以追溯;突如其来的疫情,又促使她向久违的三叔发起问候,并由此与上海的年轻亲戚们建立联系,从而发现了新的自我。小说表面上是唐念真在讲述父母与儿子的事,其实未尝不是在讲述她自己如何打开心结。
每一个敏感的当代人都无法免除对于当下的困惑。时常有人以为,疏离过往、压抑自我才能告别历史;殊不知,决然斩断历史的人将会陷入无根的惶惑,将不知何去何从。唯有亲近过往并主动融入,才能真正找到新的起点。唐念真曾自问:“现在再去回溯写作五六十年前那代人的故事,还有意义吗?”当我们把故事读完,这番讲述的“意义”也已浮现于字里行间:一个隐隐惶惑于如何确认自我的当代人,通过回溯历史而深刻理解了当下,借助怨尤与斗争而学会了宽容与接纳。当小说结尾处唐念真决定重走父亲当年的路时,她的惶惑已全然消除,取而代之的是满腔释然。
唐念真的惶惑与释然之中,想必也叠印着作家本人的惶惑与释然。读者也能从中欣喜地看到,任凭世事变幻无常,文学仍不失为应对精神难题的有效手段。我们若再细读唐念真由惶惑而释然的过程,会发现其中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出现在小说标题中的重要意象“江风”,二是陶翰墨的言行。关于江风,东坡曾视之为大自然的馈赠:“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作家陈融“取”“用”江风的方式是,通过先后数次对相关情境的描写,使主人公逐渐领悟江风之“浩荡”:以浩大之江风而涤荡人的消极体验,以博大的相互理解、包容之心取代狭隘的怨尤、隔膜心理。这是她以个人生命体验从江风中所领受的一份馈赠。倘若没有幸运地找到这个意象,没有使这个意象融入唐念真的心绪流转之中,小说叙事效果恐怕会逊色不少。至于那个有主见而不叛逆的陶翰墨,则更是母亲唐念真的幸运。他虽说在求学道路上充分显示了主见,但并不以反抗父母意愿或遗忘家族历史而张扬个性,反倒是时常促使母亲融入上海亲人群体,更与同代人一起开启了深入历史的寻根之旅。倘若不是他以新一代的新锐之气,轻松就跨越了许多历史阻隔,倘若不是他有意无意地刺激和引导,唐念真能否这么顺畅地走出父母所留下的历史阴影,还真难说。不妨认为,没有陶翰墨也就无法写成这篇小说;即便写成,那也将是意味完全不同的另一篇小说。
责任编辑杨静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