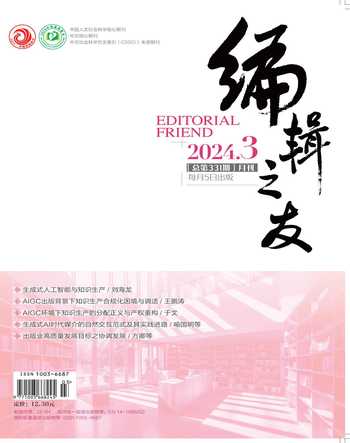场域概念视域下 网络小说IP生产逻辑研究
张煜
【摘要】IP生产是保持IP活力和实现IP价值的基础。网络小说IP作为特殊的文化资源立足于精神价值,具有可循环生产的性质。文章借由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以网络小说IP影视化生产为实例,进行切实性的规律研究,以归纳IP场域内单次生产与循环生产的具体路径。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网络小说IP生产的理想化状态是由一个内容出发,通过单次生产构成循环生产,再通过循环生产达到理想化生产,而明确场域目标性、维持场域平衡性、强调场域合作性则是推动IP理想化生产的可行方向。
【关键词】网络小说IP IP生产逻辑 场域概念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4)3-045-06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4.3.006
从2008年开始,网络小说由原本单一付费阅读的商业模式,逐渐转变为依托知识版权的开发逻辑。伴随着行业整合、资本流入、媒介推动,版权开发已然成为网络小说主要的收益来源,并由此形成了以网络小说为核心的IP产业链。然而,这种开发模式目前仍然处于发展变革的过程中。归结开发实例、厘清生产逻辑是进一步保持IP活力和实现IP价值的重要课题。
每个单独事件只有放在系统中去分析才有意义。[1]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为开展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它的不确定性提供了研究演绎的可能性,正如布尔迪厄所认为的“场域观念的主要价值在于促进和发扬了一种构建(对象)的方式”。[2]不少研究者从具体对象出发进行了切实性的研究和演绎,开拓出另一种显现宏观性特征的研究视角。这种视角回归生产本身,将整个生产场域作为观察对象,将参与者和生产资料看作构建和推动场域生产的元素。约翰·B.汤普森以出版领域为例提出统一价值体系和生成场域。[3]布莱恩·摩尔安强调场域内要素的互动与交流,提出“可供性场域”概念。[4]这些论述中,场域内的争夺、对立、竞争属性减弱,更趋向于积累、参与、合作。场域内参与者的关系与资料彼此捆绑,由此削弱了原概念中的批判性和对抗性,转而突出合作性。场域并非通过某种强制行为来实现构建,而是在参与者达成某种共识,彼此拥有相似的目标与认可的规则时才可能发生。
从产业发展角度出发,这种视角显然更适合当下的研究。因此,本文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参考约翰·B.汤普森、布莱恩·摩尔安等学者对理论的切实性演绎方式,从携带各类资本元素的行动者们所搭建的网络小说IP场域出发,对网络小说IP现状进行总结,对其生产逻辑进行阐释,并基于IP的单次生产与循环生产,探究推动IP理想化生产的路径。
一、跨场域的价值转化:网络小说IP的单次生产
网络小说IP生产以原文本为基础、新文本为延伸,打破原媒介设置的固定场域,通过原内容背后可被预估的商业价值(用户群体和用户黏性)降低新项目开发的风险,具体而言,有两种路径。
1. 价值驱动:“原文本—新文本”的开发路径
网络小说IP的生产路径一般以一个文本内容为源头,该文本在其领域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后再逐渐跨越到其他领域中,从而形成更多类型的延伸文本或体验形态。在“原文本—新文本”的开发路径中,单一文本的形成过程伴随着用户通过追更阅读完成的初次文本消费,及其在消费过程形成的对文本内容和文本价值的认同。这意味着小说完成了文本特定领域市场的初次检验,同时与用户建立了一定的情感联结,使文本、作者、受众形成一个高度交互的状态。伴随文本的生成,IP原生场域内的价值资本开始逐渐累积。对影视这样一个高风险、高投入的产业来说,网络小说IP的优势在于文本在完成基本构建的同时,经过了初级市场用户检验和筛选。而互联网媒介又将检验结果,直观地展现在大众视野之中。这让改编行动者们能看到网络小说IP内容的潜在转化价值,吸引他们加入IP改编生产场域中。其中经典、极具人气的作品凭借自身直观且稳定的原始资本构成,成为电影改编者们的首选。如今,在影视市场看到的网络小说改编作品基本都源自经典和超人气之作,如《少年的你》《琅琊榜》《大江大河》《苍兰诀》等。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行动者希望在网络小说中寻找适合开发的文本内容,经典网文趋向供不应求。因此,市场资本转而投向正在培育中的文本,即改编主体在平台中寻找有人气、有潜力的文本提前购买版权,即时进行改编延伸。这种即时性的改编项目需要对文本进行各方面的预估和判断,虽然开发更具时效性、更为高效,但对价值预估的判断要求更高,改编风险也相对有所增加。
2. 内容孵化:“新文本—新文本”的开发路径
“新文本—新文本”的开发路径是一个内容孵化与产品组合发行策略下的产物,即一种多领域多媒介共同开发、构建一个IP的路径。它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原IP的概念,而是体现为一个复合型内容群的概念,将“购买开发”转变为“创造开发”。然而,这种开发路径的实行有其前提,且在实施過程中存在难度和风险。这种开发路径需要立足于互联网的渠道特性,基于已经成型的各潜在受众群体以及他们的情感需求,围绕一个个既有群体进行内容设计。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即使再小的群体也能找到自己的虚拟社群。互联网吸引力法则把共性变成了一个个数字世界中的超链接,让拥有共性的成员都能互相看到、彼此吸引,在同频共振、同质相吸下逐渐形成群体。由此,这些群体便成为推动内容转变为IP的动力,以及影响IP开发的重要因素。如腾讯集团在推出《勇者大冒险》项目前,洞察目标用户群体的情感需求,尝试创作出一个无割裂、相统一的IP世界,从而打通各个用户群体。与文本先行的路径不同,这种路径需要针对特定场域内的受众进行意见的收集和处理,并且反馈到各领域的创作者中,进而左右后续创作的走向。就如程武等所说,IP培育与粉丝经济紧密相连,本质上就看用户和粉丝的意见反映到具体创作中的程度。[5]这种路径显然已经把用户统统纳入项目的创作团队中,以沉浸式的互动和参与加深其对于文本的情感联结。
这种开发路径要想可行,需要依附于相对完整的全产业链体系,形成IP全产业链一体化的生产方式,即打通产业链上各门类的关联,获得商业利益的最大化。[6]一方面,同步开发路径对各个媒介文本的统一性有着更高要求。IP开发体系中的文本互相辅助、互相延伸,要求不同的改编主体彼此联动、共同协商,以构建一个完整的系统。《勇者大冒险》在IP构建的过程中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将小说作者、游戏策划人、视频制作者以及漫画创作人等各领域文本的主创团队,组织成一个IP文本的创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定期进行文本构建的相关讨论,决定故事的走向、人物的设定以及情节的设置等,以此来保证各领域之间的文本保持联动。另一方面,这样的联动方式需要在实施前就组建一个有一定体量的开发团队,如《勇者大冒险》的开发公司腾讯集团自身拥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生产链系统。同一个团队范围内的同步开发显然更便于项目的策划和运行。就目前来看,各大互联网公司纷纷创立各自的IP开发体系,设计IP孵化计划,无论是上游网文平台还是下游影视开发,都呈现出产业链整合的趋势,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因此,这种路径可能成为各大平台占据IP市场,创建旗下IP品牌的普遍开发策略。
二、多场域的价值联动:网络小说IP的循环生产
网络小说IP的循环生产立足于场域集合概念,在多次生产活动中形成场域的有机联动,完成原文本的价值增殖,因此显得更为复杂,其中可能包括不同媒介的多次生产、同一媒介的多次生产以及超文本的循环生产。不同媒介的多次生产指同一个网络小说IP在不同媒介中实现生产;同一媒介的多次生产指同一个网络小说IP在同一种媒介中被多次生产;超文本的循环生产,指的是IP效力延伸至文本以外,超脱IP文本本体所构成的循环生产路径。就目前来看,网络小说IP的循环生产涉及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品牌化生产路径、多文本借势路径以及作者再生产路径。
1. 价值共享:品牌化的IP生产
对项目进行单次开发也许可以依靠项目本身的价值,但循环模式下的开发则需要一定的品牌化构建。品牌是用于识别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者或消费者名称、术语、标记、符号、设计,或者上述因素的组合。[7](234)品牌所拥有的意义远远超过关联的产品本身,是推动产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尹鸿教授认为,“IP应该不只是生产一个IP产品,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个品牌,是可延伸产品”。[8]因此,IP的品牌化构建要基于原文本以及延伸文本,在用户群体中塑造自身的识别系统以及独特的符号,最终建立与受众之间持续性的品牌关系。就如同“漫威模式”,IP的品牌化生产路径可以推动IP价值开发最大化,让IP生产实现可循环。
(1)品牌化的构成主体与生产环境,即构建一个统一的生产环境,通过各行动者加入IP生产场域,打通IP开发的各个环节和渠道。如此一来,行动者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自身携带资本投入IP生产当中,以增加IP的资本价值,而且需要紧紧围绕IP的文本特點和固有价值,设置准入标准,以选择合适、对位的行动者共同构建良好的生产环境。
此外,不同于产业上下游阻隔、粗放型的开发模式,品牌化的开发是一个可循环、可延伸的过程,从品牌开发的构成来看,最理想的状态是不同的改编团队能够通过认真研究作品的特点和用户心理做出预案,形成高度统一,在IP的各个环节里,达到一个最大的阀区,[9]让文本能够在一个统一且和谐的环境中跨界。阅文集团推出的“IP共营合伙人制”,就是为了打造一个品牌化的构建主体和生产环境。该制度以IP为核心,连接项目开发的上下游产业,形成完整统一的产业链,从而发挥磁铁效应,让作者、上游平台、粉丝、下游开发方都能够获得最优的项目结果。阅文集团副总裁罗立表示,合伙人模式可以有很多种合作形式,未来或将与下游厂商针对高端IP成立IP运营公司,甚至一起构建IP的世界观。[10]
(2)品牌化故事世界的构建,即原文本和新文本承载于不同的媒介,提供有差异的叙事文本,彼此形成文本故事的扩展以及不同文本间的互文关系,共同构建出同一个故事世界。亨利·詹金斯曾以《黑客帝国》现象为例,详细阐述了跨媒介叙事的概念。其指出跨媒介叙事是把多种文本整合到一起,创造出宏大的叙事规模,通过一个媒介作为故事的开头,而后通过其他媒介内容进行进一步详述。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建立在上一步基础之上,同时又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且任何一个产品都是进入作为整体的产品系列的一个切入点。[11]在品牌化的IP生产和再生产中,无论是不同媒介的文本改编,还是同一媒介的多次改编,若想构建一个完整的品牌化IP宇宙,都需要考虑各个文本之间的联动性。
这种联动性不仅存在于不同的文本之间,还存在于IP受众中。其一,受众本身在故事世界的构建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叙事学家戴维·赫尔曼提出了“故事世界”的概念,用以界定被叙事或明或暗地激起的世界,无论是书面形式的叙事,还是电影、绘图小说、手语、日常对话,甚至是还没有成为具体艺术的故事……“故事世界”是重新讲述的事件和情景的心理模型。[12]该概念强调受众在接受对叙事文本的外部叙述后,在内心进行故事内容的构建和重现。其二,受众作为品牌的感知主体和价值来源,需要考虑其品牌认知。品牌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或者一个象征,还存在于消费者的头脑中,表达了消费者对某种产品及其性能的认知和感受。[7](89)也就是说,受众判断文本是否属于某一品牌序列的标准来自他们大脑中的感知,而在统一故事世界中,彼此联动的文本是构建受众对品牌认知的关键。
(3)品牌化新文本呈现,就影视产业而言即经由同一媒介内的多次生产所构建的品牌化文本概念。目前的改编影片,主要包含单部、重拍以及系列(多部)三种类型,其中系列是品牌化最为明显的一种。系列作品立足于文本的IP效应,通过IP文本的多次改编,构建一个同一媒介内完整的故事世界,一个庞大的IP宇宙,在生产和消费循环中,形成稳定、庞大的受众群体以及系统的制作模式。借由已受市场检验的文本和制作模式完成项目的推进,无疑是最为简单且低风险的做法。系列电影的创作者通常会选择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根据原文本的原始积累进行持续挖掘和开发,表现为根据同一篇小说或小说集进行多次改编,或者借由原文本的部分背景、角色进行改编创作。如根据《鬼吹灯》改编的《龙岭迷窟》《云南虫谷》《昆仑神宫》三部电影均由同一名导演进行指导,试图构建一个统一且连贯的《鬼吹灯》故事世界。第二种则回归原文本,在此基础上进行续写。通过人物小传、故事前传、后传等文本的创作,形成一个源源不断的文本来源,从而再进行文本的改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南派三叔的代表作《盗墓笔记》。南派三叔创作了《老九门》《沙海》等系列相关小说,使《盗墓笔记》的文本世界不断扩充,并策划创作了相关电影。
2. 同源互动:多文本的借势活动
多文本借势路径以多次IP生产的同源性为基础,即使用同一个IP。其不同于有规划、有目的性的品牌化生产逻辑,而是立足于既有的线性IP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对新一次生产的影响推进再生产活动。因而,改编行为者需将这种脱离计划的多文本借势纳入前期分析和调研环节,选择适宜的营销策略,以更好达成借势目的。
在此过程中,改编行为者需要正视网络小说IP改编的同源性。在当前以单一线性开发为主体的情况下,多次生产的转化行动者、转化媒介、转化体系等要素,或许相互间存在着一定差异,但同一IP文本却将它们绑定在同一个文本空间,这是客观存在的同源性所形成的客观事实。网络小说IP的生产是借势于IP原始价值积累的转化活动,IP文本的多次生产所面对的转化价值不仅仅要基于原文本,而且应基于原文本以及既有新文本共同累积的当下价值。此外,同一文本的多次改编,在时间上、媒介上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新一轮的IP生产环节中,改编行为者需要在认识到IP原文本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将既有的改编作品也纳入改编考量之中。
此外,改编行为者要正视IP多文本改编的两面性。首先,原文本会给新一次的生产带来借势的可能。新文本的生产存在时间差异,为其提供了借势的可能性。《步步惊心》《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诛仙》等热门网络小说IP,均是先推出电视剧版,而后才推出电影版。随着电视剧版的热播,收获了一批新的受众,为原文本附加了一定的价值资本,连带着增加了电影版的关注度。其次,联动在带来关注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文本间的比较。IP的生产活动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文本,还有新的受众,是对整个IP空间的重新构建。如果说首次改编的文本面临的比较对象是单一的原文本,那么新一次的生产面临的比较对象则是多样的。这种比较行为将会对新一次生产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同一媒介的新文本而言,这是同一个文本空间带来的必然结果。
3. 超文本生产:作者IP的生产延伸
作者再生产路径是超文本循环生产中最具代表性的路径。作者先借助网络小说完成自身价值资本的积累,而后转换主体实现IP的超文本再生产。此时IP再生产的核心虽然从原先的文本转为作者,但生产活动持续受到原小说IP价值的影响。作者、读者以及小说文本依托互联网共同构成了一个虚拟的群组。群组成员中作者是小说文本构建的主体,也是文本的实际拥有者。文本的创作、生成以及转化,伴随着文本作者个人价值资本的生成和累积,共同联结着作者个人的特殊象征性功效。由此,作者便有可能在网络小说IP生产的路径中,构建出一个围绕自身的特殊再生产逻辑,贯穿到整个IP的生成和转化当中。
(1)内容创作阶段,确立作者身份,价值资本逐渐生成。不同于传统文本的创作者拥有明确的作家身份,网络文本的创作者拥有着特殊的“吸粉”优势,他们从大众中诞生,与受众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纵览网文创作者,从早期的安妮宝贝、宁财神、邢育森,到后来的慕容雪村、南派三叔、辛夷坞、天下霸唱、唐家三少,再到如今的我会修空调、忘语、我爱西红柿,都不是专业作家。网络中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文本的创作者,[13]消解了作家頭顶上神圣的光环,网文创作者创作的内容也随着创作者身份的变化而趋向大众。同时,受影视和ACG(动画、漫画、游戏)文化的影响,网文创作者的作品更容易受年轻受众的喜爱。互联网提供了一个让作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联系和沟通的渠道。在网络小说创作、连载的阶段,作者作为核心发起人,以文本为纽带吸引并牵连起所有读者,从而构建起一个情感共同体。在这个彼此交互的过程中,作者树立起文本群组中的权威身份,拥有受到认可的对于小说文本的特殊阐释权。
(2)IP内容生成阶段,文本带动作者个人价值资本的累积。文本内容在小说群组收获了一定影响力后,普通文本转变为IP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的个人风格被用户认可,拥有了一批粉丝受众。作者的身份逐渐发生转变,开始构建群组中的个人品牌,孕育作者IP,在特定领域产生名人效应。此时,作品反而成为孕育作者IP的要素。伴随着新文本的加入以及文本延伸产品的不断推出,作者的个人资本不断增加、个人品牌不断巩固,从而扩大了整个IP所覆盖的版图和内在价值。以南派三叔为例,其凭借《盗墓笔记》系列小说,收获了一批固定书迷,微博粉丝早已突破千万。2014年,南派三叔成立了南派影视投资管理公司(2016年更名为“南派泛娱有限公司”),围绕个人效应,积极推进IP生态产业链的开发和运营。其不仅围绕《盗墓笔记》系列小说,进行版权的自营、深度开发,扩展经典作品,如在起点中文网恢复更新《盗墓笔记》小说,担任编剧参与制作电影版《盗墓笔记》,投资制作系列话剧等;还与各大平台和公司合作,开发新的IP项目,如与腾讯集团合作连载《勇者大冒险之黄泉手机》小说,与湖南卫视合作,担任《寻找爱的冒险》监制,参与场景和情节的设计等。此时的作者在自身文化产品的积累下,形成了个人化的IP符号,并开始IP内容的转变和再生产。
(3)文本转化阶段,价值资本伴随权力效果推动身份转变。从文本转化的角度来看,在文本进行跨媒介转化的过程中,往往会考虑邀请作者加入创作。作者作为文本的创作主体,对文本有足够的了解,同时在文本创作过程中,与读者群体有着大量的互动和交流,充分了解读者的喜好。此外,更重要的是作者个人资本所赋予其的特殊权利。作者作为虚拟群组中的核心角色,早在文本创建的过程中,就已经完成了作者身份的构建以及个人资本的累积,在群组中具备了一定的受群组成员认可的文本阐释权,可大大增加改编文本对原文本拆解和重组的空间,同时降低IP项目的开发风险。正因如此,《悟空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傲娇与偏见》《如懿传》《沉默的真相》《第三种爱情》等改编项目均选择邀请作者加入文本创作过程。在电影《摆渡人》的制作中,作者张嘉佳甚至直接以导演的身份参与文本的转化。但作者与读者一样具有双重性,文本作家与影视编剧、导演毕竟有所不同,就彼此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具体案例中,还需审慎思考。
三、场域集的价值可供性:网络小说IP的理想化生产
IP生产的目的是实现自身的增殖,其理想化的状态可以被理解为由一个内容出发,通过单次生产构成循环生产,再通过循环生产达到产业可持续性,在此生产模式下构成一个以IP文本为核心的IP生产场域。IP文本实现横纵向、多媒介的生产活动,并在场域内的循环生产中始终保持着自身的增殖性,使得原文本的IP价值得到最大化的释放和源源不断的扩展,从而形成场域集的价值可供性。本文通过对场域概念的阐释,代入现有的生产逻辑,尝试总结出推动网络小说IP理想化生产的可行路径。
1. 明确IP场域的目标性
IP生产活动的目标是推动整个IP的不断增殖,实现IP的循环生产。增殖本身是行动者和IP自身的追求。然而,一批网络小说IP改编实践的成功,让业界关注到网络小说IP所具备的巨大优势以及丰沛价值,大批市场资本涌入改编市场,投入改编项目的开发中。改编者把这股浪潮视为“闪现的良机”,将变现思路贯穿整个改编过程致使其缺乏系统、循环的生产逻辑。如今的IP生产大多仅仅局限在单次生产之中,通过消费IP的即时价值,来实现自身资本的变现回报,这显然将IP开发目标狭隘化,并没有立足一个宏观视角。需要强调的是,网络小说IP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具有可循环的生产性质,盲目追求单次获益只会造成IP价值的大大贬值。
2. 维持IP场域的平衡性
IP生产涉及场域的跨越,使IP既无法完全摆脱原场域的影响,又要适应新场域的生产逻辑。场域转化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借势来完成资本的增殖,而场域间的差异性却构成了彼此的对峙。IP生产行为所牵连的是复杂场域的构成,每个场域并非由任意行为所产生,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14]每一个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则,这种差异性是自然存在的,行为者能做的就是去尽量平衡。具体来看,改编行为将IP文本连带其场域内的相关资本一同由原来的场域转化至新的场域,此过程中所要面对的差异性,一方面,来自以媒介构成的元场域转化,譬如,网络小说场域到电影场域,与之对应的是创作规律、审美体系、文本载体、呈现方式、受众对象等构成的差异;另一方面,回归至某一项目特定子场域转化,所面对的是资本的结构、位置、效力、总量以及场域内的生产模式、目的、逻辑等方面的差异。
3. 强调IP场域的合作性
合作性是场域概念的一种切实性研究视角。英国社会学家约翰·B.汤普森所创作的《文化商人:21世纪的出版业》一书中,就以合作视角对场域进行了演绎。书中以出版行业为对象,构建了一个出版的领域逻辑。这个生产领域由不同的动力要素组成,各行动者都拥有不同的价值资本,通过彼此合作的方式进行价值的累积。布莱恩·摩尔安在布尔迪厄场域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可供性场域”,[4]强调场域内要素彼此的互动和交流,即场域内包括各种不同的可供性要素,各要素互相连接构成一个集合网络,一同推动场域内的文化生产。同一文本参与多个场域内的文化生产,由此构成一个特定的场域集合。无论是IP生产的目的、IP循环生产的同源性影响,还是实现IP的理想化生产,都无法脱离场域内个体、资本,以及各个场域间的彼此联系和合作。推动IP的循环生产并非单一人群、单一资本、单一媒介所能实现的,就如同学者向勇、白晓晴所提出的场域共振的概念,生产场域内的可供性要素互相结合形成一种复合作用力,达成一种处于平衡状态的可供性环路,即实现场域共振,最终推动IP价值达到1+1>2的效果。[15]
结语
网络小说IP是网络时代崭新的文本来源。经过二十余年的行业探索,网络小说逐渐形成以版权开发为主的商业模式,然而,这种开发模式仍然处于探索和变革的阶段。基于现实实践而言,文本先行与同步开发路径,已然显现出网络小说较为成熟的单次开发逻辑,行业内也确实在探索IP循环开发的可行路径,但市场资本裹带着简单的变现思维,始终左右着网络小说的IP生产。场域概念给予当下切实性的路径指引。从价值角度来看,IP生产的目的是实现自身的增殖,IP生产的理想化状态是以IP在场域内的循环生产来保持IP的增殖性。这使得原有内容的IP价值得到释放和扩展,如何推动网络小说IP的理想化生产将是行业内外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J.达德利·安德鲁. 经典电影理论导论[M]. 李伟峰,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27.
[2]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51.
[3] 约翰·B.汤普森. 文化商人:21世纪的出版业[M]. 张志强,何平,姚小菲,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9.
[4] Brian Moeran.The Business of Creativity: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rth[M]. New York: Left Coast Press, 2013:50.
[5] 程武,李清. IP热潮的背后与泛娱乐思维下的未来电影[J]. 当代电影,2015(9):17-22.
[6] 许昳婷. 生产式的参与和抵抗:创意时代的中国IP文化[J]. 编辑之友,2021(7):52-57.
[7] 菲利普·科特勒,加里·阿姆斯特朗. 市场营销:原理与实践[M]. 楼尊,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8] 尹鸿,王旭东,陈洪伟,等. IP转换兴起的原因、现状及未来
发展趋势[J]. 当代电影,2015(9):22-29.
[9] 马季. IP的实质:网络文学知识产权漫议[J]. 文艺爭鸣,2016(11):66-73.
[10] 程贺. 阅文集团推IP共营合伙人制 欲做中国“漫威”[EB/OL].
[2016-06-08].https://tech.ifeng.com/a/20160608/41620464_0.shtml.
[11] 亨利·詹金斯. 融合文化:新媒體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 杜永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55-157.
[12] 尚必武. 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戴维·赫尔曼访谈录[J]. 外国文学,2009(5):97-105,128.
[13] 欧阳友权. 网络文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
[14] Paul Michael Garrett. 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M]. 黄锐,译.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149.
[15] 向勇,白晓晴. 场域共振:网络文学IP价值的跨界开发策略[J]. 现代传播,2016(8):110-114.
The Logic of IP Production in Internet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Concept
ZHANG Yu(School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Media,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production is the foundation for maintai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vitality and realizing IP value. Internet novel IP, as a special cultural resource, is based on psychological value and has a recyclable production nature. This article borrows Pierre Bourdieu's field theory and takes the IP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of online novels as an example to conduct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laws. This is done in order to summarize the specific paths of single production and circular production within the IP field. Simultaneously, we propose that the idealized state of IP production of online novels starts from a single content, forming circular production through single production, and then achieves idealized production through circular production. Clarifying field objectives, maintaining its balance, and emphasizing field cooperation are the practical directions for promoting the idealized production of IP.
Key words: Internet novel IP; IP production logic; field conce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