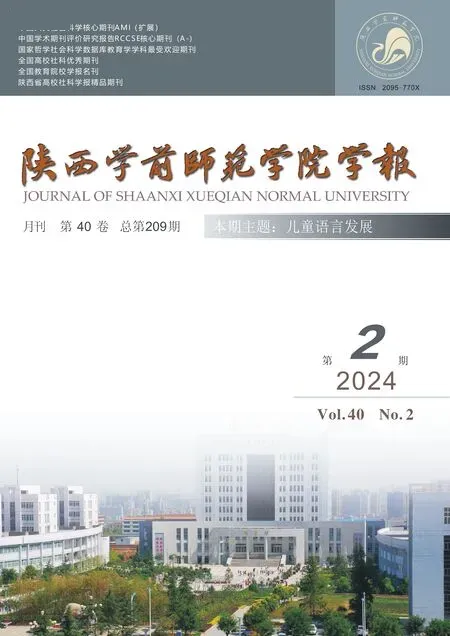何以成人:“开笔礼”仪式铸魂育人的理论逻辑、历史溯源与当代价值
王喜斌
(青海民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青海西宁 810000)
回顾教育历史,不难发现在古代中国和希腊等许多地区,儿童开始接受正式教育或者正规教育的起始时间是一致的,基本开始于6-7 岁。对于儿童而言,接受正式教育或正规教育不仅表明教育的重心从身体养护转变到了学习相对复杂的知识技能,还意味着生长和生活环境发生了从幼稚园到小学、从小学到社会的转变,同样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社会角色、身份以及社会关系的开始。从孔子时代流传至今的开笔礼(俗称“破蒙”)发生于儿童脱离家庭,进入正式教育机构开始接受正式教育之际,是儿童在教育场域中面临的第一次人生礼遇。
仪式指举行典礼的形式。现代“开笔礼”仪式由古代蒙养教育传统发展而来,作为一种守正与创新并存的教育实践活动,它既着眼于培育根植传统的现代儿童,又指向儿童个体与未来生活、社会以及文化的相互建构关系。问题的关键是,“开笔礼”仪式何以能发挥这种铸魂育人的教育作用,进而促进儿童走向“成人”。对这一问题学界尚未进行理论探索。鉴于此,本文试图以“理论逻辑—历史溯源—当代价值”的思路阐释“开笔礼”仪式的铸魂育人逻辑。作为一种分析框架,这一分析脉络不仅多角度注解了“开笔礼”仪式的本质内涵,也为其建构了多层次的教育、社会以及文化意蕴,适宜于学校文化育人体系的建设。
一、“开笔礼”仪式的理论逻辑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个体生命的转化与进阶依托于过渡仪式的“阈限”思维而实现。“阈限”概念来自拉丁文“极限(limen)”,意指所有间隙性的或者模棱两可的状态,也有“门槛”之意思,仪式的受礼者既不在“门槛”之内,也不在“门槛”之外,而是处于一种特征不清晰的非此非彼状态之中。“阈限”概念的建立使得过渡仪式理论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模型”化的分析规则,它将人的生命阶段的物理性质社会化,将人的生长与发展引入一种“分离(前阈限阶段)—过渡(阈限阶段)—组合(后阈限阶段)”,即“结构—反结构—结构”的进程之中。具有生命过渡意涵的“开笔礼”仪式并不仅仅追求当下的仪式效果,更是追寻儿童生长与发展的长久意义,因此无法摆脱对这一理论逻辑的依附,只是为了适应现代性的教育生态与育人要求而有所变化和调整,呈现出了“告别—分离”“交融—过渡”与“接纳—调整”阈限特征。
(一)前阈限阶段:告别与分离
过渡仪式生命转化与进阶的前阈限阶段以“分离”为前提。在特纳的笔下,恩丹布人举行的成年过渡式中,受礼者要与过去的生活环境以及过去的自己相分离。“开笔礼”仪式内涵过渡仪式“告别”与“分离”的意蕴,儿童旧有的角色、身份、地位以及思想认知在仪式开始的那一时刻被“抛弃”,准备迎接一种全新生命状态的到来。
1.“开笔礼”仪式是儿童向幼儿告别的一种讯号表达
个体从幼稚到成熟是一种时间性的过程,而这种过程与儿童的年龄相关。在教育学、心理学的范畴下,个体从6—7岁起开始从幼儿的生命状态中脱离出来而进入到儿童期,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角色与身份—小学生。范热内普认为人的社会生命不是当一个人到达了某一年龄阶段就会自然获得与进步,而是需要过渡仪式才能够被赋予,“开笔礼”仪式正是对这一生命转换的“合法性”佐证与说明。在仪式进行前,儿童被成人以“说教”的方式不断告知即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获得什么样的身份”“可以干什么样的事情”,如在仪式的致辞环节中,一位校长这样说道:“举行开笔礼,就是让你们从今天开始学习做正直的人、高尚的人、有修养的人、有文化的人、能掌握现代技术的人(BYX—20210916)”。伴随着这样的话语表达,儿童们开始产生了面对全新生活的心理预设,以更加“成熟”的心态预期着未来生活中的种种可能性:“游戏”生活的逐步松懈,对父母、老师的依赖程度逐步减弱,开始独立学习更为复杂的知识和能力,同样也意味着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与使命。
2.“开笔礼”仪式向儿童提供了一种与“过去”分离的实践路径
仪式作为“社会文本”本身就包含着社会实践的意思,因此可以说实践构成了仪式的基础特性。在一些学者眼里,仪式实践活动的情境与策略是相互的,换句话说,人们之所以会在一个特定的情境里发生和进行某一项活动,原因在于他们策略性地根据自己的目标和目的进行选择后的行动和行为[1]22。在此意义上,“开笔礼”仪式是为了实现儿童向“过去”分离,进而促进他们“向上”“向前”发展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性实践”。一方面,作为自然之人,个体的生命成长是一个线性的生长过程,儿童在不自觉中参与到各种成长事项之中,“主动”与自己的“过去”分离;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之人,学校的积累性教育传统,家长的期许与意愿将儿童置于一种“不得不”的境况之下,迫使他们“被动”地向“过去”分离。总而言之,这种“策略性实践”指向了儿童生长与发展的根木目的,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它都将儿童引入生命的流程之中,并以各种实践策略告诉他们:与自己的“过去”分离是必然的生命经历,是不可抗拒的生命冲动。
(二)阈限阶段:交融与过渡
过渡仪式生命转换与进阶的阈限阶段是指受礼者在“告别”与“分离”之后,从不同的生命状态发展成为一个持续、稳固的生命存在。在这一过程中,仪式中不同角色、身份与地位的参与者,以及仪式过程中的“世俗与神圣、社会与个体”实现了“在场性”交融,而交融的根本目的在于帮助受礼者实现顺利、平稳地过渡。
1.儿童多重身份的交融
在特纳笔下,青春期仪式上的受礼者“被装扮成为怪兽的样子,身上披上一块布条,有的甚至赤身裸体,以此来表现作为阈限的存在。他们没有地位、没有财产、没有标识,没有世俗衣物(这些衣物体现着级别或者身份),在亲属体系中也没有他们的位置——简言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把他们与其他的初次受礼者或初次参与者区分开来。”[2]95-96“开笔礼”仪式中的儿童却没有这样的遭遇。在仪式阈限阶段,他们仍然是爸爸妈妈心中的好“宝宝”、老师眼中祖国的小“花朵”,学校、年级、班级是他们明确的组织标识,统一的校服让他们和高年级的同学看起来并无差别。从仪式教育的实际功效来看,这样的阈限状态比特纳笔下的青春礼仪式力量稍逊,因为一无所有的人性白板才是接受教育的最佳状态。但从人文角度来讲,这样阈限状态却更为温暖、充满着极度的人性关怀和现代性特色,为儿童进入小学生活、开启正式学习之旅提供了一种“阈限期”的缓冲与适应,让他们在一种较为平缓的节奏中实现角色与身份的转换,开启全新的生命状态。
2.参与者多重角色的交融
领导、班主任、其他教师、高年级同学以及家长是“开笔礼”仪式常见的参与者,他们虽然角色各异,但所发挥的仪式功能是一致的,即形成仪式的阈限氛围,对已经处在阈限状态的儿童产生影响。从现实表现来看,多种角色杂糅的状态使儿童对各种参与者所起到的仪式功能及功能背后的意义混沌不明:分不清谁才是真正的施礼者、谁才是仪式进程的主导者,如在访谈中一位儿童这样说道:“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们会有这么多人,台上的好多‘老师’我都不认识,不认识他们,为什么还要给我们点红点呢?(YW—HMF—20210916)”。实际上,这种多重角色交融的仪式过程能使儿童在与他人的仪式性互动中从个人主体走向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个人主体到类主体的一个过渡阶段。相对于个人主体性,主体间性反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关性与一致性,是主体在公共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品格特质。”[3]钱穆指出:“人必从我与他之两心之相互感知中认有我。”[4]75万俊人强调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达成普遍有效的伦理原则。”[5]561正因为从个人主体走向了主体间性,儿童才走出了各自独立的生活,走向了与他人交往和共在的公共生活,进而树立团结、合作、尊重、平等的公共立场与品质。
3.仪式符号的相互交融
“开笔礼”仪式中不仅有孔子圣象、笔墨纸砚、汉服、小鼓、仿古桌椅、朱砂等“传统性”道具,同时也有电子屏幕、彩色旗帜、音乐、书、智慧笔等“现代性”元素。特纳认为仪式的符号象征包含两个清晰可辨的意义极,一是“感觉极”,二是“理念极”,前者唤起人最底层的、自然的欲望和感受,而后者透过秩序与价值引导或控制人,在群体或(社会给予)的分类中安身立命[6]。“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符号状态不仅渲染了浓郁的仪式氛围,增强仪式体验感。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集中展现“开笔礼”仪式所蕴涵的蒙养文化知识、价值体系与行为准则,承载着儿童身心整全的价值取向,意味着学校、家庭和社会予以期望的向着儿童未来可能生活世界所敞开的教育信念。遵循符号象征主义阐释策略,能够让儿童在感物入心、物感物觉中实现观念与行动的相互激荡、相互符合,从而激发他们的文化自觉与生命自觉。
(三)后阈限阶段:接纳与调整
过渡仪式的“告别—分离”与“交融—过渡”最终指向未来,面向一种全新的生命接纳与调整,这是所有过渡仪式的根本逻辑旨归。
1.“开笔礼”仪式是对儿童“小学生”身份的接纳
“小学生”身份的获得不是简单的符号赋予,还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行动与规范去坐实。第一,在学习知识方面,儿童面临着由随意游戏学习方式向有目的、有计划的学习活动转变。学会学习,这是他们身份转变的首要条件。第二,在行为习惯方面,从幼儿园到小学,是一种个体和松散的群体活动向有规律、有组织的集体活动的转变,此时,严格的校级班规、规范的课程制度、繁复的作息时间、差序有别的角色身份都需要儿童去践行和遵守。第三,在思想道德方面,蒙台梭利认为6-12 岁,儿童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及他人行为的善恶[7]151,文明礼貌、诚信友善、宽和待人、孝亲敬长等道德规范意识开始形成。从外在形式来看,“开笔礼”仪式是儿童脱离幼儿生活,成为一名“小学生”的活动媒介,但从其内在旨归来看,其所承载的修身、正心、匡行等文化调适功能在于帮助儿童“做成”一名真正的“小学生”。
2.“开笔礼”仪式是对儿童“同一性混乱”的调整
儿童期是幼儿走向青少年的过渡时期,由于身心急剧发展和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儿童在作息时间、组织特征、身份结构等生活规范方面完全不同于幼儿阶段,学习、生活中会遇到一些观念上的困惑和认知冲突,因此自我同一性混乱的问题在童年期也是常见的问题。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在一定的生命阶段出现认知冲突,产生“同一性混乱”,这是个体正常的发展过程。基于教育学、文化学的分析原则,“开笔礼”仪式的“接纳性”正是对儿童“同一性混乱”的诊断与调整,使他们逐渐产生一致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从这一层面来看,“开笔礼”仪式的“接纳”性最终是为了实现儿童被社会所“接纳”,是帮助儿童从“个性化自我”向“社会化自我”的顺利成长与过渡,而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儿童成长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理想。
3.在教育的逻辑系统中,“开笔礼”仪式不必然单独表现为“分离”“过渡”与“接纳”,而是至少表现为其中两者之间的连续性过程
正如阿兰·巴迪欧所说:“你有能力放弃你已经建造起来的东西,因为有其他东西召唤着你,去寻找真正的生活。”[8]42质言之,“分离”“过渡”与“接纳”三者之间并没有矛盾,不仅相互赋予意义,而且是儿童连续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作为整体构成了儿童童年生活中较为重大的社会以及文化事件,以温润的文化力量赋予了儿童肯定自我、勇敢向前的生命自觉与自信,让他们在“分离”时能够肯定,并有勇气告别过去的自己;在“过渡”时能够正视当下的自己,直面生活中真实的自我;在“被接纳”时能相信未来的自己,朝向更加自觉、更加人性的光明未来。正如仪式过程中主持人的串词所说:“人字一撇一捺,一撇是长处,一捺是短处,它告诉我们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凭借着长处和短处组成的平衡,不断取长补短,完善自我(BYX—202109)”。
二、“开笔礼”仪式的历史溯源
《礼记·礼器》有云:“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9]293礼仪本身表现了人的本性回归,也表现了对历史和传统的遵循。“开笔礼”仪式源于历史蒙养传统而存在,既守正古典传统,又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探寻儿童走向成人的行动线索。
(一)蒙养传统中的“礼教”知识是“开笔礼”仪式的经验原型
《礼记·冠义》记载:“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辨讼,非礼不决……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仪也。”[10]738《诗经·都风·相鼠》中说:“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11]26简良如认为“无仪”只能解释为“无所匹配”[12]320,也即是说,“无仪”将与“人之为人”不相匹配。“成人”是教育的根本旨归,将“开笔礼”这一传统文化现象引入教育场,根本目的也在于此。
历史蒙养传统中的“礼教”知识在“开笔礼”仪式中成了一种永不过时的“蓝本”,是“开笔礼”仪式的“经验原型”。“原型”不仅仅指一个事物的开端,一种潜在的规范,“它是一种活的东西,要遗传、继承、发扬、变型”[13]144。在“正衣冠”环节中,主持人说道:“古人云:大地为人,先要身体端正,自纶巾、衣服鞋袜皆需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所谓先正衣冠,后明事理。礼请学童肃立,跟随‘礼协’所展示的正确姿势正衣冠(BYX—202109)”。通过在场性解释,使两个不同历史(时间)上的知识性文本建立在目标一致的关系之上,并通过仪式中的操演体验,将蒙养传统中的“礼教”知识落实于教育实践过程之中,以此来隐喻“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实现“铸魂育人”的育人理想。事实上,历史蒙养传统代表着人类心理的共同经验,不仅在发生学意义上成为当下“开笔礼”的文化之根和经验之源,而且在仪式的开展过程中成为了“开笔礼”仪式实践的“母题”。以此来看,历史性的蒙养知识并不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文本,而是一种被历史所检验过的“经验”,将这种历史“经验”运用于当下小学的“开笔礼”仪式,同样也可以折射当下人们所追求的育人理念和教育哲学。
(二)蒙养传统内涵的道德理想是“开笔礼”仪式的精神之源
人们在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中,需要传统文化温润的力量来探求价值以外的东西,并借此寻找一方可以暂停脚步,潜下心来感受教育的文化力量的意义空间。庄孔韶认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视教育(教化)的文化传递对人的作用。几乎可以说,中国儒家(理学)文化的传递总是和教育联系在一起,或者说规划了教育是儒学与制度传播的车轮,是民众儒学思想内化的有力手段。”[14]176-189“开笔礼”仪式所传递的“礼”“正”“敬”“拜”正是儒家道德理想的重要内涵与现实表现。
就大教育观而言,学校并不能履行每个人的终身教育功能,而早已化民成俗的儒家学说总是从各种渠道、各种场合以及生活中再现出来,向各辈人施教[15]344。另外,礼仪教育相比于校纪班规等刚性的、外在的教育手段,是一种建立在人性本善基本判断和人性可教认识基础之上的柔性的、内在的教育手段。在“写人描红”环节中,主持人进行话语渲染:“人字一撇一捺,两笔划间相互支撑,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行。人与人之间也像这个人字,需要互相扶持,我们要学做人,做好人,做社会有用的人(RY—202109)”。借助于“开笔礼”这一现代性教育仪式活动,儒家化民成俗的传统道德理想有了得以实践的现实路径。老师、家长以及儿童得以感受正统文化的教化力、感染力以及渗透力,从而生发出强大的内生动力,培育“人人自育”“个个自治”的生命自觉。在“流量”裹挟着众多不确定与虚无的当下,“开笔礼”仪式或可成为人们追寻并坚守传统大道的一股精神之力,并借此寻找一方可以暂停脚步、潜下心来感受传统教育文化力量的意义空间。
(三)蒙养传统的历时性阐释是“开笔礼”仪式的创新动力
知识一旦成为“历史”,其生命力和解释力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的解释者们。正如赵汀阳所说:“历史考察必须有助于决定未来的行动,否则就只是关于‘故事’的知识,而几乎没有思想性的意义。”[16]194在仪式进程中,不管是主持人,校长以及老师致辞中惯用的“在古代……”“古人云……”“古代学童……”等话语表达,还是“仿古桌”“笔墨纸砚”等仪式道具,亦或是“拜师”“正衣冠”“朱砂点痣”等实践操作,都隐喻着“开笔礼”仪式对历史蒙养理念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对历史蒙学知识以及实践的创新性运作,其动力已不再是文化自身的进化功能,或者是教育文化涵儒过程中的自我更新,而在于当下人们与时变化的教育观念与行动。通过对传统育人观念与思想的体验和实践来实现当下教育目的,以宣扬现代教育理念和社会赋予小学的文化传承功能。如在“击鼓鸣志”环节中,“开笔礼”仪式将“古代读书人进入学宫学习往往要通过击鼓的方式表达他们上进的愿望”这一传统创造性地发展为“一击鼓,孝敬父母,二击鼓,热爱学习,三击鼓,为校争光”。“执前人之道,以御今之有”,这是一种知情意一体化的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的探寻过程,是一个不断解释、不断体验、不断变通以及“与时”协调的过程,不是绝对的逻辑与原则过程。不得不说,这种文化传统的创新发展属于教育文化传统的延续与重建,目的在于在现代文明中营造一种让儿童审视自我、储存记忆,并且能和传统“对话”的空间。
三、“开笔礼”仪式的当代价值
作为教育实践的“开笔礼”仪式,以“打基筑模”“习事明理”“修身正心”为价值预设,为儿童走向成人上好了“第一堂课”,并在具体的仪式过程中实现了引导儿童走向成人的根本教育旨归。
(一)打基筑模:奠定儿童走向成人“底样子”
朱熹在《小学》一书中提到了“做人底样子”。清代儒学家张伯行在《小学集解》一书中认为“做人底样子”“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纲,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心术、威仪、衣服、饮食为目。”[17]可见,“做人底样子”内涵着一个人走向成人的必备要素。在“开笔礼”仪式中,这些要素体现在以下三个关键方面。
1.奠定“知识底样子”
在知识与行为的先后顺序上,朱熹认为当以致知为先。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在学习知识方面儿童面临着由随意的游戏学习方式向有目的、有计划的学习活动转变。这一时期的儿童对知识获得的渴望与潜力逐步显现并迅速发展,小学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儿童的知识获得而奠基,培养儿童可持续学习的能力。“开笔礼”仪式作为儿童进入小学的“第一课”,是为儿童身心的这一过渡而做出的适时安排,目的在于科学有效地促进儿童开始学习人文等各领域的知识,掌握和运用人类优秀知识成果,涵养内在精神,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从而对人际关系、道德规范、事物价值以及行为方式的正确认知与判断奠定基础。
2.奠定“行为习惯底样子”
“古者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17],这里的“撒扫应对进退”与其说是基本的学规教育,不如说是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小学生模仿力强,容易做到习久成性,在儿童时代养成的好习惯,可以牢固地保持一辈子。在“行拜师礼”环节中,“礼协”老师在示范正确的拜师动作后说道:“礼请诸位学童按照‘礼协’所展示的正确姿势,敬拜谒师,端庄正礼,肃整衣冠(BYX—202109)”。“开笔礼”仪式遵循儿童的基本天性,从儿童可见、可知、可感的具体事件中着手,在仪式操演过程中通过话语规训、身体示范、切身体验来引导儿童逐步养成“礼”“正”“敬”“拜”等待人做事的良好行为习惯。朱熹认为少时养成了这些良好的习惯,成年后只要细心保存,时刻反省就好了。相反,“小学阶段养成的不良习惯,到中学和大学纠正起来就很困难。”[18]18正如他所感叹:“做人底样子”若“自小失了”,“要填补,实是难”[19]125。
3.奠就“道德信仰底样子”
蒙台梭利认为6-12 岁,儿童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及他人行为的善恶,善恶问题成为这一阶段儿童典型的问题,道德意识开始形成,并强调“如果渴望民众拥有更好的素质、更高文明程度,就必须想到儿童,才能实现预定目标。”[7]55一方面,通过“写人描红”、宣誓(堂堂正正立身,顶天立地做事)等实践体悟,儿童开始涉猎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知识与观念、开始学习学以做“人”的方法与路径、逐步懂得做“有用之人”的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开蒙启智,明礼修身”的主题条幅、孔子圣象等符号元素使得“开笔礼”仪式现场相较于其他稀松平常的教育场景显得更加庄重,使儿童产生敬畏与崇拜,从而产生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身份的一致认识与认同。总之,在道德信仰的培育上,“开笔礼”仪式承载着新时代全新的内涵与使命,那就是引领亿万儿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学习、练就本领、接续奋斗,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力量的崇高道德信仰。
(二)习事明理:形塑儿童走向成人的现实理路
《小学》记载:“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19]124“开笔礼”仪式作为当下蒙养教育“第一课”,依托于具体事项,并在身体体验中引导儿童由事入理,进而形塑出了一条儿童走向成人的现实理路。
1.以事起见,萌发儿童走向成人的理想种子
“开笔礼”仪式所内涵的“正衣冠”“拜师礼”等传统文化知识教育不是在课堂上完成的,而是在“校园田野”中与日常生活中易闻易见的事情联系起来而展开的。朱熹强调:“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19]125如果不顾儿童少知识、缺悟性,多记性、爱动手的特点,超越于具体的事情而教授一些“理”,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一方面,“开笔礼”仪式从整理仪容、礼敬长辈等儿童熟知的具体事项入手引导他们增进认知,日与性成、习与渐长,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美好的道德品行。另一方面,通过仪式转化,将一些抽象的知识符号转化为具体的生活观念。如通过描摹“人”字,儿童方能体会人“写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一基本事实,也才能萌发学做人、做社会有用之人的理想种子。
2.亲身体验,激发儿童走向成人的内在自觉
朱熹认为,由于蒙学儿童的认识、辨别以及接受能力较弱,所以对他们的教育不能灌输以高深的道理,而是要以可操作的实践活动加以引导。在“开笔礼”仪式中,作为受礼者的儿童不仅通过“礼协”示范、主持人解说去学习仪式动作、聆听训辞教诲,还通过家长与老师的现场指导实现了身体与心理上的全方面体验。如在书写“人”字的过程中,家长和老师不仅手把手教儿童比划和书写,还为他们细心讲解着人字的深刻寓意。这一过程中,儿童将身体动作的改变和一系列象征符号的印记相统一,用心感悟仪式的文化意蕴,时刻提醒着自己作为“成人”者的角色转变和身份确认应该具备的仪容和德性,透过时间不断前行以及伴随而来的智识、意志、情感与行动力而朝向更加自觉、更加人性的光明未来。
3.以事明理,引导儿童领悟走向成人的生命意义
“开笔礼”仪式中的“朱砂启智”“写人描红”“击鼓鸣志”等程式内涵着成人之理。具体来讲,“朱砂启智”以“朱砂”的文化意蕴喻示打开儿童学习技能与文化知识的智力与心性;“写人描红”以“人”字启示儿童“成人”的条件,并向他们表明为人子、为学生、为社会公民的种种规范;“击鼓明志”通过鼓的“轰鸣”象征来取证儿童立志的信心,树立一心向上、一心向前的决心与志向。“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这是“教育”一词的中国传统表达。“开笔礼”仪式对成人之理的教育过程,即是以一件件具体的、能触发生命感知的文化事项来滋养儿童的生命意义,让儿童从小开始,从“根底”开始就拥有丰盈的生命根基,从而在现代技术与物质主义遮蔽的时代之中寻求自身生命意义的根源。
(三)身心统一:实现儿童走向成人的整全发展
从“习事明理”的成人理路来看,修“外在之身”与正“内在之心”是儿童走向成人的必然要求,而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儿童生命的整全发展。
1.修“外在之身”
中国传统道德观念非常注重外在形象对一个人德行的修养作用。屈原在《离骚》里多次提到了修外在之身:“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香草满怀,将自己打扮的规整优雅。朱熹将修身看做蒙学第一要务,而修身必先始自衣服冠履。《童蒙须知》强调:“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20]4-5开笔礼仪式中,“正衣冠”为仪式之首,强调“衣服鞋袜皆需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正是诠释并践行了修外在之身的要义与要求。儿童更多的是作为身体的存在,修外在之身就是要充分激活儿童身体向着周遭世界的感受力,以大方、得体的姿态舒展自我,向着周遭他人与世界充分展示新时代少年儿童的良好精神面貌,在融入周遭人与事物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超越自我,达成自在生命更高水平的和谐与秩序感[21]。
2.正“内在之心”
从中国传统教育观来看,儿童只有从年幼之时逐步习得尊师、敬长、孝亲、爱国之道,才能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人要求打下基础。也即是说只有在身心不断成熟、知识不断增长的同时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树立远大的理想信仰,才能按照社会所期待(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去行动,“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准此,才能避免成人后“扞格不胜之患”[22]1。“开笔礼”仪式中的“点朱砂以启迪智慧、行拜礼而尊师敬长、击鼓鸣志而树立抱负、集体宣誓而坚定理想信念”等程式与操作正是这一育人理念的实践表达。在小学教育场域中植入这一蒙养理念,并用这一要素来浸润、感化蒙童,本质是要使其自觉树立“自暗养成”的意识,自觉践行儿童作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接班人”的责任与担当,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自育”与“自治”。
3.在“内外”的统一中实现儿童生命的整全发展
朱熹在蒙养教育过程中一再强调“知行相须相法”的思想,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修身方法加以提倡。“开笔礼”仪式的操演程式将儿童“成人”的标准与实践的标杆匹配在了一起,最终使得“开笔礼”仪式现场成为了一个“训练场”,通过一套完整的仪式程序,以“成人”的诸多规定性孕育儿童个体身心的内在秩序,并以亲身实践的方式让儿童整体地与自我、他人以及社会相遇,逐步敞开儿童个体文化浸润的可能性,一点点培育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生命,将“成人”“做人”以及做“有用之人”的规范标准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伦理体系内化在儿童的内心,实现对他们身心意志的规训。
四、总结与思考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儿童步入小学而举行“开笔礼”仪式,是教育关于儿童“成人”的构想与努力,更进一步来说,是关于教儿童如何做、并如何做好一个中国人的教育理想。
尼采说人是一根悬于深渊之上的绳索,“向前进是危险的,停在中途也是危险的,向后张望也是危险的。”[23]5“开笔礼”仪式将儿童置于“过去—当下—未来”的生命流程之中,让他们在可见、可感的教育氛围中感知“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生命真相、体悟生命流转与进步的意义。以“化礼成俗”的方式,“开笔礼”仪式在守正创新中完成对蒙养传统的再生产,通过凭借历史蒙养知识,赓续历史蒙养传统所内涵的道德理想,强调历史蒙养经验来塑造儿童的灵魂和生命,进而寻找儿童走向成人的行动线索。以“打基筑模”“习事明理”“修身正心”为价值预设,“开笔礼”仪式在操演程式中将儿童“成人”的标准与实践的标杆匹配在了一起,“促发儿童通过身体力行和做中学的实践尝试获得自我生活经验”[24],帮助儿童从自我走向他人、集体和社会,实现生命的整全发展。
“开笔礼”仪式指向儿童成人的希望,承载他们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开笔礼”仪式是未来中国少年儿童的画像,描绘的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想图景,而达成这一理想的实践路径就是逐步敞开儿童个体文化浸润的可能性,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求并汲取生命养分,一点点培育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生命,进而以共同的教育使命为导引,开启自我建构的追寻,达到臻于完满的人生追求,最终成长为一个知礼达仪、恪守正道,真正具有中华文化之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