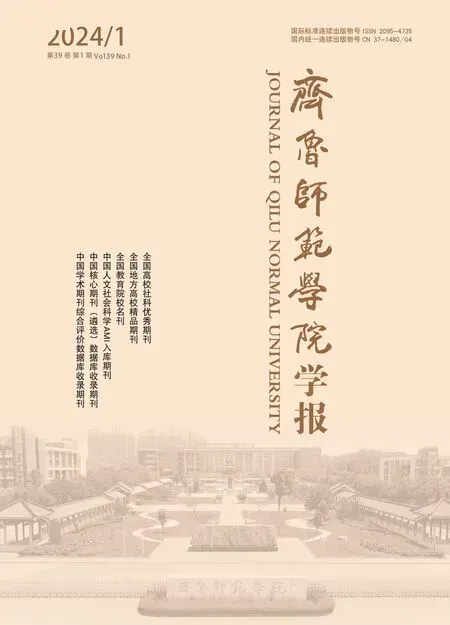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的家国情怀传承
任现品 田 明
(1.烟台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2.山东单县龙王庙镇中心小学,山东 单县 274326)
习近平同志在2012 年11 月29 日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复兴之路》展览后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36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既要对接国际发展的时代节奏,又要以现代因子激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潜隐价值。家国情怀作为中国最为突出的优秀文化传统,注重个人由爱家向爱国的纵向情感提升,强调个人、家庭与社会、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其本质是一种基于自然情感认同与文化价值认同的民族国家认同;2014 年3 月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强调,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着力完善青少年学生的道德品质,培育理想人格,提升政治素养。”[2]家国情怀是国人特有的人文信仰,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与现代国家认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近现代以来,中华儿女救亡图存、渴望民族振兴的艰难求索无不以家国情怀为内在情感依据,从洋务派的实业兴国、维新派的变法改良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推翻君主专制、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直至新中国的成立,民族复兴是其不变的初心,并在与之同步的现代文学中留下了清晰的投影。孔庆东曾说:“现代文学以其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与当代生活的关联和在整个文学研究中承上启下、左右勾连、内外交通的坐标位置更多地感召了我。”[3]221现代文学用审美形式生动展现了民众从眷恋家园到认同民族国家的情感提升,推动了家国情怀的现代转换与历史延续,因而它并不处于民族复兴历史之外,也不只是描绘其艰难历程的语言工具,“它处在中国梦之中,是中国梦的主要精神内容和内在驱动力之一。”[4]14现代文学本身即是民族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其教学目的不仅在于让学生掌握相关的文学知识,“更重要的在于思想的传输与培育,在思想教化的同时引导人们实现精神建构,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人、国家、社会的利益互动,这就需要从每一个组成要素出发,通过深入分析教育感受与表现而不断调整教育策略。”[5]89激发家国情怀的精神建构功能就是其一。在高校教学过程中,我们教研室的教师十分重视传承课程内容的家国情怀内涵,以有效融入民族复兴的历程之中,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救亡图存的民族需要:现代文学发生的根本动因
作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现代文学既与古代文学保持着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又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古代文学常借助崇高道德理想对社会现实邪恶的战胜以礼赞人生美德,实现道德教化的目的;现代文学则以西方价值观念为参照坐标审视、质疑文化传统,其意重在启蒙,“追求人的解放与使人成为‘顺民’甚至奴隶是现代启蒙文学与古代教化文学在价值目标上的主要分野;思想内容的多元化与道德说教的单一性是现代和古代文学的重要差别。”[6]11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根源除中国社会、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外,还有西方文化强烈冲击的外在契机,是内在要求与外在契机合力作用的结果;其转型也是多层面的,主要包括人的观念、文学观念的转型等。因此,讲授现代文学,教师最先需要向学生阐释清楚的就是其发生根源。
现代文学的发生与中国社会、制度及文化的转型同步互动,其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动因乃是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在传统社会,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只是家族的一员,没有自我身份和主体性,“在中国文化中,个体只是社会网络中的一分子,女性臣服于丈夫,丈夫臣服于王权,同样无独立的主体性。”[7]77宗法家族不仅直接造成了民主、科学意识的匮乏与个人权益观念的阙如,而且家族群体之间互相排斥,致使社会大群体的凝聚力不足,因而相对于强固的家国观念,民族意识比较淡薄。西方列强与日本的武装入侵使中华民族被动生成现代民族意识,空前的生存危机需要打破家族壁垒以凝聚全部社会力量一致抗敌;新的民族理念既调整着民众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构成为现代文学生发的现实依据;赵京华曾说:“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出现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契机的,一方面现代国家要求国民凝聚共识,形成一致对外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传统的臣民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家国一体的观念不再以儒家天地君亲师为终极目标,不再以效忠帝王为旨归,而是以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为认同对象。这给传统中国文化里的家国一体理念和家国情怀注入了新的要素。”[8]“五四”文学的兴起标志着现代文学的发生,它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白话代替文言,在积极引进西方个人价值观念、社会进步理论的同时,激烈批判家族礼教对个人独立性的压抑;“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9]9在此,教师不能局限于讲授“五四”文学的具体主张,更要将阐释的重心聚焦在何以会提出这些主张,以剖析其深层动机:正是为了救亡,“五四”文学才承续晚清白话文运动对文言文的激烈批判,进一步推广白话文,因要“立国”必先“立人”,而要“立人”则必先启迪民智,文言文业已成为开启民智的最大障碍。由此使学生领悟其内在逻辑:现代文学的生发动因是有志之士对家国命运的担忧和民族复兴的殷切期望,传统家国情怀作为内在驱动力获得了新的现代形态。
在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家国情怀注入现代内涵方面,文学叙事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功能,“现代文学的语言实践是民族国家的自主性的体现,或者反过来说,现代文学的语言实践,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部分。”[10]6现代文学和现代民族主义、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同时兴起并非偶然,从鲁迅的《祝福》、巴金的《家》到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等,都意在打破传统家族观念的思想束缚而唤醒人们的个人权益观念和民族国家意识,恰如樊星所言:“家国情怀在历史上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分野,那就是从古代到近代,基本上是以集体主义为主的家国情怀书写,而从现代到当代,家国情怀书写中开始显现人的个体觉醒与个性解放的因素。”[8]这与西方现代文学的生成机制有着明显不同。任课教师抓住家国情怀这根隐藏其中的金线,向学生阐释清楚无论是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1930 年代的“文艺自由”论争,还是抗战时期“民族形式”之争,都意在民族救亡,都以家国情怀为内在价值依据,让学生在历史脉动中捕捉到家国情怀的精神支撑功能,并从内心深处激发出对祖国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课堂教学对现代文学发生根源的剖析,既使教师充分利用优秀文化传统的最佳材料,依据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揭示出家国情怀的不同表现形态;也使学生在深刻理解现代文学内在机制的同时,将自身对家园的道德情感凝聚为爱国主义情感,将家国情怀根植到自我心灵中去。
二、离家找寻民族出路:现代经典作家的人生选择
在现代性开启的转型时代,家国情怀表现为救亡图存意识,落实在有志之士的行为上便是出走寻找民族出路,离家出走成为当时作家的流行行为;因而讲授现代文学,教师还要向学生强调经典作家的人生选择与民族需要之间的深层关联。现代作家的家国情怀早已超越迷惘愤懑的阶段,而积极投入到救国救民的实践行动之中,他们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甚至走出国门,怀着“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心愿,到国外去寻找振兴民族的药方,希望从欧美、日本的发达中找寻到中国落后的原因,从而展现出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不断将对故土的伦理情感提升为对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感的心路历程。
出走找寻民族出路并非个别作家的行为选择,而是一种富有时代性的集体行动:鲁迅先在南京矿路学堂学地质,后进日本仙台学医学,幻灯片事件使他最终决定弃医从文,从解除民众的身体病痛转向救治国民的精神麻木,寻找到了以精神启蒙来救国的道路;“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1]439鲁迅人生选择的最大意义在于体现出了真正爱国者对民族命运的深沉忧虑,其冷峻外表下跳动着疗救病态国民的炽热之心。
此外,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也都曾东渡日本学习医学,胡适十九岁时则考取清华大学留学奖金、进入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徐志摩曾先后在美国、英国学习银行学、政治经济学,闻一多于1922 年7 月赴美国留学专攻美术,巴金先从成都到上海、南京求学,后去法国留学;茅盾先从浙江到北京、上海求学,后又去日本学习等等。异国的学习、生活一方面使他们掌握了相关的科学知识,更新了自身的知识谱系,为今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仿吾认为,研究文学没有进文科的必要,我们也在谈文学,但我们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有科学上的基础知识。”[12]82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跨入了一个开阔崭新的精神原野,为其完成自我文化上的重构提供了契机;更为重要的是,异国的生活体验使他们深切品味到了弱国子民的屈辱与愤恨,个体遭际与祖国命运实现了有机对接,他们最终走上了改造社会、重塑国民性的文学道路,“至于他们在异域文化的环境中,体味到‘弱国子民’的无限挤压时,又促成了他们把独特人生体验,升华为独特的民族体验,孕育生成了超越个人恩怨的宏大社会情怀,为其创建五四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石。”[13]14可以说,没有在日本所经历的幻灯片事件,也就没有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创作;没有赴美留学期间对祖国的热切期望,闻一多也就无法创作出主题深沉、情感浓烈复杂的爱国诗作《死水》;至于老舍,留英经历对其创作至少有两方面影响:“(一)走上文学道路,确立了反帝爱国主义和批判国民性中落后面的创作主题。(二)英国文学温和宽容,幽默讽刺的风格深深影响了他,而现实主义文学则是他主要吸取的对象。”[14]103出走探寻是现代作家的人生选择,也体现了他们内在而炽热的家国情怀;而无论寻找的艰难过程如何不同,他们都寻找到了最合适自己的报效祖国、振兴民族的方式。
其实,在大多数现代作家身上都能看到民族需要对其人生选择的影响,正是内心深处的深厚民族情感,才使他们远走异乡积极寻找个人与民族的出路,上文所举的只是其中有限的几个。教师对经典作家出走动因的介绍,不仅是传授知识、传递文化,更是通过揭示作家们的内在情感结构,来观照人的精神生活,指向人的心灵支撑与意义世界,“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15]3让学生认识到作家的文学创作道路与家国情怀的深层关联,体会到民族复兴的实现离不开个人创造性的发挥,将个人的创造性思维、具体生活追求和实现民族复兴融为一体,从而在家国情怀的链条内凸显人的意义、人的价值,最终实现个人、家庭、国家三位一体的价值同构。
三、家国休戚与共的生命体验:代表性文本的内在意蕴
现代文学课程的主要内容,除文学运动的演化机制、经典作家的创作历程外,最重要的自然是悬挂在文学史之树上的作品,它们犹如自然孕育、逐渐长大成熟的果实,既汲取着社会时代的精神风雨,又蕴含着作家个人的情感倾向与价值诉求,更承载着民族共同体的独特记忆与审美心理;可以说,它们是现代作家以强烈的身份认同,从自身感性生活出发,将个人生命遭际与民族苦难体验、自我精神追寻与国家前途道路凝聚为一体的结晶,因而在描绘作家自身感触最深的生活细节的同时,揭示广大民众的艰难困苦及其对民族复兴的渴盼之情,其中家国休戚与共的生命体验得到了多维度、多层面的展现。
家与国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已构成为国人的精神根基,因而,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宗教式外在超越,中国社会更多依靠的是人文信仰——家国情怀,其核心是家与国之间情感与责任的贯通;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通过文本解读的审美方式将家国休戚与共的价值观念传递给学生,通过鉴赏、领悟式的情感激发,引导学生认同、内化这种思想观念与文化精髓。鲁迅的七言绝句《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即表达了怜民忧国的深切关怀,“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一个“没”字,将形象与环境融为一体,活画出民众出没蔓草的悲苦生活画面,抒情主人公对民族国家深陷困境的悲愤之情也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沉沦》的主人公“他”,在生之困苦与性之苦闷的双重挤压下,悲愤地投海自杀,自杀前喊出:“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16]240作者在肯定青年一代追求个人权益的同时,将个人在异国他乡的遭际与民族国家的贫弱关联起来,揭示了个人、家庭和民族荣辱与共的事实。闻一多的《死水 》运用一系列具体、繁密而浓丽的日常意象,既有“破铜烂铁”“剩菜残羹”“霉菌”“白沫”“花蚊”等丑恶意象,又有“桃花”“翡翠”“云霞”“绿酒”“珍珠”等美好意象,将丑陋不堪的社会现实包含在唯美颓废的艺术形象之中,在寂静腐烂的“死水”下,涌动的是抒情主人公憋闷的怒火;正是透过憎恨现实、满怀诅咒的“死水”意象,读者触摸到了诗人悲愤而炽热的家国情怀;有研究认为“闻一多的《死水 》是唯美、颓废和爱国的统一”[17]76,其根据亦在此。艾青的著名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感情深厚凝重而又蓬勃热烈,从个人对土地的生活依赖到对家园亲人的深刻眷恋,直至对民族重任的自觉当担,可谓集中体现了当时国人共同的情感路径,因而引起了时人的强烈共鸣。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借助“我”的视角,通过大量富有情趣的生活细节,逐步展示出王哑巴那隐藏在拙笨、胆怯言行下的精神根基——家国情怀,“晚上我同差半车麦秸睡在一块儿,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加入我们的游击队?’‘我为啥不加入呢?’他说,‘你们都是好人呵。’停一停,他大大地抽了一口烟,又加上这么一句:‘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18]7王哑巴投入抗日,不是他人教育、动员的结果,是为了早日回家种庄稼,而只有赶走侵略者才能重返家园。《四世同堂》中,祁老人式的北京老派市民最大的盼头就是几代阖家同住、世代繁衍下去,至于北平之外、与家族成员无关的事都在他们的考虑之外;但日本侵略者的长期占领,使其几代同堂的愿望化为泡影:儿子祁天佑受尽屈辱自杀而死、孙子祁瑞全离开北京去抗日、重孙女妞妞被活活饿死等,接连不断的家庭灾难迫使祁老人逐渐悟出家庭安危和民族强弱的内在逻辑,并萌发为自身的民族国家意识。有研究指出,“从新文化运动到改造国民性,从文学革命到政治革命,从五卅运动到‘九一八事变’,一连串的外患内乱都在唤醒和制造中国人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把历史上具有文化同质性的泛中华观念,改造和制造为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强化着民族主义的思想和激情,救亡救国就是近现代中国思想与政治的主旋律和最强音。”[19]174家与家族意识就这样在刻骨的痛苦感受中生长、提升为民族国家意识,家与国的休戚与共也由此得以彰显。
当然,也正是在家国休戚与共的生命体验激发下,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端木蕻良的《大江》等作品,才从不同的视角展示各阶层在外来侵略的危难中所完成的思想转换与人格升华,这些作品对民生疾苦的刻画、对个人灵魂冲突的聚焦正继承了以描绘苦难来凸显家国情怀的文学传统,无不散发着深厚的人文意蕴。
通过对代表文本的内涵阐释,学生们不仅可以体会到深厚的家国情怀不止有保家卫国这一种形态,还有对民众苦难生存状态的切实描绘和知识分子于漂泊跋涉中的痛苦求索等其他形态,而且能领悟到家国情怀的具体形态与作家自身生活体验的息息相关,是作家自我生命体验和民族国家命运关联、凝聚的结晶;教师借助作品提供的多样化情景体悟,不断凸显个人心理感受、情感记忆与民族复兴的深层互动,以持续滋养学生报效祖国的执着感情。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宗教式外在超越,中国社会更多依靠的是人文信仰——家国情怀,即注重个人由爱家、爱家乡向爱祖国、爱民族的纵向情感提升,突出个人对家庭、国家之间的情感与责任的贯通,其实质是一种在自然情感、文化价值认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认同。这种深厚而持久的家国情怀以其丰富多样的形态蕴藏在现代文学的课程内容之中,除文中所讨论的现代文学发生的根本动因、现代经典作家的人生选择、代表性文本的内在意蕴外,还包括文学运动的演化机制、文学意象的营构等;教师不仅要以一种自然而多样的方式向学生揭示其现代转化机制及内在的价值维度,还要透过作品的百变面相透视家国情怀的内在支撑作用与精神启迪功能,从而达到和学生一起探索、思考个体生命价值的共生互融境界;最终引导学生把学习专业课程和自我人生选择、民族复兴结合起来,以摆脱物质主义时代的价值迷茫,重新确立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教师自身也在现代文学的教学活动中,既圆满完成教学任务又有效传承了家国情怀这一优秀文化传统,承担起教书育人的社会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