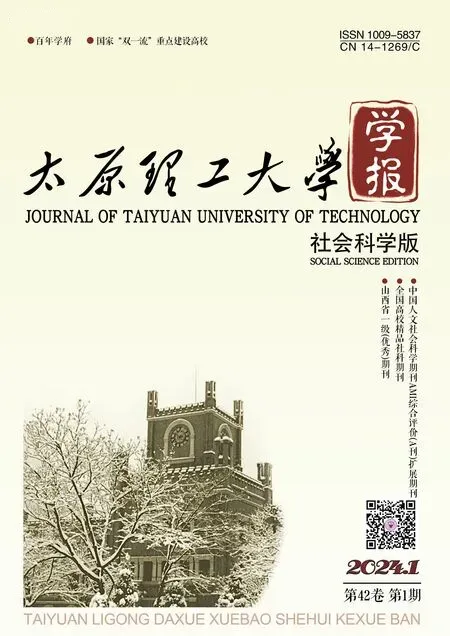“阿尔法城”记忆:村上春树文学的“近代”景观
徐谷芃
(南京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6)
哈佛大学教授、日本文学研究者杰·鲁宾(Jay Rubin)认为,探究生与死的意义、真实的本质、时间的感觉和记忆、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以及爱的意义等等问题,显示了村上春树文学世界的本质及其核心[1]1。作为美国学者,杰·鲁宾旨在说明村上文学在探讨“人之存在”及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上具有普遍性意义。
村上作品获得了众多国家和读者的认同,除杰·鲁宾所论以外,还有诸如吸收美国大众文化、借鉴美国文学等特点。笔者曾分析美国文学巨匠菲茨杰拉德的巅峰之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并将其与村上的代表作《挪威的森林》作了比较,得出如下结论:《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村上的影响堪称巨大,从创作基调、创作风格与文学技巧等方面全面规范了《挪威的森林》的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被称为“美国式剧作法”的三个基本特性,即“高贵性”“喜剧性”“悲剧性”在《挪威的森林》中历历可见,说它是村上文学形成的源点也不为过[2]。
再把两部作品分别置入作家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又可以发现,无论菲茨杰拉德还是村上春树,他们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也超越了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所处的不同的社会。二位作家努力通过文学创作,积极思索“近代”资本主义席卷世界过程中出现的困扰人类社会的同质性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法。正是这种思索“人之存在”的尝试和挑战,才使他们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反响与共鸣。
那么,“近代”社会的同质性问题具体指向又如何呢?这些又是如何在村上春树的文学作品之中反映出来的呢?本文以长篇小说《天黑以后》为中心试作探讨。
一、“阿尔法城”与《阿尔法城》
评论家黑谷一夫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基本上以追求物质生活的时代青年作为描写对象,这一特点也适用于村上春树,只是后者的人物形象中还要加上某种“丧失”的特性[3]160。什么是丧失?究竟又丧失了什么呢?
村上春树曾经明确指出,《天黑以后》是向高中时看过的法国电影《阿尔法城》的致敬之作[4]129。此作的核心场域正是一家名为“阿尔法城”的情爱旅馆,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在此登场,展开各自的故事。
《阿尔法城》拍摄于1965年,由让·吕克·戈达尔编剧并导演。村上借用主人公浅井玛丽和情爱旅馆的老板薰之间的对话,对《阿尔法城》作了一番介绍。
“《阿尔法城》,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让·吕克·戈达尔的。”
“这个没听说过。”
“很早以前的法国电影,20世纪60年代的。”
“那么,没准是从那里取来的,下次见到社长时问问看。什么意思呢,阿尔法城?”
“虚拟的未来城市的名字。”玛丽说,“位于银河系某处的城市”。
“那,是科幻电影喽?像《星球大战》那样的?”
“不,不是,没有特技镜头和打斗什么的……解释不大好,是一种观念性影片。黑白片,台词多,在艺术电影院上映的那种片子。”
“观念性的?”
“比如说,在阿尔法城里,流泪哭泣的人要被逮捕、公开处死。”
“为什么?”
“因为阿尔法城不允许人有很深的感情。所以那里没有爱情什么的,矛盾和irony也没有。事物全部使用数学式集中处理。”
薰皱起眉头:“irony?”
“人对自身、对属于自身的东西予以客观看待或反向看待,从中找出戏谑成分。”[5]49,50
银河系、未来城市,玛丽的介绍让薰立刻联想到类似“星球大战”一类的流行科幻电影,然而实际的《阿尔法城》却是极为小众的观念性影片: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不能流泪,不允许有感情,也没有主观或客观认识,有的只是冰冷的数字处理。
在村上的眼里,“阿尔法城”显然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人失去眼泪和感情,失去了属于“人之为人”最为宝贵的东西。借用这个比喻,村上在作品中是如何表达“丧失”的呢?
出现在情爱旅馆“阿尔法城”里的人物,几乎都有难言的苦衷和困境:薰作为老板,原是职业女子摔跤手,可没到30岁身体就土崩瓦解且身无分文,至今孤身一人[5]51;员工蟋蟀由于惹了大麻烦,3年多来一直被人追踪,在全国各地东躲西藏怕暴露其真实身份[5]134,135;中国妓女郭冬莉被黑社会用船偷渡过来接客且被剥削[5]37;浅井玛丽和姐姐爱丽之间无法正常交流沟通,只有深夜独自一人游荡;跻身白领有着正常家庭的电脑工程师白川怀着一肚子不满在这里伸手打了郭冬莉……
村上描述的各色人物看似性格迥异,但其实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内心都深深隐藏着虚构的“阿尔法城”所象征的东西。在这里,个人的情感被剥离开来,人们得不到爱,成为孤独的象征。身处现代社会的这些年轻人,在光鲜亮丽的情爱旅馆“阿尔法城”内,无论怎样也挥散不开笼罩在内心深处的一片黑暗,游走于“丧失”的边缘。
然而,村上对“丧失”的叙事在郭冬莉的人物设定上却涉及另一个更为重大而深刻的问题。玛丽从郭冬莉的口音中判断她来自中国北方,于是薰立即问道:“过去的满洲那边?”[5]35日本学者水牛健太郎据此认为,“对中国妓女的暴行,毋庸置疑是对包括日本曾叫作满洲的那一区域的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以及对居住民加害行为的隐喻”。刘研在此基础上也指出,“过去的满洲”暗示了《天黑以后》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6]208。玛丽会说中国话,郭冬莉来自中国东北,这些描述显示了《天黑以后》具有浓厚的中国元素。有学者指出,经历过日本战后学生运动的村上春树在远离日本的场域且在某种“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通过《奇鸟行状录》中的诺门坎战役和《天黑以后》等作品展开了所谓“满洲叙事”。这些凸显出战后日本流行文学中并不多见的“二战史观”,然而村上的历史反思并未完全摆脱日本后现代文学强调体制与个人宿命对抗的表达范式[7]。
加藤典洋专门分析过“中国,对于村上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一命题。在他看来,这可以说是“属于村上春树独有的,甚至是以某种原初的形式出现的,面对中国产生的极为强烈的罪责感或者说是良心上的呵责”[8]250,这无疑为思考村上文学的中国叙事提供了有益启示。
《天黑以后》出版不久,不少读者猜测其舞台应该是东京的涉谷或是新宿,然而村上春树本人在一次采访中明确指出,“作为小说舞台的城市是虚构的城市,……我要说的是在‘阿尔法城’”[9]。前面已经指出,“阿尔法城”是法国同名电影所描述的一座虚构的城市,而村上肯定此作的背景是“阿尔法城”,显然是要强调故事发生的背景有着某种普遍性。
四方田犬彦发现,村上小说中的人物经常会在对话中提到美国或者欧洲的电影,这些电影对于村上小说的影响绝不是基于现代实验精神的某种东西,而是他们那代人共同经历的展示[10]。那么,共同经历了什么呢?
在处女作《且听风吟》中,村上曾借用主人公之语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想说。写文章不是自我疗养的手段,因为它只是为了自我疗养的一种尝试”。横尾和博就此指出,村上的“我想说”三个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多数人想说不能说,患上了失语症的时代[11]159。
2017年出版的长篇《刺杀骑士团长》其中一段针对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村上借用小说人物之口发出了这样的诘问:“无数市民被卷入战争甚至被杀害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说中国死难者超过40万的,也有说10万的,但是40万与10万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据说这句话在日本国内遭到不少人的抨击和责难,认为村上是在讨好中国,因此特意把中国报道的30万死难者之上另加10万,上升到40万。透过这段话,可以将村上的意思理解为,比起纠结于数字,更应认识到大屠杀这种行为的本质[12]。由此来看,在一个几乎“丧失”了说真话的时代,勇于尝试“我想说”的村上实属难得。
在《天黑以后》中描写了弱小而受人控制的、出身中国东北的女性郭冬莉在“阿尔法城”遭到文质彬彬的日本人白川的毒打,而主人公玛丽因为会说中国话而卷入其中,由此展开故事叙述。显然,村上是要通过“过去的满洲”的记忆,唤起日本人已经或正在“丧失”的对中国的罪责感和良心上的呵责意识。作品的最后,会说中国话的玛丽主动伸出双手拥抱了“沉睡”的姐姐爱丽,这对姐妹如同虚拟城市“阿尔法城”的居民,在失去了长时间的交流后,又同时在各自孤独的心理中找到了让她们相互联系的爱。
“阿尔法城”作为一个借喻和象征,实质是“丧失”:既有个人感情、日常生活的失落与纠结,也有战争记忆的消失。村上通过虚构和写实的双重叙事刻画出各种人物的内与外、光与影。需要指出的是,村上的文学创作一般多在作品中设置较为明显的双线:现实的线与非现实的线,或者说阳线与阴线,而这个特点在本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那么,这种创作手法与“丧失”的主题有何内在关联呢?
二、村上文学的叙事二重奏
按照村上自己的概括,将“存在”与“非存在”这样平行的世界进行比照是他喜爱的方式,也是他所有作品的基础。所谓“存在”属于可以认知的“现实”,而“非存在”则属于臆造的世界[1]125。例如《挪威的森林》,阳面的有绿子、玲子、永泽、五反田,阴面的有直子、木月等。再如《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也按照平行的阴阳线展开,一条“冷酷仙境”背景是东京;另一条“世界尽头”是山川寂寥,只有成群的独角兽和头盖骨。《刺杀骑士团长》同样也描写了“我”穿过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法则所支配的地下世界。
早在第一部作品《且听风吟》获得1979年“群像”新人奖时,就有评委认为村上的叙事风格是“现实与虚拟世界交织在一起,把历史与当下融为一体”[13]。第三部长篇《寻羊冒险记》堪称典型。此作描绘了一位暗中掌控政治、金融、大众传媒、官僚机构、文化等所有一切的老板,而操纵老板的却是一只1936年进入其脑中的羊。村上借此讽喻控制日本当代消费文化的关键性因素源于邪恶、不纯的动机,而这种动机与驱动日本走向毁灭的那场侵略战争一脉相承。杰·鲁宾进一步指出,这种邪恶和暴力还与20世纪60年代末镇压学生的理想主义运动及给现代日本社会带来极度无聊和过度劳累的权威主义传统密切相关[1]89,101。
在人们正常的社会、文化生活背后,是暗中操纵一切的老板及其脑中的羊,发动侵略战争、镇压学生运动、宣扬消费文化等充满邪恶和暴力。一明一暗的两条主线,现实与虚拟世界、历史与当下的交织在此清晰可见。
《天黑以后》也承袭了上述阴、阳双线的创作手法。姐姐爱丽在虚拟的世界里无休无止地睡在床上,受到“无面人”的窃视,而妹妹玛丽在现实中则敢于面对一切,会说中国话,计划去中国留学等等。不过,村上文学的叙事二重奏在此作中除了人物性格的设定以外,还有着更为广阔的背景。
村上为作品精心设定了一个时间带:晚上11点56分到第二天早上6点40分。作为长篇小说叙事,7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未免太短。正常而言,黑夜原本是普通商店歇业,人们美美入睡的时间。可是随着便利店和家庭餐厅开始24小时营业,商业的发展力求将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最大化,导致人们无法正常入眠。于是在“天黑以后”,作品为我们一一剥开众多人物在白天不愿意暴露的世界。重要的是,支配这种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是一个将白昼和黑夜混淆,试图提高效率的“系统”。这个“系统”的首要特征便是物质生活的繁盛。为此,人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往往与物质密切相关,“唯物”至上。过度追求身外的东西,其结果便是使人们陷入心情上、精神上的巨大苦痛之中。郁闷、压力、孤独等等,这些来自心灵上的痛楚,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们。物质的繁荣与内心的苦闷,同昼夜颠倒的消费生活一道构成了《天黑以后》强烈的叙事二重奏。
村上的成名作是1987年出版《挪威的森林》,这也是他最受世人欢迎的一部作品。如果说《挪威的森林》还停留在描绘男女之间忧郁的爱情故事,局限于一种精心雕琢的情调之中,那么17年后出版的《天黑以后》在立意上显然大相径庭。有学者调查了2011年10月1日的“豆瓣网”,发现当时《天黑以后》的阅读人数不到2 000人,而《挪威的森林》的读者却达到了188 200人,《海边的卡夫卡》为59 920人。这些数据或许说明《天黑以后》受欢迎的程度不及《挪威的森林》或者《海边的卡夫卡》[14]。但在我们看来,村上春树已经超越了男欢女爱的狭小范围,而是以成熟、深刻的笔调直诉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矛盾与困境。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的人物,如郭冬莉(り)、玛丽(マリ)、爱丽(アイリ),在她们的名字中有着相同的发音,即“リ”。有学者指出,这实际上也暗示了三人虽然国籍和立场不同,在作品中分别属于明线和暗线的人物,但她们身上存在着某种共性[15]。这种共性,显然是村上力图刻画的21世纪现代都市人内心的孤独与压抑心态。作者旨在强调,随着物质文明的日益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都市人的精神世界倍感压力、寂寞和空虚。人性的正常部分遭到扭曲和埋没,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愈来愈大,相互之间不易走近。然而,心理上的压抑还只是属于个人内心的问题,所谓隔阂也还在可控范围之内,而一旦心理问题发展成为社会问题时,就显示出“系统”的脆弱与危害。
在1988年出版的长篇《舞!舞!舞!》中,村上描述小说人物五反田杀害应召女郎喜喜时,说这是出于“某种自我破坏的本能”。胜原晴希指出,这种心态的背后反映出人们对支撑“近代”这一所谓“进步”的虚幻像及其意识形态逐渐丧失了信仰[16]。加藤典洋也认为,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像五反田这样自我封闭的人物,在自我与他人眼中的自我之间痛苦挣扎,直至走向毁灭[17]158。换句话说,这种“恶”其实在整个“近代”社会中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具有异常可怕的普遍性。
我们来看《天黑以后》中打完人的白川。回到公司处理完事之后,白川乘出租车回家,路上专门绕道去了一家便利店,购买妻子特意吩咐的牛奶。
店里没有客人,收款台的年轻男子正用手机聊得起劲。南十字星全明星乐队(Sazan All stars)的新曲正在播放。白川径直走到牛奶柜跟前,把高梨低脂肪牛奶袋拿在手上,确认保鲜期。还不要紧。又顺便买了装在大塑料容器里的酸乳酪[5]118。
便利店、流行乐曲、低脂肪牛奶、妻子的嘱咐、消费期限等,这些构成了“恶人”白川的另一个侧面,是一位普通市民的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
“阿尔法城”隐喻了人们正常感情的丧失。然而村上通过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目的是要说明比感情丧失更为可怕的是人类正常生活的丧失,是人性的丧失。村上文学的叙述二重奏除了增加文本的层次感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揭示这种可称之为暴力的恶,也正是通过白川这极其平凡的现代社会市民形象,有意宣示像他那样通过暴力来宣泄的“恶”其实就隐藏在我们四周,而这种“恶”犹如在电影《阿尔法城》中因为流泪哭泣而遭到逮捕、公开处死一样,令人绝望。
诚如村上所言,《天黑以后》是向《阿尔法城》的致敬之作,然而村上显然不只是停留在“致敬”,而是试图揭开产生这些邪恶和暴力的原因,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近代”这样一个系统。
三、“近代”的虚像与实像
中岛一夫指出,《天黑以后》的“以后”二字代表了减少乃至限制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某种“监视”与“管理”[18]。作品中,姐姐浅井爱丽被放在一个巨大的空间中,永远被“无面人”窃视着,而自己却一无所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爱丽受到“无面人”的监视、管理,其实正是承受着“近代”这一装置的暴力侵袭。
二位学者的指向十分明确。“近代”突进到21世纪的今天,世界已经发展成从穷人到富人都离不开携带电话的数字化时代;是一个可以忘记汉字怎样写,却不能不知电脑怎样打的时代;是一个只要把自己的名字打入网络,全世界都能找到你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你可以不用出门便能在网络上购物,与人交流,便利至极。可是,在这样高科技的“先进”时代里,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它们有形无形地困扰着人类的生存。
村上在小说中写道:“连锁店里端出来的鸡往往喂了莫名其妙的药物,像催生素之类的东西”[5]7; “钢铁出口倾销问题;纠正日元骤然走高的政府对策;母亲带着两名幼儿自杀;往汽车里浇汽油放火,整个儿烧焦的汽车图像,还在冒烟;街上差不多已经开启圣诞节商业大战了”[5]148;等等。在全球化的今天,恐怕每个国家的读者都很难说这些描述与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可是,村上却将问题的焦点对准了物质繁荣背后的“系统”问题。
作品描述高桥在便利店购物的行为时,十分巧妙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近代”社会的视角。
高梨盒装低脂肪牛奶袋放在冷藏柜里。高桥一边轻轻吹着《天黑以后的五点俱乐部》主题曲的口哨,一边在物色牛奶。他没带东西。伸手拿起高梨低脂肪牛奶,但低脂肪这点让他蹙起眉头。对他来说,这甚至是涉及道德核心的问题,而不单单是牛奶脂肪多少的问题。他把低脂肪牛奶放回原来位置,拿起一盒普通牛奶,确认保鲜期,放入筐中[5]73。
高桥与白川一样,都是生活在现代都市的普通市民,但在对待低脂肪牛奶这一点上,显示了两者的不同。“低脂牛奶”是指减少了脂肪含量并添加了脱脂奶粉的“牛奶”,味道较淡,但热量低,成本也比普通牛奶低。多余的脂肪则可以用来生产黄油、奶酪等加工产品。这种饮品是工业、商业乃至管理等全都系统化的“近代”社会的典型象征。高桥不满意“低脂肪”,认为这是“一个涉及道德核心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说明他对卷入这个系统乃至“装置”的结构之中深感担忧[19]。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1931—2003)对所谓后现代社会有着十分深刻的观察和洞见,他对人们的时间观念与近代社会之间的关联性作了如下评述。
在芒福德的著作《技艺与文明》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被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20]14。
钟表的发明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推进了人类社会的秩序化,然而技术和文明也为人类带来了副作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然生活规律被钟表所带来的分秒的世界所替代,人工的、人为的东西变成自然。于是《天黑以后》中的人物,或者世界各地的读者自己,在享受着物质上的愉悦时,天黑以后却入不了眠。这种严重违背人体自身规律的行为及现象,不能不说是对人性的打击和毁灭,也是“近代”社会的阴影与危机。
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白天需要辛勤地工作与学习,当天黑以后,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时,孤单、寂寞、无助、不安会同时侵袭而至。此时,人们往往会感觉到同白天截然不同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那是一个想放松、想宣泄白天的压力,想向朋友亲人倾诉自己的苦恼,想消除和亲人之间隔阂的自我。
弗洛伊德1929年出版了《文明及其不满》一书,指出对“近代”社会的巨大技术进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困境。
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及其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步……虽然这种新近获得的掌握时空的能力和这种对自然力量的征服满足了人类千万年来的渴望,但是这些成就并没有增加人们希望从生活中获得的令人快乐的满足,也没有让人们感到更加幸福。如果认识到这一事实,我们应该满意地得出结论,即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是人类活得幸福的唯一先决条件,正如它也不是文化奋斗的唯一目标[21]138。
科学与征服自然的确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但是它们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感,100年前的弗洛伊德如此认识,可以说十分深刻,直到今天仍然是振聋发聩。这种认识与生活在现代发达国家日本的村上春树有共同之处,不过后者已然超越了“技术控制自然”这一视野。
在村上笔下,作品中的登场人物,玛丽、爱丽、高桥、蟋蟀甚或白川都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着种种的压力和苦恼,虽然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一样,但也都是“近代”压制之下的产物。例如,尽管在“阿尔法城”工作的小麦和蟋蟀用的是假名,但无论“小麦”还是“蟋蟀”实际上都属于被捕食的对象。也就是说,村上给她们取的名字有着象征意义,象征她们都试图远离社会的环境中,努力逃离要把她们捕食的某种社会系统或装置。问题在于,生活在“近代”的个人都有他们的难言之隐,都有自己的无奈和困境,但是为什么却都无法逃脱呢?对此,村上借用小说人物高桥的分析,给出了答案。
一个人,无论他是怎样一个人,都将被巨大的章鱼一样的动物紧紧抓住吸入黑暗之中,不管出于怎样的理由,那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场景[5]84。
杰·鲁宾十分关注高桥的这段话,认为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巨大生物”的某个部分,二者已经成为一体,就像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一样,注视着所有的东西和人,而每个被“监视”的人实际上也可以借此观察另外的个体[22]392。由此而言,在一个到处设置摄像头的“近代”社会及技术无比发达的“系统”中,已经化为“巨大生物”一部分的人们既是这个“系统”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如同打人者的白川既是牺牲者同时也是加害者一样,“近代”社会的个体其实同时扮演着牺牲者和加害者的角色。面对“近代”这一“系统”或者“生物”时,作为社会一分子的我们,似乎更应努力承担某种责任。只不过,人们在面对邪恶和黑暗时往往持有本能的恐惧,从而无法从其中逃脱。
1989年,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之后撰写了第一篇短篇《眠》,开头一句“17天,我不曾合眼。17个白天,17个黑夜,无眠的世界,你能做些什么?”[23]1不禁令人感到了一种与《挪威的森林》截然不同的恐怖气息。杰·鲁宾对此有着十分锐利的评价。
《眠》是个真正的转折点,一个新层次的标志,几乎完全丧失了旧有的冷静和疏离感,是转向恐怖和暴力的清楚标志,这种因素看来已逐渐成为村上作品不可避免的重要内容,他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这是身为一位日本作家必须恪尽的职责[1]187。
通过描述恐怖和暴力,展示作家恪尽的职责,杰·鲁宾的评价点明村上文学与暴力的深层次关系。在《天黑之后》中,白川殴打中国女性,显然是一种表面性的肌肉式暴力,也可说是看得见的硬暴力。然而,村上春树的着眼点并不在此,其作品中真正令人感到窒息的是无时无刻无所不在的“近代”及其系统的软暴力。
《天黑之后》提出的问题及所包括的内涵,较之男女之间的恋爱故事更为深远、广阔,更具有普遍性意义。村上用轻淡的笔墨勾画出了一个世界,给予读者以深深的共鸣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作者对“近代”社会那冷彻而犀利的反思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四、结语
村上在《天黑以后》中借用法国电影《阿尔法城》的隐喻,通过叙述二重奏的创作手法,立足于“近代”这一坐标,去观察和把握当代社会和各种事件,质疑既有的善恶标准,探讨历史记忆与现实、未来的关系,在此过程中,表明了自己对日本乃至世界现状、人类未来的担忧和思考。
在村上作品中,对恶、暴力的描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恶主要表现为非日常性的、绝对的恶,如《寻羊冒险记》中的“先生”、《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夜鬼”、《奇鸟行状录》中的剥皮鲍里斯和绵谷升、《地下》中的奥姆真理教事件和《海边的卡夫卡》中的“父亲”或琼尼·沃克;第二阶段的恶大体表现为日常性或普通人的相对的恶,主要体现在《天黑以后》中的白川身上。对于绝对的恶,村上将其归因于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体制,即“国家暴力性”,由此可见村上春树有着可贵的内省精神和历史责任感。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暴力与恐怖构成了《天黑以后》这部作品的两个主体元素。村上笔下生活在“近代”的这些人物,显示了孤独和苦痛的心理状况,作为高度发达的“近代”人的悲哀感跃然纸上[24]。他们如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世界尽头”,或者《阿尔法城》的数学式集中处理一样,生活在了无声息、冰冷刺骨的“系统”中。科技日趋发达,然而人却逐渐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真实意义,逐渐沦为“系统”的傀儡。
然而,正如村上春树为《寻羊冒险记》这部小说的命名所显示的那样,他要告诉读者:追寻一只神秘的羊实际上暗合英文Wild-goose chase,注定是一场荒谬而徒劳无益的追求[1]89,101。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天黑以后》的最后,看到高桥以超然、勇敢的态度挑战黑夜,而玛丽也从黑夜中找到了久违的温暖并试图感化姐姐。
村上春树秉承了自己一贯注重人性与现实社会关系的风格,目光须臾不曾离开人类灵魂深处的善与恶这一终极问题。就此而言,他对于人性恶亦即“本源恶”的思索其实超越了人本身的视野,而是将视线对准了更为普遍的“近代”及其系统:只要人生活在“近代”这个世界,就要面临陷入黑暗时候的恐怖和无助,面对日益发达的科技文明,人之为人的真实意义究竟何在?如何避免沦为“系统”的傀儡呢?对这些问题,村上及其作品构成了一种警示、一种呐喊。应该说,村上春树并不悲观,他始终在探讨如何破局,如何走出“近代”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