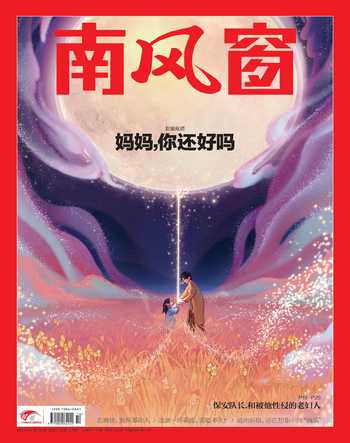如何看待美债问题?
谭保罗

当地时间4月25日,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一季度核心PCE(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价格指数季环比增长3.7%,超出此前预期的3.4%。换句话说,美国的通胀依然没有被降下来。这个原点将影响到很多财政金融政策的实施,并将对全球产生广泛的外溢效应。
过去一年,全球很多投资者都在焦急地等待美联储“降息”。现在,愿望再次落空—至少是暂时落空。
在整个三四月份,美联储的说法都富有外交辞令的色彩。比如,“正在寻找通胀稳步下降的迹象”,或者“在抗通胀方面缺乏更多进展”。其实,美联储的表态已经很明确,暂时不会降息,他们必须先解决这个逼向4%的通胀问题。因为,2%才是美联储在通胀率上的常见目标。
降息还是不降息,很多人会想到其对股市的影响。一些美股投资者早已提前入手美股蓝筹,特别是几大科技股,等待着美联储降息之后的新一轮大涨。全球其他市场的投资者也在各自的母国市场重复这样的操作,他们认为美联储如果推动2024年在新冠暴发后的又一轮降息,将为全球所有市场带来充足的流动性外溢,从而推高很多经济体的股市。
除了股市,全球债市也在时刻牵挂着美联储的“降息”。实际上,美元债券市场远比股市更加需要一次降息。而且,这事关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政府融资问题。
股市,还是债市?
降息希望的暂时落空,对全球股市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以美股为例,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美股至少经历了两轮上涨,每一轮都伴随着一个科技概念。
第一轮美股大涨的推动力,是特斯拉为代表的新能源或者智能汽车概念。特斯拉在2020年经历了一轮大涨,之后回调,在2022年再次大涨,其间,马斯克数次问鼎全球首富。第二轮美股大涨的推动力是AI概念,以英伟达为代表,相关的科技股普遍上涨。衣服只有皮夹克,个子也不高的黄仁勋,突然成了全球科技界最厉害的男人。
在2020年疫情暴发之初,道琼斯指数才2万点出头,而2024年4月底,已经接近4万点。也就是说,美联储为了应对通胀,实施偏紧的货币政策,收紧了流动性,但对美国股市的影响并不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两轮科技概念的崛起,让全球美元加速回流美国,来到美股追逐科技股,从而有效对冲了货币相对紧缩给市场带来的负面效应。
然而,债券市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2022年,美国的通胀率一度超过7%,于是美联储启动加息,新冠疫情暴发后的新一轮紧缩政策开始了。利率的走高,对债券市场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首先,债券的发行者在发行债券的时候,需要承担更高的票面利率。
另一方面,加息等同于向市场提供了一个未来利率的上涨预期。这样一来,投资者在购买债券(融出资金)时将更加谨慎。因为,当他们认为未来利率会更高,那么将持币待购(债券)。于是,二级市场中现有债券的需求降低,价格就会下降,债市的交易活跃度也会受到影响。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加息和高利率的环境,对债市都是一种伤害。尤其对融资者来说,很难说是一件好事。在美元债券市场,美国财政部背后的美国政府无疑是最大的融资者之一。截至2024年3月,美国国债存量已经突破34万亿美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政府可能是西方资本市场中最大的债券融资主体。
从2023年开始,不断有消息称,美国国债出现了“发行难”。这种说法略带夸张。实事求是地说,美国国债依然是全球资本市场中的高质量资产,它的收益率一直都是全球利率定价重要的“锚”之一,这个状况暂时还不会改变。而所谓的“发行难”,更多是指发行利率的走高,发行者必须支付更高的利息,投资者才愿意购买债券。
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在2023年8月,美国一次两年期短期国债发行的票面利率竟然达到了5.024%,创下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票面利率超过5%,这意味着,如果发行1000亿美元的债券,假设一年付息一次,那么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就超过了50亿美元。
除了股市,全球债市也在时刻牵挂着美联储的“降息”。实际上,美元债券市场远比股市更加需要一次降息。
而过去,类似短期国债的利率要低得多。假设过去是3%的票面利率,那么就等于现在要每年对债券投资者支付20亿美元以上的额外补偿。考虑到美国国债巨大的发行量,如果利率依然保持高位,推高债券市场的整体融资利率,那么对债券发行者来说,仅仅是利息一项,就已经是极其沉重的负担,更不要说未来的还本问题。
也就是说,更低的利率环境对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来说,无疑是有利的。因此,美国金融市场的大多数“利益相关方”—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以及美国政府在内,都希望看到美联储降息。他们要么希望低利率助推资产价格走高,要么希望降低债务的融资成本,改善融资环境。
然而,美国独特的财政金融体制,尤其是美联储盯紧失业率和通胀率两大指标的历史传统,决定了“利益相關方”的想法,并不一定能够马上兑现。美债市场的未来走向,依然是未知数。
不是阴谋,是市场
4月4日至9日,美国财长耶伦访问中国。美国财政部是美国政府发行国债的代理人,财政部首席长官的访华,被一些观点解读为,美国需要“向中国借钱”。
在逻辑上,这种解读有一定的自洽性。截至2024年3月底,美国国债的境外持有者中,日本、中国和英国位居前三。日本持有美债在1.2万亿美元的水平,中国不到8000亿美元,而英国持有规模刚超过7000亿美元的水平。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特殊时期,对耶伦访华一事,不应做过多评论。但我们不能忽略,美国国债不一定是严格意义的“好资产”,可横向对比全球金融市场的主权债务,那么很容易发现,它至少是全球大型主权基金在配置巨额资产时,并不多的选项之一。换句话说,买美债,对大家而言是一种相对无奈的选择。
在1990年代之前,美债在全球的主权债务中的地位,并非如同现在般一枝独秀。对那个时代的全球投资者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强大,那么它的主权债务往往会被认为是优质资产。美国自然不用说。其他国家,比如联邦德国发行的债券,也一定是投资者眼中的抢手货。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苏联作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债务市场融资也不难。

这是因为,西方投资者进入全球债务市场,其第一目的是赚取利息,而不是盯着意识形态不放。于是,苏联依托强大的国家信用和石油等自然资源禀赋,能够很通畅地从国际债务市场融资。苏联解体的时候,留下了超过900亿美元的债务。换个角度看,这既可以说苏联“举债度日”,也可说国际投资者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信用,特别是其对国内资源的超级掌控能力和征税能力。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同样被国际投资者信任。在很多投资者看来,苏联的GDP曾一度是美国的六成到七成,继承了苏联衣钵的俄罗斯,如果通过结构性改革,未来的经济潜力无穷,是值得信赖的债务人。
然而,1998年,俄罗斯却宣布主权债务违约,给国际资本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一次违约,间接地导致了美国最具明星效应的资产管理公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给华尔街和全球的投资者上了沉重的一课。之前,很多国际投资者认为,政府强大即意味着主权债务低风险或者零风险。之后,这种信仰破灭了。
由于各国财政没有统一,欧元区的经济强国无法统一发债。尽管欧元币值相对稳定,但热衷于发行欧元债的往往是欧元区的经济弱国,无法满足全球大型机构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需要。
1990年代是一個特殊的时间通道,国际资本市场中的优秀主权债务融资者,变得越来越少。除了俄罗斯有了违约记录之外,另外一些优秀的融资主体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中欧和西欧,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合并后,德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后来,欧元区成立。由于各国财政没有统一,欧元区的经济强国无法统一发债。尽管欧元币值相对稳定,但热衷于发行欧元债的往往是欧元区的经济弱国,无法满足全球大型机构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需要。
当全球主权债务的优质发债主体越来越少,美国国债才有了一枝独秀的可能性。可以这样说,美国国债之所以成为全球机构投资者在配置债务资产时的重要选择,是市场演变和市场选择的结果,并不是什么华尔街搞的“阴谋论”。
当然,美债并不会一直都是其他国家配置外汇资产的理想选择。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很多变化正在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和日本近年来不断增持美债,超越中国重新成为美债第一大境外持有者不同,中国对美债一直都处在不断减持的通道之中。2014年,中国持有美债规模超过1.3万亿美元。此时,是中国持有美债规模的顶峰。此后,中国持有的美债规模就在不断降低。目前,中国持有的美债不到8000亿美元。
与之对应的是,截至3月末,中国已连续第17个月增持黄金储备,目前中国黄金储备估值已经超过1600亿美元。另有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我国央行的黄金净购买量在全球央行中排名第一。
美债,不过是一种金融资产。它的发展和崛起,固然有国际政治博弈的因素,但更多是全球金融市场自然演化的结果,是全球主权债务投资者在经历多次剧烈市场冲击之后的选择。它有它的盛衰周期,无论这个周期有多长,我们都不应该以“阴谋论”的观点去看问题,而是应以金融常识去洞察变化。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外汇资产配置,正朝更多元化、更安全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