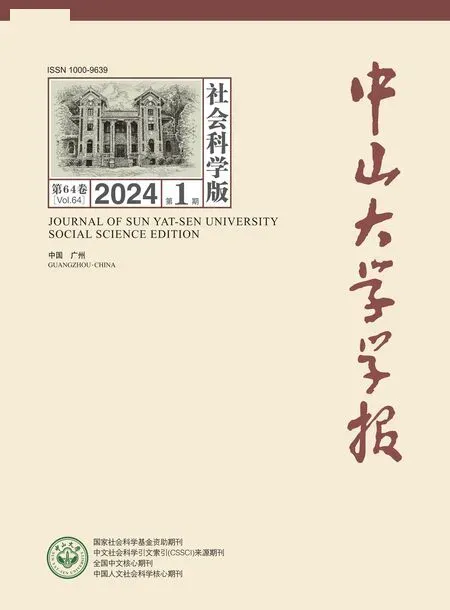晚清中外防疫交涉及其影响 *
杜丽红
晚清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在成为世界贸易网络一员的同时,也受到全球疫情的影响。由于中国与西方在何时防疫以及如何防疫问题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当发现疫情时双方开始围绕如何防疫的问题展开交涉,防疫就此成为外交议题。中国一般认为,防疫远没有治疫重要,主要在疫情暴发之后采取治疗的措施;西方各国重视的是如何通过清洁卫生预防疫情的暴发,疫情暴发之后不以治疗为主,而是将染疫者与健康者隔离开来。在中外人士共同生活的口岸城市出现疫情的时候,外国势力会就采取何种防疫措施与中方进行交涉和争论。概言之,疫情是防疫交涉的催化剂,而防疫交涉的基本内容则是列强以外交手段强迫中国按照西法防疫,中方则坚持传统防疫,采取各种策略进行软对抗,即表面上采取相似的组织和制度,但拒不接受西法防疫的措施,而将之化解为相似之道。
“西法防疫”并非简单的防疫方式,而是建立在西方医学知识体系之上,由一系列组织和制度构成,并受到国家法律规章的保障。以西法防疫为中心的防疫交涉,引发了中外间政治冲突和文化观念之争,不但关系到制度和组织层面的卫生行政,而且与医学知识和文化习俗密切相关,结果促使西法防疫传入中国,进而影响到中国在一些开放口岸建立卫生行政机构。晚清防疫交涉的参与者众多,不仅有力主西法防疫的各国驻华外交人员、外国商业组织和租界当局,还有既排斥西法防疫又惧怕外来压力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以及完全排斥西法防疫的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故而防疫交涉涉及面广,既有国家层面的外交斗争,也有地方社会层面的交涉和文化抵制。
中外防疫交涉实质上是中西之间的碰撞,源自西方列强强制要求清政府采取西法防疫,由此引发中国官民对此举的反思和应对,由于这一碰撞是在有着丰富抗疫经验的中国社会进行的,须面对中华传统医学和文化观念的挑战和质疑,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过程。本文拟通过考察晚清中外防疫交涉的演化过程,分析其前因后果,揭示出中华文化在面对防疫交涉时的韧性,即使被迫采纳西法防疫,各方仍设法维持中国的行政主权、人道主义精神和医学理念。需强调的是,近代中国卫生防疫如其他事务一样难以摆脱列强的干涉,以迫使清政府推行西法防疫为目标的防疫交涉,展现出列强通过强权外交对若干开放口岸的卫生防疫施加影响的侧面,这是晚清卫生防疫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内容①近代中国卫生防疫制度建立的问题早已为学界所关注,形成了不尽相同的理解、解释和判断。有的采用近代化研究视角,聚焦于具体卫生制度的形成。见Kerrie L. MacPherson, A Wilderness of Marshes: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1843-189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日]饭岛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卫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東京:日本研文出版社,2000 年;[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有的侧重西方各国尤其是日本的影响。见刘士永:《“清洁”、“卫生”与“保健”——日据时期台湾社会公共卫生观念之转变》,《台湾史研究》2001 年第1 期;刘士永:《武士刀与柳叶刀:日本西洋医学的形成与扩散》,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12 年;杜丽红:《近代中国地方卫生行政的诞生:以营口为中心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9 年第4 期。余新忠从防疫机制强调了疫情和观念传播对近代卫生行政体制的重要影响。见余新忠:《清末におけtf「衛生」概念の展开》,《東洋史研究》2005 年第3 期;《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一、背景:西法防疫的扩散
19 世纪以来,人类交往和迁徙的增多为传染病在全球的传播提供了便利,霍乱和鼠疫交替流行。在帝国主义国家殖民扩张的加持下,西法防疫成为通行全球的瘟疫应对方法。然而,此时所谓的西法防疫不过是15世纪以来形成的一套以隔离、检疫为主要内容的防疫措施②15世纪以来,在对抗鼠疫过程中,欧洲各国在西方医学文化理念的支撑下,形成了一种长期有效的防疫措施,如给船只发放健康证和建立隔离所,政府监视来自被传染的地中海港口的船只,将它们隔离开,或拒绝它们进港。见Paul Slack, “Responses to Plagu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Implications of Public Health”, Social Research, Vol. 55, No. 3,1988, pp.441-442。。
早期,各国在传染病来源和性质方面少有共识,应对传染病的预防措施很简单。1825年,英国海港检疫隔离法案通过,要求船只离港或到港时,必须持有政府发给的健康证书(Bill of Health),对于发现鼠疫、黄热病、瘟热及其他传染病的船只,由海关负责检疫隔离。此后,检疫成为航运大规模扩张时代跨国海运的一项重要措施,各大港口纷纷配备了高效而简便的检疫设施,以博取旅行者和商人们的信任。面对传染病,人类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物理性防御:隔离和封锁③[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强朝晖、刘风译:《世界的演变:19 世纪史》I,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373页。。然而,这些措施实际让人们感到害怕与愤恨:健康的乘客害怕与染疫病人共处一室,商人们则愤恨于船只延误带来的巨额贸易损失。海港检疫隔离政策花费昂贵,且与英国自由主义信条相冲突,被人们指责为“野蛮的负担、干扰商业、妨碍国际交往、威胁生活以及浪费大量公帑”④Krista Maglen, “‘The First Line of Defence’: British Quarantine and the Port Sanitary Author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15,No. 3, 2002, pp. 413-428.。到1860 年代,英国实行包括检疫、隔离、消毒和监测在内的新检疫规则,并取得了显著成功,被称为英国模式。与此同时,为缩短隔离的时间,整个欧洲大陆都转向了检疫、通报、隔离和消毒等新检疫技术,用检查和治疗无症状乘客取代简单检疫,并对病患及其财物和居住地进行清洁和消毒。此后,政府设立一系列检疫站,负责检验人群,焚烧尸体,收容染病者⑤Peter Baldwin, 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 1830-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p.151-188.。
随着病因学的发展,对传染病的应对出现了跨国界的预防战略趋同。19 世纪中叶起,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蒸汽轮船和铁路交通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成为联系日益密切的整体,而传染病的传播随之速度更快、范围更广。为此,欧洲各国加强了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自1851年开始就防治霍乱的传播召开了8 次国际卫生大会,在“文明欧洲”和“东方”之间增加了国际主义、信息技术、现代科学以及现代行政机构等新的文化鸿沟。这种现象正如学者们揭示的那样,海港检疫实际上代表的是以对抗疾病(Against Disease)的全球联合取代通过疾病(By Disease)的全球联合①Emmanuel Le Roy Ladurie, “‘A Concept: the Unification of the Globe by Disease’”,The Mind and Method of Historian, Brighton, 1981, pp. 28-91; Valeska Hube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Globe by Disease? The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s on Cholera, 1851-1894,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 49,No.2, 2006, pp. 453-476.。
在欧洲帝国野心勃勃地进行政治、军事和商业扩张的过程中,疾病及其传染被视为最根本的危险,所以医学不仅是帝国的“工具”,而且是欧洲殖民统治的一种实践形式。疾病预防的需求倒逼帝国建立起更加系统的卫生和医学制度,“卫生秩序”成为帝国政治秩序的一个重要侧面②Roy MacLeod, “Introduction”, Disease, Medicine and Empire: Perspectives on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an Expans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p. 3-4.。西法防疫虽然并未成熟,却是人类混合使用医学和传统手段,对一些历史上曾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的传染病展开的阻击。尽管这些措施未能使传染病彻底绝迹,但基本遏制住了其迅猛的传播势头③[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强朝晖、刘风译:《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I,第350—351页。。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西法防疫成为殖民扩张的工具,成为一种殖民政治话语,成为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成为构造欧洲自我同一性的工具。
19世纪70年代起,科学医学介入防疫,西法防疫方式被赋予了科学的内涵。然而,科学的进步是缓慢的,直到二十多年后,各界在科赫研究的有效性基础上,才基本实现了新检疫原则的国际趋同④Peter Baldwin, 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 1830-1930, p190.,但人类仍在继续寻找对抗传染病的有效工具。如艾伯斯指出的那样:“尽管在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中,人们在识别鼠疫致病细菌和传播方式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积累了新知识,但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现代医学权威真正采取的防疫措施还是传承自欧洲的健康委员会,也就是和15世纪和17世纪第二次鼠疫世界大流行时一致。”⑤[美]约翰·艾伯斯著,徐依儿译:《瘟疫:历史上的传染病大流行》,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第85页。
受西法防疫全球传播的影响,清政府开始在个别开放口岸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进行检疫。187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考虑,在港口疫情暴发的时候,像中国香港或日本那样,设立检疫制度⑥R. Alex Jamieson,“ Memo.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Yang-King-Pang and Hongque Settlements at Shanghai”,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Mar. 22, 1870.。直到传染病来袭,海港检疫才真正得以执行。1873年,暹罗和马来半岛出现严重霍乱,将中国置于疫情的威胁之下。由于大量中国苦力往来于厦门与暹罗和马来半岛,厦门税务司休士(Mr. George Hughes)预感到有必要预防霍乱从厦门港传入。为此,他制定了三条简单的卫生规定,要求来自新加坡等霍乱流行港口的船只必须在指定地点下碇,等候海关医官的检查,且规定没有海关同意禁止卸货和卸客⑦“Circular No.4304 (Second Series)”,吴松弟整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第248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版),2016年,第597—598页。。同年8月29日,上海领事团会议讨论通过了上海海港卫生规则,得到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批准⑧“Meeting of Treaty Consul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Sep. 6, 1873.。根据中外合作的原则,上海制定出《上海口各国洋船从有传染病症海口来沪章程》,其中规定:道台任命海关医官负责港口卫生事宜,在征得道台和领事团的同意后海关医官可以征收检疫费用①《上海口各国洋船从有传染病症海口来沪章程》(1874 年7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档,U1—16—2877。。对清政府来说,此时的海港检疫不过是在海关任职税务司的外人要求举办的一项海关业务,并不代表国人认可其是有效的防疫手段。中国人一直将瘟疫视作是上天的惩罚,“凡疫疠之作,其起也无端,其止也亦无端,大抵天意使然”,故往往求神拜佛,打醮修斋或请神巡游②《论防疫之禁令》,《新闻报》1894年5月24日,第1版。。无论是精通医术的江湖郎中,还是各地官僚,没有人相信疾病是由传染所致,更无人意识到对感染者和疑似病患采取隔离措施的必要性③[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强朝晖、刘风译:《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I,第362页。。
因而,港口的卫生规则并未得到有效的执行,时人指出:“这些规则是被没有经验的人草拟的,是无效的。即使被采用,也提供不了保护。”④“Sanitary Precaution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April 15, 1879.1882 年12 月21 日,一位名为Audax 的读者在给报纸的一封信中,控诉上海港并未对载有天花患者的船只采取任何的防疫措施。虽然船长遵从规则,给吴淞港发了电报,报告天花患者的状况,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回电或信号,客货都如常卸载,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这表明在上海这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卫生规则就是一个笑话,对那些执行港口卫生规则的人来讲,挂黄旗几乎没有效果⑤Audax, “A Serious Accusation”,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Dec. 27, 1882.。此后情况并未好转,1887年上海的英文报纸感慨道,上海从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建立一套检疫制度⑥“Quarantine and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Feb. 2, 1887.。
在西法防疫扩散的背景下,中国海关在海关税务司和各国领事们的主导下雇佣外国医生,开始办理海港检疫。然而,海港检疫不过徒有其名,敷衍了事,基本未对中国人产生直接影响。直到1894年香港鼠疫暴发,港英当局坚决采取西法防疫措施,引起英国人对华人抗拒西法防疫的不满,也让中国官民感受到西法防疫的严苛,进而正式开启了中外防疫交涉。
二、香港鼠疫与防疫交涉的开启
香港鼠疫期间,西方列强除在管辖范围内严格执行西法防疫外,开始采取外交措施干涉中国的防疫事务,防疫上升为中外政治交涉的议题。防疫交涉开启的原因在于,列强意识到中西处理疫情的态度和方式不同,希望通过交涉促使清政府按照西法进行防疫。清朝官员则认识到西法防疫的种种弊端,并积极应对列强防疫交涉,尽力避免其强制性隔离消毒措施给中国社会带来混乱。
当香港发现鼠疫后,列强在亚洲势力范围内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预防疫情的蔓延。1894年5月11日,香港洁净局颁布《防疫章程》,明确规定洁净局有权将染疫者迁徙隔离在医船或专处,对患疫者的居所进行消毒或焚烧,埋葬患疫毙命者,以及患疫者应向差馆或官署申报⑦《香港治疫章程》,《申报》1894年5月22日,第10版。。5 月底,澳门要求洁净沟渠、保持卫生,并派医生对所有来自广州或香港的乘客进行检验,“发现有疔疮疫症,或疑其患此症者”,或不准其登岸,或用火船拖带出埠⑧《澳门防疫》,《申报》1894年6月1日,第9版。。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颁布章程,规定如有轮船由香港驶抵西贡,“须照例泊于禁界内6日,方准客货登岸”⑨《选录西报》,《申报》1894年5月31日,第9版。。
港督威廉·罗便臣(William Robinson)出示晓谕:“患疫者特归一所,毙命者迅速掩埋,并将房屋水洗药熏,不许挠阻洁净。各总差入屋巡查,并迁徙病人或死者,及洒扫房舍,熏除秽气等事。”港英当局强硬执行的这些西法防疫措施与中国人习俗相去甚远。尤其是诸如隔离病人、消毒或烧毁患者所住房屋之类的措施,引起了生活在当地中国人的不解和恐慌,进而激发了强烈的反对意见。香港绅商高度关注防疫事务,与港英当局商议改进之策,改由东华医院分局收容华人染疫者,并由华医疗治。不过,总督并未批准不许洁净局人员进屋查搜的请求,也未同意将医船上的病人搬往东华医院分局①《港疫续述》,《申报》1894年5月28日,第2版。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33页。。结果,严苛的防疫造成大量人口逃亡,6 月初香港回粤者每日不下千余人,有携眷来者,有结伴来者,有肩挑负担来者,有拖男带女来者,老的、幼的、贵的、贱的,纷纷逃避②《迁地避瘟》,《新闻报》1894年6月22日,第2版。。
时人在观察和经历香港防疫的基础上,形成了对西法防疫的基本认知。时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西法防疫不适用于中国人,“香港以洋法治华人,闯入船内,饮以药酒冰块,熏以硫磺,以致死者日众”;更明确反对“封仓禁人,不许来往”的隔离措施③《函复粤督查复香港瘟疫逐渐减轻琼州丹教士已饬保护》(1894 年5 月26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总理衙门档,01—37—001—03—003。下文所用总理衙门档案均出于此,不另注。。在时人看来,防疫不是政府的职责,而是社会的公共事务,一般应由善堂、同乡会等组织以施药和祈祷的方式应对,只有在疫情严重时才由地方官府主持拜神仪式。1894年3月,广州发现鼠疫后,地方官府与士绅合作,“凡祈骧医治之法无不举行”④《为广州瘟疫已减轻香港改用中医治法以本土流行事》(1894年5月28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电报档,2—02—12—020—0287。下文所用军机处电报档均出于此,不另注。。鼠疫暴发后,上而官宪,下而士民,“或诵佛经,或烧香药,不一而足”⑤《焚香肇祸》,《申报》1894年5月7日,第2版。。5月1日,广州府知府张曾敭督同南海县令杨荫廷、番禺县令杜友白在城隍庙设坛祈禳致斋3 日,不理刑名,并示谕各屠户不许宰杀⑥《时疫未已》,《申报》1894年5月21日,第2版。。稍后,督抚司各员札饬南海、番禺两县令开释狱中百余犯人归家⑦《遇灾而惧》,《申报》1894年5月4日,第9版。。可见,西法防疫与中国传统防疫格格不入,遭到了官府和社会的集体抵制,被斥之为不人道。恰如“传统与现代化是水火不相容的,前者代表着人性,而后者代表着非人性”⑧[美]艾恺:《持续焦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第5页。。
然而,列强并不理会文化上的差异,反以保卫在华外人健康的名义直接对清政府防疫进行干涉,将之升级为外交层面的交涉事务,由此引起朝野上下对其可能引发内乱的担忧。香港鼠疫期间,中外防疫交涉主要集中在中央层面,外国驻华大使仅仅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防止疫情蔓延,尚未强迫其采取西法防疫。5 月25 日,驻华各国大臣领袖俄国公使喀希呢(A.P.Cassini)致函总理衙门,要求告知“所得之病如何情形”,“贵国设有何法,或欲行设法之处”,从而“勿使瘟病布散华境”⑨《广东时疫流行请为设法》(1894年5月25日),总理衙门档,01—37—001—03—001。。次日,总理衙门将李瀚章防疫办法告知喀希呢,“已饬局散药医疗,官绅合力,凡医治之法无不举行”⑩《函复粤督查复香港瘟疫逐渐减轻琼州丹教士已饬保护》(1894 年5 月26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总理衙门档,01—37—001—03—003。下文所用总理衙门档案均出于此,不另注。。此外,各国驻沪领事团和租界工部局直接跟上海道台交涉,要求采取防疫措施⑪。
面对升级为外交事务的防疫交涉,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不得不开始关注防疫。由于,西法防疫遭到广大民众的坚决反对,官员们更担忧可能由此引发排外内乱。由于香港严苛防疫,广州善堂绅董愤懑地表示,“再烧香港民房,即焚省城、沙面以图报复”。李瀚章密饬文武员弁,严拿造谣之人,禁止张贴,并添派兵勇保护租界,以期无事①《为香港瘟疫情形事》(1894年6月18日),军机处电报档,2—02—12—020—0384。。军机处电知此事后,致电李瀚章,“港官焚民房逐疫,省城骚动,欲与洋人为难”,明确表示“港疫不息,民心总不能清”,令其加意预防保护②《为香港瘟疫设法派船接回内地医治事》(1894年6月16日),军机处电报档,2—02—12—020—0377。。
然而,对于洋人的交涉不能不有所回应,于是官绅提出了华洋分治的策略。其实,华洋分治是中外双方的共同选择,两者在这点上有着惊人的共识,但其背后所遵循的逻辑却各不相同。清朝官民在经历或见证过严苛的防疫措施后,切实了解到西法防疫的具体内涵,指责其毫无人道,违背基本的人伦天理,明确提出“华人用华法,洋人用洋法”。李瀚章表示:“香港时疫,洋官用洋法医华人,岂能不毙?”③《为香港瘟疫设法派船接回内地医治事》(1894年6月16日),军机处电报档,2—02—12—020—0377。与之相对,外国人在见证清朝官民的防疫举措后,虽然指责他们的愚昧落后,但同意了“华人用华法,洋人用洋法”之方案。港督罗便臣批准了东华医院绅董有关香港民众要求回省城治病的禀请,并表示“自后如有患疫之人迁往玻璃局,由华医调理,不复舁赴医船医”④《香港疫信》,《申报》1894年6月2日,第2版。。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亦采取华洋分治的措施,同意不信西法者转而就华医,“乐就西医者,则有西医诊治,乐就华医者,则有华医诊治”⑤《继防患未然说》,《申报》1894年6月8日,第1版。。自此,中外双方在防疫交涉中的策略基本形成,清政府视西法防疫为洋人专用之法,不适合中国社会,西人则意识到必须采取外交措施才能强迫清政府执行西法防疫。防疫交涉迫使清政府提出采取华洋分治,华人用华法也就意味着当疫情发生的时候,清政府必须与洋人共同采取措施应对疫情。至于采取何种措施,则在此后的防疫交涉中日渐明晰。
三、交涉深化与自办防疫
香港鼠疫之后,挥之不去的鼠疫和霍乱交替威胁着中国沿海及陆地各口岸。与此同时,科学医学快速发展,列强愈加坚信西法防疫能够很好地控制疫情的蔓延。更重要的是,甲午战败后,列强加深了对华侵略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干涉地方防疫事务,要求地方官推行西法防疫。因此,防疫交涉的范围和深度都得到增强,各地领事要求地方官府遵照西法防疫,各地官员虽严词拒绝,但迫于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又不得不遵办。为应对列强的交涉压力,清朝官民力主自办防疫,坚持中西有别,要求洋人用洋法、华人用华医。由于列强在各地的影响力不同,这些策略在各地有着不同的运作形式。
19 世纪末,列强屡次要求清政府在港口和陆地边界地区采取检疫和防疫措施,防疫交涉成为列强对华外交的重要事务之一。1897年2月18日,俄国公使巴布罗福(Pavlov Aleksandr Ivanovich)照会总理衙门,指出英属印度暴发瘟疫,为防瘟疫传入喀什等地,要求中国仿照各国进行西法防疫,在中印交界处留验入境人员,“不准骤入华境,俟过一定日期确知并无瘟疫,方准入境”,对其所带物件进行消毒,“应量力烟熏,或用他法,以除瘟萌”⑥在电文中,俄公使明确了各国采取的防疫之法,即:“以防瘟疫传入各国境内,并在各口岸暨交界处安设查瘟疫局,由凡有印度说来之人在该局暂行留住,以便确验有无瘟疫,所带之物用药除瘟。”见《印度瘟疫盛行宜预防传入喀什噶尔希示复由》(1897年2月18日),总理衙门档案,01—37—001—04—001。。总理衙门22 日电知新疆巡抚饶应祺照办⑦《照复喀城设局防瘟已电疆抚照办》(1897年2月22日),总理衙门档案,01—37—001—04—002。。同年7 月8 日,驻厦门、福州的各国领事致电总理衙门要求颁布检疫规则,聘请西医检查船只。东海关道锡桐、东海关税务司贾雅格与各国领事议定章程7 条,于8 月4 日开办⑧《东海关呈送厦门各处奉行检疫规则经费清折》(1897年10月6日),总理衙门档,01—37—001—05—001。。1908 年7 月,厦门、福州、台湾恶疫流行,各国领事致电外务部要求实行检疫,规定自此三口到烟台船只必须请西医检查,每艘船收取25两医费,由关道筹款付给①《为厦门等处检疫用款可否由俄商码头地价内动支事》(1897年7月9日),军机处电报档案,2—07—12—023—0295。 《卫生施医》,《申报》1899年11月25日,第2版;《营口卫生所来函》,《申报》1900年1月2日,第3版。。从内容来看,这些交涉仅仅要求海关和陆关按照西法防疫的程序进行防疫。
随着西法防疫的施行,中国官民对其利弊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首先,时人意识到中西对于疫的认知是不同的。华人多将疫气视为时症,但并非不可治,而西人则“以此种症候皆名为疫,见之甚畏,防之甚严”②《与客论验疫》,《申报》1902年8月5日,第1版。。其次,中国人认为西法防疫非但不是善政,反而是一种虐待③《论争回西牢押犯事》,《申报》1905年8月13日,第2版。。再次,时人对西法检疫多持怀疑的态度。两广总督陶模认为不仅不能以西法治华人,而且质疑禁止运柩回乡的防疫措施④《据广东各善堂禀请旅港华民染病者准其回乡调理》(1901年7月3日),总理衙门档,01—37—001—03—006。。御史张元奇质疑“仅以行步、面色为凭”的验疫之法,指出“死后更将尸身焚化抛弃,不许本人眷属领回,稍与辩论,便遭殴辱”的做法不人道⑤《御史张元奇奏近年轮船进口验疫请咨各国领事变通办一折奉旨外务部知道钦此》(1903 年7 月31 日),“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02—14—014—03—009。下文所用外务部档均出于此,不另注。。考虑到中西防疫的差异,为应对来自交涉的压力,清朝官员提出华洋分治和自办防疫的策略。张元奇提出国人应由华官派医自检,不能授权于洋医。工部尚书陆润庠在给外务部的公文中提出:“与西人分段办理上船验病、入院调治,西人归西医经理,中人则归中医经理。”⑥《函送汪麟昌等禀诉吴淞验疫情形由》(1902年8月8日),外务部档,02—26—002—02—002。
那么,防疫交涉的具体状况如何呢?营口是列强通过防疫交涉,强迫地方官采取西法防疫的典型案例。1899 年7 月,营口暴发鼠疫,当地外国领事通过外交途径向地方官府施加压力,强迫地方官府接受西法防疫章程。领事希望各国能给总理衙门联合施加压力,“因为没有这些压力,中国地方当局无疑将像过去证明的那样顽固且故意阻碍”⑦“The Plague at Newchwang”,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Sep. 11, 1899.。事实证明,各国领事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8月17日,各国领事团公共会议拟定《营口防除疙瘩瘟疫章程》,提交给山海关道明保,结果被拖至9月8日才被婉拒⑧“Dr. C. C. De Burgh Daly’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ewchwang”, Medical Reports, 58th Issues, Shanghai: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00, pp. 20-23.。此举引起各国领事的不满,他们通过各自驻华使馆向总理衙门施压,要求其电饬营口地方官府按西法防疫章程防疫⑨《议定防疫章程请山海关道筹办由》(1899年9月12日),总理衙门档,01—37—001—07—006;《请电饬牛庄地方官会同各国领事妥定清洁章程以免厉疫流行由》(1899年9月12日),总理衙门档, 01—37—001—07—005。。接到总理衙门督饬其与各国领事妥筹办理的电令后,明保态度有所缓和,会见各国领事,“允妥定禁章”⑩《咨送各领事所拟防疫章程由》(1899年10月9日),总理衙门档,01—37—001—07—021。。
各国不仅要求中国严格按照西法防疫,而且要求中国政府直接办理,不能由旧有地方社会组织代办。根据章程,营口设立卫生局,由10人组成的卫生委员会控制,采取西法防疫:派医挨户查找病人,将患疫者送往医院收治;对患疫者房屋进行消毒;在土围各门派兵查验有无病人通过;要求各义庄、义地的暴露棺木一律瘗埋,不准再厝,患疫死者只能经扬武门送五台子义地瘗埋⑪。对此,营口商人表示坚决反对,提出国人自办防疫的主张,并得到了明保的暗地支持⑫《营口各号商欲仿照防疫章程自置买义地并开设医院以免外强干预请为立案由》(1900 年2 月21 日),总理衙门档, 01—37—001—08—001。。然而,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以寄存棺木处理尸体的办法,事实上便利了鼠疫的扩散①“The Plague”,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2, No. 2032, Dec.9.。中东铁路公司董事璞科第(D.D.Pokotiloff)呈文总理衙门,要其命令明保遵照西法防疫,协助俄国医生开展工作,说服那些坚持要修改条文的当地头面人物②《中东铁路沿革史》,[俄]谢·阿·多勃隆拉沃夫著,刘秀云、吕景昌译:《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2页。。营口自办防疫的主张就此被防疫交涉打压了下去。
不过,这一状况并未持续很久,自办防疫逐渐成为东北地方官应对日俄防疫交涉的重要策略。自日俄开始在东北进行侵略,卫生防疫就一直是当地中外交涉的重要内容。无论在营口还是在哈尔滨,地方官和社会组织遇到外国人干涉时,往往仿照日俄成立相应组织,采取一些类似的简单卫生措施,但都未真正大规模采用隔离和消毒的防疫方式。在鼠疫刚刚出现的时候,铁路附属地周边的城市仍然采取旧有策略应对日俄那些早已耳熟能详的外交措辞,早早成立防疫会,与日俄医官合作办理防疫。1910 年11月初,哈尔滨东清铁路公司与滨江关道于驷兴联系,要求派俄医到傅家甸查验,将接近疫病患者的人都送交医院③《俄员拟派医士在道外验病》,《远东报》1910年11月11日,第2版。。于驷兴立即成立滨江防疫会,其组织形式和规章与道里十分相似。于是俄国舆论认为,傅家甸官厅及自治会留意防疫,不仅通饬商民一律遵守卫生章程,而且“组织卫生局十分完全,如巡警局、自治会中外各医士,以及道里卫生局代表等皆参预其事”,因此“傅家甸不致盛行瘟疫”④《预防瘟疫之要》,《远东报》1910年11月24日,第1版;《滨江防疫之效力》,《远东报》1910年11月21日,第2版。。
然而,如俄医卜得白尔哥所指出的,滨江防疫会各种措施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模仿,由于对鼠疫有不同的认知,防疫会骨子里不愿意、也事实上无能力按照西法防疫。事后,于驷兴在总结办疫经验时亦承认未严格执行防疫章程:“此间调查、消毒、检验诸法,早经照章实行,惟小民安于自便,检查太严,辄相反对。绅商亦每称不便,办事员遂不免因此顾虑。”⑤《哈尔滨于道来电》(1910 年12 月3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锡良档,甲374—15。下文所用锡良档案均出于此,不另注。可见,地方社会自办防疫的策略在于,仿照外国人设立相似的防疫机构,却仍然恪守传统防疫办法,其目的在于既抵制西法防疫的非人道之处,同时也避免列强对国家主权以及人民生命造成侵害。
与之不同的是,上海由各行政机构共同参与建立起一套海港检疫体系,基本实现了华洋分治。1899年前后,江海关开设崇宝沙防疫医院,并颁布海口检疫章程,建立了以崇宝沙医院为中心的海港检疫体制,不仅有了专门的医院,而且有了一套消毒、隔离、治疗的机制。1899年,崇宝沙医院中分设华人和洋人养病所,并有专门妇女房间,由华医之妻照料。1901 年5 月后,上海口岸的检疫均由中国医士随同洋医前往验看⑥《上海验疫事据好税司复称办理情形并道署派员查看回报事妥协等语布达由》(1902 年8 月27 日),外务部档,02—26—002—02—027。。
直到1910 年11 月东北鼠疫暴发初期,华人才争取到了在公共租界自办防疫的权力。当月初,工部局因发现鼠疫毙命者而采取严苛的防疫措施,命令毗连铺面及周边的居民一律搬出,将房屋封闭,进行消毒和灭鼠⑦《工部局防卫鼠疫之举动》,《申报》1910年11月5日,第2张第1版。。结果引发了严重的风潮和骚乱:“殴西人,伤华捕,闭交易,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其势岌岌,殆不可以终日。”⑧《论英界检疫与华人治安》,《神州日报》1910年11月14日,第1页。工部局全体董事邀请华商领袖、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召开特别会议,很快就检疫问题达成协议,决定由国人自设中国公立医院,选派执有西医文凭的华医办理⑨《中西绅董议决检疫事宜之捷报》,《申报》1910年11月19日,第2张第4版;《工部局宣示防疫办法》,《申报》1910年11月21日,第2张第2版。。自此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防疫交给国人自办,但工部局卫生处仍负责租界内查疫的职能①《检查鼠疫之善后谈》,《神州日报》1910年11月25日,第4页。。双方达成妥协的基石在于遵循西方医学原理,无论是任用有西医文凭的华医,还是成立防疫医院,都采取以检疫、隔离、消毒为核心的西法防疫措施处理疫情。
香港鼠疫后,中外防疫交涉在口岸城市日渐扩散,其核心内容是明确要求清政府采取西法防疫。无论是中央级别的外交,还是地方级别的交涉,基本都围绕着具体防疫方式展开。面对来自列强的外交压力,清朝官民坚持中外有别,或主张华人由华医治,或自办防疫。这些应对之策反映了国人抵制外人干涉的思想,也成为外人不得不依靠防疫交涉迫使国人采取西法防疫的动因,结果造成防疫交涉日渐频繁。
四、东北大鼠疫期间的交涉与防疫
历时半载之久的东北大鼠疫,沿铁路线从哈尔滨蔓延开去,在很短时间内传至长春、奉天、天津、北京及华北各地,死亡相继,引发各界的恐慌。由于东北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防疫交涉贯穿整个防疫过程,清中央政府不得不面对来自公使团的外交压力,东北地方政府则面临来自同城的日俄势力的干涉,正如锡良所言:“防疫一事,主权民命攸关,办法稍未完全,贻害无所应止。”②《饬各道府厅州县电》(1911年2月17日),锡良档,甲374—26。清政府坚持以避免干涉为第一宗旨,要求各级政府把握防疫的主动权,处于领导防疫的核心地位,避免防疫主权的旁落。因此,避免外国直接干涉成为清政府在防疫交涉中的核心原则,而这一策略客观上起到了促使清政府采纳西法防疫的效果。需指出的是,避免干涉并不是东北大鼠疫过程中清政府才有的政策取向,而是晚清从中央到地方在处理涉外事务时所采取的一贯政策。无论是中央政府在处理涉外事务时,还是东北地方官府在处理相邻铁路附属地事务时,都将避免干涉作为重要目标。
在东北,防疫交涉一直是中外日常交涉的事务之一,日俄势力自然习惯于通过交涉强迫清政府重视防疫。究其原因,仍然在于中西医学和文化观念的不同。中医认为鼠疫并非不可治愈,或服药,或针灸,都可起到防疫的效果。西医则认为无法医治,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通过隔离、消毒、检疫等手段将疫情控制在特定范围内。无论是以锡良为代表的清政府官员,还是普通中国人,都对西法防疫持怀疑的态度。锡良对中国不能厉行西法的原因有着清楚的认识:“查各国防疫以断绝交通,严杜传染为要,着我国素无防疫之法,商民狃于习惯,对官府之禁阻交通,则以为虐政,每遇实行隔离消毒,百计抵制,谣诼繁兴,甚至疫毙之尸藏匿不报,以致蔓延未已,传染甚烈,实堪浩款。”③《致军机处电》(1911年2月16日),锡良档,甲374—46。施肇基在万国鼠疫大会致辞中描述了国人对于西法防疫的不满之处:“执行如此明显的粗暴工作,即尽快地把鼠疫患者与他们的家属分开,并移送鼠疫医院或其他隔离营等等,给政府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④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张士尊译,苑洁审校:《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年,第7页。
官员们心里非常清楚社会对西法防疫的抵触,“至以卫民之良法,疑为贼民之苛政”⑤《民政司张贞午司使亲临防疫会演说词》,《盛京时报》1911年1月20日,第3版。。此外,在疫情结束后撰写的疫事报告书中,防疫官员对社会各界反对西方防疫措施的根源作了深入分析,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西法防疫措施与中国人习俗不合,人民很难从内心深处接受。首先,焚化疫尸的举措与传统丧葬习惯不符。其次,强制诊治及隔离染疫者与民间忌医习俗不符。再次,断绝交通的举措与民间返乡过年的乡土观念不符。最后,隔离和消毒举措与人们的伦理观念相冲突①[清]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译,吴秀明、高岚岚点校:《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载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12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305页。。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列强在面对严重的疫情时,必然会展开防疫交涉,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强迫其采取西法防疫。
鼠疫暴发后,日俄两国遵循国际医学界对鼠疫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措施,在铁路附属地、租借地厉行防疫。与此同时,日俄积极与东北地方官府进行交涉,要求重视疫情,并采取相似的防疫措施,以避免疫情的蔓延。哈尔滨疫情逐步恶化后,俄国认为地方交涉方式已经无法迫使地方官绅遵照其意见办理,转而通过俄使与外务部的正式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即以武力干涉为手段威胁清政府,由中央政府以命令的形式让地方官府遵照办理。日本人则指责:“华官所管各处,防疫事宜毫不仿文明办法,惟装饰外面之形式而已,绝无实行,以致鼠疫日炽一日。”②《奉天防疫之与各国领事》,《泰东日报》1911年2月11日,第2版。在整个疫情期间,日本一直通过外交施压的方式试图攫取并控制中国的防疫主权,甚至将临时防疫本部从大连迁至奉天,旨在直接跟东三省总督进行交涉,并干预中国防疫指导工作。
由于疫情未得到及时控制,鼠疫从哈尔滨沿着铁路线蔓延到京师,威胁到外国人的安全,各国一致采取自上而下施加外交压力的方式,与外务部交涉,要求清廷命令东北督抚厉行西法防疫,“中国政府虽在中国土地自有高上主权,然瘟疫之危险奚止关乎中俄两国,故不得不共起谋之”③《瘟疫与中国政府》,《远东报》1911年2月16日,第1版。。在外交压力下,清政府坚持以避免干涉为原则,要求各级政府一方面积极防疫,避免落人口实,另一方面注意把握防疫的主动权,避免主权旁落。
来自外国的干涉压力和清廷的政治压力日增,以施肇基、锡良为首的官员们不得不认真对待防疫事务:一方面慎重对待日俄等列强的要求,主动采取西法防疫,将防疫的领导权掌握在清政府手中,尽力避免外国对防疫工作的直接干涉;一方面主动举办万国鼠疫大会,避免日俄攫取中国防疫的指挥权和主导权。简言之,清政府维护防疫主权的方式是,以听从西方要求的方式换取不干涉,从而将防疫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锡良在对待日俄具体交涉时非常慎重,尝试做出有理有节的回应,尽量通过中国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避免外国插手,“本大臣于此次防疫不少宽假雷厉风行,无非欲使疹疠早除,以杜外人干涉,但救一分民命,即保一分主权”④《昌图议事会日前条陈防疫事宜》,《吉长日报》1911年2月24日,第6版。。他非常在意是否让外国人满意,将避免干涉作为一种追求。在给外务部的电文中,锡良写道:“奉省防疫办法不敢谓无暇可指。惟始疫至今,一意进行,实已不遗余力,英德美各领事及来奉医员尚无间言,足资印证。近与日领会议,尚无显然干涉情形。”⑤《致外部电》(1911年3月9日),锡良档,甲374—46。
在防疫交涉进行的同时,外务部派伍连德前往哈尔滨领导防疫,实现了国人自办西法防疫。他经过调查研究后决定厉行西法防疫,在傅家甸建立了防疫体系,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疫措施。通过中俄交涉,解决了道里、道外断绝交通和火车停运问题,断绝了鼠疫向外扩散。在医务人员和军队的援助下,防疫局的触角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保障防疫措施落实到每条街道、每个房屋、每个人。隔离、消毒、焚化尸体和接种疫苗等措施得到有效执行,疫情在30 天内得到了控制,每日死亡人数从二百余人降到零⑥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张士尊译,苑洁审校:《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第315页。。哈尔滨有效的防疫客观上使俄国人干涉的声音消失了,得到了锡良的肯定,要求“各属亟应斟酌情形,仿照办理”⑦《致军机处电》(1911年2月16日),锡良档,甲374—46。。
此后,清政府将这一成功经验在整个东北乃至全国广泛推行。1月25日,锡良在给军机处的电文中表示,必须“病者治疗,生者隔离,死者消毒掩埋,非西医不办”①《致军机处电》(1911年1月25日),锡良档,甲374—46。。奉天民政使司韩紫石表示防疫之法“首以遮断交通为第一义,次以扑灭微菌为第二义”②《韩紫石司使复关东羁客论防疫行政书(续二十三日)》,《泰东日报》1911年2月26日,第1版。。锡良在通饬地方官的电文中,特别指出鼠疫无完全疗治方法,注重预防,以消毒、隔离,遏其传染③《通饬三省各道府厅州县电》(1911年2月9日),锡良档,甲374—26。。需强调的是,虽然采取了西法防疫,但东北地方官员仍然采取一种调和的态度,试图维系整个防疫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既要保障防疫效果,杜绝外人干涉之意,又要关照地方官民心理,以防社会反抗之举。锡良在给吉林巡抚的电文中指出,西医视受病之人必死,因此西法防疫注重于预防生者的传染。这一做法“诚非民情所愿”,因此主张一方面从西医预防,一方面仍设法疗治,“尽我心力”④《致陈简帅电》(1911年1月29日),锡良档,甲374—15。。
除了自办防疫避免干涉外,清政府还当机立断,决定举办万国鼠疫大会,掌握鼠疫研究和讨论的主动权,避免日俄利用医学优势攫取医学发言权。1 月20 日,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I.J.Korostovetz)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各国专门医生,前往该各处考察最重之地及致疫之源,并报告瘟疫流行之情形,已通告各国政府矣”⑤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2082376900(第246画像)、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一件/一般的防疫施設(B—3—11—4—8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务部担心俄国人喧宾夺主,指出“此事关系主权,碍难听彼干涉”,应当由清政府设法倡办。于是,外务部决定给清政府驻外使节发电报,照会各国驻京大使和公使,请各国政府选派医生前来中国讨论致疫缘由和防救方法。清政府决定提供各国医生到京后旅费,并令吉林、黑龙江两省巡抚妥善招待到东北考察的各国医生⑥《外部来电》(1911 年1 月25 日),锡良档,甲374—46;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2082376900(第245画像)、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一件/一般的防疫施設(B—3—11—4—8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事后,时人对举办万国鼠疫大会的决策评价颇高:“盖早悬一发起召集万国会议之志望,卒如其所志望,而召集万国会议。中国人居发起人之荣名者,以是为权舆噫?是宁得以寻常战绩相提并论乎?”⑦旁观者:《战胜北方鼠疫之二杰》,《青年》第14卷第8期,1911年9月,第166页。
东北大鼠疫初期,西法防疫措施因与中国防疫方式相悖,受到中国民众的抵制。列强藉此干涉中国防疫内政,防疫交涉成为影响清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为避免列强侵害中国国家主权,尤其是日俄借机侵略东北,清政府任命中国医生领导防疫,主动大规模推行西法防疫措施,避免了直接干涉。与此同时,为减轻推行阻力,避免因此引起的民变,清政府也不得不多加变通,兼顾民众的利益与情绪。更重要的是,在万国鼠疫大会上,清政府明确表达了对西法防疫及科学医学的接受。施肇基表示:“从今以后,我们决心用所能获得的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去战胜所面临的鼠疫。”⑧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张士尊译,苑洁审校:《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第8页。与会的外国专家赞赏了清政府采取“文明途径”(即西法防疫)应对鼠疫蔓延,肯定其“御疫之策,尤称适宜”⑨《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记》,《中西医学报》第13期,1911年5月,第4页。。
结 论
近代以来,外国人多聚集在新兴贸易口岸城市,繁忙的海外贸易潜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疫情的威胁。为保障侨民在华的健康,西方各国需要促使当地中国人重视疫情与卫生,接受西方防疫观念,并推动清政府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卫生行政机构,采纳西法防疫作为国家政策。在此过程中,防疫交涉在晚清中外关系中逐渐兴起,承载着制度、文化、权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历史偶然性和结构必然性①此处的结构是理解事件发生的关键,具体而言就是“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竞争以及相应的社会权力都有着不同的结构性特征,而分析这些结构性特征则是理解时间/历史的结构的关键所在”。赵鼎新:《时间、时间性与智慧:历史社会学的真谛》,《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期,第9页。。这种偶然性体现在,疫情是无法控制的,暴发是难以预测的,空间是随机的,而每次疫情中的交涉及诉求基本围绕着列强督促清政府采取西法防疫而展开,体现出结构性的特征。
疫情暴发是防疫交涉的导火索,但防疫交涉的过程主要受制于文化和政治因素。从医学文化层面来看,以检疫、隔离、消毒、遮断交通等措施为内容的西法防疫,旨在将健康人与染疫者隔离开来,与中国传统的以散药治疗为核心的防疫措施有着天渊之别。那些亲历西法防疫的国人,无论是香港居民,还是出国淘金的劳工,并未体会到西方医学文化的优势,反而遭受的是带有种族歧视的非人道的强制性隔离和禁闭。这些经历必然引起国人对西法防疫的强烈反感。因此,承载着现代制度文明理念的西法防疫,遭到了国人的坚决抵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这种文化上的不认同成为中外防疫交涉产生最直接的原因。
防疫交涉深受中外关系的影响,是强权政治压迫下的产物。近代中外关系是由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所塑造的,因此防疫交涉是不平等的,实际上是一种“文明”强加于“他者”的过程。由于医学理念差异过于明显,列强在处理卫生事务中形成了必须通过外交干涉才能迫使清政府接受西法防疫的认知。无论是租界当局,还是各开放口岸的外国领事,对于各口岸时有发生的疫情都非常关注,往往通过交涉迫使清政府采取西法防疫。可见,防疫交涉是近代中国不平等外交的产物,列强所主张的西法防疫自然带有西方政治霸权的色彩。
基于中外之间政治不平等和文化差异,晚清中外防疫交涉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19 世纪70 年代,厦门、上海设立海港检疫,由海关税务司和领事团的外人办理,尚未涉及中外交涉。香港鼠疫期间,如何防疫成为中外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由此开启的防疫交涉仍停留在要求中方采取防疫措施的层面。经此一疫,中国人真正认识到强制性防疫造成的社会混乱和危害,更加倾向于采用传统方式对待瘟疫,外国人则强烈感受到中国人对检疫、隔离、消毒措施的坚决抵制。最终,中外双方采取华洋分治方式实现了彼此的共存。此后十余年间,疫情频发,加之帝国主义侵华程度日深,列强通过强推西法防疫干涉中国内政,中外防疫交涉得以深化。对此,营口、哈尔滨、上海等口岸城市的官民采取自办防疫的应对策略,形式上接受了西法防疫。及至东北大鼠疫,防疫交涉迫使清政府主动实行西法防疫,以维护国家主权,避免受到列强的直接干涉。可见,中外防疫交涉促使清政府逐步接受西法防疫,国人则显示出对西法防疫的辩证态度,政治上接受而文化上拒绝。
在中外防疫交涉过程中,国人自办西法防疫成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形式。此举通过认可西法防疫的合理性,保障了中国防疫主权,避免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矛盾上升为外交事件。在接受西法防疫形式的同时,官府往往坚持中西有别论,采取既接受西法又坚守传统的“洋人用洋医,华人用华医”的策略,力图在博弈中维护中华文化传统,在固有文化中调适异文化的措施。当东北大鼠疫疫情严峻,防疫交涉力度骤增,清政府才完全自主施行西法防疫,接受科学医学,在东北各地建立起防疫组织和制度。换言之,晚清中外防疫交涉是现代卫生防疫进入中国的重要动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