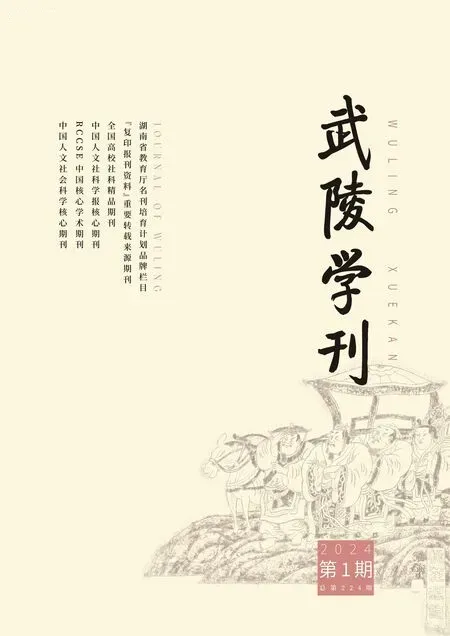太宰治《人间失格》在中国三十年的阅读史
王瑞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日语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10)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日本文学译介空前繁荣。日本现代著名作家、被称为“战后文学旗手”的太宰治(1909—1948)的作品于1980 年代开始被翻译出版,《人间失格》(1948 年) 的中译本于1993 年首次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此后,我国文学界、学术界围绕《人间失格》发表了一系列感言、评论、研究等。进入21 世纪后,《人间失格》中译本热度持续不衰,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太宰治文学迷”,并延续至今。这在中国的外国文学阅读史上十分罕见,也形成了太宰治《人间失格》在中国的三十年阅读史。因此,有必要从中日文学交流史、日本文学汉译史与研究史的角度,将这段阅读史置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之下,在时代与社会,译者、研究者与读者的相互作用之中,进行多层面的分析。
一、社会学层面的阅读
《人间失格》是一部中篇自传体小说,这部作品几乎说尽了太宰治一生中所有的痛苦和烦恼。全书由作者的序言、后记,以及主人公的三篇手札组成。主人公大庭叶藏自幼体弱多病,生性怯懦敏感,对“人间”的生活充满恐惧与不安。如,他在第一篇手札中说道:“从孩提时代起,就连家里人,我也猜不透他们活着有多么痛苦,又在想些什么。我只是心怀恐惧,对那些尴尬的氛围不堪忍受……”[1]7“我一直对人类畏葸不已,并因这种畏葸而战栗。”[1]8于是,叶藏将滑稽逗乐的方式作为与“人间”联系的手段,乃至作为向“人间”求爱的方式。然而,社会的黑暗混乱,“人间”的丑陋世故,家人的伪善欺骗,爱情的背叛创伤等,使叶藏不断走向颓废堕落、孤独绝望、自暴自弃、自残自虐的深渊,最终沦为“丧失资格的人”。
《人间失格》创作于日本战败初期,有着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1945 年,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昔日称霸一时的“皇国”一下子沦为被占领国,天皇由“神”降格为人。当时整个日本满目疮痍,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经济、文化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尤其是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被抛弃,而新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尚未建立,民众充满了孤独、悲观和虚无,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在崩溃的边缘彷徨……在此背景之下,太宰治宣称:“自由思想的本来姿态,是反抗精神,是破坏思想……是作为压迫和束缚的一种反应,也是与其发生斗争性质的思想。”[2]上述言论实际上代表了文学中“无赖派”的思想,其本质具有逆反性、反叛性。然而,“无赖派”不是正面的反叛,而是在作品中设置一些荒唐不羁的情节,架设几个放浪形骸的主人公,通过对他(她)们的肉欲、犯罪、酒瘾、毒瘾、自杀等情节的描写,来表现其反抗传统和世俗的心理。《人间失格》便是“无赖”思想的典型代表,作品中充满了作者对社会既存价值体系的“无赖式”的反叛。如:
有个说法叫作“见不得人的人”,指的是那些人世间悲惨的败北者、背德者。我觉得自己打一出生便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人”。所以一旦遇到那些被世人斥之为“见不得人的人”,我的心就不由分说地变得善良温柔,而且这种“温柔”足以使我自己也如痴如醉。[1]32
……特别是我,处在那种不合法的世界中,居然比身在绅士们的合法世界中更显得悠然自得,游刃有余,也更显得所谓的“健康”……[1]33
被作为犯人捆绑起来,竟然反而使我如释重负,万般惬意。[1]47
这样的表述在《人间失格》中比比皆是,不论是对“败北者、背德者”的温柔,或是在“不合法”世界中的游刃有余,抑或是作为犯人的万般惬意,看似颓废堕落,实则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消解,是一种激烈的反俗精神。具体而言,就是以颓废的色彩渲染社会的丑恶,以自我的“败德”破坏既成的道德,以个人的“堕落”反抗社会的堕落。总之,太宰治以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反抗传统与世俗,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然而,不论是其作品中的主人公,还是太宰治本人都最终对社会充满了绝望,“不幸。在这个世上不乏各种不幸之人,不,即便说尽是不幸之人,也绝不为过”[1]88。于是,他们在自我沉沦和放逐中走向了毁灭……
《人间失格》不仅是日本战败后社会和日本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更是战败初期日本国民心态的普遍反映。整部作品充满了对社会病态的揭露,对人性阴暗面的嘲讽,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1948 年《人间失格》连载于当时日本文学界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展望》,并于同年推出筑摩书房出版的单行本,该作品甫一出版,便成为评论界热议的对象,被誉为太宰治文学的巅峰杰作。《人间失格》作为经典文学作品,不仅在日本,也被中、欧、美等多国翻译引入。改革开放后的1980 年代,我国掀起“日本文学热”,在大规模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的大背景下,太宰治文学也随之进入了中国大众的视野,其中最早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是《斜阳》。该小说于1981 年由张嘉林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当时在读者中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太宰文学热”[1]1,此后,几乎每年都有太宰治文学的译介。
《人间失格》(最早书名译为《丧失为人资格》,也有学者译作《丧失作人的资格》《人的资格》)于1993 年由王向远教授翻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事实上,在该作品进入中国之前,一些知名的学者已对其进行了解读。李芒认为:“中篇小说《丧失作人的资格》,就是集中笔力以主人公大庭荣藏的手记的形式,描写了他从病弱走向堕落进而变成废人的短暂一生,并向社会、神祇和人类提出抗议。不难看出,太宰治的所谓抗议,并非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他笔下的革命也无非是用腐朽堕落的生活来反抗封建礼教和世俗,所谓战士就是象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那样为所欲为,爱所欲爱,亦即恋爱至上加绝对的自由主义和放纵主义,最后走向毁灭。”[3]平献明指出:“这部小说从一定的角度揭示了现代日本社会人的异化问题。……太宰治的小说在日本有众多的读者,特别是战后初期,对当时的青年一代有很强的吸引力,其原因在于他的作品内涵,有深刻的社会性。”[4]
王向远教授在该小说译本的“编选者序”《“垮掉”的证明》中,爬梳了19 世纪以来颓废无赖小说的发展史,指出了当代颓废无赖文学较之二战以前的新变化,分析了日本无赖派文学的两位代表作家太宰治与坂口安吾的作品,并总结指出:“颓废无赖文学是一代青年‘垮掉’的证明,是关于当代社会肌体的一份病案……作为病案的颓废无赖文学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5]8何乃英同样认为:“无赖派是日本战后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一般说来,他们的无赖思想和行为是对当时混乱社会和腐化的世俗道德的反抗,是对这种状况不满的表现。”[6]此外,刘炳范在《论“无赖派”与日本战后文学的转型》中说道:“他们的作品主要以消极的、悲观的、颓废的眼光,来表现日本战后初期的社会面貌,表现了日本国人由曾经强盛到衰败的凄凉忧伤和空虚无聊及战后的动荡和混乱,并刻意渲染一种病态心理和受压抑的性苦闷倾向。”[7]
显而易见,上述解读和评论都是站在社会学立场之上的,换言之,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标准进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以典型反映社会本质,强调政治教育功能[8]。事实上,中国人传统上就比较崇尚文学的现实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我国文艺创作、文学批评,以及外国文学译介的最高准绳。这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及此后较长一段时期中国学界及思想界的创作与批评,也深刻地影响了大众的阅读趣味,即便到了21 世纪之初,由于长期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惯性,大部分读者、学者还是认为文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干预社会、批判社会。因此,在译介外国作品时,更注重其社会性。毋庸置疑,《人间失格》的确体现了强烈的社会意识,如,揭露日本战败后社会的崩溃、价值体系的倒错、民众精神的迷惘……这些不仅符合当时中国读者的文学观念,更是了解日本战后社会“病案”与日本人心理病态最生动、最形象、最便捷、最可靠的途径。因此,从社会学的层面阅读太宰治《人间失格》,得出上述结论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日本很快便摆脱了战后的困境,步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民众也很快从沮丧绝望的情绪中走了出来。从这个角度而言,太宰治文学已不再适合担当反映日本社会及日本人精神状态的角色。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读者群的变化,太宰治《人间失格》的追捧者却有增无减,特别是2009 年太宰治一百周年诞辰以来,几乎每年都有新译本和复译本推出,如此看来,仅从社会学的层面阅读恐怕还不能全面理解其文学价值。
二、心理学层面的阅读
如上所述,《人间失格》的确反映了特定历史时空之下的社会危机和生存危机,然而它也反映了人类的普遍生存体验及共通心理。人类的心理与社会、历史、时代息息相关,同时它又有着比较稳定的、超越时代、超越社会与民族的某些共通方面。《人间失格》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经久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反映了人性,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性,反映了人性中最根基的东西。例如,怯懦、胆小、孤独、渴求被爱;与家庭和周围相处时感到痛苦,却又无法割舍;经历友情、爱情的挫折,怀疑自己的多余、无用,乃至于“丧失为人资格”……这种心理困境在任何时代的任何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存在。而太宰治坦诚地、赤裸裸地把这些心理困境通过《人间失格》讲述出来,将人类最隐秘、最真实的人性揭露出来,这些都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排解压抑,释放消极情绪,获得心理上的治疗。
一般认为,文学文本具有“宣泄功能”,即,通过阅读可以调节情绪,维持人格平衡与心理健康。文学的这一功能最早来源于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指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9],朱光潜先生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人间失格》属于悲剧小说,由于太宰治对人性的深刻解剖,不少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到主人公那令人窒息的痛苦。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与作品中的人物产生共感,情绪从失衡变为平衡、从压抑变为轻松、从苦闷变为平和,最终得到心灵的治疗。而《人间失格》的“治疗”功效又与日本传统文论中的“慰”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日本的‘慰’论是建立在人性羸弱、人心脆弱的判断基础之上的,本居宣长在《紫文要领》中所说‘真实的人情就是像女童那样幼稚和愚懦。坚强而自信不是人的本质’云云,是说本质上每个人都需要‘慰’。”[10]153而读者在《人间失格》的阅读过程中可以寻求慰藉,消愁解闷,进而得到精神的抚慰和心灵的治疗。
除此之外,《人间失格》还可以从日本“物哀”美学的角度加以理解。在“物哀”的审美视域中,只要属于人情人性的东西,即便不善不美,也可以转化为审美对象来欣赏。例如,太宰治笔下的那些窝窝囊囊、缺乏男子气概的主人公,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同情与青睐,也可以从这个角度予以说明。在我国,长期以来普遍认为美与善是统一的,美是健康的、向上的,通过接触外国美学,人们逐渐认识到美是一种感性,并不等于善,因为感性中不仅包含着美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丑的一面,这使得我国的美学观由伦理道德的美学逐渐转变为严格意义上的作为感性之学的美学。反映在艺术接受之中就是:人们能够容忍那些并不美的,甚至很丑的东西,如,书法中的丑书,绘画中的涂鸦,建筑中的丑怪建筑;能够接受并包容没有伦理道德价值却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如,波德莱尔、王尔德、三岛由纪夫、太宰治等作家充满“颓废色彩”的文学作品。因为“文学的本质是审美的艺术,丑这一样式亦属于此范畴之内。即使审丑会带来人的厌恶感,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厌恶感滋生的同时会带来审美快感的‘高峰体验’。”[11]这也是《人间失格》译本在中国有增无减的重要原因。
在此背景之下,读者不再囿于伦理道德的阅读趣味,文学界也不再局限于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方法,在对《人间失格》的解读上开始趋向多元的视角。如:王向远教授在肯定该小说社会学方面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丧失为人资格》是一个滴血的灵魂的自白。颓废是他痛苦的一种麻醉,无赖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5]4“我们对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形形色色的颓废无赖行为,必须坚决予以排斥和唾弃,这是应该丝毫不能含糊的。同时,我们对于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颓废无赖小说,却不能简单地以伦理道德的、社会学的价值标准予以排斥和否定。”[5]8上述言论为读者读解《人间失格》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后,蔡超在《〈人间失格〉与太宰治的基督教思想》中说道:“他对自己深刻的剖析和严厉的惩罚,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最根本的基础——诚实。正是这种对诚实孜孜不倦的追求使得他的作品保持着一种历久弥新的鲜活性,在他自杀辞世60 余年后的今天,仍旧在日本文坛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称为永恒的青春文学,而太宰治也成为了日本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12]在“诚实”这一点上,林少华先生对太宰治文学的分析更加细致透彻,他认为小说以赤裸裸的自供状手法,将主人公对人、对于人世的疏离感、孤独感、恐惧感以至绝望感毫不掩饰地剖析出来,同时将作者对爱与真诚、对友情与信任、对自由与幸福的诉求推向极限,展示了边缘人和生活在自闭世界之人血淋淋的真实的灵魂切片[13]。
杨晔在2017 年《人间失格》的译本序中提到:“可以说,《人间失格》是毁灭式的绝笔之作,是一部滴血的灵魂自白。本书蕴藏了太宰治短暂一生的种种境遇和迷茫挣扎。就算时过境迁,那种迷茫和彷徨都几乎贯穿了太宰治和我们每个人的青春。所以,人们视《人间失格》为残酷而永恒的文学,是‘青春文学的巅峰之作’。”[14]同一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廖雯雯翻译的《人间失格》,她基于阿德勒心理学的目的论、课题分离、自我接纳、“life style”等纯心理学的角度对该作品进行的阐释:“整部《人间失格》展示的便是太宰治为了达成某些目的,而让叶藏择取的某种生存之道。他的痛苦并非来自过去、他人、世道和时代,而是来自他对它们的诠释、对自我的定位。所谓的‘丧失为人的资格’,是叶藏主动选择了活得不像个人样,是他自发贯彻了绝对向下的人生观,其目的在于保护自己,消解源于人际关系网的烦恼和伤害”[15]。
由上可见,随着中国社会价值的多元,《人间失格》的阅读视角从社会学的层面逐渐转向心理学的层面。这表明中国读者除了看到其社会学的功能之外,越来越重视其心理治疗功能和审美转化功能,也表明了中国读者对于日本文学的阅读经历了一个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的变化过程。而在当今全球化逆流的冲击之下,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中国社会处于全面转型期,加上近几年“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等因素,不少人的精神出现了不安、迷惘、虚无等状况,在此语境之下,《人间失格》在中国多次复译再版,愈加彰显其历久弥新的现代性及当代性。
三、《人间失格》现代性与当代性的发现
“现代性”是一个难以界定的词。根据汪民安《现代性(modernity)》一文,现代性是16 世纪以来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事实,到了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后的19 世纪,现代性逐渐成熟,表现为疆域固定的民族国家、自由民主政治、机器化的工业主义、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主体—中心的理性哲学以及所有这些之间的功能联系,等等[16]。而“当代性”既是现代性的延伸,也是对现代性的限定,指现代性的当代化。一般认为,在高度社会化、高度个人化的当代,不少人会感到孤独渺小、无力无奈、无趣无感,越来越找不到归属感和安全感,于是就出现了精神世界的混乱、迷茫、病态等心理问题。在此背景下,《人间失格》消极颓丧的思想与上述心理状态不谋而合,引起了不少人的强烈共鸣,推动了新译本的显著增多。与此同时,在时代与社会,译者与研究者的相互作用下,《人间失格》的阅读也超越了此前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层面,进入现代性与当代性的语境之中。
杨伟指出:“太宰文学却具有一种超越了时空的不可思议的普遍性和现代性。阅读《斜阳》和《人间失格》等作品,不能不感受到,太宰治所直面的乃是人类、特别是现代人共同面对的普遍课题,描写了现代社会中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的自闭者、叛逆者、边缘人或多余人的悲剧。”[1]13杨伟从太宰治及其文学的心理轨迹出发,做出了十分精准的评价,他在太宰治的文学中发现了其现代性,乃至现代人的心理困境,还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结论:“与其说太宰文学业已跻身于功成名就的经典作品行列,不如说在现代语境里反倒越来越彰显出历久弥新的鲜活的现代性”[1]14。此外,田原也从这一立场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庭叶藏被刻画得活灵活现,他栩栩如生的形象超越时间、时代、人种、文化和宗教的樊篱,不仅不会因年代的久远变得陈旧与过时,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年代的久远变得愈加生动与逼真……”[17]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人间失格》在中国出现了空前的译介高潮。通过当当网进行统计,从2016 年至2022 年2 月《人间失格》的新译本达到49 个(不包括复译和重版),几乎每年都有6 个以上新译本推出,特别是2019 年,新译本的数量多达13 个,创下历史新高。而这种译介现象与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40 余年,中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物质财富高度发达,另一方面,各种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如,社会阶层固化,收入差距扩大;就业难、发展难、住房难、看病难;各行各业“内卷”化严重;近几年新冠疫情对经济的严重冲击……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在网络平台的推动下,青年群体中兴起了“丧”“佛系”“躺平”等“负面”文化。2016年一张“葛优躺”图片在社交网络爆红,图片上的人物一副消极颓废、生无可恋的样子,该图很快被配上“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颓废是糖,甜到忧伤”等文字做成“自嘲”表情包,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起中国“丧文化”的流行。“丧文化”的“丧”字,除了词典上“失去”“失败”“逃亡”“消耗”“忘掉”“悲伤”和“失意”等意思之外,在当代又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它代表了“无力悲观”“麻木不仁”“不思进取”等消极感情。
2017 年,某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名为《胃垮了,头秃了,离婚了,90 后又开始追求佛系生活了?》的文章,“佛系”一词进入大众的视野。该词本源自日本的“佛系男子”,主要指无欲无求、不悲不喜、云淡风轻、追求内心平和的生活态度,代表了“一切皆可”的随性心态。随后,《新世相》发表了《第一批90 后已经出家》的文章,文中用“佛系”描述了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该文将佛系文化推向了高潮,并衍生出了一系列流行语,如,佛系老师、佛系玩家、佛系养生、佛系打卡、佛系心态、佛系人生等等。2021 年,因百度贴吧一篇《躺平即是正义》的帖子,“躺平”一词兴起,并受到了不少人的追捧。“躺平”指对事物的变化不做任何反应或反抗,看似妥协、顺从,实则是以无所作为或“向下堕落”的方式进行反叛。事实上,不论“佛系”还是“躺平”,都是以颓废消极等负能量为核心的“丧文化”的延伸,而这些与《人间失格》中表现出的颓废、失落、抑郁、空虚、绝望等心理相当契合。
但是,在中国,这些“丧文化”绝非主流文化,而是属于青年亚文化,这种文化是由青年群体创造的,对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和批判性。尽管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是社会心态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的确也有不少年轻人常常将“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什么都不想干”“漫无目的的颓废”“颓废到忧伤”等散发着颓废绝望的话语挂在嘴边,这些话语也符合部分青年群体的生存困境,但绝大多数也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自我调侃或情绪宣泄的渠道,事实上这些消极思想并没有真正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就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认真梳理当前流行的所谓‘丧文化’,可以发现,其实不少年轻人喜欢的‘丧’,和外界对于‘丧’的解读,有着微妙的区别:最明显的一点是,其实‘丧’不等同于负能量,‘丧’也不意味着绝望,而大多是作为一种自嘲和排解压力的方式。”[18]此外,《从〈人间失格〉浅论丧文化》一文的作者指出:“今天的年轻人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占据社会各行各业。‘丧’只是一方面,是一种对不满的微弱抵抗,请相信你们用心培育出来的年轻一代错不了!”[19]该文非常符合当前的语境,作者不仅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丧文化”,而且也看到了“丧文化”背后青年的态度和积极意义,十分有见地。
如上所述,这些“丧文化”不仅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社会存在的矛盾,其更重要的功能还在于它作为宣泄消极情绪的一种手段。因此,在对待社会负面情绪上,不能一味地遏制和否定,要允许它一定程度地存在,从而使民众宣泄内心的不满,释放潜在的负能量,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当面对“丧文化”时,除了否定其消极的一面之外,也应该肯定其消解负面情绪、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的一面。倘若一味地干预遏制,负面情绪得不到释放,将会成为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隐患。因此,“佛系”“躺平”等“丧文化”的宣泄净化功能亦不容小觑,这又与阅读《人间失格》有着殊途同归之效。太宰治辞世后的75 年,其《人间失格》显得更接地气,更具魅力,新译本不减反增的事实正是诠释了其文学的现代性和当代性。
结 语
综上,太宰治《人间失格》在我国三十年的阅读史历经了社会学、心理学、现代性及当代性三个层面。从1980 年代到21 世纪初,一方面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出于了解日本战败后社会及日本人现状的需求,多数人将阅读重点放在其社会批判上;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价值观念的多元,人们的阅读趣味不再拘泥于社会学的层面,而是深入到了作品的内部、人性的深处,更加重视其心理治疗及审美转化功能;此后,在社会经济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受自媒体平台的推动,青年群体中兴起了“佛系”“躺平”等“丧文化”,这与《人间失格》中“丧”的文学思想不谋而合,引起了年轻读者群的共鸣,该作品又被用来诠释当代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因此,对这段独特的阅读现象进行论析研究,不仅具有阅读史研究的意义,而且对于研究文学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