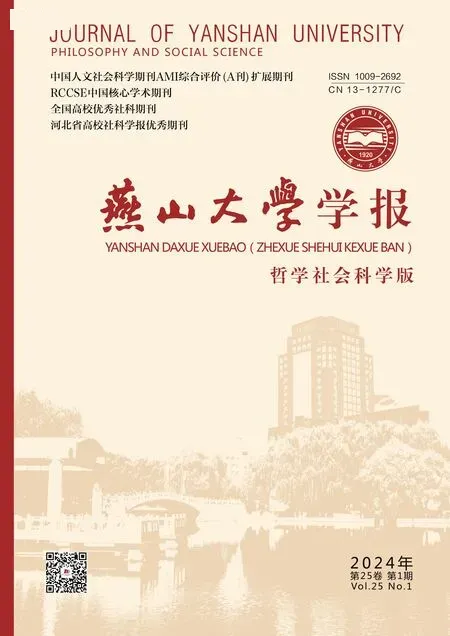从“三史”论冯友兰荀学研究方法论的嬗变
李 娴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中国哲学研究大家冯友兰对荀学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其荀学研究贯穿学术生命始终。早在1921年,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期间就对荀学有所关注,他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中提出荀子有着西方人的特点,是“中国历史上力求发展中国思想的人为路线的哲学家”[1]43。冯友兰生活在不同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一生都在寻求如何理解、如何解决这种文化矛盾,以及自己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与之适应的方法。荀子兼具中西方人的双重特点,其思想无疑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因此荀学研究也是冯友兰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在数十年的学术探索中,冯友兰对荀学思想体系的建构随着时期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些差异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厘清冯友兰荀学体系建构方法的变化,无论是对当代荀学研究还是对于理解冯友兰的哲学思想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笔者拟通过历史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呈现出冯友兰荀学研究的发展脉络,揭示其荀学研究的嬗变原因、内容及其发展特点,以期能为荀学研究和冯友兰思想研究略尽绵力。
一、以“西”释“荀”:《中国哲学史》中的荀学研究方法论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对荀学的理解是在东西文化矛盾冲突这个前提之下进行的。当时的中国处于不同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他认为当时所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相适应”[2]307。正源于此,冯友兰在这一时期荀学研究的目的是“想对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作一种广泛的解答,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种广泛的解释和评论”[2]172。他当时非常期待能“有一部用近代史学方法写出的中国哲学史,从其中可以看出一些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一点系统,以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2]183。又因冯友兰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在主观志愿上是想向中国介绍西方的哲学,但客观机缘上却是做了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工作,最后归到研究中国哲学史。其研究荀学最直接的契机是1927年冯友兰被燕京大学安排讲授中国哲学史,这一时期的荀学研究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冯友兰在前人和自己的学术经验的基础之上,对荀学进行了自己的理解和评价。
首先,冯友兰以“释古”的方式辨别荀学的研究材料,重视对荀学学说的义理阐发和体会。五四新文化时期,虽然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已经出版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两点明显的不同。一是对于史料的真伪判定不同。胡适用证明的方法“确定历史中一个哲学家的年代,判断流传下来的一个哲学家的著作的真伪,他所认为是伪的都不用了”[2]18。冯友兰则认为哲学史料的真伪只是时间上的先后问题,但重要的是史料内容本身是否有价值,他说:“一个资料是真是伪,并不断定它本身的价值,只断定它的时代的先后。”[2]190二是所采用的学术传统不同。胡适更倾向于“汉学”传统中注重文字的考证和训诂,对于义理的了解和体会比较肤浅,而冯友兰则更重视“宋学”传统中对各家哲学思想的了解和体会,因而冯友兰采用“释古”的方式来辨别荀学的研究材料,不因资料时代的先后来断定它本身的价值,而是就内容本身有无思想来断定价值,从而改变了以往疑古和辨伪,先辨别内容真伪再论思想的状况。概言之,冯友兰抛弃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汉学的考证、注疏方式,而采用宋学阐发义理的方式,重在对荀学思想的理解和体会。
其次,冯友兰采用西方哲学研究的范式对荀学的研究材料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以往的哲学史家对于荀学思想主要是进行选抄编排,史料分析,然后综合叙述出来。在《中国哲学史》“荀子及儒家中之荀学”一章中,冯友兰对于荀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是按照西方哲学中的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三大研究内容进行编排的。其中“天及性”一节中涉及荀子的宇宙论,冯友兰认为:“研究存在之本体及真实之要素者,此是所谓本体论;研究世界之发生及其历史,其归宿者,此是所谓宇宙论。”[3]246“荀子之心理学”一节中涉及荀子的知识论。冯友兰所理解的西方知识论不仅包括研究人是什么的心理学内容,也包括人究竟应该怎么样的伦理学内容。用以西释中的方式将荀学思想用西方哲学研究范式进行重构,把一体的荀学思想细分为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几个部分,虽然可能对荀学思想本身有所误读,失去了荀学本身含有的中国哲学语境下的特殊性,但是这种建构方式也让当时的学者见识到了荀学思想的多面性,启发了人们对荀子的多维度思考。当代学者周炽成认为以西释中的方式“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对已经过去了的中国哲学的新看法,而且还会影响着当今的中国人的哲学思维”[4]。
再次,运用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分析。对于如何理解当时时代文化冲突的矛盾,冯友兰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思想阐释,来表达自己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解,其荀学阐释就是其中的一种途径。这种理解的方式主要是指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和比较法。他在汉学家研究荀子著作成果的基础之上,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弄清楚荀学的一些哲学观念。逻辑分析法,即以“正的方法”告诉我们荀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包括哪些,因为荀子的哲学思想分布在他的文章之中,“其原有形式,不可能像现代解释者所表述的那样清楚。”[5]280一是因为专业术语比较少,二是因为不具备形式上的体系,三是荀子的文章是用古代的语言写成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对荀子的解释就是:“告诉我们,哲学家的字句,这些人自己在过去实际上是意指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意指什么。”[5]280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有助于使荀学思想获得清晰、抽象的观念,也利于尽可能地使人们理解荀子本身的思想。此外,冯友兰用比较的方法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荀学的思想,在整章中都穿插着此方法。比如在第四节“天及性”中,冯友兰在论述荀子之天时,是通过论述孔子之天、孟子之天与荀子之天的不同之处,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荀子之天是什么。类似的论述方法同样出现在“礼论、乐论”“王霸”“正名”等小节之中。比较法的运用,一方面从横向的角度分析荀学思想与其他思想的不同,突出荀学思想的特色,另一方面也从纵向的角度讲述了某一思想的历史性变化,突出了荀学的地位。他评价荀子是继孟子之后的儒学大家,最善于批评哲学。“孟子以后,儒者无杰出之士。至荀卿而儒家壁垒,始又一新。上文谓中国哲学家中,荀子最善于批评哲学。”[3]503
综上,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对荀学思想的研究在于弄清楚他的观念,重点是要说明荀子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样说的,更倾向于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陈述性工作。用“释古”的方式辨别荀学史料,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来建构荀学的哲学系统,用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分析和阐释,没有以任何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建构荀子哲学,而是以平等的态度进行一视同仁的比较分析,只是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荀学本身。虽然冯友兰的思想倾向于实用主义,但是他也仅以逻辑分析的方式去建构哲学体系,而没有以实用主义的观点来批评中国固有的哲学。冯友兰以哲学为说,建构荀学体系,讲出荀学思想的道理,他所注重的不仅是道而且是理,不仅是实质而且是形式,不仅是问题而且是方法。
二、中西比较:《中国哲学简史》中的荀学研究方法论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冯友兰开始转变学术志向,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哲学史家,而是做一个哲学家。四十年代及以后的作品融入了冯友兰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想法,而不是只谈别人就某些问题的所想。随着时间、阅历和学识的增长,他开始了解到“要解释不同文化的矛盾冲突,无论是用地理区域还是用历史时代都不如用社会类型来得令人满意”[2]308。在五四运动时期,冯友兰已经认识到东西文化问题并不是一个东西问题,而是一个古今问题。再后来,他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觉解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不从纵的方面看历史,而从横的方面看历史”[2]219。所谓纵的方面看历史,是着重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成和发展、衰老和死亡。从横的方面看历史,是把社会分为许多类型,重点在于看各类型社会的内容或特点。这一理解使冯友兰认识到所谓古今之分其实就是社会类型的不同。更广泛一些说,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共相和殊相的关系问题。“某一种社会类型是共相,某一个国家或民族是殊相。某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某一时期是某一类型的社会,而在另外一个时期可以转化或发展为另一种类型的社会。”[2]219有了这种觉悟,冯友兰也更加清楚中国哲学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认识到中国哲学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对荀学思想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
第一,简史中的荀学思想主要集中探讨荀子的政治哲学理论。中国哲学所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必定与政治思想不能分开。尽管中国哲学各家不同,各家哲学无不同时提出了它的政治思想……所有哲学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政治思想联系着,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既代表他的整个哲学,同时又是他的政治思想”[5]12。在结构安排上,不再像《中国哲学史》中那样分节陈述,各部分之间关系不大,简史中的荀学思想,无论是人的地位、人性的学说、道德的起源还是礼乐和逻辑礼论等问题都是荀子政治哲学的一部分,其核心主要是围绕荀子政治哲学思想这一问题,描述荀子是如何期待建立一个圣王之治的政治社会,结束动乱的时代的。论述其人性论,旨在说明人性之恶,如何在道德方面为善,所以引出道德的起源问题。冯友兰认为:“第一个方面,荀子指出,人们不可能没有某种社会组织而生活……还因为,人们需要联合起来,才能制服其他动物。”但有了社会组织以后,还需要行为的规则,所以冯友兰又谈到了荀子的礼、乐学说。他认为荀子的礼是为了克制人的欲望,“遵礼而行就是道德,违礼而行就是不道德。”[5]130礼的功能在于调节人的欲望满足,还有就是使人文雅。而音乐的功能则是道德教育。其逻辑礼论中的正名思想,虽然也有知识论的理论,但是冯友兰认为荀子的正名思想主要还是为君及政府的职能服务。
第二,运用“正”和“负”的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分析。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分析荀学思想所使用的主要是逻辑分析的方法,也就是正的方法。可是到了《中国哲学简史》时期,他开始意识到负的方法也很重要。“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作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5]277虽然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并没有过多涉及荀子的宇宙论思想,但是在谈到荀子的这一思想时,用的就是负的方法。他认为荀子将宇宙分为“三种势力:天、地、人”,用人的职责来突出天和地的职责。“‘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这是天、地的责任,但是人的职责是,利用天地提供的东西,以创造自己的文化。”[5]12通过负的方法的使用,可以让人们对于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宇宙论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冯友兰认为荀子的宇宙思想受到道家的影响,“在以前儒家中,孔子所说底天,则是自然之天。他所说底天,就是自然。在这一点,我们看见,他所受于道家的影响。”[6]58当然,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冯友兰认为荀子表面上是在谈天、地,其实根本上却是在谈论人本身。荀子思想中“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5]128。当时“西方的汉学家们把中国文化当做一种死的东西来研究,把中国文化当做博物院中陈列的样品”[2]313,而简史中冯友兰用西方读者习惯的方法介绍荀学思想,语言简短精炼,更通俗易懂。
第三,冯友兰将自己的中国哲学功底与西方的现代学术方法结合起来,用正和负的研究方法,用西方人熟悉的观念研究荀子思想。在语言表达方式上,虽然在内容上字数不多,论题聚焦荀子政治哲学,论述逻辑严谨,层层递进。此时期冯友兰的荀学研究不再流于对荀子思想的简单介绍,而是对于荀子思想中的核心问题——政治哲学进行自己的建构和解读,不再只追求面面俱到而思考不深,而是舍弃很多繁杂的史料,仅仅就核心论题进行描述,让人更能体会荀子哲学思想的精妙之处,也更通俗易懂。在写作手法上,将荀子哲学的概念与西方哲学家的概念作比较,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荀子的思想。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以“儒家的现实主义派:荀子”为整章命名,是与“儒家的理想主义派:孟子”相对应,也是通过相互引证的方式使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荀子的思想。
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对荀学的论述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论述荀学思想的特殊性。儒家的现实主义派是冯友兰对于荀子的总体评价,这种现实主义也“有右有左:右就右在强调社会控制;左就左在发挥了自然主义,因而直接反对任何宗教观念”[5]127。这一时期的冯友兰不再局限于对荀学思想的铺陈总结,而是涵盖着他自己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和体会。
三、以“马”建“荀”:《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的荀学研究方法论
新中国的诞生使得旧邦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出现,不同的文化在中国的矛盾冲突也就解决了。当然还会有新的矛盾。”[2]311中华民族的前途问题是冯友兰一直所牵挂的事情。所以,冯友兰希望在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中能够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他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看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来源”[2]313。又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儒法斗争非常严重,评法批儒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这一时期冯友兰的荀学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其一,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以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融合自己的新理学体系建构起新的荀学研究体系。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一方面冯友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着重分析荀子思想中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发展规律,为荀子重新定位,把荀子评价为先秦最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认为荀子最主要的贡献是“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对于自然、社会、认识论和逻辑学各方面的唯物主义的理论”[7]625。他将荀子的著作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唯物主义思想,旗帜鲜明,立场明确,确切是可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确切是和孔丘、孟轲针锋相对,这是古代哲学中极有价值的著作。这是荀之所以为荀者,是《荀子》的主要部分,是其精华。第二类是因循没落奴隶主旧制度,但也给以新的解释,使之继续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既然能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在当时还是有价值的著作。第三类是荀况或其学生从儒家带来的包袱。”[7]577另一方面,他又结合唯物主义体系和新理学来对荀子哲学进行建构。“这个范围,大概说起来,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自然,一部分是社会,一部分是个人。自然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天;社会和个人,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天人之际。人类的生活,无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都是和天人之际有关系,所以中国哲学认为天人之际是哲学的主要对象。”[2]307刚好把荀子的哲学思想分成自然、社会、认识论和逻辑学几个部分,分别进行论述。
其二,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荀子哲学思想形成的原因。当代学者高秀昌认为冯友兰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自从接受唯物史观以后,“就一直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用它来考察社会历史及精神文化”[8]。“一个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知识与生产技术的有意或无意的总结。”[2]161冯友兰判定荀子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当时的科学知识与生产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战国后期,科学知识及生产技术的发展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荀况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就是这个发展的理论上的总结。”[7]626此外,冯友兰在论述荀子统一的思想时,也认为他的这一思想主张“是当时政治上统一趋势的反映”[7]625。冯友兰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荀学思想,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他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作的努力,看作是他终身致力的中西哲学的一个新阶段”[9]。
其三,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更加重视阐释荀学的法治思想。他将荀学放入儒家思想发展的脉络之中进行探讨和分析,认为孟子和荀子都是孔子的真正继承人,孟子是儒家思想向唯心主义的发展,荀子是儒家思想向唯物主义的发展。在“荀况论‘王’、‘霸’”一节中,主要论述了荀子“力术止、义术行”的礼法并举的王道思想。冯友兰认为荀子与传统儒家对于王、霸的理解不同,“王、霸有所不同,王是以德服人,霸是以力服人,王优于霸”则是儒家的共同认识,荀子对于王和霸的理解是同种类型的不同程度,修礼者为王,为政者是霸,修礼是霸的进一步完善。他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将荀子的礼和法看作是上层建筑,“法是政治方面的上层建筑,礼是文化、道德方面的上层建筑。”[7]584其目的都是为了同一经济基础服务的,将百姓按照职业进行分类,“规定贵贱、上下等社会秩序”[7]584,其关系是互相补充、互相为用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值冯友兰创作《中国哲学史新编》时期,也是学界儒法斗争非常严重的时期,或多或少都打上了评法批儒的烙印。
其四,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在荀学思想的写作内容上,将荀子的自然观与认识论、人性论、伦理学联系在一起。荀子的自然观讲的是天人关系问题,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命题就是“天人之分”,其原则是“明于天人之分”,冯友兰认为荀子较为正确地论述了天人关系问题,评价此为“荀况在哲学史上的一个最大的贡献”[7]592。紧接着,冯友兰将“明于天人之分”这一自然观原则应用于认识论、人性论和伦理学之上。根据这一原则,冯友兰认为荀子在认识论上明确了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和认识对象的关系,反对认识过程中的片面性和主观性。荀子的“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就说明了“客观的事物是复杂的,人所欲的利跟人所恶的害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7]597。从而将荀子的认识论引向人性论和伦理学。原因是荀子的“性”虽然属于自然的一面,但是性对于外物的反应表现为“好、恶、喜、怒、哀、乐”等情。情的复杂性就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会出现相互冲突、相互争夺的状况,若要对这一情况进行调节,就要通过学习的方式进行,而学习所得到的东西,就叫作伪。冯友兰认为“照荀况的说法,社会的制度、道德、文化,都是从伪出来的”[7]619。所谓性伪之分,也就是天人之分,伪的意思就是人为。荀子主张化性而起伪,这有用人力改变自然的意义,和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意思是一致的。因此,在冯友兰看来,荀子的整个哲学体系在自然观方面强调天人之分的原则,认识论、人性论和伦理学都是天人之分在各个方面的表现而已。
总之,冯友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重构荀学思想体系,并且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东西,融合自己的新理学体系,写出使人信服的荀学思想,这是非常困难,也是非常难得的。
从三史看冯友兰荀学观的嬗变,在研究方法上,冯友兰原本只重视西方逻辑分析“正”的方法,到后来“正”“负”方法并重,以及晚年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重新构建荀学体系,可以看出冯友兰对于任何一种方法论的使用,都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而是在充分学习和理解每一种方法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荀学的建构范式上,一开始《中国哲学史》用西方哲学研究范式来建构荀学的思想体系,目的是通过文化引进,用现代学术方法建构中国的思想体系,使古代哲学思想获得“新生”。《中国哲学简史》侧重于用西方人熟悉的范畴来讲解荀学的核心问题——政治哲学,目的是文化输出,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的问题和对象。《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体系来建构荀学体系,提炼出荀学思想的精华,总结出荀学中的智慧,为中国的哲学建设提供营养和借鉴。在研究荀学的深度方面是随着时间不断递进的,《中国哲学史》倾向于对荀学思想用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进行铺陈和梳理,告诉我们荀学思想里都有什么;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融合了自己的人生体会,有了很多哲学创见成分,告诉我们荀学思想的核心命题是什么;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将宏大叙事与细微分析相结合,把国家命运和时代需要的命题融入了荀学思想研究中,目的是告诉我们荀学思想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冯友兰对于荀学的理解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自己曾说过:“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7]4虽然每一时期冯友兰对于荀学的理解有所差异,但是这其中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始终关心着中华民族的兴亡和中国文化的前途,其为国为民,为学术本身之心从未改变,这也是值得我辈青年学者钦佩和学习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