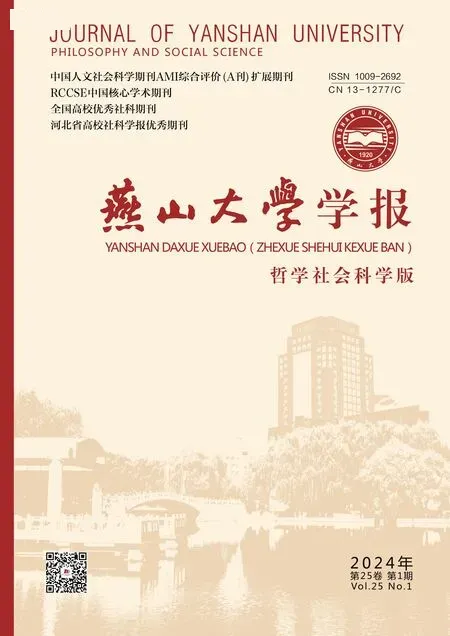沈从文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马慧娜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1418)
中国的“现代性”始于20世纪初期,有关沈从文思想与创作现代性的早期研究以肯定其现代性品格为主。新时期之后,现代化进程加速,所谓“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现代性”也逐渐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概念进入到文学研究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沈从文思想的复杂性逐渐为学界所重视。张清华认为在中国现代社会与文化的多向冲突中,沈从文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努力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沈从文是一位“以充分现代的哲学与文化意识为思想支撑的作家”,同时又对五四神话感到强烈失望。[1]解志熙理解的沈从文是一个具有现代人灵魂的“乡下人”,折射着“五四”之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趣味和意识形态”的思想,但其复杂性也有待能被更准确、更人性地理解。[2]杨联芬注意到沈从文与五四现代性之间的疏离,得出沈从文是“反现代性”的结论之后,又不无犹豫地指出,“或许,沈从文选择的是另一种现代性?”[3]
“现代性”本身是一个普泛化的、聚讼纷纭的题目,它像是一个拥有丰富色彩的多棱镜,透过这一棱镜对沈从文探赜索隐是一种见仁见智的研究,自然会出现“既有类同又有差异甚或矛盾的判断和评价”。对于沈从文来说,不能说没有受到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但他的思路与五四以来的现代理论大不相同。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借用“现代性”反射的光谱来打量沈从文,进而体会其独特性与复杂性,则可以丰富和拓宽沈从文研究的格局。这其中可以涉及的议题不在少数,这里仅从时间的角度、沈从文的风景描写与“风景中的人”来分析沈从文思想与创作中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并行的独特性。沈从文的这一独特性与其“修辞以立诚”是分不开的,这也是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法则——“真实”。沈从文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它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是开放给一代代学人来持续探讨的话题,将“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引入对这一问题的思研,有助于更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一、沈从文指向“未来”又返还“过去”的时间观念
由于“现代性”首先代表时间,因此,从时间的维度来叩问沈从文思想与创作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是挖掘沈从文创作丰富性与独特性的一条必经之途。“现代性”是一个跨越东西方的理论,虽然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旅行经历了明显的“错位位移”,但建立在新的现代时间观念或心理状态之上的对“进步”或“现代”的推崇,中西方却有相通之处。尤西林认为,时间观本身具有生产方式与文化意义的双重根据,犹太-基督教救赎史与启蒙历史哲学的衍化最终促成了现代时间的确立:一种指向“未来”不再返回或倒退至“过去”的矢量时间。在这样的起源背景下,现代性的时间重心在于“未来”,而非在古代社会里常常被奉为楷模时间的“过去”。因此,现代性的这一时间观念不但区别于缓慢循环的古代自然时间,同时也必然地成为一种从低级进向高级形态的进步信念的依托框架。[4]这种奠定“进步信念”的时间观念,是现代性最深潜的核心,以此比照,沈从文的时间观念指向未来但又返还过去,很难用“现代性”或“反现代性”来简单概括。
一九三四年的冬天,重返故乡的沈从文发现,昔日里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快要被“现代”社会中唯实唯利人生观所代替,原有的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被常识摧毁,一起泯没的却还有义利取舍的是非之心。沈从文感喟“过去”湘西人勤俭治生忠厚待人的好处,以及素朴自然景物衬托下的那种简单信仰里所蕴蓄的抒情诗一样的浪漫感人气氛,被“现代”的洋布煤油破坏殆尽,“现在”的年轻人已全然不能知晓那些好处与气氛,更遑论可以从那“过去”中去学习去认识了。[5]1-2可见,面对“现代”冲击下的湘西,沈从文是痛心和哀伤的,他希冀的美好生活与古代社会奉为楷模时间的“过去”相通,并不是指向“未来”不再返回或倒退至“过去”的矢量时间即现代时间。因为现代时间是无休止追求“未来”、否弃“现在”、遗忘“过去”的高速矢量直线时间,在现代主义的术语里,“过时”意味着“落后”,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沈从文确实游离于现代性思潮之外。
沈从文留恋“过去”岁月的同时,又因这种不变而感到痛楚,“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6]254。沈从文是矛盾的,他忧伤和无奈于历史的变动、时间的流逝,同时又哀痛和悲戚湘西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向往着变动的“气息”。最早使用“现代性”一词的法国思想家波德莱尔认为,变动不居的运动性是现代性的首要特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这种过渡的、短暂的、其变化如此频繁的成分,你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7]。在波德莱尔看来,现代性具有短暂性、飞逝性,它永远都在不断地消失,同时又在不断地再生。身处五四启蒙思潮的中心,“现代”了的沈从文确实受到了现代性思潮的影响,也期待着现代性变动的气息吹拂到故乡。
杨联芬从时间的角度关注沈从文的反现代性时也认为,沈从文是矛盾的[3]。具体来说,沈从文的时间观念指向未来,与五四时期含有“未来”和“理想”意味的现代性观念是相合的,但是,沈从文希冀的“现代”充满了“过去”的质素,并非一直指向未来的矢量时间。因而,从现代性的时间观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认为“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在沈从文笔下实现了共振,全然否认沈从文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品格,会遗憾地丧失探索沈从文复杂思想的乐趣,也会错过体味沈从文作品独特美学韵味的机会。
沈从文的这种时间观念,与其自身的气质秉性关系密切,这种气质使其能够“修辞以立诚”,进而实现马斯洛“第二次天真”说所提倡的,不被他人之见所左右,突破流行理论的侵蚀,从而展现出艺术的创造力。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和接受的大多是有关“现代”抽象而宏大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沈从文对这些却没有多少兴趣,他是一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8]。沈从文承认,他非常喜欢狄更斯的《冰雪姻缘》《滑稽外史》和《贼史》,因为这三本书不像别的书尽说道理,与人隔膜,而是仅仅记下一些生活现象,丰富而有趣,这正是他自己“所要明白”的道理。这种气质偏好决定了沈从文理解“现代”的焦点必然更多地集中于自己目见耳闻的实在生活现象。对此,施蛰存在《滇云浦雨话从文》中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有丰富的现实性……不是语文修养的产物,而是他早年生活经验的录音”[9]。施蛰存这里讲的“录音”,类同达芬奇的“镜子说”,其本意并不是否定艺术家的创造力,而是认识到沈从文可以依从自己的真实感受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从而可以抗拒五四现代性理论的侵蚀。沈从文笔下的“现代”,是他“生活经验的录音”,也是当时中国的“平常”现象。在《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长河》和《湘行散记》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现代”与“新生活”“来了”,它们带给“乡下人”的,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不解、担忧、压力与焦虑:
“妇人正因为不知道‘新生活’是什么……现在又听人说‘新生活’也快要上来,不明白‘新生活’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拉人杀人。因此问了许多人,人都说不明白。……现在听说‘新生活’快要上来了,因此心中非常愁闷。竹笼中两只小猪,虽可以引她到一个好梦境中去。另外那个‘新生活’,却同个锤子一样,打在梦上粉碎了。”[5]41-42
与其说这些是沈从文从“乡下人”的视角对彼时“现代”进行嘲讽与解构,不如说这只是沈从文记录下的真实景象。用沈从文的话来说,他只是在讲平常的故事,《大小阮》中的“君子会”“棒棒团”是平常故事,《边城》《长河》也依然只是平常故事。这些平常故事寄托了现代人的人学理想,是具有现代性的;但同时沈从文的“生活录音”式的真实,又使其有别于主流精英们对“现代”乐观明朗、简单抽象的理解,展示了当时虚妄不实的现代景象,从而表现出“反现代性”抑或“非现代性”。
二、“清浅”的风景与风景中的人
“清浅”的风景与风景中元气丰沛的人,是沈从文文学创作魅力的重要所在,也是考察其“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重点。
首先来看风景描摹部分。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提到,近代文学经由“透视法”而从山水变为风景,并展现为“有深度的风景”。在现代性的语境下,人类成为万物的主宰,风景是被“看”、被宰制的对象,这一点在“透视法”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透视的方法是将许多线条汇聚到一个点,从而传递出视觉图像的深度。并且,透视法并非展现了我们真实的观看过程,而是方便我们去整理与控制所看到的东西。[10]沈从文的景物描绘虽然具有现代小说风景描写的特质,但总体上表现出“清浅”的特点,“反现代性”的意味更强烈一些。
我们以沈从文对川南内江的一段描写与王维《新晴野望》进行比较,来深入地分析沈从文风景描写的这种复杂性、独特性。
“昨天饭后,独自出去走走,到屋后高处悬壁上去,四野丘陵连亘,到处是褐土和淡绿色甘蔗林相间相映,空气透明,潮润,真是一片锦绣河山!各处山坡上都有人在点豌豆种。远处人小如米点,白布包头蓝长衫,远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山坳或悬崖间,照例都有几户人家在竹树林间扬起炊烟,田埂间有许多小孩子和家中小狗在一齐走动。山凹间冲里都是水田,一层层的,返着明光。有些田面淡绿,有些浅紫。四望无际情景全相同。一切如童话中景象。一切却十分实在。”[11]
这一段描写了四川内江的风光,乍看之下,与王维的“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在语言、内容和风格上都有相似甚或相同之处,这是非常明显的,在此不再赘述。需要注意的是,古今两处田园风光的描摹都富有中国传统绘画的画意而区别于“透视法”,如果说唐代的王维没有选择的可能,那么沈从文对传统绘画画法的选择,体现出对模仿与追随西方的现代性追求不一样的姿态。并且,与“透视法”呈现深度视觉图像相比,沈从文非“定位”“定向”和“定范围”地“看”,使其景物描写具有“浅”的特点,与透视法所体现的现代性不同,具有“反现代性”。
这种非定向的“看”使沈从文笔下的景物描写与风土人情刻画成为故事的“前景”,而不是纵深的“背景”,《边城》不能被理解为《翠翠的故事》,风景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不是渲染故事与人物的“陪衬”,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体”[12]123-124,景物本身自具意义。沈从文笔下的景物几乎不存在弥漫于古代山水泉林文字中 “仕”与“隐”的意念纠结,以及传统文化中“比德”的山水自然观。与王维《新晴野望》“将没有生命的大自然写出生命来”(叶嘉莹语)相比,沈从文的这段文字是“让这个世界自己表现自己”[12]11。在这里,沈从文与王维相似的地方在于他们都不使自己浓郁的情感去沾染山水,不同于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相异的地方是,沈从文在描述完与王维相类似的田园风光之后,他说,“一切如童话中景象。一切却十分实在。”“如童话中的景象”是从旁静观,有点类似《新晴野望》作为“旁观者”或“分享者”的王维。王维的“白水明田外”很可能来自谢脁在《还涂临渚》中的联句“白水田外明,孤岭松上出。即趣佳可淹,淹留非下秩。”面对“白水田外明”的风光,谢脁是怎么想的呢?他看到孤岭上的“松树”。“松树”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了独特意义,是人的一种高贵品格的象征。“即趣佳可淹,淹留非下秩”,言其久留在此的原因并不是贪恋“下秩”这样的小小官职,而是爱其山水可亲。钟嵘评论谢脁时,说其“意锐而才不足”,所以往往“末篇多踬”,即使考虑到这一点,联诗中的“士大夫”意识也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这一意识在王维的这首诗中也有,只是较为隐蔽一些。而沈从文“一切却十分实在”则意味着自身与眼前所见之景物并无内外高下之分别(沈从文在同一封信中说,他望着这些山寨总是眼睛湿蒙蒙的,他渴望自己的生命与这些印象结合起来以获得艺术的创造力),对于眼中看到的一切,他“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多少来为百物做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沈从文既不打算作为旁观者来与读者分享这些好风日,也不想用其映照自己的品格,创造出了让眼前之景自己表现自己的独有风格。
沈从文对风景的描摹,与柄谷行人所讲的现代文学中“有深度的风景”毫无牵涉,也迥异于传统文学中那些具有思想或道德深度的山水形象,从而呈现出“清浅”的美学风格,具有比较明显的“反现代性”。这两种“看”的方式,可以推究到沈从文选择诚实地面对生命中真实的印象,发抒自己的真感、真情,“我手写吾口”,从而与“现代性”保持了距离。更重要的是,沈从文因此做到“凭情以会通”,创造出一种接连着天地生命、“让这个世界自己表现自己”的新的艺术表现风格,在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山水田园文学史中独树一帜。这种风格也突破了“现代性”或“反现代性”可以笼括的范畴,这是用现代性的理论来打量沈从文景物描写时获得的对其独特性的理解。
我们再看沈从文作品里“风景中的人”。“风景中的人”的写作是沈从文自己认为有“些些特长”的,也是思考沈从文“现代性”与“非现代性”更加重要的部分。
20世纪初期,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这一西方舶来词进行了颇具工具理性色彩的“挪用”,这一“挪用”建立在对“现代性”时间的接纳之上,并确立了以“进步”为指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线性历史演进目标、呈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将西方现代文明理想化的特点。对一位作家或理论家的批判,需要将其放置于历史语境下加以理解,才能客观和有的放矢,这是“温情与敬意”的态度,也是 “知人论世”“文化诗学”或“事件化”的研究方法。从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性想象出发,沈从文风景描画中的人同样是“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并存的。沈从文塑造的生气蓬勃的人,是他对现代民族国家构想的一部分,同时,“乡下人”的姿态,又有别于以“西方”和“进步”为指南的现代性诉求。解志熙认为沈从文对理想人性的书写,以及其背后的民族性改造的人文理想,是对“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的呼应,与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一脉相承。杨联芬则指出,沈从文在“创作动机”或“再造民族精神”一类“目的”的层面上属于五四新文学,而再造的“过程”及其所依据的文化思想和价值判断这些基本的人文尺度不能与五四认同。[3]
具体来说,沈从文风景描写中对人物生气的描画、对理想人格的希冀,是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部分,这也是学界探讨沈从文“现代性”时比较着力的地方。其实,早在1930年代,苏雪林就提出沈从文的创作具有“民族国家想象”的成分,认为沈从文“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13]。事实上,沈从文思想的现代性还不止于此,“风景中的人”其实与五四时期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构建的理想人格一样,承祧了传统文化的理路,但主要闪现的是新时代的思想。大致来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价值取向中往往会或明或隐地伴随着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些追求偏好于把个体安身立命的期冀投寄于儒家仁爱之心、道家“心斋坐忘”以及禅宗“明心见性”的心学传统。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人格建构的设想,既属于这一传统,又拥有与传统文人“在心上用功”的不同新思路。20世纪初“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下,民族生存、社会生存和士人个体生存三种具有生存意义上的矛盾突然激化并纠缠在一起,知识界对人格建构给予特别关注,以期找寻到富国强民的路径。如近代魏晋研究在士人人格上倾注了较多热情,从谭嗣同、严复、梁启超到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现代中国美学建构生命形象和设计理想人格取向的确立,等等。这些人格建构的设想,在学理背景和构建思路上显然与传统文人有很大区别,沈从文也属于这一潮流。
不过,沈从文笔下元气充沛的人物与五四时期具有启蒙特性的理想人格又有所区别。以与影响较大的现代中国美学“审美人格”比较为例。“审美人格”的逻辑为,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人心太差”,因此要用“艺术”“审美”等来进行改造,再通过改造人心与灵魂解决现实的种种问题。因而,朱光潜痛心地讲“我们也要换个心才好”[14],倡导“人生的艺术化”,希冀通过人心的“净化”来拯救社会;蔡元培说中国人的灵魂出了问题,要以“美育代宗教”,期待让美育塑造出中国人的现代性;宗白华试图用“中国艺术心灵”建构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些主张振聋发聩,“审美”具有独立意识与启蒙理性,富有浓郁的五四色彩。相比之下,沈从文在讴歌热忱于人类前途、虔诚于工作的人的同时,作为“乡下人”,他并不习惯 “城里人”所谓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他的道德标准与爱憎与“城里人”是不同的。因此,沈从文“风景中的人”往往富有朝气、充满自由,胆量大、精力强,村妇农夫、贩夫走卒乃至土匪妓女都不是五四理性光晕下被启蒙的小人物,不是需要被“现代性”俯瞰或宰制的乡曲野村的有待开化的群体,而是存在于自然山水之中,与天地一体,充满生命的元气,庄严充实,令人感动。显然,沈从文“风景中的人”不同于五四时期对具有“现代性”特质的审美理想人格的构想。
再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虽然沈从文充满元气的人物形象与宗白华的“晋人之美”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相似性,即对生气和力量的偏爱,但是,沈从文“景中人”的这种“生动”,与同时期宗白华“晋人之美”包含的“生生不息”的区别,并不止于回溯到老子与《易经》的分别。宗白华美学的人格理想是“空灵”与“充实”的和谐,他早期提出“超世”与“入世”的人生观,号召“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有着非常明显的唯理崇真思想与德国哲学背景。另外,宗白华盛赞唐人诗歌中的民族精神、惊喜敦煌文化的“力之美”以及发掘魏晋风度的真精神与真血性,是带有非常明确的五四启蒙特征的。[12]151而沈从文元气丰沛的“乡下人”,则是对人自身生气的强调,他提倡有生命力的、审美的“人性”,与宗白华“晋人之美”中强调“生生不息”之精神有很大的不同。强调“动”之美的两种理想人格差异的背景是两人个性禀赋、成长经历和学理支撑的不同,这也是沈从文很难归入五四现代性主流思潮的重要原因。
沈从文对“乡下人”饱含赞赏之意的呈现,不仅仅像本雅明所说的,是作家远在他乡的空间与时代里感受到的乡愁和乌托邦,更是“湖南骡子”执拗地回溯真实的生命体验所磨砺出来的珠宝。沈从文“自我的发现”是“得其自”的过程,而非五四启蒙以现代理论为基础的“自我的觉醒”[12]151,这种真诚地面对自我的真实,使得作家没有启蒙者的优越姿态,但也不能说“乡下人”就完全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形成了很强的张力。
三、从“亦此亦彼”的思路看沈丛文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在沈从文身上看到“现代性”的因素,也可以看到“反现代性”的特质,甚至于沈从文已经超出了“现代性”与“反现代性”所能涵括的范围。如果考虑到“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更加复杂的内涵,问题就更为棘手且让人深思了。
五四时期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所得到的“进步”观念认为进步意味着势不可挡地使人类和社会发展到更加完美状态,这一对“现代性”的理解其实遮蔽了欧洲启蒙时代思想的宽泛、多元和复杂。在18世纪西方的思想家眼中,“进步”的含义是通过一连串相关的阶段取得的进展——也就是说,进步可能是积极的、向前的运动,也可能是消极的、向后的衰退,甚至还可能是循环的。启蒙哲学家康德的好友兼批评者哈曼则认为,进步意味着恢复原始的感受力和诗意的表达方式。秉持这样一些“现代性”的内涵来烛照沈从文的创作时,其思想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就更加难以仅仅用“现代性”或“反现代性”来涵括了。况且,“现代性是一个悖论的聚合、一个无法聚合的聚合。它将我们推入了一个大漩涡中,那里是永久的崩溃和更新;是争斗和矛盾;是含混和苦痛。”[15]现代性的内涵与边界总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国内外不少著名学者曾反思其使用的合法性,极端如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认为“现代性”无本质可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沈从文“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争论恝然置之,沈从文笔下那些平常故事牵引我们心绪的,是我们期待拥有怎样一种气质的“现在”或是“未来”,我们又如何拥有?这或许就是沈从文包含于现象中的“道理”,也是其作品的现实性之所在。“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学术界对这一难题的关注、搁置及重新发现,也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同呼吸,共命运”的。这场讨论聚讼不休,未来可以涉及的议题也不会在少数,这里试用“亦此亦彼”的思路对这一难题作初步的思考以抛砖引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上的细小研究,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16]
恩格斯“亦此亦彼”的思维方法可以在昆德拉、理查德·罗蒂那里看到,也引起了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童庆炳先生的重视。童庆炳先生认为,“恩格斯在书中提出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不一定非此即彼,可以‘亦此亦彼’。这是一种思考问题的重要方法,我不但记住了它,而且后来看问题,就往往采用‘亦此亦彼’的方法”[17]。“亦此亦彼”是童先生的学术研究态度,也是其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在“文学五十元”“内容与形式相互征服说”“当代文学创作的精神价值取向”和“文学创作中艺术情感双重取向”等研究中都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亦此亦彼”的思维特征。陶东风说“在我与童先生的长期交往中,我发现他学术研究的最大的特征是坚决拒斥所谓‘片面的深刻’,坚持‘鱼与熊掌都要’”[18]。这种“鱼与熊掌都要”的方法,被赵炎秋和杨晓青进一步概括为,在学术研究中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注重将彼此矛盾和对立的因素进行重新整合从而达到真理。[6]4
就沈从文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而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式的挖掘,确实有助于我们思究这位作家纸背的思想与情感,但“非此即彼”的思路在理解沈从文的复杂性时也可能会捉襟见肘,而“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恰好可以搁置将二者对立的思路,承认沈从文的复杂性,并由此领悟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竟然是沈从文独特魅力的重要原因,从而趋进沈从文思想的某些内里状态。沈从文倚重自己的真情实感,记录了湘西与现代“遭遇”的实景,成为对历史的一种直接、感性甚至最可信赖的表达,这样的表达避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并不少见的简单化、平面化、概念化或模式化的问题,也成为吸引我们阅读的一种力量。“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矛盾两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形成了极强的艺术与思想张力,这种张力来自于艺术领域的不二法则——真实,也造就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和耀眼。艺术家的“赤子其人”,成就了“星斗其文”。
理解沈从文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沈从文自己也曾感叹:“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8]或许,“亦此亦彼”可以作为一个切实的起点,启发我们对沈从文冲淡之中蕴含和隐伏的情意与悲音有会心的体悟和整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