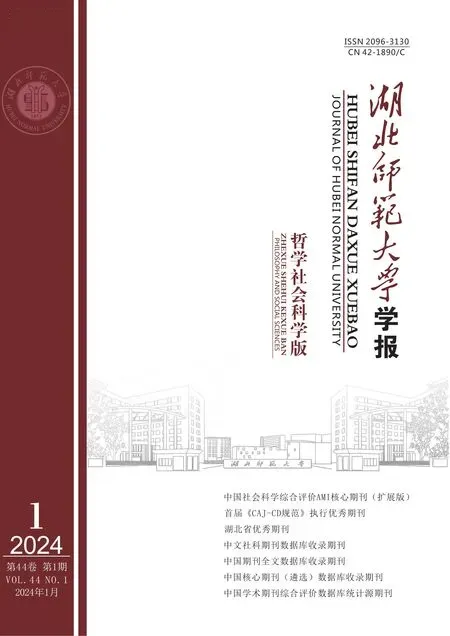不自证己罪原则于行政程序之适用
——以欧陆法为考察中心
徐孜男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前言
不自证己罪(nemo tenetur se ipsumaccusare)乃法治国之基本立场,“没有人必须自我控诉”“不得强迫任何人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人”,系立基于人性尊严的自明之理[1]。依不自证己罪原则,个人无须为自身犯罪的认定积极做出贡献,而仅负有消极协助与忍受的义务[2],换言之,不自证己罪原则禁止强迫个人主动配合刑事追诉,使其沦为国家机关发现事实真相的工具[3]。虽在刑事程序中,被告能够自由决定是否将自己作为犯罪的证明手段[4],然置于非刑事程序领域,景况便有所不同,特别是为了达成一定行政目的,法律或要求公民为真实完全之陈述并提出调查所需之证据,甚至还施加行政法上的不利益,以督促其协助行政机关澄清事案[5],此种情形遍及破产法、租税法、强制执行法及道路交通法等规范之中,在经济行政法领域更是司空见惯①。倘若国家机关为充分获取资讯以善尽监管职责,得课予公民行政法上之资讯提供与协力义务(Auskunfts-und Mitwirkungspflichten)[6],那么当公民将因履行该义务而引起对自己的刑事追诉时,此是否与不自证己罪原则有所扞格,遂生疑问。本文之写作,即端在检讨不自证己罪原则于行政程序中能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之问题。下文拟先简要介绍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裁判作为说明基础,再对其见解进行分析评释(二),继而引入德国立法判例以为借镜,探寻不自证己罪特权与行政协力义务的调和之道(三、四),最后总结本文论点,并结合目前我国法制的整体规范状况,指出未来的改进方向,代为结语(五)。
二、欧洲人权法院之标杆裁判
(一)芬克诉法国案
1993年的芬克案系欧洲人权法院对不自证己罪原则的首次表态,该案中法国海关官员根据税务机关提供的线索,依《海关法》之规定要求芬克出示银行账簿以了解其资产情况但遭到拒绝,芬克因此被法院判处1200法郎的罚金,但自始至终司法当局都没有将其刑事起诉。随后芬克申诉至欧洲人权法院,主张法国政府强迫其出示银行账簿违反不自证己罪原则,从而侵犯了自己依《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所享有的公正审判权。欧洲人权法院最终判定,法国海关之所以对芬克提起罚金之诉,意在获取特定文书以追诉其非法金融交易之犯罪——尽管他们根本不确定这些文书是否真实存在,由于无法或不愿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取这些文书,海关官员才试图强迫芬克提交他们所称的犯罪证据,但是,《海关法》的特殊性并不能作为侵犯被指控有刑事犯罪者保持沉默和不自证己罪权利的正当理由②。
(二)桑德斯诉英国案
本案涉及英国《1985年公司法》,为对抗公司欺诈等不法行为,该法规定公司的高级职员和负责人对检查员负有如实答复与协助的义务,不仅答复内容可以在刑事程序中作为证据使用,违反该义务者还会被判处藐视法庭罪。桑德斯共计参与了检查员组织的九次面谈,后来检察官在审判中援引了桑德斯的陈述,于是桑德斯被判犯有多项罪行。桑德斯向欧洲人权法院主张,个人有权不为自己的定罪提供证据,而本案中调查员的询问笔录“构成了公诉案件的重要部分”,这与《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的精神相抵触。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保持沉默和不自证己罪的权利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其要求检察官必须努力证明他们提出的指控,而不能倚仗胁迫、压制被告意志所取得的证据,在后来的刑事程序中使用个人在受到犯罪指控之前被迫作出的供述,同样侵犯了个人不自证己罪的权利。De Meyer法官在其协同意见书中还补充道,就支持起诉的目的而言,检查员面谈所得到的资讯相较于警察或司法官员通过严格意义上的刑事程序所获得的资讯,两者并无本质之不同,皆为确定被告刑事责任所需考量证据的一部分,既如此,检查员所为“行政性”或“预备性”调查便实际上属于刑事程序的一部分,自然也应适用不自证己罪原则③。
(三)国民诉瑞士案
在2001年的J.B.案中,瑞士税务机关怀疑申诉人未依法申报全部投资收入,遂发动逃税调查程序(tax-evasion proceedings)命其提交相关文书,在被拒绝后瑞士税务机关陆续对申诉人科处了四次罚金。瑞士法院声称,逃税调查程序属于真正的刑事程序,应适用《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之规定,但补税义务(supplementary tax)旨在督促公民缴纳所欠税款和补偿国家的税收损失,而非施加刑事制裁,故本案之肯綮,乃政府于逃税调查程序中可否要求负有补税义务之人提供其财务信息,而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盖若允许其保持沉默,常态的税务调查程序将不得不按照刑事追诉的方式运作。欧洲人权法院在此重申其对“刑事指控”(criminal charge)的自主解释权,并对不自证己罪特权的“刑事要素”作了进一步阐释,其认为判断某种程序是否属于刑事程序,应取决于三项标准:1.国内法对该程序的定性;2.违法行为的性质;3.违法者所受制裁的性质与严重程度。欧洲人权法院指出,本案程序具有多重目的,包括确定申诉人的应纳税额以及视情况责令补税或科处逃税罚金,并且无法明确区分究竟系逃税还是补税的调查程序,不过清楚的是,瑞士税务机关对申诉人科处的罚金具有惩戒性与威慑性,其数额亦不容忽视,毫无疑问具有刑罚性质,因此无论本案程序出于何种目的,均具备刑事指控之特征;此外,瑞士税务机关强迫申诉人出示相关文书虽是为了方便进行税基评估,然纵使查明申诉人有无未纳税收入非常重要,但不能排除这些文书有揭发其逃税罪行之可能,故瑞士政府的行为有违不自证己罪原则④。
(四)欧洲人权法院裁判之评释
强迫个人在行政程序中主动参与自己所涉犯罪的调查,同样违背了自我保护的自然法理念,不宁唯是,此种协力义务还会使个人陷入比一般刑事被告更加不利的境地,因为其被剥夺了选择“认罪奖金”(Geständnisbonus)而从轻量刑的机会[4]。欧洲人权法院虽然在上述案例中判决各国政府违反不自证己罪原则,却并未将不自证己罪原则明白适用于行政程序领域,申言之,芬克案虽发轫于海关程序,惟欧洲人权法院认定法国政府侵犯了芬克的不自证己罪特权,系因海关官员“以行政检查之名,行刑事侦查之实”,此时芬克的刑事被告地位已然形成,可谓其已经身处刑事程序之中。De Meyer法官对桑德斯案所包含的前后两段程序进行了合并观察,依其见解,若将个人为履行行政法义务而提出的证据用于刑事追诉,行政程序便成为刑事程序的一部分,不自证己罪原则的保障也不再局限于刑事程序正式发动之后,而须回溯至“前置”行政程序为实质取证之时[5]。J.B.案采取的解决途径则是重塑“刑事指控”的判断标准来扩展不自证己罪原则的适用范围。由此可见,欧洲人权法院的三则判例均不是针对非刑事法领域的不自证己罪问题而作,其并未正面回答不自证己罪原则的效力能否延伸至行政程序,而是通过直接将案涉程序认定为刑事程序回避了该问题。
但换个角度来看,以上判决似乎也可以理解为,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不自证己罪原则得适用于能够为刑事追诉搜集证据(芬克案与桑德斯案)及具有“准刑事”特征(J.B.案)的行政程序。前段结论不无道理,盖若行政机关得先藉行政协力义务强迫个人自曝犯罪,再将犯罪证据转交追诉机关,则行政协力义务无异于“变相之自白义务”[6],国家机关即可操弄程序,以迂回战术恣意游走在行政规范与刑事规范之间,进而架空不自证己罪原则[7],行政程序不啻不自证己罪原则的化外之地,为国家机关搜集犯罪证据大开方便之门,正所谓“假如于刑事程序之外得违背被告意愿强制取得证据,并在对其进行的刑事追诉中使用,沉默权的赋予便不过一纸空文”,昭然明甚。惟后一类行政程序或只会引起行政罚而无联结刑事追诉之可能,倘于此类行政程序中也适用不自证己罪原则,这是否逸脱了不自证己罪原则效力范围的最外延?关此,有学者主张,强迫个人协力促成对自身的行政罚,既违背人之常情,亦有损人性尊严,果尔行政程序除令个人有受刑事追诉之虞外,在仅涉及行政罚之情形,亦有适用不自证己罪原则之余地[8]。诚然,若不自证己罪原则与其所彰显的价值追求相伴而生、不可分离,那么强迫个人在行政罚程序中充当于己不利的证据,非不得谓与不自证己罪原则有悖,但不自证己罪原则的效力并不能因此想当然地覆盖其价值追求可触及的全部范围,否则不自证己罪特权将被曲解(尤其是“罪”的涵义),并对非刑事法领域产生侵蚀[9]。故是否在纯粹的非刑事程序中要求公民承担积极配合之义务,立法者应有一定自由评估的权力,只要遵守法律保留与比例原则,纵使公民将因此在受违反义务之制裁与自我揭发行政违法之间进退维谷,亦属立法政策选择之结果。但另一方面,行政罚动辄课予公民数万甚至上百万之罚金,或永久剥夺从事特定活动之法律资格,其对个人权利之侵害程度有时更苛于刑罚,刑事程序不因披着行政程序的外衣而易其本质,此种可能严重影响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行政罚程序,应有别于一般的行政罚程序而与刑事程序等同视之,在此即应有适用不自证己罪原则之必要[10]。欧洲人权法院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为德不卒的是,其所确立的判断标准仍较为笼统模糊,难以厘清准刑事程序与非刑事程序的界限,这还有待国内法院不断积累判例以做进一步解释。
三、不自证己罪特权与行政协力义务之调和
(一)免除行政协力义务之可行性
若要避免行政协力义务成为不自证己罪原则严密防卫的“阿喀琉斯之踵”,最直接的策略就是让公民在行政程序中也无须揭露自己的犯罪,使国家的资讯利益让位于个人潜在的刑事权利,德国法上的典型例子,如《联邦福利法》《对外贸易法》《武器法》等皆有规定:“负有资讯提供义务之人得拒绝提供相关资讯,如其答复将使自己或《民事诉讼法》第383条第1款第1至3项规定之亲属,有受刑事或行政追诉之虞。”在桑德斯案中英国政府曾辩称,个人权利的保障固然重要,但监督公司诚信经营、追诉其犯罪行为亦关乎公共利益,鉴于公司欺诈案件大多颇为复杂,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答复,并将其陈述用于刑事审判,实属必要之举,然而欧洲人权法院并未接受这套说辞,其认为不自证己罪原则应一视同仁地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刑事程序。常言道:“不计代价地发现真实,向来不是刑事诉讼法的原则”,行政协力义务之设定虽可经过立法权衡而取得合法基础,但此种权衡的空间并非没有边际,不得强迫任何人以自己的陈述为刑事定罪或施加相应制裁提供前提条件,乃不自证己罪原则之核心领域⑤,立法者不能以案情复杂或维护公共利益为由完全否定个人源于人性尊严的不自证己罪权利,以此论之欧洲人权法院的结论可资赞同。但与此同时,欧洲人权法院也承认:“如果要求预备性调查也受到《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的司法形塑,将不当妨碍政府对于复杂金融和商业活动的有效监管”,故欧洲人权法院审查本案程序是否侵犯了桑德斯的公正审判权,“唯一关注的是相关陈述在刑事审判中的使用”⑥,由此引发的疑问是,若为贯彻不自证己罪原则而免除公民一切可能揭露自身犯罪的行政协力义务,是否有滑向极端之嫌?
现代社会可谓信息社会,行政行为之作出,无论是施加义务抑或给予恩惠,皆需依靠各种信息资料,“正确的情报是公正、合理的行政所不可欠缺的”[11]“资料有如行政引擎运转之燃料,没有它,行政机关将不能明智地实践法规制定和裁决之实质权力”[12],洵属至言。为减少行政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实现案件事实的最佳认定,徒以惩戒相威胁尚不足够,还需赋予行政机关适当的特殊权力,使其不仅能实施搜查、扣押等强制措施,更得要求当事人参与调查并提出其所知悉的事实及证据方法,虽然这种合作的要求通常只是一种负担(Belastung)而非义务(Pflicht),并无强制履行之效力,但若当事人不履行此项程序负担,也会产生一些不成文的间接不利益法律效果,如证据评价上的不利推论、行政机关的客观义务减轻和国家赔偿上的与有过失等[13]。因而有学者主张,法不强人所难,行政协力义务之设定亦须符合比例原则与合理原则,当履行将使公民有受刑事追诉之虞时,应认欠缺期待可能性而构成行政协力义务之界限[14]。惟循此见解,行政机关可采用的调查手段也将被限缩,势必影响其事证搜集之能力,继而可能导致执法成本增加、行政程序窒碍难行,这又该如何克服?可否透过不利证据评价或降低证明度使行政机关顺利完成其举证?显然,该法律效果只适用于当事人未依法履行行政协力义务之情形,如协力义务已被免除,则无理由再使当事人因拒绝合作而承受不利益,亦即在行政程序中当事人有权对犯罪信息缄口不言,行政机关也不可因此施加于其不利之影响。然若如此,不仅会挫伤执行刑事法律以外的其他公共利益,使国家难以对现代社会的多元化需求作出回应,个人也将获益于犯罪行为而不必履行行政法义务,刑事犯罪在先,行政优待在后,皆受不自证己罪原则之庇护,守法之人的境遇尚不如违法之徒,此与不自证己罪原则的初衷龃龉不合[15]。
(二)可能的选择:强制手段禁止与暂缓协力
不自证己罪特权体现了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但随着特权的含义从“任何人在受到正式指控之前都不应被要求宣誓回答问题”发展到“不得要求任何人提供于己不利的证据”的宽泛主张,其道德合理性也备受指摘,特权仿佛不再是对守法公民的保护,而被人们视为违法者的避风港。故20世纪末以来,各法治国家对不自证己罪特权的解释也变得不再那么慷慨,特别是当面对其与政府利益的紧张关系时,法院从未放弃限制特权以降低其援引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而这些努力也为我们正确认识不自证己罪特权给予了一些教诲:首先,不自证己罪特权无意促成新的不公正[16];其次,不自证己罪特权不会免除法律课予所有处境相似的人的社会义务[17];最后,对不自证己罪特权的保障不是绝对的,并非必须以牺牲其他公共利益为代价。职是之故,本文主张,倘若行政目的无法舍弃,纵然公民可能要将自己的罪行开诚布公,亦应保留其行政协力义务。那么接下来亟待解决的课题便是,此与不自证己罪原则之间的冲突应怎样调和?兹举两种德国税法领域相关立法判例所采用的方案说明之。
1.强制手段禁止
基于税收的负担平等性和价值中立性,德国《租税通则》(AO)规定犯罪所得亦须纳税,纳税人应向稽征机关完整、真实地提出其掌控范围内的课税重要事实和证据,除该义务可通过罚款、替代履行或直接强制来执行外,未遵守该义务者还将成立逃税罪。由于诚实申报纳税是保障国家财政利益的需要,免除罪犯的诚实申报义务所形成的“第二次不公平”也难以接受,故在德国此项义务的合宪性并未受到过强烈质疑。惟该法第30条第4款还规定,纳税人提供的资料可在针对其进行的租税刑事程序(Steuerstrafverfahrens)中作为证据使用,是以公民作为犯罪嫌疑人时尚可保持沉默,身为纳税人时却必须主动向国家机关交付自己的罪证,这岂不矛盾?于是德国立法者在该法第393条第1款第2句中特别规定,如果在征税程序(Besteuerungsverfahren)中纳税人将被迫供认租税犯罪或租税违反秩序之行为,则不得对其采取上述强制措施,此即所谓强制手段禁止(Zwangsmittelverbot)。
虽禁止使用强制手段,但纳税人的协力义务依旧存在,故其拒绝配合之行为仍可在推计课税时加以斟酌⑦。普遍的看法是,税基评估旨在使调查结论尽可能地贴近实际情况而不具有惩罚性,即使稽征机关出现了估算上的错误,也应归咎于不愿提供协助的纳税人,此乃征税程序采行职权调查原则的必然结果,况且不自证己罪特权并不保护个人免受经济上的不利益,所以除非存在故意偏离实际为推计课税,企图依靠经济压力勒迫纳税人揭露犯罪之情形,否则不构成对自证己罪的间接强制[18]。然而,实务中税基评估对纳税人来说仍然是一种威胁,盖其既身处两难困境之中,自对反驳稽征机关确定的“可疑数额”一事有所忌惮,以至税基评估通常在纳税人尚没有机会在不危及其他利益的前提下为自己进行适当辩护之前,就已经被执行了[19],即便纳税人有权提出异议,因其应为异议的成立提出事实和理由,这种举证责任的倒置也会产生强迫自证己罪的效果[20]。再者,为了主张强制手段禁止,纳税人须揭露自己的罪行,尽管根据判例其仅需说明非法资产的范围即为已足,而不必提供有关资产来源的信息⑧,但这只不过是降低了证明度,纳税人的陈述仍然会引起稽征机关对其刑事犯罪的初始怀疑(Anfangsverdacht)⑨,并最终成为还原犯罪事实的“第一块马赛克”。
2.暂缓协力
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⑩,为保障纳税人不自证己罪的自由,同时防止国家的财政损失永久化,如果针对同一税收事实已经启动了租税刑事程序,那么在租税刑事程序终结之前纳税人的诚实申报义务可以暂时中止。但这同样不是一种明智的对策,盖若租税刑事程序进展滞缓,国家财政利益的落实恐将因此迟误,加之稽征机关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折返追究纳税人的行政责任,并命其重新参与案件调查,倘案涉征税程序依欧洲人权法院所确立的标准本身即属于准刑事程序,此时亦将违反一事不再理之基本原则。概言之,强制手段禁止与暂缓协力两种方案均不能妥善调和纳税人不自证己罪权利与国家财政利益间的冲突。
四、未来的出路:以证据运用禁止为中心
(一)先决问题:不自证己罪原则之底线
在探寻一条适当的中间路径之前,我们需要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不自证己罪原则不能逾越的底线是什么?如前文曾提到的,德国法传统上认为,只要不强迫个人以自己的陈述为刑事定罪或施加相应制裁提供前提条件,即未侵犯不自证己罪原则的核心领域,于此之外,是否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课予公民积极协力之法律义务,以及要求公民提交的文书等证据资料能否在对其进行的刑事追诉中使用,立法者拥有自由衡量之权力。然而欧洲人权法院否定了这一论点,在“乔罗诉德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指出,尽管不自证己罪特权主要涉及对被告保持沉默意思的尊重,但根据本院已往的判例,不自证己罪原则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含义,而判断某种程序是否对其造成了侵害,应依次检视以下几个方面:为获取证据而使用强制力的性质和程度;调查和惩罚犯罪对于保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是否配有适当的程序性保障措施及所获信息资料的用途。本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德国政府违反不自证己罪原则,系因:第一,德国政府实施催吐取证严重干预了申诉人的身心健康,这是不人道且有辱人格的;第二,申诉人最后仅被判处六个月的缓刑,追究其罪责的公益需要尚不足以成为催吐取证的理由;第三,催吐取证是在没有全面检查申诉人身体承受能力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不符合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四,德国法院将催吐取得的毒品作为认定申诉人有罪的关键证据。有鉴于此,本文主张,若为达成行政目的而强迫个人提供其犯罪资讯,则强迫必须在法律保留的基础上,以人道与合比例的方式,依法定程序而为之,并应设置预防措施,使藉此获得的任何资料不致成为刑事指控的不利证据,此乃不自证己罪原则无可退让之最低要求。前项诫命较易理解,下文将重点透过德国宪法法院破产人裁定(Gemeinschuldnerbeschluss)对后一项诫命展开阐释,破产人裁定虽并非缘起于行政程序,但其堪为处理非刑事法领域不自证己罪问题的效法典范。
(二)破产人裁定:宪法层次的证据禁止
德国宪法法院破产人裁定之出炉,不仅确立了不自证己罪原则的宪法地位,更掀起了修订非刑事法规的大浪潮,迄今余波未平。依德国旧《破产法》(KO)之规定及学说实务之见解,破产法院应通过讯问破产人、听取证言与鉴定意见等方式进行必要调查以澄清诉讼状况,破产人有义务回答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委员会和债权人会议的问询,否则破产法院得拘提并于听审后拘留破产人,准此,破产人只能踌躇于遵守法定义务而自证己罪,或为虚假陈述而另犯新罪,或保持沉默而承受强制处分。就此三难困境,德国宪法法院指出,宪法对人格权的保护不是毫无例外的,而应以不侵犯他人权利为界限,个人须接受立法者为维系和促进社会共生而对其自由作出的合理限制,被告、诉讼当事人与证人享有的保持沉默和拒绝作证的权利,并不适用于具有法律上之特殊原因而有义务向他人或国家机关提供资讯之人,盖其不自证己罪的权利与他人的资讯需求相冲突,立法者有权衡量各主体之间彼此对立的利益。既然债权人因破产人的行为而蒙受财产损失,债权人的利益就应优先于破产人的利益受到保护,况且破产人是破产程序中最重要的资讯提供者,破产程序之依法合宜进行尚仰赖其所提供的资讯,故破产人应负担无限制的答复义务;不过,此项义务仅为实现破产程序之目的而存在,如果违背破产人的意愿将其被迫作出的自我指控挪用于刑事追诉,破产人的人格权将受到不合比例的损害,破产人有义务提供资讯并不意味着其有义务贡献己罪,这不仅缺乏期待可能性,也有损人性尊严,故破产人无限制的答复义务还应以证据使用禁止(Verwertungsverbot)加以补充。
(三)证据运用禁止之效力
破产人裁定作成时,德国《破产法》尚未订有证据使用禁止的明文规定,为填补该法律漏洞,德国宪法法院在此类推适用了《租税通则》第393条第2款,惟该款原文系纳税人为履行税法义务而向稽征机关披露之事证“不得运用(verwendet)于追诉其租税犯罪以外之犯罪行为”,于世纪末出台的《债务清理法》(InsO)第97条亦沿用这一表述,此又被称为证据的“运用禁止”(Verwendungsverbot),与破产人裁定“使用禁止”之措辞略有不同。证据使用禁止是指法院不得将已经取得的证据资料作为自由心证的对象与判决的基础[21],殆无异议,然证据运用禁止具有何种效力,却众说纷纭。
最激进的观点是,证据运用禁止要求“全面禁止利用”或“禁止追诉”(Verfolgungsverbot)[22],债务人为履行法定义务而披露的事证不得用来建立犯罪的初始怀疑,亦不得作为发动刑事侦查措施与调取其他证据的根据[23],此外还应责令办案人员保密,非经债务人同意不得作证,并从档案中删除相关内容,使追诉机关无法接触到这些资讯[24]。保守派则不承认这种放射效力,但此派的见解也莫衷一是,有认为证据运用禁止之规定并不禁止收集证据(Beweiserhebungsverbot),其使用禁止之效力也不及于衍生证据,因而不会阻碍追诉机关获取相关资讯并据此启动刑事侦查程序[25],反之将造成“有高犯罪能量的债务人只需在破产管理人或破产法院第一次问询时将自己的罪行和盘托出,便能够完全逃避被刑事起诉”的荒谬局面[26]。此种担忧未免有些过甚其词,盖追诉机关已经掌握或通过其他途径取得的事实证据仍然可以使用,即使债务人先前或后来提供了相同的资讯[27],况且正如“毒树之果”所宣示的那样:如果允许追诉机关在债务人已经指明的道路上继续侦查以发掘其他罪证,那么禁止使用原始证据对不自证己罪特权的保护便徒劳无功。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债务人提供的资讯可以用来建立犯罪的初始怀疑,因为法律仅禁止在刑事程序中运用这些资讯,而犯罪初始怀疑的建立发生在刑事程序开启之前;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确保债务人不会被迫成为于己不利的证据,因此在主审程序中,检察官的证据链不能以相关资讯或自该资讯间接取得的事实证据为基础,若检察官无法证明其提出的证据拥有独立的来源,该证据即没有证据能力[28]。然而,对不自证己罪特权的侵犯并不以实际在审判中使用强制取得的证据为前提,且证据来源的区分虽从学理层面上来看比较清晰,付诸实践操作却绝非易事,因为“检察机关的思考不被法律束缚”,一旦其从别处获悉债务人的罪证,后续的追诉工作便难免会受到影响。故依本文之见,债务人披露其犯罪资讯乃基于破产程序非刑事目的之需要,这不仅是披露义务正当性之所在,也是对相关资讯用途的限制,既资讯收集之目的已经明确化,俟后之利用行为亦应与此相符而单一化,一言以蔽之,对证据运用禁止效力的正确理解应当是:个人为履行非刑事法义务而披露的信息资料不得为针对其进行的刑事追诉活动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它们对检察机关而言从未存在过”。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德国学说上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证据运用禁止不适用于债务人根据税法、商事法及社会保险法等法律例行记录保存的文书,因为其不属于履行《债务清理法》第97条所课资讯提供义务之结果[29],此可谓德国版的“要求记录规则”(Required Documents Doctrine)。当然,不自证己罪原则并不排斥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而要求公民记录提交特定的信息,相反从法律到政府规章,此类规定俯拾皆是,但当这些信息可能会成为有罪证据链的一环时,个人即应受到不自证己罪特权的保护,此不因证据形成的法律依据不同而有所区别,更重要的是,如果仅仅因为立法要求保存这些信息,公民就有义务主动将其披露并自我指控,国家机关便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制定一项法令从而规避不自证己罪原则。另有论者,尽管证据是根据债务人提供的资讯非法取得的,但倘若通过法律上无异议的方式同样可以找到这些证据,则取证程序上的瑕疵不会产生运用禁止之效力,此又可称为非刑事法领域的“假设侦查流程理论”(HypothetischeErmittlungsverläufe)。然卜卦灵不灵验日后还可印证,站在事后角度去猜测未曾发生之事的可能性,根本就是一种臆想,何况即使这种假定的因果关系能够成立,也无法否认证据的取得实际上受益于债务人所提供资讯的事实。
五、结语
假如于行政程序中得强迫个人提交犯罪证据,并在对其进行的刑事追诉中使用,那么即使刑事程序对不自证己罪特权的保障天衣无缝,也将是形同虚设,因此不自证己罪原则在行政程序领域的发展,其重要性不容小觑。为因应行政协力义务对不自证己罪原则的冲击,有多种调和方案可供立法选择,在特定的法律体系中,不同的方案也可能并存。归纳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不自证己罪原则得适用于能够为刑事追诉搜集证据以及具有“准刑事”特征的行政程序,惟后者的认定应格外谨慎,以防对非刑事法领域造成过度干涉。至于适用之方式,为平衡兼顾国家的行政利益与个人不自证己罪的权利,本文主张纵然有强迫公民揭露犯罪之效果,亦应保留其行政协力义务,但强迫必须遵循法律保留、正当程序与比例原则,并辅之以证据运用禁止之规定,使藉此所获的任何资料不致成为刑事指控的不利证据。
凡有关不自证己罪原则之问题,在欧洲人权法院和德国总是吵得沸沸扬扬,反观其在我国现行法制中的处境,却可谓内忧外患。内忧者,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虽订有“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之文本,其含义至今仍模糊不清,学说和司法实践对法条的理解也各不相谋。外患者,我国行政法上存在许多要求公民如实回答或提交证据的规定,且行政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等材料,还可以转化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尽管立法部门的解释排除了当事人归罪性陈述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但其衍生的实物证据应如何处置,却未曾着墨。我国法制改革的当务之急,一是应确立主动基准的不自证己罪原则,并肯认其基本人权地位,使不自证己罪原则的效力范围不再局限于刑事程序领域;二是应在刑事诉讼法与各行政法规中建立周密完备的证据运用禁止制度,为此首先应阻截行政机关与刑事机关之间的资讯流通,规定公民为履行行政协力义务而披露的犯罪信息资料,未经其同意,刑事机关不得调取,也不得作为实施搜查扣押等强制措施的标的,否则行政机关将沦为犯罪证据的中转站。如果刑事机关已经从行政机关处获取了相关资讯,除不得将其作为发动进一步追诉活动的依据之外,还应责令办案人员回避。最后,当案件已行至审判阶段,由于违反证据运用禁止之规定并不构成程序障碍(Verfahrenshindernis),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若法院根据被告的异议,审查认定检察官提出的证据与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提供的证据同一或指向同一事实,检察官又无法证明其证据系通过其他途径而取得者,则法院应排除相关证据,关于此处证明度之要求,虽证据来源之事实无须与犯罪构成要件等量齐观,然为避免刑事机关藉行政程序掩人耳目,间接强迫个人提供自我入罪之资讯,宜令其承担“高度盖然性”之举证责任。虽然此般大刀阔斧的改革可能会影响国家机关迅速有力地打击犯罪,但这不应成为折损不自证己罪基本人权的理由,这所宣示的也正是:没有不用付出多少代价的法治国原则。
注释:
①如我国《税收征管法》第64条、《企业所得税法》第44条、《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7条、《药品管理法》第99条、《行政处罚法》第55条、《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52条等。
②ECHR, Funke v. France (25 February 1993), Application no.10828/84.
③ECHR, Saund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17 December 1996), Application no. 19187/91.
④ECHR,J.B. v. Switzerland (3 May 2001),Application no. 31827/96.
⑤BVerfGNStZ 1993, 482;BGH NJW 1960, 1580.
⑥有学者认为欧洲人权法院的立场是,若未将所获证据用于刑事审判,则先前在行政程序中强迫个人揭露犯罪的行为不构成对不自证己罪特权的侵犯,因为“特权不适用于刑事法之外”。See Trechsel, S.Human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349.但本文认为欧洲人权法院在此仅承认了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强迫个人揭露犯罪的正当性,但其并未明确表示“强迫揭露犯罪”本身是否被不自证己罪原则所禁止,而从后来的判例中可以看出欧洲人权法院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
⑦BFH BeckRS 2004, 25007404; 2005, 25008878.
⑧BGH NStZ-RR 2004, 242.
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证人若有自证己罪之虞得行使拒绝证言权,判例学说一致认为“自证己罪之虞”发生在证人的答复将引起对其犯罪的初始怀疑之时。
⑩BGH NJW 2002, 1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