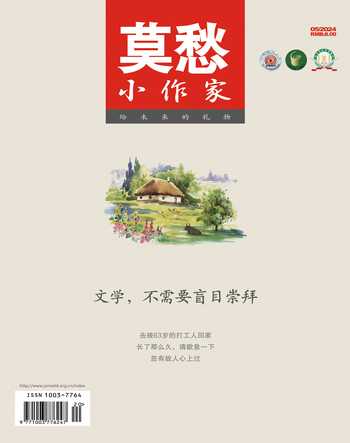文学,不需要盲目崇拜

周国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无锡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有作品《青城诗抄》《夕阳风笛》《无题》《笨拙境界》《闲思杂集》《四俊散记》《弟弟最后的日子》等。先后获第二届中国地域诗歌奖大奖、江苏省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太湖文学奖等28个文学奖项。
经常有年轻朋友跟我讨论阅读与写作的技巧,我认为,读书为文的最高目的和境界,是做一个真正的好人;而写作是一门学问。一些写手谈起这一话题,时有高论,令人感佩。有人问我对此如何看,我却木讷而窘迫,无言以对,莫名想起契诃夫所云:“写作的技巧,就是删掉一切多余之字的技巧。”以下即我对写作的一些看法。
真实,创作的生命力
散文与小说,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散文贵在“真”,但事实上很难做到绝对真实。想象、记忆误差、选择性记忆等等,都会导致非真实成分的产生。这很正常,散文允许少量、微量的非真实成分存在,关键要节制,最大限度减少非真实成分的掺入。掺“水”较多即失真,就不仅是矫揉造作,而是造假了。
虽说文无定法,表现手法各异,难断孰优孰劣。然而,散文或随笔的书写,要么是文学性与思想性高度融合,以深广度辐射见长;要么是率性随意,幽默机智,以富有趣味性耐人咀嚼出彩。与小说家较多考虑“读者意识”、编织精彩故事情节吸引读者不同,散文作家宜淡化“读者意识”,顺应心灵的指引,以创作出情感充盈、简约隽永的文本为重。
简淡素朴,语言美的高级形态
语言始终以简淡素朴为宜为高。文字只要“够”表达即可。能将深邃思想蕴藏于细节中,引人反复品味、领悟其隐含之意,乃大家高手。
行文进入宜快忌绕;过程宜明暗交替,适当跳跃,气脉贯通;思维宜多维度拓展;收尾则宜干脆,戛然而止却又回味无穷。
有人说:“散文是语言的散步,诗歌是语言的舞蹈。”这个比喻比较形象,也有道理。常用的汉字也就几千个,任由作者搭配、组装、串联,组合的好坏,决定了文章水准的高低。
有一类作家,在语言上下足功夫,竭力追求异于他人的语言风格,专致打造辨识度,但过度追求,往往会有刻意雕琢的痕迹,甚至滑入做作的泥淖,仿佛精心掘一口深井,用力过猛,一不小心,落入井底难以自拔。语言风格自然而然为宜。
你爱文字,文字也会爱你;你爱文字愈深,文字就会加倍爱你。任何付出,都有回报。
文字功底之外,生活的积累和沉淀,阅历的丰富,识见的提炼,知识的储备,学养修为的贯通,思想(哲学)资源的充沛,都是写好文章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对已用滥、贬值了的语言,进行改造、净化,乃至再造,使其更精纯、鲜活,更富弹性、张力,拥有更高层面指涉心灵、揭示存在的能力,应当是为文者的自觉修为。用最经济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容;用最平白的文字,表述最灵动的语境。
一些人常自云很敬畏文字,敬畏文学。可你所谓的敬畏,不就是把文字刻意雕琢得精细、简练和标致一些,甚至唯美一点吗?但,你敬畏后的文字和作品,有否提供文学性、思想性、趣味性的交融呈现,有无人生、人性、苦难与社会现实的观照穿透,从而使读者获得精神性、审美性的体验和启迪?
所以,文字纵然再好再美,设若达不到哲学、思想层面上的高度,难称上乘之作。
格局,写作者顶级的修炼
为文要有宇宙精神,思维和视野所及乃天地人与万物苍生。知“万物皆有灵”,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相无”,才会以众生平等的尺度,满怀悲悯,多维度、多向度思考和叙写事物的本质。文章所透露的,不仅是作者的学识和才华,更是作者的格调、襟怀、气势和格局,以及对宇宙、生命本原、人性的领悟和认知程度。
量与质是辩证的,没有相当的写作量,作品便难有较高的品质。从这一角度讲,质量似乎来自数量的基数大小,却又不尽然,人的智力、精力、知识库存、认知能力等,都是有限的,甚至会枯竭。读书等“充电”虽会有所弥补,但总归有上限的。这种情形下,如无再次突破瓶颈的可能,仍在无休止地写,变着法子写,无疑是自欺。写那么多平庸的“翻烧饼”文字何苦呢,不如不写,读者也会不买账。
一个作者若要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并非炒作、包装,官方钦定而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天分(优异天赋,悟性);情分(用情专注勤奋,锲而不舍);运势(运气,机缘)。三者合一,不成功才怪呢。反之,很难说。
文学,不需要盲目崇拜
绝大多数畅销书都会被时间逐步淘汰,所以,完全用不着去崇拜谁,也不要以获奖为尺度,去衡量一本书的质量,更无必要对文坛乃至文学的功用抱过多幻想。文学并不神秘,无须迷信。
为文忌迎合之作,作家须有批判意识,服从良心,恪守良知,葆有文人风骨,关注现实中的疾苦,为社会公平正义鼓与呼。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就像做人要干净一样,文字也必须干净。干净,才有力量。
没有人是别人写作上的真正老师,语文老师、编辑、作家、评论家、书籍,可以给你一些點拨或启发,甚至有所触动、推动,却教不了你写出锦绣文章。文学创作是极具个性化的劳动,是一个边写边悟、边悟边写的循环过程,没有捷径可走。
在我心里,没有什么一级作家(“文学创作一级”的虚用)、二级作家、三级作家之分,只有一流、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作家的区别。作家,得靠作品说话,而非职称和头衔。有些所谓名家,名不副实,还赫然罗列一串“代表作”,令人反胃:一个作家,哪来这么多代表作?一生中,能有一两部上乘之作已属莫大造化;甚至,有一二篇文章、几句诗或格言传世,已很了不起,因任何人都有局限,思想的、时代环境的、体力精力等等限度和制约因素。
不为写作而写作,不为获奖而写作,不写没感觉的东西,不写应景、命题之作,不写迎合之作;写有感觉的东西,写内心深处最想表达的东西,写屡屡冲动、难以释怀和非写不可的东西,这是我写作一贯之遵循。且,生活始终比写作重要,写作比获奖重要。
作家,应该是安静的
我从没反对“作家是孤独的,孤独是财富”之类的说辞,但我更倾向于作家是安静的,需要以安静之心,认真观察并思考宇宙万物、人性生命、历史纵横、社会现实和人间百态,敏锐于其间的内在关联;进而退入内心,观照自己与之外的雷同或异同的联系,以独特的经验体悟,写出迥异于别人的真实感受,从而更好地彰显别人无法替代的个性。故,写作是心灵的事业,也是安静的事业;作家的对话对象包罗万象,也包括自己,即便其作品仅有一个读者,他也是在向人类世界发表意见。
创作需要热情,甚至激情,以保证创作时的饱满情感,供应文章舒展之需。但,也需要沉静,以适度的理性元素,节制过分的感性激情。只是这种理性认识的成分,尽量要拿捏得有分寸,以助于文章的精神性呈现,而不致影响作品的文学性。
与学问家做学问搞学术不同,作家是搞创作,不能“掉书袋”,故作高深,更忌酸腐。既然是文学创作,就应该创造出异于别人的、独特的、生机勃勃的东西;设若不是,则是做作、造作,甚至下作。
也曾读过几本大名家的散文作品,书中一会儿东方,一会儿西方,旁征博引,时不时夹杂些英文,更是频频用典,迫使你中断阅读去稽考。这种作品,类似飙车,有炫技之嫌,不读也罢。
文学最难的是不能重复自己,即便是隐性的重复也不行。它应该是纯粹的不可复制。不可复制意味着不断创新和突破。
为读者提供思想、审美、趣味等可资心灵滋养的价值要素,促使其思索、辨识人世间真假善恶美丑,精神和人格得以独立,生命得以化育成长,这是作家写作的应有之义,也是作家文学创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追求目标,也是文学的主要功用之一。但是,放眼目下文坛,有多少作家是基于文学这一纯粹目的在写作?有些奔奖项、排行榜、版税和头衔等去了。
见过一些自以为是的作家,头衔一大堆,好为人师,经常穿梭于文青之间,热衷搞文学讲座、文学笔会、文学赛事,指指点点,混吃混住混玩混名声,不以为耻。这类人,充其量只是一些误人利己的江湖活动家。
作家的名声和作品的质量,并不能简单认为成正比,因为难免存在垄断文坛、垄断评奖、互相吹捧、炒作、运作等等现象。所以,读者不能一味跟风,而是要有自己的思考。
艺术,还是以单纯为上佳,单纯之中蕴丰富。但,要做到单纯,往往比复杂更难,就像写出白描般的文字,要比浓墨重彩难得多一样。有些作家叙述不紧不慢,笔调淡淡的,文字平白简洁,丝丝入扣,话外有话,音外有声,意味深远,叫人咀嚼和沉思。
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自媒体的普及,使人的時空观发生了变化,便捷、轻快式的阅读,成了一些人的偏好。这就对作者行文的进入、语速、句式、节奏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有的作者以简洁明了的笔法,顺应和适应了这一潮流,而不少作者却不为所动,只按自己的习惯写作,甚至仍保留“围炉夜话”般的叙事方式,这也不失为一种难能可贵的坚守。
文学,应该保持单纯。这是我最想跟年轻朋友说的一句话。
编辑 木木 6913729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