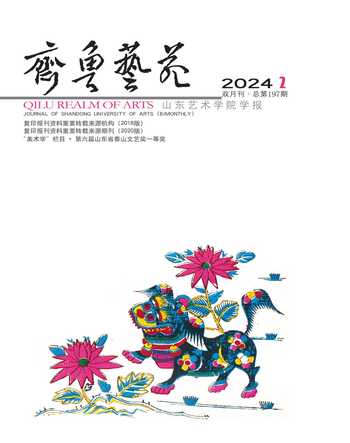晚明徽州《程氏墨苑》刊刻缘起考
程国栋
摘 要:本文聚焦于晚明时期徽州墨商程大约编刻的版画墨样图集《程氏墨苑》,详考此书刊刻背后的动因,即程大约与《方氏墨谱》编者方于鲁之间的一段恩怨。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时徽州两大墨商竞争的史实,以及诸多士人介入纷争而构成的舆论场。要之,方程二家在制墨业的竞争超出了一般商业的范畴,程大约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也远超一般工匠,在方于鲁寻求文化认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本非竞争主题的版画艺术却因此受益而在晚明的徽州迎来爆发,获得了出类拔萃的视觉效果。
关键词:《程氏墨苑》;程大约;徽州版画;《方氏墨谱》;方于鲁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236(2024)02-0060-09
晚明徽州滋兰堂刊《程氏墨苑》,由歙县墨商程大约辑成,原本是关于程氏自家墨店所制精品墨锭的宣传图册,但因其配图丰美,世所罕有,从而成为明清徽州版画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在中国古版画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不过它并不是徽州首例以版画插图称名于世的墨书。众所周知,晚明时期徽州地区的制墨业已经享誉全国,在《程氏墨苑》诞生之前,就已经有歙县方氏美荫堂的《方氏墨谱》大放异彩。两本墨书一先一后,争奇斗艳,无疑为中国古版画史平添了许多光彩。至于《程氏墨苑》版画为何后来居上,除了名画家和名刻工这些表面因素外,就不得不提及《方氏墨谱》的编者方于鲁。方氏不仅是程大约生前头号的商业对手,更是后者最憎恶的人之一。时至今日,当我们翻看《程氏墨苑》,犹能体察到这一页页华丽的图文背后,充斥着向《方氏墨谱》挑战的意味。但若将二者置于一起,则又不难发现两套版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困惑之余,我们不禁要问,方氏和程氏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两人的恩怨对各自的制墨业乃至徽州版画又产生了何种影响?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两本墨书背后的故事展开过分析,但结论仍嫌浅略。是故笔者欲借此文,以最大限度地还原程大约制作《墨苑》的来龙去脉。
一、《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的概况
《方氏墨谱》初刊于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根据书中所附汪道昆的“墨谱引”(署年為“癸未”),可知此谱从酝酿到梓行,约花了六年时间。[1](P1)《方式墨谱》问世后曾经历过多次再版,据林丽江博士考察,现存分藏在全球各大图书馆博物馆的版本就多达32个,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的记录,被国内公家收藏的更超过了50套。[2](P139-140、186)兹以刊行较早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刊本为例,此谱分六卷八册二函,卷是按墨的主题类别而分的,依次为:“国宝”“国华”“博古”“博物”“法宝”“鸿宝”,共计383个墨样,而这差不多也就是全书版画图像的数量。卷六图后、第七和第八册为众多同时代文人的序、赞等文字。全书由丁云鹏、吴廷羽、俞康中三位画家担纲图绘,徽州名工黄德时、黄德懋、黄守言负责雕版。
这数百帧版画本意虽是对外宣传自家的徽墨,但由于墨的设计内容涵盖了风景、人物、动物、植物、器物、神话、历史、宗教、民俗等等,造型又多样纷呈,故而画面荟萃了世间万象和奇思妙想,令人目不暇接。又因画面精致,穷尽玲珑纤巧之能事,览者无不叹为观止。时人钱允治曾褒美曰:“顷于百谷斋中见方于鲁墨谱,不觉大叫,谓世固有此尤物哉!欲得之心,如饥如渴。”[3](P38)宣城人梅守箕在《方建元诗集序》中言:“建元方逃名而之于墨,乃用谱而悬通都,一时为之纸贵。”可见此书甫经问世时所收到的轰动效果。
《程氏墨苑》初刊于万历三十三年乙巳(1605),此后亦多次再版。《墨苑》中图样多逾五百式,绘图者主要为徽籍名画家丁云鹏;刻工黄鏻、黄应泰、黄应道、黄一彬,则和《方氏墨谱》刻工一样出自歙县虬川黄氏一族。图形法度严谨,曲尽物态,线刻细若发丝,圆润流畅。另外还有引人注目的一点:现存近20个版本的《墨苑》,有7个版本中印有彩色墨图,多者逾50幅[4](P156-157),殊为奇异,对日后彩色饾版印刷的诞生有启发之功。难怪郑振铎生前得此书,曾惊叹:“此国宝也,人间恐无第二本。余慕之十余年,未敢作购藏想,不意于劫中竟归余,诚奇缘也。”[5](P35-36)《墨苑》能有这样的体量和品质,和程大约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据其生前自述,《墨苑》的编撰活动早在万历甲午年(1594)就已经开始了,这从他撰写的《墨苑人文爵里序》一文就能得知。他“辛勤十年”,专心笃志,至万历甲辰(1604)方“始裒辑成编”[6](P1095、1099)。
《程氏墨苑》的版本情况也很复杂,墨图有十二卷的,也有十三卷、十四卷甚至著录为十五卷的。所附诗文也有八卷、九卷的。[7](P4)以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古籍馆现藏万历三十三年(1605)初版彩色印本为例,《墨苑》全书共含墨图十二卷,人文爵里八卷。收程氏所造名墨图案520种,其中彩色墨样56幅。
作为版画图集,《程氏墨苑》在诞生之初就得到了高度肯定。王锡爵《墨苑序》就曾叹曰:“余林居,客有持墨苑示余者,铭赞诗歌倾海内,士大夫手几遍。而摹写品式,瑰形异状,皆精隽尔雅,非鬼工不能刻,非天孙手不能绘也。”[8](P1175-1176)应天顾起元亦评价道:“披阅墨苑,无论考据精博,结撰遒典,垂光艺圃,环比苕华。即其摹刻之工,擅名国手,画苑中亦当奉之为抚范矣。”[9](P1623)
无论在墨谱领域还是在版画领域,《程氏墨苑》刊行的意义都是空前的。其图像制作汇集了“全”“奇”“精”“雅”四种优点,可以说,安徽版画声名鹊起并对外产生影响,方、程两家的墨书堪称嚆矢,而后者版画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完成了对前者的超越。
二、方氏墨业骎起的背后
据李维桢《方外史墓志铭》记载,方于鲁初名大滶,字于鲁,原籍新安,但其父经商,往来于湖北一带,故其出生在湖北江陵,生年为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后以所制墨品得入大内,获皇帝嘉赏,皇帝将墨上署款的“于鲁”认作其名,方氏遂以字行,名于鲁,改字建[10](P944)。
屠隆《方建元传》和《方建元佳日楼诗序》,对方氏为人赞誉有加,云其聪慧博学,生性慷慨,善制墨而兼富诗才,其诗还曾得到过徽籍文坛泰斗汪道昆的推许,被招入汪氏发起并主持的丰干社,以及后来的白榆社。凭借着良好的文学修养和高明的交际手腕,方氏顺利地融入了徽州文人圈,这也对他未来的制墨事业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据今人统计,共有22位文人为《方氏墨谱》写过诗文题赞,其中6位加入过丰干社,9位加入过白榆社,11位出自以汪道昆為盟主的这两大诗社(因汪道昆、道贯、道会兄弟三人与潘之恒挂名两社,不能重复计算)。剩余11位文人中,来自苏州或华亭地区的如王世贞、世懋兄弟、王稺登、莫是龙、钱允治等人,声名藉甚。方于鲁能结识他们,而他们也乐意捧方于鲁的场,在很大程度上应感谢汪道昆兄弟,他们在中间做了不少牵线搭桥的工作[11]。那么,汪道昆为何会在支持方氏一事上不遗余力?笔者以为,这一方面固然出于爱才,关心家乡后辈;另一方面则多少和方于鲁与汪家沾亲带故有关:方氏的发妻即出自汪家,大儿子方嘉树,娶的也是同乡人汪雷的女儿[12](P944)。方于鲁初识汪氏时经济虽不宽裕,但背后的家族在歙县还是数一数二的,宗族中也不乏子弟和汪氏交情极佳,比如曾经接济过方于鲁的盐商方用彬[13](P943)。故此二家人交往,较之别姓有着超出一般的情感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汪道昆的鼎力扶持下,方氏制墨迅速蹿红,一时间“四夷争购,以为瑰宝”[14](P943),后更被选以供奉内廷,受到万历皇帝的青睐,于鲁的墨名也进而“含李超罗”,盖过了南唐李廷珪和同乡前辈罗小华[15](P32)。墨品为世所重,《墨谱》也就跟着洛阳纸贵了。
三、程大约的“妒忌”和“愤恨”
程大约出身商家,出生与方于鲁同年(1541)【程大约生前著有《圜中草》一书,其中收录了汪道昆为其长兄程大纲所撰“程振卿传”一文。文中有程大约自注,言自己24岁时入太学。而《程氏墨苑》中有赵鹏程“墨赞有序”一文,云自己于嘉靖甲子(1564)入北雍(太学),和程大约同学,以此,则程大约生年为1541年。】,又名君房,字幼博,别号甚多,有筱野、守玄居士、玄玄子、鸿蒙氏、墨隐道人、鸿胪近侍、鄣郡放臣、独醒客等。他家资颇丰,而早年志在业儒,24岁时即入太学。此后科举之路却一直蹭蹬,年逾50仍未摘得功名,最后只能捐个鸿胪寺序班的微末官职,但也没干多久就辞职返乡了。原因据他自己所称是“性伉直,于时靡所希合”,而“不能媚贵要”[16]。而在后来的《程氏墨苑》里,他又多次给自己署名“鸿胪近侍”或“原任鸿胪寺序班臣”。其内心的矛盾由此得窥一二。
同为歙人,同样以制墨为业,程大约处处和方于鲁较劲,还撰文抨击对手,显示出了极强的战斗欲,说他是方于鲁余生的梦魇也毫不为过。如果我们欣然相信被屠隆等人描写得像传奇一样美的方氏早年生活,那么定然会因程大约笔下的方于鲁形象而大跌眼镜:
里人方于鲁,一名大滶,父贾江汉间,幸一倡,遂生于鲁。于鲁长楚中,从父受贾。父死,亦溺志倡家,丧其资而还。居乡贫甚,数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闻余喜士,士之困厄者,恒赒焉。于是构诗为贽,介余友人来谒。比至贸贸然,入门趦趄,嗫嚅请以讴吟,当俳优供余抵掌,余笑而进之,使与末座。时值孟冬,薄寒侵人,于鲁尚曳一絺,肌尽生粟。余恻然加悯,随解衣授餐,处以记室之任。当是时于鲁方病瘵,余乃延医视之。医言夫。夫形既尫羸,脉复柔缓,药非大剂参蓍不效。时参价踊贵,每十两,值朱提一流。余胠箧给之,如是者有年,未尝厌怠。余夙抱墨癖,遍访古人搜烟和胶之法,试之果良,较罗舍人所制不翅倍徙。居恒念于鲁不能治生,尽以其法授之。法具矣,苦无资,庚贷以资;资具矣,苦无仆,庚分以仆。于鲁按法制墨,业骎骎起,衣食之外,颇有赢钱,于是淫心复炽。会余将入都,命内子遣一侍儿。于鲁向居余门,闻其美丽,阴令子嘉树贿媒者,托以他人,展转谋娶。余归讼之有司,卒致离析。于鲁窭复如故,诡制赝墨,以罔市利。余重自咎,术授匪人,因损赀督制以矫之。而四方具目者不之于鲁,而之予矣。乃于鲁不自悔祸,反相雠憾。[17](P52-53)
这段文字来自程大约的《续中山狼传》,程氏云自己生平乐善好施,曾救济过很多人。但其中有一些人心无善念,不仅没有感谢,反而对自己恩将仇报。1606年他再度北上,获读宋人谢枋得的《中山狼传》[18](P32),深有感触,于是自己也写了这篇长文,痛陈这些人的恶劣行径,再请人配以图画,和谢氏文一并附于《墨苑》书后出版。读完整篇可知,方于鲁还不是最令程大约憎恶的那一个。但因为是同行,所以程氏把他列为“中山狼”之一,就格外引人注目了。
考虑到两人在商业上的竞争关系,我们很难断定程氏此文对方氏没有丑化之嫌疑。但程氏所述生动,且至今也没有证据表明其全系捏造。在他看来,指名道姓绝非抹黑行为,只不过是揭穿对方的老底而已。同时也要向世人宣告,作为制墨人,方氏的奸商行径配不上收获名利。
笔者认为,最起码,情况不似多数人认为的程氏因妒生恨进而挤兑方氏这么简单。据程大约在《程氏墨苑·人文爵里》卷八中所云:“余惟先世遗产不逮中人,比余修业息之,幸累万金。”又言自己“为童子时,性即嗜墨”。所以与方于鲁早年返乡时经济拮据相比,程大约资金雄厚,且较方氏更早留心墨艺应当是不争的事实。据其青年时期的好友赵鹏程回忆,自嘉靖四十三年(1564)到四十六年(1567),程大约和自己同在北京太学内读书:
自甲子至丁卯,两人日夕过从,情逾兄弟。诗文之暇,见幼博酷嗜古墨。人有携晋唐以下遗墨来售者,即残缺过半,必以重价购之。余调幼博:子有墨癖,墨将磨子。[19](P1473-1474)
而且,如李维桢所写的那样,甫一接受汪道昆的提议,就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迅速将墨业做大,也的确不符合实际:即使启动资金和销路有汪氏可以做靠山,制墨的经验、人手还有原料又该如何获得?面对程大约的攻讦,方于鲁埋头不应,到底是因为性格温和,不愿同人做口舌之争,还是心虚程氏所述多系实情?至今我们仍无从知晓。倒是方氏的拥戴者们按捺不住,遂替方氏还击。如梅守箕就曾在《方建元诗集序》中说:
有阳与建元交而忌之者,非能忌建元才,直以建元有名当世间。其人豪于赀,卒能以赀用其豪,建元竟以是遂北游中原,走都下,以避其不祥。是时建元诗亦进而亦日有文,缙绅先生多有知建元者,以自适于游耳。而豪者终迹之都门,必欲关前路而阻绝之。然建元归则穷十于昔矣。其愤邑不平之气与侘傺无聊之怀,无所之而致于诗。
梅氏此文作于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他虽未在文中明言是程大约跟方于鲁过不去,但根据方于鲁在自己的《佳日楼集》中的五言诗所云,他大约是在1590到1591年间离开徽州北上的,到了1592年时还在河北固安地区。而程氏《圜中草》一著中有“寄送吴京江宪副补选之京歌”一首,可证1592年到1593年期间他在北京任职。程氏自己亦说在京师执事鸿胪时,得知方氏来此“贷市人金,戴罪窜业”,随后“捕而执之,递遣以归之”[20](P1272)。故梅氏所指无非就是程大约了。
李维桢亦云:
故为墨者嫉之,百计务出其上,卒不得,无所发愤,则中以狱,财势所使,无如之何,走京师避之,久之事解。[21](P943)
梅、李二人和汪道昆、屠隆一样,是方氏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关于方氏在《墨谱》人气正旺的时候悄然北上这桩蹊跷,他们含糊其辞,把问题归咎为程大约的妒忌心和仗势欺人。这在笔者看来未免有些牵强:程氏也只是一商贾而已。在此期间,方氏的事业正值鼎盛,有儿有女,还有汪道昆等缙绅在背后撑腰。正常情况下,怎至于被一个同行整到连在老家都待不下去?
其实,原因很可能还出自于方于鲁自身。不光程氏揭露了方氏在制墨过程中以次充好,时任歙县令的彭好古也曾披露云:
新安以墨名旧矣。方余令歙时推方氏于鲁,而于鲁墨推“寥天一”为绝胜。余尝取其绝胜者赠四方修文之士,姗姗胥薄之曰:是胡赝也。因磨而试之,则见其膏如糊,其色如煤,不可以笔。乃叹曰:新安无墨哉,奈何以墨名相黑?郡守古公重价购墨,于鲁亦以赝应。古公怒,请验于汪司马,逮而笞之。于鲁以赝乱真,不避郡邑长吏,他可推矣。[22](P1231-1233)
查《康熙徽州府志》卷三“郡職官”,可知“郡守古公”即四川梁山籍进士古之贤,他到任徽州时在万历十四年(1586)。而据《民国歙县志》卷二“官司志·职官”所载,彭好古官歙县的时间约在万历十六至十九年之间(1588—1591),故彭氏所述之事和方于鲁北上可以衔接。既然方氏的这次不诚信累及到了汪道昆,他失去汪氏的庇护也就成为必然。另外,邢侗也曾批评方墨名不副实:
方于鲁擅名歙州,当以色泽规模取胜。磨之若糨,有香气,无墨气。所属非烟、寥天一,殊谬不然。左司马公差愧太玄氏董狐。……于鲁墨满天下,闻亦能走四夷,想心手与世代低昂。此犹末季乌衣中侨肹耶。傥亦别有秘合,独为司马公出一瓣香,故司马据实标目乎。[23](P1437-1445)
邢侗工书法,亦善鉴墨。虽然是文见录于《程氏墨苑》,但实际完成于1589年,故而不存在为了程氏而刻意贬低方氏的动机。还有一位徽州名士——曾指导过丁云鹏艺事的詹景凤(1520—1602)也说:
近日歙人某子甲造墨,内悉煤炭,外为雕饰,饰极伪滋。司马汪公不察,为作文夸神圣至不可名状,又为号之曰“方墨”。名遂传布,价腾一时。多为大珽,忆得者必以供目玩,不忍磨,故中藏黑土臭秽,而市拾倍。[24](P5-6)
詹氏与程、方二人并无私交,其立场应属公允无疑。由此看来,方氏墨在其成名后品质转劣已无可辩驳。是故言其遁走北方是受程氏倾轧有违事实。然而后来谢肇淛(1567—1624)、姜绍书(?—约1680)仍站在方氏一边,谢肇淛说:
国朝方正、罗小华、邵格之皆擅名一时,近代方于鲁始臻其妙。其三十年前所作九玄三极,前无古人。最后,程君房与为仇敌,制玄元灵气以压之。二家各争其价,纷拿不定。然君房大驵亡命,不齿伦辈,故世论迄归方焉。……方于鲁有墨谱,其纹饰精巧,细入毫发,一时传玩,纸为涌贵。程君房作墨苑以胜之,其末绘中山狼传,以诋方之负义。盖方微时曾受造墨法于程,迨其后也,有出蓝之誉。而君房坐杀人,拟大辟,疑方所为。故恨之入骨,二家各求海内词林缙绅为之游扬,轩轾不一。然论墨品人品,恐程终不胜方耳。[25](P238)
谢肇淛没有否认程氏曾传授过方氏制墨之法,还交代了程氏曾被指控杀人而入狱,差点丢了性命一事。出狱后的程氏怀疑自己吃官司的原因是方氏在背后捣鬼,所以撰文公开痛斥方氏。但谢肇淛仅据此项内容做出程氏墨品人品不如方氏的评价,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味道。
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中所云和对程氏的评价与谢肇淛大体相同,而多出的一段关于方氏谋娶程氏侍妾未果的八卦,则更让人觉得其扬方贬程之结论莫名其妙。以此二君的逻辑,程大约的济弱扶贫和授人以渔不能算作人品的加分项,方于鲁看上熟人家女眷也不能算作减分项。而一朝身陷囹圄,不论冤屈与否,便足以对人品盖棺定论了。内心纵有不平,也要保持沉默而不应控诉,否则也是人品低劣?
程氏下狱一事发生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也就是他从北京辞归的第二年。提及此事,程氏尤其义愤填膺,认为方氏忘恩负义,伙同他人陷害自己,致使自己家庭分崩,身被不白之冤:
迨余杖一老竖,兄子一凤以恨余责逐继母之故,计移之岳庙中,实幸其死。于鲁趁其创甚,赂医投以犀角地黄汤,顷之死矣。于鲁父子鼓市之无赖者,亡虑数十指,弁其死尸,蜂拥于余之门,喧乎杀人,以激众怒。予坐是系居圜户六载始出。方余狱急时,谋秘不泄。及事白,客有知者,从容为余陈说,历历有征,盖信其不诬云。……嗟嗟,夫人以饿莩投人,而活之以衣食,已有更生之德矣。况病而汤药之,又贫而生业之。贷资斧以给饔飱,分仆役以供任使,为恩已极,不翅生养之二天也。胡乃以淫夺理,而谋及闺闱之侍。又以怨叛德,而搆其聚杀之谋。又以类结党而肆其交谤之毁。即狼虽恶,恐不若于鲁之特毒也。[26](P55-57)
六年的牢狱之灾对程大约造成的打击无疑巨大。其言凿凿,其愤铮铮。如若说撰写此文的动机是诬陷,能做到如此理直气壮,实难令人置信。而在《圜中草》中的“孝孙女请状”一文中,程氏将命案的起因说得更清楚:
甲午,不佞综理先人故物,将卜宅以奉先人之灵,遂见雠于侄霖。霖主家,奴孽,祸怙跋扈而侮慢之,因薄惩以家杖,大都分在理然,非过也。奴归愬凤。凤往不德于后母,忿不佞规己,而衔之有时。至是乘间而谋于霖。[27]
文中提到的“侄霖”,是程大约长兄程大纲的儿子程公霖,“凤”是指二哥程大纪的儿子程一凤。读程大约自述,大抵可以想见他是一个率直且嫉恶如仇的人,在处理家族内务时难免有些家长作风,从而招致两个侄子的怨恨。程氏认为自己所做在理,却没有料到程公霖和程一凤竟然会和外人方于鲁合谋算计自己。程大约不避家丑公开了事情始末,可见其并未将矛头专门指向方于鲁个人。因此笔者认为,程大约为人固然有狷急的缺陷,但谢、姜二人一刀切的道德观对程氏而言是不公平的。果真如谢肇淛所言“世论迄归方”,那也恰好反映出当时知识界对程氏的偏见。
四、从玩票、不满、争胜再到雪耻——《墨苑》版画产生的行动逻辑
事实上舆论并非都是一味挺方的,程氏于狱中发愤写了一部文集《圜中草》,锓梓后就博得了不少人的理解和同情,如朱之蕃、吴光裕、顾起元等,更还有曾为《方氏墨谱》写过序赞的王稺登。王氏在读过《圜中草》后,称程氏之集“孤愤悲壮不减邹阳《狱中书》,堪令飞霜六月”[28](P1353)。尤值一提的是,万历五年(1577)进士江东之对程氏的声援最见真诚:
余友人程鸿胪幼博先生,幼好墨,擅昌言之癖,所烧烟和胶,妙廷珪之制。不佞交幼博且久,其制墨而遗不佞,若效岁赋焉。表里如一,绝类其为人,玄德茂矣。其同里人奇觚氏方甲,贫而给事幼博。幼博极怜爱之,推食与食,解衣与衣,己资墨业与业。久之输攻,悖德滋甚。且以司马引重,横猎时名,反噬而中幼博。幼博始复业墨,以其季君房行,破大墨之奸,供四方利用也。今上冲年,入圣宸翰天藻,上追二祖,文宣之遺,尚方进御,万机挥洒,新都称良者三四家,君房其选也。方甲诡取,而妄承之以艳仕林。罔缙绅不自知,其为垄断,为盗侠,古有贱丈夫者,未足贱矣。……奇觚氏利则趋蝇头,媚则掉狐尾,声则假虎威,忮则肆虿毒,施施骄哆于皮相,依附于辞客。其售奸作伪,远欲动遐服,罔王公大人。乃识者则饶辨焉,若墨谭纪中凡数十则,卑其墨与糨等,邢侍御子愿之言是也。近欲掩里闬,欺五尺童子,如用之,奸状毕露。若性理小辨中大加丑抵,詹太史东图之言是也。两君子皆鉴赏家,大诎奇觚氏,败度奇邪,愧死无地。而且谱之图之,欲以信今传后,耳目谁为涂哉?[29](P1483-1487)
文中的“奇觚氏方甲”明显就是指方于鲁。贬斥方氏人品及墨品如江氏这般不留情面者,可谓再无二家了。虽然是文收录于《程氏墨谱》,但江氏是在1599年去世的,基本可以认定为程氏出狱前所写。且江氏生前官至右佥都御史。一位正四品官员,能如此深度地“掺和”民间的私人矛盾,不像是受程氏意志调动而为之,而更可能出于一己之正义心。况且江氏与程、方同辈,又是歙县人出身,故而其说法还是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的。
面对程氏出狱后的犀利声讨,方于鲁本人最终还是做出了回应。在儿子方嘉树为其整理的诗集续编《师心草》中,有一篇名为“喻谤”的文章,在是文后半部分,方氏用隐喻的手法讥讽了程大约,云其“慕虚名而窃污简牍,作视肉以昡曜金赀,类负重之戴石,譬赑屃之守碑”。“喻谤”作于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丁未)春天,之后不到一年,方氏即告离世【据李维桢《方外史墓志铭》记载,方于鲁卒于万历戊申(1608)正月二十有二日。】。其言辞已然暴露出,多年的沉默并不代表真的做到了超然物外,这位红极一时的老制墨家对宿敌的攻击还是耿耿于怀的。但这最后的,也是唯一一次的反击多少显得苍白无力。它没有掀起多少波澜,没能扭转家业在汪司马逝世后彻底陷入的颓势【汪道昆去世于1593年,其弟道贯去世于1591年。据林丽江猜测,1590年底方于鲁离歙北上,就得靠抵押《墨谱》的木刻原版换取生活费用;李维桢《方于鲁诗序》也称汪道昆谢世后,“于鲁家日益贫”。】。就连从前私交最笃的几位名士,也都在悄然远离自己:自诩“知建元人、知建元诗”的梅守箕、“一抵新都,即把臂入林”的屠隆,转而为《程氏墨苑》写起了赞文。一直为自己“受谤”而鸣不平的李维桢[30](P946-947),最后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还为程大约写了一篇《墨苑叙》, 用“输攻墨守”“后羿逢蒙”来形容程和自己。不过,两年前死对头的力作——《墨苑》的风光问世,才可能是最令他沮丧和忿恨的事情?方于鲁的儿子嘉树后来在父亲的《佳日楼诗集》中自述说,晚年的父亲“善病,齑志未就,夙愤未酬”,或可说明晚明徽州这两大制墨家恩怨斗争的结果,方氏绝不是最后的赢家。
至此,我们不妨将方、程围绕墨业而展开的斗争始末再做一番梳理:出身商贾之家的程大约,早年依靠经营典当行放高利贷,积累了大量财富。【程大约在《续中山狼传》一文中,曾多次提到自己在各地的钱庄商肆。】同时热衷于鉴藏古玩尤其是古墨,还摸索出了一套制墨秘法,自谓“尽艺之长”。但并未打算以此道治生,友人劝他开辟墨业,被他以“耻儒而工”为由谢绝了。[31](P1263、1271)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攻科举上面,期间亦涉足书籍出版行业。【在国子监就学期间,程大约还曾入名儒戚元佐门下学习,有1573年《青藜阁初稿》三卷为证,此书为戚元佐所撰,目录题“门生程大约、胡日新校刻”;1576年,程氏又编辑刊刻了《徽郡新刻名公尺牍》一书,在此书序言中,程氏提及自己还曾于钟山子共同编纂《竿牍》一编。】后来方于鲁前来投靠,程大约怜其收之,又将制墨技艺传授给了方于鲁,并资助开设墨店。也许当时程氏认为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做法:既帮助了方氏一家脱贫,又能拓展新产业而不分散自己的时间精力(这也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墨谱》和《墨苑》存在大量雷同的墨样)。[32]但是之后方于鲁的表现让程大约很是不爽。或许是在墨业起步之初就攀上了汪道昆的缘故,方氏在发家致富后对外刻意淡化程大约的恩助,而一味宣扬汪氏对自己的提携之功;抑或有可能程大约看不惯方氏在境遇改善之后独享墨名,不断打压方氏导致后者产生了逆反心理。总之两人终止了合作,方于鲁携子独立经营墨店,生意靠着文人圈朋友的宣传日益兴旺,1588年《方氏墨谱》的出版也进一步扩大了自家的知名度。程大约则一面继续雇人打理自己的墨店,不让方氏专美于家乡,一面争取在仕途上有所突破。期间两家的墨品都获得过进贡尚方的殊荣。方于鲁后因谋娶程大约侍妾,彻底激怒程氏。又一度被曝出出售假墨的丑闻,事业开始陷入低谷。而程大约在学优登仕的理想幻灭后返乡,于1594年下决心以墨为主业,并开始策划编纂《程氏墨苑》。不料却在同年坐杀人案入狱,六年后才得以昭冤释放。在被关押期间他化悲愤为力量,在少数亲友的帮助下坚持《墨苑》的编纂工作,出狱后更是东奔西走,拜访名流,赠墨求文。最终于1605年,出版了首批《墨苑》,在一定程度上洗刷了自己的污名,也对方于鲁完成了舆论和事业上的双重压制。方氏于1608年郁郁而终,而程大约身体硬朗,活跃于墨坛至少到1610年以后【1610年后所出版本的《程氏墨苑》中,有顾起元和朱之蕃的贺文,分别题“幼博翁父七十小诗奉祝求正”和“和顾太史韵祝筱野老丈七帙兼贺举少子”。两篇文章虽未标明时间,但据程氏生于1541年推断,可知其迎来70寿诞当在1610年。】,甚至有可能到天启年初仍然健在【安徽省图书馆藏原程大约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相大悲心忏》中有明天启二年(1622)方绍祚序,云:“观世音菩萨三十二相大悲心忏,幼博氏施本也。摹刻精严,洵是胜果,惜此人谢世,板随散佚,乃辐辏而归予,若有大士现身而为之说法,爰是鸠工补遗,复为流通,期与大众皈依顶礼。”序文末署天启二年如月芳春节,如月芳春节即农历二月初八,故程大约去世应在此日期之前的一段时间。又,休宁县博物馆馆藏署“明天启二年程大约监制”的 “御墨”,要么为伪,要么系程氏墨店为推销产品而对外谎称。】。
从闲暇玩票到对昔日扶持对象的不满、从争胜再到雪耻,最后立志为墨代言。这便构成了程大约整个制墨生涯的行动逻辑。在程氏悲喜交叠的人生当中,除了可以看到这位儒商不屈不挠的精神,我们也能窥见在人生价值的追寻之路上,他的思想由早年的“耻儒而工”终而变成了以业墨而自豪。晚岁时期,他自我肯定道:
窃惟吾乡素封十室而九,上者拥资巨万,次者亦累数百千金,锦绣充于篋笥,玩好溢于斋阁。自谓陶朱猗顿,意气扬扬。乃若青云之士,率以铜臭目之,间与往还,不过叙问寒暄而已。吾尚玄如杨子,守黑如老氏。身虽被放,而神日益王;业虽就堕,而名日益起。至公卿忘其贵,燕郢忘其遥。履舄填门,竿牍盈几,争持文绮白镪易吾墨,一函数挺,不啻空青水碧、珊瑚木难。由是观之,盛世所宝,诚在此而不在彼矣。[33](P1671-1672)
这份自信与豪情,漫说在刻意对外打造诗人形象的方于鲁那里找不到,放眼整个墨史也难有与之相比者。以至于提及《墨苑》时,程氏更是毫不客气的宣称:
夫《墨谱》一书,宋人仿《考工记》而作。今观其谱,厘为三卷,曰图,曰式,曰法,亦堇堇耳。若品题词翰,则未之前闻也。今余《墨苑》之中,其搜烟和胶诸法之良,是固不待言矣。而墨式之精且博,殆百倍其谱焉。况文值熙朝盛运,霞蔚云蒸,其视宋人之谱直霄壤耳。[34](P1096-1097)
结语
墨学专家尹润生先生认为,方、程二家相轧之事未出争名夺利的范围,本质就是商业竞争。[35]诚然,经济诉求必然潜伏在激烈的道义争夺的表象下面。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段戏剧化的竞争其实超出了一般商业的范畴。方于鲁借重诗社文人的手与口贩卖人设,为自家产品增加了不少品牌效应,从而赚取了大量的文化附加值,同时在竞争中率先脱颖而出。为了击败方氏,程大约起先采用的是提升产品品质和降价的策略,后来便直接效法方氏编印《墨谱》的做法。他围绕着编书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全然是不计成本的。在出狱后的数年里,他走遍全国,送出的墨与图书不计其数,只为结交名流。《墨苑人文爵里》卷尾的“名公書启”提供了大量例证。正是这种诚恳和付出打动了高高在上的士夫名流,才令《墨苑》的分量愈来愈重。随着声名渐著,商人程大约的境界也在不断提升,他说:
或者谓潘谷墨既精美,口不二价。士或不持钱以求,无多寡与之。常和之墨,岁久锋可截纸,市有赢钱,悉取盖三清殿,不以自给。二子人品,诚有大过人者,然后能不朽于世。余则以为特一节之善耳,不可语天下之士也。[36](P1098-1099)
既然一般的馈赠和公益之举在他看来还都只是小善,那么他以何种行动彰明自己的胸襟呢?他采取了一种新颖的做法:
因取先祠之东隙地方丈,特置一室,贮墨百柜,以待四方贤豪长者之求,且以遗吾后世所不知者何人,遂自署曰“宝墨斋”。[37](P1672)
由此可见,程大约丝毫不在意自己有生之年能否重新致富,只是希望自己的墨能够流芳后世。他曾不无动情地自白:
余为童子时,性即嗜墨,中年专攻其业,晚益成癖。至倾橐倒囊,一无希惜。客有规余者,谓:“子破产治墨,技固殚矣,第恐玄之尚白,异日何以为子孙计耶?”余惟先世遗产,不逮中人。比余修业息之,幸累万金,乃今毕奉墨卿,成吾所好。昔灌夫有言:“候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38](P1658-1659)
以工匠精神来打造墨锭,再倾尽余生为制墨正名,挚爱如斯,终将不为历史所负。明薛冈《天爵堂笔余》记曰:“名不必文章攻烈,时大彬之壶、程君房之墨,皆洋溢乎中国。”[39](P4)
有一点仍需澄清:晚明徽州地区的商业竞争虽然激烈,程大约与方于鲁的恩怨却不是当时的普遍现象。方程二家在制墨业的竞争超出了一般商业的范畴,程大约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也远超一般工匠,在方于鲁寻求文化身份与认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本非竞争主题的版画艺术却因此受益而在晚明的徽州迎来爆发,获得了出类拔萃的视觉效果,也因为诸多“风雅”势力的介入而变得极具话题性。
参考文献:
[1][3][15][明]方于鲁编,吴有祥整理.方氏墨谱[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
[2][4]林丽江.晚明徽州墨商程君房于方于鲁墨业的开展与竞争[G]//米盖拉,朱万曙主编.法国汉学第十三辑: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10.
[5]郑振铎.劫中得书记[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6][7][8][9][17][18][19][20][22][23][26][28][29][31][33][34][36][37][38]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程氏墨苑(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0][12][13][14][21][30][明]李维桢.方外史墓志铭[G]//陈智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二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11]梅娜芳.汪道昆和方于鲁的制墨业[J].新美术,2012,(5).
[16][27][明]程大約.圜中草卷一,“圜中草序”[M].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刻本,日本内阁文库景照本.
[24][明]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篡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杂家类,册112,卷42.北京:中华书局,1997.
[25][明]谢肇淛.五杂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32]翟屯建.程大约生平考述[J].中国文化研究,2000,(3).
[35]尹润生.方于鲁与程君房两家墨店[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4).
[39][明]薛冈著,王春瑜点校.天爵堂笔余卷三[G]//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刘德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