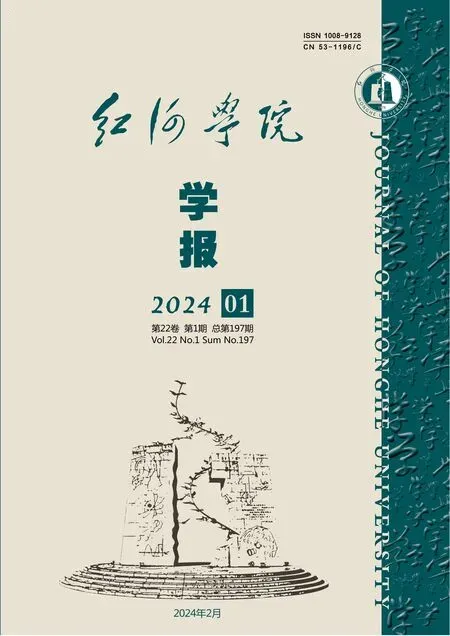乌蒙山区彝族祖灵神话研究
陶 波,李如海
(1.六盘水市社科院,贵州六盘水 553001;2.中共六盘水市委党校,贵州六盘水 553001)
祖灵即祖先的灵魂;祖灵信仰即对祖先灵魂的信仰。关于彝族祖灵的研究相关论著比较多,例如刘小幸的《母体崇拜 彝族祖灵葫芦溯源》、巴莫阿依的《彝族祖灵信仰研究 彝族古籍探讨与彝族宗教仪式考察》、吉尔体日等的《祖灵的祭礼 彝族尼木撮毕大型祭祖仪式及其经籍考察研究》等。西南地区的乌蒙山区是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是重要的民族文化走廊,至今还流传有祖灵信仰和与之相关的祭祀仪式、口头传统、活形态神话。随着时代的变迁,区域内彝族祖灵信仰和与之相关的祭祀仪式、口头传统、活形态神话也在不断变化与适应,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
一、乌蒙山区彝族祖灵神话
彝族的祖灵与“竹”文化息息相关,其最早的文献记载有《华阳国志》《后汉书》等汉文典籍以及《西南彝志》《洪水纪》等彝文典籍。乌蒙山区的彝族村寨至今还传承着彝族祠堂和祖灵筒,还有相关的祭祀仪式和活形态神话流传。
(一)竹中生子与“竹”信仰
《华阳国志》《后汉书》中关于竹王的相关记载,前辈学者研究论述较多,比较集中的是“竹中生子”神话和“竹”信仰。
《华阳国志》中竹王的相关记载如下:
有竹王者,兴于遯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濮〕。氏以竹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1]。
该文献明确记载三节大竹破之得一男孩,男孩长大后,氏族以竹为姓,所破之竹后变化为成片的竹林,即后来祭祀竹王的竹林。
《后汉书》中竹王的相关记载如下: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牂柯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是也[2]。
《后汉书》记载与《华阳国志》大同小异,《后汉书》明确了“竹王”故事的地点遯水、夜郎、牂牁郡;明确了时间为武帝元鼎六年;明确了事件为平南夷等,最后记载“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是也”,竹王夜郎侯的三子后为“竹王三郎神”。
关于竹中生子与祭祀“竹”的神话,今乌蒙山区的威宁一带还有“竹的儿子”神话流传。故事在《彝族的图腾与宗教的起源》《贵州彝族回族白族民间故事选》[3]等文献资料中均有记载。
何耀华《彝族的图腾与宗教的起源》中记载贵州威宁马街公社马街村(今威宁云贵乡马街)一带自称“青彝”的关于“竹的儿子”故事,与《华阳国志》《后汉书》等一脉相承,清楚解释了彝族为什么要用竹子制作祖灵和为什么要祭祀祖灵的风俗。
古时有个在山上耕牧之人,于岩脚边避雨,见几筒竹子从山洪中漂来,取一筒划开,内有五个孩儿,他如数收养为子。五人长大之后,一人务农,子孙繁衍成为白彝;一人铸铁制铧口,子孙发展而成为红彝;一人编竹器,子孙发展成为后来的青彝。因竹子从水中取出时是青色的,故名曰青彝。为了纪念老祖先竹子,青彝始终坚持编篾为业,世世代代赶山赶水,哪里有竹就到哪里编。……由于彝族从竹而生,故死后要装菩萨兜(菩萨兜,当地彝族称为“披卡”,是一用以放灵牌的小竹箩箩),以让死者再度变成为竹[4]。
乌蒙山区的威宁马街流传的“竹的儿子”神话故事,讲述了“竹中生子”,竹中所生五子,成为今天威宁地区彝族的白彝、红彝、青彝等彝族支系,也解释了彝族为什么要用竹子制作祖灵。经历千年,竹王神话的相关母题和“竹”信仰仍然在乌蒙山区流传,并伴随着相关的显圣物——祖灵筒和相关的祭祀仪式活形态传承。
(二)洪水遗民与“竹”信仰
洪水遗民是广泛流传于西南少数民族中的神话,乌蒙山区彝族将洪水遗民神话与祖灵的来源进行融合,解释了彝族丧葬和祭祀为什么要用“竹”的民俗问题。
彝文文献《洪水纪》(也翻译为《洪水汜滥史》)讲述了流传于贵州西部(乌蒙山区)的最完整的洪水神话,其中“洪水将临笃慕生”讲述了洪水来临前,武洛撮夫妇向天君祈祷,天君策耿苴一一答应,后来在祭坛上祭祀了灵筒,生了三个儿子,即笃慕三兄弟。洪水朝天,仅留下笃慕,笃慕在歌场遇到三个天神的女儿,后与之婚配,生下六个儿子,即六祖,后六祖分支,形成今天彝族分布居住的格局[5]。乌蒙山区至今还流传有“笃米”的神话,讲述洪水遗民“笃米”与六祖分支的内容。
白发老头要用洪水来淹没世界。笃米三弟兄听了一齐跪下请求老人救命。白发老头说:“你们三弟兄,老大造个铜桶,老二造个铁桶,老三造个木桶。洪水来了,就各自坐上桶逃命。”笃古和笃叟合就忙着去造铜桶铁桶去了。老头继续对笃米说道:“你就坐木桶我给你一个鸡蛋,你把它夹在胳肢窝下,什么时候听见鸡叫,你就什么时候踢开木桶出来。”说完,白发老头就无影无踪了。
事过三天,果真打了整整三天三夜恶炸雷,下了九天九夜的大竹杆雨,洪水慢慢地平了峡谷,淹没了山头。这天笃米胳肢窝下的蛋孵出了小鸡,小鸡“叽叽”地叫了。笃米踢开木桶出来时,木桶停在高高的洛尼山顶上,不见一个人影,只见洪水滔天,九九八十一天后,洪水才慢慢消退了。他知道他的大哥和二哥已被淹死了。
笃米就在洛尼山上弹月琴,唱歌,用弹琴和唱歌来排遣孤独和烦恼。掌管宇宙的大神策举祖听到笃米那悠扬又凄惨的歌声,就在拜谷肯呷设歌场,邀请笃米去唱歌,还请来东方天神沽色尼的女儿尼友咪补,南方天神洛色娄的女儿娄友咪多,北方天神布色偷的女儿偷友武仕。三个女子见了笃米都非常惊奇,也非常爱慕,她们就与他对歌,请他跳舞。从那以后,她们还常约他到拜谷肯呷唱歌跳舞。策举祖见他们情投意合,就成全他们,把三女许配给笃米做妻子,让他们传彝族后代。后来每个仙女各生了两个儿子,发展成彝族的六大家支[6]。
马学良先生在《云南土民的神话》采录了流传于乌蒙山区的寻甸、宣威两地的“夷边的人祖神话”“夷人的三兄弟”两则洪水遗民与“竹”信仰的神话,比较详尽的讲述了洪水后,彝族祖先因竹子获救,所以彝族用竹子制做祖灵。
寻甸凤仪乡阿世卡村“夷边的人祖神话”是这样讲述的:因为他们的命是竹子救的,于是他就以为这竹子是救他的神仙,连忙把竹子挖回来,用绵羊的毛包着,再以红绿棉线扎好,然后装在一个竹箩箩中,供奉起来,所以直至今日,夷族都信之为祖先灵魂的寄托,是他们最虔敬的神[7]。
宣威普鹤乡(今普立乡)卡腊卡村“夷人的三兄弟”是这样讲述的:用竹子编成一个精致的竹箩,作圆柱形,高五寸,内容与木桶大小恰合,将木桶装进,再将竹箩封盖。此祖神即告成功,盖即像其祖宗漂流时之状况,木桶中之红明珠,代表其祖坐于中间之意,竹箩是表示祖宗当初坠岩时幸为竹丛所阻,得免于难,故至今仍以竹保护木桶[7]28。
乌蒙山区流传的彝族洪水遗民神话中,其祖先在木桶中躲避洪水后,因“竹”获救,因此为了感恩竹的救命之情,用竹子制作祖灵,也有用竹子制作篾箩箩装着木头制作的祖灵,供奉在祠堂中世代奉祀。彝族在祭祀祖灵的时候或看到祖灵的时候,就会想到洪水遗民神话,通过叙述洪水遗民神话,解释彝族祖灵为什么要用竹子制作等原因。
(三)孝子故事与“竹”信仰
孝文化在每个民族中都有传承,孝子故事是孝文化的重要载体。乌蒙山区彝文文献《赛特阿育》是区域内流传的极具地域特色的孝子故事,是汉彝文化交融的产物。罗曲、王俊在其专著《彝族传统孝文化载体<赛特阿育>研究》对其进行充分的研究。但其著作中指出:
在彝族孝道故事里,没有以“为母埋儿”这样有失人性的愚孝,也没有“涌泉跃鱼”和“卧冰求鲤”、“哭竹生笋”这样只表现心里愿望而不可能有现实的童话[8]。
在乌蒙山区活形态神话资料的收集整理中,调研组发现一则传统孝子故事与彝族“竹”信仰融合的故事,即“哭竹生笋”故事;还在民间采录到一则口传故事,即“孟宗哭竹”故事。故事将彝族祖灵神话与孝子故事进行很好的融合,借助孝子故事讲述“哭竹生笋”,采集竹笋孝敬母亲,最后解释彝族祖灵为什么要用竹子制作等民俗问题。其文献资料见于《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曲靖地区故事卷》“梦中哭竹”,主要流传于滇东北、黔西北一带。
在远古时,我们祖先是个独儿子,他对父母很有孝心,对人们都很诚恳,对老年人很尊敬,人们称他为孝子。一天,母亲病倒了,请来毕摩医治。好心的毕摩告诉他:您母亲无救了,要寒天的竹笋才能医好。毕摩劝独儿子把所有好穿的给母亲穿了,好吃的做给母亲吃够。辞世是早晚的事,是天君的旨意,劝他不要难过。更不应让母亲知道谈话内容,以免急坏身子。可怜的祖先只有这相依为命的母亲,听到这话,不禁掉泪了。他向毕摩说,现在是冬天,虽没有竹笋,但只要能救我母命,我一定要得到它,把母亲的病治好。毕摩很感动,同情地摇摇头走了。祖先来到竹林里,睡在竹林里的地上,希望能使竹根受热而发芽,长出竹笋来,把母亲的病治好,保住她的性命。时间一天天过去,可就不见竹笋长出来。然而母亲的病日趋加重,祖先很心急,心里更难过。几月过去后竹笋出了芽,从土中冒出来。可怜的祖先掉下了激动和惊喜的泪水,把竹笋采回家中,母亲刚断气。祖先很悲伤,在悲痛中安葬了母亲,便把竹笋放在供桌上,连日来,祖先沉浸在悲痛之中。有一夜,祖先梦见了母亲,他紧抓住母亲的手,叫她回家。祖先的泪浸透氇毡。母亲在梦中嘱托:“孩子啊!人死由天定,灵魂飘悠悠,养儿有敬心,养儿有孝怀。您把这竹子,做成我金身,便是我灵竹,表你悼母心。”祖先醒来时,不见老母亲,感到很奇怪,梦中的一切,是那样的明晰。母亲的话语,如同在人世间的时候,是那样的亲切,声音也没有变。他按照母亲托梦之言,把母灵设于竹筒内,做成了“祖竹”。毕摩来把母魂指到西方,为后裔祈禳。让母魂庇佑儿子,让祖竹(或竹灵)庇佑后裔昌盛。从此,彝家便兴下了用竹设灵的祭俗[9]。
2022年10月的田野调研中,在宣威西泽乡迤那洪家村采录到一则“孟宗哭竹”口传故事,讲述人是一位87岁的老毕摩。
老人老了,要用野竹秧根、绵羊毛设灵,这个根在哪点?这个根就是孟宗。
孟宗是一位大孝子,十冬腊月,孟宗问他妈,你想点什么吃,他妈说别的我吃够了,我想点竹笋吃,她叫孟宗到竹棚边找竹秧、竹笋来炒了给她妈吃。孟宗去看,十冬腊月哪点找竹笋,他就坐在地里哭了,哭着哭着就睡着了。梦中一个白胡子老人走到他跟前,问他说,小妹,你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哭?他说,我妈生病了,我来找竹秧、找竹笋给我妈吃,找不着。白胡子老人给他说,不怕、不怕,既然这样,就不怕、不怕。孟宗一下惊醒起来,醒来后,白胡子老人也不见了,竹秧发了很高了,他就把竹秧撇回家去,炒给他妈吃。后来,我们的教主(支嘎阿鲁)跟孟宗说,将来你妈死了,你要用野竹秧根、绵羊毛设你妈的灵,背回家供起。
树长天高,叶落要归根,没有根,苗从哪里发?所以设老人的灵,就是要用根,不能用苗。(收集整理:陶波;讲述人:洪兴光)
“梦中哭竹”故事也叫“孟宗哭竹”,是传统二十四孝故事,讲述晋孟宗,其母生病,冬日想吃竹笋,孟宗为尽孝,到竹林里去寻找,抱竹大哭,感动天地,大地裂开冒出竹笋,母亲吃了竹笋后大病愈。乌蒙山区的滇东北、黔西北地区流传的“梦中哭竹”和“孟宗哭竹”故事,就是传统孝子故事与彝族“竹”信仰融合的产物,借助孝子“哭竹”情节,展现孝文化,也解释了彝族祖灵为什么要用竹子或竹根制作,同时也说明彝族用竹子和竹根制作祖灵是孝文化的传承。
从《华阳国志》《后汉书》的“夜郎竹王”神话、彝文文献《洪水纪》的“洪水遗民”神话到民间口传的“云南土民的神话”“竹的儿子”“笃慕”“梦中哭竹”“孟宗哭竹”故事,彝族祖灵神话既有汉文文献、彝文文献记载传承,又有民间口头活形态传承。在彝族丧葬仪式中、祖灵制作中和祠堂祭祀中,彝族毕摩或彝族民众都会传承相关的神话,解释丧葬仪式、祭祀仪式中的祖灵和“竹”信仰等民俗事项。
二、乌蒙山区彝族祖灵和祠堂
彝族祖灵是祖先灵魂的附着物,是祖灵神话和祖灵信仰的核心;彝族祠堂是祖灵的陈放和祭祀场所,是祖灵祭祀的神圣空间。关于乌蒙山区彝族祖灵、祠堂的详细记载,在马学良、于锦绣、范惠娟的《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乌撒”旧邦访布母一章,记录非常详细。
1981年元月,彝族原始宗教调研组在“乌撒”旧邦的妈姑(今赫章县妈姑镇)进行调研。妈姑的陈布母比较详细介绍了“灵筒”“灵房”(家族祖祠)和岩祠(宗族祖祠)。
“灵筒”即祖宗灵魂存在处。尊语称“丕喀毛载”。作法是:用色线(男红女绿)缠“白花然”草根,装在3-4寸长的一段竹筒内即成。不再放其他东西。夫妇双亡,合装在一个筒内,放人“祠堂”。
“白花然”草彝语称“堵定史”。为什么用此草根,则有一传说,大意是:
从前有夫妻二人,丈夫出门多年,到处游荡,最后游到阴间去了。在阴间他还是到处走,阴间人(死人)都称他是“新来户”。多年后,他的妻子死了,到阴间落户。一天,夫妻二人相遇,妻子劝丈夫回到阳间去,丈夫则要求二人一同回去,但妻子不肯。妻子送丈夫回阳间走到阴阳交界的河边,妻子不肯过河,丈夫一把抓住妻子,捆在背上一齐过了河。谁知到家后,丈夫发现他背的不是人,而是一根白花然草根粘在背上。从此认为鬼魂既能变成白花然草根,那么此草根也就可代表灵魂或灵魂的存在处了。
李永才还根据另一布母(龙天福)的说法补充说,因为这种草容易滋生,取其象征子孙发达兴旺之意。
“灵房”,即“家族祖祠”,为放全家族“灵筒”的地方,彝语称“丕海”。灵房多建在房后的山林中,约一立方米大小,灵房内除灵筒外,还插约一尺长一寸宽的木牌,牌子上写祖宗的名子。也有只放木牌而不放灵筒的。也有只把家族中子孙兴旺的一双老人的灵简放人祠堂,其他另行处理。
岩祠是崖上石洞内放“维补”的地方。“维补”为全宗族共祭的祖灵存在处。作法是:用一段木头,掏空,内放用金银做的匙、碗等各种食具和锄、耙等各种农具。岩祠又称宗岩祠,不是每年都祭,十年,百年不祭也算了。凡祭必通知全宗族人。
李永才后来补充说,“灵房”内只留最近三代祖宗的灵筒,三代以上的就抽走了,只留祖名在木牌上,至于岩祠已是历史上的事了,此处早已不存在,也无人见过,所以都说不清楚。此则说明当地彝族的氏族家支关系早已松弛[10]。
关于乌蒙山区彝族祖灵祠堂,2022年笔者课题组开展了深入的田野调研,实地走访了六枝特区的关寨镇;水城区的董街道、营盘乡;钟山区的月照街道、德坞街道、黄土坡街道;威宁县的兴发乡;盘州市的淤泥乡、坪地乡;沾益区的炎方乡、播乐乡;宣威市的东山镇、普立乡等乡、镇、街道的彝族村落,发现各具特色的彝族祖灵和祠堂。
(一)彝族祖灵
祖灵是彝族祖先信仰的核心,其附着物是“竹”或“竹子”制作的物体;也可以说祖灵信仰就是“竹”信仰。但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民族之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祖灵信仰的附着物“竹”也在不断变化,但其神圣性不因附着物的变化而变化,传统的祭祀仪式依旧,群体的虔诚性依旧。
清代《宣威州志》中对于祖灵筒的制作是这样记载:
以竹叶草根,用必磨(即巫师),因裹以锦,缠以彩绒,置竹筒中,插篾篮内,供于屋深暗处;三年附于祖。共入一木桶内,别置祖庙以奉之,谓之鬼桶,打牛羊大祭其先,谓之祭鬼[11]。
马学良先生在《竹灵和图腾》也有关于乌蒙山区彝族祖灵用竹制作与洪水泛滥遗民神话相关的记载:
云南夷族则传谓古代洪水泛滥时,其始祖渎阿普经太白仙指示,挖木为筒,避身其中,随水漂流,其后水退,木筒漂至悬崖,幸为山竹挂住,祖人得免坠崖,自是后人奉祀山竹,故人死后,即以山竹制灵牌,盖以山竹可以保护后裔。故事传说,虽不全同,但崇拜竹子信竹子与祖人有特殊关系,及竹能保护族裔,则各地夷族皆然[12]。
除了竹筒之外,祖灵的制作还需要红线、绿线、绵羊毛、茅草根、白花燃草、黄皮树枝、五倍子树枝、尖刀草等其他材料,都有相应的神话传说附会。《昭通彝族史探》以及马学良先生的《灵竹和图腾》《宣威河东营调查记》《云南土民的神话》等材料中均有相关记载。
关于彝族祖灵,田野调研中发现,六枝特区关寨镇箐口村依旧为篾箩和竹筒,内附一块大木牌,有彝名的则用彝文书写逝者姓名,没有的则用汉字书写逝者姓名;水城区董地街道董地村的祠堂中不见篾箩和竹筒,只有大木牌,逝者姓名有的书写彝文,有的书写汉字;2020年新建成的钟山区阿喾寨张氏祠堂已经换为灵牌,牌位上全部用汉字书写,但在灵位架下面的暗格里还藏着一块传统祠堂中传承下来的大木牌,隐约可以看到一些彝文。
整体来看,乌蒙山区的“祖灵”从传统的祖灵筒、竹篾箩箩到大木牌位、单一的灵牌等,祖灵的附着物在不断改变,但祖灵的神圣性并没有因附着物的变化而变化,祠堂的祭祀活动依然代代传承,相关的祖灵神话也在代代相传。
(二)彝族祠堂
彝族祠堂是祖灵信仰的神圣空间,按照祭祀要求进行陈列竹子制作的祖灵筒。传统彝族祠堂的地理位置有严格的要求,祠堂内部祖灵的陈列也有严格的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多元的建筑材料进入彝族村寨,祠堂建筑材料在不断更新,祠堂的选址也在不断变化和适应,但其陈列、祭祀的作用依然传承,部分地区彝族祠堂还兼具聚会等功能,成为维系家族关系的新场域。
清代《水城厅采访册》记载了今六盘水市的彝族风俗,里面介绍了彝族“宗祠无栋宇,高二尺许,植把木数株,覆以茅数束”[13]。关于彝族祠堂的选址和建筑,彝族地区和彝汉交界地区有不同的情况。马学良在《宣威河东营调查记》记录了彝汉交界地区的宣威东郊的河东营的情况。
安葬毕,便将“篾祖”(即神主)拿去供好,据说是放在后檐外的墙上。不过,现在已不多见,并改供“神主”,在后檐墙内的土窟内,与汉人供的一样,有香炉、神灯,早晚供奉。
“篾祖”是一个竹筒,内放羊毛,花针(缝纫的)花线(本地汉人之神主内,亦以针穿一红线插在红布上,很相近)。外面用竹编成一个小箩装着,也是夫妇同用一个,积三代人后,到山洞里找一个地方藏着,请人去供祀,这时供的地方,叫作“阴祠堂”[12]328。
另外马学良先生在《云南土民的神话》记录了乌蒙山深处的彝族村寨的宣威普鹤乡卡腊卡村(今宣威普立乡拉腊卡村)彝族祠堂的选址和建筑。
今白夷全族尚于村后幽静的山林中,建一供祖堂,形如各村所建之土地庙,神堂后位于山岩,其中供奉五位神,依次排列,插于堂内之瓦缝中,第一位为天,第二位为地,第三位为神仙,(即神话中之仙翁),第四位即被难脱险之祖人,第五位即先祖之妻。
神堂的位置是固定的,不能随意迁移,神堂最好的位置,是建于堂后的陡岩,前为平原,岩下满种刺竹,盖纪念其祖先之蒙难处。神堂附近树木,不得砍伐,违者全族惩罚,传说如砍伐此树,则全家得灾,所以神堂附近,老树参天,风景清幽,为夏日乘凉胜地[17]28。
关于彝族祠堂,田野调研中发现六枝特区关寨镇箐口村彝族祠堂还保存传统祠堂的建筑和祖灵,祠堂的选址一般在村寨周边幽静的竹林中或房屋背后的山坡下,祠堂的形制如马学良先生在宣威卡腊卡村所见相同。六枝特区箐口村的祠堂有一间的,也有两间的。在水城区董地街道董地村见到的彝族祠堂选址跟传统祠堂一样,选择村寨周边小山坡或屋后的小山坡,其形制比六枝的大一倍,祠堂大多数为两间,据说大的一间主要供奉正常逝世的亡灵,小的一间主要供奉非正常逝世的亡灵。在水城区营盘乡见到的杜氏祠堂选址在半山腰,其形制跟当地村民新建的小洋楼民居一样,两开间两层,有门,有窗户。在钟山区月照街道调研发现有一户彝族祠堂有三间,形制与董地街道董地村类似,一间相对较小悬挂非正常死亡的祖灵,第三间悬挂其母亲改嫁带来的其他民族兄弟。月照的三间制彝族祠堂为调研组唯一所见,这样的祠堂既保留了彝族传统祖灵祭祀,又凸显民族融合的关系,可谓独具一格。
乌蒙山区的彝族祠堂陈列的祖灵筒,是竹中生子、洪水遗民、孝子故事等神话的隐喻。当人们来到彝族祠堂,见到祖灵筒,开展祭祀活动时,随着毕摩对于相关经典的吟诵,随着袅袅的烟火,人们就能回到关于祖灵的神话空间,回忆神话故事中祖先的际遇,一代代传承着关于祖灵的神话,进行着相关祖灵的祭祀仪式。整体来看,乌蒙山区彝族祖灵祠堂,从传统的岩壁、洞穴祠堂,到茅草小祠堂、瓦房小祠堂、钢筋混泥土小祠堂和屋舍大祠堂,祠堂的变化导致祭祀场域的随之变化,但祠堂的核心“祖灵”祭祀是唯一不变的。
三、乌蒙山区彝族祖灵祭祀
彝族认为人有三魂,人逝世后,三魂有不同的归宿。乌蒙山区毕节市大方县彝文《指路经》记载:人死变三魂,一魂去祖地,一魂守焚场(坟墓),一魂留宗祠,享子孙祭奠。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彝族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魂”观念依旧存在,但是祖灵的祭祀在发生变化。既有传统祠堂祭祀,也有祖坟扫墓祭祀,还有家庭祖堂祭祀等,祭祀方式越来越多,祭祀时间也越来越灵活。
(一)祠堂祭祀
乌蒙山区彝族祠堂多种多样,但每年春节、十月年都会组织集中的家族祭祀活动。2020年12月5日,调研组参加了钟山区阿喾寨的“张氏宗祠”落成暨祠堂祭祀活动。
阿喾寨既有崖祠、传统祠堂(类似土地庙的小祠堂),也有2000年修缮的祠堂(10平米左右的两间)。2020年12月5日阿喾寨又在后山新建了一座“张氏宗祠”,祠堂牌匾彝汉双文,一共两间,一间作为家族聚会、就餐场所,墙壁上悬挂张氏相关的历史和文化;另外一间按照汉族祠堂模式建设,里面从高到低设置为阶梯状的台,将制作好的祖先灵牌,按照辈分进行排列。在祖先牌位下面还有一个暗格,里面还选挂着老祠堂传承下来的大木牌匾,因历史久远但依稀可见部分彝文。
整个祠堂祭祀活动由毕摩主持,按照传统“安灵”仪式进行,吟诵彝文经典,进行祭祀祖灵仪式活动,将新制作的逝者牌位进行一一祭奠,通过泡木树搭建的“门”,然后由家族中的年轻人将灵牌请入祠堂,按照辈分依次排位。
除了祠堂的祭祀活动,就是家族的聚餐,家族中男女老幼齐聚一堂,享受祭祀的美食,交流感情,维系家族团结。
(二)祖坟祭祀
乌蒙山区彝族传统葬俗是火葬,《炎徼纪闻》记载贵州西部彝族葬俗:“人死,以牛马革裹而焚之。”《黔南识略》卷二十四记载:“殓用火葬,招魂于野,结松棚设灵幄,谓之翁车,椎牛野祭,击鼓吹喇叭,亲戚会葬者数百人,谓之做戛。”康熙《贵州通志》卷三十《蛮僚》记载:“其长死,则集千人披甲胄驰马若战,以锦段毡衣披死者尸焚于野,招魂而葬之,张盖于上,盗邻长首以祭,不得则不能祭。”因此彝族认为,三魂有一魂归焚场,因丧葬习俗的变化,传统火葬变为土葬,因此一魂归坟墓了。
随着民族文化的交融,传统土葬风俗不断深入,土葬逐渐替代火葬,坟墓替代火葬场域,乌蒙山区出现越来越多的彝族坟墓,不断形成家族墓地。在现代化进程中,祖灵筒的存放和祭祀空间彝族祠堂逐渐退出部分彝族村寨,坟墓的祭祀地位日益凸显,坟墓也是逝者灵魂唯一的归宿,祖坟的修建和祭祀显得尤为重要。
祖坟祭祀有家族统一祭祀,也有家庭单独祭祀,在乌蒙山区的钟山区、水城区、宣威市的调研了解到,祖坟祭祀时间一般有正月初二、正月十五、清明节前、十月朝、冬至等,主要活动有拜年、亮灯、供饭、扫墓、挂青(也叫挂纸)、修坟立碑等。
2021年3月24日调研组参加了董地街道董地村彝族王姓人家的修坟祭祀活动。该户人家还有传统祠堂,祠堂仅在年节祭祀一次,相对祠堂来说,本地彝族群众更为重视坟墓的修建,认为坟墓的风水会影响后备的福禄,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维修坟墓或者选择风水宝地进行迁坟。此次修坟祭祀活动,将原本在进村委会道路旁低矮的坟墓,用雕刻精美的青石垒砌坟墓,并竖立一通精美的墓碑。家族中的亲戚都来帮忙搬运石头和垒砌,其他亲朋也来观礼,修坟祭祀的高潮是墓碑落成仪式,仪式由村里的阴阳先生主持,要献饭、供酒等,最后挂好红布,然后燃放一堆烟花爆竹。修建后的坟墓整体提升了2~3米,气势雄伟。整个修坟和祭祀活动中,主人家、主祭者和参加修坟祭祀活动的均没有谈及祖灵和祠堂相关话题,更多的是谈论这一墓地的风水及其后辈子孙的福禄。
(三)家庭祖堂祭祀
家庭祖堂祭祀,即年时节日在供奉“天地君亲师”“历代先祖”的家中祖堂开展的家庭活动或个别活动的祭祀,时间一般为春节、正月十五、清明节、端午节、七月半、中秋节、十月年、冬至等年时节日,主要活动有供饭、烧纸、上香等。年时节日在祖堂前供上斋饭、酒肉、蔬果,点燃蜡烛,焚起袅袅香火,家中长辈就会讲述彝族历史上是供奉祖灵的,祖灵是用什么制作的等神话,一代代传承民族文化和祭祀传统。
在钟山区阿喾寨的调研中发现,该村寨虽然有崖祠、传统祠堂和新修的“张氏宗祠”,但是对于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在家中祖堂。家中祖堂为“天地君亲师”,边上有“张氏历代先祖”等,初一十五、年节岁时,张家都要供饭、焚香,请老祖宗回家享受供奉。
从传统的春节、彝族年祭祀祖灵,到今天的春节、清明、彝族年甚至元旦、国庆节等其他重要节日也会供饭和进行祭祀,祭祀场域包括祠堂祖灵的祭祀、墓地祖灵的祭祀、屋内“天地君亲师”“历代宗亲”的祭祀,祭祀场域和祭祀时间的多样化,祖灵神话的活形态场域逐渐消失,祖灵的神圣性逐渐淡化,追思、祭奠祖先的世俗性不断加强。
四、结语
乌蒙山区至今还保存有传统的彝族祠堂,在彝族老人逝世后,还有毕摩主持相关仪式,制作竹篾箩箩和祖灵筒,念诵相关彝文经典,讲述相关神话故事,传承相关民俗仪式,可谓活形态传承彝族祖灵神话。更多的彝族村寨、彝族家庭随着社会的变迁,祖灵、祠堂等的逐渐改变与消失,附着在祖灵和祠堂的祭祀仪式也随之消失,活形态神话的展演语境也随之消失,其传承也陷入困境。如何更好的保护与传承彝族丧葬、祭祀文化,保护活形态神话传承的场域和语境,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长期探寻的问题。乌蒙山的活形态神话的调研和研究还在深入,不同的神话素材、神话语境还在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