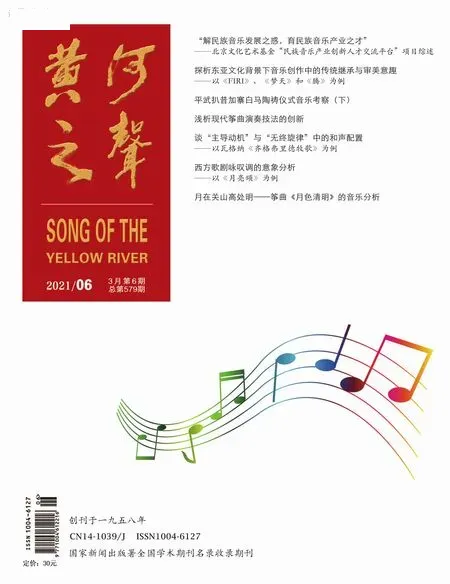西方歌剧咏叹调的意象分析
——以《月亮颂》为例
高 涵
一、《月亮颂》作品简介
(一)歌剧《水仙女》简介
《水仙女》是一部三幕歌剧,作者为德沃夏克,讲述了水仙女鲁萨卡爱上了人类王子后被王子抛弃,最终王子死去换得她回到水中的爱情故事。
鲁萨卡爱上人类王子,想去陆地生活,向森林女巫献祭声音换取人类的身份。王子对鲁萨卡无法说话感到苦恼,婚礼上爱慕王子的外国公主对鲁萨卡出言嘲讽,王子听后竟然去倾慕热情的外国公主而厌倦鲁萨卡。这时老水仙来婚礼看望自己的女儿,发现王子抛弃了鲁萨卡,诅咒王子永远无法摆脱鲁萨卡的爱情,随即带着鲁萨卡进入了湖水中。王子吓得跪倒在外国公主面前求救,却只得到公主的嘲笑。森林女巫告诉鲁萨卡变成人类的水仙女被人类抛弃后只能过着痛苦的半人半精灵的生活,而且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如要破解只能取王子的性命来换回鲁萨卡的生命和灵魂。王子听到后向鲁萨卡忏悔,最终用生命换回鲁萨卡水仙女的身份。
(二)咏叹调《月亮颂》简介
《月亮颂》节选自歌剧第一幕,鲁萨卡在人间遇到了倾慕的王子之后,又与他失之交臂,带着对王子无限的眷恋返回水中。这一唱段前面承接的剧情是:鲁萨卡告诉自己的父亲自己爱上了人类王子,想要去陆地上生活,鲁萨卡的父亲再三劝告、警告无果后,悲愤中告诉鲁萨卡她应该去找森林女巫求助。老水仙离开后,鲁萨卡对月唱出了这曲咏叹调。
二、歌剧中的审美意象
(一)审美意象
“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原本“意”与“象”是分开的,意是审美主体的心意状态,象是审美对象的感性形象,二者经过历代哲学家、美学家的研究和归纳,逐渐融合、总结成为一个词语。即对象的感性形象与自己的心意状态融合而成的蕴于胸中的具体形象。
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艺术家通过艺术表现手段将自己的意象诉诸于作品,以此向欣赏者敞开这一意象世界。但艺术创作不能将艺术家的意象世界完全转化,因此艺术作品总是对欣赏者保留一定的自由,同时艺术作品也在欣赏者的不断欣赏和阐释中不断地被发掘和揭示出新的方面和更深的层次。艺术的本体就是审美意象。因此,我认为这一中国古典美学概念也可以运用在西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中。
(二)歌剧中的审美意象
在中国古典美学看来,意象是艺术的本体,意象也是美的本体。歌剧作为一种艺术,其本体也应当是意象。意象是情与景的内在统一,是一个完整的有意蕴的感性世界,歌剧的本体也是一个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
歌剧的本体是审美意象,歌剧的创作就是意象的生成。但歌剧艺术的创造过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作曲者到表演者再到欣赏者,经历了两次创造。在歌剧艺术中,第一次艺术创造是作曲家由创作素材生成审美意象,以曲谱的形式表达出来。第二次艺术创造是表演者以作曲家创作的曲谱融合自己的心意状态,生成了复合作曲家和表演者二者审美意象的意象世界,再以表演的形式呈现给欣赏者。在第二次创造过程中,表演者既是意象的欣赏者--在表演者的欣赏中曲谱的意象世界才得以呈现;表演者同时也是意象的创造者--将自己胸中的意象呈现给观众。
叶朗在《美学原理》中将艺术作品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材料层、形式层和意蕴层。歌剧艺术作品也可按照这种层次结构加以分析。
材料层是艺术作品的物质载体,承载了“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飞跃。歌剧作品作为一种音乐作品,其物质材料是声响。歌剧作品的物质材料层对歌剧的美感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会影响意象世界的生成。西方歌剧中的西洋乐器和美声唱腔都是构筑其意象世界的基础。另一方面,物质材料会给予观赏者一种质料感,例如花腔女高音常给人一种欢快的、灵巧的质感,男中音则给人一种浑厚的、有力的质感。质料感带有情感色彩,能够给作品营造一种气氛,使歌剧的意象中充满一种韵味,从而成为歌剧作品美感的一部分。
形式层是艺术形象的物化,可分为内形式和外形式。内形式是艺术家创作时已形成但未能传达出来的艺术语言;外形式是作品呈现给欣赏者的形式符号。外形式本身也具有形式美。这种形式美相对独立于歌剧的意象世界本身,可以体现在表演者的炫技上(如唱高音、长音或出音律高、音高变化幅度大的装饰音等)。这种技巧美可以孤立的被观众欣赏,引起人的惊奇感和快感,同时也能融入整个歌剧的意象世界,从而具有审美价值。
艺术作品的意蕴是直观欣赏作品的感受和领悟,很难用逻辑判断和语言“说”出来。意蕴还带有多义性、宽泛性、不确定性和无限性。多义性、宽泛性和不确定性意味着不同的欣赏者对同一艺术品可以有不同的感受和领悟,而作品经过不同的欣赏者不断地体验和阐释,就有不断的新的方面被揭示。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歌剧作品不断被演出、被观看的过程,也是它的美感和意蕴不断显现和生成的过程。
艺术的形式层和意蕴层都具有复合性。从形式层来说,歌剧的曲谱、文本是它的第一形式,演唱、演奏是它的第二形式。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都含着歌剧艺术的意蕴,但作为一种音乐表演艺术,歌剧的意蕴对于欣赏者而言主要在于第二形式的演唱、演奏。
三、咏叹调《月亮颂》的审美意象分析
(一)材料层分析
《月亮颂》是一首女高音咏叹调,在剧情中是由鲁萨卡——水仙女,水中精灵这样一个角色来演唱的,所以其音色除了女高音本身所具有的清晰、明亮以外,还带有一种空灵、柔美的色彩。在歌剧中,先由竖琴演奏一段引子,引出交响乐的前奏。竖琴的音色高雅、纯净,前奏中竖琴演奏的琶音像是月下泛着波纹的湖水,营造出静谧、优美的氛围。管弦乐的伴奏在前奏和间奏中保持了静谧的氛围,但在尾声中演奏了高出音率的低音,然后不断向上推动,将乐曲推向高潮,管弦乐的变化象征着鲁萨卡心情的变化。作曲家通过竖琴及其它管弦乐器的配合,营造出了乐曲的氛围。
(二)形式层分析
《月亮颂》全曲共127小节,其结构是“引子+A+B+连接部+A1+B1+尾声”。
引子共22小节,在歌剧中引子开始前有4小节的竖琴音阶演奏铺垫,衔接了引子部分前3小节的属七和弦上行琶音。后接5小节的下行和弦,引入管弦乐队,前3小节力度为ff,从竖琴的下行和弦开始渐弱,至管弦乐队合奏部分转为pp。前奏表现出鲁萨卡内心渴望到陆地上与王子一起生活,对水妖的身份感到挣扎的情绪。平缓、柔和的管弦合奏为后面A段的演唱铺垫,营造了神秘而幽静的氛围。
A段为23小节到46小节,是鲁萨卡对月亮倾诉。音区偏低,曲调比较平缓柔和,像是较为平静的娓娓道来、缓缓诉说。第31小节到第37小节和第39小节到第45小节的词一样,但是音高上移了,体现出情绪的递进,表现了鲁萨卡愈发激动的情绪同时为B段作铺垫。
B段为47小节到62小节,开头就是一个八度的大跳,整段旋律中跳进较多,节奏律动感加强,伴奏织体更加丰满,音响效果更加明亮。这一段鲁萨卡对王子的思念从婉转、温柔变为激动、无法抑制的呐喊,对月亮的倾诉也从平缓的诉说逐渐变成激动的祈求。
63小节到67小节是乐曲的连接部,63、64小节节奏快、力度变化大、出音律高,延续了B段强烈、激动的情绪,65小节开始音高下降、力度渐弱,到66小节结束时最弱,表现出鲁萨卡情绪的平复,以承接A1段。
A1段(68小节到93小节)、B1段(94小节到109小节)是A段和B段的变化再现。A1段B1段和A段B段在情绪上是递进的,所以这个部分是更激动的、更急切的,尤其是B1段,即将连接情绪最紧张的尾声,这里相对于B段的变化就是要让鲁萨卡的情绪更推进、更激动,表现出鲁萨卡对王子的向往、对去陆地上与人类王子共同生活的想法变得坚定,决意去陆地上追求爱情。
尾声为110小节到127小节,110小节到116小节是一段间奏,和连接部的旋律、节奏基本相似,但是在114小节从pp做了渐强,116小节渐弱,到117小节人声进入处最弱,间奏部分的器乐演奏保持了乐曲整体的情绪和完整性。117小节到120小节,演唱的力度为p,音高全部在较低的d1,节奏快,此时表现的是水仙女对月喃喃自语的场景。121小节开始,旋律层层推进,力度渐强,歌词均为“月亮啊,留下吧”,124小节是全曲的高潮,125小节的降b2是全曲的最高音,力度最强,也是情绪爆发的顶点,之后全曲结束于调性主音的八度大跳,收在了鲁萨卡澎湃的情绪上。这种戏剧性很强的高音和大跳在表演上本身也带有一种技巧美。
曲式作为歌剧的外形式,它的形式符号与生活具有较为直接的对应性。例如引子部分的竖琴演奏就对应着静谧的自然环境中的水波,平缓进行的A段对应着演唱开始时鲁萨卡较为平静的情绪,B段、尾声的音高上移和八度大跳都对应鲁萨卡激动、急切的心情。这些形式符号构筑出一个完整的意象世界,引导欣赏者从外形式进入内形式。外形式本身也具有其形式美,《月亮颂》工整的曲式、优美的旋律与和谐的配器本身都具有形式美。而内形式更接近作品的意蕴,下面就内形式和意蕴展开分析。
(三)《月亮颂》中的移情作用
《月亮颂》全曲的内容都是鲁萨卡对月亮诉说自己对王子的眷恋和思念,其实是将王子的生命移置到了月亮上,将鲁萨卡的情感与遥远的月亮同一化。月亮本身是无生命的,但在咏叹调中,鲁萨卡的情感赋予了月亮生命和力量,此时歌曲中的“月亮”不是物理的、客观的天体,而是意象世界中的月亮,是作为一种审美对象的存在。
歌剧中的形象是艺术家借助形象手段将自己的艺术发现和审美经验揭示出来的产物。这种艺术发现虽来源于生活经验,但其创作的形象化手段往往需要将艺术形象与纯粹的生活形象拉开距离。这种距离是对生活经验、生活形象的一种取舍,以此去把握更深刻、准确的生活本质和情感内涵。在《月亮颂》中,移情作用将人的情感移置到月亮上,这种爱情的形象与生活中爱情的形象拉开了距离,摒弃了功利性和过度的热情,从而凝练出更令人共情的艺术形象。
移情作用的核心是意象的生成。意象世界是一个情景相融的感性世界,《月亮颂》以鲁萨卡对王子的情与寂静的月夜湖边的景相交融,使观众能够身临其境,与情境“物我同一”,以达到对作品意蕴的领悟和感受。
(四)意境与飘逸
意境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场景、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飘逸是中国文化史上,以道家文化为内涵的一种审美的大风格。飘逸有三个特点,一是超越时空的阔大,二是逸兴遄飞的美感,三是人与大自然融而为一的境界。飘逸的文化内涵是精神的超脱和人与自然生命的融合为一。意境与飘逸都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
《月亮颂》以月为象,“月”是一个相对远的意象,它能把人的思绪从有限的歌剧舞台延伸到无限的时空中,引发观众的思念、眷恋、惆怅。这种感兴超越了“情景交融”,在与艺术家的情感达到同一性的基础上得到了自我确诊,在艺术形象的启发下产生了自己的情感。观众在欣赏《月亮颂》时,也化身为鲁萨卡展开审美活动。这时产生的审美感情和自我确证超越了与鲁萨卡的共情,是欣赏者自己的情感,更加亲切和自由。
《月亮颂》中,鲁萨卡移情于月,向月亮倾诉对此刻不知身在何处遥远恋人的思恋,本身就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无限感,使角色的情感不再局限于一隅舞台,而是扩散到了整个“月光漫游的世界”;而月作为一种思念的象征,能过引发欣赏者更远的思想和情感,体现出一种阔大的效果。鲁萨卡是湖中的水仙女,咏叹调的配器上多用竖琴演奏琶音以制造月下湖面水波的效果,营造林中湖边的静谧美感。人的情感与月的形象融合为一,塑造出清新自然的艺术形象。
鲁萨卡追求超越物种、超越时空限制的爱情,其精神是自由超脱的;《月亮颂》的艺术形象是人与大自然的生命融为一体的。这都体现出飘逸的审美特征。
(五)鲁萨卡的悲剧性
真正的悲剧是由个人不能支配的力量所引起的灾难却要由某个人承担责任,是以个体生命毁灭的形式来肯定人类生命中正面价值的美学范畴。
在《水仙女》中,鲁萨卡追求的爱情是纯洁的、甘愿为其奉献一切的;但鲁萨卡献出声音、改换身份以得到与王子结合之后,却遭到了王子的抛弃,她的爱情被毁灭了。鲁萨卡对爱情的追求,其实也是一种对超越物种、身份的自由的追求。鲁萨卡被王子抛弃和王子最终为鲁萨卡献出生命,都体现出一种宿命感,一种无力抗争命运的感觉。《水仙女》第一幕,鲁萨卡告诉老水仙自己向往成为人类同王子在一起时,老水仙告诉她这样势必付出巨大的代价;王子抛弃鲁萨卡时,老水仙警告他永远无法摆脱水仙女的爱情。而最终,鲁萨卡失去了爱情,王子失去了生命,鲁萨卡的抗争失败了。剧作中不可调和的矛盾,以情感和生命的毁灭作为终结。但这种毁灭引发了欣赏者内心的震撼,它带给欣赏者对命运的恐惧感,但也令人对鲁萨卡产生怜悯。鲁萨卡为了自由爱情的抗争在悲剧中显得渺小,情感也被命运所吞噬,但却给人们心中留下了纯洁、勇敢的艺术形象。
而在咏叹调《月亮颂》中,预示了鲁萨卡的悲剧。水面与月亮的距离,象征着作为谁仙女的鲁萨卡和作为人类的王子在身份和物种上的差距。鲁萨卡在咏叹调中不住的请求月亮留下来,其实是盼望王子留在她身边;但月亮的移动不会因鲁萨卡的请求而改变,不专情的王子也不会因为鲁萨卡的心意而专注于鲁萨卡。鲁萨卡向月亮请求,希望王子能在睡梦中想起她,“哪怕只有一刹那”;而鲁萨卡献祭声音和水仙女身份求得的王子的爱,连二人的婚礼都没能维持过去。《月亮颂》出现在整场歌剧的第一幕,这种与后续剧情所对应的预示感与《红楼梦》中的十二判词有些相似,都在后续情节中一一应验,在“命运”的力量下,鲁萨卡自由爱情的理想被毁灭了,她爱情的悲剧实际上是命运的悲剧。
结 语
《水仙女》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悲剧,鲁萨卡追求超越身份、物种的自由的爱情,却又被命运打败,失去了自己的爱情。而《月亮颂》这一唱段,集中表现了鲁萨卡对自由爱情的向往与期盼。《月亮颂》旋律优美、情感充沛,从审美上来说,也以音乐的手段构筑了一个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并且超越了具体的场景和物象,让人能感受到包含了人生感的惆怅与美感。对《月亮颂》进行意象分析,一方面是帮助表演者从第一形式上理解从而更好的表演,另一方面是有助于欣赏者从第二形式中领会、体悟作品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