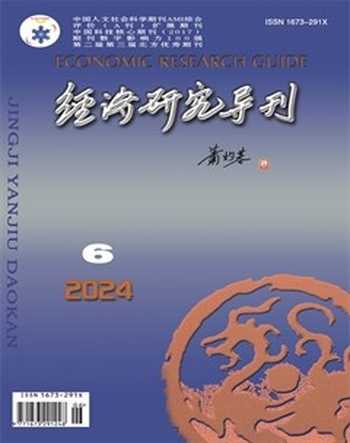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发展路径探析
孙惠敏
摘 要: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源自公司法第182条及司法解释二第1条的规定,其中将司法解散的事由定义为“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增加了司法适用的困难。同时,由国家机关运用强制力解散人合公司势必打破公司自治性、违背部分股东的意志,其正当性在于在人合失灵前提下解决封闭公司资本多数决与股权结构的矛盾,并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根据对典型司法案例及域外制度的分析,提出司法解散制度的两点改良路径。其一是确立起以公司职能机构运行困境的人合性障碍为主、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为辅的适用标准;其二是建立包括股权回购及股权让与在内的司法解散替代救济机制,以提高司法解散制度在实践中适用的统一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司法解散;人合性;股权回购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4)06-0145-04
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出台的公司法第183条(现行公司法第182条)首次确立了司法解散公司之诉,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持有公司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但是,该条款包含了诸如“经营管理”“严重困难”“重大损失”“其他途径”等弹性的模糊词汇[1],法院很难掌握明确处理这类案件的具体方向和标准。因此,3年后即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相应司法解释,对解散事由进一步明确细化。
根据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司法解散之诉的原告是共同或单独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被告是股东请求解散的公司,事实和理由限定为司法解释二所规定的四种情形。司法解释以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为前提,规定了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大)会、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导致公司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大)会决议、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大)会解决这三种具体情形,以及“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一兜底条款。司法解释二第1条的列举局限于股东或董事矛盾导致公司陷入人合性危机而与公司的经营状况无干,但在司法解释前三项列举的具体情形之外,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判断依旧较为困难,而且争议颇多。可以说这正是实践中司法解散之诉的争点所在,同时也意味着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中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可能导致因法官观念的不同,使得同类案件得到不同处理结果。
正如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对于司法解散诉讼的标准判断其实无法通过预先立法进行完全概括,正确的做法是经过司法实践充分检验之后对立法进行逐步细化。据此,本文通过对法宝网上典型案例以及国外立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研究,试图找出司法解散诉讼更为明确的判断标准以及下一步的发展路径,为司法实践添益。
(二)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对于法条所述“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探索研究非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论文都认为,公司解散标准应当是人合性问题而非公司经济利益方面的范畴。李建伟教授认为,公司经营管理困难是属于管理困境而非盈利困境,其根源在于封闭的中小公司股东人合性障碍导致的治理失灵[2]。梁清华教授认为,公司解散纠纷一般以人合性丧失作为起因,因此将人合性作为公司应予解散的核心标准是适当的。同时,公司司法解散的目的并不在于解散公司,而是以股东退出公司的手段解决人合性障碍[3]。笔者通过对学者文献的研读以及司法案例的分析,从而得出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标准界定及司法解散制度的替代性救济机制。
一、司法解散正当性分析
司法解散实质是由国家机关以强制力打破公司自治、终结公司主体资格,所以必须要具有显在的正当性。公司自治是存在局限性的,股东在设立公司时无法预见或故意忽视未来的人合性危机,从而导致公司章程对这类问题无从解决。一方面资本多数与均衡股权结构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4],另一方面非均衡股权结构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容易遭受侵害。故而需要司法解散制度收紧公司自治的底线,避免公司自治成为无底线的自治[5]。在英美法系,司法解散制度属于衡平法的范畴。衡平法最初产生就是为了补救和纠正普通法因内容和程序局限而出现的不足和不公。蒋大兴认为,破产法与公司法中的“强制解散制度”形成互补,分别重点解决“资合性欠缺”和“人合性欠缺”公司之解散。故而不应过分担心强解散对社会利益造成损失,而应当增加替代性救济方式,节省股东退出成本[1]。
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处理公司解散案件时应当保持谦抑的态度,注重纠纷调解,若当事人之间协商同意以公司回购、股权让与、公司减资等方式处理纠纷,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可以看出,法条注重由股东自主解决人合性危机,这是为了维护人合公司的自治性免于国家强制力的侵害,着重保障公司的社会价值。
二、司法解散实证分析
(一)研究范围
2005年公司法修正案中才出现有关公司司法解散的规定,2005年之前法院一般认为这类案件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例如,2002年的王文祥诉马恩树、兖州市南郊水暖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解散清算一案,最高人民法院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指出,“人民法院受理股东强制解散、清算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根据”,故对此类案件应当不予受理。因此,笔者在法宝网上键入的检索时间始于修正案生效的2006年1月1日。通过对“公司解散”及“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进行检索,笔者找到以下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进行具体分析研究。
(二)案件分析
指导案例: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一案中,林方清与戴小明就是以1:1的均衡股权结构设立凯莱公司,公司不存在亏损,但二股东因长期矛盾已四年未召开股东会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同时林方清的监事职权、戴小明的董事职权都无法正常行使,并且二人诉前已尝试由服装城管委会调解,以及采取其他途径,但都无法解决问题。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判理由认为,“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及监事会或监事的运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故最终裁判凯莱公司解散。可见,对于司法解散案件,法院的着眼点应当在股东人合性障碍,而不考虑公司的经营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法院裁判生效后直至2022年8月凱莱公司始终未解散,期间股东双方达成公司分立及赔偿的和解协议,但2014年因戴小明未全部履行致使公司未分立。2019年林方清以知情权被侵害提起诉讼,提出2014年至2018年四年间凯莱公司仍未召开股东会,林方清股东权利、监事职权始终无法行使,可见公司的人合性障碍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吉林省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宏运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认定经营管理严重困难不应当拘泥于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是否在2年以内召开,而是应当对公司在出现人合性纠纷之后公司内外部的救济情况、职能机构决议的有效性、僵局持续的时间等进行综合考量,实质判断公司是否处于“经营管理严重困难”且无从救济的状态,而不应当拘泥于司法解释二所列举的三种公司决议困难的情形。
公报案例:仕丰科技有限公司与富钧新型复合材料(太仓)有限公司、第三人永利集团有限公司解散纠纷案中,因富钧公司董事冲突,故总经理张博钦自行离开公司,致使公司日常經营管理无从进行,同时导致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自2005年4月7日起六年多始终未能有效召集董事会,以致董事会长期无法履行职能,且在长达两年多的函件沟通中股东冲突始终未能化解,可见已经达到了公司司法解散的程度。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公司解散是合法合理的。在本案中法院将被告公司亏损致使股东利益受损也作为判案理由之一。根据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公司司法解散事由仅应当包含公司的经营困境。经过前述对司法解散的正当性分析可以得出,中小股东利益也可以作为司法解散的认定事由的补充,但其必然是以公司陷入人合性困境为前提的。
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周某某与南某农业公司、何某某、金某农牧公司公司解散案就体现了对中小股东保护的思想。案例中,周某某、何某某、金某农牧公司出资额分别为26%、25%、49%成立,何某某父亲管理公司。2015年3月因股东矛盾致使何某某父亲离开公司,自此到2021年的6年间股东矛盾无法化解,致使南某公司始终处于停滞状态。法院认为,公司股东之间或公司管理人员之间冲突致使公司陷入僵局会使公司股东利益受损,赋予股东解散公司的请求权是为了保障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大股东利用控制权损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非常多,而且封闭人合公司中小股东难以通过股权转让等方式进行有效的问题解决,包括前述指导案例中林方清虽掌握50%的股权,但是相对于有董事职权控制公司的戴小明仍然居于弱势地位,致使其无法有效行使股东权、监视权,只得寻求司法救济。
三、司法解散制度域外经验
司法解散制度始于1933年的美国,之后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先后在法律中做出相关规定。本文选取英美法系的美国和大陆法系的德国来对司法解散制度进行研究。
(一)美国司法解散制度
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第十四章第三分章规定了司法解散制度,对司法解散的认定做出了以下规定。即股东无法打破董事之间的管理僵局,且公司有无法补救的损害风险或公司业务无法按有利于股东方式运转;董事或实际控制人已经或将会以非法、压迫性的或者欺诈性的方式行为;股东投票僵局连续两次年会之后无法选出任期已满的继任人;公司的资产正遭滥用浪费[6]。英美两国司法解散制度从一开始就被作为公司内部矛盾的解决机制,并承担了保护少数股东的功能。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立法发展出多种替代性救济手段,包括股权强制置换等方式,以避免强制解散的大范围适用。
(二)德国司法解散制度
德国《资合公司法》仅规定了司法解散有限责任公司,要求司法强制解散必须是由于“法律规定或者某些客观情况的出现,致使企业根本无法经营,股东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难以消除的,而且直接威胁企业存续的冲突”[7]。可见,德国法更加严格地以股东人合性障碍作为公司司法解散的适用条件。
四、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改良路径
(一)司法解散适用标准重构
司法界对于公司经营管理困难的认定障碍根本上来源于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并不明确。根据前述司法解散制度的正当性分析和司法案例及域外法研究,司法解散适用的“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应当属于公司的人合性障碍,而非盈利困境。盈利困境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的问题,只要公司内部的职能机构正常运转,就完全可以通过改善经营、技术革新等方式自主解决,不需要司法途径介入强制解散公司。
林清方案件中法院对于“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具体判断具有典型的意义,即应当综合分析公司职能机构的运行状况,而非困于司法解释规定的公司决议两年以上无法达成决议;应该结合案情具体加以分析,指导案例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吉林省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宏运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的处理就体现了这一点。同时,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作为司法解散制度的目的之一,可以将其作为司法解散判断标准之补充,确立起以公司职能机构运行困境的人合性障碍为主、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为辅的适用标准。
(二)寻求替代性救济机制
司法解散作为一种司法途径强制解散人合公司的手段,应该只有在公司陷入经营僵局,穷尽其他救济方式无从解决之时才能予以利用。英美法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将强制解散定位于对股东的最后救济,这和我国的”穷尽其他救济方式”立法机理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避免国家强制力对封闭公司自治的侵害。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是为了解决公司的人合障碍、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探索其他救济渠道时就应当避免通过法律手段扼杀公司的发展,实际适用强制解散时应当相当审慎。结合林方清一案,该案件中暴露的问题就是法院的司法解散判决最终可能无法有效实施,二股东达成和解究其原因应当是起诉的目的,也并非强硬地要求公司解散,只是没有其他途径重新获得股东权和监事职权的行使,因此应当拓宽其他救济渠道,审慎地适用强制解散规定。
目前我国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只规定了法院调解这一救济渠道,这是不够的。对于长期处于矛盾中的公司股东、董事或者监事来说,调解解决纠纷操作性相对较差。在聚法案例网上,2012—2021年我国公司解散案件调解结案率仅2.52%[8],而调解不成直接判决强制解散又过于强硬,二者中间的救济渠道应当得到拓宽。笔者以为,股权回购以及股权让与作为已经出现的公司纠纷的救济渠道,可以应用到公司人合性障碍的领域,这也是美国法的做法。由不同意公司解散的股东收购股票或股东达成一致的股权回购公司减资的方式符合公司人合及自治性,即当公司或其他股东愿意收购股权时,而且有确定股权价格的公平合理的方法时,应当向当事人释明此时公司的僵局并非只有通过解散公司才能解决[9],这样做有利于公司彻底解决其合性障碍问题,同时公司继续存续也能够保障债权人等利益第三方的权益。
五、结束语
我国的司法解散制度法条规定的使用标准虽然存在模糊性,给司法实践带来困难,但是该制度使用至今已有16年之久,形成了大量典型的司法案例。本文根据对典型司法案例及域外制度的分析,提出司法解散制度的两点改良路径。其一是确立起以公司职能机构运行困境的人合性障碍为主、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为辅的适用标准;其二是建立包括股权回购及股权让与在内的司法解散替代救济机制,以提高司法解散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的统一性和有效性。相信随着司法实践以及理论研究的深入,司法解散制度的适用进路将得到进一步明确。
参考文献:
[1] 蔣大兴.“好公司”为什么要判决解散: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号评析[J].北大法律评论,2014(1):1-51.
[2] 李建伟.司法解散公司事由的实证研究[J].法学研究,2017(4):117-137.
[3] 梁清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中“经营管理困难”认定标准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判例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9(12):112-119.
[4] 韩仁哲.公司司法解散的替代救济机制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8.
[5] 梁上上.论公司正义[J].现代法学,2017(1):56-75.
[6] 沈四宝.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12.
[7] 托马斯·莱赛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第3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665-666.
[8] 李凌霜.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功能主义比较与立法完善[J].金融法苑,2021(2):120-132.
[9] 戴庆康.论作为公司强制解散替代路径的股权强制收购:从林某诉凯莱公司、戴某等公司解散纠纷案谈起[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95-100,155-156.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Judicial Dissolution System for Companies in China
SUN Huim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6, China)
Abstract: The judicial dissolution system of companies in our country originates from Article 182 of the Company Law and Article 1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I, which defines the cause of judicial dissolution as “serious difficulties in compan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he ambiguity of legal provisions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f judicial appl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use of compulsory force by state organs to dissolve a joint venture company will inevitably break the autonomy of the company and go against the will of some shareholders. Its legitimacy lies in 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majority decision of the closed companys capital and the equity structure under the premise of joint venture failure, and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shareholde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judicial cases and extraterritorial systems, two improvement paths for the judicial dissolution system are proposed. One is to establish applicable standards that prioritize the obstacles of human cooperation in the operation of company functional institutions, supplemented by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shareholders; the second is to establish a judicial dissolution alternative relief mechanism, including equity repurchase and equity transfer, to improve the un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judicial dissolution system in practice.
Key words: Judicial dissolution; Human compatibility; Share repurchase
[责任编辑 兴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