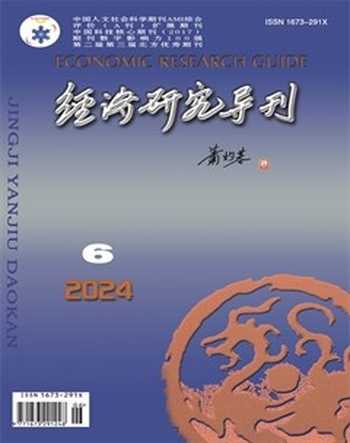涉外法律谈判问题研究
董方新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运用国际法律规则和国际惯例就涉外事务进行协商谈判成为我国解决国际矛盾纠纷、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涉外法律谈判在我国的建设发展存在明显不足。因此,在对涉外法律谈判的内涵、特征要求和主要应用领域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分析归纳出当前我国涉外法律谈判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度顶层设计缺失、人才培养机制不成熟、人才资源未有效整合和人才引进力度不足等方面的问题,进而提出完善制度顶层设计、创新人才协同培养、调整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建设涉外法律谈判智库、加大人才引进支持力度和多渠道加大资金投入等建议,为新时代涉外法律谈判事业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涉外法律谈判;国际法律规则;国际惯例
中图分类号:DF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4)06-0149-04
一、涉外法律谈判概述
(一)涉外法律谈判的内涵
涉外法律谈判是指专门从事涉外法律谈判的人员针对涉外法律事务,在充分运用法律思维、专业知识和职业技术的基础上,与相关当事人进行协商交流,最终形成一致的意见共识,并订立书面约定,承诺自愿接受该约定内容的约束的专业活动。其中,广义的涉外法律谈判是指,国家间、个人间、其他组织间,以及三者之间对于涉外利益冲突开展协商交流,调整相互利益关系,实现各方利益共赢[1]。狭义的涉外法律谈判则是指,国家间在相互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运用谈判协商的和平方式达成利益协调约定,从而使各方的共同利益得到实现。
(二)涉外法律谈判的特征及要求
首先,涉外法律谈判与国内法律谈判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其往往带有较强的政策性,要求谈判者对谈判各方背后所处的政治关系、外交关系等有熟悉的掌握。其次,涉外法律谈判的法律依据往往涉及大量的国际法律规则和国际惯例等,要求谈判者要熟练掌握并运用国际法律规则和国际惯例。再次,涉外法律谈判往往在内容上复杂广泛,要求谈判者自身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素养、较强的谈判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最后,涉外法律谈判可能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要求谈判者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各地区不同的文化,了解谈判各方的价值观、思维模式、沟通方式、决策结构等方面的情况。
(三)涉外法律谈判的主要应用领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的不断开展,我国国际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国际经济话语权在不断提升,面临的国际经济纠纷也在不断增长。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各方利益冲突,维护我国国际经济权益,促进各方共同发展,成为我国对外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是涉外法律谈判的重要应用领域。
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在对外交往中所涉及的领域在不断扩展,涉外法律谈判的应用领域也随之丰富,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国家主权与安全领域。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面临诸多外来的风险与挑战,这就需要我们更好运用国际法律规则,通过协商谈判参与到国际社会治理中,以维护好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和平和共同发展。第二,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我国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美丽地球和绿色家园的主要倡导者、参与者和推动者,是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通过运用国际法律规则和各方签订的公约协定,积极参与到全球生态治理协商谈判中,有利于保护我国生态发展权益,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实现永续发展。第三,民生保障领域。诸如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粮食以及防灾减灾等民生领域问题是目前困扰各国发展的共同问题。通过涉外法律谈判已达成在民生保障领域的国际合作共识,特别是敦促发达国家履行自身责任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社会民生保障问题,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更好发展。
二、当前涉外法律谈判面临的问题
(一)制度顶层设计缺失
就目前而言,我国涉外法律谈判在机构设置上是建立在行政职能基础之上的,即涉外法律谈判的主要职能职责是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下属各部委及其直属机构来分别承担的,具有一定的分散性,没有形成系统协调的体制机制。而通过分析近年来涉外法律谈判案例可知,当前涉外法律谈判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具有复杂性、广泛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往往是跨领域的。基于此,我国在推进涉外法律谈判事业建设发展过程中需要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增强各职能部门的协调性,保证谈判者拥有跨领域、跨部门、跨专业的资源与信息调控整合能力,避免在具体涉外法律谈判过程中出现“政出多门”的尴尬情况,确保不因部门利益冲突导致在涉外法律談判中国家利益遭受损失。
(二)人才培养机制不成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加强学科建设,办好法学教育,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机制,早日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我国高度重视对于具备专业谈判能力的高层次涉外法律谈判人才的培养。但目前来看,我国涉外法律谈判人才的培养机制尚不成熟,很多关键问题尚未明确,对人才培养造成一定阻碍。
具体而言,当前我国在参与国际社会治理过程中亟需大量涉外法律谈判人才,但目前我国教育体制机制难以弥补相关人才的供需缺口。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同涉外法律谈判相关的学科缺失。法律谈判作为法学专业的一种实用必备技能,在学科体系中没有取得与之相应的二级学科地位,致使涉外法律谈判学位出现空白,导致难以培养和输出专业化高层次的涉外法律谈判人才。再者,教育部学科评估体制机制是提升学科人才培养能力的重要形式,但由于涉外法律谈判未被列入法学二级学科之中,所以就不具备学科评估的引导和压力,致使在实践中法学培养院所未能建立与涉外法律谈判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制度体系,也未能建立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的课程标准,大大影响了高等教育培养涉外法律谈判人才的现实能力。此外,在小部分设置涉外法律谈判专业课程的学校中存在着授课内容更新不及时、相关理论和案例与现实涉外法律谈判难以有效衔接,以及未能配备专业教师,主要采用其他学科教师兼任涉外法律谈判课程或聘请校外教师进行教学的方式,对人才培养的质量造成较大影响。
涉外法律谈判人才培养不仅在高校教育体制中存在不足,而且在继续教育体制中也未能做出有效的制度性安排。涉外法律谈判方面的继续教育是对相关人员知识、能力和思维进行更新拓展的有益补充,有助于涉外法律谈判人才质量的可持续提升,其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缺失也是阻碍涉外法律谈判人才培养的重要原因。此外,专业化的涉外法律谈判人才社会教育体制在我国也处于空白状态,未能建立专业权威、标准规范的相关培训中心、研究会和行业协会等,致使相关人员难以通过涉外法律谈判社会教育平台学习到最新理论和知识。
(三)人才资源未有效整合
涉外智库为我国有效参与国际社会治理提供了系统全面的理论支撑,特别是在政策制定、国际合作、涉外规则、国别问题研究等方面,涉外智库发挥着重要作用[2]。因此,涉外智库理应为推动涉外法律谈判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但在实践中,两者之间在信息资源保障和决策交流沟通等方面存在短板。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专业涉外法律谈判人才在质和量上仍存在短板,导致涉外智库与涉外法律谈判之间难以形成高质量的产出成果,并且在涉外法律谈判中未能完全发挥好涉外智库现有成果的指导作用。此外,涉外智库在涉外法律谈判领域缺少相关研究人员,使得所产出的成果难以确保质量水平和权威可行。另一方面,是否形成有效的决策对接机制是涉外智库与涉外法律谈判能否发挥合力作用的重要一环,否则涉外智库的产出成果就难以及时传输给涉外法律谈判领域,并难以以其为基础形成相应的谈判策略,或者反过来,涉外法律谈判中的第一手情况也难以传输给涉外智库,并形成具有时效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
在涉外法律谈判实务部门和科研院所的协作方面,我国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的人才交流机制。究其原因,一是部门之间考核评价制度存在较大差别,二是部门之间在人员晋升发展方面也存在不同。由此造成两者在人才交流过程中存在现实阻碍,进而导致两者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合作,一方面科研院所在涉外法律谈判的研究过程中,因缺乏实践数据而导致给出的科研结论和科研成果过于理论化,甚至存在空想性,无法在涉外法律谈判实务中发挥指导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撑,涉外法律谈判中所制定的谈判策略往往难以经得起理论推敲,可能出现偏差错误。
(四)人才引进力度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涉外法治人才引进、选拔、使用、管理机制,做好高端法治人才培养储备。但是,当前仅有少数经选派或申请而进入国际组织学习工作,且具有完备涉外法律谈判技能和经验的人才回国在政府部门、企业和高校等单位从事相关工作。究其原因,一是国内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对回流人才是否能够适应国内政府部门运作机制以及行业工作机制、是否能够发挥好维护国家利益和行业利益认识不足,因此对相关人才重视不够,也缺少追踪机制;二是相关人才对回国发展是否能够满足自身薪资待遇要求、是否能够满足自身发展规划存在疑虑,因此缺少回国就业的热情和吸引力。基于此,对涉外法律谈判人才的引进力度不足是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三、推动涉外法律谈判发展的建议
(一)完善制度顶层设计
推动涉外法律谈判制度建设,建立高素质专业化的涉外法律谈判人才队伍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我国要着眼于涉外法律谈判制度顶层设计,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协调好履行涉外法律谈判职责的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形成促进涉外法律谈判发展的合力,从而改变当前各部门之间权力交叉、责任不明、职能分散的现状。具体而言,涉外法律谈判制度建设要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涉外法律谈判工作的领导体制、协调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机制,使得各方在专业对接、信息共享、工作协调等方面更加畅通高效,确保涉外法律谈判工作在我国全面发展中的地位得到实质提升。
(二)创新人才协同培养
正如前文分析,作为法学专业实用必备技能的法律谈判,未在法学学科体系中取得二级学科地位,导致在法学教育过程中缺乏对涉外法律谈判技能的专业化、系统化、标准化教育,进而影响人才培养产出。因此,应力争尽快将法律谈判纳入诉讼法学学科,与之相应,在高校法律人才培养方案中也要尽量体现法律谈判学科的评价内容,同时采用多种激励形式扩大法律谈判方面师资队伍和科研教学热情。再者,在继续教育领域应着眼于发挥继续教育对涉外法律谈判人才的知识、能力和思维的更新和扩展功能,成立专门项目,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形成完备的涉外法律谈判继续教育体系。最后,采取“市场+政策”的模式,提升社会教育在涉外法律谈判领域的关注度、参与度和贡献度;成立专业化培训中心、研究会、行业协会,为涉外法律谈判人才培养提供便捷且专业的社会平台。
(三)调整人才培养方案设计
涉外法律谈判人才的培养需要有一套统一化、标准化、科学化的培养方案作为支撑和引领。因此,要科学调整和优化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中有关涉外法律谈判课程、教材、教师、教学以及学生学业评价等方面的内容。首先,要立足于涉外法律谈判的实际需要,在开设好涉外法律谈判专业课程的同时,开发诸如辩论技能培养、模拟谈判等专业选修课程,形成综合配套的涉外法律谈判课程体系。其次,在教材内容编写过程中应注重整理编写一批具有典型代表性和教学价值的实际案例,使教学与实务相衔接,具有可操作性。再次,要打通高校与实务部门之间的人才交流通道,创新人才交流机制,为涉外法律谈判教育提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师资力量,同时要立足于国际视野,积极引进涉外法律谈判方面的国际专家学者,增强人才培养的国际性。最后,在涉外法律谈判教育教学中要重视对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通过实务课程和活动竞赛引导学生参与到涉外法律谈判的工作实践之中,切实提升学生对未来工作的适应性[3]。
(四)建设涉外法律谈判智库
通過重塑涉外法律谈判人才培养体制机制,释放人才培养潜力,有效解决我国目前涉外法律谈判供需缺口问题。在此基础上,要着眼于与涉外法律谈判相匹配的涉外智库建设,对涉外智库相关制度和考核评价体系进行完善,努力打造一支规模可观、专业素质过硬、具有丰富涉外经验以及拥有国际视野的涉外智库高端人才队伍,提升涉外智库的研究成果产出效率,从而在处理涉外法律谈判事务中能够保证涉外智库与涉外法律谈判相互配合,形成良好的交流共享机制,以满足国家对外开放的需求。
在涉外智库和涉外法律谈判相互协调配合的过程中要着重解决人才交流问题。具体而言,在涉外法律谈判领域,国家应当出台相关专项人力资源政策。一方面,规定正在从事涉外法律谈判工作的实务人员可以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以特定的形式前往高校、科研院所等从事相关科研工作,并且其交流经历及期间取得的成果可以作为本人职务晋升、待遇提升的依据。另一方面,在涉外法律谈判方面取得相应研究成果的专家教授也可以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方式进入到涉外法律谈判实务部门,实现科研成果的现实转化。
(五)加大人才引进支持力度
涉外法律谈判人才引进工作是一个复杂性工程。首先,要科学认识人才引进工作对我国涉外法律谈判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其次,要建立人才追踪机制,中央和各级人才管理部门要建立人才询查、鉴别筛选和信息归档储备工作机制,进而根据人才的专业方向、自身特点、能力素质等要素,积极出台相关政策,破除壁垒,将其引进到政府、企事业单位等从事相关工作,加强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储备[4]。再次,要建立人才回国培养机制,针对那些具有一定能力、水平和具备开阔国际视野,但是对国内核心利益诉求和工作机制等方面认识欠缺的潜在人才,也要积极争取其回国进行培养,在实际学习和工作中逐步立足国内具体情况积累相关能力和经验,加强涉外法治后备人才储备。最后,要立足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对标国际人才薪酬标准,适当调整涉外法律谈判人才引进的薪资待遇,并且对相关人才回国后的发展前景作出合理规划,提升对相关人才回国就业的吸引力。
(六)多渠道加大资金投入
无论是制度具体落实、智库建设,还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都需要有效的资金保障。而资金来源并不能仅仅依赖于某一方面,而是需要建立多渠道资金投入机制。具体而言,一是要发挥财政在涉外法律谈判事业发展中的主要作用,通过增加相应财政预算,出台相关财政政策,并且加强资金使用过程中的监管力度,集中力量打开发展局面。二是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涉外法律谈判事业建设,特别是动员那些产业规模大、国际业务多且有涉外法律谈判需求的公司投入资金,助力涉外法律谈判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1] 万晓丹.法律谈判的艺术与未来律师的定位[J].法制与社会,2016(21):252-254.
[2] 邓海峰.我国涉外法律谈判的现状与提升建议[J].团结,2022(1):21-25.
[3] 万勇.建设涉外法律谈判人才队伍,应对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与竞争[J].团结,2022(1):33-35.
[4] 侯佳儒.建设“谈判学”交叉学科,培养高端涉外法律人才[J].团结,2022(1):17-20,25.
Research on the Issues of Foreign Legal Negotiations
DONG Fangxin
(Law School,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0, China)
Abstract: President Xi Jinping stressed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tter coordinat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better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we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doing a good job in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build a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system and capacity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openness, and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the stabilit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rules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for negotiating foreign-related affair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China to resolve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d disputes and safeguard national interests. However, there are obvious shortcoming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oreign-related legal negotiations in China at present. Therefore,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 requirements, and main application areas of foreign-related legal negoti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rocess of foreign-related legal negotiations in China, such as the lack of top-level institutional design, immature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s, in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talent resources, and insufficient talent introduction efforts.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top-level institutional design, innovate collabor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o on suggestions include adjusting the design of talent training programs, building think tanks for foreign-related legal negotiations, increasing support for talent introduction, and increasing funding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related legal negotiation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Foreign related legal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legal rules;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責任编辑 兴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