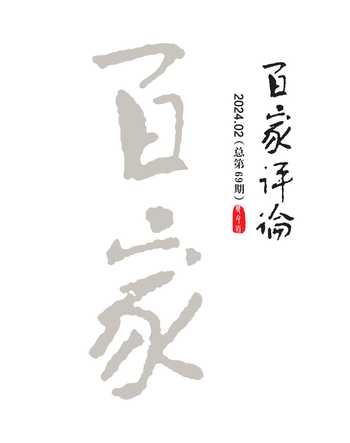自然的本体性与世界的部分复魅
马新亚
内容提要:沈念在《大湖消息》中以丰富的生命细节逼真地再现了洞庭湖区飞鸟、江豚、麋鹿的形貌、习性、生命样态以及湖区的地形、气候、历史、文化,又以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克服了“地方性经验”可能存在的理性缺失,使整部作品既具有生命的质感又兼具思想的穿透力,从而为当下生态散文的写作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本真性 复魅 自然神性
在《大湖消息》的开篇,沈念穿过历史的雾霭,追溯了洞庭湖区在《水经·湘水注》《洞庭湖志》《舆图》等古代典籍中的记载,并由该区历史上所遭受的“洪水之灾”与当地百姓所开展的“围湖造田”运动之间的拉锯战,展开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拷问,而这也正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所有对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态危机和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的诗意的栖居有强烈敏感性的知识分子所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命题。然而人与自然、生态和民生、生态和政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也不能由黑格尔的“美在形式”的理念对这些问题进行化约,特别是对文学创作而言,过多的逻辑预设与意图先行,很有可能陷入概念化、图表化、程式化的窠臼,从而使文学沦为社会学和形式美学的附庸,好在沈念对此有清晰的边界意识,他深知文学的使命不在于用清晰的逻辑去回答一个玄妙的哲思,而在于用生命的体温和诗性的思维去打开“人”的存在空间,用丰富的细节和深刻的哲学思辨对撞,用富有前瞻性的理念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对接,从而带出一个交织着思想穿透力与肉体疼痛感的悬而未决的“天问”,这也许就是沈念从《天总会亮》《长鼓王》以来一直追求一种“向内型”写作的深刻动因。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沈念在《大湖消息》中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理解为一种解不开的“结”a——一种以中国传统自然观打底、用儒家重返“身体悟”的方式亲证实践,并以原始宿命论方式来表述的“本质的直观”。
一、以生命细节为自然赋形
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的主体性地位的高扬,主客之间的分离以及它们之间的主从关系变得日益明显,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是草木山川、群鸟百兽、日月星辰越来越得成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投射对象,虽然在这中间,康德为强调自然美的独立审美价值,在《判断力批判》特意提出“审美无功利”的理念,但在审美实践过程中,人类还是难以排除前在的认知结构和审美趣味,以带有“滤镜”的“观物之眼”来筛选、过滤、加工自然万物,使之成为脱离了本真样态的“人化的自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罗尔斯顿在著名的《哲学走向荒野》一书中重申了自然本体的哲学观,强调了自然的终极价值,他说:“人类傲慢地认为‘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可这些自然事物是在人类之前就已存在了。这个可贵的世界,这个人类能够评价的世界,不是没有价值的;正相反,是它产生了价值——在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它更接近终极存在。”b罗尔斯顿的表述看似简单,但内涵却非常丰富,它至少传达了这样两个信息:第一,他强调的“价值”不是自然万物给人的实用价值,也不是自然万物对经由感官传输的与既定美学原则的契合,而是自然万物本真性存在。第二,他指陈的“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不仅意在让人们在宏观层面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更强调人们要在微观层面克服既定概念框架的遮蔽,去还原一个清晰逼真、元气淋漓的自然本体,这其实就牵扯到了如何用语言文字为自然万物赋形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中国传统美学所讲求的“涤除玄览”“澄怀味像”就对如何调适主体状态、如何观物应物、如何去除遮蔽等问题做出了较好的回答,而与此同理,《大湖消息》之所以能够将洞庭湖区的飞鸟、江豚、麋鹿的形貌、习性、生命样态以及湖区的地形、地貌、历史、人文、风俗进行一个类似于摄影家、地质学家、考古工作者似的逼真性还原,就是因为作家不是从外部概念出发,只将自然万物作为某种环保理想和精英主义审美趣味的对应物,而是从内部感受出发,用生命和体温去贴近自然万物,使其本真性得以跃现。在发表于2022年11月9日的《文艺报》中,他这样说道:“我在洞庭湖的水边生活了很多年。水,给了这片土地灵性、厚重、声名,也给了人刁难、悲痛、漂泊,更是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和源泉……长久以来,我睁眼闭眼就能看到水的波澜四起,听到水的涛声起伏,水的呼吸所发出的声音,是液态的、颤栗的、尖锐的,也是庞大的、粗粝的、莽撞的。水能把一切声音吸入胸腔,也能把声音挡在它镜子般的身体之外。我原来以为岸是水的疆界,但在行走中我懂得了水又是没有边界的,飞鸟、游鱼、奔豖、茂盛的植物、穿越湖区的人,都会把水带走,带到一个我未曾想到达的地方。”c问题的关键之处就在这里,虽然从2015年到2020年间,“青山碧水绿湖南”创作活动的主题规约和魏晋地记及清代地方志对洞庭湖的记载都在外部层面支撑着写作的展开,但如果没有生于斯、長于斯的原乡记忆打底,没有“在地行走”的写作方式作为辅助,恐怕再多的材料也只能作为静止的风景停留在文本的表层,而未能传达出生命的本真。
沈念在《大湖消息》中尽量排除知性逻辑对客观事物本真性的遮蔽,让洞庭湖的草木山石、飞鸟游鱼的形状、颜色、声音自然兴发与跃现。例如,书写湖区的天光水色时,他力避风景书写所惯用的隐喻、象征手法——在“物象”与“意义”之间设置一个人为的间距,而是以自然之眼观物,以最为原始和朴素的方式再现了自然的色泽、迹线、纹理,以“第一眼”的新鲜感受捕捉到既定宇宙秩序之外的“自然之道”:“湖洲的外滩浮动着一片沉甸甸的银灰,偶尔太阳挣出云层,银灰里又掺进些金黄、古铜和锈红。天地间的灰白变得更稠浓,冬天的湖面瘦得更狭窄、遥远、一副冷恹恹的神情。有的路面落满了枯叶,车轮碾过,发出碎裂的声音。声音像块有棱角的石头,砸得水花四溅。”其中,“银灰”“金黄”“古铜”“锈红”等彩色层次体现出了描述与描述对象的精确对应,展现了主体的精细的观察能力,而窄长的湖面、落满枯叶的路面、车轮碾过的碎裂之声又与阴沉清冷的整体环境相应和,体现出了主体较为敏锐的感受能力,然而无论是观察还是感受,都来自物象的具体存在以及物象的整体氛围在主体心灵中的投射,而不是来自有关物象的抽象概念或言物象对应的某种被区隔、分层的美学原则和审美趣味。在书写湖区上空飞翔的鸟类时,除了参阅《吕氏春秋》《中国鸟类图鉴》《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中的相关记载和图文资料、《鸟》《观鸟大年》等电影中的人与鸟的故事、聆听当地环保部门负责人的所见所闻之外,还综合了非常多的实地考察经验和原初记忆,对飞鸟的种类、分布、形貌习性、飞行技能,以及其在不同季节、天气时的不同状态都有着非常精准的观察与呈现。
二、以理性视野观照大湖生灵的美学价值
刘勰在《文心雕龙》之《物色》中有“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d一句,意在强调贴近自然、融入万汇、为山水赋形对写作的重要意义,而以《水经注》为代表的魏晋地记及之后由柳宗元所开启的“再现式”山水散文又在写作实践上回应了刘勰的观点,将“形似”这个美学元素深深地嵌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然而中国传统美学讲求的终归是一种整体性的艺术风格和精神气度,因此中国传统美学里的“形似”并不单独存在,它一直都与“神似”“自然之道”处于一个对位性的结构性空间之中,但这种结构性对位,又不同于西方美學家瑞恰慈所讲的“喻依”与“喻旨”之间的关系,不需要经过概念、推理、判断来打通,而是需要用“心-物”之间的感应(也即“嗅觉化的味觉”)和形象化的思维(象)来捕捉,并最终将山水的美态、宇宙的圣姿、人伦的理想统摄为一个和谐混融、气韵贯通的生命有机体,对《大湖消息》来说,虽然不需要在创作理念方面秉承这种深奥的、充满玄学气质的美学观,但也有需要面对的相似的写作难题,那就是如何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如何将分散在行程见闻、历史追忆、现实反思之间的零星的、即时的、碎片化的形貌声色、生命印痕和来自神经末梢的些微意绪统一起来,用一种整体性的视野来超越“地方性经验”可能存在的理性缺失,使整部作品既具有生命的质感又兼具思想的穿透力。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最终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将“记忆中最深刻的经验和细节”融入“对世界和自然的看法”之中,“在‘所见与‘所信之间,让个人的写作被生活与美学‘双重验证。”e也就是说,这些存留在作者记忆深处的生命细节并不是一种无意识的存在,它们虽然在文本中不断地被行程的实录、故事的讲述分散为一个又一个的碎片,但同时又被一种内在的统摄性力量牢牢地串连在一起,这个统摄性的力量就是被作者内化了的生态美学观念。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生态美学观念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态环保主义,也不囿于传统美学对形式美的定论,他的生态美学观念是一种融合了西方现代生态理论和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将自然的本体性地位和人的诗意的栖居放置显要位置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生态美学观念。
这种美学观念首先体现在作者对大湖生灵的美学价值的理性认识上。概括来讲,作者将大湖生灵的美学价值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与人的超越性存在相契合的“灵性之美”;二是与人的本然性存在相契合的“本真之美”。例如,相对于别的生物,鸟类显得更有灵性,它们的身体构造符合美的规律,它们的生命形态很多时候被视为人类自由和梦想的一种对应物,在对它们的凝视之中,人类自身的缺陷得到了想象性的弥补。沈念在书写天鹅、豆雁、白鹤等鸟类时,一方面突出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形态、习性、飞姿,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它们所共有的生命的美感。如:“飞翔的天鹅让人怦然心动”“它的力量从收紧的翅膀里爆发出来,如同海面上迎浪而行的鱼鳍,激荡的浪花四溅,变成满天云霞,空中的白色精灵,被渲染成移动的金色斑点,散出模糊却透明的光,让人感受到一种沉静之美。”f再如,“它(豆雁)的尾羽宽阔而坚韧,张开时犹如团扇,这是飞行时的‘舵手,转向、减速和着陆,离不开它的掌控,而如桨似的鸟翼,展开时既有机翼般的飞行表面,又靠翅尖向下,向前扇击产生推力。在不同的空气条件下,鸟翼改变形状,翼和躯体的相对位置随之发生变化,那些高超的飞行技巧因此诞生。”g鸟类的飞行一方面符合人类对和谐、沉静、优美等形式美的追求,另一方面也符合人类对自我掌控、自我超越的想象,除此之外,它们的某些习性也让人联想到人类社会才有的一些伦理观念。例如,“迁徙的候鸟都是富有冒险精神的勇士”h“候鸟是最具责任感的父母,它们要保证繁殖育雏是在最有利的季节环境里发生”“恋家的留鸟不懂飞往他乡的乐趣,是故乡的忠实守候者”i。在同伴遇难时,它们会盘旋上空,发出物伤其类之鸣叫,让听者为之动容;在受到人类的善意对待时,它们会对人类报之以相同的善意j,用鸟类特有的方式演绎着儒、释两家所尊崇的“回向之爱”;而当受到人类侵害的时候,它们总怀有宽宥之心,压制愤怒、恐惧,躲到云朵、树林、山川、河流之上,把身体与灵魂交付给自然,不带任何仇恨地飞向迁徙之路。这种宽广空灵的生命形式其实最接近自然神性,而与此相对照,以牙还牙、血债血偿的暴力逻辑则又在宣告着人间伦理的狭隘浅陋,因此在很多时候,作者笔下的飞鸟、游鱼、兽物、草木既是人类暴行的受害者,也是宇宙自然的通灵者,它们以无词的言语,嘲弄着人类的虚妄。除了凸显大湖生灵与人的超越性存在相契合的“灵性之美”之外,作者也强调了万物与人的本然性存在相契合的“本真之美”,也就是那种不需要外在附加意义的,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与繁衍。例如在书写鸟类与自然神性的相通之处时,作者并不可以避讳它的生存本能:“夜间迁徙,这是它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躲避猛禽的袭击,把受敌害威胁的风险降至最低,夜间候鸟有自己辨析方向的本领。即使没有月亮,云的反射,星的闪烁、水面的反光,也能让候鸟辨识地面轮廓,不致迷失”k“黑水鸭喜欢藏身于枯败荷塘的水面上,是潜水的高手,一头扎进水里,游出十几米远。它们不擅长飞行,遇袭或感应到危险,就不管不顾地往草丛或芦苇丛中躲藏,倒是能躲得毫不动弹。”l再如写江豚:“接近分娩期的雌豚的呼吸频率会短而急促,食欲减退,常平静地停在水面,身体左右轻微晃动”“母豚身体侧向一边,露出另一边的鳍肢,小江豚则乖顺地贴向腹部,这是母豚的哺乳。”m显而易见,这里不是强调自然万物的灵性,而是强调它们的自然本性,因为从生物学的客观规律来讲,向群友善并不能促使生物个体以及族群的存续与发展,而只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才是王者之道,所以生命有时需要用形而上的理念来振拔和提升,有时更需要用形而下的本能来维持与稳定,特别是在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当下,“生存本身有时就是生命的最高法则”n。那么,抛除这种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进化论观点,我们怎样从美学的层面来认识生物的灵性之美与本真之美呢?两者究竟孰轻孰重呢?如果从源头上来讲,用自然的属性特征来比附人的道德品质,其实最早来源于儒家的“比德说”,这种说法意在强调自然的人情味与社会色彩。而不避万物的自然本性、尊重万物的生存和发展规律则是道家生态美学思想的集中表现,这种观点意在强调自然的本位性与个体价值的合法性,介于这种哲学思想中所暗含的本真性理想和现代社会需求的契合之处,西方现代生态美学大胆地汲取了道家生态思想的精髓并将之发扬光大。由此可见,自然的灵性之美与本真之美在理论上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那么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说第一种美的形成机制在于主体因在客体身上找到了和谐、优美、崇高等美学形式和属人品质而引起共鸣和喜悦,那么看到生物的自然属性也能够让人共鸣和喜悦吗?车尔尼雪夫斯基用一句话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o。对于动物的审美,他认为凡是显示了人的生命力的动物就是美的,刚健矫捷、优雅轻灵是一种美,健康活泼、善于斗争也是一种美,因为这些属性都让人联想到人类中充满生机活力的那部分人,而不是羸弱畸形的那部分人。由此可见,无论是精神属性还是生物属性,只要有主体对在自然的属性特征与人的本质力量之间进行了“移情想象”,“美”就产生了,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于客体是否符合形式的规律,而是在于主体是否拥有物我同一的观物之眼。
三、以整体性视野打通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为草木山石、鸟兽游鱼描形摹态之后,沈念在《大湖消息》的后半部分书写了大湖周边的人,他们中有从祖辈就迁过来的(鹿后义),有新迁过来的(昆山爹、谭亩地等、许嫂),也有仅在这里作短暂停留的(砍芦苇的少年)。无论是充满传奇色彩的猎鸟神枪手,还是风餐露宿的“水上漂”,无论是在水边打发每个日子的迟暮渔妇,还是在芦苇深处对世界充满幻想少年,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机器化时代的现代人都有很大的差距,当然作者也没有将时代背景从他们身上完全剥离开来,例如造纸厂的废水污染问题、黑杨引起的生态问题、城乡经济不平衡等问题,但总体来讲,相对于都市人,他們的生活环境与自然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的命运与自然的关系也更为直接。因为触目便是青山绿水,飞鸟游鱼,他们对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厚:十五岁的湘西少年随父亲来洞庭湖,被芦苇的风姿深深吸引,不由想起《诗经》中的“蒹葭”之章;许嫂大字不认得几个,但看到白鹤的飞行姿态,她会由衷赞美,看到黑水鸭为躲过孩子而进行的伪装,她会暗自发笑,她的丈夫许飞龙以打鱼为生,但他打鱼只用网眼大的渔网,不肯将鱼一网打尽,他说,“有了鱼,水才有了颜色有了动静,也有了味道和形状,打鱼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给鱼活路”p;老实内向的小崔因不满污水处理车间任意排放污水而与车间主任理论,在沟通无果之后,一向懦弱的他竟然愤怒地用大石头堵住水管,让废水淹没车间,生产无法进行,自己也因此丢了工作。他在这件事情中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勇气,并非来自外部信念的支撑,而是常年与草木河流的共居生活,让他对自然保留着一种天然的善意,而将这份善意推而广之,则是对邻人的侠义之心——他曾用孔武有力的大手,制止了一个男性工友以饭菜分量不足为由而肆意辱骂食堂打菜姑娘的行为。他的母亲也曾用同样有力的大手,将同村两个投湖的健壮妇女救出;类似的例子还有谭亩田跳到邻船去救落水的孩子而被螺旋桨削去三根手指;昆山爹在狂风猛浪中救出邻近游船上十七个落水者,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不幸痛失爱子等。多数在风浪里讨生活的大湖儿女都会对附近的人有一种不可明言的惺惺相惜,这份感情虽没有“同气连枝”的醇厚,也没有“与子同袍”的激昂,但算得上是“同一片水养同一条船吃饭的兄弟之情”q。然而,书写江湖儿女的人性之美,书写他们心灵的宽广与深邃,书写他们所代表的生命形式与我们所失落的文明的关系,进而为人的诗意的栖居提供一个形而上的参照,并不是作者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想通过对这些大湖儿女的平凡而又离奇的个体命运的展现,深入地探讨人与命运的关系,从而间接地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从大的范围来讲,命运就是自然的一种延伸,它是以“必然”和“偶然”的形式显现于人类身上的、神秘强大而又无所不在的宇宙意志,通过对这种非理性力量的一种突出强调,人类理性使用限度的问题就得到了重申,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品的后半部分的人物书写与前半部分的自然书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的闭环,分别从自然美的本体性与回归自然神性的角度展开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
那么,究竟什么是命运?人又该怎样看待自己的命运?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到屈原的《天问》,从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到曹禺的《雷雨》,人们都试图为其提供一份精神供词,然而谁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还记得沈从文在《水云》中将这种神秘莫测的力量称作“偶然”,他习惯于把观念层面的这个“偶然”转化为本文中的“情节的突转”,以“白塔的倒坍”(《边城》)“‘城中人的夭亡”(《三三》)“阿黑的病故”(《阿黑小史》)来映衬楚人血脉带给他的命定的悲剧。如果说沈从文对“偶然”的呈现是一种文本策略的话,沈念对“偶然”的呈现则更多的是一种写实主义的必然要求,虽然《大湖消息》的后半部分借鉴中国传统志怪小说的笔法来增加作品的文学性,但其书写的人物、事件都是有现实可考的r。那些生活在大湖或者因各自因缘与大湖产生联结的人们,都是一些真真切切遭遇了不幸的人:砍芦苇的少年惦记青皮后生要带他去船上捕鱼的承诺,不顾半夜路黑只身来到芦苇丛探秘,结果却遇到暴雨又深陷沼泽,于是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灿烂的十五岁;谭亩田的独子为保护女同学而惹怒了几个社会混混儿,遭到他们的报复而殒命,尸体又被绑上石头沉入自家船下的深水之中,再到被人打捞上来时,已被水中的鱼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许飞龙出事时,湖上一片浊浪,睁眼不开,待到风平浪静,上百个船工和渔民上游下游分头打捞了五日,船骸找到不少,他的尸首始终不见”s;猎鸟神枪手鹿佬离奇地死在自己的鸟铳之下。他的儿子鹿后义年少好胜,枪法屡屡不输其父,但他晚年的时光总被噩梦缠绕,并最终在一个孤独的夜晚走向了一劳永逸的死亡。这些大湖儿女的故事,有的琐碎平凡,有的充满传奇色彩,但似乎都难以逃脱自然之子的悲剧宿命。作者并没有将悲剧的原因归结为外部的苦难,也没有用传统伦理中的善恶因果论来就环保问题进行理论宣讲和道德规劝,而是从经验的内部对人与命运关系的问题发出了存在论意义上的讨论。就以对人物的命名来说,文中的六个故事虽然都有一个血肉丰满的主人公,但作者却一概以“他”和“她”称呼,其用意一方面在于凸显人处大江湖泽之间的微茫与渺小,另一方面也意在用这种淡化具体性的泛称来增强对普遍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聚焦。
众所周知,随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观念的提出,人类将自我主体性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种以实证为基础的个体哲学的昭示之下,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世界的袪魅”,也即“把魔力从世界中排除出去”t。美国当代哲学家大卫·雷·格里芬在《和平与后现代范式》一文中判断了马克思·韦伯的观点,提倡部分地“复魅”。他说,“马克思·韦伯曾经指出,这种‘世界的袪魅,是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自然被看作是僵死的东西,它是由无生气的物体构成,没有生命的神性在它里面,这种‘自然的死亡导致各种各样的灾难性的后果。”u因此,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世界的“复魅”,并将之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种重要理论范式。那么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如何“复魅”?是回到农耕时代的人神同在、万物有灵吗?显然不是。“复魅”的观点并不是主张世界的重新神秘化,而是试图以一种情感性的链条来打破以工具理性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区隔,从而在一个更大的意义空间上重建人与自然的整一性,具体到《大湖消息》而言,笔者认为“复魅”就是对自身命运的顺应和对自然神性的敬畏。洞庭湖烟波浩渺,水雾蒸腾,整个湖面以及周边的村落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湿气,浸淫在斜风细雨中的人们,总是难逃一种命定的悲剧,因为自然在将阳光雨露、流云虹影派给这方水土的时候,顺便也送去了狂风暴雨、雾霭冷霜,所以人们在接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它无情的惩罚,这里让人不由得联想到《边城》中的这样的一段话:“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烈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v在沈从文看来,“人事机缘上的那个偶然”有时会决定命运的走向,因此在不幸来临之时,人能做到的只有信天委命。同样道理,大湖儿女朴素善良,勇敢尚义,但命运之中总是有一些不凑巧,当然这里也包括一些社会历史原因,例如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等,但大部分境遇是不为人所控制的,如身陷沼泽、突遇大风、不慎落水等,这些生命之中的“偶然”以强大的势能、乖戾的形式嘲弄着人的所信所守,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接受命运也并不等同于消极无为,它在很多时候会增加生命的宽度和韧性。例如,一连串的打击虽然将昆山爹心中的云彩化为乌有,但始终没有夺去他活下去的勇气,湖水的涌动起伏,似乎能“将他满身的苦楚卸载、溶解”w,又能通向起死回生的至亲身边。而妻子的呼唤,孙子的等待又会为他的晚归之途带去一丝微茫的亮光;冬来春去的飞鸟、来来去去的陌生人给了谭亩田活下去的一点信心,使他对“活着”有了一层更深的认识,因此当遇到不幸的人找他寻找安慰的时候,他可以这样自我解嘲,“你看看我这身又老又硬的皮囊,都得感谢岁月的艰难”x。
沈从文曾说,理解“偶然”在生命中的种种势力之后,可以为人增加一点“忧患来临的容忍力,和饮浊含清的适应力”y,他将这种信天委命的达观成为“新道家思想”,其实如果追根溯源,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与乡土文明中的结构化、空间化时间观息息相关的,因为乡土文明中是没有绝对死亡时间的,潮起潮落、月盈月亏、花谢花开,昼夜交替、季节更换、生死轮回,万物都处在一个不生不灭、循环交替的空间之中,没有绝对的新生,也没有绝对的死亡,而“现代性的时间观念,人为地将时间‘时段化,进而‘财富化,将人的一生变成了一种线形的‘财富积累游戏,实际上是一个‘死亡游戏的悲剧。因为它在理性的角度强化了时间的不可再生性。”z大湖儿女虽然生活在当下,但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使他们在情感结构上还保留着乡土文明时代的印痕,每当劫难过后,他们会在冬去春来的飞鸟上、荣枯交替的草木上、缓缓爬行的蜗牛上、来往的陌生人上,重新找到生命的一点信心,这信心的背后,其实就是对空间性、结构性时间观的一种确认,同时也是对被现代理性所规约的成败观念的一种反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世界的部分“复魅”,不是主张要重回蒙昧时代,也不知要取消人的自主自为,而是主张人们要在单一现代性之外,在工具理性所联结的功利性链条之外,再加上一点对自然神性和人间伦理之间的移情想象,这样对处在具体历史情境的人来说,可以增加一点“饮浊含清的适应力”,而对脱离了历史情境的形而上的“人”来说,则可以在一种混沌美学之中部分地重建与自然的整体性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与前面对大湖生灵的书写方式一样,作者不是由外部理念出发,将细节、事件作为理念的注脚,而是以在地行走的方式,深入每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体会他们的琐碎与平庸,善良与宽广,有时为了能够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作者甚至要避免“敬畏”“悲悯”“体恤”所包含精英主义姿态以及知性逻辑的干扰,以澄明的心境和对话的姿态贴近生活的本真,用实实在在的观察和感受来验证理念的真伪。
注释:
a沈念:《大湖消息》,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原文为:“自然与人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物欲‘满血的年代,没谁能一下把紧紧缠绕的‘结解开。”
b[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刘耳等译:《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ce沈念:《将属于江河、湖泊的时光温柔挽留》,《文艺报》2022年11月9日。
d周勋初:《文心雕龙解析》,江苏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fghiklmnpqswx沈念:《大湖消息》,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2页,第33页,第11页,第12页,第20页,第165页,第119页,第86页,第172页,第221页,第180页,第210页,第230页,第260页。
j《大湖消息》中记载了这样一桩奇事: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春天,神枪手“老鹿”从野外归家,遇到一只受伤的白鹤,白鹤的痛苦哀鸣引发了他的恻隐之心,他抱着白鹤回家,取出了嵌入白鹤体内的铁弹珠,白鹤最终被治愈放飞。一年之后,白鹤归来看他。第三年,白鹤携伴侣再次回来,看到他的孙女误入湖塘之后,飞到他家,咬着他儿子的裤脚往外拽,这种反常之举引起了他儿子的警觉,终使这场意外得以幸免。于是,深受感动的“老鹿”洗心革面,加入了专业护鸟的行列,成为国际鹤类基金会成员中的第一个渔民,并于2012年获得了“年度法治人物”的荣誉。
o[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周扬译:《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r可在《世间以海为深》(2021年版)中寻找佐证。
t[德]马克思·韦伯著,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9页。
u[美]大卫雷格里芬著,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v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y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97页。
z張柠:《废名的小说及其观念世界》,《文艺争鸣》2015年第7期。
(作者单位: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现代文学‘边地风景的发现与演变研究”(项目编号:23YBA30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