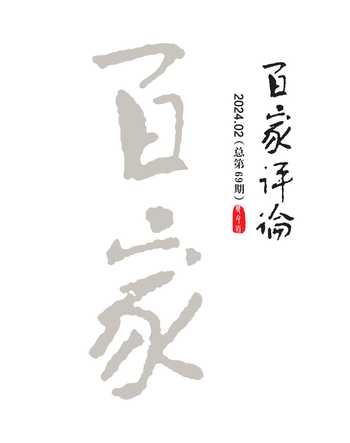时间的赋形
马春光
内容提要:随着现代时间观念的渐次渗入,现代诗人的时间体验发生深层转变,新诗的时间抒写呈现出“客观化”的整体特征。时间的客观化引发新诗“时间审美”范式的内在转换,现代诗人将时间从古典诗歌的自然化意象体系中解脱出来,将之充分“客体化”,时间本身的形状、色彩和声音成为时间想象与书写的对象。为抽象的时间赋形,是中国新诗在现代时间观念指引下的“客观化”审美方式,区别于古典诗歌“物象化”的呈现方式,内在地体现出新诗的美学特质。
关键词:新诗 时间想象 客观化
基于一种情感化的时间体验,和对时间科学认识的欠缺,中国古典诗歌“对时间的把握不是分析性的,而是体验性的;不是抽象的逻辑思辨,而是情感的自然抒发”a,普遍呈现出一种情感化的、具象性的抒情性语言。而在新诗发生之初,其对时间的把握就与古典诗歌有了一定的不同,这种不同随着“现代”的不断深入,日渐造成一种新的观照时间的审美方式。现代诗歌客观化的时间抒写是现代时间观念的产物,时间的抽象化改变了现代人的时间感知方式,时间从“物象”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客观的诗歌抒写对象。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诗学观念、诗歌语言难以包容新的时间观念,于是出现了更加新奇的时间譬喻与时间形象。在古典诗歌中,时间是具象化的,它总是包融在自然事物中,而在现代诗中,时间与万事万物拉开了距离,成为现代世界唯一的主宰。在这一背景下,现代诗人一方面感受到更加痛楚的时间经验,一方面则试图缩小自身与客观时间的距离,通过具象化的方式重新为时间赋形。现代诗中的时间赋形主要倚重以下三种方式。一是用一个具象化的形容词直接修饰时间,例如用色彩来形容时间,“黑色的时间”,“白色的时间”,“五彩缤纷的时光”,等等;或者是形态化的修饰词,例如芒克诗中的“一片光秃秃的时间”。二是用比喻的方式来形容时间,“时光如梭”“时间如流水”等比较古典、陈旧的方式,在新诗中,出现了一些新奇的比喻,并且往往是“远取癖”,比如用蛇来比喻时间,常用“时间是……”这一句式。三是隐喻、象征化的方式。这种书写方式中的“时间”往往获得了比自身更庞杂的意义指涉,或指向某些异质的意义,在杂糅多种艺术方式的同时,指向了对时间更加深邃的艺术思考与赋形。这在深层上正是在现代语境中重新获得“诗意时间”并进行“时间超越”的内在意图使然。
一、时间的“拟像”
与古典诗歌中的“天人合一”观念不同,现代诗歌在认识论上首先体认了时间的客观性,然后在此基础上将其“形象化”,通过各种修辞对时间进行赋形,这就与古典诗歌中时间表现的美学机制有了明显的不同,以汪静之的《时间是一把剪刀》为例:
时间是一把剪刀/生命是一匹锦绮/一节一节地剪去/等到剪完的时候/把一堆破布付之一炬!//时间是一根铁鞭/生命是一树繁花/一朵一朵地击落/等到击完的时候/把满地残红踏入泥沙!
这首诗中“时间是……”的暗喻修辞方式,本身已经将“时间”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客体来对待,这首诗是在此基础上对“时间”的赋形:“剪刀”和“铁鞭”,并以此表达“时间”对生命的戕害。与之相对应的,是古典诗歌“时空一体”模式在中国新诗中的瓦解,譬如,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在对空间的书写中时间是自动呈现的。而在新诗中,时间更多的时候是从空间中剥离的,诗人在这个基础上以现代修辞形式对其进行“空间化”的转换。实际上,如果洞彻了“时间”抒写在古典诗歌与新诗之间的这种内在转换,我们就找到了解读新诗时间抒写之美学特性的关键。
中国现当代诗人将时间从古典诗歌的自然化意象体系中解脱出来,使之充分抽象化,然后又运用诸种新的艺术方式建构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以路易士的《时间之乐队女》为例:
沉落下去,沉落下去,/那些是卸了七色之华衫的/全裸着的时间之乐队女:/弹唱着幼小的太阳系/与衰老的银河轮;/弹唱着此一空间的毁灭/与另一空间之成长;……/弹着,唱着,彈着,唱着,/那些是永不疲倦的/时间之乐队女,/她们微微地笑着,/而且向我挥挥手,/于是沉落下去,沉落下去。
这首诗其实是在抒写太阳西沉、世界坠入黑暗的情景,但他运用象征化的书写方式,一种对时间消逝的崭新想象方式得以呈现。相比较于古典诗歌的抒情方式,它动用的崭新意象与象征体系,都昭示着中国新诗“时间想象”的新努力。
在现当代诗人中,昌耀诗歌对时间有集中的思考,并表达出强烈的为时间赋形的诗性冲动。昌耀是一个命途多舛的诗人,西北边陲特殊的自然环境赋予了他时空感知的独特方式,他的诗因而在浓郁的地域书写中融进了对时间的地域化思考,这首先是在贫瘠自然中对时间之威权的切实叹服:“时间呵,/你主宰一切!”这种“主宰”具体体现在:“没有恐惧。没有伤感。没有……怀乡病。/一切为时间所建构、所湮没、所证明。”或许可以说,在广袤的“旷原之野”上,一种空旷感恰如其分地显示着时间的威力,昌耀的书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置身其中的生存处境的诗性哲思:“一切是时间。/时间是具象:可雕刻。可冻结封存。可翻检传阅诵读。/时间有着感觉。/时间使万物纵横沟通。/时间是镶嵌画。……”在这种多重感觉融合的抒写中,昌耀的“时间”感知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升华,一种广袤视域中的丰富时间图景得以呈现,诗人同时抵达了对时间的深层次的精神领悟。昌耀的诗在中国当代的文化语境中无疑是独特的存在,我们正可以透过他的诗来体认边疆地域中的人类生存处境。在其散文诗《时间客店》中,对时间的思考通过隐喻化的诗性语言得以呈现。《时间客店》引用了诗剧艺术形式,其具体的结构营造,则类似于鲁迅《野草》中的“梦”的模式,即先行进入梦中,在诗的最后交代梦境的原委,其用意是用“梦”这一极具心理分析内涵的意象,隐微地表达对某一心境的揭示。《时间客店》抒写的特异之处,除了“梦”的复式结构外,还在于其对时间的“拟像化”抒写:
店堂里蒸汽弥漫,伙计们忙进忙出,有几个像我早到的食客已闲坐在方桌边等候服务。我瞄好一个空位走过去,用脚背勾过来一把椅子,——我实在腾不出双手来,因为以受命自负的我此刻正平托着一份形如壁挂编织物似的物件,凭直觉我知道那是所谓“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底所无”的“时间”。
在这里,“时间”是“一份形如壁挂编织物似的物件”,这种颇具工艺美的物件,在昌耀这里隐喻着时间本身的完整性,或者诗人对时间的一种精美化想象。但“时间”是不可能精美地存在的,“破碎”是它的归宿:
于是检视已被我摊放在膝头的“时间”,这才发现,由于一路辗转颠簸磨损,它已被揉皱且相当凌乱,其中的一处破缺只剩几股绳头连属。
作为一种精美物件的“时间”的破碎,隐喻着抒情主体“时间之心”的破碎,而诗歌中言说的“修复”,最终并没有完成,“而我已本能地意识到我将要失去其中所有最可珍贵的象征性意蕴”。昌耀这首写作于1996年的散文诗,不管是在结构上,还是在修辞方式上,抑或在意蕴表达上,都是新诗“时间”想象与书写的创新之作,比之同时代诗人对时间的想象与书写,昌耀有其独到的特色。
如果说昌耀的时间拟像是戏剧性的,那么在年轻的诗人戈麦那里,拟像化的时间更加富有抒情气息。置身于1990年代的个人化语境中,敏感的诗人嗅到了急促转型的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时间压迫感,诗人戈麦从“年龄”这一视角出发,表达对“时间逝去”的焦虑:
要是我们能用年轻的巨布蒙住这匹/日夜奔向大海的马的眼睛,它一定会/安详地跃入这片无声无息的海洋/我们密致的皱纹是大海激起的波浪//要是我们能把一生中所有的过失/都分割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电影片子/其中一定会有一条耀眼的线索,那就是我们的/年龄,它紧紧地系住我们所有错误的开始//要是我们可以将我们渺小的躯体投入/更为广阔的空间,年龄就会从我们的体内/斜飞出去,像一个沉重的铅球/和投掷者一起沿弧线向外奔去//我们日趋渐老的年龄是一瓶阴暗的醋/岁月用它无形的勺子一勺一勺将我们扣除/而年龄就像是一个球体毛发和末端/我们生存在球里从未见过年龄一次(戈麦《我们日趋渐老的年龄……》)
“日夜奔向大海的马”赋予了时间一个非常灵动的形象,年轻的戈麦对“年龄”的思考与想象浸染着他的悲观思想,戈麦对时间的敏感,较多地体现在其对自身生存悖论的发现与表达之上,虽然“年龄”构成了对生命的威胁,它是始终存在的,但却从不露面。戈麦对时间焦虑的表达是与异常丰富的诗歌修辞相联系的,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异常敏锐的、陌生化的时间体验方式,例如“我们日趋渐老的年龄是一瓶阴暗的醋/岁月用它无形的勺子一勺一勺将我们扣除”两句诗,就以精彩的隐喻传达了非常细微的时间想象。相对于“革命”视野下的时间超越,现代日常语境中的“时间焦虑”是面向生命个体的,昭示了现代语境中更加显豁细腻的时间经验。随着现代科技对“时间”的不断祛魅,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更加透明化,时间节奏的加快加剧了日常生活的焦虑感。现代人的时间焦虑,成为现代生存危机的典型症候。
二、聆听与注视:时间的声音与色彩
新式交通(火车)作为一种新的媒介,改变了作为感知主体的人与感知客体的自然物之间的关系,客体以它的加速特性改变了主体的时间经验和自我感知。这是波德莱尔意义上的对“感官现时(sensuous present)”的认同,“这种感官现时是在其转瞬即逝性中得到把握的,由于其自发性,它同凝固于僵化传统中、意味着无生命静止的过去相反”b,因而彰显出典型的现代性特征。
与“感官现时”的动态性时间感知相关联的,是现代诗对时间流逝的形象化感知。如冰心早期诗歌对时间流逝的莫名焦虑:“我知道了,/时间呵!/你正一分一秒的,/消磨我青年的光阴!”(冰心《繁星·九四》)“一分一秒”的具体化抒写,正是现代时间体验精确化背景下对时间流逝的表达,也正是在这种表达中,时间感知与体验的方式,已经从古典的“物我”关系中抽离出来,一种新型的抽象时间与现代自我的关系趋于建立。小时、星期都是作为外来词出现的,它们伴随着现代时间观念逐渐被固定在现代汉语中。19世纪中叶以来,“时、分的概念进入人们的生活,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时间观念和时间意识的不断强化反映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变迁”c。在由“星期”和“钟点时间”建构的现代时间制度中,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也从对自然的感知转变为机械标度时间。在《一天》中,“时间流逝”获得了更加形象化的表达:
今天十二个钟头,/是我十二个客人,/每一个来了,又走了,/最后夕阳拖着影子也走了!/我没有时间盘问我自己胸怀/黄昏却蹑着脚,好奇地偷着进来!/我说,朋友,这次我可不对你诉说啊,/每次说了,伤我一点骄傲。/黄昏黯然,无言地走开,/孤单的,沉默的,我投入夜的怀抱。(林徽因《一天》)
在抒写“时间流逝”的诗歌中,林徽因的这首《一天》无疑是别致的。将“十二个钟头”比喻为“十二个客人”,其实是一种新的时间与诗歌思维方式,这就与古典诗歌中时间感知的“自然维度”拉开了距离,在这里,林徽因首先将时间“抽象化”,随之再将抽象的时间“拟人化”,白天的十二个钟点、黄昏、夜都是以人格化的形式出现的。也正是基于此,林徽因诗歌的时间意识是现代的,她的诗歌的时间抒写是一种戏剧化、人格化的诗学建构。
诗人绿原以拟人化的方式设置了“我”与时间的对话,以“戏剧化”的方式写出了时间的流逝,以及“我”面对时间的复杂情绪:
我在时间身旁踌躇着/时间对我说/我要走了,你呢//我对时间说/我走不了,我带不走/我的足迹//时间说,没有关系——/托付明年的新草/顺便把它埋掉吧/你总得跟我在一起(绿原《题赠》之三)
把“足迹”埋掉,而“总得跟时间在一起”,其实写出了对于时间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归属感。应该说,这种时间的拟人化、人与时间的对话等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广泛存在的,鲁迅就表达过这样的主题。在这里,所谓“睹物识时移”(张载)的感受与言说方式让位于对时间的抽象化、哲理化思考。
在充满奇妙想象力的诗人顾城那里,时间获得了另一种方式的赋形:
我喜欢靠着树静听/听时间在木纹中行走/听水纹渐渐地扩展/铁皮绝望地扭着/锈一层层迸落/世界在海上飘散/我看不见/那布满泡沫的水了/甚至看不见明天/我被雨水涂在树上/听着时间,这些时间/像吐出的树胶/充满了晶莹的痛苦/时间,那支会嘘气的枪/就在身后(顾城《傾听时间》)
顾城在这首诗中以“儿童”的视角来“倾听时间”,赋予时间以生命,其实是借用空间意象来暗示、隐喻时间的流逝或变化,正是“时间空间化”的抒写方式,“时间的空间化不仅可以避免刻板枯燥的时间表示,而且由于时间转化为具体的可感的空间意象,就有可能打破物理时间顺序流动的局限,出现时序的倒流、超越、停滞、错乱,从而提供了意象重新组合的无穷的可能性,以充分显示诗人的主观世界”。d在这首诗中,时间不仅“在木纹中行走”,而且“像吐出的橡胶”,顾城诗歌中这些奇崛的意象展露了他出色的时间想象力。将“时间”比喻为“枪”,其实就设置了“我”与“时间”的一种紧张关系,这样一种“远取譬”的表达形式,形象准确地传达了顾城内心深处紧张、局促的时间经验。
“时间空间化”作为一种为“时间”赋形的艺术方式,在中国新诗中得到了丰富的表现。例如在江河的《没有写完的诗》一诗的第一部分《古老的故事》中:
我被钉在监狱的墙上/黑色的时间聚拢,一群群乌鸦/从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历史的每个夜晚/把一个又一个英雄啄死在这堵墙上(江河《没有写完的诗》)
这一部分意在叙述漫长的历史时间中的英雄受难,但却是通过“空间”来表达的,首先为“时间”赋色,然后用“一群群乌鸦”隐喻历史中一个个特定的英雄受难的时刻,这就使抽象化的时间获得了异常生动的、形象化的表达。需要指出的是,新诗的“时间空间化”有别于古典诗歌的“时空不分离”,前者是一种自觉的艺术方式,而后者则是不自觉的,受制于时代的认知水平。
现代交通从根本上修正了人们感知时间的方式,“火车”作为一个移动的视点使人们获得了全新的时间体验。在骆耕野的《车过秦岭》一诗中,诗人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了对时代、时间的哲理化思考:
黑色的 白色的 时间
蜿蜒着 蜿蜒
列车
穿行在隧道与空谷之间
——骆耕野《车过秦岭》
这是长诗的第一节,其后的每一节之前都有这四行诗的复沓,只不过“隧道”与“空谷”分别被替换为:“黑暗与光明”“痛苦与欢乐”“现实与理想”“死灭与新生”“邪恶与正义”“历史与未来”。每一组里分别是两个意义对立的词语,前者对应于“黑色的时间”,后者对应于“白色的时间”。当代诗对“时间”的思考,是在将“时间”充分客体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时间”本身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特性的客体,在诗歌中被作为抒写的对象。
实际上,19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在“钟表”上已经辨识出“时间的踪迹”,随着人们时间观念的日渐复杂,诗人对时间之形状和色彩的书写浸染了政治、文化的内涵,在这些书写中,时间即是书写的对象,又具有“中介”的功能,这类似于艾略特所论述的“客观对应物”。但都以时间的抽象化、客观化为基本的前提,这本身既是现代时间观的表征。新诗中对时间之色彩和形状的书写,与古典诗歌中自然时间的多姿多彩有着不同的诗学内涵,这是“客观化”之后的再次“具象化”,体现了现代诗的智性诗学特征。某种意义上,对抽象时间的“陌生化”赋形,成为现代诗最内在的诗学表现特征,同时挣脱了古典诗歌相对稳定化的时间表述方式,在考验着诗人想象力的同时,也以“晦涩”“模糊”等面容构成现代诗与它的读者的阻隔。
三、诗意赋形与时间的客观化
中国新诗中“时间”的客观化与抽象化,既是现代时间观念在诗歌中的呈现,更是诗人诗歌观念、审美观念的彰显。时间的客观化,促成了诗人感知世界方式的巨变,并引起诗人审美方式的内在转换,与时间客观化相伴随的是一整套现代审美方式的生成。随着现代时间观念的渐次渗入,现代汉语中表述时间的概念经历了一个持续更新的过程,一些表述时间的“新名词”和“新概念”相继出现,并在新诗中获得了丰盈的表达。“晚清民初的新名词和新概念,借助现代媒体的流播,不只是丰富了中国语言而已,还由此多方面深刻而微妙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e以“世纪”“时分秒”“日历”“凌晨三点”为代表的现代时间意象在新诗中的出现,在更新时间意识的同时,也为新诗带来了新的美学内涵。这体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时间意象从自然化到科学化。古典诗歌中较多地用自然事物指涉时间,时间意象多为“日出”“夕阳”“黄昏”等自然事物,而在现代诗歌中则被科学话语精确化,年、月、日甚至分钟,在诗歌中大量出现,标志着现代时间意识的普及。时间在诗歌中的精确化,重要的表现在于它基本上弃绝了传统的自然表征系统,而代之以严格的“钟表时间”,时间意象也逐渐脱离自然,“疏离了中国古典诗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以物观物,反对主观干预的表现传统”f,而与人的现时的生活密切相关。
第二,时间抽象化抒写与“远取譬”。现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从乡土向都市的转型,现代城市中的时间观念已经与传统乡土时间观念相去甚远,时间观念的更新在敏锐的诗人那里获得了精彩的表达,现代都市激发了现代诗人新的感受能力,与之对应的是,诗歌中出现了更多的以立交桥、高速公路等为代表的现代时间意象系统。在对这些意象的隐喻化书写中,相伴随的是诗歌主体“心理时间”的拉伸、延长、凝固等艺术方式,更加多样地思考“内在时间”与“外在时间”的繁复关系。
第三,时间精确化。“时间精确化”在深层上指向了一种“知性时间”,它强调生命主体对时间的“知性”把握,有着浓重的科学化气息,在诗歌中,则产生了“诗性”与“知性”交融问题。相较于古典诗歌中时间的相对模糊或“无时空”状态,中国新诗中的精确时间是一种深刻的美学嬗变,“时间”在精确化的同时,逐渐告别古典诗歌“天人合一”所依赖的自然维度,而转向更为深邃的内心世界,“它的突出特征不再是主体融入物象世界,而是把主观意念与感受投射到事物上面,与事物建立主客分明的关系并强调和突出了主体的意志与信念”g,进行另一种意义上的“象征化”。通过特定时刻对潜意识的透视以及某一精准时间意象对现代城市、工业展开的审美与思想批判,彰显了中国新诗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思想与艺术特质。
为抽象的时间赋形,是中国新诗时间抒写最为常见的艺术方式。以“异质化”的复杂技艺对时间进行“陌生化”抒写,意味着新诗“异质性”时间想象力的获得。现代时间观念指引下的“客观化”时间抒写,区别于古典诗歌“物象化”的呈现方式,显豁地体现出现代诗歌新的美学动向。
注释:
a詹冬华:《中国古代诗学时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页。
b[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页。
c郭福祥:《时间的历史映像——中国钟表史论集》,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d吴思敬:《吴思敬论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
e黄兴涛:《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fg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頁,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