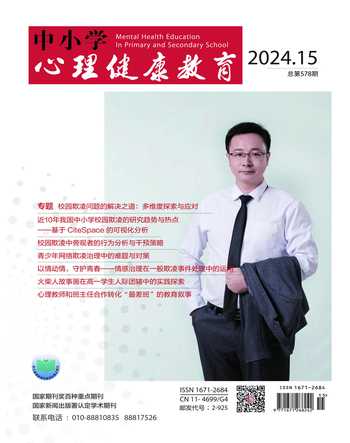当受害者不再沉默:欺凌受害与中学生社会适应的关系
童晶 郭成 曾晋逸



摘要:为探究欺凌受害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影响以及攻击性和表达抑制在其中的作用,采用Olweus受欺凌量表、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问卷、中文版Buss-Perry攻击性问卷和儿童青少年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对1328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 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后,欺凌受害不仅直接负向预测社会适应,还通过攻击性的部分中介间接预测社会适应。(2)表达抑制调节了中介模型的后半段路径,即当表达抑制水平较低时,攻击性对社会适应的负向预测更强;当表达抑制水平较高时,攻击性对社会适应的负向预测较显著,但作用较小。这提示教育者和监护者,不能一味地将表达抑制视为一种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要关注欺凌受害是否导致个体的攻击性增强,如果攻击性增强,则要适当培养其表达抑制策略以提升社会适应水平。
关键词:欺凌受害;社会适应;攻击性;表达抑制
中图分类号:G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684(2024)15-0012-05
一、引言
校园欺凌是全球教育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顽疾。当一名学生反复遭到力量较强的一名或多名学生的蓄意伤害时,这个学生就受到了校园欺凌[1]。我国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为20%~33%,约有32%的学生至少有过一次受欺凌经历[2]。欺凌受害经历与一系列的消极结果相关,但目前少有研究考察欺凌受害对个体社会适应的影响。社会适应是个体心理适应状态的整体反映,欺凌受害个体社会适应状态理应受到关注。本研究拟考察欺凌受害对中学生社会适应的影响及其中的中介和调节因素,为促进欺凌受害中学生的社会适应提供建议。
(一)欺凌受害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根据邹泓、刘艳、张文娟等[3]的定义,社会适应是个体在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心理、社会协调状态的反映。校园侵害是引发青少年社会适应不良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4]。研究发现,欺凌受害会损害人格发展并导致各种负面结果,包括学习成绩不佳、心理适应不良(焦虑、抑郁和孤独)和行为问题(社交退缩、成瘾行为和欺凌行为)[5],这都是社会适应不良的表现。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欺凌受害会负向预测社会适应。
(二)攻击性的中介作用
一项元分析发现,欺凌受害经历与抑郁、焦虑、孤独、低自尊等心理适应不良有关[6],指出欺凌受害与内化问题的联系,这一联系似乎表明被欺凌青少年是“沉默的受害者”。也有研究表明,欺凌受害者是最具有攻击性的群体,遭遇欺凌的青少年会出现愤怒控制问题和外化问题[7],这表明欺凌受害者不仅有“沉默”的一面,还可能会表现出攻击性的一面。攻击性是指个体在遭受挫折、感受到威胁或挑战时,产生的攻击、侵犯、挑衅等行为倾向或情绪状态。根据“挫折—攻击”理论,挫折情境是导致攻击性水平升高的重要线索,而遭受欺凌就是青少年常见的挫折情境,经历挫折的青少年有可能出现更高的攻击性。研究表明,遭受欺凌与个体更高的攻击性水平有关[8],并且攻击性会阻碍社会适应的发展[9]。根据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本研究提出假设H2:攻击性在欺凌受害和社会适应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三)表达抑制的调节作用
欺凌受害可以通过攻击性影响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是否存在一些保护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缓解作用?有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能力在个体社会适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0]。根据Gross[11]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表达抑制是情绪调节策略的一种,其核心思想是控制自己不表达出内心的情绪,且发生在情绪已经形成之后。因此,在攻击性情绪已经形成之后,个体的表达抑制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表明,情绪管理能力较低的个体在面对冲突时容易冲动,更容易发生攻击行为。一般攻击模型认为,输入变量(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改变了个体的内部状态,然后个体经过思考与决策决定是否做出攻击行为[12]。欺凌受害作为环境输入变量改变了个体的内部状态,引发了攻击性情绪,其是否转化为攻击性行为需要经过思考和决策,而表达抑制作为反应关注的调节策略,会影响个体思考和决策的过程,从而决定攻击行为是否会发生。因此,表达抑制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可能会抑制自己冲动的攻击性行为,从而减缓攻击性对社会适应的消极影响。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表达抑制会调节攻击性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為探究欺凌受害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影响,本研究以攻击性为中介变量,以表达抑制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在四川省某所中学发放纸质问卷,收取有效问卷1328份,其中男生616名(占46.4%),女生712名(占53.6%),所有被试平均年龄为15.18岁(SD=0.51,年龄范围13~18岁)。
(二)研究工具
1.Olweus受欺凌量表
采用张文新和武建芬[13]修订的Olweus欺凌量表中的受欺凌分量表,该量表共6道题,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受欺凌的情况越严重。参考以往研究者的划分标准,若被试在某个题项上的回答≥3,则划定为受欺凌者。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5。
2.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问卷
采用缪华灵、郭成和王亭月等[14]编制的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问卷,该问卷共34道题,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适应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7。
3. 中文版Buss-Perry攻击性问卷
采用李献云、费立鹏、张亚利等[15]修订的中文版攻击性问卷,共30道题,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攻击性越强。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5。
4.儿童青少年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
采用陈亮、刘文和张雪[16]修订的儿童青少年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中的表达抑制分量表,该量表共4道题,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越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本研究中,表达抑制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689。
(三)研究过程及数据处理
采用SPSS软件和Hayes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15个,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15.335%,远远小于40%,说明各个变量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二)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对欺凌受害、攻击性、表达抑制与社会适应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描述统计结果显示,被试社会适应(3.600±0.469)和表达抑制(3.893±1.192)的得分均值均高于理论中值,而攻击性(2.687±0.439)的得分均值低于理论中值;另外,本研究的欺凌受害检出率为26.5%。相关分析发现,青少年欺凌受害与攻击性呈显著正相关,社会适应与表达抑制、欺凌受害、攻击性都存在显著负相关,而表达抑制与欺凌受害、攻击性相关不显著。
(三)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分析过程采用SPSS中的Process宏程序,参数估计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重复取样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除了性别和年龄以外,将各主要研究变量标准化,以欺凌受害为自变量,社会适应为因变量,攻击性为中介变量,表达抑制为调节变量,并控制年龄和性别,分别通过两步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第一步,对简单中介模型进行检验(model 4)。上述结果表明,欺凌受害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攻击性,同时显著负向预测社会适应。加入攻击性为中介变量后,欺凌受害对社会适应仍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同时攻击性也能负向预测社会适应。采用矫正偏差的Bootstrap检验表明,攻击性的中介作用显著,直接效应值为-0.106,占总效应的54.922%,95%的置信区间为[-0.161,-0.051];间接效应值为-0.087,占总效应的45.078%,95%的置信区间为[-0.114,-0.063]。这表明攻击性在欺凌受害和社会适应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第二步,将表达抑制纳入模型,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model14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表达抑制调节了攻击性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即表达抑制调节了中介路径的后半段(见表2)。为进一步揭示表达抑制的调节作用,根据表达抑制的取值进行高低分组(±1SD),进行简单效应检验。
总体而言,表达抑制水平高(+1SD)的个体比表达抑制水平低(-1SD)的个体社会适应水平低。当表达抑制水平较高时(+1SD),攻击性对社会适应的负向预测显著,但是作用较小(βsimple=0.163,t=4.330,p<0.001);表达抑制水平较低时(-1SD),攻击性对社会适应的负向预测更强(βsimple=-0.354,t=-10.452,p<0.001),如图2所示。也就是说,当个体表达抑制水平较低时,随着攻击性的升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水平下降得更快。
四、讨论
(一)校园欺凌的现状
在欺凌受害方面,本研究的欺凌受害报告率为26.5%,该结果低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5年针对我国10个省市欺凌情况的调查结果(32.5%),但高于2022年郝义彬、张恒榛和吴柯等[17]的调查结果(12.4%)。我國高度重视校园欺凌问题,教育部分别在2017年和2021年印发了《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和《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据此各地深入开展中小学生欺凌行为治理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欺凌受害率显著下降。但2023年欺凌受害率有回升的迹象,这警示我们需要持续关注校园欺凌问题,完善欺凌治理方案。
(二)攻击性在欺凌受害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欺凌受害既能直接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还可以通过影响其攻击性进而间接作用于社会适应,即攻击性在欺凌受害和社会适应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1和H2得到了验证。
首先,欺凌受害会导致个体社会适应状态变差,这与已有的研究一致[6]。同伴关系是影响个体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而遭受校园欺凌就是同伴关系不良的表现,遭受同伴欺凌的个体会出现更多的情绪、行为和人际适应问题[18-20],较难发展出良好的社会适应。
其次,欺凌受害会通过增强个体的攻击性进而影响其社会适应水平。根据“挫折—攻击”理论,遭受过校园欺凌的青少年会表现出现更高的攻击性。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4],即欺凌受害会增强受害者的攻击性,遭受欺凌的个体可能会采用同样的攻击行为报复欺凌者,导致恶性循环。由此可见,遭受欺凌是攻击性增强的一大风险因素,而攻击性增强又与个体的社会适应状态下降有关。
具体而言,在行为方面,攻击性高的儿童经常打人、骂人、破坏公物或破坏他人东西,会出现更多的反社会行为,而在亲社会行为上存在缺陷[21]。在认知方面,攻击性高的个体倾向于对他人的行为作敌意归因,并且容易选择性地注意和唤起攻击性线索[22]。在情绪方面,攻击性强的儿童在面对挑衅情境时,更容易产生愤怒、激动、暴躁等情绪,情绪调节能力更差,发泄水平较高[23]。总的来说,那些遭遇校园欺凌而攻击性增强的青少年,在行为、认知和情绪三个方面均可能会出现不良表现,最终导致其社会适应情况较差。
(三)表达抑制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表达抑制可以调节中介模型的后半段路径,假设H3得到了验证。
以往的观点认为,表达抑制是一种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其结果不具有适应性,但本研究发现表达抑制不全然是一种不好的情绪调节策略。事实上,Gross和John[24]的研究也发现,当表达抑制灵活且使用得当时,它可以作为一种有益的情绪调节策略。另外,文化在情绪调节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研究者发现东西方国家在情绪调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25]。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强调“和为贵”,隐藏个人情感,避免伤害他人,努力维系人际和谐,因此抑制情绪的功能显得尤为重要。那些因遭受校园欺凌而攻击性增强的青少年,如果其表达抑制水平较低,则更倾向于做出破坏关系的攻击性反应;相反,那些表达抑制水平较高的个体,会对因欺凌受害引发的攻击性进行表达抑制调节,较少表现出攻击性行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之下,这样的抑制表现是被强调和推崇的,由此会表现出更好的社会适应。
五、教育启示
首先,欺凌受害不仅会直接损害个体的社会适应,还会通过增强攻击性损害个体的社会适应。这提示教育工作者,对于已经卷入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要关注其社会适应状态,采取必要的干预手段,保护其学业、人际、生活和对环境认同的发展。尤其需要关注那些频繁遭受欺凌,同时又表现出高水平的攻击性、对抗性和冲动行为的个体。
其次,在进行情绪调节策略的干预时,要注意引导高攻击性的受害者适当且正确使用表达抑制策略。如果个体因欺凌受害导致自我的攻击性水平增强,并且不能控制自己的攻击情绪,即表达抑制水平较低,就会出现更多的攻击、冲动行为,较难发展出良好的社会适应。因此,对于那些因受欺凌而导致攻击性增强的青少年,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有关情绪调节的心理辅导时,要培养其适当使用表达抑制策略,减少因攻击性产生的冲动行为,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帮助他们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1]Olweus D. Annotation—Bullying at school—basic Facts and effects of a school-based intervention program[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1994,35(7):1171-1190.
[2]熊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数字背后:结束校园暴力和欺凌》报告[J]. 世界教育信息,2019,32(4):73.
[3]邹泓,刘艳,张文娟,等. 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保护性与危险性因素的评估[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31(1):29-36.
[4]梁雅丽,金岳龙,丁蕾,等. 校园多重侵害对青少年社会适应不良行为的影响[J].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8,39(3):315-319.
[5]Li L,Chen X,Li H. Bullying victimization,school belonging,academic engagement and achievement in adolescents in rural China:A serial mediation model[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2020,113(10):49-46.
[6]Hawker D S J,Boulton M J. Twenty years' research o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social maladjustment: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cross-sectional studies[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2000,41(4):441-455.
[7]Salmivalli C,Nieminen E. Proactive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among school bullies,victims,and bully-victims[J]. Aggressive Behavior,2002,28(1):30-44.
[8]Ostrov J M. Prospective associations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aggression[J]. Child Development,2010,81(6):1670-1677.
[9]耿毅博,刘衍玲,严玲,等. 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对社会适应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43(8):10-19.
[10]王亭月,郭成,缪华灵,等. 新冠肺炎疫情下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及其与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43(8):1-9.
[11]Gross J J. Antecedent and response 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Divergent consequences for experience,expression,and physiolog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8,74(1):224-237.
[12]Anderson C A,Bushman B J. Effects of violent video games on aggressive behavior,aggressive cognition,aggressive affect,physiological arousal,and prosocial behavior: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J].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1,12(5):353-359.
[13]张文新,武建芬. Olweus儿童欺负问卷中文版的修订[J]. 心理发展与教育,1999(2):8-12,38.
[14]繆华灵,郭成,王亭月,等. 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问卷的信效度评价及应用[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46(10):106-113.
[15]李献云,费立鹏,张亚利,等. Buss和Perry攻击问卷中文版的修订和信效度[J].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11,37(10):607-613.
[16]陈亮,刘文,张雪. 儿童青少年情绪调节问卷在中高年级小学生中的初步修订[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24(2):259-263.
[17]郝义彬,张恒榛,吴柯,等. 父母婚姻质量与中小学生受欺凌及自伤行为的关系[J]. 中国学校卫生,2022,43(9):1342-1345.
[18]刘燊,洪新伟,陈燕铃,等. 中学生受欺凌与抑郁情绪的关系:安全感与自尊的中介作用[J]. 应用心理学,2022,28(6):516-523.
[19]Hanish L D,Guerra N G.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patterns of adjustment following peer victimization[J].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2002,14(1):69-89.
[20]Healy K L,Sanders M R,Iyer A. Parenting practices,children's peer relationships and being bullied at school[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2015,24(1):127-140.
[21]寇彧,谭晨,马艳. 攻击性儿童与亲社会儿童社会信息加工特点比较及研究展望[J]. 心理科学进展,2005(1):59-65.
[22]Dodge K A,Frame C L. Social cognitive biases and deficits in aggressive boys[J]. Child Development,1982,53(3):620-635.
[23]王振宏,郭德俊,马欣笛. 初中生情绪反应、表达及其与攻击行为[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3):93-97.
[24]Gross J J,John O P.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Implications for affect,relationships,and well-being[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3,85(2):348-362.
[25]Butler E A,Lee T L,Gross J J. Emotion regulation and culture:Are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emotion suppression culture-specific?[J]. Emotion,2007,7(1):30-48.
編辑/于 洪 终校/石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