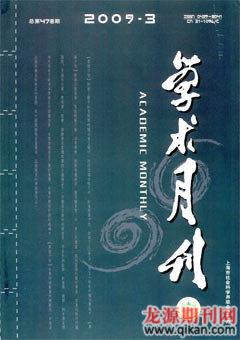“麻城孝感乡”:一个祖源地记忆的历史解读
梁 勇
[摘要]“湖广填四川”是明清时期规模盛大的移民运动,“麻城孝感乡”则是明清以来四川众多移民共同的祖源地记忆。对于明代的移民来说,洪武二年(1369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其背后隐藏着移民对夏政权与明政权的认同态度,即部分移民通过改动入籍时间的方式表达对夏政权的一种怀念。清代此一传说的再次盛行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明末清初的连绵战争不仅造成四川人口的大量减少,同时也让“麻城孝感乡”成为了明代“孑遗”共同的祖源地;另一方面,清初的“移民实川”政策也使得大量的湖广籍移民来到四川。可以说,清代至今此传说的盛行,是湖广籍移民与明代“孑遗”共同倡导的结果。“麻城孝感乡”祖源地传说表达了地域社会中不同族群对文化符号的建构、模仿、选择,及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嬗变的过程。
[关键词]麻城孝感乡湖广填四川族谱历史记忆
[作者简介]梁勇(1976-),男,重庆市人,历史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清社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3—0140—07
一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提议迁湖广民众来川时,曾对战乱之后的四川人口籍贯作了简单的调查,张氏称:
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士……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
二百年后,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也说:
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张、魏两人的说法见之于地方志、族谱、文集等资料中,同时也为现今的四川1人(含重庆)所津津乐道。在人们的闲谈中,“麻城孝感乡”这一移民来源传说的大概过程是这样的,明末清初,“八大王”张献忠入川,肆意屠杀川人,清朝占据四川后,从湖广,特别是麻城县孝感乡迁移了大量民众来川,以至现今大部分四川人的祖籍都来自孝感乡。
如果我们检视一下明以来中国移民祖源地传说,与麻城孝感乡齐名的还有山西洪洞大槐树、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等地。这些移民传说的背后有着不同的历史意义,赵世瑜教授在对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解析中发现了蕴藏其后的北方族群关系变化的历史、卫所制度等地方基层制度的历史,而刘志伟教授则从南雄珠玑巷传说中读出了明初在广东的地方社会中,由于王朝政府编排里甲,面临入籍困境的土著、贱民为了能够被纳入王朝的户籍之中,而附会出来的一个祖源地传说。那么,“湖广填四川”、“麻城孝感乡”背后又蕴涵着什么样的历史深意呢?它是历史事实还是由地方精英建构出来的历史过程?它反映了老百姓怎样的期望与诉求?
虽然有学者认为有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的祖源记忆“大多都是虚构的家族起源记忆”,但此一记忆是如何来的,人们为何要构造出这样一个传说?就现在学界来说,至少已有三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对此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早在20世纪30年代,民国《南溪县志》的作者在谈及“湖广填四川”、“麻城孝感乡”说:
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伙。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移住,何以独迁孝感一乡。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
因此,他认为,这里面可能有“冒其籍求萌以自庇”者,也就是从其他省籍移民冒籍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一观点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如有学者认为,当大批外省移民涌人四川时,在身处异地的他乡,基于生存竞争的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身份无疑是一个较为明智的选择。而当时在所有移民中,来自于湖广两省的移民占了人口的主要部分。一些其他省份的移民可能隐瞒了自己的原籍,冒籍为湖广麻城人,以求得到所谓同乡的庇护和支持,这种附会湖广籍的移民无疑在数量上加强了“湖广填四川”的影响力。这样的解释对理解移民为何宣称自己来自“麻城孝感乡”,无疑会有帮助。但它不能解释,为何那些湖广的人总是自称为孝感乡人,而不称是随州人、武昌人或长沙府人。换言之,冒籍论能够解释非湖广人宣称自己是湖广人的问题,但不能解决湖广人自己为何宣称是孝感人的问题。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如果冒籍论要成立,那么得有一个值得大家改变籍贯的理由存在。即原籍麻城孝感的人一开始就在四川拥有很强势的地位,这样才使得后来者或其他人愿意改变原籍而冒籍。历史事实表明,并不存在原籍为麻城这样的人群。
葛剑雄教授在“冒籍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移民“从众心理”这样的解释角度。他认为,这个故事盛行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由于移民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贫民,经过在战乱中的辗转迁移,几代、十几代后的后裔已经不知道祖籍的确切地点了。二是明夏政权的文武官员或军人的后代,或系被征入伍,或系犯罪充军,即使子孙明白,也不想多加宣扬。等到子孙发迹,或家族繁衍,需要编造家谱,往往不知如何下笔,或者不便再写上祖宗低微的身份,所以其他家庭也都称自己是麻城孝感人。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如果四川的绝大部分移民都宣称自己是麻城孝感乡人的话,那倒可以解释得过去,但是在四川各州县中,湖广籍移民并不占绝对的多数,只是相对的多数,而且还有地域之分,川东较川西、川南为多,而川北等地是陕西人的后裔占主导地位。
张国雄教授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与元末和明末麻城均有军事强人路过有关。元末红巾军首倡者之一的邹普胜,为麻城人,徐寿辉在蕲水(今浠水)称帝后,邹普胜以军功被任命为太师。麻城作为他们的首义之地,给他们的记忆便是元末战乱从麻城始,对他们的记忆影响深刻,独特的战争经历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以致后来被视为故乡的标志。这样的解释在很多情面上都说不通,如果因为邹普胜是麻城人,大家就以麻城为记忆故乡的标志,那明玉珍作为堂堂大夏国的皇帝,应该有更多的人来以明玉珍的籍贯随州作为自己的祖籍地才更有道理。
总的来说,上述三家观点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虽不能完全解释“麻城孝感乡”现象,但也都有自己的部分合理性。笔者在这里试着从文本的考察和移民历史传说的考订角度人手,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并分时期地来看这个故事在明清时代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及其内涵。
二
在张德地给康熙的奏折中,他也对这么多明代“孑遗”宣称自己的祖籍是湖广麻城感到纳闷,“然无可稽考,亦不敢仿此妄请”。从中可以看出,关于麻城孝感乡的记载,在明时就很流行,这也得到族谱资料的证实。列举几例如下:
宣统隆昌《郭氏族谱》始祖本传载:
公讳孟四,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明洪武初年避乱入蜀。至富顺赵阳乡居之,是为本族始祖。
仁寿《李氏六修宗谱》中保存了一份大概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由该族后裔李如薄所做的“序”,内称:
窃闻李氏之先,原籍麻城县孝感乡青山下。于有明洪武时,上川入籍仁寿县,置业大屋新屋。
如果上述两份族谱关于原籍的传说记载还是口耳相传的,下面这一份族谱所载则来自当事人的回忆。隆昌《王氏族谱》中有明景泰七年(1456年)王氏三世祖王仁义所写的谱序,该序详细记载了该族移居四川的经过:
予思我父讳(保)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区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
景泰七年距离明初只有八十余年,其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这份族谱提供了几个有价值的信息值得重视:(一)王氏并不是麻城县孝感乡人,族谱清楚地表明他们是河南省汝宁府信阳州罗山县崎岖乡木斗管第五都人,不知道是何原因他们“挈家游至”麻城孝感乡,“喜其风土”,居住了三年。从他们起身入川到八月十四日正式到泸州的日期表明,他们是随傅友德讨伐明夏政权的军队从陕西进川的,“孝感乡人尽搬入四川”。从这些资料可以推知,王氏入川始祖可能是军人,也就是说王家是军户。他们随大明军队在麻城一带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入川准备后进军四川的。(二)这次迁徙,共有“老幼男妇二十二名”,族谱资料表明,王久禄共带有遂九、成九、永九、保九、年九等九个儿子一同入川,说明王氏的这次迁徙是合家的、规模较大的迁徙,同时本人则可能是有功名或官职的。王氏家族以占领者或胜利者的姿态定居隆昌后,整个明清两代,都是当地巨族,“烟火数百家,丁男数千口”。
从上述三个明代移民家族的个案可以看到,“湖广填四川”与“麻城孝感乡”这样的民谣在明代的中晚期已经在四川各地流传。
明代湖广人移居四川的原因,胡昭曦认为大概有四类:一是元末因徐寿辉部红巾军在湖北争战而避乱入川的;二是随明玉珍部入川的;三是随明军入川的;四是明初因四川人口稀少而自发迁徙,来川寻求生计者。这样的划分大体不错,也得到了族谱资料的证实。
第一类:如据江津《周氏家乘》载,周氏族原籍江西,后迁湖北,“世居黄州之麻城孝感等处”。迁蜀始祖周经世,幼名绳九公,元末,刘福通、徐寿辉、陈友谅等起兵反元,“蔓延各省,江西、湖广蹂躏几遍”。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周经世同妻子徐氏一道,率领五个儿子从湖北迁到了四川忠州。
第二类:如黄陂《周氏族谱》提到,元至正十二年(1362年),明玉珍在四川建立大夏政权后,“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制礼乐,境内不见兵革几十余年”,不少湖广人“以随州明玉珍、黄陂万胜在蜀有治行,凭借乡谊,襁负从者如归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籍者”。
类似的记载也见之于四川地区的族谱,如重庆《明氏族谱》,该份族谱保留了一篇明隆庆六年(1572年)明氏二十代孙明守仪写的序言:
(元顺帝时),因闻族人蜀川,玉珍称帝可以避乱而往四川依焉……祥和公见真主帝业无成,蜀川既年遂卜重庆家焉。
至于第三、第四类,前引族谱中已多次提到,如隆昌《王氏族谱》即为明证,这里就不再多举例。
但这样的划分只是一个粗略的轮廓,它掩盖了不同性质入川移民对于各自家族记忆所持有的观点。据族谱所载的入川时间,洪武二年(1369年)是个有趣的现象。罗江《罗氏族谱》曰:
罗氏谱亡久矣,其原籍由江西迁移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于明之洪武二年从高河坎入蜀插占筒东仁乡,世居东岳山玉皇庙丙灵殿罗家沟等处。
又如,内江《黄氏家乘》载:
我祖一支于明初洪武二年由楚入蜀,落业内江邑西黄石坎。
从移民家谱的记载上来看,明洪武二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该年按明夏政权的历法,为开熙五年,此时四川尚不在明太祖的控制范围之内(洪武四年,明派傅友德、廖永忠等人灭明夏政权)。民国资阳《陈氏家谱》所辑的严正相《湖广填四川说》称,“蜀人楚籍者,动称明太祖定鼎之二年,由麻城孝感乡人川,言人人然”。至于为何如此,他继续解释道:当时明太祖“已谕昇(明玉珍子,时大夏国皇帝)归命,遂各占田土”,待到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明昇降服后,乃“令编户册,先占籍者,辄署为洪武二年,后占籍者,遂署为洪武四年”。该族谱还屡次改动入川的日期,如在清雍正五年(1726年)的《陈氏族谱原序》上,原本写道:陈氏乃“湖广麻城孝感乡居民坝人氏,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入川是实”,但是,到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陈氏族规序》上,却改为自洪武二年己酉又二月十四日入川。到了同治年间,又把入川时间改为“明初”。从陈氏的个案来看,由于朱元璋在明初实行的编户齐民政策,不同时间段的移民后来在选择填写入川时间时,都选择两个有意思的年份:洪武二年和洪武四年。而这两个年份,其后面却有不同的内涵,即先占籍署洪武二年,后占籍署洪武四年。这两个年份包含着的是对两个不同政权的认同态度,即明夏政权与朱元璋的大明帝国。为何如此,内江《晏氏家乘》称:
内邑旧户,多称祖籍系楚麻城,沿明洪武二年奉诏徙麻城,实蜀语故也。今考《明史》,太祖平蜀在洪武四年,先尚为伪夏明玉珍所据,何由有此诏?且咏化等书于明事口微毕注,亦无徙楚事。后阅升庵谱注,及本邑王侍御墓志,皆云先世籍楚麻城,元末避红巾乱来此,余书类此甚多。始元季大江南北,干戈猬起,明玉珍以至正乙未入蜀,据有诸郡。东人避乱者归之,玉珍又楚北随州人,招乡人以自固其势,然也。迄明平蜀革伪号,人讳称之,故成谓洪武初迁蜀,即吾族中人向来修谱亦有此语者,今时澄也。
从这份族谱的解释来看,在明中后期有关“麻城孝感乡”的记忆更多地是对于明夏政权的一种怀念与记忆。“个人通过这类记忆,就有了特别的途径来获知有关他们自己过去历史的事实以及他们自己的身份。”而这份怀念便逐渐表现为对“麻城孝感乡”的记忆。该书族谱指出,“麻城孝感乡”其来源则在于洪武二年的“奉诏徙麻城”。作者经过考证,此时的诏书不可能是洪武皇帝下的,因为当时四川还不在明朝的统治范围之内,而只有可能是明夏政权的诏书。这给我们一个提示,明中后期流行开来的这个移民祖籍地的故事可能是明夏政权旧部遗民和在明夏政权期间移民到四川的湖广人对于祖籍地的一个认同。
三
这份记忆随着明末清初的战争,其内涵逐渐也在发生变化。
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明代所修的谱牒大都散佚,清代的后人在重修族谱时都会提及由于不见了
旧谱,所以对明代的往事无法考证的遗憾。如明代巴县四大家之一的刘氏,据民国《刘氏族谱》称:
吾族谱帖创自省斋公,至明季遭变,族人东奔西驰,或迁黔省,或徙古滇,纷纷鸟散,而谱帖遂因之失。洎国朝定鼎,携眷回川者,仅存宗派图一轴。
同为明代巴县四大家之一的牟氏,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形,据民国《牟氏族谱》载:
惟传至恩野祖,当明末之乱,巴邑被献贼屠毒尤甚,爰避难遵义。迄我朝还定安集,恩野公于顺治年间,还居云篆山下石马场三角箐,斯时谋生不暇,何暇及谱,以故明代之世次,皆不可考焉。
由于明朝的前事湮没不可闻,虽然已经在巴县居住了二百多年,但乱后回乡的“孑遗”,也不得不以大难不死、幸存回乡的人为始迁祖,“今墓下子孙繁衍约千余,皆以恩野祖避难回籍为迁徙始祖”。
上述文字我们从中除了能够感觉战争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巨大破坏影响外,也可以感觉得到清代牟氏族人对祖先“失忆”的无奈。明时的世系因战争的破坏,已经完全无法考证,所以新的世系表只能从清初开始计算。同样的道理,对祖籍地的认识也失去了具体的指称,而只能通过传闻来判断了。
内江黄氏家族六世孙黄典,生于康熙乙未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殁于乾隆乙卯年(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在临终之前曾对自己家族在明清之际的发展情况有专门的回忆:
吾成童时,闻父口传,先世由楚麻城县孝感乡,自洪武年间入蜀,占籍内江西乡贤良二里人筑黄金桥、黄石坎、黄鹤镇等处,当时世系由来载之谱者详矣。崇祯十七年,张逆叛蜀,邑境糜烂,人民逃亡者殆尽。先祖讳学瑞,携吾祖兄弟二人,逃至贵州仁怀县。大清定鼎,复垦旧业,其时仓促往还,遗失旧谱矣。今欲修刊,将何自而始哉。惟知我太高祖讳佳令,以至于典确而不紊耳。其前有未祥(详)者,俟后之来者博访参稽,据实而序之,以补其遗恨焉。是则吾之至望也矣。
黄典的曾祖黄学瑞带着两个孩子避乱逃到贵州,逃难途中不仅丢失了族谱,同样也丢失了对家族祖先的记忆,到康熙中后期重修族谱时,对明中前期的很多事情就茫然无知了。他对祖籍地的认识也只能“闻父口传”。
重庆涪陵《徐氏家谱》在明代谱牒不传的情况之下,解释了不传的原因及理由,“明清交际,世运否极,由楚达蜀,道途遥遥,仓皇奔走,或彼时未暇携谱,或携谱而失于中途,亦乱世人民之常识”。这样的说法应该不单独存于涪陵徐氏。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初的土著在记忆明时的情况往往就一问三不知,只有人云亦云了。
内江《段氏族谱》里保留了一份咸丰四年(1854年)七世孙段朝良的序,从这份序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当时他们重修族谱时对于祖籍地模糊不清所带来的困惑局面:
(段氏)始居河南,继迁金陵,复迁江西,后迁湖广……素闻吾祖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入川卜居内邑西乡安良里,落业四处,一段家冲、一段家坝、一段家岩、一段千子冲……由洪武至崇祯历居二百数十载。冤遭献逆屠川,流毒几尽,吾家独幸,有太高祖成文公与堂侄应宏公避难至贵州遵义府,厥后娶祖妣杨氏,生伯高祖应荣公。迄国朝定鼎后,不忘祖业,仍旋故乡,始生高祖应华公。归里时仅寻得子顺祖公阴氏祖妣二老枯骸,合葬于周家坡。至子顺以上之祖均不能记忆,非成文祖止知有父母,忍置列祖而不顾念也。盖因避难时年甫十二岁,兼之家谱遗亡,所以洪武二年入川之祖并中间数世列祖,尽被献贼蹂躏,直令数世列祖屋宇、坟茔概归湮没,无从深考。
段成文逃难时,年仅十二岁,父辈可能都死于逃难过程中,由于年龄太小,对家族的来源情况当然记不清楚,再加之家谱也在逃难过程中丢了,更不能记清楚明以前的情况了。在此困境下,他们一会说自己是麻城孝感乡,一会又听上辈传说好像是湘水麻城。问题实在是很困惑,他们也解决不了。干脆把这些困惑都写下来,希望后人找到新的资料后再来解决。
这样的困惑不仅仅是内江段氏有,巴县牟氏在谈及其入川前祖籍地时同样如此:
吾祖讳夷,生三子,长九章、仲万章、季宪章。万章、宪章子孙无考,惟九章祖牵楚荆州府公安县牟家坪,一名黄州府麻城孝感乡,娶祖母陈氏,乃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陈世恺尚书之女也。
牟氏是明时巴县四大家之一,“科甲联第”,在明代其对祖先的记忆应该十分清楚,可是在清代再修族谱时,却对自己的祖籍地不甚清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清中前期四川原有的土著对明代及明代以前的情况已经丧失了“记忆”,而人云亦云地说自己家族是“湖广填四川”,祖籍地是“麻城孝感乡”,这可能就是葛剑雄所说的“从众心理”吧。
从上述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土著来说,明代的事情成为了不可考证的历史记忆,他们只记得本家族是从湖广麻城孝感乡而来得。“湖广填四川”、“麻城孝感乡”这个在明中晚期流行于部分移民家族的传说,到了清初便成为张德地所见到的所有残余土著对自己祖籍地的认同的标志。如《新津县乡土志》称:
新邑自遭献贼之难,土著仅余数姓,……国初始还旧籍,其后插业之家,多自洪雅,询其原籍,概系湖广麻城孝感乡,是以湖广籍邑人几十居八九。
四
经过长达四五十年的战乱影响,入清以后的四川人口损失殆尽,耕地从明万历时的十三万顷降到了顺治时的一万多顷。“移民实川”成了清初很长一段时间清政府在四川实行的政策。大量移民的到来,为此一故事的传播又添加进了新的内涵。
由于地利及交通的便利,湖广籍移民占据了这股移民潮的先机,并成为这股移民潮的主流。有研究者根据族谱、地方志资料指出,在川东、川中地区,湖广籍移民的比例占到了70—80%,在比例相对较少的川西地区,也有三分之一左右,总量占移民总数的60%。大量湖广籍移民的到来也为清政府在四川的治理增加了难度,为此,康熙认为应采取特别的措施来约束在川的湖广移民,“嗣后湖广民人,有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貌、姓名、籍贯,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四川巡抚,令其查明”。“湖广填四川”“麻城孝感乡”的故事继续在家谱中得到书写。华阳、新繁《陶氏族谱》载:
一世,明晓公,原籍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人氏。明末由楚入蜀,卜居华阳县太平镇,距场数里,地名石隼偏插业居住。
这批新来的湖广人再加上此前一直宣称为孝感乡的明时四川人后裔,使得自称为麻城的人在四川部分州县人口结构成为相对多数。地方志也有这样的记载,如咸丰《云阳县志》云:
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乡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湖)北人较多。
这些湖广籍的移民在其族谱中,还顺带记有康熙皇帝颁给他们的移民诏书。如陈彰模所撰的《陈氏家乘记》就详细地记载了该份“圣旨”全文,兹引如下。
清圣祖仁皇帝招民徙蜀诏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承先帝遗统,称制中
国,自愧无能,守成自惕。今幸四海风同,八荒底定,贡赋维固,适朕愿也。独痛西蜀一隅,自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抚(芜)有年,贡赋维艰。虽征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费,倘起江西、江南助解应用,朕甚悯焉。兹据御使温、卢等奏称:湖南民有毂击肩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即著该部,饬行川省、湖南等处文武官员知悉,招民徙蜀。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扰。俟六年外奉旨起科。凡在事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嘉奖。钦此。
清康熙三十三年岁次甲戌正月元日
类似的“圣旨”还见之于其他族谱中。这里姑且不论诏书的真伪,但该份圣旨背后的意义还是值得讨论。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的移民招徕政策,并没有省份之别,在最初阶段,凡是愿意来川的移民清政府都一律欢迎,大开绿灯。我们从其他族谱资料也可以看到,这个时期,来自陕西、贵州、广东甚至福建的移民都有入川开荒的。康熙皇帝似乎不可能单独给湖南入川开荒的民人颁以圣旨,而对其他省区的入川民人不闻不问。这应该与湖南移民在四川的心理优势有关。湖南临近川东,来往四川相较之于他省,更为便利。川东地区,移民也以湖南人为主,如重庆府《定远县志》(今武胜县)载:“土著绝少,嗣后广为招集,民多自楚来徙,垦荒占田,遂为永业”。将该份圣旨载入族谱则更加突显湖南籍移民在川东乃至四川地区的优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麻城孝感人成为了当时四川老百姓最重要的祖籍地认同标志。可以说,麻城孝感乡成为了湖广籍民众共同的族源记忆。
对于那些清代来川的移民来说,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多为下层民众,因此,大部分家族最初并无族谱之类,现存族谱中不少是后来的追忆”。这样的认同直至今天还在进行着。许多此前并不是湖广麻城籍的移民后裔通过这个不断传播的移民祖籍地传说,也开始相信并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于麻城孝感乡了。
如重庆府永川县五间铺吴家坝,为吴氏所聚居之地。道光十年(1830年),吴氏九十七世孙,同时也是入川十七世孙吴正瑶在碑刻资料的基础上纂写的入川始祖妣《王孺人墓志》中称,“孺人原迹(籍)湖广黄州府蕲水县……大明洪武五年迁蜀”。表明该族并不是孝感乡人,但笔者现在访谈吴氏后人时,他们无一不宣称自己的家族是“湖广填四川”时,由麻城孝感乡迁徙而来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龙门阵》就记载了荣昌县一位原籍湖南宝庆(今邵阳)的移民后裔,称他的祖籍有两个说法:概言之,湖北麻城孝感乡;细言之,湖南宝庆府桃花坪。
可以这么说,在清初,“湖广填四川”成为了四川土著自身身份的一种标志。“湖广填四川”、“麻城孝感乡”在明清之际的认同内涵已经完全发生了转移,即从对明夏政权的认同到清代转变为四川土著的认同。在清代,那些新从湖广入川的民人和“失忆”的明代移民后裔都把“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祖籍地认同,这不仅仅是一个“从众”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身份选择的过程。当大批外省移民涌入四川时,在身处异地的他乡,基于生存竞争的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身份无疑是一个较为明智的选择。
正如实验心理学家所认为的,“记忆不是一个复制问题,而是一个建构问题”。对同一事物的历史记忆,随着时空环境的改变和人们的利益诉求变化而有所变化。从明清两代“湖广填四川”、“麻城孝感乡”不同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明时湖广人宣称自己祖籍来源于“麻城孝感乡”时,更多地是对于明夏政权的一种记忆。而到了清代,“麻城孝感乡”则成为了老民和新近某些湖广人的自身认同标志。这里面不仅有某种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同时也含有现实社区政治的考虑。当然这个故事的产生,和族谱的编纂原则有关,正如赵世瑜教授在研究华北移民有关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时所指出的,“越是晚近修的族谱,吸收传说的内容越多。传说进人族谱,便成为可信的史料,族谱所说再被采择进入正史或者学术性著作,历史就这样被亦真亦幻地建构起来了”。
[本研究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清代移民社会地方基层制度研究——以巴县客长制为中心”(批准号:07JC77001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