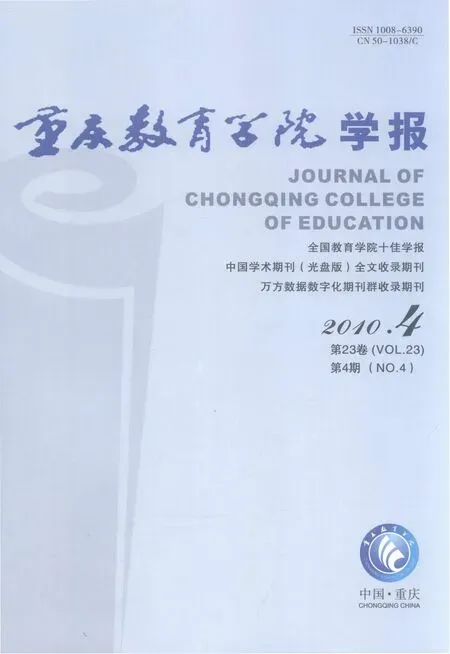《麦克白》与《施洗的河》的原罪意识之比较
程晓雪
(四川外语学院 研究生部,重庆 400031)
“原罪”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基督教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原罪”,就是上帝面前的罪人。西方许多文学作品都涉及“原罪”思想,有些作家甚至以此为主题写成小说。例如:美国19世纪作家纳撒尼尔·霍桑、赫曼·梅尔维尔等。“原罪”就像幽灵,始终回荡于西方文学之苑。基督教认为,这是对人类灵魂的拷问——人与生俱来的是理智、道德还是欲望、罪恶?人类应该崇尚制约还是应该放纵欲望?“原罪”观点揭示了人类内心理性与欲望的冲突、灵与肉的纠缠,正是这些构成了西方文学悲剧情怀的思想基础。
一、原罪——灵与肉的纠缠
《圣经·创世纪》说,天造万物毕,最后造了人,一男一女,配为夫妇,以便繁衍人类。亚当,夏娃,置于天堂福地。此处无病无痛、万福齐备、不用劳苦、五谷自生。上帝曾指知善恶的树给亚当夏娃说:“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而,夏娃经不住蛇的诱惑,首先偷吃了伊甸园里的智慧之果,然后又劝亚当吃下了智慧之果,于是人类的始祖对上帝犯下了罪,被上帝发现后,为表示惩罚,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从此上帝预先注定人将遭罚”。此即 “原罪”。原罪延及子孙,代代相传。
在西方文化中,原罪是人类精神上沉重的 “十字架”。虽然后来有上帝之子耶稣的救赎,但作为背负着沉重肉身的个人,西方人从未卸掉过自己身上背负的沉重的十字架。
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类似于西方文化中的“原罪思想”体现在那里呢?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是有很大区别的。但这并不是说基督教原罪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没有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之一的《庄子》一书中,我们就看到了西方基督教“原罪思想”的影子。《庄子·应帝王》中有这样的记述: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我们权且认为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原罪思想吧!但这种原罪与亚当夏娃的“罪恶”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不能不影响到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形成了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原罪意识的区别。如果说西方人的原罪是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结果,那么我们权且认为中国人的原罪就是从倏忽“谋杀”混沌开始的。
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还是其后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处处都可见到灵与肉纠缠所带来的痛苦。神性与人性的深刻矛盾,在信仰与理性的互动中造就了恒久不变的痛苦。《圣经》说罪与生命同时诞生,人为自己创造了罪的世界,罪进入世界,世界就变成人类共创的一种困境。罪的世界反过来束缚我们的人生与心灵,任何人自出生开始都在这困境中难以自拔。这就是基督教教义中 “原罪”观念。而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原罪主题并不占主要地位,20世纪前半叶出现的曹禺的 《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作品各以不同的视角展现了原罪思想。但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原罪思想销声匿迹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了一批蕴含西方基督教原罪意识的作品。北村的长篇小说《施洗的河》就是这些作品的代表。
二、对原罪的不同表述
《麦克白》很好地阐释了原罪观念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灾难和悲剧。应该说,麦克白开始不是一个坏人,他是一个勇敢善战的英雄,甚至是民族的骄傲。在他看来,荣誉和美德是人的内在价值所在。他甚至不愿干违背道德准则以至有损自己荣誉的事。可以说,在他身上良知与邪恶并存。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在成为一个英雄的同时又表现了追求名位的野心。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麦克白的性格就决定了他的追求名位的野心,起初他还是踌躇,但是接着就伸手去抓王冠,为着要抓到手,不惜谋杀国王;为了要保持住王冠,不惜采取一切残暴凶恶的手段。”
那么,麦克白这种矛盾分裂的悲剧性格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原因使他的性格如此复杂多变?答案正是原罪观念。由于人自身的原罪意识,他内在的野心与他对荣誉的追求、美德的向往互相抵触,与他自身本来存在的一些美好品质互相冲突,他的内心始终是矛盾的。强烈的内心谴责与极度恐惧使他掉进自设的“心狱”。正是基督教中的原罪观念和忏悔意识引导、控制、主宰着麦克白走向人格的分裂,以至于造成最后的悲剧结局。麦克白的内心是矛盾的,在遇到女巫前,在他心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荣誉和美德,内心虽有邪念,但还没有达到泯灭道德和良心的地步。当他遇到女巫后,在女巫的“麦克白,未来的君王”的胡言乱语中逐渐引发了他内心隐藏的欲望和野心,他内心深处的原罪意识被唤醒了:“星星啊,收起你的火焰!不要让光亮照见我的黑暗幽深的欲望。眼睛啊,别望这双手吧,可是我仍要下手,不管干下的事会吓得眼睛不敢看。”在原罪的支使下,麦克白作为人的行为选择突破了躯体等自然限制,进入了追求潜在无限自由的普遍悲剧命运之中。
说穿了,原罪意识就是一种欲望,一个人如果完全受欲望的支配,铤而走险,那么悲剧就是很自然的结局。
如果说是女巫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野心和欲望,而另一个女人——他的妻子则是进一步促使他实现野心和欲望的动力。作为妻子,她深知麦克白的性格“弱点”,这个“弱点”就是麦克白内心深处还有善良的一面。如果这个弱点不克服,也就是说他内心的善良和正义不被泯灭,那么女巫的预言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文本中这样写到她的心理:“我却为你的天性忧虑,它充满了太多的人情的乳臭,使你不敢采取最近的捷径。你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人物。你不是没有野心,可是你却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系的奸恶。你的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一方面不愿玩弄欺诈,一方面却又要作非分的篡夺。让我把我的精神力量倾注在你的耳中,让我用舌间的勇气把那阻止你得到王冠的一切障碍驱除吧!”
不难看出,此时的麦克白内心善与恶的较量还难分胜负。当他的妻子要求把刺杀邓肯的事由她来做时,麦克白此时还处于犹豫中,他说“我们还要商量商量”;“我们还是不要进行这一件事情吧”。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巨大外力的推动,他完全可能放弃这次谋杀。但在他的妻子的怂恿甚至是威逼和责骂下,他终于采取了行动。关于这一段情节,《麦克白》是这样描述的:“从这一刻起,我要把你的爱情看作同样靠不住的东西,你不敢让你在行为和勇气上跟你的欲望一致吗?你宁愿像一头畏首畏尾的猫儿,不惜让你在自己眼中成为一个懦夫,让‘我不敢’永远跟随在‘我想要’的后面吗?”表面上看来,是麦克白夫人的这些话刺伤了作为男子汉的尊严,迫使他行动。实际上,由于原罪意识,他的野心和罪恶欲望从来就存在于身体里,恰巧在这个时候让他为自己的罪恶行动找到了合理的借口。于是他说:“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我有更大的胆量。”他的原罪意识彻底主宰了灵魂,最后走向众叛亲离的可悲结局。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麦克白》在关于人类的原罪意识是与生俱来的表述上是透彻的,说明作者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清晰的。作者承认主人公英雄的一面,也揭露了人性恶的一面,它与现实世界对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外因是起辅助作用的。莎士比亚让我们触摸到了人内心的挣扎,他告诉我们人的天性中都潜藏着罪恶的成分。“罪”是通过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相互综合得以传播的。《麦克白》文本中,麦克白在女巫的引诱下,在妻子的威逼和教唆下触发了人性中的“恶”,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同样的。
《施洗的河》是北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讲述了上个世纪40年代毕业于医科大学的刘浪历尽俗世中的罪孽生活,走向灵魂觉醒的过程。刘浪孩提时代生活在一个缺少温情的家庭,生逢乱世。他成人后继承父业,在南方一个城镇以恶抗恶,不择手段地贩卖烟土,杀人越货,成为黑社会的一方霸主。但与此同时,他在精神上却找不到依托,以致最后精神崩溃,万念俱灰。但他读医科大学的一位奉读《圣经》的女信徒却一直对他产生着潜在的影响。在经历了大奸大恶、大风大浪,面对了周围无数人的死亡之后,在经历他的精神生命无数波折扭曲之后,他找到了精神皈依之所。
在这部小说中,人性得到了深度开掘,颓败混乱时期的男人曲折隐秘的内心世界被充分曝露,是一部充满激情、直逼人的灵魂世界、震撼人心的作品。
小说在霍童和樟坂两个城镇的背景上展开,而情节冲突则主要围绕樟坂的两大黑势力龙帮和蛇帮的争斗残杀而变幻。作家选择一种特殊的观照视角展示了生命和人性的形态,表现了特定生存境域中生命的凋残和人性的丑恶。可以说,罪恶正是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它作为一种媒介沟通了小说中众多的生命存在。在《施洗的河》中“作恶”成了主人公的共同的选择,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和性格特征,罪恶都是支撑他们人生行为的重要支柱。在小说的“罪恶”大厦中,刘成业、刘浪、马大、董云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四大恶人,他们在不同的时空中共时态地编织了一张覆盖整个小说的罪恶之网,以四重奏的形式演绎了以诋毁,亵渎生命为主题的罪恶故事。事实上,他们也正构成了我们进入《施洗的河》必须首先跨越的门槛,他们的遭遇将是本文无法回避的宿命。主人公刘浪是出身于富贵之家的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却存在着严重的精神病态,很早就体现出他灵魂中“恶”的一面,两次弑父未遂。正如小说里的另一个人物马大所说的那样,刘家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即是疯狂。这种疯狂不是植根于聚敛财富或者攫取权力的欲望之中,而是植根于性格纵深的幽暗之处,蛰伏于血管与神经里面。无疑,刘浪是《施洗的河》的真正主角,小说也正是以他的出生、堕落、获救为中心情节编织故事的。在他身上,人性恶的本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已经变成了罪恶的根源和证明。刘浪如同被逼急的野兽,除了杀人越货之外,他还时常做出一些乖戾乃至匪夷所思之举。他会因为某种变态的性感射杀无辜的女人,他也会在转念之间击毙珍爱无比的猎犬,他会毫不姑息地让弟弟死于自己喽啰的枪口之下,他也会逼迫自己的手下在火车驰过时卧在铁轨上饱受惊吓。他甚至对侍奉刘家几十年的老花工缺少怜悯之情,他会在某一个早晨毫无理由地逐走花工,然后自己将花园糟踏得一片狼藉。尽管如此,刘浪仍然不是十足的恶棍,他也有乐善好施的时刻。他可能重赏下人,可能爱抚儿子,甚至可能殷勤地善待对手的老母。但是,这一切无法割除刘浪性格深处的恶念滋生。令人可怖的是,这些恶念可能在任何一个时刻喷涌出来。刘浪的笑意时常转瞬即逝,折磨与杀人的愿望会在顷刻之间漫过他的心头。所以,这些恶念甚至不是工于心计的结果,它所带来的残暴与血腥让他人甚至让刘浪本人猝不及防。《施洗的河》仿佛证明,人的内心潜藏着一个罪恶的渊蔽,一个黑暗王国隐匿于人性内部。在这个意义上,罪恶是无因可循的,它们源于人的本性。小说中罪恶是其无所不在的主题。然而作者并不是单纯地去揭示罪恶,而是把着眼点放在了写出刘浪在罪恶世界中精神的虚无,恐惧成了作品中一个鲜明的主题词。当刘浪发现自己完全无力摆脱罪恶与黑暗的时候,他干脆选择了堕落。这恰如美国评论家莱肯所说:“在试图掩饰原有罪恶的过程中,一个罪恶会导致另一个罪恶。”
三、“面对”原罪
面对“罪”的名义,麦克白和刘浪无疑都成为了负担人类“原罪”的“受难基督”。麦克白弑君后,对自己的罪行及其结果表现出明确的认知:“人生已经失去它的严肃的意义,一切都不过是儿戏;荣誉和美德已经化为灰烬,生命的美酒已经喝光,剩下来的只是一些无味的渣滓”。由于麦克白以资与上帝沟通的灵魂的失落使他对肉体之死感到万分恐惧,于是暗杀了具有“高贵的天性”、使他“惴惴不安”的班柯,又向女巫求取不死秘诀。然而,“死的毒钩就是罪”。麦克德夫未足月就被从母腹中剖出;士兵们用树枝作伪装使勃南的树林“移”向邓西嫩,击溃了麦克白在罪里挣扎的信心,使他最终完结了必死之悲剧命运。
麦克白为突破自身存在的有限性而弑君获罪,又为弥合自身的疏离状态而在原罪和本罪里苦苦挣扎,但人本身所具有的潜能无限性驱使他在欲望和自我提升中不断摧毁神人平衡统一体,走向必然的悲剧命运——死亡,从而成就了对“罪”的一种诠释。
北村在创作中也同样关注人的现实生活,挖掘人性的复杂与罪恶,询问人生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倡导在耶稣的关怀下进行灵魂的自我拯救。这也是考验作家灵魂深度与高度的凭证。从这个角度来讲,北村拥有对生命本质的探寻以及自己的理解。北村大概是中国当代第一个自称信仰基督教的作家。他努力在对人类苦难的真切深入的体验中,探寻出一条从绝望中走向救赎的希望之路。他企盼凭借神的指引和人类灵魂的自我拯救,在基督光芒的照耀下走出黑暗的笼罩,获得人性的光辉,以神的爱来拯救整个人类。在此角度上,北村是扮演着灯塔守望者的角色。
终于,在上帝的召唤声中,刘浪找到了方向与去处,忏悔和眼泪使他获得重生。北村通过刘浪这个寓言性的人物形象,似乎在宣告人的灵魂得到救赎的可能性,而这种救赎无一例外地都归功于上帝的仁爱和良知的复归。
[1]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2 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杨慧林.罪恶与救赎—基督教文化精神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5]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J].花城,1996.
[6]勒兰德·莱肯.圣经文学[M].徐钟等译.天津: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7]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卷八[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8]Bradley, A.C.Shakespearean Tragedy.London: Macmillan @Co.Ltd, 1965.
[9]Charles Lamb·Mary Lamb·Tale form Shakespeare·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88.
[10]关少锋.试谈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M].洛阳:河南戏曲艺术出版社,1981.
[11]贺祥麟.麦克白浅谈[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12]庄子[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13]查尔斯·兰姆姐弟合著,萧乾译.阅读莎士比亚——永不谢幕的悲喜剧 [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14]北村.施洗的河[J].花城,1993.
[15]北村.施洗的河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16]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M].陈观胜,李培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