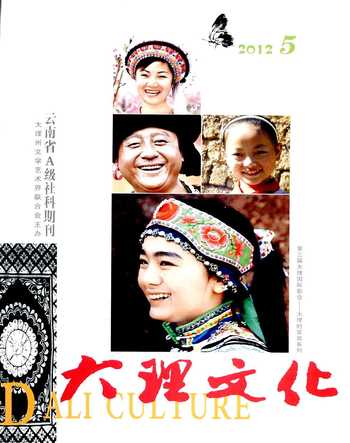路(二题)
刘绍良
回家的路
一个人不应该没有家。没有家的人是他忘记了回家的路。
没有家的人是漂泊者。他的一生,像一枚树叶,在风中打旋。
我有三个家,三个家被一条公路串连着。两头各一个,中间一个。路不太长,五十来公里。两头的两个家是命中注定,是在我未出娘肚之前就已经预料到的。一个是父亲、母亲,一个是妻子、儿子。
另一个家是始料不及的。每个人在走路的时候,都会有很强的选择性,为了实现既定的目的。而我,也曾经有过选择性和目的性。但是,走着走着的时候,双腿就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另一条路上。而且,常常是行人很少,很冷僻的那种。如此,可以说,是我的大脑支配不了我的双腿,是我的双腿在带领着我的大脑。
只有回家的路是固定的,家就是路的尽头。因此,当走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大脑和双腿才达到一种高度的协调。
双腿应该是没有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即使走岔了道,吃尽了苦头,甚至遍体鳞伤,也不能完全把责任归咎于腿。
其实,我觉得我已经走了很多很多的路,却并没有真正地走到一望无际的平原上,让我看到路的尽头,以及那位在天之一隅,水之一方伫立着的伊人。而且,在那些相对的平原风光展现在眼前的时候,感觉到的是单调、平庸和失望。因此,我便几十年在不尽相同的大山里转悠着。
我在大山里转悠着的时候,需要到达什么地方,需要寻找什么东西,恍恍惚惚地,我说不清楚。但是,我的大脑是思考着的,只有此时才明白,我是被我的大脑带领着的思想的飘泊者。并且,似无归期,似无居所。
每一条路都有目的,目的就在路的那一头。因此,当你在路上走着的时候,你的脚印已经印在了无数的脚印之上。至于最上面的,和你的脚印刚好重叠在一起的那一个,你会知道,是因为你还能看见他的背影;你也许不知道,是因为你走慢了几步,他已经转过了一个山坳。
在别人走过的路上走着,你不仅省力,还会有一种亲切的感觉,甚至,你还会嗅到不同的人身上散发出的不同的气息,让你去作猜想、去发感慨。转而,你会似泄尽了力气一般,突然地产生了一种错觉:在别人,别的无数人走过的路上,尾随其后,不知尽头,没劲。于是,你就会去看看羊群踩出的路,野兔走出的路,麂子跑出的路。甚至,头顶上有鸟群飞过的时候,划在天空上的那道鸟路。
一个人,若能看得清鸟路,必然高深莫测。
我曾经设计过一幅照片:一个孤独的旅行者,背着简单的行囊,在夕阳的余辉里,踽踽地艰难地前行着;他的前面,是有尽头的山脊,夕阳,就在山脊上等候着他的光临。他的身后,一片野草一片荆棘,每走一步,小路就延长了一步。他的前方,并没有路。
他是小路的开拓者。但是,“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到了山脊的时候,也许夕阳仍在,也许一片迷茫,也许小路已到尽头,也许小路还应该延伸到更为遥远的地方。
小路的起点就是小路的尽头。没路的地方留着许多与路有关的痕迹,让你去走。
我的第三个家在一片曾经荒蛮着的山坡上。前面,有一座梵音萦耳的佛教寺院,叫慧明禅寺。十余年前,我第一次到寺里焚香朝拜之后,极想到寺后的山野里走走,但是,简易的乡村公路到寺后的一个鱼塘边就是尽头,当我把北京吉普车在鱼塘转角处艰难地调过头的时候,我明白,前面的路就是回家的路。
每个人在走着自己的路,别人走路的时候,都不可能永远照直地走下去;转弯是偶然的,或者不得已;调头却是必然的、规律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在这次调头的时候,还会不会在不久之后又再调头,进入那片荒蛮的山坡腹地。那是,有一段路等待着我去开拓,有一个家等待着我去奠基。
人离不开房屋,是人的悲哀;很多地方本来有路,但没人看见,无人去走,是路的悲哀。
我在这片山坡上看见了一条很宽的,可以供车辆行走的路。因此,我跑前跑后地指挥着推土机去拱。拱出的土壤是红褐色的,散发出的氤氤亘古的气息,将很快地被汽车尾气冲淡。我明白这是一种开拓。在人们的眼光里,开拓是明确的,破坏是隐蔽的。
我有一种莫名的欣喜,许多年之后才明白过来,是因为我拥有了一段被我发现的被我行走的回家的路。
路的尽头必然是家。因此,我在这条路的尽头盖了很多房子。每个人都会住在房子里,不过,那房子是别人盖的,或者是你的爷爷,或者是你的父亲。你在这样的房子里出生,及至长大成人,及至你离开了这个家,到别人的村庄去,到别人的城市去,你还是会想方设法地住进房子里。不过,房子不等于是家。只有住久了,不想再移动的时候,才可能是家。
房子的前面总会有路。一条已经历史久远的路;或者,一条为了房子才修的路。这路,已经走过了许多人;这路,也许正在走着许多人。凡是永久地暂时地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人,都会和你说着同样的话:“那条,是我回家的路”。你说这话的时候别人都认可,因为你的家确实在这条路的某一个地方。但是,你在家门前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别人,也许还正在寻找着自己的家门,还需要在这条路上继续走着。
为了有一个家而修路,还是修了路才发觉应该有个家。在我刚进入那片山坡的时候,我心里并不明确。那时,家的概念,在我站立之地的南方和北方。不过,由我选址,由我画图,由我带人施工完成的第一幢房子,我想到的是我住、我的亲人和我的朋友们偶尔小住。
一个人,在山坡上愉快地生活着;或者,寂寞而艰难地生活着,都不能构成人类意义上的家的内涵。因为,没有亲人,没有那种以沫相濡的温暖。
我长久地居住在那间房子里,常常也向南走,沿着那条回家的路,看望母亲、弟妹;往北走,同样也是沿着另一条回家的路,看望妻儿。但是,当一个人在一幢房子里住久了,那么,你离开时的这条路,必然在返回时成了你回家的路。尽管,是一个人的家,一个人的路。
我在一住十年的山坡上扩展了家的内涵。亲人是门外满目皆是的生灵,其中以羊、狗、鸡,以蜜蜂、斑鸠、白翎花鸟为主;比邻是日月星辰,花草绿树。甚至,我觉得我的脚底已长出了根须,我觉得我的双臂已成为翅膀。
在已经走了很多路之后,才发觉人的一生根本不必去走很多的路。走了很多路的人和走了很少路的人,结果都一样:你老去的时候他也老去;你归宿在哪里,他也归宿在哪里。路走一条就已足够,这就是,从家里出发,再回到家里。飘泊是白云和树叶的事情。因此,人的生命和思想都应该在人的范围内驻足。
我比许多人幸福得多,幸运得多。我有三个家,有的是别人盖的房子,别人修的路;有的是我盖的房子我修的路。我总是把属于我家的房子记得很清楚,也把回家的路记得很清楚。因此,我常常会很随意地在家与家之间旅行着。
我常常会对自己说也对别人说:人的一生只有一件事,记住回家的路。
通往墓地的路
我从一个土堆旁走过,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土堆应该比低凹处更干燥,刺蓬却长得十分茂盛。土堆已经坍塌得没有形状了,只有面向空旷的地方,还有几块不规则的石头,支撑着一个人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居所。
一个人的居所对一生来说非常重要。活在世间的时候,不管居所是用什么材料建盖的,都应该具备夏能避暑冬能避寒的作用。这个人一走,就把什么都留给活着的人了,包括他的故事。
一个人既然什么都不能带走,活着的时候就不该有更多的奢求。吃饱穿暖,有儿有孙有老伴,再加上几匹牲口、几头猪,便是富贵了。土地是固定的,张家的便是张家的,李家的便是李家的。如果必须经过别人的地,才能到达你的地,你就小心一点,避免恶目相对。假如别人又必须经过你的地,踩坏了几株豆苗,也不妨说声没关系。如此,把你抬出家门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辛苦一下,并会比平时更在意你的好处。你把福气留给儿孙了。
这个土堆的主人想必是个绝户,从来没有人来上坟烧纸。刺蓬是很生发的,承担起了保护一方安宁的责任。现在我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我已经砍了很多刺蓬,只把这一个刺蓬留着。刺蓬是鸟雀歇脚做窝的最好环境,让我看见了一个小小的鸟巢和几只小小的雏鸟。人会有对人非常厌烦的时候,那是活人对着活人。对这个人来说,已经远离了许多是非。因此,有刺蓬和鸟雀在自己的头上,时时能够看见,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这个人没有名字,我只能猜测。
另一边也有几塚老坟,我看见它们的后人们,在去年清明的时候,目中无人地从我身边走过,从我的地里穿过,为老坟重新整容。老坟被整成新坟之后,美观、大方、气派,一律用打凿好的石料围砌。正面是工艺不错的碑圈,雕龙刻凤,还有两只狮子,永远地蹲在墓碑两侧。正中砌着一块上方是圆弧下方是方形的墓碑,一律为大理石板材,显得华贵而典雅。详看字样,方知此人生平及儿孙满堂。
一天,有个放羊的村人从坟前走过,对我点了点头,说:“这人有福气,房子比活着的时候好。”但是,今天的这座好房子其实很寂寞,连鸟也很少歇脚。只在每年清明,会有一天热闹。这份热闹,对那些活着的人,不妨说是一次郊游、一次聚会、一顿美餐。从他们的穿着打扮,谈吐嬉笑看,应该是一种很满足的人世的享受。至于里面的那一个,必然什么也不知道。
一个人的一生走到了尽头,有个居所是应该的。在我接手这块土地的时候,也认真地察看了地形地貌,也看到了安静地卧在草丛中的坟墓。我只想,与这些曾经在近旁的村子里生活了一辈子的人为邻,又有何妨。也许,他们会在温暖的地层下,用他们的方式,说些故事给我,说些经验给我。
然而,阳世的事情却并不乐观。有人已经来找我商量事情了。他们说:“你修羊场的时候,弄掉了我家祖坟上的山神石;害得我的家里人生病了。这是发票。”事情就是这事情。接着,他又算了一笔账:“发票七百,请地师看风水重立山神石一百、办四桌酒席八百,共计一千六百。”
四位汉子在我的厨房里,他们这样说就明显地带着山神的旨意。这位山神,也可能曾经在我的山坡边缘地界内有着权威。
山神的旨意是不能违抗的。不过,在这群还活着的人的面前,我觉得我才是名正言顺的山神。阳间的山神决定要和阴间的山神作一番较量了。于是,阳间的山神对那四人说:“你们从不看望你们的山神,你们的山神就遁形了,这是你们的山神对你们的惩罚。”此时,四位汉子里有三位站了起来,提着拳头。阳间的山神说:“且慢,待我先去挖三个坑,好把你们交给你们的山神。”
转而,两界山神用神的语言达成协议:“由阳界的山神,出资三百,由四位汉子请地师择日立石,办酒席三桌共享,以结永欢。”
数日之后,我已还原成我,被四位汉子中的老大三邀四请地上到羊场,在绿翠松毛铺就的地上席地而坐。那位地师见我大惊,即呼:“贵人、贵人,好面相!”说完掐起指头,数说子丑寅卯。此时,我与阴界山神已意唔在先,由此,我用阴界山神的语调对地师说:“风水学乃大学问,源自《易经》。浑沌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重叠为八八六十四卦,再加五行,以此为据,风水皆准。”
自此,地师一言不发。
自此,数年后的某一天,我开车下山,见四位汉子在收冬瓜,那位老大便问我要几个,我说一个,送上山去。
果然,那是一个我见过的最大的冬瓜。
这是一块面积可观的山坡好地,位于两个村子的中间,地权属后面的村子。前面的村子位于平坝边缘,无地可以耕种,无地可以埋人。如此,在漫长的一拨又一拨的活人与活人争斗的岁月中,前村的聪明人疏通了后村的聪明人,要么埋上一位两位先人,要么种上三亩五亩好地。至于前村不聪明的人和后村不聪明的人在这块地里相遇,纠纷便是极普通的事情;有时,也会用拳头用锄把干上几仗,多少放点血出来,也属正常之举。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村的村长大智大慧,把这块“兵家”必争之地以极少的价钱,以五十年的时限,承包给林业站的职工,合股开垦为梨园。如此,保住了后村的尊严,也缓解了两村的矛盾。几年后,林业站为收回投资,转手于我。我便成为看守许多坟墓的阳间的山神了。
阳间的山神没有供奉。阳间的山神还得时时面对这些亡人的后人们的骚扰和进犯。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那些古老的村庄里,村人们都明白一个真理:亡人的旗帜神圣无比。
我常常在亡人的旗帜面前败退。因为,每个人都会成为亡人。
有位官员是我的朋友,凑巧,她夫人家的坟地就在离我居所不远的地方。每当清明的时候,他常常会来找我叙话,一根烟点燃之后,一杯茶里,还会浸泡着些人情。不巧,在数年前的清明那天,他家坟前的纸火引燃了周围的干草,一时火势猛烈,待我聚众扑灭之后,数十株梅树、板栗树已成亡树。临别,我们对视一笑,都说:“没事”。
三天后,林管员来找我,他问:“你地里三天前发生火灾?”我说:“是。”他是执法者,他又说:“你违反了《森林法》,为什么不报?”我说:“火已经扑灭了,受损失的是我。”他再说:“不对,受损失的是国家,你必须上报,等候处理。”我又回答说:“是”。
三天后林管员又来找我,他说:“对不起,没事,弄毬错了”。
死人是不会把事情弄错的。把事情弄错了的常常是活着的人。那些早我一步进入这块土地的死去的人,他们不断死着的后人,又被一个一个地抬了上来,埋在他们的前后左右。由此,我糊涂了好长时间,怀疑自己,是不是侵犯了死人的领地。
在我还糊涂着的时候,又有一个我已日渐熟悉的村人找到我,他非常客气非常亲切地对我说:“我的族人中,昨天有一个不在了。但你的树已长得很大很密,人抬不上去了。而且,为了给以后留条路,只好把树挖掉几棵,砍掉几棵。”
他和他的族人对我很客气也很亲切,挖树砍树的时候他们要我去看,我说:“好。”刚走几步,我的心口便痛了起来,让我迈不出步子。当他们说送我去医院的时候,我勉强地说出了几句话。我说:“我痛得受不了啦,恐怕就要死啦!”
我又活回来的时候,去看望了那位新来的邻居。我是在林地里,顺着那条新挖出的小路走上去的。但是,我的树没有被挖也没有被砍,只把一些确实挡人的枝桠弄掉了一些。
人活一世,是应该留条通往墓地的小路的。只是,这条路,不管多好,平时并无人行走。而且,这样的小路,留在你的地里可以,你却要把它留在我的地里,让我得了心口痛的毛病。
我在种树的时候,最关心的是这棵树的根须。它的根须长得好不好,关乎这棵树一生的荣辱和生死。那么,人呢,人的根究竟有没有,究竟长在什么地方。恍恍惚惚地,我不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确确实实地看见了人的根。这些根是从坟墓里长出的。但是,只见根而不见树干和枝叶。树干和枝叶只有在清明的时候才长出来,是他或他们的那些吱吱喳喳着的后人们。
他们把根扎在我的土地上,渐渐地扩展着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地盘。
这是一块曾经因纠纷因争斗而长满荒草的土地。因为我的原因,眼前已果树成林,兽走鸟飞。而且,我一呆就是整整十年。十年来,绿树增长着的同时,新坟也在增加。由于我修了车道的原因,很多埋在我地界之外的亡人,也常常被抬着,雄赳赳气昂昂地沿着此道从我的土地上穿过,让那些用很少的阳钱买来的冥钱洒满了山坡。有一张,还被风把它贴在我的脸上。我小心地把它揭下来,先放到鼻尖闻闻,然后,又举到眼前。我从那些钱孔里,看到一些零零碎碎的风景。
责任编辑:彭琼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