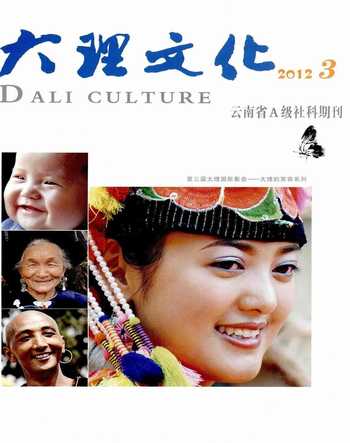哀牢小村人物
狗 妹
小村小。
全村二十来户彝家竟没个厕所,各家养了几条吃屎狗,内急了,便跑进后阴沟或地边栅栏下,嗷嗷唤狗,大肆方便。
小村是小,小到不论哪家娃打架打伤了、哪家田里地里庄稼被哪家牲口吃了、踏平了,或是哪家的猫抬了哪家的腊肠、哪家的老鼠药闹死了哪家的猪、羊,当事主妇只需怒气冲冲站在村头“无名高地”——土包上鸡啦驴啦……拍屁股大骂一通,保准全村震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小村是小,这里方才愤怒难平地退下“高地”,那里又心平气和地或笑着相互借油借盐有来有往,或站在土包子上邀约着去村中打歌场上搂肩搭脖欢快地打歌。
小村确实是小,小到从唐末逃难隐居于此到如今祖祖辈辈就这样点着松明,唱着“日子过得不自由,唱个山歌解忧愁”的山歌,住在鸟窝大的山旮旯里,看着巨蟒般的黑■江滚滚而来,咆哮而去……
“我想去闯江湖!”
有一天,村长的独子阿狗终于憋不住,说了这么一句。
“人乏一饱水,马乏一盆料。江湖人杂,险恶着哩,莫去莫去……”小村人轮番劝阿狗。
“楸木开花不结果,秧草结籽不开花。松毛装拢灵芝草,象牙装拢狗骨头。黄狗卵子充麝香,你拗什么?!”村长阿土抬起长烟锅杆瞪大眼吼了儿子一声。
阿狗言听计从,最后当了小村“一师一校”小学的民办教师。
可有一天,小村人突然发现小村的人多了起来,杂了起来。在那个雨哗哗下个不停的日子,小村人一觉醒来,发现峡谷两岸全是人——操着各式各样口音的人。
三大五粗的男人在挖洞打桩搭棚子。
听说要在小村峡谷建个好大好大的水库发电。
“江湖来了?”最初小村人惶惶不安。但慢慢地,小村人发觉,“江湖”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可怕。连祖祖辈辈烂在树根的鬼李子,也可以拿到峡谷两岸工地上换成钱。工地那些“老表”好像一群狼,隔三岔五就到小村买鸡买羊,老说生活太苦。
小村有了江湖?!
狗妹灵机一动,决定闯一闯,于是在小村村头的那几转烂墙院上搭了几间茅草房,置了几套碗筷,开起了饭店。
狗妹哪点人?
她就是小村寡妇张阿姥的独女,是小村唯一和村长儿子阿狗到过山外,念过“暗歌你戏”的“女秀才”。
店开张了,然而吃的却只有自家的猪腊肉和荞面粑粑。刚开始,工地上的“老表”都说狗妹的山歌好听肉好吃,可时间一长,都摇头。
狗妹为这事急得如同火上了房。
看着漫山遍野跑的吃屎狗,狗妹心一亮,私下暗想:狗肉补,又治跌打劳伤,好哩!
当夜,便点着松明火把,系了个扣子下在院子里,把自家的吃屎狗套住了。
天麻亮,狗妹便烧狗剖肚忙个转。
很快,大锅里就煮了一锅用核桃油、腊肉、糊辣椒炸黄的狗肉坨子,惹得工地“老表”老远闻见香味,就一窝蜂跑来“打牙祭”。
“每碗十块。”狗妹说。“不贵,不贵!只可惜缺了提神酒。”“老表们”欢欢喜喜吃完肉,欢欢喜喜走啦。
从此,狗妹便天天唱山歌卖狗肉汤锅,“老表们”酒自个捎上,肉越吃越香。
狗妹家穿的吃的用的越来越好,还玩起了“卡拉OK”。“老表们”吃饱喝足,还在店里五角一曲鬼哭狼嚎唱“卡拉OK”。
狗妹呢,穿上迷你红裙和白高跟皮鞋,整日挺着高高的胸脯,在小村人面前走来走去。她今天唱“正月花甲口中梅,朵朵拜下属鼠人,小鼠咬烂含香笼,露出美女绣花鞋”,明天唱“三根竹子一样高,一刀砍来做吹箫,白天吹得团团转,夜晚吹得妹心焦”,后天唱“阿妹有钱无使处,买给一副人笼头,把你拴在妹身上,阿妹不动哥不走”,永远有唱不完的山歌。
狗妹惹得工地“小老表”和全村山哥心神不定,他们心痒痒的,老想到狗妹店里闲,有时干着活放着牛也会偷偷跑到店子背后,从烂了的墙缝里瞄几眼“过过瘾”,几个胆大的山哥甚至整夜在店背后的山包上唱:“情妹呀,隔山隔水唛难相生,格是喽——说给情妹你听去,你绕山绕水唛绕拢来,哎咦哟”、“情妹呀,不怕千山唛十八凹,格是喽——说给情妹你听去,誓将妹唛娶到家里来,哎咦哟”。
小村的山妹们又急又恨,一齐跑到狗妹的店里看看这,看看那,她们搓搓红裙、摸摸高跟鞋,问狗妹:“哪里买,哪里买?”。
“坝里,尽是!”狗妹满脸得意洋洋。
小村山哥山妹们痒手痒脚,也想开个狗肉汤锅店。可是,他们的阿爸阿妈阿爷阿奶一百个不准。他们的阿爸阿妈阿爷阿奶关上大门,提着烧火棍大骂:“冷死不向佛灯火,饿死不吃猫儿饭,偷狗卖?呸!伤风败俗,欺公灭祖!丢尽南诏先祖腊罗巴呢脸!……”
山哥山妹们谁也不敢碎,不敢把这话传给狗妹。话丑撕面子,她们孤儿寡母的,过日子也不容易,再说手头不便了,还得向狗妹借个十块、八块的,把狗妹惹日气了也不好。
小村人不声不响,把自家的狗拴好看好,防止它们别去踩那扣子。可狗多了,拴着喂不赢,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管毬它,全村又不是只有我家这几条吃屎狗。”很多人都这么想。
但是,小村人坚决反对自家的山哥山妹,坚决不允许干这种伤风败俗、欺公灭祖的杀吃屎狗卖的事。
小村山哥山妹们嚷嚷闹闹仍不肯罢休。
这可激怒了阿爸阿妈阿爷阿奶。
阿爸阿妈阿爷阿奶牛眼冒火,举着吆牛棍大骂,要把山哥山妹赶出家门,断绝关系。
山哥山妹可怜巴巴地整天叹气,满眼泪花看着狗妹挺着高高的胸脯,在她们眼前走来走去……
然而,有几家阿爸阿妈阿爷阿奶嘴里骂得很凶,心里却巴不得自家的山哥山妹也能多挣些钱。
小村终究又开起了几家店子,也卖狗肉汤锅,可他们卖的狗肉却不如狗妹的“味足”。山哥山妹的狗肉削价卖也卖不完,于是便天天卖馊狗肉,最后再也没人吃了。
“小小公鸡才学叫,拍拍翅膀又歇掉。噶佩服?!我说你们这些欺公灭祖的败家子,叫你们搞不得搞不得,你们不听。这回噶见啦?噶还想再搞?!……”阿爸阿妈阿爷阿奶们得意洋洋地说。
“有心绕到这边过,搭妹要口凉水喝。不是别家要不到,妹的凉水才解渴”。
狗妹依旧穿着迷你红裙、白高跟鞋,卖着香喷喷的狗肉,唱着优美的山歌……
村里的狗越来越少,各家不得不在自家的核桃树梨树下挖坑盖厕所。
阿嘎老姆在自家的七条吃屎狗全都失踪后,终于忍无可忍地跳到村头“无名高地”上,破口痛骂,满嘴都是“烂草垫”啦、“破袜子”啦,脏话满天飞。
后是阿九姆。
再是村长阿土老婆……
“无名高地”变得热闹异常。
狗妹老妈在忍了七天七夜之后,终于也忍无可忍,一脚蹿到“无名高地”,指天划地,捶胸顿足,声泪俱下:“他爹呀,你睁睁眼,蚊虫虱蚤子乱来叮,人家在欺负我们母女俩;南诏务底老天呀,你睁睁眼,不要脸的人借走了两千多块钱不想还……”
小村的狗风波,以狗妹妈的最后“泪诉”平息。
狗少了,小村“嗷嗷”唤狗的习惯没了。
没狗上扣,狗妹的狗汤锅也卖不下去了。
在村长阿土和阿土老婆的极力游说下,在那年的腊月,狗妹背着被老熊抓瞎了眼的老妈嫁到村长家,做了阿狗的老婆。
不久,工地上的“老表们”也三三两两地走了。
小村依然还是那么小,小到只要有人站在村头“无名高地”上鸡啦驴啦拍屁股大骂一通,保准全村震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小到这里方才息怒退下,那里又心平气和地笑着相互借油借盐,相邀着去打歌。
小村没变。
唯一变了的是,巨蟒般滚滚而来的黑■江到了小村,在那里汇成一个清清的湖……
老张老爹
逢年过节喜白两事,海吃米酒,大坨吃肉,打歌唱调,这些都是彝家最古老的习俗,小村很好地继承了。
然而,小村几十号人中,与这习俗完全无关的还有一个,一个非常古怪的瘸老爹。
没有人知道瘸老爹的年纪,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的人?叫什么姓什么?只知道他古古怪怪,爱吃耗子,爱吃麻蛇肉,爱一个人自言自语,爱一个人疯了似地笑……
小村阿公讲,这老爹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里的一个冬天,拄着一根拐杖,背着一包破衣物来到小村的。小村的彝家兄弟姐妹见他憨厚老实又可怜巴巴,便让他住在队里的场房里,给他饭食……
初来时,这老爹不言不语,也不和村里人一起打歌唱调。村里人送给他饭菜,他也只叽哩呱啦说些小村人听不懂的话。但小村人从老爹泪花花的眼中,看到了老爹善良的心地。
老爹便这样活下来了。
村里人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见他非常爱吃耗子、麻蛇肉,又不吃油盐,都觉得非常古怪。村里有位老爹,年轻时到过很远的地方挖过飞机场,见过这样的人,也一样地爱吃耗子肉和麻蛇肉,他们都叫“苗子巴”(苗族人)。
后来,有人听见老爹说了个“张”字,便以为他姓张,便把老人叫作“苗子张老爹”。
每逢过年过节和过冬,小村人都争着给张老爹送柴送饭。小村人自来信奉只要在世的时候“积阴功行阳善”,将来死了就不会下地狱,于是张老爹自打来到小村后不愁吃也不愁穿,生活得不错。
老爹有时乐了,会一改自言自语的傻样,笑眯眯蹲在小村口逗小孩,把小村里没人看管的小孩照顾得好好的。慢慢地,老爹也会学着小村人唱:“大理有名三塔寺,蒙化有名巍宝山,每年二月朝山会,人满山头彩云间”、“会打歌的来打歌,不会打歌干站着,得以来到歌场上,不来打歌白来玩”……他常在村头的包谷地里转,常操着呱呱的话把进了庄稼地的牛马猪羊轰赶出来。
张老爹就这样,不言不语地在小村里生活了十多年。农村土地下放到户的时候,小村人分给他一只母羊和一块好地,直到这时老爹才淌着眼泪开口说了话。
“他也会说我们彝家话?”小村人惊奇地看着老爹,奇怪老爹竟能讲一嘴彝家话,虽然有些词句有些拗口,却也字字句句都说对了。老爹张嘴笑了:“学!我来了这么多年,怎学不会?”
小村人更加喜欢张老爹了。
从此,老爹变得活跃起来。他又唱又跳,唱的尽是《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之类的歌,跳的尽是小村人从未见过的“抬脚舞”。小村人很爱听,也很爱看。
老爹见小村人喜欢,便讲起了“古本”。老爹讲的尽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贺龙等英雄人物的“古本”。老爹讲得有头有尾,津津有味,尤其讲到爬雪山过草地死了好多人,老爹流泪了,小村人也哭了。
老爹天天讲,夜夜讲,讲得小村人越听越过瘾,就像村里来了电影队似的。
小村人每天早早收工,匆匆扒完饭,便三三两两牵着小孩一窝蜂挤进场房里,听老爹讲红军打鬼子的“古本”。
小村读过点书或到过山外坝里的人都很奇怪:老爹讲的“古本”怎这么好听,这么细致,有些书上和电影里没有的,老爹也能一一讲出来……
“老爹是什么人?”老爹的身份,他从未提起。
后来,老爹去世了。小村人按照彝家自南诏便流传下来的古老风俗,用喂狗的葫芦瓢给老人洗净脸、蒙上黑脸布,胸上压上装有鸡蛋和米的碗,为亡人装魂。床底下放一个盛有熟饭、肉片,插两炷香的碗,祭亡人。请来毕摩念经:“……今晚院心里,盖起松毛房,地上铺松毛,彩纸扎花棚,灵前竖燎钱,纸马千万匹,送你到阴间……”《开吊经》,并打了三天三夜的歌。
在清理老爹遗物时,小村村长阿土从老爹当初背来的烂麻包口袋里,翻出一个用油布包得很紧的包。打开,一层又一层。翻到最后,掉下一本红彤彤的小书本。阿土打开一看,哇——是党员证!里面夹着一张发黄的纸:
我叫张贵根,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六八年蒙冤,从此与组织失去联系。包里的七百八十三元五角六分是我补交的党费……
小村人对老爹的身世感到更加神秘。
此事传到坝里。县里知道后,派来两个干部,把老爹的东西全取走了。
再后来,小村人终于知道:老爹是个老红军连长,爬过雪山,走过草地,打过无数胜仗。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爹就被革命小将们斗倒,批斗中,他那条曾经被子弹射穿的左腿旧伤复发,因得不到医治而弄成了残废。一天夜里,他趁看守不注意,一颠一跛地偷偷从牛棚逃走。文化大革命结束,地委李书记——张连长的警卫多次派人四处找寻张连长,可最终杳无音信。几十年过去了,大家都以为张连长早已在文革中悄然离开人世……
谁也没料到,曾经立过赫赫战功的张连长,为躲避黑白颠倒的批斗而逃跑,而在小村里隐居了二十多年!头发胡子花白的地委退休老书记找到小村里来,他眼泪花花地在张连长坟前站了整整一个下午。
这事很快轰动了小村。
“怪不得老爹会讲那么多古本。”小村人感慨地说。
阿呜雄
阿呜雄无儿无女,是小村里唯一“领国家工资吃国家饭”的孤寡老爹。
阿呜雄是小村远近数百里山林的护林员。
小村人都叫他“护林老爹”。
国家发给老爹一支电警棍防豺狼。老爹整天唱着“一条大路通大理,路边有对姑娘花;前边那个随她走,后头那个不放她;一把拉着围腰带,不说实话不放你”、“郎弹弦子无人唱,自弹自唱自宽心……”之类的山歌,领着三条猎狗,扛起电警棍在山林里悠转。
国家抓“天保”工程没几年,小村山头的松树齐刷刷长到了房子高。“再小的蚂蚱也是肉,树小可以砍来当椽子。”小村的一些小年轻人又在打松树的主意了。
这可惹火了老爹,老爹见人便说:“不要再砍松树了,再砍再砍,山可要变了,又要整人了”。可小村人不爱听,砍一天椽子能捞个二三十块钱,偷偷卖掉,够花销两街了,小村人算的是这盘账。
“国家不让砍,咱偷砍!”小村人开始跟老爹闹猫猫玩转转。
这可把老爹的胡子气飞了。
老爹一脚纵到村头“无名高地”上,啊咳一声清清嗓子,开始高声宣告:“各家各户听着,从今天开始,不准再到山林里来砍木料了。猫不在家鼠打歌,你们偷砍不是跟我阿乌雄过不去,而是跟你们自己过不去。你们噶记得,往年山光秃时雨水咋个些?风不调雨不顺,再砍再砍,你们噶想吃饭?老天不饶人……我阿呜雄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人,吃的是国家饭,说的也是国家话,要是哪个不听话,再来砍,我阿呜雄一电警棍电断他的狗腿!”
不知是害怕阿呜雄的电警棍,还是终于从“风不调雨不顺”中领悟到了点什么,小村人从此很少再到山林里偷砍木料了。
可是仍有狗胆包天的一两个婆娘不服管,边骂汉子窝囊,边带上汉子背上弯刀麻绳,趁月亮摩挲亮的时候,偷偷摸摸上山砍木料。汉子在林子里偷砍,婆娘就跑到阿呜雄守林的山棚稳住阿呜雄。阿呜雄不吃这套,婆娘一来他就扛起电警棍准备去转山林。
婆娘死皮赖脸缠住老爹:“歇一下得了,这冷天冻地的哪个来?”婆娘边用火辣辣的目光粘住老爹,边用手往老爹裤裆里乱摸。
老爹不理不睬,大步跨出棚子。婆娘急了,一个纵步拦在老爹前面,一把扯拉住老爹的手唱起火辣辣的情歌: “得已来到玩笑处,不玩几回心不甘;鲜花不采白开败,人不风流白托生……蚕豆豌豆豆腐豆,一家一样抖拢来……”
老爹气得全身发抖,二话不说,闭上眼睛把电警棍对准婆娘的脸大吼:“滚远一点,我阿呜雄堂堂呢南诏王后裔噶是那种骚烂人?!”
“老鸹莫说母猪黑!”婆娘吓得灰溜溜地跑了。
老爹的威名从此传开了。
另一件事更是让老爹的威名倍增,使他成为小村最有影响力的人。
有天傍晚,老爹唱着“砍柴割草要约伴,灰迷眼睛要人吹”、“郎脱衣裳妹抖床,妹脱裤子郎吹灯。小郎脱得黑麻麻,阿妹脱得白生生。齐夺夺呢睡下去,象牙筷子一小双……”的山歌优哉游哉转林回来,听见村背后的林里有人在咕哝咕哝说话。老爹蹑手蹑脚走近一看,呸!原来有一个山哥正在扯山妹的裤子。
老爹大吼一声:“哪个胆大包天,竟敢大白天来偷砍木料……”
林里静悄悄的。老爹又大吼一声:“出来!”
林里仍静悄悄的。老爹假装自言自语:“没人?刚才咕哝咕哝说话的难道不是人?啊咳,哪是什么?喜鹊老鸹叼鸡吃,罪名背给饿老鹰……”老爹装作寻找的样子开始在旁边转圈。
山哥山妹吓得连滚带爬溜回了家。
第二天大清早,老爹啊咳一声站在“无名高地”上宣告:“房屋破了还能补,花蕊损了花自败。各家各户的山哥山妹听着,我阿呜雄身为国家人,要说国家话,唱唱情歌丰富一下生活是可以的,但若是要乱来伤风败俗,丢南诏老祖宗的脸!啊呸!往后要是还有谁敢跑到林子里来乱搞,我阿呜雄一电警棍电断他的狗腿!”
小村老少听到这,都扑嗤笑了:“老爹管得真宽!”
阿嘎姥姆
阿嘎姥姆开了个饭店?!
小村人笑得前仰后合眼泪像核桃花一样落。
谁去吃她屎爪子抓出来的饭菜?
阿嘎姥姆也是小村的“拉罗巴”彝族本家人,住在村西头大麻栗树疙瘩下花椒箐里。
小村人曾把阿嘎姥姆称为婶,那是在她刚结婚的时候。
一年后,他汉子见她肚子老瘪着,就醉熏熏唱了调“向阳桃子背阴梨,湿处核桃热处桔;四季握你不挂果……”之后,便闹了离婚。
小村人不再把她尊称为婶。“她不配!”小村人都这么认为。
阿嘎姥姆不会生育,全村人都把她改称作 “漂沙人”。
阿嘎姥姆开了一个饭铺。
阿嘎姥姆开饭铺?!小村人笑得前仰后合,直到笑出了眼泪还在笑:哪个傻蛋会去吃“漂沙人”屎爪子抓出的饭菜?!
一日,阿嘎姥姆的前汉子卖完菜,灌了壶酒唱着“太阳落坡山背黄,豹子下山咬小羊,咬猪咬羊只管咬,莫咬我的小情妹”、“左脚一搭右脚上,好像蝴蝶戏牡丹。绣花枕头郎不靠,专靠阿妹手弯弯。一更赤龙下海岛,二更白虎在山朝,三更鸳鸯对舞好,四更蝴蝶绕花梢……”的山歌从阿嘎姥姆铺子门前经过。
阿嘎姥姆的前汉子也住在小村,也是小村人。他甩了阿嘎姥姆后,讨了隔村的狗花做婆娘。狗花嫌他又懒又贪吃喝,骂他“一夜说得胡子嘴,天亮还是光下巴……有钱能使鬼推磨,还有懒鬼不爱推”。于是跟他离了。
阿嘎姥姆的前汉子在小村,可算个人物哩!他会掐八字择吉日祭神送鬼,村里小到劁猪骟狗大到结婚抬死人都离不了他,都得求他。每出台一回,一只鸡一壶酒一升米,一把盐一串辣子稳拿了。汉子倒也生活得有滋有味,像个“半神仙”。
“三穷三富不到头,九转十八不通头”。土地下放到户后,小村的人渐渐不再来请他,再不管什么吉不吉利了。
“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小村这群没心肝的坯子!没老爹我给你们看的好地基,没老爹我给你们掐的好八字,没老爹我给你们择的好吉日,你们哪来的好日子过?!”阿嘎姥姆的前汉子时常这么愤愤地想。
小村虽然还有几家仍尊他为“神仙”,但东西拿来的越来越少。他的日子实在“有了筲箕无笊篱”过不下去了,种田种地酸筋痛骨三天两病的,做生意又没本钱,最后只好拣了个“种着河边田,图个手不闲。收成有不有,不必挂心间”轻便活儿——种菜。
每逢街天,他打早鸡叫头遍走起,把菜背到蛇街卖,卖完菜后称米称盐称油,整半斤蛇酒回来。
阿嘎姥姆见到她的前汉子,热情地和他打招呼:“阿山哥,进来歇一下咯”。
老爹一听得这声甜甜的喊,纳闷了。心想,二十几年了,狗日的婆娘还从未叫过我一声哥呢,就在同房时也不曾这么亲热地叫过!今个咋啦?
他混想的当儿,阿嘎姥姆又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他乐了,心想,这 “漂沙人” 是不是想复婚哩?他用那双死鱼眼盯着她,心里一喜:贼婆娘没生过娃,还嫩着呢!
“阿哥,今个生意咋个些?”阿嘎姥姆满眼含笑地问他。他连答:好!好!
阿嘎姥姆招呼他坐下后,端了一大碗猪肉坨子和一大碗酒摆在他面前,催促着:吃,快吃哩!
他望着肥滋滋的一大碗肉,馋得口水沥沥啦啦直往下掉。他迟疑着不肯下筷子,心想:这菜钱可是大爷我一个街子的口粮哩,一顿吃了不成。
吃呀阿哥!阿嘎姥姆见他迟疑,又甜蜜蜜地叫了一声,随口唱了一调:“太阳落了有月亮,姊妹黄昏好粘连;妹是一只无窝鸟,阿哥怀里先歇歇。”他心底一乐:看来钱不用付哩。
他大口大口啃起肉坨子来,满嘴巴油。他一面啃,一面乐滋滋地看着阿嘎姥姆,暗自得意:这《三世演禽婚姻簿》真格应验了,大爷我老来有福,“天上孤单是月亮,地上孤单我一人”、“一只筷子难夹菜,一个漏碗难装汤”,大爷我孤苦生活就要结束了。嘿嘿,说不定“漂沙”还不“漂沙”了哩!这回复后要对她好点,再不懒,再不贪吃贪喝……
酒至半酣,他“啪”一声砸碎酒壶,对天发誓:“火烧芭蕉心不死,我……我从此不再吃酒贪懒……我阿……阿山对不起你……我不是人……”阿嘎姥姆看着他发红的双眼,心里一颤,倏地变了脸色:“猪心猪肝街上卖,人心人肝各自带。阿哥,人活着为哪样?不吃不穿,钱往那撂”?
他更乐了。这贼婆娘真会体贴人,我阿山真个老来有福了“大河涨水小河清,不知小河有多深。拣个石头试深浅,试妹真心不真心?”……
正这么想着,突然黑云翻滚,旋风阵阵,风雨欲来。
阿嘎姥姆一面收碗收筷,一面看着天自语:“蚂蚁赶街,老天变筛,天快黑哩,要来大雨了”。
他暗自道:人家在暗示哩,再不走又要遭小村这帮浪娘胡猜哩,“刀尖头上舔蜜吃,尝倒尝得要小心”走走走……
阿嘎姥姆见他站起身,不紧不慢地说:阿山哥,菜钱五块,酒钱八毛。
轰——
一个雷在屋顶炸响,震得他摇摇晃晃,酒全醒了——
“做梦跌深谷,马骑骡子上大蛋了!”。
“黑山神”得旺
小村有个混汉,矮矮胖胖墩墩实实,满脸皱纹填满污垢,裤腰斜系一根大拇指粗的从旧马鞍上割下来的皮条,整天敞开肚皮,露着黑漆漆的圆肚皮,见人便满脸嘿嘿堆笑“阿老友、阿老表”地叫个不停。小村村中央一路的牛屎马粪路上,数他吹牛吹得最过瘾,就他讲得最天花乱坠。他有本事把自个年轻时渴急了扑母牛背的丢人事也讲得津津有味,也有本事把别家媳妇与野汉在野外瞎搞的事编得有声有色具具体体。得旺最大的本事是淌着口水眯眼,吹嘘他昨晚梦见挖到金山掏着了银窑骑着大红马做了县太爷,然后嘿嘿一脸傻笑……
这混汉叫得旺,自小聪明又机灵,四岁就能吹白话唱调子。坏就坏在那年的一天,小村来了个算命先生,得旺妈领得旺去算了一卦。算命先生闭眼掐指节一算,突然伸大拇指赞叹:“此娃乃大贵之命,成人必当大官!”从此,得旺便洋洋得意地不学好,东家诳西家诓,“以后长大当官我罩你!”成了他的口头禅。从此他充当娃娃头到处骗吃骗喝欺负别的村里娃。小村人处处让着捧着得旺,父母也惯着他。得旺越学越坏,上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小学未毕业就跑回家“等着发迹当官”。辍学回村的得旺更野了,搅得小村鸡飞狗跳。得旺父母便早早给得旺娶了亲,巴望媳妇管住得旺。无奈得旺铁了心硬了肠仍恶性不改,整天游手好闲吊儿郎当,饿了偷缺了拿,回家还拳打脚踢冲媳妇发气发火,最后气死了老妈气疯了老爹,以后得旺更没人管了,也更野狂了。
小村人对得旺忍了又忍,怕的是得旺时来运转当官,二来是大家都是血亲家族谁也下不去手,再说得旺这小子脸皮厚人也尖,偷小不偷大,摸黑不摸明,捉到也不抵不赖嘿嘿笑着讨好,甚至一把鼻涕一把泪乞求“都是你家侄饿坏了,被逼得没法了!”事主也只能发善心让得旺把东西带走。全村人只好整日整夜提心吊胆守好自家东西,不让得旺偷到。得旺虽然过得窝囊,但也和村里人相安无事多年,这让整上二两小酒后的得旺有时还自鸣得意。
可有一件事把得旺弄臭了,令得旺虱叮虫咬着实坐立不安慌了几日。就在那年的秋收时节,也亏得旺这混人穷急了想得出,跑到远村大姐家借驴,谎言洋芋大丰收背不完,借姐家驴驮几天,还驴时顺便驮驮洋芋给姐。大姐不在家,大姐夫听了很高兴,舅子终于出息了便爽快地把驴借给了得旺。可日子过了几天又几天仍不见弟弟还驴。阿姐便买上一包糖来到得旺家。得旺这混人一见姐就笑哈哈跑出大门满嘴“阿姐来了噶?阿姐辛苦了!”热情地把大姐迎进家门,乐得阿姐甜滋滋提不起半个驴字。第二天临走,阿姐才说明来意。谁知得旺这混人说:“阿姐你说哪样?说什么说!我什么时候拿了你的驴?从你左手里牵过驴绳还是从你右手里牵过驴绳的?”气得阿姐气都缓不过来。阿姐哭嚷嚷跑到村长家,请村长评理解决。村长说:“我确实没见过得旺牵回家什么驴”。最后,得旺姐夫也赶到村长家。村长又说:“谁不知得旺是块又臭又硬的厕所里的石头?人穷得不疼不痒,要说要劝的我早说早劝过了。得旺听进去了半句?要叫得旺赔?一间烂草房摇摇欲坠,全家吃了上顿没下顿,拿什么赔?再说你们血亲姐弟……”气得得旺姐哭哭啼啼不肯善罢甘休又跑到派出所告状,值班民警和蔼地劝得旺姐:“大妈,算了,得旺的情景你又不是不知道,怎抓?”
“告就告吧,抓就抓吧,我巴之不得,坐牢有什么不好,不愁吃不愁穿,不用再为一家老小七八口奔忙口粮,抓?嘿嘿……”
隔村阿狗证实,得旺在路上把驴卖给了四处串门买牲口的汉家老表,可得旺抵死不认。自此,小村人冲得旺脸黑心黑私下把他称之为“黑山神”。“黑山神就黑山神,有什不好,山神不消为吃为住发愁,多自在!嘿嘿……”
小村人有些容不下得旺的无赖行为……
村长便硬着头皮去劝得旺开块山地种点荞豆,好好养家活口。得旺这混小子竟不识好人心,嘿嘿两声冷笑“有福之人你莫忙,无福之人跑断肠”末了痛骂村长看不起他嫌弃他欺他穷,唬得村长一拖烟杆就跑。说来也巧,那年秋天,得旺孤寡老舅放羊砍犁弯掉下老鹰岩去世了。得旺作为小村唯一的财产继承人接收了老舅家的荞地和羊。得旺还四处吹嘘:“噶是我就说了有福之人你莫忙?!”
这可真激怒了小村人,借姐家驴抵赖、捡老舅家荞和羊还洋洋得意,这可把小村有良心的有识之士的肺泡全气炸了,小村人再容不下这号人了,先前怕得旺当官报复,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得旺都快四十岁了,“那鬼算命先生瞎说,怕个球,好好收拾不要脸的黑山神!”
“好嘛,试试看嘛,你们敢收拾我,老子先下手为强!”得旺竟把老婆拖到村口,吊在村口的大青树上毒打,向全村人示威“收拾黑山神的神圣还没在小村投生!”得旺骂个不停。第二天得旺老婆趁得旺不在家,牵着娃背着娘家陪嫁的嫁妆哭哭啼啼回了娘家。得旺回来可不得了,跳跳脚抄起自家扁担满嘴山东话直奔岳母家。这天正好岳父和岳哥帮人家杀年猪,岳母家只岳母和得旺老婆在家。得旺一冲进家门便揪住老婆左右五六个耳光,又一巴掌打得前来助战的老岳母满嘴血水跌倒晕在地。得旺骂骂咧咧把老婆扭翻在地,一个纵步骑在老婆身上拳打脚踢一顿毒打。打够了,还尿了泡尿在老婆身上。得旺老婆鼻青脸肿一时气窍堵塞,昏倒在地上。得旺发泄完怒气,抽支烟,见老婆倒在地上不哼不喘气了,便摸了摸鼻子,没气了。回头一见岳母倒在血泊中不动不扭,吓得脸倏地煞白,一个雀跃奔出了岳母家门,一路恐恐慌慌跑回了家。得旺这混汉这回真慌了急了,杀人赔命,人头不保了。得旺大汗淋淋裤衩湿透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得旺认为这回死定了,没救了,玩完了。越想越恐惧,最后便呜呜哭着脚抖手抖找了根麻绳吊在自家草房梁上一命呜呼。弄得一时休克又活过来的得旺老婆又哭天喊地连夜回家披麻戴孝葬得旺,得旺的几个娃哭着喊着扯着阿妈的裤脚要阿爸。
得旺死了,小村人又悲又喜,悲的是小村人志志气气、清清洁洁活了七八代,竟出了个欺公灭祖、臭名远扬的偷鸡盗狗的无赖,还是个吊死鬼,败坏了小村风清气正的风水,全村人也可怜得旺老婆和孩子。喜的是这早该天收的背时鬼终于不会再行凶了,小村又恢复了平静……
小村人一直赞成把得旺葬在全村人放牛、砍柴、上学、赶街上路就能一眼看到的路边土包子上,好让全村人世世代代记住,不能听信算命先生的话,不能好吃懒做偷鸡摸狗,不能……
从此,小村牛屎马粪路上大白天吹烂牛的懒鬼渐渐少了,村里什么鸡啦瓜啦蛋啦核桃啦也不再莫名其妙丢了。
编辑手记
读只廉清的小说,有一丝欣喜。作者扎根乡土,汲纳民间文化,将民间的语言,民间的山歌小调,自然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叙述风格。同时,乡间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这种植于泥土的写作方式值得大理写作者借鉴。
责任编辑 杨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