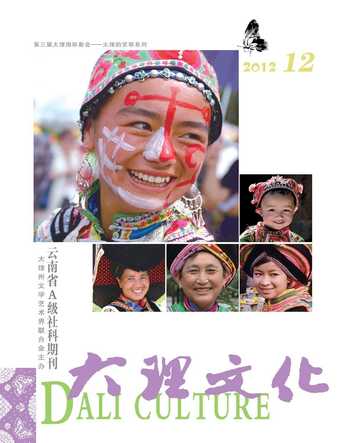对故乡一条河的近距离表述
李智红
“无论你走到我故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听到人们谈论这条河,就像谈到他们的神。”
——于坚《河流》
一
在遇见了许多诸如长江、黄河、澜沧江等著名的河流之后,我才知道,故乡那条名叫板桥的河流,实在算不上是一条真正的河流。因为它太缺乏真正的河流所必须具备的那种磅礴与深远,那种荡气回肠的流淌与喧哗。它实在只能算是一条小溪,一条非常普通,非常平实,充满着柔弱与随意的,小小的溪流。
它所流经的地方,也多是一些通俗而浅显的山谷,再就是一些平淡无奇的田畴与村庄。然而,在我的故乡,在我的童年,在滇西大高原深处那个名叫初一铺的小山村,在所有至今依旧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父老乡亲的心目中,它的确是一条真正的,无与伦比的河流。一条与衣食住行,与春种秋收,与繁衍生息休戚相关的,生命的母亲河。
板桥河作为故乡唯一一条有代表性的河流,它的来临和消亡,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一种浓郁的宿命意味。它任何形式的流动与喧哗,都早已深深地介入了故乡所有人的日常生存状态。以致它每一次小小的涨落,都会使得世代生息于这块艰辛而又贫瘠的红土地上的人们感到揪心。不过,在我的印象中,板桥河的流淌一直充满着一种少见的沉着与平稳。无论春夏秋冬,它总是那么的宁静,那么的平实,像一篇古老的寓言,像一个清远的童话。即使是在那些暴雨如泼的日子里,板桥河依然是理智而又仁义的。河流两岸那些葱郁的森林,像一排排忠诚的绿色卫士,经年守护着那清清的流水。每一个故乡人心里都明白,板桥河是关乎整个村落兴衰存亡的命根子。因而,从未有谁动过河岸上那些森森古木的邪念。
在我的记忆里,板桥河还从未有过哪怕一次小小的泛滥,也从未吞噬过任何一个落水者甚至一条狗,一只鸡。只是在雨季来临的时候,河水有些泛黄。一种淡淡的、玉米色的金黄。不过,这样的情形持续不了多久。一年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板桥河的水流都是清澈的。清澈得让人心情愉快,清澈得让人一眼就能透见河底那些五彩的砾石,那些细腻的流沙,那些永远也长不大的丁丁鱼和大丛大丛翡翠似的水芦子。这种近乎童贞的清澈,很容易便让人联想到时光深处某些早已被我们渐渐淡忘的,美好而又朴素的东西。
在我曾经谋事供职过的永平县城,也有着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那日渐消瘦的河床,那不舍昼夜的流水,都远比我故乡的板桥河要气派许多。小城人都习惯叫它银江河,很是引为自豪。不过,打我1986年进城做事的那天起,就未见过这条先前曾倒映过夜月晚翠,倒映过楼阁亭台,素有“烟柳十里映城廓”之誉的河流,有过真正清澈的时候。一年四季,河水中总是漂浮着诸如破鞋、废塑料、避孕套、烂布头以及死猪死狗一类臭气熏天的物件。大城市的小河沟下水道中有的玩意,这条河中一样应有尽有。在尚未完全整明白工业文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的小城人,懵懂中便已经开始在无奈地品尝工业文明中最苦涩的那一部分。而且,就现在的污染情况来看,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让银江河重现我故乡板桥河那种刻骨铭心的清澈,对所有的小城人来说,当下还只能是一种诗意的梦想。因为有半数以上的小城人,至今依然津津有味地沉湎于他们丰沛的物质追求和肉体的享受,而对生态环境的一些基本概念,也茫无所知。好在最近县委、政府已经响亮地提出了一个建设“水乡永平”愿景和理念,想来会在一定程度上使这条河的面貌有所改观。毕竟,一个城市的灵气,是需要清澈的水流来丰润,来滋养的。
在离我当下上班的地方不远处,也有一条名叫沙河的小河,三十多年前,我曾在这条河畔的沙河埂一号,与于坚、刘克、吕二荣等一大群诗歌的朝圣者,用几个昼夜在谈论诗歌以及与诗歌相关的诸多话题。那段值得记忆的岁月所衍生出的精神,曾鼓舞我在诗歌的领域,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坚守。前几天,得空又去看过这条河流,满眼是污物与泡沫,一种腐朽的气息四处弥漫,昔日流水清清的沙河,已经是一条濒临死亡的河流。心情极坏,便时常悬吊吊地怀念起故乡的板桥河,怀念起它那清碧得彻心透肺的浅浅流水。尽管无论从气势到内涵,它都只能算是一条小溪。它所发端的挂红山,在永平众多的高山峻岭中,不过是一座极其平常的小山岗。尽管从挂红山到澜沧江的八十多公里流程间,板桥河便完成了它充满烂漫意味的流淌与跋涉,并最终成为澜沧江众多支流中最卑微最纤小的一脉,但我一样认为板桥河的魅力是无可替代,无可比拟的。这除了它曾启蒙了我最初的,关于诗歌、关于爱情、关于远方、关于美的许多梦想,并最终引领我沿着它清清流水的走向,走出大山,走向另一个比故乡更为广阔,更为丰富的五彩世界外,还在于它在千百年的时光里,始终在用它那细小的血脉或者乳汁,浇灌着故乡那近三万亩的良田沃野,使得我故乡那近五千口的父老乡亲,最终得以安居乐业,衣食温饱。并轻松地品尝到了生活中最可口的那份醇厚,那缕芳香。
二
今年的冬天干燥而少雨,故乡的板桥河比起往年,似乎又消瘦了许多。
板桥河是我生命中一条极其重要的河流,它几乎贯穿了我整个的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我无法准确地描述它在我降生人世以前,那久远的流淌与喧哗,但自1963年那个极其平常的冬天,我像所有贫寒农家的子弟一样,不声不响地降临到这个纷繁的世界之后,40多年来它便一直在我的生命中随意而温润地流淌着。并始终在以一种平静的方式,翻腾着它细小的浪花,挥洒着它朴素的喧闹。
2012年春节来临的时候,我乘休假回了趟老家,我对送行的友人说:我想念远在乡下的兄弟和老家的板桥河了,得回去看看。朋友开玩笑说,看父母情有可原,但一条普通的河,有什么看头?我说,板桥河可不是一条寻常的河,那是一条贯穿我生命的,美丽而宁静的河。板桥河对我而言,仿佛是一脉永远也难以割舍的血缘,始终在滋养着我的心性,哺育着我的灵性,给我以生存的力量,给我以生命的抚慰和温暖。
在回家过年的那些天里,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便是独自一人到板桥河边去,寻一棵古迈的老柳,背依着苍老而敦实的树干,静静地独坐着,任凭思绪信马由缰地飞扬。
那些天,板桥河一直美好地沉浸在晴朗的天空下面,像一匹轻柔地铺排开来的,透明的丝绸,清澈得让人感动。在明媚的阳光下面,河水中那些五彩缤纷的砾石,非常安静地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泽。再经过几缕翠嫩青苔的烘托和点染,更显现出了板桥河那种少有的清丽与净洁。
我一直在揣想,板桥河那清冽的流水中,一定隐藏着一条通往旧时光的路。
板桥河与其说它是河,还不如说它是一条真正的小溪。它的源头离我的老家并不遥远。我曾逆流而上,抵达过它真正的源头。那是挂红山的浓绿深处一个不起眼的草甸子,草甸中长满了半腰高的顺水柳和零乱的三棱草。在那些绿色的草甸深处,到处是细细密密的泉眼,每一眼都很细小很瘦弱,只有麻线那么粗。但就是这无以数计的泉线聚合到一起,才造就出了这条美丽而又温顺的河流。
板桥河上的唯一建筑,是一座古老而破旧的水碓房,那是我外公捐钱为乡亲们修建的。外公去世许多年后,那水碓房还在。记得小时候时常跟随大人们一道去舂米,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石臼窝,一只笨重的铸铁杵锥,杵锥的根部开凿了一个深深的木槽,槽口正对着木板镶成的“水溜”。当飞梭而下水流灌满木槽时,杵锥便会高高地扬起,将木槽的水倾倒而出,杵锥便“扑通”一声捣入臼窝。如此反复,便会捣舂出白花花的大米。不过,水碓房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年一度的“舂粑粑”。过大年的头两天,即便生活再困难的人家,也会毫不吝啬地选上几斤上等的白米,用开水涝过,再放入甑子蒸个半熟,然后挑到外公的水碓房来舂。舂成面团状后,便拿回家去“拓粑粑”。记得奶奶最喜欢用一块雕刻有各种古朴图案的栗木模子,拓压出各种形状的粑粑。有鲤鱼状的,有蝴蝶状的,有元宝状的,有菊花状的,也有各种各样的生肖图案。粑粑拓好后,还要用鸡毛蘸上各种食用颜料,细细地画描。那可真是一件件古朴的艺术品,那么拙朴,那么随意,却饱含着许多与丰厚的民俗文化相关的诸多元素。
近一两年,碾米舂粑粑都早已被机械所替代,水碓房也早已成了一片荒草萋萋的废墟。但我每次回到老家,都要到水碓房的遗址上看一看,坐下来,吸上一支烟,回想那些曾经的恬淡,寻找岁月不经意间滞留下的点点痕迹。
面对着那一截残垣断壁,我像是感受到了一种过程,倾听到了一种回声。我喜欢看那半截残破老墙在夕阳下的剪影,油画般浑厚而神秘,沉寂而静穆。它就那么褴褛地横迤在板桥河上,像一位饱经沧桑,饱经世故的老人,真实而又满足。
板桥河是故乡一条唯一的河流,它从大山深处流淌而来,又幽幽地流向遥远的大山深处。它仿佛只是一个行色匆匆的过客,故乡只是它漫长的苦旅中一个小小的驿站。但它所给我的故乡带来的,远非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它为我们带来了绿荫,带来了恩泽,带来了收获与希望,也给我单调的童年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为我的成长,为我走出大山,给予了许多有益的滋养和启迪。以至在离开故乡许多年之后,在一座遥远而喧嚣的城市,我依然能够清晰地倾听到它昼夜喧哗的,朴素而清凉的水声。
三
许多年以来,故乡的板桥河一直非常宁静地在滇西高原的群山和草甸之间,优美地徜徉,悠闲地漫步。
暖暖的阳光,非常随意也非常亲切地洒满它清冽的河水,把它装饰成了一条波光粼粼的,流金泛银的河。一年四季,河岸边总有大片丰茂的水草夹杂着浪漫而朴素的野花,把宽广而平坦的河床,装饰成了一条生机盎然的彩色飘带。尤其是春夏两季,河岸边更是绿草蔓长,嫩叶婆娑,自然成了故乡一个天然的,丰肥的牧场。
在我的印象中,板桥河不但是一条充满着童贞意趣的河流,还是一条生长佳肴美味的河流。
我从六岁开始,便与板桥河契结下了割舍不断的情缘。
记得那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常赶着家中的牛羊,到河边放牧。牛羊们很省心地在一旁美滋滋地咀嚼着肥嫩的水草,我们则一个个脱得溜光,整天浸泡在清冽的河水中,摸鱼、游泳、打水战。
那时节的板桥河还不像眼下这么寡淡,河里有许多的鱼儿,多是那种又嫩又鲜的细鳞鱼,每条都有半斤多重。我们捉那鱼儿的时间久了,便有了经验。与伙伴们用手一围,鱼儿便慌慌地钻进了石头窝子。伸手一逮,每次都能逮住个一二条。捉到鱼后,便顺手在河边扯根水杨柳穿了鱼鳃,放养在岸边的浅水塘里。等大家都玩耍得累了,便捡一堆碎柴,在河滩上燃一堆篝火,然后就着彤红的火炭烧烤鲜鱼。那肥嫩的鱼儿,用火一烤,便滋滋地往外直冒油花。抹上偷偷从家里带来的椒盐,然后与伙伴们一道赤条条地围在篝火边,就着烤鱼啃那从家中带来的苦荞粑粑。一个个全都吃得大汗淋漓,眉飞色舞。那烤鱼的滋味着实甘美,许多年后回想起来,我依然忍不住会馋涎欲滴。
板桥河里有许多种石蚌,我们都按老习惯叫它“石鸡”。它们的样子与青蛙很相像,但个头比起青蛙要大许多。三角形的头,鼓鼓的金鱼眼,脊背上的皮儿青中泛麻,肚皮却白里透灰。样子虽然生得丑陋,但肉质细嫩。特别是那两条粗壮结实的肥腿,整个一坨脆生生的好肉。
阳春三月是捕捉石蚌的大好季节,我们叫“打石鸡”。选个月明星稀的好夜,打理好一竹篮松明火把,再预备上两根四五尺长的细铁丝,邀约上几个小伙伴,便可从家门口一直向着板桥河的源头捕捉“石鸡”。天刚擦黑,那些石蚌便会迫不及待地钻出洞穴,蹲伏到岸边的石块上或浅草丛中捕食飞虫。逮石蚌得讲究手疾眼快,反应敏捷,还要胆大心细。我天生胆小,老是害怕碰到水蛇,反应又迟钝,所以从没有享受过亲手逮石蚌的快乐。在“打石鸡”的队伍中,我每次都是负责火把照明,逮石蚌的差使,全由那些胆子周正,机灵敏捷的小伙伴担当。亮亮的火光下,看准了石蚌蹲伏的位置,便迅速出手,一把将其逮住。然后用铁丝穿了嘴壳,拎在手里。这东西鬼精得很,出手慢了,让它溜进了深塘,那你纵有三头六臂,也奈何它不得。只要一二公里长的河道,便能逮住百十来只。拿回家用开水一烫,去了皮和肚杂,便是一道上好的大菜。无论炒、煮、蒸、烧,都是上上的口味。不过,我更喜欢另外一种吃法,那也是我母亲最爱做的一道拿手好菜。把剔了骨的石蚌肉与火腿或鸡蛋一起宫爆,有时也用它来清炖一种叫马蹄香或手帕果的草药,母亲说这种吃法能补气提神。
板桥河中除了生长细鳞鱼、石蚌两大美味之外,还生长爬沙虫和水木耳等许多同样著名的美味。
爬沙虫是书本上的叫法,我们都叫它们盘冠虫。这种两寸多长的虫子皮肤黝黑,嘴巴上长着一对锋利的甲子,喜欢生活在河水中那些大小不等的石块下面。每到逮爬沙虫的深秋季节,我和伙伴们总是一边玩耍,一边翻起河水中的石块,捕捉那些早就养得肥肥胖胖的爬沙虫,捞捡那些在碧绿的水波中晃来荡去的,晶莹剔透的水木耳。
爬沙虫用滚水涝过之后去掉苦皮油炸,水木耳淘尽泥沙后再佐以辣椒、酱油、姜末、葱花凉拌,不用说,自然又是一道美味可口的好菜。
对故乡而言,板桥河是故乡笃实的农事耕作中一条极其重要的河流。可以说,故乡每一寸土地的丰产或者欠收,都与板桥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于我而言,板桥河则是一条充满童趣的河,一条寄托梦想的河,一条浪漫而神秘的河。我整个的童年,都与板桥河的流淌与喧哗紧密地契合在一起,融会在一起,交织在一起,以至在我离开它20多年之后,它那久远的清澈,它那殷实的富足,它那深厚的朴素与宁静,依旧在我的记忆中,清晰地呈现着,诗意而深远。
责任编辑 彭琼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