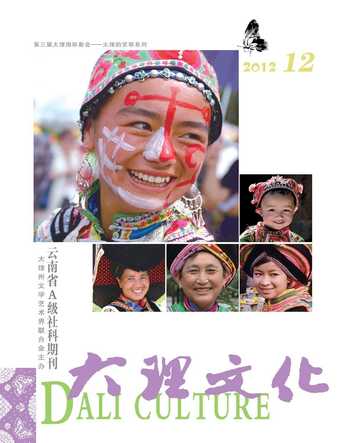小舅
张旗
小舅今年八十岁了,我还是喊他小舅。他年轻时赶马,吆牛耕田,一生都和牛马牲口打交道。现在家里买了微耕机,买了客货两用的皮卡车,不养牛也不养马了,小舅也老了。
母亲去世时还牵挂着小舅,嘱咐我要常常去看看他。母亲去世已经十六年了,每年的中秋节、春节,我都去看小舅,年年都去。
小舅说,我日子过得好好的嘛,你不用来看我了。
我说,我还要来的,看到你,我就像看到我的母亲。
小舅双颊下陷,颧骨高耸,寿眉低垂,眼边的纹路多如皱纸,浑浊而迟滞的目光中,透出苦难的命运塑造的乐观与豁达。他是母亲的幺弟。他们兄妹三个,母亲的大哥,我的大舅和母亲,都先后去世了,只有小舅还活着。看着这个佝偻的躯体,我总有一种来不及的焦虑,那模糊遥远的岁月,还有与之相关的历史,终将有一天会随着这个人的逝去而消失。
小舅是读过书的。小时候,有一次,我和母亲回外婆家,小舅一见我,劈头就问:“七文铜钱挂两边,一边挂几文?”我说,一边挂三文半。小舅不说对,也不说不对,只是笑。下次见面,小舅照旧还问我:“七文铜钱挂两边,一边挂几文?”想起上次我的回答,想起小舅那不明不白的笑,我就赶紧说,一边挂四文,一边挂三文。谁知小舅仍然只是笑,仍然不说对,也不说不对,给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那时候,我最喜欢和小舅在一起,喜欢听他讲故事。外婆家有一个果园,就在纳溪河边。我常和小舅去纳溪河边放牲口,到果园里去玩,就央他讲故事。
小舅讲的故事里,最好笑的是猪八戒过“稀屎河”。我后来看《西游记》,才知道猪八戒过的是“稀柿衕”,根本不是什么“稀屎河”。不知小舅为什么要那样讲,是不是他有意要戏说搞笑逗乐呢。小舅还给我讲过什么杨状元的故事,讲过慌张三的故事。这是些流传在我们当地民间的故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杨状元,就是明代的文学家杨慎,就是《三国演义》开篇那首著名的《临江仙》词的作者。这位状元公,当年在朝廷上因直言敢谏,忤逆了皇上,获罪被“下放”到云南来,在云南当了三十多年的“下放干部”,最后客死云南。有人还说,他到过我们宾川的鸡足山呢。慌张三则是个类似阿凡提的机智人物,或者说,他就是一个“云南版”的阿凡提。
在村里,小舅也算得上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了。土改那年,果园里的橘子卖不掉,果园分给贫雇农,都没人要。大舅和小舅赶了两头骡子,和别人搭伙,把自家果园里的红橘驮到昆明去卖。大舅去了一次,小舅去了一次。橘子是自家的,一头骡子是自家的,另外一头雇了别人家的,不计什么成本了,兄弟俩权当自费去逛了一趟昆明城,卖橘子的钱都用来做了开销了。我问他,赶马到昆明,要走几天。他说要走七八天呢,一去一来要半个月。那时候,通宾川的公路还是土路,一到雨季,公路就被山洪冲断了,跑宾川的汽车很少。汽车还有烧木炭的,一辆车上路要两个驾驶员,跑一趟昆明要两三天,一个来回要四五天呢。爬那个祥云飞天坡,哼哼唧唧老半天,挣不上去了,抛锚了,那个副驾驶得连忙跳下来,把个三角木塞在后轮下垫好了,让汽车歇会儿气呐。上到坡顶,要歇两三回。大舅小舅赶牲口上昆明卖橘子回来以后,外公也雇了一辆烧木炭的汽车,上昆明去卖了一趟橘子,逛了一趟昆明城。那时候,上省城去一趟多不容易哟。
外面的世界在不断“提速”,生活节奏,新农村建设,包括汽车的速度,小舅并非全然不知。但当我告诉他,现在到昆明去,高速公路,坐上车三四个小时就到了,他还是吃了一惊:“啊!是吗?”
小舅爱看书。我还记得,那次他从昆明买回来的两本书,一本是《李家庄的变迁》,一本是《新儿女英雄传》。还给我买了一个小皮球,上面有红一道绿一道的花纹,可稀罕了。那时,我们小孩子玩的是泡球,是把一团烂棉絮,用麻线一道道绑紧扎起来的泡球,任你使劲拍也跳不高的。在院子里,在打麦场上,我们拿着泡球,你抛过去,我丢过来,你抢我夺,追逐嬉戏,还真好玩呐。所以,我说不上来,到底应该叫它泡球呢,还是叫它抛球?拿着小舅买的小皮球,我像拍泡球一样,使劲一拍,咚!一下跳起来砸在我的鼻梁上,吓了我一大跳。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去看他,除了带点糖、茶、酒,总要找几本书带上给他。有一年,我在大理街头逛旧书摊,看到一本什么人整理出版的《慌张三的故事》,喜出望外。我知道小舅喜欢这个慌张三,书虽说有些破损,还是买下了,去看他时带去送给了他。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把书拿在手里,一边翻看,一边喃喃自语:“哦哟,慌张三都写成书了!”
我一生喜欢看书,喜欢文学,说起来就是小时候受了小舅的影响。老话说,外甥多像舅,这话还真是不假。
父亲去世那年,我在城里办丧事,他到我们家里来住了两天。我让他睡在我的书房里。我看他脚上只穿着套鞋,没穿袜子,出去买一双递给他,说什么他也不要。他说他穿不来袜子,说他一生赶马吆牛,泥一脚、水一脚的,一会脱,一会穿,麻烦。土改那年冬天,我在他们村里上小学。一天早晨,我去上学,那正是寒冬腊月间,路旁水沟边的草地上,马牙霜白花花的。我亲眼看着,小舅提着一把板锄,鞋子一脱,挽一挽裤脚,咚的一声就跳进了水沟里,捞水里的泥巴,堵塞水坝,拦水泡甘蔗。一进腊月,甘蔗就要砍了榨糖了。这一声刺耳的水响,当时给我的感觉,就像有人拿竹签在我的身上猛地扎了一下,啊啧啧,我浑身一激灵。
宾川的冬天是不结冰的,田坝里只有大白霜。俗话说,“冬至前后,冻破石盐臼”,即使是在这个最寒冷的日子里,水沟里、池塘里、河里也不结冰。那年冬天,在外婆家里,小舅却让我第一次看到了冰。
漫长的冬夜,火盆里拢着煤炭火。外婆一家,四代同堂,一大家子人常常围着火盆,坐在草墩上向火,吃橘子,吃甘蔗,说些家长里短的闲话。火盆的三脚架上,支着一个祥云土锅,冬至刚杀了年猪,煮着肉。记得那天夜里,小舅拿着一个土巴碗,里面盛了大半碗水,水里放了一小截外婆纳鞋底用的麻线。他神秘地对我说,明天早上我让你看一样东西。他小心翼翼地端着那碗水,从楼上爬到屋顶上,把水碗搁在屋脊上。不知他耍什么把戏。第二天一大早,他给我看那个从屋顶上拿下来的土巴碗,像变戏法一样,把那截麻线一提,从碗里提出一坨亮晶晶的东西,像冰糖。小舅说是冰,不是冰糖。他让我拿手摸一下,我一摸,冷得扎手,又拿舌头舔了一下,果然不是冰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冰。
半个世纪后,当我读到《百年孤独》开头那个经典的句子:“很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我就想起了小舅让我第一次看到冰块的那个遥远的早晨。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我从课本里知道冰是怎么回事,却不知道家乡这个干热河谷地区,冬天的夜里也会出现冰点温度,时间虽然不长。小舅给我看的冰块,就是在那样的夜里,把一碗水放在屋顶上冻结成的。
每次去看小舅,他都要在堂屋里的火盆里烧起火来,从院子里的水井里提一桶水,灌满一铁皮壶,放在火盆锅的三脚架上,烧着水,然后把个烧得浑身发黑的陶土茶罐放在火炭上烤热了,放上茶叶,轻轻地上下抖动,边烤边抖。待铁皮壶里的水烧开了,茶罐里的茶叶烤得差不多了,冲上开水,茶罐里即刻发出一阵扑噜噜的声响,水泡冒起,带着茶叶末子潽出来,顿时,满屋子弥散着茶香。小舅把他炮制的烤茶戏称为“百抖斑鸠茶”。在一个白瓷茶杯里,他给我倒上小半杯。烤茶汤色浓酽,咂一小口,茶香一下子就咬住了我的舌尖,久久不放。他只给我倒两次,每次只倒小半杯。他还是依那个古旧的乡村风俗,忌讳倒茶倒满了杯,所谓“茶满欺人,酒满敬人”。给我倒了两次茶后,他就不再倒了,要吃就自己倒。小舅说,一杯是品,二杯是饮,三杯呢,他说得很难听,是牛饮。说归说,每次我们甥舅俩边说闲话边喝茶,谁知道喝了多少杯!
那次从城里回去后,他曾对我说,你们城里人过日子不容易噢,吃菜没块菜地自己种,要出钱买,吃水要出钱买,连上个厕所也要出钱,哪来那么多钱呵!还有,你们用电用煤气,煮的饭菜没有烟火气,不香。我听他讲,心里酸酸的,不好对他解释什么,只好赶紧把话题岔开,说他最近看的那些书里的人和事。其实,他家里也是用电的,也有电灯、电视、电冰箱,他也在电灯下看书,也看电视。现代文明他也并非全都拒绝。只是他不让家里人用电饭煲、电磁炉煮饭做菜。理由就是,没有烟火气的饭菜不香。
小舅从来不抽纸烟,遇到有人递给他一支“红河”,甚至一支“云烟”,他连连摇手,说我只吃老草烟,纸烟吃不来。又指指自己的喉咙,说吃上四五锅纸烟,这里就有口痰。他不说抽烟,他说吃烟,也不说一支烟,而是说一锅烟。他还用着一杆草烟锅,那是拇指粗的一根荆竹,一头斗着亮锃锃的铜烟嘴,一头斗着一疙瘩铜头烟锅。烟锅头底部铸有一把隐隐突起的铜棱锥。平时出门,他倒背着手,手里就握着这杆草烟锅。他说,他的这杆草烟锅,可以用来防身,遇到什么歹人,顺手就可以给他头上一“发财”。他指指烟锅头上的那把棱锥,指指自己的胸口,说也可以直刺对方。我说小舅,你这个铜烟锅头可以做文物了。他笑笑说,差不多吧。他说“大跃进”那年,“大战钢铁铜”,家里的铜盆、铜壶、铜锣锅都动员给卖了,这个咋个说我都舍不得卖。那个铜锣锅卖了实在可惜了,现在你拿钱也买不着了。铜锣锅煮的米饭太好吃了,锅巴特别香。锣锅饭,腌菜汤,他咂咂嘴,叫了一声“哎哟喂”!他说到“文化大革命”,有人还说他的这个铜烟锅头是“四旧”,“破四旧”,要没收的,他把它藏起来了。
现在像小舅一样还吃老草烟的不多了,就农村里几个七八十岁的老倌老奶。这年月谁还好这一口!栽草烟的人家也不多了,大多数人家只栽烤烟,国家只收购烤烟,不收购草烟。就几个好这一口的老人,自己栽了吃一点,卖一点。他常常对我说,最好吃的草烟就是南涧的乐秋烟,可惜现在买不到了。每当说到这,他总是一脸非常向往的样子。怎么个好吃法,他却没说。他只说南涧的乐秋烟,栽在乱石嶙峋的山坡地里,这里栽一窝,那里栽两窝,山基土,不施肥,也不浇水,全靠老天雨水浇的。当地街子天,在乡镇农贸市场的什么角落里,还有几个老人蹲在那里卖草烟。小舅说,那是栽在菜地里的本地草烟,施化肥不说,还喷洒农药呢,烟叶长是长得好,梢子长,味道比起南涧乐秋烟可就差远了。
这锅刺鼻呛人的老草烟,对于小舅,对于一个一辈子和牛马牲口打交道的读书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至少释缓了他什么难以言说的沉重吧。
小舅的这份“烟火”情结,让两个表弟很为难。在浇灌钢筋混凝土小洋楼时,要拆掉原来那些土木结构瓦屋面的老房子,不得不留下了三间撒瓦小平房。一间准备打一下水泥地板给小舅住,小舅不让,他说,就原来的泥土地面好,好接点地气。最后粉刷了一下烟熏火燎的墙壁,小舅还说这是多余的呢。另外两间,一间堆放杂物柴草,一间做猪厩养猪。农民嘛,还要种田,还要养猪,总不好把杂物柴草堆放到小洋楼里,也不能在小洋楼里养猪吧。两个表弟的为难,是怕村里人说闲话,怎么现在还让老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呢!他们不能理解小舅的眷恋和焦虑,那种既苦涩又温馨的农耕文明的简单生活,正在急遽逝去。而那逝去了的,就永远不会再有。有的对我们来说,却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是那段历史残留的标本,是那个时代仅存的符号。
责任编辑 彭琼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