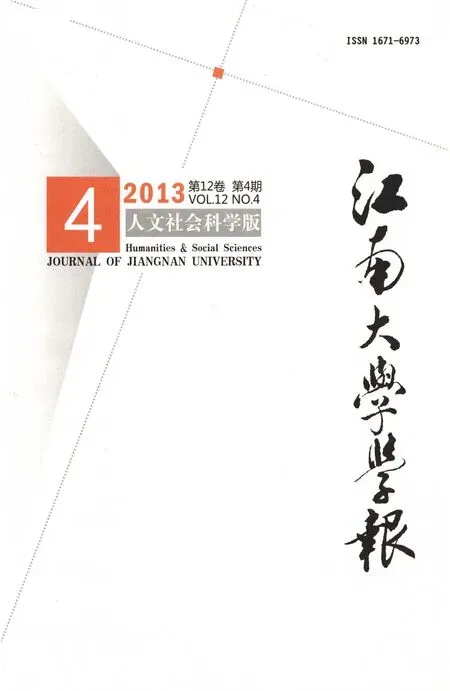何以利吾国——民国孟学“义利观”研究述论
李 锐,陈 晔
(1.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北京100165;2.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重庆400030)
“义利观”作为孟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同样也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问题,更是儒学之安身立命处,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张栻在《孟子讲义》中便说,“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朱熹更是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可见其对于“义利观”的重视。传统“义利观”在进入民国社会之后,在内涵上比之前代有所变化。明辨这一变化,才能更为深刻的理解民国社会之种种,也才能更为深入了解国人在处理中西古今问题的态度。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义利观”的研究,虽然成果丰富,但仍有未尽之处。①从现有成果来看,学界更多关注的是作为哲学命题的“义利之辨”,以及儒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或将这一问题至于学术史的脉络之中,重在厘清其在各时期的发展脉络及嬗变。而对其进入近代社会,特别是民国社会后之命运较少关注。本文正是立足于此,力图厘清民国学者对于“义利观”之研究,进而探明作为传统问题范畴的“义利观”,如何影响着人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
一、孟学“义利观”之基本内容
在孔子之时,“义”与“礼”相辅相成而发生作用。时至战国,礼“只剩下一些徒具形式的礼仪还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1]。因此,孟子将“义”加以改进,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并将“义”提高到与“道”并列的高度。虽然“义”在孟子仍有规范性和行为性的特点,也就是朱熹所谓“义者,人心之裁制”[2]1,但是“从孔子的‘杀身成仁’到孟子的‘舍生取义’则意味着道德理论由理想化、内在化向现实化、外在化的转变,由注重道德的自愿原则到注重道德规范原则的变化”[3]。
“义”在《孟子》中共出现108次,频率相当高。前代学者大都将“义”与“宜”并举,以后者来解释前者。朱熹便认为,“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2]1,这样解释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是对于理解《孟子》全文以及孟子之“义利观”则稍显不足,“因为孟子谈‘义’,很大程度上是和义利之辩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分别事理,各有所宜’的‘义’与义利之辩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种传统的解释还难以说清楚。”[4]226因此,对于“义”的内涵还需进一步分析、解释。
据周淑萍统计:“义”作为名词,指伦理道德之义,共出现80次;“义”作为动词,指人们的思想合乎义,共出现18次;“义”作为名词,指意思、道理之义,共出现10次。[5]通过这样的解释可以更清楚的了解“义”及孟学“义利观”的基本内涵。
“利”字在《孟子》中共出现39次。与“义”字相比,“利”的含义则相对比较简单、清晰。其主要有三个基本含义:一是锐利之“利”,指兵器的坚固锋利;二是利益之“利”,指在经济上的利益;三是利于之“利”,即“有利于”的意思。[4]231
二、“义利观”之历史演化
“义利观”这一传统命题并非一以贯之,其在古代社会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特定内涵。自孟子提出“义利之辩”这一课题之后,历代学者对此多有争论,使得“义利观”在各代学者的不同诠释下,内涵也逐渐发生变化。只有明辨这一内涵的变化,才能避免将其作为整体化,且视为近代“义利观”之稳定坐标,从而了解近代“义利观”之渊源。
大体言之,两汉学者对于“义利观”多主张舍“利”而取“义”,其中以董仲舒最具代表性。董仲舒认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明确的将“义”、“利”对立而言。但“董子对统治者发言,此所谓‘利’指统治者之‘私利’而言。董子生当西汉武帝时代,正直逐利之风大行之际,他对当时汉帝国的统治者与民争利的行为有极痛切的批判”[6]430,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使得董仲舒如此斤斤于“义利之辩”。两汉学者大多反对政府对于“私利”的谋求,主张谋求长远的“公利”。
进入唐代,“义利观”的内容发生了较为复杂的变化。唐代政府主张臣下应该追求“公利”,然而“公利”的含义却与两汉不同。唐代统治者所说之“公利”指的是“公家之利”,而非人民之“公利”。与统治者相反,“唐代政论家多从人民利益立场言‘公利’。”[6]431
宋代之后,“义利观”的含义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化。司马光认为,“利”为财利,并以此来批评王安石,强调“义”、“利”不能并存。王安石则认为,孟子所否定的“利”是一己之私利,而理财是“义”。司马光、王安石二人从其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对孟子“义利观”进行迥然不同的诠释。“与司马光、王安石政治上的解说不同,程颐主要从学理上考察二者的关系,承认义利的普遍性,认为‘义与利,只是公与私利也’,利为天下之常情,常人趋利避害,而圣人‘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7]。自程颐之论出,对于“义利观”之解释基本定型,后世学者大体都在此基础上立论。
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较大的变化,中国社会再一次被外族所统治。而自刘宗周绝食殉难后,流行百年的王学时代也宣告结束,中国思想史出现了新景象。②韦政通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认为,以刘宗周去世为标志,在其之前,有明一代,王学兴盛,其后则是内外情势俱变。王学虽然呈现出儒学新气象,但在学风上仍是承继南宋之遗风。明末清初所开辟的经世新学风,乃上承北宋,遥契先秦。清初顾、黄、王、颜诸家的人格气魄,儒学规模,所表现的精神,颇能与先秦儒家内外并重的精神相应,这使他们在儒学史上,颇具特殊意义。(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第987-903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王汎森认为,明代后期社会风习变化极大,且渗透力极强,道德哲学中“经验”——也就是所谓气质流行的部分便不应该再被视为应该去除的负面性的东西,如果对现实相应不理,或全盘抗拒社会的新变化,这种学说便完全无法打动知识分子及一般平民。现实的改变要求在儒家到的哲学中将现实生活的部分包括进去。(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一种道德严格主义》,见王汎森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1页。)这一思想变动,使得学者在处理“义利观”问题时,便会对“利”有更大的包容性,从而保持着比前代更为开放的态度。然而,在王汎森看来,明末清初学者在其反程朱理学,寻求“欲”之解放之外,还存在一种道德严格主义倾向。所谓“道德严格主义”,即在看似解放的思想之下,反而对理欲之别有着更为严格的界定,王汎森称之为“米中取盐,矿中取金”。这样的一种倾向对学者之“义利观”必然也会发生影响,使其虽然畅谈“利”之合理和必要,却也以更加严格的道德要求去处理代表世俗生活的“利”。在此背景之下,“义利观”的内涵也发生较大的变化,重视功利与实用成为这一时期“义利观”的主要内容,吕坤、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都反复强调“人事”、“民用”、“学贵实效”之重要。由此引申而出,便是这一时期的“重商”思想。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大儒分别否定了为富不仁之说,表现出较为一致的“重商”思想。
如此检视“义利观”之历史演化,便可发现其内容并非稳定且同一,而是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有论者为便于考察近代“义利观”之特点,将古代之“义利观”内容视为一稳定的参照坐标,进而论证近代“义利观”内容之新变化,这一结论显然是值得商榷的。①赵璐、白俐认为,传统义利观主要是指先秦之明清的义利思想。且认为,撇开具体的时代和阶级内涵,仅从一般意义上而言,“义”是泛指一定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利”则主要是指人们的物质利益及谋取物质利益的活动。纵观中国传统义利观,其脉络是比较清楚的,重义轻利是传统义利观的主流,且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国思想史、伦理史、哲学史,对中国社会影响至逛至深。(赵璐、白俐:《论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及特点》,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1卷第1期。)笔者认为,上述结论过于空泛,且将中国传统思想的复杂发展脉络简单化。而“撇开阶级内涵”、“主流”等语也略显笼统。两位作者将“重利”作为近代“义利观”发展的独特特点,正可见罗志田先生所说之学统中断所引发的吊诡现象。不仅如此,近代“义利观”的诸多“新”特点显然与明末清初“义利观”之内容有着密切联系,这也是研究近代“义利观”所需要关注的。
三、“义利观”民国命运考察
先秦时代,“义利之辩”已初具雏形,孔子首先因袭西周以来的价值概念,把“义”作为与“利”相对的修身问题的一部分提出来。《孟子》七篇,开篇便正言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明确将“义”与“利”对举。“义利之辨”自孔子将其作为修身问题的一部分提出来之后,不仅贯穿了整个孟学史,也贯穿于中国思想史之中。正如黄俊杰所说:“‘义利之辨’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仅仅是作为抽象思维的问题而出现的,它在历史的进程中必然要落实到社会经济及政治的现实情景上”[6]112。
进入民国,作为孟学重要问题的“义利之辨”逐渐趋于冷落。据笔者所见,民国孟学中将“义利之辨”作为专门问题进行讨论的论文仅有3篇,而在专著中设专门章节进行论述的仅有3家。何以在前代颇受重视的问题,在民国却备受冷落呢?这一方面与前代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有关,其学术空间已经比较狭小,无法引起民国学者的研究兴趣;另一方面,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学术风气密不可分。
当时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想、学说杂糅交错,西方文化的大举进入必然会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发生碰撞。碰撞之中一部分人对西方之学发生兴趣或为之迷醉,进而对中国之学进行检视、批评甚至鄙弃;另一部分人则在碰撞之中走向文化保守,以此作为一种反击的姿态。这种态度的分野,导致了20世纪初的东西方文化之争,这一争论实际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思想界以及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其对民国时期的孟学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且在“义利之辨”这一问题上极为明显。作为孟学基本问题的“义利之辩”时至民国备受冷落,与当时的东西文化之争中激进派对于中西文化的认定密不可分。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先进其原因之一便是西方文明是实利而非虚文的,而中国则是“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以昭垂,人心之所以祈向,无一不是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8]5-6李大钊也认为,西方文明是物质的、积极的,“守静的态度,持静的观念,以临动的生活,必至于人身与器物,国家与制度都归粉碎”[8]134,对物质生活则明言其不可或缺。陈独秀及李大钊们的这一认识,实际已经是对于“义利之辨”某种程度上的消解,当其将国家民族进步与物质的追求相联系时,传统儒家所认为的“义”与“利”的对立实际上已不存在。
不仅是激进派如是说,保守一方似乎也默认了这样的文化特征认定。杜亚泉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中便接受了这样的文化特征认定,“西方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8]339。尽管,杜亚泉主张调和中西,却也不得不承认西方社会由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而趋于进取,中国文明则“仅仅抱一个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之目的”[8]345。
尽管,保守与激进两派对孟学“义利观”的认识有相近之处,然而,两者的关照处则迥然不同。保守派将之视为中国文化安身立命处的“义利之辨”,之于以救国、强国、富国为己任的“新青年”们则不过是一个再迂腐不过的说教,以及中国富强之路的障碍。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也就无怪乎作为专题的“义利之辨”的没落。
吊诡的是,尽管所谓“新派”或“激进派”对传统持批判态度,并将“义利之辨”视为封建余毒。但是其判定中西文化的思考逻辑,却仍然笼罩在中国传统的“义利之别”范畴下。他们对于中西文化的取舍标准,无一不暗合其认定的“义利之辨”标准。符合“利”之标准的西方文化,成为解救中国的良药,而以“仁义”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文化,则已难以承担“何以利吾国”的重任。
四、民国时期孟学“义利观”诠释
民国时期,“义利之辨”的讨论有“返祖”现象发生,学者不再将“义利”之间进行绝对的对立解释,而是为其寻找现代情境下的合理性。学者不再断言“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2]。“利”被还原到为《论语》中“公利”与“私利”两种,并认为《孟子》中所反对的是个人私利,从而使“义利之辨”与西方公共道德概念发生联系。不仅如此,由于对于“义利观”解释不一,导致了对于孟子形象判断的分歧。
1.以孟子为非利主义者
王治心在《孟子研究》中认为,“不肯枉己,乃是中国历代相传的道德中心,就是所谓道统相传。因为枉己即是枉道”[9]137,而“道”也就是“义”,为了私利去枉道更是万万不可。因此,在王治心看来,孟子是一个“极端的非利主义者,他的人生观……就是‘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前者是消极的,后者是积极的”[9]138。在消极方面,孟子多论及“讲利”的害处,且认为要审视“利”中是否有“义”的存在,“不义而富且贵,更有伤于道”[9]140,“伤道”即是不义。不仅如此,孟子更是将“义”置于生死之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而这在王治心看来,即是孟子的理想人格,也是最高人格。
余家菊在《孟子教育学说》中对于何谓“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存于心者为端,见于事者为实。义之端为羞恶之心,义之实为恭孝之行”[10],且“义主于敬,其精髓在有所守于己”。因此,“义”是一种自我修养的重要手段。朱熹将“义”解释为“心之制,事之宜也”[2]1,而所谓“宜”就是适宜,是对于事物适当性的判断。基于此,余氏认为,所谓“义”是人群的一种离心力,只有“仁”与“义”相辅相成社会才能安定。而孟子之所以严界“义利之辩”,是因为假如人只关心一己之私利,而罔顾社会之公义,就会造成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崩溃。因此,只有讲求公众利益才能真正保证个人的幸福。
杨大膺在《孟子学说研究》中认为,“所谓义,依照孟子的说法,当然是一种先天的范畴,能直觉地辨别行为的是非的,即韩愈解为行而宜之之谓义的意思,孟子主张拿这种先天的范畴,去做人们活动的标准,和孔子以仁为标准一样,两者并不冲突。而义还是助仁德实现的。因为义只是限于人生行为方面的标准,这种标准含有裁制性的;而仁却是整个的理想模型,含有目的性的。所以孟子多用一个义,并非对孔子思想有什么不满,是因为孔子偏重忍道,离普通人的程度太远,恐难实现,于是借重这个义,以联络这理想的人格和实现的人生”[11]。“义”之所以可以帮助实现仁义礼智,完全是由于“义”的这种自明作用。也正是基于这种自明作用,人们能够判断事情正确与否,以及是否可以施行。
冯友兰在《新原道》中认为,儒家将“仁义礼智”四端并列而讲是始于孟子。在冯友兰看来,孟子所说的“义是道德方面的应该。这种应该是无条件底。无条件底应该,就是所谓‘当然而然,无所为而然’。因其无条件底,所以也是绝对底。无条件底应该,就是所谓义。义是道德行为之所以为道德行为之要素”[12]3。当人无条件的做他应做之事时,便是“行义”,而有条件的去做应该做之事时,即是“求利”。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冯友兰看来就是道德境界与功利境界的分别。
另外,冯友兰认为,孟子的“义利之辩”并不是反对“利”,而是专就个人之“私利”来说的。“求个人的私利的行为,是求利的行为。若所求不是个人的私利,而是社会的公利,则其行为即不是求利,而是行义”[12]6。在冯友兰看来,当一个人以社会公利为其行为的目的时,他的行为就不是“求利”,而具有了道德价值,从而成为“行义”,进而“凡有道德价值底行为,都是义底行为;凡有道德价值底行为,都蕴含义。因为凡有道德价值底行为,都必以无条件地利他为目的”[12]6-7。然而,冯友兰的这种推而广之的说法也是存在问题的。“孝”这一行为是具有道德价值的,但是这一行为却是一种个体行为,属于“私”的范畴,将其归为“义”也并不符合“义”这一概念的传统解释。我们当然可以说“凡有道德价值底行为,都蕴含义”,然而说“凡有道德价值底行为,都是义底行为”则是不合适的。
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中认为,严“义利之辩”是孟子的一大功绩。吕思勉认为,孟子严“义利之辩”是为让人们明白只有“仁义”才是真正的“利”,斤斤于“利”而亡“义”,反而会带来不利。至于后来孟子的这种“义利之辩”被董仲舒发挥成“正其谊不谋其利”,在吕思勉看来也并非全无道理。他认为,“义利之辩,正谊不谋利之说,最为今之恃功利论者所诋訾。然挟一术利之心以为义,终必至于败坏决裂而后已。此今之所谓商业道德,而昔之所谓市道交者也,几见有能善其后者乎?孟子之说,能使人心由此而纯,其有功于社会,亦不少也”[13]。
2.以孟子为乐利或功利主义者
胡适认为,“孟子的政治学说含有乐利主义玩物可讳的”[14]356,而且“说到应该食功不是食志,重行为的结果,不重行为的动机。几乎要与功利哲学的学说沟通”[14]。然而,孟子又让人注重个人的修养功夫,并且注重行为的动机,不是以行为的结果来定道德的标准,因此“孟子止(只)有直觉的伦理论,没有功利的伦理论。答彭更的话是偶然强辩,不是本心”[14]357。胡汉民则认为,“孟子的书,涉着功利思想的很多。不过就个人内部的修省说,不以此为满足。而就外部一段的评价,就撇不了他,……从伦理的方面,讲自我的修省和从社会的方面讲道德的评价,也是两样说法”[14]357。
俞平伯在《孟子解颐札》中认为,孟子的“义利之辩”是误尽苍生,并且认为孟子本就是功利主义的,“他不言利,正是因为‘利’字这一字,被当时一般人用滥了,全当作自私自利解释,所以另标仁义立说。其实,利如作正当之乐利,则利犹仁义也”[15]。这一点来说,俞平伯的见解是十分有见地的。然而后文论至管仲的问题时,俞平伯纠缠在孟子不谈齐桓、晋文之事,认为孟子是故意对这一问题避而不谈,却对孟子为何避而不谈不甚了了。孟子之所以不谈是因为孟子认为齐桓公、晋文公所成就的是霸业而不是王政。孔子之所以赞赏管仲,也是因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论语·宪问》)从这一点上来看,孔子也是欣赏其能不用霸道,而王天下,因此才会说“如其仁”。
从民国时期孟学中对“义利观”的研究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学人多研究的是“人禽之分意义上的义利之辨”[16],从而在研究中多将“义”、“利”绝对的对立起来,而忽视了孟子“义利观”中的差别性。《孟子》开篇便是孟子与梁惠王的一段对话,而这段对话也常常被当成是孟子“义利观”的主旨思想,在梁惠王问道孟子“何以利吾国”的时候,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仁义而已”。但是,今人杨泽波认为,这里孟子的重点并不是在强调道德意义上的“义利之辨”,而是“治国方略意义的义利之辨”[4]240,孟子与梁惠王的这段对话在杨泽波看来,其谈论的主旨是孟子劝梁惠王行“仁政”,而不是单纯的追求富国强兵,因为在孟子看来只有行“仁政”才是治国的最好的办法。然而,民国孟学研究中对于孟子“义利观”的论述中,常常认为孟子是绝对的先义后利论者,并将孟子与梁惠王的一段对话作为论据,忽视了孟子本身对于义利的要求是有差别的。在《孟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孟子认为要先义后利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的宣讲对象都是一国之君,或者是“君子”。因为在孟子看来这些人是先知先觉者,是要“立其大体者”。而对于人民来说,孟子则认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於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此,对于人民的要求则是要“先利后义”,也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意思。民国时期对“义利观”的研究则大多忽视了这一问题,从而也将“义利”放在了对立的角度,仅从道德角度来论述了孟子的“义利观”。
此外,通观民国学人“义利观”研究,其在处理“义利”问题上,对“利”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承认“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不仅如此,“利”由“私利”、“私欲”一变而成为“公利”,只要其包含有“公”的成分,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只不过此时“公”的主体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略带抽象色彩的“公理”、“公义”之“公”,而是有明确主体的现代国民之“公”。对于“公利”的认定也并不再是“公家之利”,而是有更广泛基础的一般国民之“利”。而近代以来,人们多将国家视为国民的集合体,有利于国民,当然就是有利于国家的。①沈松侨在论述晚清“国民”概念时认为,中国之“国民”概念形式上近于西方people一词,但却在转译过程中被赋予了citizenship一词的内容。不仅如此,西方社会是在现代国家形成的基础之上,进而塑造现代之国民,而中国则是由塑造现代“国民”为基础,进而实现对现代国家的塑造。(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2002年12月。)正因为如此,“国民”概念中的个人主义成分逐渐被剔除,从而成为一集体概念,“国民”与“国家”逐渐被画上等号,成为一利益共同体。原本是个人内在道德取向的“义利观”,最终外化成为了一种外在价值取向标准。而随着西方观念的大举进入,这一基于传统的道德取向的判断标准,逐渐被更为世俗化的态度所取代。
总的说来,民国时期学者对“义利观”所进行的论述,并非是横空出世的无根之论,而是有其学术源溯。由民国学者对“义利观”所阐释的内容来看,无论是“重义”还是“乐利”,都是承接前代学术之余韵,都仍是在中国传统学术内在里路思考之下的自然结果。正如罗志田所言,近代学术传统中断后,经常会出现所谓的“假作真时真亦假”,过去常见之事反而成为现在的“突破之举”。[17]民国学人对“义利观”的思考也有类似情况。早在明末清初已颇为盛行的“乐利”论调,在民国“义利观”的阐释中经常被视为向保守势力宣战的武器。反观中国学术发展之脉络,才发现不过是承接古代学术之余续,无论这种继承是自觉的还是被动的。所谓保守派固然是以继承传统自居,通过对“义利观”的阐释表达自身之价值取向。而所谓新派人物实际也仍是在中国学术内在里路之中,表达着自身的判断标准。新旧双方,尽管目标不同,然而却各自由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在里路的思考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不管这种,思考是自觉自主的,还是被动消极的,民国时期学者对孟学“义利观”的重思,无不反映着其对于中国社会命运的思考,同时也影响着他们对中国社会前途的思考。“义利观”这一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命题,在经历了内化过程后,在民国时期又再一次的外化成为行事之准则与标准。
[1]董洪利.孟子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32.
[2]朱熹.孟子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6.
[3]张奇伟.亚圣精蕴:孟子哲学真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0.
[4]杨泽波.孟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周淑萍.孟子义利观新探[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8(2).
[6]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卷一[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
[7]张荷群.北宋孟子学案[D].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5.19.
[8]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9]王治心.孟子研究[M].上海:群学社,1928.
[10]余家菊.孟子教育学说[M].上海:中华书局,1935:48.
[11]杨大膺.孟子学说研究[M].上海:中华书局,1937:31.
[12]冯友兰.新原道[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3]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82.
[14]胡适.胡适文集·中国古代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胡汉民.孟子与社会主义[J].建设,1919,1(1).
[16]俞平伯.孟子解颐札(一)[J].东方杂志,1924,21(13).
[17]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