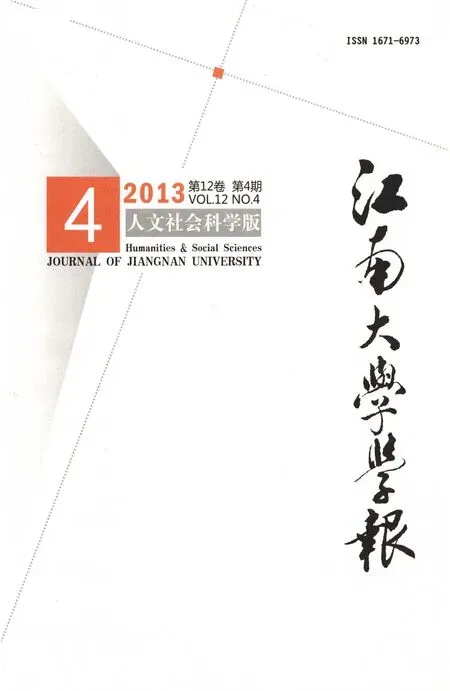王维家世、家风与家学
兰宇冬,过文英
(1.中国美术学院,杭州310023;2.浙江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杭州310023)
一
王维,唐代著名诗人,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艺术全才,据史料记载,王维在诗、书、画、音乐方面成就杰出,堪称一代宗师。不过关于王维家世却因史料的缺乏一直未有定说。《旧唐书》本传中记载:“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①本文引用王维传记资料主要来自《旧唐书》和《新唐书》王维本传,在之后的行文中简称《旧、新。其他语焉不详,《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因维弟王缙的显贵而在“河东王氏”中列出中王缙祖父四代及其兄弟五人之世系:
王儒贤(唐赵州司马)——扬州司马王知节——协律郎王胄——汾州司马王处廉——尚书右丞王维、代宗宰相王缙、江陵少尹王繟、王纮、太常少卿王紞。
《世系表》将“河东王氏”列为“太原王氏”一房,太原王氏为汉司徒王允之后,在魏晋时因重臣王昶、王浑而成为当时著名门阀,后因时局变动,门庭遭诛灭之难,唯余王慧龙只身投奔北魏,依靠北魏大姓崔浩的支持在北魏立足,至王慧龙孙王琼依孝文汉化改制之势而成为当时大族之一。到唐代其实力几为皇室所忌惮,甚至以政令干涉其婚娶。《太平广记》卷184“《氏族》七姓”条引《国史纂异》云: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赵郡陇西二李等七姓,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乃禁其自相婚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
虽然《宰相世系表》列王维家族为“太原王氏”之“河东王氏”房,但世系表中王维家世仅列五世,以上世系不明,其中颇多疑点。
《全唐文》卷545有唐王颜贞元十七年(801)撰《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其中透露出一些关于王维家族世系来源的信息,碑云:
卓字世盛,历魏晋为河东太守,迁司空,封猗氏侯。……卓翁年七十九,薨于河东。时属刘聪、石勒乱太原晋阳,不遂归葬,葬河东猗氏县焉。隋并猗氏为桑泉县,今司空冢墓在县东南解古城西二里,至今子孙族焉。……我卓翁葬河东,子孙成族,间生将相,而太原之望,独不鼎盖河东著姓乎?……猗氏房右丞维叔,左相缙叔,俱伟文耀世。
关于此碑,全唐文在碑文后引《蒲州县志》推断,疑为后人伪作,因此学者在考证王维生平时多依据此说将此条材料忽略。不过蒲州县志的怀疑经不起推敲,岑仲勉在《王颜所说太原王氏》一文中逐条反驳,详辩此碑真实性,[1]此不赘言。另外还有若干条与王颜相关的材料俱可与此碑互证:
1、民国癸亥年重修《临晋县志》卷十三收有王颜于大历十三年(778)撰《慈州文城县王景祚并仲子郴州郴县丞墓碣序》,据县志载,此文正刻于上述王卓碑阴,文中内容恰可与王卓碑互证,尤其是其中提到:
宗族内多出神仙,河东房间生将相,近则从父正见在天宝安西北庭二节度使,从父缙起广德上台掌国十四年。[2]638-697
2、全唐文卷986收有大历十四年(779)王颜状《太原乡牒》。
3、《永乐宫碑录》收有唐元和二年(807)郑云逵撰《唐故虢州刺史王府君(颜)神道碑》。此碑述王颜生平最为详细,言王颜为王卓之后,在论述其生平事迹时,又强调了他自叙本宗,自言太原王氏为周平王孙赤之后。[2]738
这几条材料都与王颜有关,特别是少有学者注意的《王景祚碑》与《王颜碑》,证明了《王卓碑》确为王颜所作无疑。依《唐故虢州刺史王府君神道碑》“君以贞元十八年二月十二日终……享年七十有五”推断,王颜生卒年为728—802,又依《旧唐书》卷118王缙本传所记:“建中二年(781)十二月卒,年八十二”,可知王颜与王缙当代,而最早提及王缙的《王景祚碑》写于大历十三年(778),依《旧唐书》元载、王缙本传,时“元载得罪,缙连坐贬括州刺史,移处州刺史”,王缙健在但已失势,此时王颜定不可能更不必捏造宗族世系与之攀附,同时更重要的又如王颜在《王景祚碑》最后所表明的:
魏之风俗,简不中礼,周之子孙,日失其序,或本是弃而他是称,宜不为薄俗所知,固不知薄俗自为也,望不可以终没,必振于后之宗杰焉,窃闻道典曰:“阴功重、阳功轻,阴罪重、阳罪轻”,颜无行而未立阴功,无嗣而多有阴罪,故镌坚石,不杀颂词,建于茔前,永以为表,冀族之后人观之知宗之祢裔也,冀乡之后贤存之,知墓之姓氏也矣。
其树碑之目的就是为了正本清流,厘清世系,从而得到先祖认可得以获取“阴功”,其间既有彰显宗法血缘传系之缘故,亦有神圣的宗教意味,无论从哪一点说,都不太可能有作伪和捏造的动机。并且可以从王颜的行事看出,他是抱着固执且虔诚的态度将之当做自己的使命:779年状《太原乡牒》;801又做《王卓碑》,此时离他去世还有一年,这一系列人生的轨迹,似乎表明在“无嗣”的负罪感中,厘清宗族光耀先祖的目标已经成为王颜后半生最重要的人生寄托,郑云逵在《王颜碑》中也将之作为王颜人生重要的事迹来介绍,可见王颜重整世系在当时定然造成了广泛影响,张目于众人眼前亦是王颜想达到的目的,这段事迹可信性也就无可怀疑了。
依据王颜所论,王维、王缙“河东王氏”一系为晋司空王卓之后,而“太原王氏”为汉司徒王允之后,细考两系人物,没有交集,可以判断两者并不同脉,清王昶《金石萃编》卷140在《王卓碑》后亦曰:“维、缙兄弟,(颜)称之为叔,当与颜同系;然检《宰相世系表》,以维、缙为河东王氏,其源不从卓始,其流又不及颜之本,皆所未详。要之颜撰此碑,自必无误,其追溯源流,亦必有据,或所传各有不同,未可据他书以疑碑也。”
王卓一系其名并不显扬,依《王卓碑》、《王景祚碑》可知王卓宗子离居四县,曰桑泉、蒲州、猗氏、虞乡,分为四房,如《王卓碑》所记四房人物虽间有出任一方官吏者,但除王维王缙外名声大都不彰,家世可考者更少:
1、王方平,《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一六六”有《唐故幽州都督寿阳县男王府君墓志》“公讳方,字平,太原人也,曾祖适”[3],未提及世系。又《王卓碑》曰“广州都督方平翁”,然《王景祚碑》云“幽州都督寿阳公方平”,《太原乡牒》亦云“幽州都督寿阳公方平”,又依《唐故幽州都督寿阳县男王府君墓志》可证王卓碑误,应为“幽州都督王方平”。
2、释昙延,道宣《续高僧传》卷八“俗缘王氏,蒲州桑泉人。世家豪族,官历齐周”②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昙延传》,见《大正藏》册50,第488页上。,其中虽提到昙延为“世家豪族”,但对其先祖却缺乏记载,殊不合理。
从列举人物可以看出,其家世都不显著,仅概括称为“太原人”。特别是碑志,如若家世显赫,很难想象在六朝以来岑夸家世的风气中会遗忘先祖,由此亦可判断,王卓一脉实为在地方上拥有一些势力的中小地主,其实力与北朝望族“太原王氏”相比较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王维家族“河东王氏”为晋司空王卓宗子四房之“猗氏”房,甚至“河东王氏”之名称本源于王卓,王颜《王卓碑》中云:
卓翁年七十九,薨于河东。时属刘聪、石勒乱太原晋阳,不遂归葬,葬河东猗氏县焉。
不过《宰相世系表》中将“河东王氏”也归入到“太原王氏”,在注重世族血脉传统的当时,却也非无的放矢,其主要原因与太原王氏王慧龙一脉本身的先天不足有关。
陈爽在《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深浮》一文中认为:王慧龙因只身入魏,虽有崔浩支持,但缺乏根基,因此主动吸附地方宗族势力,如“中山王氏”,从而形成势力的互补。这也造成了《宰相世系表》中太原王琼一脉唯余一房世系清晰,其它各房“乌丸”、“中山”、“河东”则都郡望可疑。[4]
结合前文,不难推断出,如同“中山王氏”一样,“河东王氏”亦是地方上拥有实力的家族。其家族很早就意识到了自身在势力和声望上的天然缺陷,主动地寻找依附,王颜《神道碑》透露出重要信息:
自古太原乡也,亦犹润州上元县有琅琊乡。后魏定氏族,佥以太原王为天下首姓,故古今时谚有“鼎盖”之名,盖谓盖海内甲族著姓也。我卓翁葬河东,子孙成族,间生将相,而太原之望,独不鼎盖河东著姓乎?况本支奕叶,金辉玉映,洪源长派,碧注清涟。袭官婚者,戚属兼之,澄而为止水;绝资荫者,徭税不暇,漫而为众流。隶军府而耳顺方免,负终身之耻;戍积石而万里交镇,有次死之苦。更接二京之庭,驱出九流之外。盖魏地狭隘,迫而使之然也。……且河东王承太原显望久矣……
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所谓“太原之望,独不鼎盖河东著姓乎”恰从反面透露出一条重要信息:“河东王氏”之所以依托“太原王氏”,其最直接的原因是来源于河东当地望族之间的势力竞争。唐时的河东,包括今永济、临晋、猗氏、虞乡、解县、运城、蒲州、安邑一代。河东一地,历来是望族聚居之地,依《世系表》所记大族十姓十三家中,就有河东裴氏、河东薛氏、河东柳氏三姓,《太平寰宇记》卷46云蒲州河东郡九姓:裴、柳、薛、费、吕、满、聂、茹、廉,王姓甚至未预其列,可以想象,仅靠地方家族势力,“河东王氏”并没有与其它大族抗衡的实力。而依托借“天下首姓”太原王氏之势,便足以在声势上“鼎盖河东著姓”。
第二,依托“太原王氏”的时机当在“后魏定氏族,佥以太原王为天下首姓”之后,确切说来,从《王卓神道碑》中可以看出,“河东王氏”并没有试图与“太原王氏”先祖“汉司徒王允”建立必然的血脉联系,两者先祖世系并没有发生交集。可见,是否为同脉血缘这一相当关键的问题似乎被“河东王氏”有意地忽略,而重要的在于强调后魏时太原王氏为天下首姓的事实。①依《北史》王琼及其四子本传所记,王琼四子在孝明帝时占据高位,长子遵业领黄门郎,多参机事,世谓“小宰相”,弟广业卒于太中大夫,延业位中书郎,季和位治书侍御史、并州大中正。时人呼为“英英济济,王家兄弟”。也就是说,“太原王氏”吸引“河东王氏”的直接动因并不是其足可堪夸的历史,而是体现在当下的政治实力,作为地方大族,缺乏与中央政治的交集是其致命的缺陷,由此使太原王氏很早便确立了从地方向政权中心逐渐靠拢的家族发展策略,依托于“太原王氏”寻找政治帮助是其首步举措。“河东王承太原显望久矣”恰可证明这一点。依托于望族不但确定了这个家族的政治策略,同时无疑也为这一家族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由此再来看《世系表》中对王维先祖的介绍,可以得出以下被隐藏的信息:王维高祖王儒贤之前的空白,其主要原因不仅是资料的缺乏。被历史所湮没的,正是一个地方家族从边缘向政权中心靠拢过程中的悄然努力与铺垫。其世系中除王胄之外,其他几人任官止于司马,司马是州的副知事,官品因州的建制为从五品下到正六品下,尽管是地方官吏,距离中央政权还有不小距离,但这却恰恰是一个地方世族经历若干代积累能够达到的合理距离。并且似乎目标也触手可及了。
王维家族向中央政权靠拢的努力从其高祖王儒贤开始已经能够成功地维持其成效了,接连四系任官不断,对于真正的世家大族这种维系不足为记,但对于王维家族来说,无疑表明了与真正“太原王氏”世家大族距离正在接近,从王维祖父一代就表现出若干信息。王维祖父王胄任协律郎,《大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云:
协律郎二人,正八品上,协律郎掌和六律六吕,以辨四时之气……凡太乐鼓吹,教乐则监试,为之课限。
从品秩来说,尽管协律郎仅为正八品,但毕竟更为靠近政权核心,且唐代太常寺所设官吏,一般为士人,所掌管的音乐,又多与礼仪相关,若不是具备了世族身份且本身有较高的修养,很难担任其职。王维家族出现的这样一个依靠本身音乐素养而靠近权力中心的人物,虽然官职不高,却意义重大。这也绝非是一个突然现象,它是家族有意塑造的结果,是整个家族从地方势力向世家大族的更深层次的特质——文化家族同化靠近的结果。白乐日在《中国的文明与官僚政治》中说:
(中国)士大夫(官吏)阶级在数量上仅是少数人,但是由于他们有力量、影响力、地位、声望,掌握有所有的权力,拥有大量的土地,因此权力显得无比的巨大,这个阶级并且有每种特权,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垄断教育而享有塑造其本身成员的特权。[5]
王胄的出现正是家族这种“垄断教育而享有塑造其本身成员的特权”的成果,而王胄子王处廉——也就是王维父亲的婚姻正可作为其家族影响扩大的证明。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说:“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赵殿臣《王右丞集笺注》卷17《请施庄为寺表》之按语中说“《宰相世系表》有博陵安平一派,当是右丞母氏所出”。从前引《国史纂异》可知王维母族正是唐代“禁婚令”中所涉及的“博陵崔”,“山东士大夫以五姓婚姻为第一”[6],在注重婚姻的高门世族中,王处廉如若不以“太原王”的名号,定难促成与博陵崔氏的婚姻。这也就意味着至晚到王维父亲一代,“河东王氏”作为“太原王氏”一脉无论是地方势力还是家族影响均已获得时人的普遍认可。这种认可也昭示出对河东王氏家族所蕴含的潜力的认同,同时亦预示着最迟至王维父亲这一代,其家族已经基本开始了从一个偏安一隅的地方势力“河东王氏”向世家大族“太原王氏”的进一步迈进。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王维家族在北朝时实际上是在地方上具有一些势力的小地主家族,借着北魏“太原王氏”王慧龙只身北奔向地方寻找强大势力援助的特殊契机,王维家族得以“冒族”而托世系于“太原王氏”。同时也逐渐转变家族形象,从王维祖父一代开始努力向中央权力靠拢以实现突破,这也就直接影响了其家族的教育策略和人才策略。
二
所谓“世家大族”,决非一个简单的名号,其评判标准除了政治、经济实力外,更重要的在于如白乐日所言“垄断教育而享有塑造其本身成员的特权”,从汉末魏晋以来随着士族的形成,从政治、经济地位的垄断逐渐转向更深层次的文化垄断,从而在士族内部形成所谓的“门风家学”,如陈寅恪所言:
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7]
门风与家学实际包括两个层面,钱穆所说更为明晰:
今再归纳上面各项叙述而重加以一番综合的说明,则可谓当时的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至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称为家学。[8]159
重视“孝友之内行”,一方面是因为“孝友”是维系家族繁衍的最重要的内在动因,另一方面也与汉代以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察举”制度有关,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可见尽管有通经、明法之分,但“孝悌”却是所选人才最基本的要求。“孝友”也就成为家族所共同推崇的基本素养了。
“河东王氏”向“太原王氏”的靠拢过程除了“名义”上的统一,从更深层次首先要达到“门风家学”的同一,这种“同一”对于缺少世代文化积累的“河东王氏”来说,照搬或借用成为其捷径,《王卓神道碑》恰好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
晋司徒昶翁诫宗人曰:“若结婚姻,如暴贵无识,猥富不仁,慎勿为也。”又诫曰:“勿三代不仕不学,不看客失婚无谱,不葬无坟墓,不修仁。若是恶事,三代皆沦小人也。戒之慎之。”首先需要指出,这种在追宗溯祖的“神道碑”中出现家诫、家训是汉魏之后的一种常见模式,其目的正是为了以门风之严正而自显其门第之高贵,在这一点上,王卓一系自不能免俗。不过有趣的在于,其所用来标榜门第而选出的“晋司徒昶”却与此前所列王卓一系并不同宗,王昶《三国志·魏书二十七》有传,依本传记王昶为魏司空,晋司徒应为王昶之子王浑,但不管是王昶还是王浑,都是正宗“太原王氏”一脉,为王慧龙之祖,而引用其家训不仅仅是为了拉近两家族的距离,更是一种模仿和借用。
另外,从其内容看,家训中强调了婚姻的选择性,政治、学术的连贯性,重点强调了“修仁”,婚姻、政治、学术等等方面是魏晋以来世家大族非常注意的方面,自无需多提,“修仁”却正是钱穆所归列“孝友之内行”的门风体现。
《王卓神道碑》所表现出的内容,也正是王维家族从其祖辈就开始一系列努力的缩影,王维及其兄弟,从小所接受的正是如世家子弟一般的良好教育,特别注重“孝友”方面的一些基本品德的教育,史传中尽管对门风教育没有直接的叙述,但仍留下不少相关线索。
具体来看王维家风,钱穆归结为“孝友之内行”,因为“孝”与“友”是一个家族保持延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礼法实与门第相终始,惟有礼法乃始有门第,若礼法破败,则门第亦终难保。”[8]165而在汉代以来的正史中,多有对“孝悌之行”的记载,其中不仅仅是对个人的揄扬,在其背后更多地隐含着对良好家风的褒奖,同时也暗示出传主本人在社会中的高贵门第。
王维本传中专门记载王维孝行,《旧传》云:“事母崔氏以孝闻……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新传》云“资孝友……母丧,毁几不生”。他也曾在《为相国王公紫芝木瓜赞》中阐明孝悌真意,强调其重要性,也充分显露了他的天生美质。
《旧传》云:“闺门友悌,多士推之”。
《全唐文》卷447窦蒙注窦臮《述书赋》提到王维幼弟:“幼弟紞,有两兄之风,闺门之内友爱之极”。
王维兄弟“友悌”之情最突出地表现在维、缙兄弟间仕途上的互援,王维旧传记载,安史之乱后因王维伪职一事王缙请削去自己刑部侍郎之职为兄赎罪,从而使而王维仅降官职而得以身全;晚年时王缙为蜀州刺史,王维上《责躬荐弟表》,替弟缙说情,不惜自贬而扬弟之所长,愿尽削己官,放归田园,以使其弟得还京师。王维王缙兄弟互贬官职而惠及对方之行为,究其根本,其不仅仅是“友悌”的体现,更是为家族整体谋划更大政治利益的表现。
家学如钱穆所谓“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王维所接受的家学教育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家学教育进行很早。《新传》云“(维)九岁知属辞”,从“知属辞”的水平来看,其教育的起步很早,正因为其家族对下一代振兴家门寄予厚望,所以自然对早慧的王维着力培养,这种关注,也引发他的诗中一个特殊的现象,在其文集中,少见的有若干首诗作表明创作年龄:
《题友人云母幛子》,原注:“时年十五。”
《过秦始皇墓》,原注:“时年十五。”
《洛阳女儿行》,原注:“时年十六。一作十八。”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原注:“时年十七。”
《哭祖六自虚》,原注:“时年十八。”
《赋得清入玉壶冰》,原注:“京兆府试,时年十九。”
《李陵咏》,原注:“时年十九。”
《桃源行》,原注:“时年十九。”
《息夫人》,原注:“时年二十。”
《燕支行》,原注:“时年二十一。”
王维的文集中只有早年的这些诗作标有创作年龄,而之后的诗作尽管从诗歌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早期,但却没有任何年龄的标注。唐代诗人在诗作中表明创作年龄并不罕见,一般诗人常在成名后删掉少时之作,但少有如王维这样,在诗作中独独为早期创作做特别标注。结合本传,不难做出如下推想:首先,早慧的王维一定被家族给予了很多的期望,为了提高家族声誉,不遗余力的为之宣传使他早早成名,唐薛用弱《集异记》卷二《王维》写公主初见王维诗作后表现出的惊叹:
公主览读,惊骇曰:“皆我素所诵习者,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
一个从外地到京城的十几岁少年其实早已诗传天下,这样的荣誉又无疑给年少的王维以很大的成就感,以至还有专门的记录,其中不无自矜之意;其次,因为较早地就开始了有针对性地训练,所以王维在很早就熟练地掌握了写诗的技巧,并且也较早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使得他在十九岁写出的诗已经能够放入他整个诗集中,与他后来创作的诗并立却毫不坠其诗名了。
第二,从具体的教育内容来看,王维兄弟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家族式的教育注重传承,固然对天才倾注了更多的心力,但同时也没有放松对整个家族子弟全面的基础教育。
从两唐书宰相世系表来看,可以知道王维诸兄弟除王纮外都担任官职:
尚书右丞王维、代宗宰相王缙、江陵少尹王繟、太常少卿王紞。
尽管没有具体材料,但是能将家庭中五位兄弟培养成才,可以看出王维家庭良好的教育环境。其中特别是王缙,其本传云“缙连应草泽及文辞清丽举”,后直至宰相之高位,王维因为他才在两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保留了更多的家族信息,王维文集的最初编订也是源自于他之手,王缙本人也是多才艺,并且善写文章,以“笔”与王维的“诗”并立而名于当时,前引窦蒙注《述书赋》云:
二公名望首冠一时,时议论诗,则曰王维、崔颢;论笔,则曰王缙、李邕,祖咏、张说不得预焉。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亦云:
兄弟并以科名文学,冠绝当时,故时称“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也。[9]
仅就王维而言,尽管并没有直接材料说明他接受教育的情况,但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的知识构成,明顾起经在《题王右丞诗笺小引》中说:
玄肃以下诗人,其数什百。语盛唐者,唯高、王、岑、孟四家为最;语四家者唯右丞为最。其为诗也,上薄《骚》、《雅》,下括汉魏,博综群籍,渔猎百氏,于史、子、《苍》、《雅》、纬侯、钤决、内学、外家之说,苞总并统,无所不窥,邮长于佛理。故其摛藻奇逸,措思冲旷,驰迈前榘,雄视名俊。[10]
当然,因为王维家族毕竟只是新进士族,在家族底蕴上还是不能和延续数百年的高门士族相比,但在家庭教育方面却因为与时变契合较紧,仍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三,教育非常全面,同时特别注意魏晋以来的新兴项目,其中书画和音乐可能有其家学渊源。
魏晋南北朝以来之家学发展,除了文史经籍还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颜氏家训》“杂艺”条总结有“书、画、射、卜、弈、算、医、琴”等项目,而其中魏晋以来门第之家学教育最为看重者,当为书法与绘画,如钱穆所言,“其中尤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极重要地位者,厥为书法与画绘,当时门第中人重视此二艺,正尤其重视诗文,皆为贵族身份之一种应有修养与应有表现。”[8]184
前文已经介绍过王维精通才艺,其中就包括书法和绘画,书法一艺,《新传》云:“维工草隶”,《述书赋》云:“(维)弟太原少尹缙,文笔泉蒌,善草隶书,功超薛稷”,两兄弟都擅长草书和隶书,结合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子弟的教育情况来看,书法的训练基本上已经成为每个子弟最基本的启蒙教育,可以判断这是源自于王维兄弟从小有针对性的训练。
关于王维的绘画教育,未有史料提及,但其诗中却也留下了一条隐约的线索,王维《题友人云母障子》云:
君家云母障,时向野庭开。自有山泉入,非因彩画来。
诗题下注曰“时年十五”。赵殿成注云:“唐时呼屏障为障子”,因此内容描述了朋友家云母石障,其中天然的纹路似山泉涌出,逶迤漫延,如此形似,却非人手绘成、添彩作色,完全出自于“自然”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之手。从这首诗来看,十五岁的王维不但对屏风的自然纹理表现美术家的特有敏感,从中构画出一幅山水墨色,并且已经隐约表达出这样一种艺术观念:自然的创造胜过人工的雕琢,通观王维一生的创作,特别是他的山水诗、山水画,不难发现,将在后来被他发扬光大的艺术特征,已经在这样一首小诗中微萌出艺术的灵光了。由此可以推断,十五岁的王维对绘画已经有所触及,并具有画家对图像、色彩的敏锐视角与独特观念,这其中应该包含着为期不短的专业训练吧!
王维所接受的音乐教育也未有史料提及,但仍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如前文所揭示的,王维祖父王胄担任协律郎,因此王维所接受的音乐教育,当与其祖父有关,应该也是从小就开始的专门的学习。而《集异集》中“郁轮袍”一事所云王维“年未弱冠,文章得名”应是初到长安,求京兆府解头之前,这时已经“性闲音律,妙能琵琶”,可以得知音乐一艺,至少应在十几岁时已经达到自如境界了。
还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诗中所留下的线索,王维可能在15岁左右就离开了家,奔赴长安,在京城寻求更多机会。至少在17岁时,就已经深深体味到只身在外的孤独,从他这时写成的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一个辞亲离家的少年如何思念亲友,从而在“遥知兄弟登高处”的幻想中借安慰对方来慰籍自己,这时的他可能已经长时间没有再返故乡了。而15岁,最多至17岁对于王维已经是一个值得留意的分水岭了,他的家庭教育在这个时候完成,而他已经掌握了诗、文、书、画、音乐等诸样才艺,未来的基础在这时已经打好。当今天我们谈论到王维的多才时,仍不得不赞叹于其家庭为教育而付出的心血,不得不惊叹于贵族时代中文化传承的特殊脉动。
[1]岑仲勉.王颜所说太原王氏[M]//金石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4:156-168.
[2]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五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67.
[4]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M].上海:上海书店,2002:8.
[6]李华.唐赠太子少师崔公神道碑[M]//全唐文:卷318.北京:中华书局,第3230页.
[7]陈寅恪.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M]//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72.
[8]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M]//中国学术思想论丛:卷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9]温肇桐.唐朝名画录[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16.
[10]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