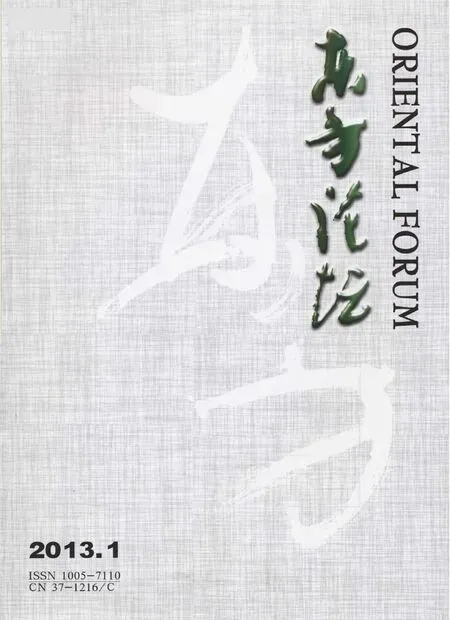明代官修边疆史籍特点述略
李怡 潘忠泉
(北京科技大学 人文素质教育中心,北京 100083)
明代官修边疆史籍特点述略
李怡 潘忠泉
(北京科技大学 人文素质教育中心,北京 100083)
明代官修边疆史籍颇具特色:边疆问题长期存在是明代官修边疆史籍的直接编辑动因,宏观层面指导边务是明代官修边疆史籍的根本编纂目的,中央地方上下联动是明代官修边疆史籍的特有组织形式,史事连续资料准确是明代官修边疆史籍的突出文献价值。
明代;官修;边疆史籍
有明一代,边疆史籍的编纂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明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明代边疆史籍是指明人所撰有关明代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等内容的专门史籍,包括明代边政史籍、边防史籍、边疆战争史籍、边疆民族史籍等等。明代边疆史籍的编纂发轫于明代初期的永乐年间(1403-1424),此后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至嘉靖年间(1522-1566),边疆史籍的编纂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活跃非凡并达到繁荣,这种发展态势一直持续到明末。这一发展过程,与明代边疆问题的发展相始终,明代史家以经世为目的的编纂特点非常明显,且官修与私修并存,形成了一个官私参与、共同投入、多向发展的系统工程。
从组织形式上划分,明代官修边疆史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机构出面组织,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进行相应的纂修工作,如兵部霍冀辑《九边图说》;另一类是地方督抚根据边疆战争或边疆治理的需要而进行的史籍修纂,如郑若曾《筹海图编》、邓钟《筹海重编》、范涞《两浙海防类考续编》、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等,这些史籍虽以个人修纂者的名义行世,但其修纂过程中,整个地方督抚于史料和资金等方面予以配合,书成之后又以官府的力量刊行,严格意义上属于官修。整体看来,明代官修边疆史籍在编辑动因、编纂目的、组织形式、文献价值等方面特点十分鲜明。
一
明代官修边疆史籍的编纂与明代边疆“北虏”、“南倭”问题的长期存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边疆问题是史籍兴盛的前提,而史籍的编纂又是边疆问题的集中反映。所谓“北虏”,是明人对不断侵扰其边疆的蒙古人的称谓。“北虏,东至兀良哈,西至瓦剌皆其地,而兀良哈以内附为属夷,别有传。其窜据沙漠为中国患,离合盛衰,代变靡常,大抵元遗孽也。”[1](卷5)明朝与蒙古的边疆军事冲突几乎与有明一代相始终,其发展态势大抵以隆庆年间(1567-1572)“俺答封贡”为标志,“隆庆和议”以前问题比较严重,以后有所缓和。双方的军事冲突在各个阶段的战争态势、目标和策略不断变化,而蒙古政治是在内部割据与统一斗争中演变的,其政治变迁先后主要经历了北元时期,鞑靼、瓦剌争霸时期,也先时期,达延汗时期,俺答汗时期和林丹汗时期,这种演变同时又与明朝密切相关。
洪武、永乐两朝,明朝侧重“以威服之”的战争政策,以武力消除蒙古贵族的实力,明显处于攻势。正统以后至隆庆俺答受封以前,蒙古方面还有也先“求大元一统天下”和达延汗恢复元朝的意图,处于主动进攻态势。明朝方面则由于国力衰退,军备废驰,处于全面防御态势。达延汗初期,为了集中力量统一蒙古,和明朝保持着和平关系,双方维持了十年的和平通贡、互市关系。弘治十三年(1500),双方又展开了战争,甚至终嘉靖一朝,北部边疆一直处于刀光剑影的战争状态。自隆庆俺答封贡至明末,双方态势持平,战事较少。此后,后金兴起,明朝和蒙古都成为其攻击的目标,明朝的边疆问题重心也转向了辽东。
所谓“南倭”,是指嘉靖年间倭患渐起,且愈演愈烈,成为举国震惊的大事。当时政治极其腐败,海防松弛,因此倭寇所到之处,无力抵御,倭寇“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2](卷205),不久又发生了争贡事件,明朝撤销了市舶司,海禁更加严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巨商、海盗便和倭寇相勾结,亦商亦盗,兼行劫掠。正当倭寇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明军中出现了两位抗倭名将,即戚继光和俞大猷。他们招募训练新军,依靠人民的支持,终于讨平了倭寇。隆庆到万历初,沿海虽仍有倭寇的侵扰,但势力不大,危害较轻,明朝军民对倭寇问题有所放松,“言倭事者略矣”[3]。
但万历年间(1573-1619),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使明代的海防危机重新出现。此时,明廷一方面加强沿海戒备,另一方面应朝鲜国王要求派兵入朝应援,“迎敌于外,毋使入境为上策”[4](卷4)。自万历二十年(1592)至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朝派军队两次入朝作战,援助朝鲜人民赶走了侵略者,同时粉碎了丰臣秀吉侵略中国的图谋,明朝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费饷银780余万”[5](卷412),但是却避免了百姓遭受比嘉靖年间倭患更大的灾难。此后,倭寇入侵十分衰弱,且在日本幕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之后,中国沿海的倭寇基本绝迹。除了“北虏”、“南倭”问题之外,万历以后的辽事问题、自明初到明末一直难以平息的南方动乱等问题,亦使明廷殚精竭虑、张惶四顾,不敢有须臾忘怀,深刻影响着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
从总体上来讲,明代边疆地区可谓险象环生、祸患接踵,这种严峻局面的出现,激发了边疆史籍修纂者在深层次上的思索。在忧患和危机意识下,他们自觉地将边疆史籍的撰述与筹边谋防加以结合,力图将史籍内容应用于实践。如杨时宁纂辑《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是有感于“祸患有形已久”,而边疆“形势之要害,兵粮之虚实,战守之利便,胡可不预闻也”,希望“是图也,(皇上)倘万机之暇试一观省,则指形胜而悉要害之处,核兵粮而知虚实之分, 审利便而达战守之机”[6],且“试一披览,而虏在目中,机宜在掌上矣”[6]。同样,为了抗倭的需要,郑若曾则是“追迹寇始,详稽典制,忝质风谣,即贼所入寇,岁月道路,克捷偾北,与今昔主客兵马馈饷之数,舟楫器械、战守屯戍之法,备书具载,凡为卷者十有三,盖后经世者据依矣”[7]。
二
明代有关陆疆的史籍自明初以来一直不断出现,数量众多,其中一些史籍很受朝廷的重视,有的在进呈御览之后得到充分肯定,甚至令边臣共阅。例如许论《九边图论》即是如此,“(许论)因著 《九边图论》, 上之,帝喜,颁边臣议行”[2](卷186)。但私修史籍在资料的获取上具有一定局限性,尤其是有关边疆问题,对有关军马钱粮、关隘城堡等情况的准确性有着极高的要求,如果朝廷能够出面进行组织谋划自是理想。尽管有着客观的需要,但长期以来明廷并未真正实施纂修行动,直至隆庆初年穆宗登基,命吏部品评州县、兵部品定所属各军镇:
各处府州县大小繁简冲僻难易不同,……士风日坏,吏治不修。吏部通将天下府州县逐一品第,定为上中下三等,遇该推升选补,量才受任,……其各将官所任地方,兵部亦以边腹冲缓分为三等,遇该升调,照此办理。(卷首《兵部题为仰遵明诏恭进〈九边图说〉以便圣览事》)[8]
在此情况下,自是需将各地实际情况上报,作为评定的依据,以尚书霍冀为首的兵部遂因势利导,将各地方军镇资料汇总,画图贴说,纂辑为帙,终成《九边图说》。
霍冀《九边图说》成书于隆庆三年(1569),汇集了当时九边镇的最新资料,内容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九镇,各有图说。每镇记载先述其地势险要、历史沿革、防御特点等,次之以官员配置及兵马钱粮数目。例如该书之中的《延绥镇图说》,先以总说:
延镇东起黄甫川,西止定边营,边长地远,为套虏充斥之地。然自神木迤东逼近黄河,难通大举,迤西直至石涝乾沟等处,环绕千五百里,虽有二边,倾圮已甚,不足为据。虏不来则已,来则必入,矧长驱无忌,关以内尤为可忧,该镇所系顾不重哉。考之先朝经略西事诸臣,如余子俊、杨一清、王琼辈,皆訏画鸿猷,脍炙人口。至究其所建置,则修筑先焉。……而建置仓庾,改征本色,未闻议及,皆今日之所宜汲汲者。
此后,以“本镇冲次地方文武官员并兵马钱粮数目”记载其军力、兵饷等配置情况,记载十分详细。
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的编撰与此相类似,它是杨时宁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应朝廷上报宣大山西三镇情况的要求,“檄三镇文武将吏各绘图条说”,并“谨集其成而裁核之,绘缮进览”[6]。该史籍共分三卷:第一卷宣府镇,第二卷大同镇,第三卷山西镇,全面保存了万历三十年(1602)前明朝宣大地区的军事防御资料。书首有宣大山西总图说,而后按镇、路、城堡逐级分别叙述,图文结合,详细地记载了三镇及所属各路、城堡的形胜沿革、边情兵略。可以说,这些官修陆疆史籍的编纂因客观需要而起,对宏观层面指导边务意义重大。
与陆疆史籍相对应的一系列海疆史籍的编撰,是由于嘉靖年间倭寇猖獗,但人们对倭寇认识却非常缺乏,正所谓“文墨之士不能详其本末,即缙绅枢筦者流亦与相忘久矣”,海疆防务任务艰巨,急需指导性的书籍。但是,有关海疆史籍的编纂与陆疆史籍“其舆地形势与书疏论著世多有而传焉”[7]的情况完全不同,该领域是一片空白,故一线主管官员征召贤者,动用官府的力量编纂而成:
少保梅林胡公徵昆山郑若曾辑《筹海图编》,制府箫公命晋江邓钟辑《筹海重编》,督抚刘公命海道范公涞辑《海防类考》,凡御侮机宜有成书可按矣。(卷首《凡例》)[9]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官修边疆史籍的发展态势既和明代整体出版事业的各个发展阶段相一致,也同边疆危机发展深度吻合:在嘉靖朝之前,编纂非常有限,而官修边疆史籍的大量出现是在嘉靖朝之后。据明代人自己的亲历,在嘉靖之前,得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生活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江阴人李诩曾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今(指隆、万)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10](卷8)李诩生于弘治十八年(1505),他学举子业大概是在20岁左右,即嘉靖初,这说明明代出版事业的勃兴、出版物的骤然激增,是在嘉靖中叶之后。《明代出版综录》也可从侧面进行佐证,其共著录图书7740种,其中洪武至弘治时期的出版只有766种,嘉靖至隆庆时期2237种,万历以后4720种[11](P2)。
三
明代官方对边疆史籍编纂事业十分重视,尤其各级地方政府如布政使司、按察院、分巡道、州、府、县等,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进行边疆史籍的编纂刊刻,遂形成中央地方上下联动的有效组织形式。例如,在《九边图说》一书的编纂中,首先是国家动员。在将诏书“抄捧到部”后,“送司就经呈堂咨行,各镇督抚军门将所管地方开具冲缓,仍画图贴说,以便查照去后,随该各镇陆续开报前来。或繁简失宜,或该载未尽,又经咨驳,务求允当。往返多时,始获就绪。”然后,兵部从主官到僚属整体投入,“本司稽之往牒,参诸堂稿,东起辽左,西尽甘州,……无不毕具,诚为简要。”当时兵部的参与者有“兵部尚书霍冀,左侍郎曹,职方清吏司郎中孙应元、赵宋,署员外郎事司务王凭,主事石磐、刘寅、朱润身、桂天祥、赵慎修”等[8]。总之,《九边图说》的纂修可以说是一次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体动员。
地方督抚衙门编纂的《两浙海防类考续编》、《筹海图编》、《筹海重编》、《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等,在组织上也是从督抚到总兵、副将及其他各级官员,直至幕僚等整体投入;在程序上正式行文、资料报送、各级官员行文指导催促、军马钱粮的查核,直至编纂、颁行等,各个环节组织缜密,法度谨严,全面确保史籍编纂的高质量完成。例如,范涞《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在立意纂修阶段,“大中丞瀛海刘公,并先后台察马公、吴公、周公,虑切同舟,计先未雨”,为了“固神灵威武”,谋划纂辑史籍,“画一周防可规万世”,意图在书成之后,“得是编而善守之”,则“萧何立法,曹参代之,守而弗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12]。立项之后,即行文督促:“本都院刘,宪牌前事,奉此为照,浙省东南一大都会,郡邑半临海滨,每年汛期,防倭为急,昔有《类考》、《筹海》诸书,规画亦颇详,悉第纂辑岁久,各区事务,增减渐殊,若非及时重修,可以昭示法守,遵经备行,布按都三司,兵巡海兵各道,总镇参游等衙门,将见在设备、水陆官兵、粮饷、马匹、战船、军火器械、地方关隘、驻劄、会哨、派守,及关钞军储,犒赏军需,船税钱粮,与夫征调应援,增益汰减各事,宜开册送核”[12]。书成之后,“报大中丞瀛海刘公,按台吴公,盐台周公,皆曰可寿之梓,逭愆忘时,前按台马公以代行业已授指,而中丞公复谕藩臬使宜有序不敏”[12],并“移文督促,如各区报到事宜,内别有新议可采,或系一区规制事可通行者,不妨斟酌详订,定为画一,其余悉照原行,校阅编辑施行”[12],从而完成了史籍的编纂和实行。
他如《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编辑之时,动员的各方面力量更是可观,除了要求三镇所属各部将地形厄塞,道里远近及士马分布等上报外,因涉及各个边疆防务的细节问题,在编辑和校正中,各级主管官员负责参与各自防区的有关纂修,而在整个过程中,钦差总督宣大山西的杨时宁为总其成者。如卷一《宣府镇总图说》署名是:
钦差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时宁纂集,钦差巡抚宣府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彭国光同纂,分巡口北道兵备山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张国玺、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分守口北道右参政郭士吉、整饬怀隆等处兵备山东提刑按察司副使马维骃同校正。(卷1)[6]
而在卷二《大同镇总图说》的纂集中,除了杨时宁仍是总纂集外,其他人员则是大同镇的主管官员,署名分别是:
大同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悌同纂,整饬大同左卫等处兵备山西按察司按察使樊东谟、分守冀北道兵备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兼佥事李芳、分巡冀北兵备道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兼佥事陈所学、整饬阳和兵备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刘汝康同校正。(卷1)[6]
其他各卷的编纂大体亦是如此。在修纂过程中,参与之人自是兢兢业业,不敢须臾大意,正如彭国光所言:
臣待罪宣府,罔裨边计,幸得督臣要束,与二三疆吏完陴缮鄣,简卒搜乘,广储除器,所为先雨绸缪,不敢有遗力。(彭国光《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后序》)[6]
总之,《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得以纂辑成书,可以说是宣大山西三镇边臣共同努力的结果。
四
明代边疆史籍编纂繁荣兴盛的直接导火线是边患的不断发展,但即便是边患,在有明一代的各个历史时期,分别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明廷对边患也必须做出各种灵活的富有针对性的反映,更何况明朝的边防策略、军马钱粮、武器装备、官员士卒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所以针对边疆问题进行总结和筹谋的边疆史籍修纂也必须根据客观需要和具体情势的发展不断展开,自是不可能靠一部史籍总揽全部。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一系列边疆史籍的连续出现,即以一代之书记载一时之事,并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时移事宜,进行新的总结和调整,以满足边疆治理的需要。
如有关“九边”的边疆史籍纂修,自嘉靖初年郑晓《边纪略》出现后,继之者不断,嘉靖十七年(1538)许论著《九边图论》、嘉靖二十年(1541)魏焕著《皇明九边考》、隆庆三年(1569)霍冀著《九边图说》,至万历年间刘效祖《四镇三关志》、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等史籍的出现更是不绝如缕。在这些史籍中,固然有内容上的承继,但更重要的是对当时当地边疆史事的总结和记载,既有对前代有效治边措施的发扬,更多的是对一些随着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而不合时宜的举措或记载的补正。正如霍翼在进呈所辑《九边图说》中所言:“及照先任本部(指兵部)尚书许论先为礼部主事时,曾奏上《九边图考》,嗣后本司主事魏焕亦曾续之,迄今近三十年。边堡之更置,将领之添设,兵马之加增,夷情之变易,时异势殊,自有大不同者”,因此,“移文各省督抚遵照旧例,每年终将建革缘由开报到部,本部随即更正”,纂辑成编,“庶筹边之士不必身履其地自可得闻其详,而他日经略疆圉者有所凭籍矣”[8]。
此外,这种连续性并不单单表现在对陆地边疆的记载,对海疆的记载也是如此。自郑若曾嘉靖四十一年(1562)著成《筹海图编》之后,继之以万历三年(1575)刘宗岱的《两浙海防类考》、万历二十年(1592)邓钟的《筹海重编》、万历二十九年(1601)范涞的《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万历四十一年(1613)王在晋的《海防纂要》等。其中王在晋所辑《海防纂要》,很大程度上是在全面总结前述史籍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编辑之时,他对海防事宜需要不断更新和总结的状况深有体会:“今所谓防倭要书,曰《筹海图编》,再缉为《筹海重编》,迩又纂为《海防类考》谟略具载,而近事或有所遗佚,又其书漶漫,间出于书生之腹笥,而未亲质于矢石锋镝之场,”故而“间常窃取”“指麾调度筹画机宜”,且“载籍旁搜,统括并述,中丞公所为谢咨计议有关海务紧要者,汇为一书,分十有三帙,名曰《海防纂要》”[9]。
同时,明代官修边疆史籍采用资料大多直接可靠。明代官修边疆史籍的撰述者大都是边事的直接责任者,他们要么是边疆事务的主管官员,要么是边疆第一线的战斗人员或幕僚,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在进行史籍撰述时能广泛地使用第一手资料,保证了史籍内容的可靠性,而他们进行史籍编纂的意图又是要能够在边疆治理和管辖的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所以又必须具有直接性。因此,这些史家充分认识到要想使自己的记载和研究取得真正效果,一方面需要翻检大量案牍资料,严密考证,除其伪而存其真,另一方面则需要进行实地的考察和亲身的实践,在此基础上,将公私牍牒和周历目睹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最终得出综合而详实的结论并载于书册,完成史籍的编纂。正如胡松在介绍郑若曾如何进行《筹海图编》的纂修时所言:
(郑若曾)有志匡时,窃观当时举措,有慨于中,念欲记载论著,贻之方来,即凡兴兵以来公私牍牒,近搜远索,手自抄写,最终成编。(胡松《序》)[7]
明代官修边疆史籍以其采用资料的直接可靠性,从而增加其著述的可信度,表现出了认真谨严、实事求是的学风。
此外,从明代官修边疆史籍涉及的范围来看,可以说有相当大的广泛性。其中有对边界、设施、城址、关隘的研究与考订,如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等史籍图画条说各镇的形胜、要害、边防情况;有对边疆防务的建立与发展情况的记载,如郑若曾《筹海图编》、邓钟《筹海重编》等对如何用兵、防守等海防问题记载尤详。总之,明代边疆史籍编纂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边疆地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记载和研究,完全突破了前代对边疆地区记载的局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具有突出的文献价值。
[1] (明) 叶向高. 四夷考[M]. 北京: 文殿阁书庄, 1934.
[2] (清)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 (明) 邓钟. 筹海重编[M]. 明万历刻本.
[4] 宋应昌. 经略复国要编[M]. 台北: 学生书局影印万历原刊本.
[5] (明) 陈子龙. 明经世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6] (明) 杨时宁.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M]. 南京: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6.
[7] (明) 郑若曾. 筹海图编[M]. 明天启四年(1624) 刻本.
[8] (明) 霍冀. 九边图说[M]. 玄览堂丛书本.
[9] (明) 王在晋. 海防纂要[M].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 刻本.
[10] (明) 李诩. 戒庵老人漫笔[M]. 四库存目丛书本.
[11] 缪咏禾. 明代出版史稿[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12] (明) 范涞. 两浙海防类考续编[M]. 明万历三十年(1602) 刻本.
责任编辑:侯德彤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ontier Historical Books in the Ming Dynasty
LI Yi PAN Zhong-quan
(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Center,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
The officially written frontier history in the Ming Dynasty is very unique. The long-term frontier problems were the direct motivation; macro-guidance of the border affairs was the essential purpose; and joint ac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ities was a uniqu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writing border history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accuracy of continuous historical data is its outstanding value of literature.
Ming Dynasty; official compilation; frontier historical books; purpose; value
K092
A
1005-7110(2013)01-0013-05
2012-11-26
本文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FRF-BR-11-011A。
李怡(1976-),女,历史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