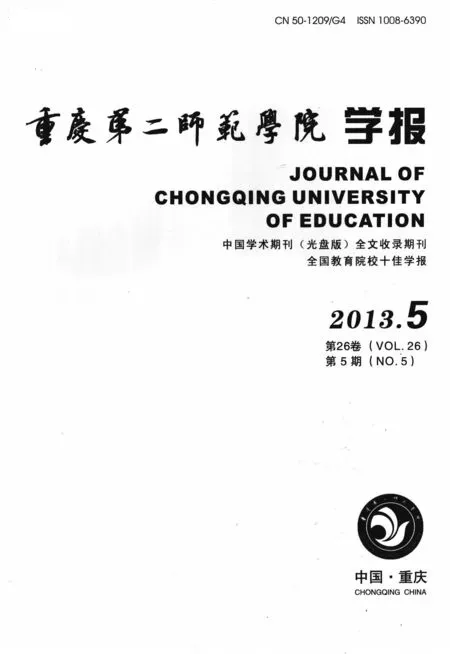我国古代文献整理中的功利性取向及其影响
刘家书,杨 婷
(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我国古代有关文献的整理活动不外乎书籍的辨伪、校正、编目、注解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以校勘、目录、版本为主的校雠学和以阐释、注解经典为目的的训诂学。而在这些文献整理活动中都存在着很强的功利性取向,表现在政府方面就是其文献整理活动中有着明确的统一思想、压制异端的政治目的,以整百家之不齐;表现在学者方面就是其文献整理所有的“文以载道”、“述先圣元意”的现实功用,其典型的例子就是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一、整百家之不齐
两汉的文献整理活动对我国古代典籍的传承起着奠基的作用,一方面中国的元典在这个阶段写成定本,另一方面,在两汉学者将这些文献写成定本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完善而又系统的文献整理程式。在这些文献整理活动中,其表现出来的功利性取向对于后世的文献整理活动具有很大的示范性影响。
《汉书》记载:“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刘向死后其子刘歆继续未成的事业:“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1]对于整理书册这些细枝末叶的工作为何关注有加,汉政府是有良苦用心的。
秦在统一了六国之后,虽然建立了强大暴力机器来保证统治层政策的实施,由于春秋、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处士横议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当时的知识分子——儒生——经常借经典之名对政府的政策横加指责、说三道四。对于这些儒生的聒噪,秦始皇甚为不满,于是进行了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活动,其中包括手段残忍的焚书坑儒。众所周知,秦始皇的这些基于暴力手段来进行思想文化统一的措施虽然堵住了儒生们的嘴,却也将知识分子推向了秦王朝的对立面,并由此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可以说其“焚书”的文献政策是失败的。章碣诗“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①就是对其的讽刺。
汲取秦始皇的教训,西汉的文献政策是宽松的,甚至是政府鼓励的,包括惠帝“挟书令”、武帝献书令,直至前述让“刘向、刘歆父子校书”诏书的出笼。东汉政府对于校书的热情更是有加无减,皇帝甚至亲自参加了讨论文献版本及解释的白虎观会议。宽松的文献政策下,经过几代学者们的努力中华元典得以写定、集结,而熹平石经就是其文献整理成果的一个真实写照。对于汉政府来说,元典的集结、经典文本的厘定不过是意识形态统一的副产品,借厘定经典的文本来统一思想、控制与笼络知识分子才是其根本目的。在中国历史上,纠缠中国文献史近两千年的“古今文之争”为汉政府宽松的文献政策实施之初衷做了很好的诠释:古今文之争不仅是对于传世经典文本的争执,更代表着两种施政理念的对立,其中的冲突与矛盾决定着政策的实施。经典文本的厘定及解释只是表达施政理念的工具,其原文、原意之究竟反而成为次要的东西。
为大一统的王朝提供理论支持、借统一文献来统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政府政策来讲,与直接的焚书坑儒相比其功利取向还是隐形的、不易被时人所察觉的。而紧随两汉的魏晋南北朝对于文献整理的重视,其功利性取向则是直接表露的。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点就是王朝对立。从三国开始的王朝对立,为了在斗争中取得有利地位正统问题被分外的关注。在争夺政治统治权的斗争中,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对于中华文化继承者身份认同的争夺。当时的社会风气认为文献图籍的拥有就是中华文化正统所在的表现,为此当时的各个王朝的统治者对文献的收集整理皆不遗余力。《隋书·经籍志》记载,东晋义熙十三年,刘裕攻进长安,曾嘲笑北魏藏书之少: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2]难怪后世的胡应麟感叹道:图籍废兴,大概关系国家气运,岂曰小哉?[3]
虽然各朝对于文献收集整理很是用力,但是由于其为争夺文化正统而服务,其功利性目的太强而导致大多成为无用功。以北魏为例,道武帝时期即“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者加以优赏”。后来的太武帝、文成帝、孝文帝、宣武帝、孝庄帝、孝武帝时期,政府皆有收集图籍、整理文献的行动。甚至还有《众文经》、《甲乙新录》、《魏阙书目录》等成果问世。然而随着尔朱兆入洛阳、北魏在内乱中衰落,大部分官藏图书毁于战火或散落民间,直到最后“才四千卷”。
这些用于显示文化续统的文献长时间藏于秘阁,其作为书籍被阅读利用的机会是十分有限的。况且政府长时间收集整理的文献,随着王朝的衰落一旦付之东流。长时间收集整理文献似乎就是为了在战乱来临时集体销毁掉它们,这样的悲剧在随后的隋朝、唐朝一再上演,到了明朝、清朝时期,这就不再是历史的玩笑,而成了历史的真实。其代表就是清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在编纂《四库全书》这个前所未有的浩大文献整理工程中,被清政府认为不利于其统治的书籍被大量销毁:对于抗清学者诸如钱谦益、屈大钧、吕留良等人的作品及其他文献中凡有“悖妄”、“轻浮”、“明季恶习”者,皆明令禁毁。[4]
总之,在政府主导的文献整理活动中,政府在保存与抢救珍贵文献的同时,在其强烈的功利性取向主导下也对文献的整理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一方面是书籍的收集、整理随朝代兴衰而聚散,文献破坏严重;另一方面就是政府在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为政治服务的价值取向导致对文献的解读、整理、取舍存有偏见,这些偏见导致部分珍贵文献被扭曲,甚至被销毁。
二、述先圣元意
不仅在历代政府主导的文献整理活动中存在着很强的以“整百家之不齐”为代表的政治功用,在私人学者的文献整理活动中很强的功利性取向也存在着,其典型代表就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思想的高扬。
学者冯友兰曾把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经学时代学者“有无新见,皆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5]。这个划分与中国古代史常识有矛盾,若严格按照冯友兰的定义,经学时代从孔子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孔子宣传自己政治主张大多并不是直接提出自己的观点,而是以《尚书》、《诗经》等上古文献中的表述为自己立论,用文、武、周公等先代政治领袖为自己代言。这样的表述在论语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在宣传自己的主张,而是在“述先圣元意”。这与孔子的生活时代及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春秋时期周天子权威不再、诸侯起而争霸,面对礼乐崩坏的社会现实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的主张,希望用礼的约束来安定混乱的现实。其实践就是他以“微言大义”为标准而进行的一系列的文献整理活动,其代表就是删定《诗》、《书》和据鲁史而作《春秋》。孔子通过点校、解读这些上古文献,表达了他明确的价值取向。在对于尧、舜、禹、文、武、周公等先代政治领袖的颂扬与膜拜中,寄寓着孔子强烈的现实关怀:通过对明君贤臣的礼赞和对于暴君庸臣的鞭挞,把政治的合法性演绎为道德上的说服力。以孔子作《春秋》为例:《春秋》的作用不只是记录历史,更多的是微言大义、在褒贬中表达作者的政治观念,有时为了尊周甚至不惜篡改史实。孔子“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在这种道德化的历史中,历史不再是一个过去的事件,而是成为普遍为社会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判断,从后来的“春秋断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认同在整个社会意识领域内化到了何种程度。如孟子所说不能“以辞害志”,记载文献的“辞”如果妨碍了自己的政治宣传目的,无论真假曲直似乎都应该弃而不顾的。
可以说在孔子的文献整理活动中,“述而不作”是其指导思想。对于古文献内容的“述”,即删或留完全服务于其政治宣传目的,特别是传说中孔子删诗、书的篇幅,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这些传说的真假且不追究,对于孔子为了其政治理念而对历史事件或人物而故意扭曲史实给予赞扬或是贬低,则是没有疑问的,其功利性取向所造成的伤害主要在于对古文献的“删定”,而在另外一些学者私人的文献整理活动中,其功利性伤害则主要在于“述先圣元意”的价值取向之上对于文献的解读。借鉴冯友兰的“经学时代”的概念,这样的功利性取向可以表述为:在提出某一观念时,热衷于从经典中、从先圣们的言行中去寻找根据,有时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古已有之”,不惜曲解古籍。
依傍先圣言论来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增强说服力,这样的做法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学者们“我注六经”时其归宿不是真正的阐释经典,而是为了让“六经注我”,这种过分的功利性取向就值得商榷。极端的例子就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了“托古改制”康有为不惜捏造史实,以得出“孔子托古改制”等荒诞的言行。
历代经学大师的“我注六经”,大都如郑玄所说“述先圣元意”[6]。解读经书为的是探求古圣贤的思想,为的是在经典中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对此,宋代经学大师朱熹的理论有着普遍的代表意义。
朱熹十分推崇孔子述而不作的文献整理观。述,就是借助整理文献、借助对于经典的注解、诠释来阐发思想的创作方式,朱熹正是对于它的利用而构建起了他的理学体系。
在朱熹看来,诠释与解读经典需要经过三个境界,就是:理解经文原义——理解圣贤原意——读者所悟之意。对于经文原义和圣贤原意,朱熹说“唯文本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本文原义、圣人原意都应求解,而且正是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理解来认识和理解圣人。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中论述道:文献整理工作就是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朱熹的观点是完全可取的,但是他又说“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乎经”,在这里,因为经典中蕴含着“天理”,解释经典就成了通“天理”的手段和途径。这个解释归到最后就是“读者所悟之意”,就是解释者的主观体会:“从浅近平易处理会,应用切身处体察,渐次接续,便能领会其无穷之意趣”。[7]
朱熹的“悟”,又回到了个人经验的起点。经典文本是一样的,而个人由于经验的不同对于文本的解释是有出入、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就像对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②句,不同的句读有着对立的表达意义,而朱熹为代表的文献解释的观点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文献的整理过程就是复原文献真实的过程,而恢复文献的原文和作者的原意是为了保证被记载的历史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保证作者真实思想在后世的传达,在“六经注我”的观念里,“对于文献的复原”是很难实现的。
三、总结
政府层面来说,对文献进行或明或暗的管制以为其政治需要服务,无论是对于当时代不利于其统治的文献传播的限制,还是对于尚存远古文献的文本方面的争论和解释的扭曲,在中国自秦以来的各朝代都存在着。功利性取向驱动下,这些限制、争论和扭曲对于文献保存、整理、解读所造成的伤害都是非常严重的,而为了达到维护其统治阶层利益的目的,政府对此并不以为然。
同时,在孔子“学而优则仕”的积极入世思想鼓励下两千年来中国的私人学者们对于古文献的整理、解读方面的“学问”也大都是抱着很强的功利性目的而进行的:其文献整理和解读并不仅仅是钻研学问或闲暇消遣,而是要在整理和解读中借助经典之名阐发自己的政治理念、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这与我国古代文人、儒士的性格是相符的。所谓“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或得志或失意的文人对于“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的追求则是一样的。在这样功利性的价值取向上而进行的文献整理和解读,其“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思想之存在就不再让人感到费解和疑惑,与此同时,在他们的文献整理活动中也就难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而给文献真正的整理、解读带来干扰。
无论政府、还是私人学者在进行我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功利性取向归根结底表露的还是“求真”与“实用”的关系。我们不赞成空做纸上功夫,比如梁启超的观点把文献学定义为史料学,对于文献学的建设和发展就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学以致用没有错,只是在用的过程中不能扭曲了文献。在涉及古籍文献整理的活动中,不能任由需要来处置文献的文本、对其内容做主观的取舍,甚至湮没、销毁不利的文献。更不能置事实于不顾,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来任意解读文献。可以看出,不论康有为的从政理念如何,他代孔子立言、借扭曲经典来为自己变法行为辩护的做法不仅没有得到同情,反而招致了当时士大夫的集体抵制。急功近利的做法是并不可取的。如果人人都像康有为那样随意歪曲经典,在解读中把经典搞得面目全非,对于我国古代文献的整理、保存、利用必定是一场灾难。
注释:
①出自唐代诗人章碣所作《焚书坑》。全诗为: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②语出《论语·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原文既可以断句为“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可断句为“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这两种断句,解读出的意思是完全相对立的。
[1]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1.
[2]魏征.隋书·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907.
[3]转引自高俊宽.从校雠学到文献学:中国文献学理论认知的轨迹探讨[J].图书情报工作,2002,(10):118.
[4]王俊杰.文献学概论[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58.
[5]转引自王国强.汉代文献学的特点及其对汉代学术的影响[J].郑州大学学报,2005,(2):29.
[6]范晔.后汉书·郑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1209.
[7]潘德荣.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J].中国社会科学,2002,(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