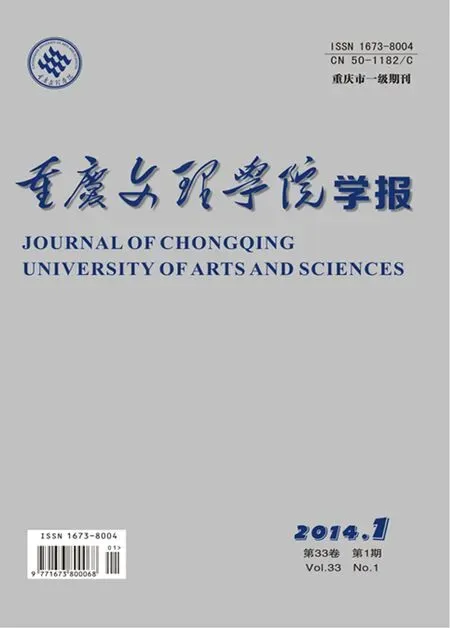未竟的现代性
——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
余红艳
(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未竟的现代性
——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
余红艳
(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现代性是来自欧洲启蒙运动并迅速全球化的哲学理想,现代化是其社会图景。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初期的启蒙救亡、中期的政治遽变、“文革”后的经济建设,至今仍在现代化过程中努力前进。然而中西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形态,决定了现代性进入中国后的曲折与变形。20世纪的中国文学被捆绑在现代化之路上,其审美特质与自主精神都必然受到特定时期历史社会的影响。
现代性;现代化;审美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
20世纪的中国是“现代化”的中国。“对于‘现代性’的想象以及渴盼社会迅速‘现代化’的理性构想和情感诉求”,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中心内容[1]。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便作为一个阐释代码在中国20世纪研究中崭露头角。“现代性”成了社会思潮和文艺现象的关键词,并渐渐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特质之一。然而,大多数人对“现代性”的内涵缺乏准确把握,因此本文将首先溯源“现代性”,再把文学与文学主体的命运置于“现代化”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加以观照,以增进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文学所处境遇的再认识。
一、现代性的源起
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以销毁宗教神权、打破封建专制、建立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为目的。现代性便发轫于此。但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通常限于社会学领域,即现代性意味着个体独立、资本经济与民主政治。吉登斯说:“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2],内含四个基本制度:资本主义、监督、工业主义和军事实力。然而现代性本质上是一个哲学理念,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来自启蒙精神,其实质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坚持理性存在与进步观念。于是,哲学界产生了孟德鸠斯的“法治理性”、伏尔泰的“天赋人权”、康德的“人是最终目的”等思想,社会领域迎来了以法国大革命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现代性产生于实践,并回归指导实践,整个过程伴随着社会变革和思想转化。而变革和转化过程就是今天常提的“现代化”过程。
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表述途径之一,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存在。韦伯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以及‘自我’的发现,引发了客观意义上的‘自然’的发现,进而推动实践领域中的道德自律、政治自由与审美领域里的艺术自主原则。”[3]现代性于是扩展到审美领域。
美学家卡林内斯库进一步将现代性发展概括为两股潮流: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高举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大旗,以科学技术为工具,以民主政治作保障,为改造人生和社会进步而奋斗。启蒙现代性主要体现为社会外在结构,包括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契约精神、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等。审美现代性来自人的内心结构,重在人的自我阐发,坚守文艺的自主性原则,不受外界干扰,不随社会而动。从卢梭退居田园,到席勒的游戏说,到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4],从《恶之花》到《尤利西斯》——审美现代性就始终表现出对现代化社会的批判与不合作态度。因为审美现代性产生于启蒙现代性,主张人的特征、美的特征、超越的特征,希望在反思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中重构人的信仰、价值系统,故而一产生便持有反传统、反进步、反理性的姿态。
二、未竟之路:20世纪中国以及文学的审美现代性
现代性在晚清进入中国。入驻中国的现代性,早已包孕了卡林内斯库所谓的两股矛盾冲突的潮流: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纵览20世纪一百年的时间里,现代性在中国的境遇基本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清末到民国是启蒙与审美的合奏;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遭到民族国家与共产主义的联合抵制;新时期再次兴盛,然而激情与梦想却被现代化和后现代瓦解一空。
(一)启蒙与审美的合奏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严复《天演论》,直到20世纪初,现代性方才在中国扎下根来。时值内忧外患、生死存亡之际,“启蒙与救亡”成了社会主题曲。来自强大西方之现代性,正满足了中国复兴的渴望。因此,中国对现代性的最初反应主要集中于思想意识与社会政治层面。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五四运动,都是中国人对现代化国家的想象的集中爆发。
但是,民国没有真正树立起现代性,启蒙也不彻底。要知西方现代性是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下挣脱而出,且有16世纪文艺复兴做铺垫。中国人却是在坚船利炮的打击下被迫接受西方思想,被迫承认中国贫弱落后的事实。此前的中国人,一直怀着以“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去度化四夷的帝国心态。所以,启蒙之不彻底,首先就在于政治、经济、军事层面的变动并不能撼动广大国民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心理;其次,文化启蒙者也并不真心拥护西方的理性与科学至上的现代观,他们对西方文明态度时有反复。如陈独秀,一面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5]一面又批评西方社会不平等,赞扬孔子的“均无贫”和许行的“并耕”。另外,西方自身现代性危机的呈现与暴露,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启蒙的态度与进程[6]。
中国文学,却凭借中西古今、风云际会之机,制造出了一场热血沸腾、情绪激昂的大戏。五四前后的局势演变给了文人自由发挥的历史契机,政权更迭让他们获得了充分言说的内容与空间,文学的形式和观念因而表现出多样态存在: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革命文学、通俗小说纷纷上台,展演自身。救亡?启蒙?审美?孰轻孰重,文学界吵成一片。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社会变革派,秉持文艺改良社会观,将文学与政治联姻,把政治小说推到最高。反之,王国维的“为人生”文学观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和游戏功能,他批评古代中国文学家的创作:“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7]启蒙与审美的论战到30年代以后变得激烈。冯雪峰认为艺术要为政治服务才能获得价值。胡秋源主张文艺与政治分家;朱光潜提倡“纯正的文学趣味”;沈从文也说:“1929年的新文学运动,又与国内政治运动不可分,成为在朝在野工具之一部……也就看出一点堕落倾向。”[8]启蒙强调对现实的正视与反映,审美强调张扬个性与主观精神,二者逐渐演变为“左翼文学”思潮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对立,引发了文学何为之争。
鲁迅则同时展开启蒙与审美的追求。他既描述“世风之变”与“文学之变”的关系:“光绪庚子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9]又认为“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10]83在鲁迅看来,文学既要有强劲有力、积极反思的批判精神,也要坚持审美的独立性。弃医从文更能察其对科学与审美的不同态度,他说:“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门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所谓门机,即人生之诚理是已。”[10]83可见,鲁迅实际是个怀揣火热情怀和革命性格的文学家,对社会、人生、人性的洞察力和表达力使之成为了卓越的思想家。总之,鲁迅是少有的能将启蒙思想与审美艺术完满结合之人,在他这里,审美并不排除启蒙。
自先秦以来,中国文人尤其是儒家,秉持内圣外王、穷独达兼、治国平天下的自我实现理想,希图“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以著书立说、积极参政。然晚清列强侵侮,时局动荡,加之1905年废除科举,知识分子参政的途径被一一切断,逼使知识分子重新寻求话语空间。当接触到西方现代性时,他们感受到巨大能量,于是紧握“现代性”作武器,充当起民众的精神文化导师。这种自觉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追求,为他们获得了新的生存“广场”[11]。他们呼唤“大写的人”,高喊“去礼”“非孝”“打倒孔家店”“反封建主义”等口号,欲把个人从传统社会与儒家伦理观中解放出来,欲打破中国僵化封闭的文化体系以推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然而,在这股启蒙大潮中,一些文人初衷不改,他们注重文学本身的价值,即使国难当头仍坚持纯文学、审美文学,虽遭到诟病和不懈,被批为“无用”,依然我行我素。他们批评文学实用性与功利性,自在地活着,自由地观照,自我地写作。他们其实有现代性渴望,也有迷惘和失落;对心中的乡土桃源,他们一面赞美,一面悲悯;一面批判,一面想回归……不管如何,此时的文学界处于比较自由的状态,文学创作者独立不羁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作家能遵照自己的真实内心去体验、去感悟、去写作。可以说,五四启蒙并不成功,现代化也未上道,但文学的独立、自主却实现了,审美现代性成绩斐然。然而,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这一时期的审美现代性:探索汉语的现代性转型,提倡白话文写作;以保守发展为主,不主动针对启蒙现代性;守住自身一方净土,不参与乱世纷扰。究其原因,中国刚刚引进现代性,中国确实需要现代化,现代性也还未暴露出严重后果。
(二)国家和主义的共谋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中国政府的精力主要放在社会基础建设和政治制度转向上,这是历史情境和意识形态所必须。一方面,数十年内外交战,中国大地遍布疮痍,羸弱不堪,亟须提升。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绝对地位。新中国经土地改革、人民公社、三反五反、整风运动、大跃进等,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大步向着共产主义理想迈进。
西方现代性到这里是否荡然无存了?不尽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虽然狼狈退出中国舞台,现代性却仍然残留,尤其是关于“民族国家”这部分内容,被推上了最紧要的日程。18世纪以来,西方经过启蒙和大革命建立起一个个现代化民族国家。而中国民众在近百年的外族入侵、军阀混战以及解放内战中,早已累积对一个富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丰富想象与热切渴望。新中国成立正应和了百姓的愿望。因此,新成立的国家即使为应对生存危机,也不能抛弃现代化道路。所以毛泽东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只是“四个现代化”里不包括现代性中的人本位思想和资本经济。首先,绵延千年的礼教束缚,互助的群居生活,平和的民族心态,使得中国人大多不追求个性和自由。其次,农耕文明的自给自足,社会对经济的抑制,世人对商人的贬斥,使得资本经济在中国难以壮大。再次,中国文人抱有世界和平、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马克思主义呼应了这个理想,而共产主义是反思资本主义的产物。最后,新中国的烂摊子,也要求集中所有能动力量去收拾。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似乎只能是:同心同德搞社会主义建设;个人意志必须服从国家意志,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
由此,西方现代性在新中国只保住了“民族国家”和“宏伟叙事”,“个人主体”和“资本主义”被剔除出局。但强烈认同这个新兴民族国家的文人心甘情愿甚至不乏欢喜地参与到“民族国家”的“宏伟叙事”中来。文人的现代性理想没有破灭,至少留在大陆的文人对新中国还抱有美好幻想。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热情讴歌伟大新时代的来临。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婉拒胡适的赴台邀请时说:“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12]
假如五四时期是“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语),那么新中国的主旋律则变为“建设压倒审美”。很快,文学被纳入国家框架,被国家统管和安排了。文学变为工作,文人成了单位人,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潮之中。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毛泽东提出“人民的文学家”这一称谓,由此确定了文学工作者的任务,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和工农兵服务。50年代后,“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了硬性规定,要求作家必须贯彻执行。“政治的文艺”占据了最高阵地。兴起于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左翼文学,在毛泽东1942年延安《讲话》后成为革命文学,到新中国则跃升为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学。现实主义成为常态,“开始严格而全面地整肃文学领域的规范———从文学史描述、作家协会奉行的纲领、文学想象的来源到形式或者美学风格类型以及人物性格的解读。”[13]自由主义、现代主义等非主流文学成为改造对象,被贴上“资产阶级”、“颓废主义”“个人主义”等标签而最终丧失了地位。文学工作者的话语由“革命”“人民”“阶级”“解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组成,文学工作者被要求体验生活,书写新中国的日新月异,歌颂共产党的伟大胜利。在这种创作方针指引下,文学失去了对人的真实把握,大量作品变成观念与政策的图解,作家创作个性丧失,人文关怀弱化。建国十七年来,在宏伟叙事的框架内,虽产生过一些颇为优秀的作家作品,《暴风骤雨》《红日》《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红岩》《创业史》等,但一些杰出作家的独创与灵感也被扼杀殆尽。如沈从文就直言“框框太多,无从下笔”,转而钻进故纸堆中研究起服饰。
此时,作家虽然享有国家给予的历史合法性和一定地位,却也从此成为政治的附庸。一旦失去政治地位,他们的一切都将消失,身份、供给、福利,包括写作的资格。所以,十七年中,作家必须把自己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文学只能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情感和形象的依据,较少反思;主要为宏伟叙事,类型化叙事,作家的主体性被湮没。十七年来,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大跃进”,文学的审美现代性近乎消亡。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与此前的历史铺垫一脉相承,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必然到来的“高潮”。文革鼓动一种打倒一切,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精神,从传统的“三娘教子”转向“子教三娘”,看起来似乎与传统桎梏全然断裂,人人得了自由,人人享有平等,中国似乎已经踏上了一个纯粹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的巅峰。但实际上,文革打倒一切权威,却树立了一个最大的权威;清扫一切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却培育了一种最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并形成了一种前现代的野蛮倾向和反西方、反现代的“怨恨情绪”,是中国本土现代性之“革命”精神的疯狂展演,是西方现代性的大清退[14]。十年中,现代化建设遭到破坏,科学理性精神基本失去,社会公平正义无从谈起,文学艺术沦为政治斗争的器物。革命文学发展到极端,文人尊严丧失,连性命也全然不保,何谈审美现代性?
(三)激情与梦想的踏空
李欧梵说:“革命与战乱,而革命是否可以当做是现代性的延伸呢?是否可以当做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延伸呢?是的。整个20世纪都在延展现代性。还没做好,就开始后现代了。”[15]这句话可以作20世纪的总结语,也可以作文革到新时期的过渡语。确实,“十年文革”是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毁灭性”建构,没有“十年文革”的惨痛失败,西方现代性的反弹不至于这样猛烈。80年代,又的确是现代性之“现代与后现代”同声喧嚣的时代。
学术界将80年代称为新时期,或新启蒙时代。回望一下现代性在中国的坎坷路途:初期遭遇本土文化的坚硬内核,中期碰了民族国家的钉子,到如今才算被真正接受并全面推行。称80年代为“新启蒙时代”确实比较中肯。
“文革”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改革开放,思想界中西交汇,学术界百家争鸣,中国迅速从思想禁锢和物质匮乏中解脱出来,重新走上现代化发展路途,成为西方现代性之一员。此时,中国的话语形式由革命斗争转到发展经济,文学也不再提“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开始走上独立思考与创作阶段。文学家们致力于寻求文学的规律性和艺术性,寻求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文学的回归”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文学回归到感性、形象、情感的审美本性上来。
首先出场的是朦胧诗人,作为急先锋,他们大声宣布新美学时代来临。诗人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仅仅“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16]。小说也开始转向人的内心写作。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陆续出现。刘心武的《班主任》,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蒋子龙的《开拓者》,个人化特征逐渐凸显,作家开始关注人的命运,人的价值。随后,文学从意识形态的历史化层面转向了语言本体层面,转向了个人化经验层面,从“假大空”回到了对世界和人性的审视。出现了由宏大叙事转向多重叙事、小叙事的“非历史化”叙事;出现了以荒诞手法展开对“前现代的悠远追怀(王一川语)”的寻根小说。实验小说、先锋小说里,既有现代性的主体张扬,也有后现代的主体解构。许多文学作品倾向于文字和智力的游戏,展开对文学形式的极致探索。新时期,大众文学、通俗文学流行。而针对无意义、无主题写作,新写实与新现实主义作家企图力挽狂澜,还原生活琐碎庸俗本色。
总之,80年代与五四时期遥遥呼应,政治暂时解禁,经济强力复苏,个人登上舞台,社会迸发活力,中国的现代化车轮轧轧向前。文学也被激活,显示出勃勃生机,文学队伍空前壮大。文学工作者虽没有脱离国家体制,但已部分拾得了自由身,获得了“专家”地位,不再被政治统领。文学饱含非理性精神,强烈反拨着前期政治化文学,个体化、多样性在文学领域里展露无遗,文学的审美现代性特征得到充分发挥。王富仁认为,中国八十年代文学是“把中国文学提高到现代性高度的文学,是体现着中国文学家对文学的现代性理解的文学,是表现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的感受和情绪的文学。”[17]
在类似狂欢中,文学迎来20世纪的最后十年。苏联解体表明世界正越来越清楚地被西方资本主义占据,中国只有更快地发展现代化才能进入全球话语体系。“白猫黄猫”论,“发展才是硬道理”,“南巡讲话”等,一次次把中国现代化的目标锁定在迅速挺进全球化经济生产和贸易中。因此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18]可以想见,发展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政治法规、科学与人文,将是未来整个社会的主要任务。
90年代,西方现代性继续在中国制造经济神话,但却是单向膨胀。作为制度保障和精神支撑的法治、契约、公平、正义、人权等难以跟进,现代性的后果便益发严重。经济腾飞带来贫富差距和生态恶化,商业竞争和消费欲望被激活,传统价值观沦落,贪腐成风。作为社会与人心衡准器的文人与文学在何处?反思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在何处?
随着全球化逼近,传统文化体系崩塌,个人解放后的轻松感带来无所适从的茫然,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个人失去了稳定感和归属感。文人和文学面临着自我身份认同困境,这时期的文学便体现了自我存在感的缺失和焦虑。新生代和新写实文学已经彻底生活化,对生活的专心投入彻底取代了对革命和政治的书写热情。朱文的《我爱美元》里,一边是对欲望的满足快感,一边是满足后更深层的挫折。池莉的《来来往往》里则太多平面化生活和戏剧化情节。接着解构潮来临,文学开始化解历史、消解永恒,描述偶然、片段、无意义。刘震云用《故乡面和花朵》解构了传统叙事,王安忆《长恨歌》则构筑了一个语言乌托邦。林白、陈染的女性写作,深度揭示了女性的自我监禁与自我丧失。陈忠实、苏童、叶兆言、阿来的新历史小说,张炜、余华、曹文轩对特定历史阶段的挖掘,都在历史书写中避免了“沉沦于世和封闭自身”[19]。某种程度上,此时的文学延续了80年代的审美现代性道路,回归人心,剖析人生人性,向多维度拓展新的书写疆域。不仅如此,文学甚至已经超越现代性,走向了后现代。
产生于60年代的后现代几乎和现代性一起造访中国。当后现代嘲笑中国新启蒙现代性的不合潮流时,却没注意到西方现代性已经几百年,中国的现代化才刚刚起步。因此,中国后现代只是西方的拙劣照搬,来自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警告丝毫不能阻挡,甚至更坚定了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的决心。但后现代文学的出现却再次表明文学不与社会同步,不考虑外在因素,有其自主发展轨迹。只是,后现代文学的颓废虚无,提前揭示出世界的无意义,极大地消解了80年代的激情与梦想。
文学解构了世界存在的意义,而打破文学虚构世界的却是另一种力量。90年代文学有个特点,不谈政治。80年代,在政治的宽容与鼓励下,作家通过书写苦难,为迎接新时代做铺垫性叙事。当文人过度介入政治时,毫不留情的挫折劈面而来。经过特殊时期的洗牌,文学对政治的态度益发晦涩:要么嘲讽、解构政治,用高超的手法来批评政治;要么,全然脱离政治,甚至脱离社会生活,将文学孤悬于现实之外。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渐渐疏远。文人在生活里,在历史中,在概念里玩得不亦乐乎,但就是不谈政治了。从只谈政治到不谈政治,这都是不正常的。中国是政治化国家,文学避开这个最大的现实,能谈什么呢(川大李怡教授语)?莫言:莫谈政治,谈文学。“莫谈”后的潜台词实在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仍然未能充分实现。
三、结语
20世纪,西方在不断反思和推进现代性,非西方在不断追赶变化中的西方。至新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还远未实现。中国的思想界和社会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太多:如何使现代性中国化?如何使中国全球化?如何规避现代性危机?如何保证人的生命质量?在这过程中,非功利的具有审美现代性的文学将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起某些责任。20世纪的中国文学,身处风起云涌的时代交接点,其审美现代性直接受制于外在世界。文学一直在西方现代性中国化的历史语境中左冲右突,寻找出路。因此,新世纪的文学,要做到既不迎合,也不羁绊,要走好自己的路,真正实现审美现代性,还需付出极大努力。
[1]耿传明.“现代性”的文学诉求——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性考察[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12.
[2]吉登斯,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69.
[3]耿传明.“现代性”的文学诉求——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性考察[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13.
[4]张万盈.传统与现代:比较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审美现代性[J].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4):58-62.
[5]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9. [6]高力克.五四启蒙的困境:在历史与价值之间[J].浙江学刊.1999(2):5-12.
[7]钱中文.曲折与巨变——百年文学理论回顾[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6):45.
[8]沈从文.沈从文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102.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252.
[10]鲁迅.摩罗诗力说[G]//陈雪虎.中国现代文论新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83.
[11]周保欣.“文学”祛蔽与现代性起源[J].文艺研究,2003(4):154-155.
[12]《学着独立思考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 blog_485324f90101mmyp.html.
[13]南帆.现代主义、现代性与个人主义[J].南方文坛,2009(4):6.
[14]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15]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J].文学评论,1999(5):131.
[16]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G]//吴思敬.中国新诗总系9:理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538.
[17]南帆.现代主义、现代性与个人主义[J].南方文坛,2009(4):11.
[18]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天涯, 1997(5):7.
[19]肖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全球化与自我认同[J].文学评论,2000(2):110.
责任编辑:黄贤忠
Incomplete Modernity——Additional on the Aesthetic Modernity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YU Hongy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China)
Modernity is the global idea of philosophy from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and modernization is the social vision.In 20th century,China has three stages,national salvation and enlightenment,unstabl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oday,China is still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the modernization.However,because of many cultural and soci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the entry of modernity into China faced many twists and variations.The Chinese literature was tied up in the way of modernization in 20th century,thus,its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independent spirit were destined to be influenced by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society.
modernity;modernization;aesthetic modernity;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I206.7
A
1673-8004(2014)01-0053-06
2013-09-19
余红艳(1981-),女,四川眉山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