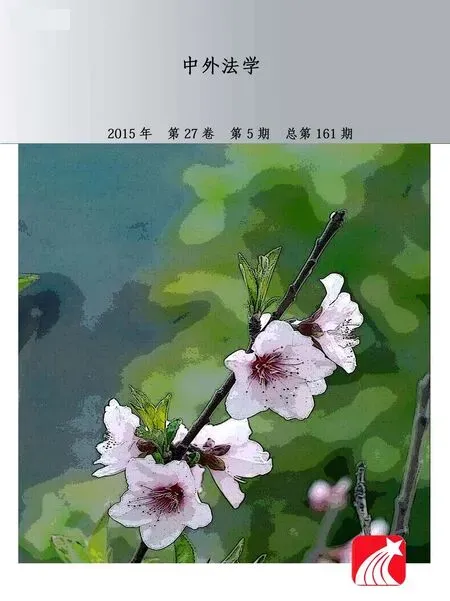防卫过当的认定与结果无价值论的不足
劳东燕
防卫过当的认定与结果无价值论的不足
劳东燕*
当前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在防卫限度上采取严苛的标准,防卫过当则一般按故意犯罪来处理。它是实务中唯结果论倾向的产物,结果无价值论则为其提供了理论性支持。结果无价值论的“结果→行为”思考进路存在缺陷,这是由立基于法益衡量的优越利益原理所致。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应定位为个体权利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由此,在解释《刑法》第20条第2款时,应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理解为两个独立的条件,前者涉及行为限度,后者涉及结果限度。有关行为限度的判断,有必要采取行为时的一般人标准。在防卫过当的场合,若确定行为人存在罪责,应优先考虑成立过失犯罪;只有蓄意滥用权利的情形,才有成立故意犯罪的余地。
防卫过当 结果无价值 正当防卫 正当化根据 法益衡量 行为无价值
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在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上,采取的是不同的立场,前者试图从所保护法益与所损害法益的权衡中去寻找阻却违法的根据,后者则努力从防卫行为本身为行为规范或社会伦理秩序所容许的角度,来诠释正当化的理论基础。在正当化根据上所持立场的不同,必然对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解释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意味着,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间在正当防卫领域的意见分歧,会波及对防卫过当的认定,包括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以及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的认定,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
本文拟由防卫过当切入,结合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争,来审视当前防卫过当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所在。本文认为,我国当前对防卫过当的认定,由于深受“结果→行为”思考进路的影响,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有必要在考察实务做法的基础上,反思我国结果无价值论的不足,抛弃其“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重新界定正当防卫正当化的理论根据。只有这样,才能对《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做出妥当的解释,并在具体个案中实现对防卫过当的合理认定。
一、当前防卫过当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1997年的《刑法》修正,对正当防卫的规定做了重大的立法修改。除增设第20条第3款的特殊防卫之外,又将防卫过当的标准由原先的“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改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立法修改的目的非常明显,意在放宽正当防卫的成立标准,以纠正此前普遍存在的对防卫限度的把握过于严格的做法。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对这样的立法目的均有清晰的认识,且表现出支持的态度。〔1〕参见赵秉志、肖中华:“正当防卫立法的进展与缺陷——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十九)”,《法学》1998年第12期;沈德咏、戴长林:“完善刑事立法强化公民的正当防卫权”,《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不过,从迄今为止的立法施行效果来看,对正当防卫成立标准把握过严的倾向并没有得到扭转,尤其是在防卫过当的认定上。
一方面,无论是学理还是实务,对是否超过防卫限度的把握仍然偏严。具体个案中,只要受保护的法益小于受侵害的法益,特别是在出现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情况下,防卫人便容易被认定为防卫过当。
对限卫限度的把握过严,缘于通行的标准采取的是以基本相适应说为基础的折衷说。在防卫是否超过“必要限度”的问题上,历来存在基本相适应说、必需说与折衷说(也称适当说)之争,其中,基本相适应说与折衷说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早期学说在防卫限度的标准上,便强调防卫强度必须与不法侵害强度相适应,认为应始终“以不法侵害的强度(包括行为性质、方法手段、工具、作用力量的程度、作用部位以及行为人的特点等等),来约束防卫行为的强度,使之不超过不法侵害的强度。”〔2〕金凯:“试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这种防卫强度必须与不法侵害强度相适应的观点,虽然在之后没有占据通说的地位,但却构成通说所主张的折衷说的基础。
早期主流的教科书中,对防卫过当的判断采取的便是折衷说,认为防卫的必要限度,是指防卫人的行为正好足以制止侵害人的不法侵害行为,而没有对后者造成不应有的危害,主张应将基本相适应说与必需说结合起来进行判断。〔3〕参见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页153;何秉松主编:《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页121;马克昌、江任天编著:《刑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页53。在1997年立法对正当防卫的规定做重大修正之后,我国刑法理论仍压倒性地坚持折衷说。〔4〕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页134;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201;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147;赵秉志主编:《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392。折衷说宣称要将基本相适应说与必需说相结合,但其实与基本相适应说并无本质区别,二者之中,基本相适应说才是判断是否超过防卫限度的决定性标准,拥有最终的否决权。因而,它不可能消除基本相适应说所固有的缺陷。诚如论者指出的,按照折衷说的见解,确定防卫行为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并不足以排除成立防卫过当的可能;如果防卫与侵害之间不能保持基本的相适应,则防卫行为依然会被认为超过必要限度。这样一来,折衷说的结论与基本相适应说就不可能有任何区别,而基本相适应说的弊端在通说中也根本没有得到有效克服。〔5〕参见陈璇:“正当防卫中风险分担原则之提倡”,《法学评论》2009年第1期。
另一方面,在具体个案的处理中,一旦认定防卫超过规定的限度,防卫人便往往直接被认定构成犯罪,且成立故意犯罪;在实务中,防卫过当几乎都是按故意伤害罪来处理。
实务界将防卫过当一般按故意犯罪处理的做法,不同于学界的主流观点。在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上,学理上传统的见解一直认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限于过失与间接故意,〔6〕参见高铭暄等,见前注〔4〕,页135。晚近以来有力的学说则主张也包括直接故意;〔7〕参见张明楷,见前注〔4〕,页203;陈璇:“论防卫过当与犯罪故意的兼容”,《法学》2011年第1期。同时,按照学界主流的看法,防卫过当的情形一般成立过失,特殊情况下才构成故意。学界与实务界在防卫过当罪过见解上的对立,早已有论者注意到,〔8〕参见姜伟:“防卫过当不应一概定为过失犯罪”,《现代法学》1984年第3期。但究竟为什么会如此,相关的论者并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一般认为,实务界的观点是源于对故意概念作形式的理解。〔9〕参见张明楷,见前注〔4〕,页202。这样的解读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实务界在防卫过当的罪过上持故意说,而在假想防卫的罪过上则持过失说。
从逻辑上讲,如果坚持对故意的形式理解,则实务界在假想防卫的罪过问题上原本也应持故意说才对。但就假想防卫的罪过问题而言,实务界的立场与学界的主流看法〔10〕高铭暄等,见前注〔4〕,页131;张明楷,见前注〔4〕,页195;陈兴良,见前注〔4〕,页144。并无差异,同样认为假想防卫要么成立过失要么构成意外事件。在一起假想防卫致人死亡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庭在裁判要旨中明确指出:
不能把刑法理论上讲的故意与心理学理论上所讲的故意等同、混淆起来。……假想防卫虽然是故意的行为,但这种故意是建立在对客观事实错误认识基础上的,自以为是在对不法侵害实行正当防卫。行为人不仅没有认识到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而且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正当的,而犯罪故意则是以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为前提的。因此,假想防卫的故意只有心理学上的意义,而不是刑法上的犯罪故意。〔11〕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第20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页12。
在假想防卫的问题上,实务界对故意概念的解读分明是实质的,而非形式的。这就不免让人疑惑,为什么在假想防卫的问题上,实务界对故意概念采取的是实质解读,而在防卫过当的问题上却倾向于形式解读?
认为防卫过当一般构成故意犯罪,而假想防卫至多成立过失犯罪的实务立场,会遭遇诸多的疑问。其一,为什么在不法侵害客观上不存在而防卫人误以为存在的情况下,其主观上的防卫意识被认为能阻却故意的成立;反之,如果不法侵害客观上存在,防卫人主观上的防卫意识却反而无法阻却故意的成立?其二,如果认为防卫过当一般构成故意犯罪,则为什么防卫人基于杀人的意图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成立的是故意伤害(致死)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其三,假想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行为人,主观上都具有防卫意识,客观上,前者是造成无辜之人的重伤或死亡,后者则是导致不法侵害人的重伤或死亡,照理说前者的不法程度应高于后者才是,为什么前者仅构成过失犯罪,而后者构成性质更为严重的故意伤害罪?对防卫过当与假想防卫在不法评价上的轻重倒置,缺乏起码的合理性。令人困惑的是,存在这么明显的逻辑漏洞,防卫过当一般按故意伤害罪处理的实务做法却并未受到应有的质疑。
综上来看,立法修正的目的在相当程度上是落空了。为什么立法的目的会落空?仅仅将防卫限度的把握过严追溯至基本相适应说,把防卫过当按故意犯罪处理归因于对故意概念的形式解读,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它们无法解释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必要限度”的判断标准没有随着立法的修正而有所调整?为什么防卫过当罪过问题上学界主流的观点始终未能扭转实务的做法?尤其是,为什么近十余年来刑法教义学所取得的进步,对防卫过当的研究却基本没有产生影响?笔者以为,这与实务中长期存在的“唯结果论”的倾向存在密切关联,而晚近以来结果无价值论在我国的强势兴起,则为这种“唯结果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根据,使防卫过当认定中的惯习得以强化。
结果无价值论与实务中的“唯结果论”能结合在一起,缘于它们都是以结果作为关注的核心与起点,采取的是“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此种思考进路在防卫过当的认定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有关防卫限度的规定做出立法修正后,刑法学理与实务仍然继续坚持以基本相适应说为基础的折衷说。只要以结果为核心与起点来考虑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区分,对立法修正的这种阳奉阴违的态度必然难以避免。同时,实务中将防卫过当一般按故意犯罪处理的做法也变得可理解。强调客观结果之于正当防卫的决定性意义,必然降低主观因素在认定正当防卫中的作用。按“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在不符合第20条第3款的情况下,只要防卫人所损害的法益大于不法侵害人所针对的法益,便会被认为存在结果的不法。既然结果本身遭到法的否定评价,防卫人有意识地追求或放任这种结果出现,也便被认为符合《刑法》第14条有关故意的规定,构成故意犯罪自是理所当然的结论。至于为什么学理上的进步对防卫过当的研究没什么影响的问题,其中的缘由更是一目了然:它是结果无价值论占据优势地位的产物。结果无价值论为防卫过当领域既有的“唯结果论”做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任何试图在这一领域寻求突破的论者,首先面临的便是如何肃清结果无价值论的主导性影响的问题。
二、“结果→行为”思考进路的缺陷
我国实务中“唯结果论”的做法与结果无价值论之间的关联意味着,在正当防卫的适用领域,若要从根本上解决对防卫限度把握过严与防卫过当的罪过认定问题,就必须对“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进行认真的审视,而这又势必牵涉对结果无价值论的不足的反思。
结果无价值论基于结果主义的逻辑,在排除违法的根据方面采取的是法益衡量说。为了解决正当防卫中所牺牲的法益允许大于所保护的法益而引起的冲突,结果无价值论特别强调,对不法侵害人的法益需做缩小评价,以将正当防卫纳入以法益衡量说为基础的优越利益原理的框架下。在防卫过当的认定上,由法益衡量出发,采取“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无论是从解释论的角度,还是从方法论、逻辑或刑事政策的角度,都存在缺陷。
首先,采取“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会大大降低《刑法》第20条第2款所规定的防卫限度的门槛,有违立法的基本目的。
根据第20条第2款,只有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才应负刑事责任。该条对防卫过当规定了两个要件:一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二是“造成重大损害”。如果承认立法修正的目的是要扩张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扭转过往对防卫限度把握过严的弊端,则理应将这两个要件之间理解为是并列关系,而非同一关系或从属关系。换言之,要成立防卫过当,必须同时满足这两个要件,且两个要件是相互独立的。这样的解读也符合立法文字表述的含义。具体如何处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在第四部分做出交待。
受“结果→行为”思考进路的影响,当前无论是学理上还是实务中,对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都着眼于最终发生的严重损害而展开。对结果无价值论者而言,这缘于其将刑法有关正当防卫的规定首先视为是裁判规范,而非决定规范或行为规范所致;对实务中的“唯结果论”者来说,它更多地是一味追求简单明了、可操作性强的司法判断标准的产物。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在解读防卫过当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的要件时,都倾向于消解前一要件,而片面地将严重损害的出现与否当作防卫过当的核心条件,使得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往往从属于有无造成重大损害的判断。
有论者明确主张将防卫损害视为必要限度特定的、唯一的限定、制约对象,认为对防卫损害之轻重予以允许和限定,是必要限度的核心内容;只有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才可认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也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12〕参见杨忠民:“对正当防卫限度若干问题的新思考”,《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也有论者虽然名义上是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理解为两个条件,并承认二者是并列关系,但在具体界定时,却又认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取决于重大损害的出现与否。比如,张明楷教授与黎宏教授都断言,不存在所谓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也即,只有在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才存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问题。〔13〕参见张明楷,见前注〔4〕,页202;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页142。这种以“造成重大损害”为基础来理解“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内容,是所有在防卫限度问题上持折衷说论者的通病。折衷说论者一方面宣称以防卫的客观需要作为判断其中的“必要限度”的标准,另一方面又强调以实际导致的后果来界定“必要限度”。这意味着,在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考量中,便要求考虑防卫行为实际造成的损害结果。这必然使“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要件在解释学上丧失独立的意义。对于此种弊端,山口厚有着清晰的洞悉:将结果的重大性之判断纳入防卫行为的相当性的判断中,不但会加剧防卫行为的相当性这一概念及其判断基准的不明确,而且会导致广泛地认定防卫过当,过于限定正当防卫的成立。〔14〕参见(日)山口厚:《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131-132。
其次,“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机械地割裂作为整体的防卫行为,并脱离构成要件来展开不法的评价,在方法论上存在严重的缺陷。
结果无价值论所采取的“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由于着眼于最终发生的损害结果,往往将防卫行为人为地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能阻却违法性,另一部分则超出制止不法侵害所需,具有违法性。在此基础上,人们来展开防卫行为是否过当以及是否具有违法性的论证。这种机械割裂作为整体的防卫行为的做法,可谓“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之一。
将防卫行为进行拆解尽管在理论上可行,但正如有学者批评的那样,由于防卫行为往往是防卫人在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下实施,且通常是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防卫人由起先对其防卫行为和结果持正当的防卫意识的瞬间突然转变为犯罪的故意。人为地将一个完整的防卫行为机械地割裂开来,将前一半认定为正当防卫,后一半认定为防卫过当不符合实际,也没有意义。果真前一半行为是正当防卫,后一半行为也难以认定为防卫过当,而宜认定为防卫不适时。〔15〕参见胡东飞:“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法学评论》2008年第4期。对于结果无价值论者从整体事实中抽取并不重要的事实单独进行评价的问题,周光权教授也做过犀利的批评。〔16〕参见周光权:“行为无价值论的法益观”,《中外法学》2011年第5期。
“结果→行为”思考进路在另一方法论缺陷是,脱离构成要件来认定刑事不法。不法作为一种犯罪类型,本来应当与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紧密结合在一起。结果无价值论由于以结果为核心与起点来展开不法的判断,往往脱离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抽象地来讨论不法成立与否的问题。这种弱化构成要件价值的做法,容易使结果无价值论笼统地得出因为存在损害,所以具有结果无价值的结论,至于是什么具体犯罪的结果无价值,在所不论。〔17〕同上注。如此一来,不仅构成要件对于违法性的制约机能以及构成要件的违法推定机能在相当程度上丧失殆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也经常导致在界定评价范围时眉毛胡子一把抓,将本应剔除的因素也混入其中,由此而得出错误的推论。
就防卫过当而言,人们本应在否定故意犯的不法后,再去考察是否成立过失犯的不法;但由于脱离构成要件来认定不法,“结果→行为”思考进路的奉行者往往不由自主地将已被正当化的有意伤害行为,又重新纳入到犯罪事实之中来进行评价,从而动辄得出防卫过当成立故意伤害罪的结论。对此,陈璇博士的分析可谓切中要害:将防卫过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严重混淆了防卫的有意性与犯罪故意,从刑法评价上来说,由于防卫人的有意伤害行为是以正当防卫为根据的合法举动,故该行为本身并不是刑法予以否定的对象,不存在成立故意伤害罪的可能;刑法要追究的只是行为超过必要限度所造成的结果,只有伤害行为所导致的加重部分,即过失至人死亡(或重伤)的事实,才成立犯罪。〔18〕陈璇,见前注〔7〕。在防卫过当的认定上,实务中时常将正当防卫的有意性与犯罪的故意混为一谈,正是“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在方法论上脱离构成要件来认定不法的缺陷所致。
再次,“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使得人们在“必要限度”的判断上采取行为后标准,并存在由结果反推故意的逻辑漏洞。
结果无价值论者基于对“结果→行为”思考进路的奉行,在界定“必要限度”的概念时,往往要求同时考虑防卫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并与防卫行为所保护的法益相权衡。〔19〕参见张明楷,见前注〔4〕,页201;黎宏,见前注〔13〕,页141。这必然使得原本针对防卫行为本身的“必要限度”,时常取决于事后出现的损害结果。在涉及“必要限度”的判断上,结果无价值论者采取的是行为后标准。也即,站在裁判时的角度,以事后查明的客观事实为基础,来判断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如此一来,但凡不能适用第20条第3款的场合,只要客观上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或重伤,且防卫所要保护的法益客观上小于实际造成的损害结果,防卫行为便容易被认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对“必要限度”的判断采取行为后标准,让防卫人承担了过多的风险,也背离现行立法有关防卫过当规定的基本精神。防卫行为超过限度的本质不在于严重损害结果的发生,而在于防卫人以明显违反社会相当性的方式和手段造成严重的后果。〔20〕参见陈璇,见前注〔5〕。一味倚重事后查明的客观事实,脱离一般人对防卫行为发生时具体情境的可能认识,必然造成动辄认定防卫过当的结果。
在“必要限度”的判断上采取行为后标准,不可避免地产生由结果反推故意的问题,即犯罪故意的成立与否,不是依据行为时的情境来决定,而是由结果反推所得出。故意的成立与否判断,本来应当采取行为时标准,即根据行为时所蕴含的风险与行为人对行为时风险的认知与意欲来确定;实际结果的出现与否仅影响既未遂的成立,不能以结果的严重来反推故意。但在防卫过当中,由于对“必要限度”的判断采取行为后标准,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反过来是由最终的损害结果来决定,这就等于是让故意的成立取决于实际出现的结果。只要防卫人有意识地造成这种结果,其便容易被认定具有故意。可以说,也正是由于在“必要限度”判断上采取行为后标准,黎宏教授才会得出防卫过当只能成立故意犯的结论。〔21〕参见黎宏,见前注〔13〕,页142。在防卫过当中,由结果反推故意的做法,在不当扩张故意伤害罪的适用的同时,也使得过失犯罪几无成立的余地。其中的缘由,不得不追溯至“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
最后,从刑事政策的角度,防卫过当的认定中采取“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无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按“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来认定防卫过当,对防卫人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结果→行为”思考进路的奉行者,由于对防卫人的真实处境缺乏必要的想象与体谅,经常以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明智,要求防卫人在遭遇突发的不法侵害时严格控制防卫的强度,以保护不法侵害人的生命与重大健康。防卫人由此而身陷困境:要么忍气吞声地忍受不法侵害,要么因展开反击而面临被犯罪化的高度风险。将防卫人逼入这样的境地,不仅有违常理与常情,在刑事政策上也极不明智。
对正当防卫而言,决定性的并非不同的权利与法益之间或类似的价值之间的矛盾,而是法与不法之间的冲突;被侵害人与不法侵害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而以有利于前者的方式予以解决,其法益被置于优先地位。〔22〕Vgl.Jähnke/Laufütte/Odersky,StGB Leipziger Kommentar,§§32,33,11Aufl.,1992,§32 Rn.6.这意味着,在由防卫引起的风险问题上,既有的制度做出的是不利于不法侵害人的分配。作为积极侵犯他人自由领域的一方,不法侵害人理应承担由此而引发的不利后果的风险。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这样的风险分配安排有其合理性,它在给作为无辜方的防卫人提供必要保护的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威慑潜在的不法侵害人。“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却改变了这样的风险分配格局,基本上要求不法侵害人与防卫人平均分担防卫所带来的风险。这样的改变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一方面,在我国公力救济资源不足且社会保障机制薄弱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让无辜的公民忍受对自身合法利益的不法侵害。另一方面,它会降低违法的成本,助长潜在不法侵害人的嚣张气焰,同时严重挫伤人们抗击不法的勇气。以当前我国不法侵害日益猖獗的现状来看,需要担忧的恐怕不是对防卫权的滥用,而是对正当防卫限定过严而带来的后遗症。
正当防卫属于私力救济的一种。考虑到我国公力救济资源严重不足,有效性也颇值得质疑的现实,在正当防卫这样的领域,提升私力救济的份量与权重有其必要性。因为“立法者必须考虑私人惩罚和公共惩罚各自的比较优势,以决定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公共资源投入到一个特定的社会控制领域。如果私人监控和私人惩罚的成本更低但收效更大,法律就应当更多地利用私人之间的监控和惩罚”。〔23〕桑本谦:“公共惩罚与私人惩罚的互动”,《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5期。采取“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由于要求防卫人与不法侵害人以大体相等的比例来承担防卫带来的风险,间接地具有排斥私力救济的效果。从社会控制总成本(即公共控制成本与私人控制成本之和)的最小化来看,在正当防卫领域过于倚重公力救济并不可行,且不可避免地有脱离现实语境之嫌。
三、正当防卫正当化根据的重新定位
防卫过当认定中流行的“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必须要追溯到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问题。正是由于将正当化的根据建立在法益衡量的基础上,才导致人们在界定防卫限度的要件时,采取以结果为核心与起点的判断。欲纠正这种唯结果主义的倾向,势必要抛弃以法益衡量为基础的优越利益原理,而对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进行重新的定位。
德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或指导思想,根源于个体权利面向的保护原则与社会权利面向的法确证(Rechtsbewährung)原则。所谓的保护原则,其核心是自我保护思想,即允许每个人保卫自身的法益,当国家在确定的情形中不能履行保护其公民自由免受他人侵犯的任务时,作为人的自我防卫的“原权利”必须为公民所保留。所谓的法律确证意味着,防卫人防护自身或他人的同时,也在保卫法秩序的意义上确证了法,此即“法无需向不法让步”;由此,防卫人在国家无法亲自确证法的场合成为法的守护者。〔24〕Vgl.Kühl,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6 Aufl.,2008,§7 Rn.8-10;Jescheck/Weigend,Lehrbuch des Strafrechts.Allgemeiner Teil,5.Aufl.,1996,S.336.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共同作用,法确证需求的不同会影响保护权限的安排。〔25〕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4.Aufl.,2006,§15 Rn.3.换言之,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法确证原则无论如何不仅仅建立在绝对的国家意识之上,其意义也不单限于消极的一般预防,它扩张了随个人保护视角而得出的防卫人的权利;同时,基于法保护任务理应由国家自身所保留的考虑,通过使正当防卫仅在基于个人保护理由而必要的场合得到“权力授权”,个人权利的面向也限制了社会权利的面向。〔26〕Vgl.Schönke/Schröder,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28.Aufl.2010,§32 Rn.1a.这种以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为基础来解说正当防卫的二元论,构成德国的通说。〔27〕Vgl.Roxin(Fn.25),§15 Rn.3.无论是保护原则还是法确证原则,就其单独而言,被认为不足以说明正当防卫的根据与界限:一方面,将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仅仅定位于个人权利面向的保护原则,将使“法无需向不法让步”的格言被化约为防卫人的“主观权利”与不法侵害人的“主观不法”。问题在于,此处总是涉及法共同体的利益,而不只是被侵害人的利益,这也是对不法侵害原则上无需回避的缘由所在。同时,正当防卫中要求侵害人自担风险的想法,理由也只可能在于侵害行为的违法性,而这一点再一次归结到法确证利益。此外,单纯的个人权利面向,也不可能解释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自救行为、抓捕行为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单是法确证原则,也无法成为正当防卫正当化的全部根据所在。有关正当防卫的立法条款,并不包含一般意义上的防止不法的权利,而只适用于行为人制止针对自身或他人的侵害的场合,法确证利益在此“仅通过个人保护的媒介”而出现。〔28〕Vgl.Schönke/Schröder(Fn.26),§32 Rn.1a.
黎宏教授的前述批评难以成立,其论证逻辑存在诸多的问题。
其一,黎宏教授将本来以权利为核心的个人保护原则,错误地解读为个人的自我防卫本能,得出正当防卫由此成为责任阻却事由的结论;这样的推理建立在误解保护原则内涵的基础上,其所做出的批评因而也就有无的放矢的嫌疑。根据个人保护原则的内在逻辑,防卫不法侵害系个体的正当权利,正是这种权利的存在,使得通过损害相对方法益的手段来防卫自身或他人法益的做法为法所容许。这意味着,依据保护原则来解读正当防卫,必然认为正当防卫属于违法阻却事由,而不可能得出成立责任阻却事由的推论。
其二,黎宏教授将法确证原则的内涵偷换为代理理论,并据此展开批评,这样的批评并未切中要旨。在正当防卫中,被侵害人不只是处于事实上的紧急状态中,也处于法定的紧急状态中,对被侵害人而言,来自侵害人的侵害不仅危及其利益,而且对其权利构成威胁;由此,制止不法侵害不只是有关个人自我保全的斗争,而更是涉及一般意义上的法保卫的斗争,即对法秩序的有价值的防卫。〔30〕Jähnke/Laufütte/Odersky(Fn.22),§32 Rn.13.同时,法确证原则涉及一般预防的考虑,通过允许为保护个人而进行必要的防卫,立法者同时追求一般预防的目的;因为每一个在正当防卫中遭遇抗击的不法侵害表明,人们不可能在不冒风险的情况下来损害法秩序,同时,它也具有稳定法秩序的效果。〔31〕Vgl.Roxin(Fn.25),§15 Rn.2f.因而,从法确证的原则出发,并不能得出个人代行法院权限的结论,其不过是在申明与确证“法无需向不法让步”的法秩序立场。实际上,防卫人是否代行国家刑罚权的问题,并非法确证原则所带来,其涉及的是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之间关系的法哲学定位。在一种主张合法的暴力只能由国家垄断的语境下,承认个人在遭受紧急的不法侵害时具有正当防卫的权利,本身便意味着个人在代行国家刑罚权。因而,只要不否认正当防卫是公民享有的权利,即便是以优越利益原理为根据来解说正当防卫,也存在防卫人是否在代理国家行使刑罚权的疑问。
与黎宏教授类似,西田典之也批评法确证观点的根底潜藏着代行国家刑罚权的意识,并认为据此相关理论将归结为,仅仅对能理解规范的含义者才具有法确证的利益,不能对无责任能力者实施正当防卫,也不存在对物防卫,而这样的结论难言妥当。〔32〕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页132。西田的观点也明显建立在误解法确证原则的基础之上。法确证原则确证的是一般的法秩序立场,并非特殊预防。在不法侵害人本身不理解规范含义的场合,只能表明难以起到特殊预防的效果。但即使是无责任能力者实施的侵害,也仍构成不法。从社会权利的角度,正当防卫意味着法秩序无需向不法屈服;尽管保护法秩序的一般利益在正当防卫中共同发挥作用,但其对侵害人而言并不具有刑罚的特性,因而,正当防卫并不限于有责的侵害。〔33〕Jescheck/Weigend(Fn.24),S.336-337.允许对无责的不法侵害进行防卫,合乎法秩序对自身立场的确证要求。至于所谓的不存在对物防卫空间的问题,刑法上法与不法的评价对象乃是人的行为,对于并非来源于人的侵害所造成的损害,又何来“法”或者“不法”之说?将单纯动物造成的损害,纳入“不法侵害”的范畴而容许对物防卫,本身便有违行为刑法的宗旨。一个并非基于人的意思的举动,不可能成为刑法评价的对象。这样的举动在构成要件之前的行为阶层,便已被排除出去,又怎么会进入违法性阶层?是故,得出对物防卫并无存在空间的结论,恰恰体现的是法确证原则的合理性,而绝非其缺陷所在。
其三,黎宏教授将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相互割裂,理解为两种独立的一元论的做法值得斟酌。当黎宏教授对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分别展开批评时,他分明将二者割裂开来,把二者当作为内容迥异的两种一元论来处理。这样的解读方式,误解了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德国刑法理论中,二者构成作为通说的二元论的两轴,并非两种独立的理论。西田典之在对法确证原则展开批评时,也存在类似的错误。因而,他才会以将不法侵害人的行为当作犯罪来处理,也完全有可能确证法规范存在为由,而主张法确证的观点存在未能说明正当防卫为何不需要补充性的缺陷,即无法说明正当防卫之中并无躲避义务的问题。〔34〕参见西田典之,见前注〔32〕,页131。在此,西田不仅对法确证原则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而且明显是在一元论的基础上来展开解读。抛开其对法确证原则的理解偏差不论,只要将法确证界定为二元论中的一元,其所谓的缺陷根本是子虚乌有。在面临紧迫不法侵害的场合,基于保护原则的考虑,会得出个人有防卫自身或他人合法利益不受侵害的权利,而既然是防卫人的权利,自然也就不需要在别无避免侵害的方法时才行使。此点足以说明,正当防卫为何不需要补充性。
本文认为,相较于建立在法益衡量基础上的优越利益原理,将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定位于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更具合理性。
首先,从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出发,可合理解释正当防卫成立要件中的一系列疑问,而优越利益原理对此却无法给出合乎教义学逻辑的说明。
第一,为什么不能对单纯的公法益进行正当防卫?一般认为,正当防卫所保护的利益仅限于个人法益与涉及个人法益的公共利益,不包括单纯的国家、社会利益。这样的观点大体上也为结果无价值论者所认可。〔35〕参见张明楷,见前注〔4〕,页193;黎宏,见前注〔13〕,页130。保护原则能够对这样的限定做出合理的解释:既然正当防卫具有个体权利的面向,自然只能对涉及个人法益的不法侵害进行防卫,而不允许扩张至一般的公共利益。优越利益原理由于缺乏这样的面向,很难从中得出类似的结论。按优越利益原理的逻辑,只要所保护的利益优于所侵害的利益,便足以使相关行为正当化。因而,从理论上讲,针对任何危及合法利益的不法侵害,都是允许进行防卫的,而这样的结论结果无价值论者也并不接受。
综上分析,边坡稳定性影响的主控因素是人类工程活动、降雨,诱发因素为地形条件和地震。以上因素综合作用,促进滑坡的形成、发展与发生。
第二,为什么防卫人一般没有退避的义务?在面临不法侵害时,防卫人并不负有采取退避措施的义务,这一点在各国刑法理论上都几乎没有争议。从法确证原则的角度,其间的理由一目了然,法无需向不法让步;同时,既然针对不法侵害而实施防卫,是防卫人在行使其自身的权利,则作为权利者一方,其无需蒙受屈辱而退避。相反,建立在法益权衡基础上的优越利益原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防卫人不承担回避义务。如果防卫人能通过躲避,在实现保护自身或他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又不损及侵害人的法益,则根据优越利益原理,理应得出相反的结论才是。
第三,为什么不要求所保护法益与所损害法益之间保持均衡或基本的相当?我国刑法的学理与实务都承认,为保护处于较低层级的法益,而损害不法侵害人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不影响正当防卫的成立。换言之,正当防卫的成立,并不要求所保护法益与所损害法益之间保持均衡。从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出发,对均衡性要求的放弃很容易得到解释:从个体权利的面向而言,既然防卫是行使权利的体现,则其间的关键只在于,“为有效制止不法侵害,什么措施是必要的,而不取决于侵害人在此过程中必须承受哪种损害”;〔36〕Jescheck/Weigend(Fn.24),S.337.从社会权利的面向来说,由于防卫行为同时也是在保护法秩序利益,法秩序利益与所保护法益叠加之后所具有的权重,使得放弃均衡性要求成为当然的推论。反之,依据优越利益原理,往往仅允许“正当防卫所造成的损害表面上略大于所避免的损害”。〔37〕参见张明楷,见前注〔4〕,页190。如此一来,便难以解释,在不成立特殊防卫的情况下,为什么也并非但凡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便一律否定正当防卫;而根据其法益衡量的逻辑,其本来应当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四,为什么防卫人享有比国家更大的“惩罚”权利?从第20条第2款与第3款的规定来看,防卫人的权利行使力度比国家机关职权的行使力度要大得多。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在警察依法履行职务抗击不法侵害的场合,其行为应依据职务行为而非正当防卫予以正当化。〔38〕我国实务的观点有所不同。根据1983年9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实行正当防卫的具体规定》,警察执行职务中制止不法侵害被认为属于正当防卫。这样的观点难说合理,尤其是,在1997年立法修正增设特殊防卫,并大幅放宽防卫限度的情况下,允许警察实行正当防卫,会带来诸多的问题。因而,在抗击强度方面,警察并不享有一般防卫人的权利,更不允许行使特殊防卫。比如,在遇到不法侵害人盗窃他人财物时,一般的防卫人可采取损害侵害人身体健康的方式来防卫,而如果抗击的主体是警察,则原则上不允许采取此种方式。在遇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如抢劫、强奸等场合,防卫人可直接将不法侵害人置于死地,而警察则一般不被允许这么做。实施相关行为的不法侵害人即使被移送司法机关,在仅仅对他人重大人身安全创设危险的场合,依据现有的刑法规定,也不过是按抢劫未遂或强奸未遂等被判处若干年有期徒刑。对此,只有以保护原则作为正当化的根据之一,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防卫人的防卫权并非来源于国家的惩罚权,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后者。反之,若是依据法益衡量的逻辑,无法理解为什么对警察就不能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为什么防卫人权利的行使力度比司法机关职权的行使力度要大得多。
第五,为什么正当防卫的成立,要求防卫人至少具有防卫认识?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成立正当防卫,防卫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防卫意思。晚近以来,要求放松防卫意思的要求,认为只要具备防卫认识即可满足防卫主观要件的观点,〔39〕参见陈璇,见前注〔7〕。渐具影响力。结果无价值论者也持防卫认识必要说,同时认为偶然防卫虽不成立正当防卫,但因缺乏法益侵害性而不可罚。〔40〕参见黎宏,见前注〔13〕,页136;黎宏:“论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此外,张明楷教授似乎也并未全盘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要求具备防卫意识,他批判的重心显然放在只有主客观相一致的正当行为才排除犯罪成立的观点之上,故而他才会得出偶然防卫类似于不可罚的不能犯的结论。倘若正当防卫的成立无需防卫意识,他本来应得出偶然防卫成立正当防卫的结论。参见张明楷,见前注〔4〕,页197、199。要求正当防卫的成立必须具备主观正当化要素的见解,从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的角度考察,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只有当防卫人意识到自己在行使权利,在对个体利益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在与不法相抗争,其行为才得以正当化。这是基于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得出的结论,即某一行为若要阻却违法,必须同时否定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而要求存在防卫意识,正是对其中的行为无价值的否定。因为刑法的禁止内涵,“绝对不可能仅仅存在有因果作用的法益侵害(存在结果非价)之中,而是基于刑法旨在影响人的举止的目的,始终以一个‘行为非价’(为法所不容许的行为的目的性)为前提。”〔41〕(德)许逎曼:“刑法体系思想导论”,许玉秀译,载许玉秀、陈志辉合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逎曼教授六秩寿辰》,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页279。相反,如果以法益衡量为作为正当防卫的基础,则只要客观上所保护的法益较所损害的法益优越,即足以全盘否定违法;据此,正当防卫的成立,必然不以主观上存在防卫意识为必要。我国的结果无价值论者之所以做出妥协,肯定防卫意识的必要性,显然是考虑到《刑法》第20条第1款中,存在“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规定。如果承认是基于这一规定而得出相应的结论,则这无异于表明,基于对立法文意与立法目的的尊重,不应以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来解读有关正当防卫的规定。
第六,为什么在不法侵害系由无责任能力人或责任能力减轻者所实施的场合,防卫人便负有退避的义务,且必须严格控制防卫的限度?我国刑法理论普遍认为,针对来自无责任能力人的不法侵害,防卫人具有克制的义务,只有在无法避让的情况下才允许进行防卫,同时,在防卫限度的要求上也更为严格。〔42〕参见张明楷,见前注〔4〕,页193、205;高铭暄等,见前注〔4〕,页132;黎宏,见前注〔13〕,页130;赵秉志,见前注〔4〕,页390;沈德咏等,见前注〔1〕,页22。从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出发,对此的解释是:此类场合并不需要确证法秩序,因为相关侵害并没有或并未实质性地质疑法秩序的效力,故正当防卫权的基础仅在于或主要在于自我保护的权限;〔43〕Jescheck/Weigend(Fn.24),S.345-346.相应地,就不允许防卫人行使像一般情形中那样的防卫权。罗克辛也指出,从法确证原则的刑事政策基础来看,该原则并不适用于儿童和精神病人,原因是,对于并非有意识地触犯法律从而不可罚的人来说,法秩序并不需要在他们那里“确证”自己的效力。〔44〕(德)克劳斯·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36。反之,优越利益原理仅仅建立在对法益排序的基础上,而即使不法侵害来源于无责任能力人或责任能力减轻者,也不可能影响这种排序;因而,它也无法说明,为什么此类场合中,防卫人的防卫权限会受到限制。张明楷教授以“法益应当尽可能受到全面保护”〔45〕张明楷,见前注〔4〕,页193。为由,来解释此种场合中下防卫人的克制义务,缺乏说服力。在不法侵害来自有责任能力人的场合,又何尝不存在全面保护法益的需求?此外,西田典之提出,未必有必要强调法确证的利益,只要在防卫行为的相当性这一要件中对此加以考虑即可,即更加严格地判断防卫行为的相当性。〔46〕参见西田典之,见前注〔32〕,页133-134、146。问题在于,为什么对此种场合中的相当性,要做较一般情形更为严格的界定?从优越利益原理的前提出发,得不出这样的推论。在此,西田根本就是回避了问题,以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相当性来予以搪塞。
从法确证利益丧失或实质性降低的角度出发,也有助于解释在涉及防卫挑唆的场合,为什么当挑唆人有权实施正当防卫时,其也负有节制与退避的义务。根据我国的通说,对防卫挑唆一般不能实施正当防卫,但如果侵害程度大大超过挑唆人预想或挑唆人欲终止的场合,则允许挑唆人进行防卫,但其负有退避义务,且必须严格控制防卫限度。当挑唆者以法律秩序的防卫者之姿态出现时,其正当防卫权只能依自我保护的必要性而定,因此,挑唆者原则上负有闪避义务,他的防卫权一开始即限于单纯被动的保护性防卫。〔47〕许逎曼,见前注〔41〕,页258。相应地,挑唆者成立正当防卫,还要求所保护法益与所侵害法益之间保持相当。
第七,为什么对故意的不法侵害与过失的不法侵害,以及对因家庭成员矛盾引起的正当防卫与非家庭成员之间的正当防卫,在防卫的要求上会有所区别?法确证利益是否降低的因素,有助于解释这个疑问。在涉及过失不法侵害与因家庭矛盾引起的正当防卫的场合,法确证利益有实质性的降低,故正当防卫权主要是基于自我保护的权限。与此相应,防卫人需要承担克制的义务,且原则上应力求避免使用致命的暴力。相反,立足于优越利益原理,其关注点仅局限于客观上所保护法益与所损害法益之间的比较。故意不法侵害与过失不法侵害之间,以及对因家庭成员矛盾引起的正当防卫与非家庭成员之间的正当防卫之间,不存在实质的区别。既然相应的情形从法益的角度而言并无不同,根据结果无价值论的逻辑,也就不可能得出防卫要求上应有所区别的结论。
其次,优越利益原理实际上是以法确证原则作为基本的前提,其本身无法自洽地充当证成正当防卫正当化的全部根据。
由于正当防卫一般允许所损害的法益大于所保护的法益,结果无价值论于是面临如何解决跟其理论设定之间冲突的问题。为使立基于法益衡量的正当化根据能成立,结果无价值论者往往借助于对不法侵害人的法益进行缩小评价的手段,从而使得其所谓的优越利益原理可适用于正当防卫。但不法侵害人的法益为什么要受到缩小评价,依据什么被缩小评价,优越利益原理本身无法给出自洽的解释,而必须以“法无需向不法让步”的原理作为前提。对结果无价值论而言,被侵害人的利益优位性或不法侵害人的法益保护价值在防卫必要限度之内被否定,正是根据“法无需向不法让步”而得出。〔48〕山口厚,见前注〔14〕,页114。在我国的结果无价值论者的相关论述中,也可清楚地发现这一点。
张明楷教授提出,正当防卫中,“在面临紧迫的不法侵害的情况下,防卫人没有退避的义务,因为‘正当没有必要向不正当让步’;不法侵害者的法益虽然没有被完全否定,但其利益的保护价值在防卫的必要限度内被否认,因为在正与不正的冲突中只能通过损害不法侵害者的利益来解决冲突,于是,应受保护的法益优越于不法侵害者的利益(也可以认为,不法侵害者的利益实质上受到了缩小评价)。”〔49〕张明楷,见前注〔4〕,页190。这一论述不仅明确承认防卫人没有退避义务是源于法确证原则,而且表明不法侵害者的法益在必要限度内被否定,是因为正当防卫涉及的是正与不正的冲突。正是在“法无需向不法让步”的前提下,方得出不法侵害者的法益受缩小评价的推论。黎宏教授的相关论证也体现了这一点。当他声称“正当防卫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不法侵害人是法益冲突事态的制造者和引起人。他引起了法益侵害事态,其固有的法益就要受到否定评价,其受保护的程度相对于防卫人而言,就要缩小或者降低”〔50〕黎宏,见前注〔40〕。时,他不过是在说,引起法益侵害事态的侵害人是不法的一方,故其法益要受到缩小的评价。
以法益衡量为基础的优越利益原理将法确证原则与对法益的评价杂揉在一起,不仅扰乱了法益的一般位序,而且没有解决如何衡量侵害人与防卫人之间法益大小的问题。它一直都未能提出一个明确的标准,来解决具体的缩小比问题。含糊以对的结果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中,优越利益原理的适用给人无所适从的感觉。比如,支持者主张,在挑拨防卫的场合,由于防卫人的挑拨是引起事件的原因,所以其法益所受保护的程度要相应降低或者缩小,即便受到对方的攻击,其正当防卫权也应当受到一定限制。〔51〕同上注。据此,防卫人似乎成为不正的一方,故其利益要受到缩小的评价;同时,由于挑唆者的防卫行为仍被认为存在成立正当防卫的余地,于是,作为侵害人的被挑唆人,其法益也应被缩小评价。那么,在双方的法益均受到缩小评价的场合,怎么依据优越利益原理来展开正当防卫成立与否的判断呢?支持者显然忘记告诉人们,其到底是如何确定双方各自的缩小比的。
最后,从我国现行有关正当防卫的立法规定来看,其立足于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而非法益衡量。
在旧刑法的时代,从法益衡量来展开正当化根据的叙说有相当的依据。1979年的刑法对防卫限度规定得相当严格,与《日本刑法》第36条第2款规定〔52〕《日本刑法典》第36条第2款规定:超出防卫限度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立场较为接近,只要“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就构成防卫过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时的刑法理论普遍采取基本相适应说或以基本相适应说为基础的折衷说,来解读防卫限度的问题。1997年的刑法对正当防卫的规定做了重要的修正。在此种情况下,死守原有的理论或一味借鉴日本学说对防卫过当的解读,而不做出相应的调整,未免太过罔顾立法,也缺乏基本的正当性。
从法解释论的角度,对现行《刑法》第20条第2款与第3款的规定,不能从法益衡量的角度去解读,而理应立足于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尽管罪刑法定的明确性要求,不像在构成要件中那样属于构造性原则,但其在正当化事由中具备一种限制性的作用,即限制社会调节原则,以避免其过分地变化,法律上秩序规则的变化要服从明确性要求的限制。〔53〕罗克辛,见前注〔44〕,页39-40。基于此,任何脱离现行立法规定来解说正当化事由的做法,都不被容许。即使认为我国现行正当防卫的立法,过于扩张了正当防卫的范围,也不允许借助立基于法益衡量的优越利益原理而架空该立法规定。这也是为什么罗克辛会提出,根据德国现行法律,〔54〕《德国刑法典》第32条规定,正当防卫不违法。为使自己免受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而实施必要的防卫行为,是正当防卫。第33条规定,防卫人由于慌乱、恐惧、惊吓而防卫过当的,不负刑事责任。如下做法是不允许的:即人们将利益衡量原则普遍应用到正当防卫中,或者人们否定法确证原则,并认为在一切人们能够避免外来侵害时,都负有回避义务,从而扩张正当防卫领域的可罚范围。〔55〕罗克辛,见前注〔44〕,页40。若是以法益衡量作为其正当化的解读根基,则立法者大费周章地设立特殊防卫,并修改防卫过当的标准就会完全丧失意义。因而,如果承认在刑法领域,无论是学者还是司法者,均只能解释法律而不允许进行造法,则在正当防卫的问题上,理应尊重立法的文意表述,尊重从文意表述中透露出来的立法目的。
四、如何实现对防卫过当的合理认定
一旦肯定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应以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为基础,则防卫过当的认定,思考的重心便不应放在所保护法益与所损害法益之间的比较上,尤其是,不能以结果作为思考的起点,来展开防卫过当的判断。从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出发,防卫过当涉及的是对防卫权的滥用;而防卫权是否滥用,应立足于一般人的观念,从行为规范或社会伦理的角度进行客观的评价。因而,对防卫过当的认定,需要从禁止权利滥用的角度去考虑。在不法侵害来自无责任能力者、涉及特别近亲关系或挑唆防卫的场合,之所以要对防卫人施加特定的防卫限制,正是基于禁止权利滥用的考虑。当然,禁止权利滥用的考虑只构成界定防卫过当的指导思想,它本身不足以成为防卫过当的标准。无论如何,对正当防卫权的限制,不允许建立在有损法安全的一般条款上,而必须联系构建与限定这种权利的基本原理来考察。〔56〕Jescheck/Weigend(Fn.24),S.345.有关防卫过当的标准,第20条第2款规定得很明确。故关键在于,在对该款进行解释时,贯彻禁止权利滥用的指导思想。
(一)对第20条第2款规定的理解
如前所述,在当前我国刑法学理与实务中,对第20条第2款规定的防卫过当的两个要件,即“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的理解,往往偏重于后者,使得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从属于有无造成重大损害的判断。这是法益衡量说及其“结果→行为”思考进路的逻辑使然。将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定位于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之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势必成为两个独立的要件,二者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理解为是就防卫行为本身而言,“造成重大损害”则针对的是防卫造成的结果,只有二者同时具备,才能构成防卫过当。换言之,有必要“将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进一步细化为行为限度条件与结果限度条件。在行为限度条件中,主要以必要限度为衡量标准,若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则成立行为过当;而在结果限度条件中,以是否造成可量化操作的重大损害后果为判断基准,造成了不法侵害人重伤或死亡的重大损害后果,才成立结果过当。”〔57〕郭泽强、胡陆生:“再论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法学》2002年第10期。同时,从禁止权利滥用的角度考虑,在防卫过当的判断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要件的权重应大于“造成重大损害”要件的权重。是否构成权利滥用,首先由防卫的行为本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来体现,其次才由结果层面的“造成重大损害”来体现。如果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则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或死亡的结果,也不能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
在具体处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二者的关系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既有可能造成重大损害,也有可能因意外原因而没有造成。比如,警察A晚上执行完公务回家,看到小偷翻墙要进入自家院内即拔枪射击,但因光线较暗没有击中小偷。此案中,A的行为便属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
其次,实际发生重大损害的结果,既可能是防卫人合理的防卫行为所导致,也可能是防卫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所造成。比如,某日,杨某与管某在厂内打篮球时发生碰撞,赵某与杨某借机敲诈管某拿500元请吃饭平息此事,否则就找人打他,遭到管某的拒绝。次日,管某坐在厂门外花坛边休息时,赵某领两名无业人员李某、王某过来,并推打管某的肩膀,管某被迫自卫,王某见状也参与打管某,三人徒手扭打在一起。扭打过程中,王某被管某推倒在地后不省人事,双方即停止扭打。王某被送医院经抢救无效而死亡。经法医鉴定,王某系摔跌时右下颌着地致原发性脑干损伤死亡。此案中,管某将王某推倒在地的行为导致王某死亡,从结果来看,已经符合“造成重大损害”的条件,但管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当管某与王某、李某扭打在一起时,他并未使用刀具,而是徒手反击,且其反击行为仅表现为将王某推倒在地,完全没有超出不法侵害的强度,故本案属于防卫行为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却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
再次,防卫行为本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评价,应区别于行为是否“造成重大损害”的评价。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针对的是与实际的结果相切断的行为本身,需要以行为时的事实情节作为判断基础,由一般人的角度展开经验性的审视:从规范或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为保护相关的个人法益,防卫人采取此种程度的强力进行防卫是否尚算合理。在考察防卫行为本身的强度时,虽也要考虑其是否具有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的、类型化的危险,但此处涉及的是行为的危险,而非作为结果的危险。简言之,它仅仅是在探讨实行行为的问题。是否“造成重大损害”的判断,则涉及狭义的结果归责的判断。它包含两部分的内容:一是“重大损害”的结果已实际发生。所谓的“重大损害”,学理上一般认为仅限于重伤或死亡,不包括轻伤或财产方面的损失。这样的见解也为实务所认同。〔5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第38集),法律出版社2004版,页104。二是“重大损害”的结果客观上可归责于防卫行为。也即,在重伤或死亡结果已出现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确定其与防卫行为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有在不法侵害人的重伤或死亡结果可归责于行为人的防卫行为的情况下,才能认定防卫人“造成重大损害”。
最后,有必要将第20条第2款规定中的“必要限度”概念,区别于正当防卫中的防卫限度的概念。诚如论者所言,根据新刑法的规定,存在着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但未超过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的情形,这一部分情形,在旧刑法中以防卫过当论处,在新刑法中则成立正当防卫。新刑法中的“必要限度”一词是从旧刑法中借用过来,故其含义与旧刑法中的含义保持一致,但是对于新刑法中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则必须要有全新的理解。〔59〕参见王政勋、贾宇:“论正当防卫限度条件及防卫过当的主观罪过形式”,《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防卫限度的概念在外延上要大于“必要限度”的概念,前者包含两个部分,即行为限度与结果限度,而“必要限度”涉及的只是行为限度,故二者不应混为一谈。
在厘清“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二者关系之后,需要进一步处理的难题是,以什么标准来判断防卫行为是否属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所谓的基本相适应说、必需说与折衷说之争,便是围绕“必要限度”的问题而展开。本文认为,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理解,应采取必需说的立场。
一则,从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的基本思想出发,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只能着眼于所采取的防卫行为是否为保护个体合法的利益所必需。所谓的“必需”,意指非此即不能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或者虽可能制止不法侵害,但会给防卫人(或被侵害人)带来人身或财产安全方面的不合理风险的。只要防卫行为构成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且合理的手段,便应径直得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结论。德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必需性具体根据侵害与防卫行为发生的整体情状,特别是根据侵害的强度、侵害人的危险性及其行动,以及既有的防卫手段的可得性来确定。防卫行为的必需性应按客观、事先的标准来判定,也即,一个审慎的第三人处于被侵害人的位置时对当时情状所作的判断。在审查防卫行为的必需性时,原则上不需要对所涉及法益的价值关系进行权衡。〔60〕Jescheck/Weigend(Fn.24),S.343.只要防卫人所采取的行为对于制止侵害而言构成必需,则即使出现严重的结果,也属于正当防卫的范围。
二则,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而言,必需说相对于基本相适应说或折衷说更具合理性。在解释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时,理应考虑预防的效果。在“必要限度”的问题上,采取基本相适应说或折衷说,等于是为不法侵害者提供了护身符。由此,保护不法侵害者法益的任务就被放在防卫人身上,防卫人有义务保护不法侵害人免受防卫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这无异于变相鼓励不法侵害者去实施侵害,同时,它也给防卫人带来过大的负担。这种让防卫人承担过多风险的做法,缺乏合理性。一方面,由于侵害人是冲击整体法秩序的肇事者,从遏制不法行为的目的出发,法律有理由要求他为自己在实施侵害时可能遭受的各种损害承担风险;另一方面,由于防卫人是合法权益的积极捍卫者,为宣扬社会正义观念,刑法不应对他施加过多的束缚。只是为避免公民私力救济权的无限扩张和滥用,法律才为防卫者预设一定的风险,以督促他在实施防卫行为时不要逾越社会容许的范围。〔61〕陈璇,见前注〔5〕。
此外,采取必需说,也符合《刑法》第20条的立法文意与目的。在1997年立法修正后不久,学界与实务界就均有论者提出,鉴于新刑法放宽正当防卫的限度标准,并增设特殊防卫的制度,在“必要限度”的问题上,理应根据新的立法精神改采必需说。〔62〕参见彭卫东:“论防卫过当”,《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梁华仁、刘为波:“评新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的修改”,《政法论坛》1998年第1期;黄祥青:“刑事疑难案例分析两则”,《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5期。本文认同这样的见解。立法层面所经历的重大调整,必须忠实地体现在法解释论上。解释者不能以自己对应然法的态度,来取代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因为一旦脱离现行的立法规定,也就丧失了解释的基础,无法再被认为是一种解释了。
(二)“行为→结果”思考进路的适用
从禁止权利滥用的指导思想出发,防卫过当的考察重心不在结果环节,而在行为环节,行为才应当是思考的起点与核心所在,故需采取“行为→结果”的思考进路。“行为→结果”思考进路的适用,有助于在具体个案中合理把握“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问题,并避免将防卫过当普遍当作故意犯罪来处理。
一方面,有关行为限度的判断,即防卫行为本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采取行为时的一般人标准,以整体的防卫行为作为评价的对象。
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仅应根据不法侵害发生时的具体情况来展开判断,适用行为时的一般人标准。解释者需要站在中立的立场,结合防卫当时的具体“情境”,做整体的、假定的判断,而不是进行事后的、“马后炮”式的判断。〔63〕周光权:“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情境’判断”,《法学》2006年第12期。也即,从一般人的观念出发,考虑一般人的可能认识,设想具有通常理解能力的第三人处于防卫人当时的境地,是否会做出相同或类似的选择,是否存在选择强度较低且又能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的其他防卫措施的可能。法律解释者所假设的这个“其他防卫措施”,应具备两个限制性条件:一是在制止不法侵害的有效性方面,它必须能够达到与现实案件中防卫行为相同的水平;二是防卫人即使选择这种防卫措施,也不会使自己处于更为危险的境地。〔64〕陈璇,见前注〔5〕。在“必要限度”的判断上,要重视不法侵害发生时的情势,将双方的手段、强度、人员多少与强弱、在现场所处的客观环境与形势当作首要的考虑因素,并注意不应将作为整体的防卫行为机械地割裂开来进行评价。
其一,如果防卫行为本身的强度与不法侵害强度基本相当,或者甚至小于不法侵害的强度,则无论实际造成的结果有多严重,都不能认为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以张建国故意伤害案为例。〔6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第22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页5以下。被告人张建国与同在酒楼饮酒的徐永和(曾是张建国的邻居)相遇。张建国同徐永和戏言:“待会儿你把我们那桌的账也结了。”徐永和闻听此言,对张建国进行辱骂并质问,还掐住张的脖子,张建国即推挡徐永和。在场的他人将张、徐二人劝开。徐永和返回饮酒处,抄起两个空啤酒瓶,将酒瓶磕碎后寻找张建国。当张从酒楼走出时,徐永和嘴里说“扎死你”,即手持碎酒瓶向张面部扎去。张建国躲闪不及,被扎伤左颈、面部(疤痕长约12cm)。后张建国双手抱住徐永和的腰部将徐摔倒在地,致使徐被自持的碎酒瓶刺伤左下肢动脉、静脉,造成失血性休克而死亡。法院认定张建国构成正当防卫,并根据《刑法》第20条第1款宣告其无罪。该案中,被害人手持碎酒瓶先行攻击被告人的面部,后者采取的防卫行为是用双手抱住对方的腰部将其摔倒在地,其防卫行为的强度明显低于对方的侵害强度。只要将考察的重心放在防卫的行为本身,并立足于行为时的一般人标准,便可轻易得出被告人的防卫行为没有超出“防卫限度”的结论,不存在争论的余地。
其二,在防卫行为本身的强度超出不法侵害的强度,但从行为时的一般人标准来判断,该防卫行为系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时,仍不能认为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换言之,根据防卫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境,从一般人的观念来看,并不存在选择更为轻缓的防卫手段的可能,或者虽存在选择其他较为轻缓的防卫手段的可能,但选择此类手段会使防卫人陷入危险境地的,仍属于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情形,不存在构成防卫过当的余地。
以李明故意伤害案为例。〔6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刑事审判参考》(第55期),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页13以下。被告人李明与其同事王海毅、张斌、孙承儒等人在某迪厅娱乐时,因琐事而与王宗伟等人发生轻微冲突。李明供称其感觉对方怀有敌意,为防身,遂从住处取尖刀一把回到迪厅。其间王宗伟打电话叫来张艳龙、董明军等三人帮其报复对方。在李明取刀返回迪厅后,王宗伟向张艳龙指认李明,并指使张艳龙等人在过街天桥下伺机报复李明。当日凌晨1时许,李明、王海毅、张斌、孙承儒等人途经过街天桥时,张艳龙、董明军等人即持棍对李明等人进行殴打。孙承儒先被打倒,李明、王海毅、张斌进行反击,期间,李明持尖刀刺中张艳龙胸部、腿部数刀。张艳龙因伤及肺脏、心脏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孙承儒所受损伤经鉴定为轻伤。一审判决认定李明的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李明有期徒刑十五年;二审判决认定李明具有防卫意识,但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以故意伤害罪改判其有期徒刑五年。
就本案而言,因不法侵害方采取的是持棍殴打的方式,李明持尖刀予以反击,在防卫强度上的确高于对方的侵害强度。不过,立足于行为时的一般人标准,依据当时的情境进行整体的判断,应当认为李明的行为成立正当防卫,而非防卫过当。一则,来自张艳龙这一方的不法侵害并非微不足道,孙承儒被殴打至轻伤的事实可证明这一点。二则,李明拿出随身携带的尖刀进行反击,明显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在当时的具体情境之下,并不存在采取其他较为轻缓的防卫措施来制止不法侵害的可能。其他的防卫措施,无外乎两种:一是李明放弃使用尖刀,赤手空拳与持棍的对方相博斗;二是李明可使用尖刀反击,但应避开对方的要害部位。问题在于,事发当时为凌晨1时许,不法侵害方又事先有备而来持棍守候在现场,在李明这一方突然遭到对方持棍攻击,且己方已有1人被打倒在地的情况下,期待李明放弃使用随身携带的尖刀,或在使用时避开对方要害部位,不仅不现实,也无法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或者至少是会使李明及其同事身陷更为危险的境地。三则,当时双方人员基本相等,不法侵害方是持棍进行攻击,而李明是使用尖刀予以防卫,从双方所使用的器具与行为强度来看,并不显得过于悬殊。基于此,理应认为,尽管李明的防卫强度大于对方的侵害强度,且造成一人死亡,但鉴于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并不存在使用节制手段进行防卫的现实可能,故其行为对于制止不法侵害而言构成必需。即使其行为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也不能影响正当防卫的成立。因而,一审判决完全否定李明的防卫意识固然有些荒唐,二审法院认定李明构成防卫过当的结论也难言妥当。
其三,在涉及假想防卫是否过当的判断时,应遵循相同的标准来处理。
一般的假想防卫要么成立过失犯罪要么构成意外事件,而假想防卫过当有可能成立故意犯罪。因而,在假想防卫的场合,有时也会需要判断是否过当的问题。与防卫过当的判断相同,假想防卫过当的考察重心也应放在行为环节,立足于行为时的一般人标准,以对行为限度进行合理的把握。
以王长友过失致人死亡案为例。〔67〕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见前注〔11〕,页9以下。某晚,被告人王长友一家三口入睡后,忽听见有人在屋外喊叫王与其妻的名字。王长友便到外屋查看,见一人已将外屋窗户的塑料布扯掉一角,正从玻璃缺口处伸进手开门闩。王即用拳头打那人的手一下,该人急抽回手并跑走。王长友出屋追赶未及,亦未认出是何人,即回屋带上一把自制的木柄尖刀,与其妻一道,锁上门后(此时其十岁的儿子仍在屋里睡觉),同去村书记吴俊杰家告知此事,又到村委会打电话报警。当王与其妻报警后急忙返回时,发现自家窗前处有俩人影,此二人系本村村民何长明、齐满顺来王家串门,见房门上锁正欲离去。王长友未能认出何、齐二人,误以为是刚才欲非法侵人其住宅之人,又见二人向其走来,疑为要袭击他,随即用手中的尖刀刺向走在前面的齐满顺的胸部,致齐因失血性休克而当场死亡。何长明见状上前抱住王,并说:“我是何长明!”王长友闻声停住,方知出错。一审认定王长友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审宣判后,检察机关以“被告人的行为是故意伤害犯罪,原判定罪量刑不当”为由提出抗诉。二审法院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对于本案,两审法院均按一般的假想防卫来处理,判决结论也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庭的认可。但该案判决与裁判理由的解说,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即被告人的假想防卫行为是否存在过当的问题。被告人对不法侵害存在误认当无疑问,且鉴于此前刚发生他人非法侵入其住宅的事实,此种误认存在合理的根据。不过,立足于当时的情境,按行为时的一般人标准判断,即使被告人误认对方要袭击他,鉴于对方只是赤手空拳,并无症兆表明对方的袭击会对其人身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被告人直接用尖刀刺向被害人胸部,并非制止假想中的不法侵害所必需,应属“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基于此,被告人的行为并非普通的假想防卫,而应认定为假想防卫过当。由于被告人对不法侵害的误认具有合理性,难以认定其在此环节存在过失,故其刑事责任并非产生于对不法侵害的误认,而是取决于其实施的假想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也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并非来自于其假想的防卫,而来自过当行为。相应地,本案如何定性,要看被告人对“侵害”的强度是否存在误认,以及案发当时是否是因慌乱、紧张等因素而采用了过度的防卫手段。本文认为,被告人对“侵害”的强度不存在误认,但由于恐慌、紧张而过失地使用致命的手段,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较为妥当。
另一方面,在成立防卫过当的情况下,应当结合具体的构成要件,来判断行为人是否成立犯罪,是成立过失犯罪还是故意犯罪。
基于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的考虑,在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问题上采必需说,将使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有所扩张,这必然带来防卫过当成立范围相应限缩的后果。同时,防卫行为即使构成防卫过当,也不意味着随之便可得出防卫人构成犯罪的结论。由于防卫过当并非独立的罪名,故在追究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时,必须结合分则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来进行。倘若无法符合相关罪名的成立要件,则即使形式上具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条件,也可能得出无罪的结论。
在防卫过当的认定中,采取“行为→结果”的思考进路,意味着由防卫意识出发,去展开相应的判断。一般而言,有必要遵循以下三个步骤,来考虑对防卫过当刑事责任的追究。
首先,如果防卫过当是由于紧张、惊慌、恐惧等因素所引起,且就防卫人个体的情况而言,不具有期待其采取合理防卫措施的可能,则防卫人因缺乏罪责而难以认定为犯罪。
在我国实务中,只要肯定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由此造成重大损害,都一律地要按犯罪来处理。这样的做法并不合理。以李尚琴等故意伤害案为例。〔68〕参见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主编:《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页421-422。被告人李尚琴与被害人张铁柱离婚后仍住一起。张因不满法院对房屋产权的判决,多次在住处对被告人李素琴和李尚琴等人滋事,并曾因涉嫌放火烧该住处被采取强制措施。李素琴不得不经常报警寻求警方保护,案发前她总共报过22次警。案发当日凌晨2时许,张铁柱持柄铁锤击打睡在客厅的李尚琴的儿子孟宪宝,孟被击伤(经鉴定为轻伤)。在北屋睡觉的李尚琴、李素琴及李素琴之子张悦(15岁),冲出门与张铁柱博斗,抢下铁锤。后李尚琴看到张铁柱手中握有打火机且地上有汽油流淌,遂将打火机打掉在地,三人合力将张按倒在地上。适时,李尚琴见儿子头部大量流血,情急间持铁锤击打仍在地上挣扎的张铁柱后脑一下,并随即与张悦一同送孟宪宝去医院。此时张铁柱躺在地上已一动不动,李素琴持木柄铁锤继续击打张铁柱的腿部、膝盖、胳膊、手部、肩部等部位。张铁柱因失血性休克合并闭合性脑损伤而死亡。一审法院认为李尚琴构成防卫过当,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李尚琴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李素琴在被害人失去侵害能力时继续持械殴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本案中,被告人李尚琴在被害人已被按倒地在地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采取其他较为缓和的防卫措施,如将张铁柱用绳子捆绑起来等,故其持铁锤击打被害人后脑的行为并非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应认为其防卫行为已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过,从案发当时的情境与李尚琴个人的情况来看,要求其合理控制防卫强度,并无期待可能性。一则,当时地上有汽油流淌,而张铁柱手中的打火机也刚被打倒在地,万一张挣脱后放火,后果将不堪设想;二则,当时孟宪宝头部大量流血,作为母亲,李尚琴见此情景自然方寸大乱;三则,案发当时,被害人是在持铁锤行凶,并且,从此前多次报警的经历来看,被害人滋事的程度远非一般的家庭冲突可比。综合案发当时的情况,李尚琴处于极端惊恐、慌乱、焦急与紧张的状态中,要求其合理控制防卫行为的强度可谓强人所难。基于此,对李尚琴防卫过当的行为,理应以缺乏罪责为由而得出不构成犯罪的结论,法院的判决有失妥当。
其次,在存在期待可能的防卫过当的场合,防卫意识作为主观的正当化因素,在多数情形下将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由于缺乏故意犯罪的行为无价值,故防卫过当一般应优先考虑成立过失犯罪。
当前实务中,对防卫过当一般都定以故意伤害罪。学界也有个别学者提出,防卫过当只能由故意(或限于间接故意)构成。〔69〕参见王政勋等,见前注〔59〕;黎宏,见前注〔13〕,页143。将防卫过当普遍地认定为故意犯的做法存在疑问。
其一,将防卫过当一般按故意犯罪定性,明显忽视了防卫意识的作用与地位。在防卫过当中,防卫人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发生,基于保护法益的意思而实施相关行为,这样的“有意性”并不符合《刑法》第14条的犯罪故意的定义。认为防卫过当一般成立故意犯的论者,往往是将防卫行为与过当行为进行割裂,认为防卫行为具有防卫意识,而过当行为并不涉及防卫意识的问题。但实际上,在防卫过当中,防卫行为与过当行为是合为一体的,二者是一个整体的行为。立足于防卫意识,势必认为它的存在将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由此得出缺乏故意犯罪的行为无价值的结论。在否定成立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基础上,随之需要探讨的是,过当行为是否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论者因脱离具体的构成要件来评价不法,将本已剔除的“有意性”因素,又重新纳入评价的范围,由此不当地得出防卫过当成立故意犯的结论。只要结合具体的构成要件来展开对不法的评价,则此时分明只涉及过失犯罪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根本不牵涉故意的认定。
其二,将防卫过当一般按过失犯罪来处理,能避免违反量刑的基本原理,并遏制量刑失衡的问题。实务中,在对防卫过当按故意伤害罪定性时,往往援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通过减轻处罚来实现轻刑化的效果,最终的量刑低于七年有期徒刑。这样的做法是以违背量刑基本原理为代价。根据一般的量刑原理,减轻处罚只允许在既有法定刑的基础上降一格处理。比如,在致人重伤或死亡时,按故意伤害罪来判处,法定刑幅度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如果适用减轻处罚的规定,则理应在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来量刑。此外,由于防卫过当仅限于致人重伤与死亡的情形,如果动辄按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来定,鉴于其宽泛的法定刑幅度,而量刑的自由裁量权又掌握在具体的法官手中,这势必加剧量刑上的不均衡现象。反之,将防卫过当一般认定为过失犯罪,在过失犯罪的法定刑幅度内来量刑,有利于遏制量刑畸轻畸重的现象。
其三,将防卫过当一般按过失犯罪来处理,有助于使其与假想防卫之间的法秩序评价保持平衡。如果将防卫过当普遍当作故意犯罪,而假想防卫则至多按过失犯罪来处理,势必导致法秩序评价上的内在矛盾。以不法侵害作为防卫对象的防卫过当,竟然在一般意义上较根本不存在侵害的假想防卫,成立性质上更为严重的犯罪,这未免有些匪夷所思。毕竟,防卫过当中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防卫人处于“正”的一方;而假想防卫中所谓的“侵害”子虚乌有,假想防卫人自始便属于“不正”的一方。无论如何,故意伤害罪是比过失致人重伤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要严重得多的罪名,考虑到罪名本身所具有的污名化效果,将防卫过当普遍地当作故意伤害罪来处理的做法难说妥当。
其四,将防卫过当一般按过失犯罪来处理,在刑事政策上具有合理性。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而言,将防卫过当定性为性质严重的故意犯罪,必然使公民在行使自我保护的权利或见义勇为时束手束脚。在当下,人们在他人遭受不法侵害的场合经常冷漠以对,这多少也与刑法上对正当防卫限定得过严有关。为避免不当地限制公民的防卫权,更有效地保护法益,除放宽防卫限度的要求外,降低对防卫过当在刑法上的不法评价实有必要。有论者担心,如果防卫过当只成立过失犯,会使防卫过当行为得到两次优遇。〔70〕参见黎宏,见前注〔13〕,页143。这样的担心有些多余。现行立法本就鼓励人们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更何况,就我国而言,谁会认为防卫权是行使得太多太滥而非太少太不充分?此外,同一论者在论及假想防卫过当时,明确承认对不法侵害与侵害程度同时存在误认的假想防卫过当,可在成立过失犯罪的同时,适用第20条第2款有关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规定,只是其处罚必须高于通常的假想防卫所成立的过失犯。〔71〕参见黎宏:“论假想防卫过当”,《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倘若假想防卫过当可以享受两次优遇,为什么防卫过当反而就不能呢?
最后,在蓄意滥用权利的场合,对防卫过当可按故意犯罪来处理。
防卫过当有成立故意犯罪的可能,但其成立范围需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有在蓄意滥用权利的场合,才能考虑定以故意犯罪。比如,行为人为保护价值较小的法益,而在并非处于特别惊恐、慌乱或紧张的状态之下,蓄意地适用重度的暴力造成他人重伤或死亡的,可按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来处理。微财杀人或重伤他人之所以被认为属于权利滥用的类型,便在于,“在防卫只是保护微小的价值时,自我保护的利益与侵害人的危害行为相比经历急剧的降低。同时,法确证利益也要被否定,因为法秩序不可能为防卫价值微小的利益或针对微不足道的侵害,而允许以侵害人的实质性损害为代价。”〔72〕Jescheck/Weigend(Fn.24),S.348.在对公民行使正当防卫权表现出宽容态度的同时,对蓄意的权利滥用按故意犯罪来定处,合乎刑事政策的需要。
需要指出,为使对防卫过当的处罚与对假想防卫过当的处罚之间保持平衡,有必要纠正实务中对假想防卫与假想防卫过当不予区分的做法。对于假想防卫过当,不应一概地按过失犯罪来处理。假想防卫过当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行为人不仅误认不法侵害的存在,也对“侵害”的强度产生误认,该种情形仍按过失犯罪处理。第二种是行为人仅误认不法侵害的存在,对“侵害”的强度则没有误认。在后种情形下,如果行为人并非由于惊恐、慌乱或紧张等因素不当地提升防卫强度,而是蓄意采用明显超过限度的防卫措施,则对行为人理应按故意犯罪来处理。将假想防卫过当区别于一般的假想防卫,并认为前者存在构成故意犯罪的余地,有助于避免对防卫过当与假想防卫过当在法秩序评价上的失衡。
(责任编辑:江 溯)
In the Chinese judicial practice,when dealing with the cases of justifiable defense,people get used to setting a very harsh standard on the requirement of defense limit,and meanwhile a conduct of defense excess is often punished as intentional crime.It is a product of the focusing-on-result position, while the theory of Erfolgsunrecht(result-oriented wrongdoing),especially its logical way of thinking of“consequence→conduct”,provides a strong academic support for such a practice.In order to correct this practice,we should trace back to the problem of justifiable grounds for self-defense and defense for other people.Their justifiable ground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safeguarding individual rights and Rechtsbewährung(legal order protection),rather than on the idea of legal-goods evaluation.From this presupposition,the terms“obviously beyond a necessary limit”and“causing serious harm”in Article 20 Paragraph 2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should be interpreted to be two independent requirements for defense excess.The form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limit on the defensive conduct itself,and the latter is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harmful consequence.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defensive conduct itself is“obviously beyond a necessary limit”,an ex ante test should be adopted on the basis of a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case of defense excess,once the defendant meets the requirement of culpability,people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consider it to constitute a negligent crime;only in the situation of purposely abusing defensive rights,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f an intentional crime.
Defense Excess;Erfolgsunrecht(result-oriented wrongdoing);Justifiable Defense; Justifiable Grounds;Legal-goods Evaluation;Handlungsunrecht(conduct-oriented wrongdoing)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刑事政策与刑法理论的建构研究”(11CFX06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同时受日本名城大学研究经费的资助。
——以明某某案为例